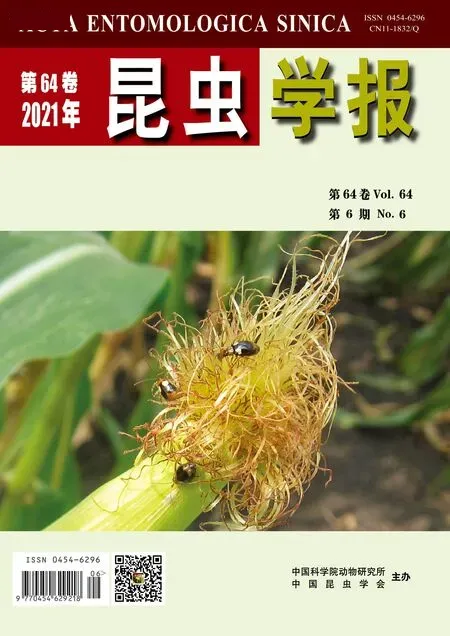有瓣蝇类分类、系统发育及演化
2021-12-26闫利平裴文娅
闫利平, 裴文娅, 张 东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北京 100083)
有瓣蝇类(Calyptratae)隶属于昆虫纲(Insecta)四大超适应辐射类群之一的双翅目(Diptera)(范滋德, 1992; 薛万琦和赵建铭, 1996a, 1996b)。目前已知23 000余种,约占双翅目已知物种多样性的20%,是有缝组(Schizophora)(双翅目:环裂亚目) 中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类群之一(Papeetal., 2011);分布地遍及南极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Kuttyetal., 2010);且生物学习性极为多样,以幼虫阶段尤为显著,不仅涵盖了捕食性、植食性、腐生性、寄生性、盗猎寄生性等昆虫纲全部常见的生物学习性类型,还包含专性寄生于哺乳动物皮下、颅腔或消化道的昆虫纲中唯一的哺乳动物专性内寄生类群——狂蝇科(Oestridae)(Zumpt, 1965),其在维系生态系统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媒介、法医、传粉和天敌昆虫学研究领域的热点类群。
相比其他双翅目昆虫,有瓣蝇类已知的化石标本极少(Evenhuis, 2014),最早的有瓣蝇类化石采自波罗的海新生代岩层,仅为花蝇科和寄蝇科各1块琥珀标本(Michelsen, 2000; von Tschirnhaus and Hoffeins, 2009),将有瓣蝇类出现的时间推进到了始新世(Eocene,约40 mya)。Wiegmann等(2003, 2011)以及Cerretti等(2017)先后基于分子钟假说推断出有瓣蝇类起源于约80-41 mya,是双翅目之树中“年轻”的分支,其演化历史很短,具有极高的形态及生物学多样性,是探索还原生命快速适应演化历史的模式类群(Kuttyetal., 2010; Wiegmannetal., 2011)。
以Carl von Linné (1707-1778), Johann Wilhelm Meigen (1764-1845), 何琦(1903-1970), Willi Hennig (1913-1976), 以及范滋德(1923-)等著名双翅目学家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先后对有瓣蝇类开展过不同层面的研究。但由于其超强的适应辐射和演化能力,该类群的系统发育关系及演化历史研究较为复杂,尤以狂蝇总科(Oestroidea)最为典型。本文以狂蝇总科为重点,对有瓣蝇类亚科级及以上阶元水平的分类概况、系统发育关系及演化历史进行综述。
1 有瓣蝇类总科分类及系统发育关系
Robineau-Desvoidy最先以“具有发达的下腋瓣”这一特征建立了有瓣蝇类(McAlpine, 1989)并获得了广泛支持(Hackman and Väisänen, 1985; McAlpine, 1989; Michelsen, 1991),有瓣蝇类的共有衍征也在众多支序系统学研究中得到了扩充和丰富(Hennig, 1958; 范滋德, 1997; Lambkinetal., 2013)。McAlpine (1989)根据成虫腹板愈合程度及下侧片是否具鬃列等特征将有瓣蝇类分为3个总科:虱蝇总科(Hippoboscoidea)、蝇总科(Muscoidea) [现已证实为多系,因此也称家蝇组(muscoid grade),详见下文]和狂蝇总科(Oestroidea)。这一分类体系得到了业内学者的广泛认可,如Yeates和Wiegmann (1999), Nirmala等(2001), Kutty等(2008, 2010, 2019), Wiegmann等(2011), Lambkin等(2013), Junqueira等(2016), Zhang等(2016), Cerretti等(2017), Wiegmann和Yeates (2017), 以及Stireman等(2019)。
几十年来,大量学者从形态学或分子生物学方向着手,分别对有瓣蝇类科、亚科以及属级的系统发育关系开展了研究,学界对3个总科间的系统关系也由长期的分歧不断逐渐达成了一致。McAlpine (1989)认为单系的蝇总科和狂蝇总科为姐妹群;Nirmala等(2001)的研究结果显示单系的蝇总科和多系的狂蝇总科亲缘较近;其他基于支序系统学的研究支持狂蝇总科与多系的蝇总科聚为一支,并与单系的虱蝇总科形成姐妹群(Hennig, 1976; McAlpine, 1989)。近年来的分子系统学研究越来越倾向于支持最后一种假设(Kuttyetal., 2008, 2010; Wiegmannetal., 2011; Zhangetal., 2016),该假设也得到了最新的基于转录组数据的系统发育研究的支持(Kuttyetal., 2019; Yanetal., 2020)。
2 有瓣蝇类总科下分类、系统发育关系及演化历史
2.1 虱蝇总科(Hippoboscoidea)
虱蝇总科最早是和有瓣蝇类同等地位的分类单元,与有瓣蝇类和无瓣蝇类共同构成了有缝组,Becher曾因其幼虫在母体内发育、产出后即化蛹而将其命名为蛹蝇类(Pupipara)(McAlpine, 1989),现在已被普遍接受为隶属于有瓣蝇类(Hennig, 1941, 1952, 1965, 1971, 1973; Griffiths, 1972; McAlpine, 1989)。虱蝇总科已知807种(Papeetal., 2011),分为舌蝇科(Glossinidae)、虱蝇科(Hippoboscidae)、蝠蝇科(Streblidae)和蛛蝇科(Nycteribiidae)(Hennig, 1973; McAlpine, 1989; Petersenetal., 2007)。由于蝠蝇的单系性未得到支持,因此也有学者将蝠蝇科、蛛蝇科并入虱蝇科(Papeetal., 2011)。舌蝇科物种也称采采蝇(tsetse fly),仅分布于非洲界(Afrotropical Realm),成虫以吸食脊椎动物血液为生并传播造成人类昏睡症的锥虫病,因此备受媒介生物学者的关注(Brunetal., 2010)。该总科其余类群成虫均具有高度特化的外寄生习性。虱蝇科、蝠蝇科和蛛蝇科均为广布类群,目前仅南极洲未有相关分布记录。成虫均依附寄主体表,以吸食血液为生。虱蝇科寄主为偶蹄类、食肉类和鸟类等脊椎动物;蝠蝇科和蛛蝇科以翼手类动物为寄主吸食血液——因此这两个科也被统称为蝠蝇,成虫几乎不离开寄主。与这种特殊的生活史相适应,虱蝇总科的昆虫在形态学和生理学上都表现出了大量特殊的适应性,如成虫具有极度特化适合吸血的口器,采用腺养胎生(adenotrophic viviparity) (特指虱蝇总科昆虫,幼虫在母体内孵化后并不马上产出,而是仍寄居于母体的阴道膨大而成的“子宫”内,由母体的附腺供给养分,直至幼体接近化蛹时才产出,刚产出的幼虫即在母体外化蛹)的生殖方式以缩短幼虫期(Meieretal., 1999)。
近30年来先后有学者利用形态学或DNA数据在不同分类阶元水平对虱蝇总科的系统发育关系开展了研究,如McAlpine (1989)、Yeates和Wiegmann (1999)、Nirmala等(2001)。虱蝇总科的单系性在形态学(Griffiths, 1972; Hennig, 1973)以及分子系统学(Nirmalaetal., 2001; Dittmaretal., 2006; Petersenetal., 2007)方面都得到了支持。目前,除蝠蝇科以外,其余3个科的单系性都已得到了很好的验证(Bequaert, 1953; Griffiths, 1972; Hennig, 1973; Maa and Peterson, 1987; McAlpine, 1989; Nirmalaetal., 2001; Dittmaretal., 2006; Petersenetal., 2007);形态学(Hennig, 1973; McAlpine, 1989)和分子系统学(Nirmalaetal., 2001; Dittmaretal., 2006; Petersenetal., 2007)研究都支持寄生于蝙蝠皮外的两个科(蛛蝇科和蝠蝇科)形成一支;舌蝇科和虱蝇科的系统地位尚不十分明确,一些研究支持它们为姐妹群关系(Dittmaretal., 2006),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舌蝇科与虱蝇总科其余类群为姐妹群关系(McAlpine, 1989; Petersenetal., 2007)。
虱蝇总科昆虫是极为特化的吸血蝇类(Dittmaretal., 2015),演化出了特殊的口器、不同程度退化的翅、腺养胎生的生殖策略等适应性特征,但该类群昆虫的生物学起源仍不明晰(Dittmaretal., 2015)。根据少量的虱蝇总科化石信息,结合关键的寄主演化事件推测,虱蝇总科的起源时间不早于中新世(Miocene)(23-5 mya)(Dittmaretal., 2015)。Dittmar等(2006, 2015)、Petersen 等(2007)先后从寄生习性演变、寄主选择、地理起源等多个角度诠释了该类群的演化历史。虱蝇总科昆虫单一起源于类似于舌蝇的营自由生活的吸血蝇类,在形成密切依附寄主生活的真正外寄生习性后,又至少经历了两次由哺乳类向鸟类的寄主转移事件(Petersenetal., 2007)。相比之下,寄主专一性弱的舌蝇幼虫可自主钻入土壤化蛹,而寄主专一性强的蝙蝠寄生蝇(蝠蝇科和蛛蝇科)幼虫完全由母体粘附在蝙蝠粪上,表明随着寄主专一性的增强,虱蝇总科昆虫幼虫的自主活动能力逐渐降低(Petersenetal., 2007)。因此,对于蝠蝇科和蛛蝇科昆虫,寄主的穴居性和洞穴中积累的蝙蝠粪很可能是促使其寄生于蝙蝠的关键因素(Jobling, 1954)。蝙蝠寄生蝇有两个起源中心,分别为新热带界(Neotropical Realm)和东洋界(Oriental Realm):其地理演化路径追随并相对滞后于其各自翼手类寄主的冈瓦纳大陆和劳亚大陆起源历史(Jobling, 1954; Dick and Patterson, 2006; Dittmaretal., 2006, 2015)。
2.2 蝇总科(Muscoidea)
基于形态学特征,McAlpine (1989)认为蝇总科是单系,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类群为多系,因而又被称为家蝇组(Kuttyetal., 2010, 2019)。蝇总科物种多样性十分丰富,目前约有8 000个已知物种(Papeetal., 2011),分为厕蝇科(Fanniidae)、蝇科(Muscidae)、粪蝇科(Scathophagidae)和花蝇科(Anthomyiidae)(Hennig, 1973; McAlpine, 1989)。厕蝇科主要分布于全北界(Holarctic Realm)和新热带界(Neotropical Realm);其幼虫取食降解的有机质(粪便或动物尸体等),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分解者的角色,少数物种可造成人畜蝇蛆病(Kuttyetal., 2008)。蝇科昆虫广泛分布于南极洲以外的其他大陆;在幼虫发育阶段,其龄期数量不一,且幼虫生物学习性分化极为明显,一般为粪食性,部分为腐食性,少数为捕食性、吸血性和植食性(取食花粉和花蜜)(范滋德, 2008; Kuttyetal., 2008)。粪蝇科仅南极洲和澳洲无分布记录,其分布地集中于全北界(Bernasconietal., 2000);幼虫以不同类型的动物粪便或腐殖质(如腐烂的海藻)为食,或取食植物的叶、茎、未成熟的花头等,少数物种捕食小型无脊椎动物或石蛾卵块(Bernasconietal., 2000; Kuttyetal., 2008)。花蝇科昆虫主要分布于全北界,在副北极地区(Subarctic Realm)和山区也较常见,主要分布于林地或潮湿生境;其幼虫大多为植食性,也有少数为盗猎寄生性、寄生性或粪食性(Kuttyetal., 2008; Polidorietal., 2015)。
随着形态学特征的大量挖掘和分子系统学研究的开展,蝇总科的系统关系逐渐得以揭示。Hennig (1973)和McAlpine (1989)曾根据雄性肛门位于肛尾叶之上、雄性第10腹板形成杆状突、雌性第7气孔位于第6背板上等形态特征认为该类群为单系,并认为其与狂蝇总科形成姐妹群(McAlpine, 1989)。但Michelsen (1991)认为上述特征也是狂蝇总科的祖征,因而将蝇总科定义为除虱蝇总科和狂蝇总科之外的有瓣蝇类。此外,Lambkin等(2013)选用双翅目42个物种,基于来自幼虫、蛹和成虫等不同发育阶段的371个形态特征构建了系统发育关系,研究结果支持蝇总科为多系群;除厕蝇科未被包含于研究中以外,各科间关系为(粪蝇科+(花蝇科+(蝇科+狂蝇总科)))。“蝇总科为多系”这一假设近年来也被分子系统学研究所证实。一方面,Kutty等(2008, 2010), Wiegmann等(2011)和Cerretti等(2017)先后联合多个线粒体基因和核基因片段构建了有瓣蝇类或双翅目的系统发育关系,蝇总科均为多系,其中(花蝇科+粪蝇科)与狂蝇总科构成姐妹群。另一方面,线粒体基因组逐渐被引入有瓣蝇类系统发育关系研究,虽有少数研究利用线粒体基因组数据得到了单系的蝇总科(Dingetal., 2015),但未获得高置信度的系统关系;其后的研究则支持前述多系的蝇总科,即(花蝇科+粪蝇科)与狂蝇总科形成姐妹群关系(Junqueiraetal., 2016; Zhangetal., 2016),这一关系也得到了基于转录组的系统发育研究的支持(Kuttyetal., 2019; Yanetal., 2020)。在科级阶元水平,无论基于形态学还是分子数据的研究中,仅有花蝇科的单系性尚未得到广泛认可。花蝇科在分类学研究领域被认为是极其困难的双翅目类群,可信赖的基于雌性特征的鉴定还处于属级水平(Michelsen, 2000),导致该类群的系统发育研究基础十分薄弱且存在极大争议:形态学证据支持花蝇科为单系群(Hennig, 1976; Michelsen, 1991, 1996),分子系统学研究却认为其为并系群(Kuttyetal., 2007, 2008)。
蝇总科昆虫幼虫的生物学习性十分多样和复杂(Kuttyetal., 2008),其中尤以蝇科和粪蝇科最为突出。Kutty等(2007, 2014)先后以粪蝇科和蝇科为目标类群,探讨了其生物学习性的演化历史,发现粪蝇科祖先类群的幼虫取食植物叶片,其后经历过两次由植食性向腐食性、一次由植食性向捕食性、一次由腐食性向捕食性的食性转变(Kuttyetal., 2007);蝇科祖先类群幼虫为腐食性,其后经历了多次演变,出现了更为特化的嗜尸性、植食性和捕食性,且捕食性的起源还伴随着幼虫发育龄期的减少,即由祖先的3个龄期减少至2个龄期,最终成为1个龄期(Kuttyetal., 2014)。
2.3 狂蝇总科(Oestroidea)
从科和family group (Griffiths, 1982; Pape, 1992)到如今被认可的总科(Hennig, 1958; Pape, 1986; McAlpine, 1989; Rognes, 1997),狂蝇总科曾被列为不同的阶元,并先后被称为丽蝇总科(Calliphoroidea)(Hennig, 1958)、寄蝇科(Griffiths, 1972)、寄蝇总科(Tachinoidea)(Rohdendorf, 1977; Pape, 1986)、狂蝇总科(McAlpine, 1989)或Tachinidae family group (Griffiths, 1982; Pape, 1992)。狂蝇总科已知约15 000种(Papeetal., 2011)。该类群昆虫生物学习性极为多样,不仅有常见的粪食性、嗜尸性、拟寄生性,还包括盗猎寄生性和寄主专一性极强的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专性寄生性(Zumpt, 1965; Colwelletal., 2006b; Kuttyetal., 2010) (详见下文总结),在医学、兽医学、法医昆虫学以及保护生物学领域都是不容忽视的类群。
随着双翅目支序系统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形态学特征支持狂蝇总科这个分支的划分(Griffiths, 1982; McAlpine, 1989; Pape, 1992; Rognes, 1997)。Lambkin等(2013)不仅基于支序系统学进一步验证了狂蝇总科的单系性,还发现了更多支持狂蝇总科单系的同源特征:狂蝇总科下前侧片鬃序为2+1,上后侧片具鬃,下侧片具垂直鬃列,后气门厣后缘具缨毛,阳体中腹骨化。近年来,许多分子系统学研究也证实了狂蝇总科的单系性(Kuttyetal., 2010, 2019; Wiegmannetal., 2011; Marinhoetal., 2012; Singh and Wells, 2013; Zhangetal., 2016; Yanetal., 2020),但因物种多样性高、关键类群分类系统仍存争议、样品采集难度大等原因,狂蝇总科的科级分类和系统关系等关键问题多年来一直悬而未决,严重制约了有瓣蝇类系统发育和演化历史的研究。
2.3.1狂蝇总科系统分类及各科概要:狂蝇总科的科级分类体系十分复杂,一般被分为6~10个科不等。本文采用科级分类单元数量最多的将狂蝇总科分为10个科的分类系统,以对该类群进行详述。
2.3.1.1丽蝇科(Calliphoridae Brauer and Bergenstamm, 1889):丽蝇科已知1 500余种(Papeetal., 2011),广布于世界各地(Kuttyetal., 2010)。取食范围极广,包括脊椎动物[如红颜金蝇Chrysomyarufifacies幼虫以脊椎动物尸体为食,部分阜蝇亚科(Phumosiinae)幼虫专性寄生树蛙卵(Rognes, 2015)]、无脊椎动物[如部分迷蝇亚科(Ameniinae)幼虫取食蜗牛(Crosskey, 1965)、孟蝇亚科(Bengaliinae)幼虫寄生白蚁(Szeetal., 2008)],另有专门吸食脊椎动物血液的类群,如原丽蝇Protocalliphoraspp.吸食雏鸟血液(Bennett and Whitworth, 1991)、燥蝇属Auchmeromyiaspp.分布于非洲并吸食疣猪、鬣狗等动物血液(Capinera, 2008)等。
丽蝇科亚科的分类先后经历过多次变更(范滋德, 1997)。Hennig (1973)首次基于支序系统学提出了5个亚科的分类体系。在此基础上,Rognes (1991)又提出了6个亚科;随后,Norris (1999)以澳大利亚特有的Aphyssura新建了1个亚科(Aphyssurinae)。虽然鼻蝇亚科(Rhiniinae)、墨丽蝇亚科(Mesembrinellinae)、粉蝇亚科(Polleniinae)先后提升为科(Guimarães, 1977; Evenhuisetal., 2008; Cerrettietal., 2019),丽蝇科的亚科数量依然达10个之多。
丽蝇的演化历史一直吸引着大量学者的关注,然而由于形态和生物学习性分化非常多样,其系统分类一直存在争议,各类群间系统关系也无定论,使得该类群成为了有瓣蝇类系统发育研究中最大的难题(Rognes, 1991; Kuttyetal., 2010, 2019)。有学者认为丽蝇科为单系(Lehrer, 1970; Rognes, 1986, 1991; McAlpine, 1989; Pape, 1992),但缺少有效的证据支撑(Hennig, 1973; Griffiths, 1982),也有学者基于形态学(Rognes, 1997)或分子证据(Kuttyetal., 2010, 2019)认为丽蝇科是多系群。
2.3.1.2墨丽蝇科(Mesembrinellidae Shannon, 1926):墨丽蝇科已知仅36种(Marinhoetal., 2017),仅分布于新热带界潮湿的原生林(Guimarães, 1977),因此也被认为是生态指示类群(Cabrinietal., 2013)。成虫一般取食腐烂的动物组织或果实,幼虫生物学习性未知。
该类群原是隶属于丽蝇科的一个亚科(Hennig, 1973; Pape, 1992; Rognes, 1997)。但相比于丽蝇科其他类群,其独特的生物学特征(Hall, 1948; Crosskey, 1965)促使学界将其提升为科(Guimarães, 1977)。其科级阶元地位又分别被形态学(Rognes, 1997)和分子系统学研究(Kuttyetal., 2010, 2019; Marinhoetal., 2012; Singh and Wells, 2013; Winkleretal., 2015)所印证。墨丽蝇亚科在有瓣蝇类中的系统地位尚存在争议。Marinho等(2017)提出墨丽蝇科与麻蝇科互为姐妹群,但支持率不高。Cerretti等(2017)联合分子和形态学数据,扩增了取样,得到墨丽蝇科与乌鲁鲁蝇科(Ulurumyiidae)亲缘较近的假说,这一假说也得到了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研究的支持(Kuttyetal., 2019)。
2.3.1.3须蝇科(Mystacinobiidae Holloway, 1976):须蝇科目前已知仅1属1种,即新西兰蝠蝇Mystacinobiazelandica。该种仅发现于新西兰短尾蝙蝠巢内,成虫无翅,眼退化,一般附着于寄主蝙蝠的皮毛因而爪极度特化。相比于虱蝇总科的蝠蝇,须蝇科昆虫仅取食蝙蝠粪并利用蝙蝠进行迁移。由于成虫形态极为特殊,学界对于须蝇科的系统地位一直存有争议,如Griffiths (1982)认为其隶属于丽蝇科,Rogness(1997)则认为其是狂蝇总科其他类群的姐妹群,而Cerretti等(2017)得出须蝇科与(花蝇科+粪蝇科)成为姐妹群。虽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但可以肯定的是,越来越多的形态学(Griffiths, 1982; McAlpine, 1989; Pape, 1992; Rognes, 1997)和分子系统学(Gleesonetal., 2000; Kuttyetal., 2010, 2019)证据都表明其应隶属于狂蝇总科。
2.3.1.4狂蝇科(Oestridae Leach, 1815):狂蝇科已知4亚科170余种(Papeetal., 2011),均为脊椎动物专性内寄生蝇类,其隐蔽而神秘的专性内寄生生物学习性引起了学界的长期关注(James, 1947; Zumpt, 1965; Grunin, 1969; Sabrosky, 1986; Hall and Smith, 1993; Guimarães and Papavero, 1999; Colwelletal., 2006b)。4个亚科在雌性产卵和幼虫寄生部位选择等生物学特征方面具有显著的分化(Zumpt, 1965; Colwell, 2006)。胃蝇亚科(Gasterophilinae)主要产卵于奇蹄类等大型哺乳动物的口、颊、颈等特定位置,幼虫寄生于消化系统;狂蝇亚科(Oestrinae)是唯一的卵胎生类群,雌性成虫直接将1龄幼虫喷射入奇蹄类、偶蹄类等动物鼻腔内,并寄生于其鼻咽腔和颅腔中;皮蝇亚科(Hypodermatinae)主要产卵于啮齿类、偶蹄类等动物体表,幼虫经体内发育后最终寄生于寄主的真皮层下;疽蝇亚科(Cuterebrinae)产卵于啮齿类(偶见寄生于有袋类和灵长类)寄主活动频繁的生境中,幼虫主要寄生于真皮层下。狂蝇昆虫寄主专一性极高,在当前生物多样性急速降低的情况下,该类群面临着极大的随寄主灭绝的风险,如已随猛犸象灭绝的猛犸象胃蝇Cobboldiarussanovi(Grunin, 1973)。
Pape (2001, 2006)先后基于支序系统学对狂蝇科的系统发育关系开展了研究,研究证实了狂蝇科的单系性,且认为狂蝇科内各亚科亲缘关系为(疽蝇亚科+(胃蝇亚科+(狂蝇亚科+皮蝇亚科)))。但由于狂蝇科生活史过于隐秘,样品采集难度大,且已有样品多为数十年甚至约百年前采集的博物馆标本,难以获得分子数据,针对狂蝇总科或有瓣蝇类的系统发育研究多以1~2种常见狂蝇为代表(Kuttyetal., 2010; Wiegmannetal., 2011),近期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研究则获得了多系的狂蝇科(Buenaventuraetal., 2021)。
2.3.1.5粉蝇科(Polleniidae Brauer and Bergenstamm, 1889):粉蝇科已知仅8属147种,分布于新热带界以外的其他动物地理区(Gisondietal., 2020)。其成虫大多访花、为传粉昆虫;在已知生物学范畴内,其幼虫寄生蚯蚓,其他寄主仅有极少数记录(Cerrettietal., 2019)。
该类群原隶属于丽蝇科,近期被上升为科级阶元(Cerrettietal., 2019)。近年来基于分子数据的系统发育关系研究均支持其与寄蝇科形成姐妹群(Singh and Wells, 2013; Winkleretal., 2015; Zhangetal., 2016; Cerrettietal., 2017, 2019; Kuttyetal., 2019)。尽管粉蝇科的系统界定(Cerrettietal., 2019)和属级分类单元的厘定已非常明确(Gisondietal., 2020),目前对其内部系统发育关系和演化历史的研究仍有缺失。
2.3.1.6鼻蝇科(Rhiniidae Bauer and Bergenstamm, 1889):鼻蝇科已知约400种(Papeetal., 2011),仅分布于旧世界(Old World)气候温暖的地区,除Villeneuviellaspp.会导致蝇蛆病外,其他物种生活史均与白蚁或粪便相关,也有研究报道从直翅目昆虫卵块中培育出了鼻蝇(Ferrar, 1987; Rognes, 2002)。
该类群原隶属于丽蝇科,后被上升为科级阶元(Evenhuisetal., 2008),这一观点随后也得到了分子系统学研究的支持(Kuttyetal., 2010)。但学界对鼻蝇科的系统地位一直未能达成共识,Kutty等(2010)认为鼻蝇科与(寄蝇科+邻寄蝇科+丽蝇科)或(狂蝇科+寄蝇科+邻寄蝇科+丽蝇科)较近缘,Cerretti等(2017)与Kutty等(2019)得出鼻蝇科与丽蝇科中的孟蝇亚科形成姐妹群。
2.3.1.7邻寄蝇科(Rhinophoridae Robineau-Desvoidy, 1863):邻寄蝇科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但仅包含170余个已被描述的物种(Papeetal., 2011)。在已知生物学范畴内,它们均为鼠妇的内寄生虫(Thompson, 1934; Pape, 1998b; Cerrettietal., 2014),1龄和2龄幼虫以血淋巴为食,3龄幼虫则破坏组织并在被取食后的寄主体内化蛹。
该类群的单系性及其在狂蝇总科中的系统地位仍有争议。Cerretti等(2014)基于支序系统学研究得到了4个支持邻寄蝇科为单系的非同源近裔性状,但这些特征也存在于丽蝇科和寄蝇科的部分物种(Pape, 1986),意味着邻寄蝇科在成虫时期形态上没有明显的独征(Wood, 1987; Rognes, 1997; Pape and Arnaud, 2001)。目前仅有1龄幼虫的部分形态特征可作支持其单系的确切依据:尺蠖状或翻跟斗状运动;口钩背面具锯齿状结构;表皮包裹鳞片状棘刺;多数体节具小乳突;腹部末端具一对囊状叶突或可变的长囊泡(Bedding, 1973; Pape, 1986, 1992; Wood, 1987; Pape and Arnaud, 2001; Cerrettietal., 2014)。分子系统学研究也尚未能明确该类群的单系性及其系统地位(Kuttyetal., 2010; Wiegmannetal., 2011; Cerrettietal., 2017)。
2.3.1.8麻蝇科(Sarcophagidae Macquart, 1834):麻蝇科为世界广布类群,分布地遍及南极洲以外的全部大陆。已知3 000余种(Papeetal., 2011),多数物种幼虫为腐食性,取食哺乳动物尸体或粪便,也有一些类群营拟寄生或盗猎寄生生活(Pape, 1996)。其下分为3个亚科:蜂麻蝇亚科(Miltogramminae)、野蝇亚科(Paramacronychinae)和麻蝇亚科(Sarcophaginae)。蜂麻蝇亚科除少数取食动物尸体外,其余大多为膜翅目昆虫的盗猎寄生虫(Pape, 1996),且在形态学、行为学方面都表现出了对盗猎寄生习性的适应性特征。野蝇亚科昆虫通常拟寄生于无脊椎动物,或捕食无脊椎动物,仅污蝇属Wohlfahrtiaspp.少数物种可导致脊椎动物蝇蛆病。麻蝇亚科幼虫生活习性非常多样,包括专食脊椎动物粪便的粪食性(如Oxysarcodexiaspp.和Raviniaspp.),(拟)寄生于脊椎动物(如Lepidodexiaspp.)或无脊椎动物(如Blaesoxiphaspp.)并造成蝇蛆病的(广义)捕食性等(Pape, 1996)。
麻蝇科的单系性已被很多研究所证实并得到广泛接受(Pape, 1992, 1996)。根据形态学特征,蜂麻蝇亚科很可能是(野蝇亚科+麻蝇亚科)的姐妹群(Pape, 1992, 1998a),该假设得到了一些分子系统学研究的支持(Kuttyetal., 2010),但通过增加建树的分子标记和取样,更多的分子系统学研究倾向于支持麻蝇亚科与(蜂麻蝇亚科+野蝇亚科)形成姐妹群(Piwczyńskietal., 2017; Yanetal., 2017, 2020; Buenaventuraetal., 2020)。
2.3.1.9寄蝇科(Tachinidae Robineau-Desvoidy, 1830):寄蝇科已知约10 000种(Papeetal., 2011),该类群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是双翅目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科级分类单元之一。成虫形态高度多样,所有已知生活史的幼虫均为其他节肢动物体内的寄生虫,宿主通常是植食性昆虫,如鳞翅目、鞘翅目多食亚目以及半翅目昆虫(Stiremanetal., 2006),是农林害虫重要的天敌(Stiremanetal., 2006)。
发达的后小盾片、1龄幼虫缩小的口钩等特征均支持寄蝇科的单系性(Rognes, 1986; Wood, 1987; Pape, 1992; Tschorsnig and Richter, 1998)。分子系统学研究方面,虽然Kutty等(2010)得到了多系的寄蝇科,但Winkler等(2015)和Stireman等(2019)改变分子标记并增加取样后,均得到了单系的寄蝇科,各亚科系统关系为((长足寄蝇亚科Dexiinae+突颜寄蝇亚科Phasiinae)+(寄蝇亚科Tachininae+追寄蝇亚科Exoristinae)),并且都有很高的支持率。
2.3.1.10乌鲁鲁蝇科(Ulurumyiidae Michelsen and Pape, 2017):自1979年在澳大利亚南部被发现(Ferrar, 1979)以来,麦氏蝇(MaAlpine’s fly)在有瓣蝇类中的系统地位长期未能得到明确(Meieretal., 1999),直至2017年才被确立为独立的科(Michelsen and Pape, 2017),并被认为与单型的须蝇科聚为一支,再与麻蝇科成为姐妹群(Kuttyetal., 2010);而基于转录组的研究则表明,其与乌丽蝇科聚为一支并与狂蝇总科其他类群形成姐妹群(Kuttyetal., 2019)。有意思的是,乌鲁鲁蝇的自然生活史从未被记录过,目前仅在实验室内观察到其以牛粪为食(Kuttyetal., 2010),但牛却是在近代才随人类迁入澳大利亚,因此该类群的自然生活史仍是未解之谜。
2.3.2狂蝇总科内科级系统发育关系:在早期研究阶段,只有少数研究者对狂蝇总科的科级系统关系进行了支序系统学研究。Hennig (1976)认为狂蝇科是狂蝇总科所有其他类群的姐妹群,而Griffiths (1982)认为丽蝇科是狂蝇总科最早独立的分支。Rognes (1997)提出狂蝇科进入丽蝇科且与麻丽蝇亚科和孟蝇亚科两亚科较近。Roback (1951)认为狂蝇科和寄蝇科形成单系群,Pape (1992)则支持狂蝇科和丽蝇科构成单系。McAlpine (1989)的研究最为全面,他提出((丽蝇科+须蝇科)+麻蝇科)作为(狂蝇科+(邻寄蝇科+寄蝇科))的姐妹群。Pape (1992)研究了Tachinidae family group (不包括须蝇科)的系统发育关系,提出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假说:(邻寄蝇科+(狂蝇科+丽蝇科))作为(寄蝇科+麻蝇科)的姐妹群。其中,丽蝇科的单系性一直未被解决(Rognes, 1997; Kuttyetal., 2019),使得任何意在解决狂蝇总科(甚至有瓣蝇类)系统发育的研究需将丽蝇科各亚科的代表物种基本包括在内。取样困难成为丽蝇科和狂蝇总科分子系统学研究的瓶颈问题:Nirmala 等(2001)用来代表狂蝇总科的13个物种仅涵盖丽蝇科3个亚科,Gleeson等(2000)所用11种有瓣蝇类仅涵盖丽蝇科2个亚科,即使是近期的研究也在亚科覆盖度和系统发育分子标记选取上有所欠缺(Kuttyetal., 2010, 2019; Marinhoetal., 2012; Singh and Wells, 2013; Cerrettietal., 2017)。
2.3.3狂蝇总科演化历史:狂蝇总科昆虫只经历了短暂的演化历史(Wiegmannetal., 2011; Cerrettietal., 2017),但其生活史类型十分丰富,幼虫食物来源和取食习性都极为多样。与此相适应,狂蝇总科昆虫形态、生物学习性等方面的多样化在有瓣蝇类乃至双翅目中都非常显著,是研究昆虫生物学习性演化等进化生物学问题的理想类群。然而,囿于狂蝇总科有限的生活史信息记录,以及其尚未有效解决的系统发育关系,目前仅有少数研究对狂蝇总科部分类群的演化历史进行了探究。
麻蝇科是有瓣蝇类中分类系统最完善、生物学习性最多样、生物学信息记录最全面的科级分类单元,基于此,Yan等(2020)通过构建超树获取了涵盖麻蝇科超过80%属级分类单元的系统树,研究结果明确了麻蝇科及各亚科均起源于美洲界;其祖先类群以动物尸体为食,随着多样化进程的持续,捕食性、盗猎寄生性等更为特化的生活习性开始出现,其中蜂麻蝇的盗猎寄生习性很可能起源于幼虫具有钻地习性的尸食性蜂麻蝇类群,这种习性为盗猎寄生性蜂麻蝇进入地面下蜂巢、白蚁巢并以巢内食物为食提供了可能性。
Stireman等(2019)对系统分类学和生物学信息较为明确的寄蝇科开展过演化历史研究,认为寄蝇科的祖先寄主为鞘翅目昆虫,寄生于鳞翅目昆虫是其在物种多样化过程中的偶然事件。
狂蝇科是双翅目乃至昆虫纲中十分罕见的哺乳动物专性内寄生昆虫,这一习性被认为起源于外寄生性的丽蝇科昆虫,如寄生于哺乳动物的燥蝇属Auchmeromyia和寄生于鸟类的原丽蝇属Protocalliphora(Colwelletal., 2006a)。Pape (2006)从多个角度对狂蝇科的演化历史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并认为该类群在第三纪(Tertiary)早期起源并实现多样化,但狂蝇科的演化历史仍存在大量未解之谜。Yan等(2019)以胃蝇亚科为代表,首次对狂蝇演化历史进行了探讨,明确了胃蝇亚科的寄主转移路径,以及雌虫产卵、幼虫附着部位等生物学特征的演化历史。
3 小结与展望
有瓣蝇类是双翅目有缝组中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类群之一,其形态和生物学习性多样性极高,对理解双翅目成功适应辐射十分关键。近年来在国内外双翅目学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该类群的系统发育和演化历史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其高级阶元(总科)的系统关系已基本得到解决。但是,丽蝇科、花蝇科等科级分类单元系统界定尚不明确,且许多类群生物学信息严重匮乏,限制了对有瓣蝇类演化历史的探索。针对该研究现状,笔者认为未来重点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几点:
(1)增加取样,构建有瓣蝇类物种树。随着全球马氏网计划(Global Malaise Program)的兴起和开展,对双翅目昆虫开展大范围样品采集成为可能,这也为探究全球尺度下有瓣蝇类物种多样性、构建物种树(species tree)提供了巨大潜力。
(2)采用高新技术手段,开发形态特征。当下虽然处于系统发育基因组学(phylogenomics)时代,但形态学特征在系统发育及演化历史研究中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Giribet, 2015)。扫描电子显微镜、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等高分辨率显微成像技术的发展,为开发具有演化意义的形态学特征提供了基础,也将为有瓣蝇类演化历史研究提供新思路(Lietal., 2020)。
(3)明确有瓣蝇类起源时间、地点,及其多样的生物学习性的演化历史。明确有瓣蝇类的起源时间和地点是重现其演化历史的基础,未来应在增加关键类群取样的基础上,尝试推断该类群更加精确的起源时间和地点,以揭示其适应演化历史。
(4)关注特殊类群,开展深入的比较基因组学、形态学研究。有瓣蝇类中不仅包含丝光绿蝇等媒介昆虫,还有狂蝇、蝠蝇等耐低氧和强酸等的极为特化的蝇类,从比较基因组学、形态学层面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明确其适应机制,甚至为生物对极端环境耐受机制研究、抗腐蚀材料研发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