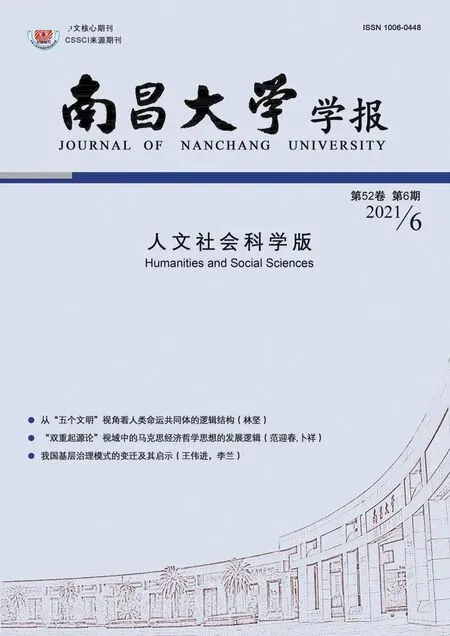安源工人歌谣与无产阶级共同体想象
2021-12-26廖美琳
廖 美 琳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的叙述,常见的描述流脉大致是:从1920年代后期的创造社和太阳社创作、1930年前后的革命浪漫派和左联创作、1930至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这一叙述线表明,纳入革命文学范畴的重要标准依然离不开对文学的传统定义。然而,随着革命文学研究逐渐被纳入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学视野,游离在文学正统之外的歌谣与革命相结合的研究,也开始浮出中国革命文学研究视野的地表。歌谣与中国革命/政治的结合,在20世纪20年代中共组织的工人运动中就已经开始,它在1930年代的苏区动员中蓬勃发展,直至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依然燎原。作为1920年代负有“小莫斯科”盛名的安源,其工人运动对歌谣的征用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文艺发展的流脉里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它不仅唱出了阶级情绪,凝聚了革命人心,而且为后续的中国革命提供了与地方文艺结合的宝贵经验。
然而,对安源工人歌谣的研究,学界迄今为止关注不多。已有的研究大部分散见于安源工人运动的史学研究著述。这类碎片式研究主要介绍安源工人运动在组织动员过程中借用了歌谣、戏剧等文艺形式,并以传统史学的视角评价安源工人歌谣“崇高的历史地位”和“开拓意义”。还有一类属于专题研究,考察安源工人歌咏的传统,以及安源工人歌谣如何受无产阶级思想浸润和安源地方戏曲小调的影响;近期的安源歌谣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6月在萍乡市举办的“安源精神学术研讨会”的部分成果,其中两篇论文集中探讨了安源工人歌谣:一篇对安源歌谣进行题材分类和音乐学层面的曲源考察;另一篇则以重返历史现场的方式,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探讨安源工人歌谣中的情感动员模式的生成与演变。
总体而言,现有的安源工人歌谣研究大部分从传统革命史和民间文艺层面简略述之,并未能有效打开安源歌谣更为开阔的文本空间,从而深入呈现其更为丰富的政治美学面向。诚然,安源工人歌谣与几乎同时出现的北大歌谣运动所搜集的作品有显著的差异——前者承载着明确的政治功能,后者则“既非音乐的,也非政治,它是文学的和学术的”[1](P131)。这一特质在传统革命史研究框架下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从纵向比较来看,与历史上为数甚少的煤矿歌谣相比,1920年代的安源歌谣携带着鲜明的无产阶级政治美学印记,尤其是革命动员视野中的共同体塑造,更是蕴含着独特的意义。然而这一面向目前并未受到研究界的足够关注。
1921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进入安源后,在安源工人中创办平民教育作为革命的突破口。从安源工人补习学校课本和小学国语课本可以看出,不少篇章的主题以鼓动工人团结为主。在一些工人的回忆录中,毛泽东、李立三等进驻安源的革命者,曾多次以“拳头”“水泥凝结石子”等描述为比喻,鼓动工人团结联合,以“推翻压迫阶级”。直到罢工成功后的工人歌谣,依然对共同体的塑造有着持续探索。这种共同体的塑造不仅有别于传统的自然共同体想象,也与近代大工业时期安源歌谣中以“物”资本为基础的虚假共同体叙述有本质区别。从这一历史阶段的安源歌谣进入,借助文本细读和史学分析的方法,梳理从传统到现代的安源歌谣共同体叙述流脉,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源工人运动时期的歌谣中涵纳的共同体想象,厘清革命文学对无产阶级共同体形成的推动作用。
一、自然共同体:安源煤矿传统歌谣的“田园风味”
据史料记载,江西萍乡的安源采煤业“最古者远在唐代”,那时以家庭个体自主采煤为主,“多出有煤露出地面,当地居民,俯拾即得”[2](P56)。古代的萍乡煤炭开采形式大多以家庭自主作业为主,直至清乾隆时期才由官方组织运营。安源煤炭作业情形在歌谣中表征出如马克思所言的自然共同体的生产关系模式。
《安源山村吟》
安源岭上搭棚所,曾有村夫非似我。
日午满山烧炭烟,夜深通垅照渔火。
短衣裁剪刚齐腰,尺布染蓝包脑里。
男妇肩挑枯块来,相摩相谑不相左。[3](P8)
这首创作于清康熙年间的诗歌,描绘的是安源煤矿山岭的劳动场景:安源山岭上安扎着临时住所棚屋,白天炼焦烧炭的烟雾在安源岭上升腾缭绕,晚上则点燃了星星点点的渔火。短衣帮的村夫们头上包裹着蓝布以防炭灰。劳作的场景没有太多劳苦辛酸的描写,倒是男女挑焦炭擦身而过时,彼此开着玩笑、互不让道的场景显得颇为欢悦。这一劳动场景体现出历史时序中“最为原始”的形态,即马克思所言的“个人的对于共同体的依赖性与非独立性”[4](P466)。马克思认为,这种以血缘、习惯语言为纽带,以家庭为最基本单位的自然生成的共同体,是“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5](P724)。
不难看出,这是一种趋近于桃花源式的共同体,在中国古代诗词中不乏此类叙述。比如:“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首描写中国古代农民生产场景的诗歌,呈现的是中国传统家庭的劳动模式:男人白天劳作耘田,女人晚间搓麻。孩子不会耕种织布,但也参与农事劳动,在桑树下学种瓜。这种“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的家庭生产模式,是一种马克思所言的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由“你”和“我”构筑的自然的/本源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无论在中国传统田园诗词中,还是在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追怀里,都被推崇为崇尚自然的“人类理想回归地”。然而,这种稳固的、自我封闭的血缘伦理共同体并非理想的联合形式,因为在这个共同体里,作为历史发展产物的个体的人是缺席的,叙述主体也并非短衣帮的挑炭工人,而是“非是村夫”的“我”。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6](P765-766)田园牧歌笔调描述的自然共同体,其本身的局限性体现在对自然的过度依赖上,由此导致共同体具有不稳定性,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类共同体在安源歌谣的描述必然遭到扬弃。
二、虚幻共同体的表现及批判:从赞“物”到惠“人”
1896年,张之洞等人推行洋务运动,这一运动在安源煤矿进行了相应的实践:封闭土井,引进大批西方采煤的机器设备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管理模式,《安源山村吟》中的生产关系寂然谢幕。一首创作于晚清的《游安源矿歌》,昭示了安源煤矿劳动模式的变化,也宣告了安源煤矿自然共同体的瓦解。
《游安源矿歌》
万峰突兀拥碧螺,菁华天蕴山之阿。
千年生面一朝辟,经营惨淡神功多。
我行来此一登眺,楼道参差金碧罗。
隧道下穷数千尺,车声断续时相过。
荧荧灯远小土豆,盘纡鸟道平不颇。
及泉讵足巨灵擘,凹凸地质费琢磨。
凭阑四望扩眼界,电车奔驶如掷梭。
轻雷转瞬碧烟杳,群山拱抱形嵯峨。
广厦万间偏森列,殷殷化育宏菁莪。
机轮大小互激荡,革带挽置群切磋。
螺丝尖劈随轴转,因材成器一刹那。
造化阴阳比炉炭,天工人代非殊科。
缩地万里此发轫,利全广握哪有他。
地灵人杰播遐迩,闻风观者来东倭。
归来万壑路盘曲,暮岚空谷暝薜萝。
东风如虎撼肌骨,长啸或可逐睡魔。
眼光一闪小天地,放怀今古空浩歌。[7](P48)
这是一首新型的工业诗,与之前的农民诗歌相比,其诗歌意象、抒情方式、美学气质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这首诗中,中国古典田园诗词的闲适静谧美学消失殆尽。抒情主体先以一种惊奇的目光赏览安源矿山上奇险壮阔的自然风光,随后,“机轮”“马力”“电车”“革带”“起重”“螺丝”等现代工业的“物”轮番上阵,生产的空间场域也随之拉开,显得尤为开阔,“隧道下穷数千尺”,“凭阑四望扩眼界”,抒情主体的眼光不再是“一闪小天地”,而是“放怀今古”。在这开阔的空间环境中,隆隆的电车“奔驶如掷梭”,机轮发出的声音相互激荡,革带在机器间运行的“切磋”声此起彼伏。这一系列诗歌意象集结而成的镜头,纵横交错地呈现了工业生产的现代图景,其中激荡出来的声音景观,也打破了古代生产方式下的闲适悠然,呈现出运动雄壮的美学色彩。
这是一种单一维度的抒情,主要抒发对新出现的大工业时代“物”的惊叹,突出的是“物”的美。抒情主体以一种游览者、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将自身内置于空间环境中,操作机器的产业工人在工业生产中只是一种隐形存在,没有形成一个自足的主体,因而未能建立起生产者和生产对象的有机联系,也无法把握人和机器之间的深层内涵。在此我们会发现,这一图景透射出共同体在“人”的维度上走向了式微,而在“物”的维度上重新得到建构。在资本的逻辑中,“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6](P419)。马克思认为这种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不是真正的共同体,而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进入安源后,对这一虚幻共同体的批判成了安源工人歌谣革命动员的叙述起点。1923年,安源俱乐部教育股副股长陈潭秋在广州参加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心情万分激动”,决心“号召全中国的劳工,要继续‘猛攻!猛攻!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回到安源后,他随即“写了一首短诗《我来了》,发表在李求实负责编辑出版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上。
《我来了》
潭秋
(一)
太阳在空中眼眯眯地笑着,
如火的热光在人们身上依恋着;
人们气喘着,汗流着!
(二)
“我来了!我来了!
欢迎我的顷刻就凉爽了。
为何欢迎的人太少呵!”
电扇呜呜地旋转着说。
(三)
“我来了!我来了!
不欢迎电扇的人都欢迎我。
渠们在热光之中电扇之外向着我唱欢迎之歌。”
风在大群中很骄矜地说。[8](P67)
诗歌第一节着力描写劳动者面对的恶劣环境,工人在酷暑难耐中做工,而“太阳在空中眼眯眯地笑着”,暗示工人的苦难只能靠自己解除;诗歌的核心部分在第二三节。“电扇”是第二节的叙述主体,电扇“来了”,意味着能让人们“顷刻就凉爽”的风来了,可是悖论随之而来:人们在酷暑难耐中无比渴望风,可带来风的电扇却遭遇“欢迎的人太少”。那么,大多数人欢迎怎样的风呢?是“电扇之外”的风。至于这是大自然的风,还是其他机器工业产物带来的风,作者并未具体述之,总之不应该是少数人专享,而是能惠及“大群”的“风”。
从诗歌内部来看,这首诗揭示了大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图景:生产资料逐步聚集在少部分人手中,大部人逐步成了贫困的无产者。这在安源煤矿的劳资工薪的分配中可得以印证。1923年,时任安源东平时段总监的王鸿卿“月薪一百八十元,月薪以外的收入却在三千元以上,超过他的月薪近二十倍。与旷工每月工薪大工七元半,小工五元半相比,超过四百倍”[9](P156)。这种财富严重不均衍生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弊端,即劳动者没有财力享受到充足的劳动产品,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常出现分离,由此产生了人与物的分离。“电扇”这一由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却无法被工人享用,以至于出现了不欢迎“电扇”的现象,这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言的异化。在这种异化下生成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是一个虚幻/虚假的共同体。“虚假”并不是说这种共同体不曾真实的存在,而是说这种共同体不但没有为个体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反而成为那些构成它并对它有期待的个体的对立。“虚幻的共同体”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分化,分工带来分配的严重不均衡和社会阶级不断分离,在这过程中,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分配在数量和质量上皆具有不对等性。“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6](P199)面对这一异化,中共二大在创立工会的决议案中指出:“劳动者是创造各种物品者,所以劳动者应该享受劳动者所创的东西。”[10](P76)而诗作《我来了》正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不合理性,呈现出革命知识分子独特的启蒙倾向。与新文化运动的作家们崇尚个性解放的启蒙动机不同,安源的诗歌作家群通过揭开阶级矛盾根源以激发革命情绪,从而号召无产者凝聚起来进行阶级的反抗斗争。后世曾把这首自由体诗解读为“意味深长地把党的‘三大’决议的精神和制定的正确策略,比喻为炎热夏天的凉爽清风,吹到安源广大劳苦大众的心窝上,他们向党唱出了发自肺腑的‘欢迎之歌’”[8](P67)。这一比附无疑过于具体,如果把给工人带来自然清凉的大风比喻为安源早期共产党人的进入,或许更贴切自然。
三、无产阶级共同体想象:“团结”与“建设新社会”的歌咏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之初,即以推行“平民教育”为革命突破口[11](P902),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以及筹办工人俱乐部报刊。从当年的教育股报告来看,“平民教育”对工人进行无产阶级共同体意识的塑造较为着力,“每周举行演讲会一次,由学生讲演,讲题如下:个人与团体的关系;私有财产之流毒;阶级制度之罪恶”[11](P181)。这其中显然包含了共同体意识、阶级意识塑造的基本主题。
关于如何对工人进行无产阶级共同体塑造,据安源煤矿工人追忆,毛泽东初入安源考察时,曾给工人们做过生动的动员:“路上有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把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搬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同心协力,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掀掉,打倒剥削者,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12](P107)对无产阶级这一新型共同体塑造的最初构想,早期共产党人意识到,应确立无产者的阶级意识,以“团结”为动员思想核心。安源歌谣成了承载这一传播功能的重要媒介。安源工人读本中最常见的歌谣主题,便是以围绕“团结”这一主题展开的共同体塑造。比如《工人读本》(第1册)第36课《团结起来力量好》:“独木不能防屋倒/片瓦不能把屋造/个人才力很有限/团结起来力量好/有事大家帮忙做/有害大家相劝告/万人一条心/仇人都打倒。”[11](P832-833)较为着力表达这种构想的是同样收入工人读本的《工人学校校歌》:
《工人学校校歌》
(一)
团结团结,努力斗争!
团结团结,努力斗争!
夺回幸福,创造和平!
我们有了先锋队,
我们又有后备军,
我们要吸取斗争中的教训!
劳动军!前进!前进!
(二)
创造世界,是我劳工!
改造社会,是我劳工!
擒贼杀敌!陷阵冲锋!
开辟光明路,
打破万恶丛!
我们要推翻这全世界的牢笼!
先锋军!猛攻!猛攻!
(三)
养精蓄锐,援助前方!
养精蓄锐,援助前方!
建新社会,扫除魔掌!
看赤光万丈!
一切奴隶都解放!
显现着人们的幸福无量!
后备军!齐上!齐上!
(四)
重重压迫,我们姑姊!
重重苦痛,我们姑姊!
反抗压迫!解除痛苦!
解放全人类!男女无歧视!男女无歧视!
人类最后的一般平等无阶级!
妇女军,兴起!兴起
歌谣以“团结团结”起句,分别以劳动军、先锋队、后备军、妇女军为动员对象,呼吁工人们“团结”起来“反抗压迫,解除痛苦”,为“一切奴隶都解放”“解放全人类”而努力。从这些鼓动表述中可知,歌词的统领思想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呼吁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安源工人运动中的本土化表述则是“工人们,团结起来”的阶级凝聚。从歌谣的节奏来看,《工人学校校歌》等安源工人歌谣颇受五四“女神”诗风的影响,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歌谣中透射出有别于五四个性解放的思想诉求:“个人才力很有限/团结起来力量好”,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在安源歌谣中悄然转换成“阶级解放”,抒情主体不再是五四的“我”——一个夸诞的个体,一个凭借个体力量就可以将“日月星球全宇宙”来“吞”了的个体,而是在共产国际的话语形态脉络里,转换成“我们”“大家”等主导历史的阶级自命。
安源工人歌谣不仅呼吁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推翻全世界牢笼”,同时也以建设“幸福和平”“赤光万丈”的“新社会”提出实践构想,于是还编制了一些为工人阶级构建新的生活世界、且内容意义更为丰盈的歌谣。
《劳动歌》
你种田,我织布,
他烧砖瓦盖房屋
哼哼!呵呵!
呵呵!哼哼!
作工八点钟!
休息八点钟!
教育八点钟!
大家要求生活才劳动。
认识字,好读书,
工人不是本来粗,
读书,识字,
识字,读书。
教育八点钟!
休息八点钟!
作工八点钟!
大家要求教育才劳动。
槐树绿,石榴红,
薄薄花衫软软风。
嘻嘻!哈哈!
嘻嘻!哈哈!
休息八点钟!
教育八点钟!
作工八点钟!
大家要求休息才劳动
与前面几首鼓动型的诗歌相比,《劳动歌》在建构新型共同体表述中,不仅扩大了政治内涵空间,同时也拓宽了诗歌美学维度。
诗歌的创作背景和“三八制度”的提出密切相关。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为要求实行“三八制”而大罢工。所谓“三八制”,就是工作8小时,教育8小时,休息8小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一直将8小时工作制的实现作为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要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13](P215)。1922年5月1日,广州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案》,这一天正是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日子。因而,安源工人俱乐部也响应了“三八制”。
诗歌通过三个不同的时空场景,描绘出新型共同体的构成形态,将工人的生活组织安排成“八小时劳动,八小时受教育,八小时休息”。这无疑在向工人进行一种政治启蒙,传递一种权利信息,即应该享有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合理划分的权利——“应该尽量缩短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属于劳动者自己的自由时间”,即工人还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具体来说就是“用于娱乐和休息的闲暇时间”和“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14](P254)。“三八制”打破了田园诗歌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模式。虽然在田园牧歌的想象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满了一种恬静淡泊之美,但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缺乏明确固定划分的模式,很难说人们的闲暇时间支配是合理和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对于他们,闲暇时间是可能胡乱打发过去的,没有实现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当然不能说他们没有闲暇,但他们没有闲暇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的闲暇往往不成其为闲暇”[15](P26)。安源革命者通过歌谣宣传“三八制”观念,意在阐明革命斗争胜利的成果不仅能使工人享受到闲暇时间,而且能拥有健康的闲暇生活方式,那就是在明确的、固定的闲暇时间里,能享受相对稳定的闲暇生活内容,包括休息、学习、娱乐等。安源工人运动之前,工人除了拥有为恢复劳动能力而需要的饮食、睡眠时间外,没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闲暇生活。即便忙里偷闲的片刻自由,也只能实现如《嫖赌歌》中所唱的“一个月的饷,嫖了一半,赌了一半”[16](P25)的不健康的休闲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安源革命者对“三八制”指向的不仅是新的时间方式,不仅是“抛弃循环的时间观和历史观”,而且指向了新的生活方式的生成,“时间观的改变,就是世界观的改变”[17]。
除了新的时间分配方式产生了共同体的“新”特质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生成了一种共同体之“新”。在传统诗歌的男耕女织模式中,安源工人歌谣生长出了新的主体,即出现了新的劳动参与者——“他烧砖瓦盖房屋”。传统农业文明的劳动方式里只有“你种田,我织布”,是以家庭关系为纽带的组合方式。这首歌谣中“他”的介入,打破了“你种田、我织布”的封闭自足的劳动模式,“你”“我”与“他”没有任何情感纽带,突破了古代血缘伦理共同体模式,将人置于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一个颇具“全面发展”雏形的共同体空间。
四、无产阶级共同体想象的叙述难题:歌谣与“革命叙述”的裂隙
安源工人歌谣在确立阶级意识和构建新的生活世界方面,都具有强烈的理论和实践意识。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类歌谣在当时很难完全做到深入人心。20世纪80年代安源工人的回忆录和口述史表明,“安源工人善唱歌”,不过,老工人们印象深刻的歌谣却是“《听说安源好赚钱》《少年进炭棚》《挖炭歌》”等充满民间歌谣色彩的“悲调”[18]。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早期安源工人歌谣话语携带着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革命话语特征,即“基本上来源于俄式共产主义”,“还没有自己原创性的、体现‘中国’民族特征的、有关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叙述”[19](P207)。这种“生搬硬套”的移植话语,无法顺畅进入中国工人阶级的感觉结构,从而弱化了动员需要的情感共鸣。当然,安源工人歌谣并非只是以共产国际话语形态塑造的“铁板一块”,也尝试了融入“哀而动人”等情感叙述的歌谣编制。
除了以共产国际话语形态塑造无产阶级共同体想象,安源工人歌谣还隐藏着一缕五四诗歌的回声。“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诗歌中重叠复沓的修辞、短促有力的节奏、激越回环的音响,在“猛攻!猛攻!捣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奋进!奋进!”“先锋军!猛攻!猛攻!……后备军!齐上!齐上!……妇女军,兴起!兴起”中都得到回响。这种形式的选择并非偶然。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诸多共产党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五四精神的影响:担任安源俱乐部教育股副股长的陈潭秋,参加过五四运动中的北京学生示威游行;担任安源工人俱乐部文书股股长的李秋实,参加过五四运动中的武汉学生示威游行;担任安源俱乐部第三届主任的陆沉,在四川的一所师范学校求学时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五四时期的“女神”诗人郭沫若的诗歌,在五四青年中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毋庸置疑,郭沫若诗歌创作深受美国诗人惠特曼和德国诗人海涅诗作的启发。这两位外国诗人的诗风较为急促昂扬,主题也充满了鲜明的人道主义和阶级意识。惠特曼以反农奴制著称,海涅以《西里西西亚的纺织工人》而享誉共产主义阵营。两位具有无产阶级倾向的诗人,他们的诗歌艺术形式中包含的意识形态,无疑易于引发革命者的共鸣。如果对照马克思主义文论观,便不难理解这一呼应。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詹姆逊认为,文学身上投射了社会集团或阶级集体的集体意识形态,它们“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构建了一种象征性行为,这种象征性行为能够被意识形态地表达”[20]。安源工人学校校歌中征用的艺术形式,无疑承载着革命者意欲传播的意识形态内容。但问题在于,平行移植“力”美学的诗歌节奏,这个“旧瓶”能否掏空“个性”“个体”内容,同时装入无产阶级共同体的“新酒”。
“硬”话语歌谣编制的同时,在《劳动歌》等构建新的生活世界的歌谣里,则表现出一种“柔软”的浪漫派冲动。如“槐树绿/石榴红/薄薄花衫软软风”,风景的描写包含着传统文人对田园的喜好,又隐含着小资产阶级的美学趣味。在安源工人歌谣这一早期的左翼文艺形式中,“历史运动”和“美学趣味”之间不时传递出多种“声音”,干扰了文本意义秩序的生产。虽然新的时间划分意欲把工人纳入“方程式生活”的共同体,并使其成为现实的、高效的、自律的主体,但诗中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内容,似乎无意中消解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空间逻辑,未能编排出一套完全合乎无产阶级政治规范的行为模式,从而建立起意义上的连续性。同时,这里还很容易看出新音乐运动挥之不去的影响,五四时期的新音乐运动,无论是学院派的萧友梅、黄自,还是迎合都市商业审美趣味的黎锦晖,对西方音乐均有不同程度的个人喜好,甚至热切呼吁“尽量把西洋音乐宣传、灌输给中国社会,这是第一件必要的工作”[21](P114)。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毛泽东曾回忆,1910年在湘乡县立东山高小读书时,教员曾教过他们类似意象的日本歌曲:“麻雀歌唱/夜莺起舞/春天绿野多可爱/榴花儿红/柳叶儿绿/好一幅新图画。”[22](P99)因此,安源的革命知识分子创作工人诗歌时,也难免掺杂了一些学堂乐歌的审美倾向。安源诗歌在话语形态、政治内涵和美学趣味之间表征出的裂隙,却在无意中折射出了新型共同体想象和实践统一的难度。
五、结语
通过对安源歌谣的历史性文本追溯和细读,可以看出安源歌谣在共同体塑造中的精神流变谱系。本文重点考察的1920年代的安源工人歌谣,其共同体的建构是在对虚幻共同体即“物”的批判基础上进行的,而在主题内容和美学形式的表现上,则与同时期的五四诗歌产生了一定的合和与偏离。安源歌谣的无产阶级共同体叙述,既为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思想和艺术的双重经验,也在文学史层面为革命文学的书写提供了合法性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