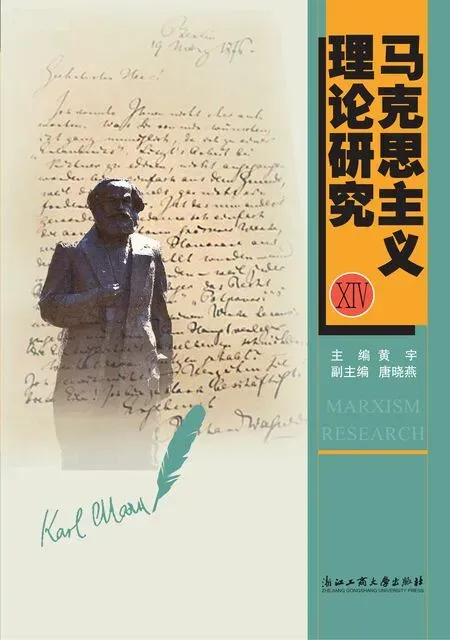人民主体的价值向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场逻辑释义
2021-12-23程丙
程 丙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是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从“社会舞台返回书房”后,对黑格尔法哲学,尤其是其国家观所做的第一次“清算”。在解构黑格尔国家观过程中,马克思因循人民本位,表达了丰富的人民主体思想。
一、跃出逻辑“圣宫”的尝试:靠近人民的唯物立场
《法哲学原理》的《国内法》部分浸透着黑格尔惯用的逻辑式、泛神化的神秘主义色彩。在论及“国家机体”出场问题时,黑格尔提出,国家机体(政治制度)是观念使自身向自己差别化发展的产物。即在黑格尔神秘“圣宫”中,国家机体内部承载不同权力的职能及活动呈现着国家机体的差别性方面,但这些差异是由“概念的本性”即抽象观念决定的,且是被预先设定好的。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了黑格尔抽象范式的逻辑学本质:国家在黑格尔的“哲学大厦”中属逻辑学范畴,黑格尔“真正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马克思判定黑格尔的哲学工作已偏离真正的法哲学,忽视了“现实的规定”,导致“完全抽象的形式规定则成了具体的内容”(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马克思强调“现实的关系”的本体价值,他认为“现实的关系”是本身存在的客观现实性,而非观念主导下的虚幻现实性。苏联学者尼·伊·拉宾说道:“在《1843年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摸索出一条引路线——哲学唯物主义,使他较顺利地转向科学世界观。”(3)[苏]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57页。一旦马克思在他的哲学论证中达到这一点,他对黑格尔的探讨就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它不再是一种纯粹哲学的探讨,而是变成了社会批判。(4)[以]阿维纳瑞:《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张东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即马克思以人民的社会生活为立足点,以现存国家的非理性批判理性国家的虚假性,力图从现实地平还原真实的国家生活。该逻辑在《批判》开篇处马克思厘定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过渡关系时尤为鲜明。
黑格尔拔高了理性国家地位,贬低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地位,更漠视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主体价值。何以消解“二律背反”?马克思走向人民生活的家庭和市民社会领域求解。在马克思看来,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实体性东西均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这些社会存在场域,归根结底是人的类存在、人的类形式,是所有人共有的存在场域,它们天然地内蕴着人的现实本质。家庭和市民社会真实、必然、自在自为、无条件地合理存在着,它们现实地构成了国家,成为政治国家的现实存在方式。政治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个群体中产生的”(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与启蒙思想家强调“个人主义”的逻辑截然不同,马克思关注的是人的类群体的社会现实性,他倾向于一种现实的人民理性。即现实的人在经由类形式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折射出的社会现实性,是理性的真正尺度;以“作为群体的各个人”的现实性考察和解释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过渡关系才是真正合乎理性的逻辑范式。
二、追问国家制度本质:“人民的自我规定”
黑格尔认为:“不是思想决定于国家的本性,而是国家决定于现成的思想。”(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在他看来,现代国家制度是观念性的意志产物,国家制度各环节必然表征观念本性,均可融解于抽象思辨的逻辑中。为能够从必然和自由的普遍联系中引申出国家制度,黑格尔试图架设一座从“机体的一般观念”通向“国家机体或政治制度的特定观念”的“桥梁”。在这座观念之桥的国家制度一端,黑格尔搬出“绝对的自我规定”的现实意志即王权,充当国家制度的现实化身。国家制度在现实的国家生活中变成了君王意志的呈现与表达。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关于国家制度的认识是浅薄之见。国家制度不是先验观念预设之下君王任意的产物,而是现实的人的类群体意志的普遍反映。黑格尔“架桥”的尝试只能是徒劳。马克思直言“这座桥梁永远也架设不起来”(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国家制度“本身具有与意识同步发展、与现实的人同步发展的规定和原则”(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马克思希求的理想国家制度是人民共同意识的凝练,是使“国家制度的实际承担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这种人民主体原则的国家制度构想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是国家制度生成的逻辑起点。君主作为单一确定性不具有真理性,它不能详尽无遗地反映现实的人民诉求和呼声,甚至可能呈现与人民对立的趋向。马克思坚信,“现实的人——而且是人们组成国家——到处都重复表现为国家的本质”(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他将观念主体变成人民主体,将观念规约和超越现实的目的论逻辑变成人民主宰和批判非人的现存的价值论逻辑。国家是人民的最高社会实现形式,国家设制的过程中蕴藏着源自人民的创造力量。“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人民是国家制度的创造主体,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客体化存在,而非黑格尔迷信的单一性。
第二,人民是国家制度运作的价值指要。马克思赞同,国家职能和活动实现其价值必须“同运用和实现它们的个人发生关系”。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便是属社会的人民的工具表征。它们不单纯把你我联合起来,而是将单独活动的人们团结成人民,他们这种活动本身就是政治活动,正是人民具有这种政治职能,它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是国家的职能和活动的范围。(12)[苏]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59页。这内在地规约着国家是社会属性的公共财产,国家职能运作和国家活动开展的要义是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实现人民主体价值。人民意志被奉为国家制度构设的圭臬,“国家制度一旦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幻想”(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第三,人民是君主主权的现实主宰。马克思反对将国家主权等同为君王意志的专属,他认为黑格尔是以“混乱”和“粗陋”的言辞为君主主权辩护。国家制度人格化的主权,并不等同于君主个人意志,而应内含全体人民意志。人民是国家主权的现实主体,国家主权是人民的主权。君主代为行使国家主权的职责,在根本上由人民赋予,象征着人民主权。马克思一语中的:“人民主权不是凭借君王产生的,君王倒是凭借人民主权产生的。”(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黑格尔在《批判》中以卑躬屈膝的方式宣称,没有君主政体国家即不再是国家,而马克思则把重点放在国家机体与人民的关系上,并指出国家始终以人民为根据。(15)George Comninel:Emancipation in Marx’s Early Work,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Vol.24, No.3, 2010, pp. 60—78.
马克思相信民主制才是国家制度本质的真实存在方式,他称之为“卓越超绝”状态。其内涵是人民意志的民主制是“好的类”,其他偏离人民本质的制度形式均是“坏的种”。马克思所言的民主是国家最先进的政治形式,在这里,人民即社会生活的真正主体,被看作有机整体,而非抽象和孤立的分散部分。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国家实际上与人民本身是一致的。(16)Roberto Finelli: A Failed Parricide: Hegel and the Young Marx,Translated by Peter D. Thomas, Nicola Iannelli Popham,Leiden:Koninklijke Brill Nv, 2016, p.213.即“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固然马克思关于民主制的设想,尚是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朦胧向往,但他充分开掘、赞扬民主制中人民意涵的做法,为在现实的国家制度构设中确立人民应有的主体地位,厚植了理论根基。
三、反思国家行政面相:“在更大程度上属于全体人民”
黑格尔对行政权的论述多以官僚政治的面目在场。行政事务被定义为是一项处于从属地位的工作,包含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的权力成分在内。黑格尔将市民社会成员的特殊利益排除在所谓的国家普遍利益之外,将行政权解释为君主主权的客观方面,也即行政权是君权的附属物。行政权用以执行和实施君王做出的决定,以维护君主利益和专制制度。
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孤立地将行政权视作维护所谓国家普遍利益的工具。行政权的职能及其内在规定的生成与市民社会内在耦合,行政权代表的首要利益对象是市民社会成员。他揭示了官僚政治本身所具有的同业公会式的本质,“同业公会构成市民社会的官僚政治,官僚政治则是国家的同业公会。”(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在市民社会领域,同业公会代表不同行业、不同集团的共同利益,这种同业公会属性应是官僚政治的唯物主义。所以,官僚政治代表的普遍利益,应是基于市民社会成员特殊利益之上的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国家的“警察”“法庭”“行政机关”,是市民社会“法定的”“固有的”利益代表,应是人民利益的全权代表;以政府成员和国家官吏为主体组成的中间等级,应是人民的中间等级。“与立法权相比,它在更大程度上属于全体人民。”(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在笃信以人民普遍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行政权才具有价值合理性后,马克思深刻批判了黑格尔该理论的伪善面相。
首先,马克思戳穿了官僚政治窃取国家目的的阴谋。黑格尔将官僚政治描述为形式主义的国家,将其看作是国家的物质内容和现实力量。这种属形式的特质渗透在其内容中,也表现在其目的上。官僚政治以泛化的形式逻辑绑架了国家内容及国家意图,将自身所在集团的形式目的夸大为国家的终极旨趣,或将国家最高追求替换为官僚集团形式主义的表象追求。“既然官僚政治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目的相冲突。”(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这种形式主义的官僚政治与本真的国家政治相对立,当前者占领国家目的的话语高地时,真正现实的国家意图即人民意志被歪曲为“反国家的目的”。
其次,马克思掀开了官僚政治私自占有国家的真相。黑格尔对官僚政治的“哲学美化”,使得“官僚政治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本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国家的现实内容到处被官僚政治的内容填充、侵占,官僚政治名正言顺地上升为国家的理想主义状态。官僚群体狂热地崇拜物质利益,形成封闭自守、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或利益阶层。国家沦为了官僚阶层的占有物,沦为了官僚群体争夺私利的“战场”。在马克思看来,将国家据为己有的官僚政治只是一种象征“虚构的国家”,而代表公民的现实的自我意识、代表人民的公共意志的国家才是“实在的国家”。
再次,马克思揭露了官僚政治的“粗陋唯物论”本质。由于行政权受君权统摄和决定,遵从等级、神化权威成为官僚政治内部运作的指导原则。行政机关及其官员一味地服从指令安排,漠视国家现状与人民处境。对官僚群体而言,行政系统内部严苛的等级制和机械的事务工作,不断地消解该群体本应具有的和善宽厚的人道精神;对官僚个体而言,追名逐利实际成为官僚从事行政活动的优先价值。他们将行政当作满足物欲、谋求高位的工具或跳板。“粗陋的唯物主义”主宰着官僚阶层,侵蚀着行政权的公共性。马克思强调,行政机关及其官员唯有奉行以全体人民普遍利益为内核的国家利益原则,方可剔除“粗陋唯物论”贻害,使行政权真正归属于人民。
四、辩证国家立法旨归:“代表人民,代表类意志”
在黑格尔国家观中,立法权被释义为依照国家制度对成文法律及国家事务进行有效规定的权力。立法主体在黑格尔的立法权理论中以混合中介的面貌出场。市民社会一方从人民之中遴选出“缩小的人民”代表作为“各等级”,与国家和政府一方的君王和国家机关成员,共同行使立法权。虽然黑格尔观照了市民社会的存在意义,但人民并非黑格尔立法权所考量的关键,君王任意才是重中之重。他强调,立法权是一个内在耦合整体,其中起作用的首先是“作为最高决断环节的君主权和作为谘议环节的行政权”(2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2页。。
马克思并未被黑格尔的立法幻象所遮蔽。他将法的自然本质与法的历史演绎做视域融合,重新论定立法权意涵。马克思主张,法是作为事物内在发展规律的自在,立法权应先于国家制度。接着,马克思考察了立法权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作用,以历史事实驳斥黑格尔“国家制度先于立法权”的伪命题。经过大革命洗礼,立法权通过象征人民主权的《人权宣言》和《民法典》被法国人民掌握。法国国家制度是法国人民立法权的“作品”。“立法权代表人民,代表类意志。”(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马克思围绕黑格尔立法对象、立法原则和立法主体相关论述,进一步阐释了立法的人民主体向度。
首先,人民事务是立法的现实对象。马克思看穿了黑格尔“普遍事务”的纯粹形式本质。现实自在的事务不是人民的事务,不以人民的诉求和呼声为内在着力点,亦缺乏人民价值取向的政治行动。发现“普遍事务”中人民被缺席的真相后,马克思将人民在“普遍事务”的地位进行“复位”,对“普遍事务”做了人民主体范式的理论阐释。他直言“人民本身就是普遍事务”(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即人民是普遍事务的现实主体,“人民的现实的事务”是普遍事务的应有之义。普遍事务是蕴含着人民意识、人民智慧和人民动机的存在,应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
其次,人民利益是立法的核心原则。马克思认为,等级要素“是作为人民的事务的国家事务的虚幻存在”(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79页。。第一,对于等级要素中必需的“知识”,人民有获取的主观渴求,但在事实上人民一无所知,其实然为官僚阶层所垄断;第二,对于等级要素中蕴含的“意志”,它总是表现为各等级的特殊意志,而各等级以人民之名义参与国家事务,仅是一种良善的愿望。现代国家借等级要素原则标榜的“国家是人民的利益”口号,是一种虚伪的、无实质行动的谎言。黑格尔的等级要素原则遮蔽了现实的人民主体需求。
再次,人民是立法的真实主体。黑格尔认为,“作为单个人的多数人(人们往往喜欢称之为‘人民’)的确是一种总体,但只是一种群体,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2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6页。。即在黑格尔看来,人民作为“无定形的”存在,无法享有参与国家立法的权利,人民只有按照等级原则从内部派出等级代表参与国家立法。遵循“市民社会就是现实的政治社会”的唯物路向,马克思提出,人民是立法的真实主体,人民应普遍参与国家立法。“立法的职能是一种不表现为实践力量而表现为理论力量的意志。”(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即发现和拟定现实法律的政治活动,是人民主体内质的知识外化。人民享有参与立法的权利,有权以自身的知识和意志商讨并决定国家事务。
五、余 论
如前所述,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倒戈”肇始于人民本位的唯物立场。他将人民主体的价值向度内化为厘定与辩证黑格尔国家学说的逻辑引线,并将人民作为现实主体的价值意蕴弥散于其批判黑格尔国家制度、国家行政与国家立法的话语之中。诚然,与马克思处同时代的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也曾试图摆脱黑格尔哲学旧框架,但他们缺乏从人民立场介入的价值关怀和道义支援,没有真正关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普鲁士人民,而是直接关注标榜自我意识的“人”,以期寻得突破路径。其结果均表现为以自我意识为症候的对黑格尔思想的错误附加或变体,仍停留于唯心主义哲学层面。显然,人民主体的价值旨归赋予了马克思实现思想跃迁的内趋力,促使他站在比他的前辈们或同辈们更高的思想阵线上。
当然,应当承认,此时马克思批判逻辑中的人民主体意涵尚未成熟。首先,《批判》中指代的“人民”仍然是较为笼统的社会群体的类概念,马克思面向的“人民”存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特定内涵,尚待跃出等级压迫和等级剥削的理论囹圄。其次,对于人民何以必然作为主体的深层探源,马克思依旧倾向于将自由、理性、民主、平等原则作为叙事总纲,还不能从社会的经济现实层面为人民辩护。然而,也正是此时遭遇的思想阈限,为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那么,《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又是如何具体演绎人民主体的价值向度的?乃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议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