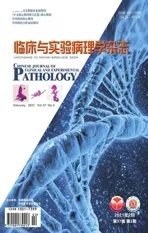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基因突变的研究进展
2021-12-22丁宇斌唐玉凤唐旭东
丁宇斌,唐玉凤,唐旭东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MDS)是一组具有遗传和临床异质性的克隆性造血干细胞疾病,特征为髓系造血细胞一系或多系发育异常、无效造血,外周血细胞减少和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转化风险增加。随着下一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技术的推广和普及,驱动基因突变的分子学数据开始加入到MDS的预后积分系统(revised 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scoring system, IPSS-R)中,对MDS的精确诊断、预后评估和治疗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全面的阐释基因突变(核基因突变和线粒体基因突变)有助于理解MDS的生物学行为,改进和完善预后评分系统以及探索新型的靶向药物治疗。
1 MDS与核DNA表观遗传调控
表观遗传调控是调控基因功能的主要机制之一。目前已发现MDS的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的表观遗传过程发生改变[1]。哺乳动物DNA甲基化是一个重要的表观遗传机制,对基因沉默和印记、X染色体失活、基因组稳定性和细胞命运的确定均至关重要。NGS已经揭示MDS存在外显子和拷贝数改变等遗传学改变现象,结合微阵列核型分析和高通量毛细管测序,发现TET2、IDH1/2、DNMT3A、EZH2、ASXL1、RUNX1等基因突变是MDS常见的基因突变。
1.1 MDS与核DNA甲基化调控DNA甲基化是由DNA甲基化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 DNMT)将甲基转移至胞嘧啶鸟嘌呤二核苷酸(cytosine phosphate-guanosine, CpG)的5号碳原子上,形成5-甲基胞嘧啶鸟嘌呤二核苷酸(5-methylcytosine guanine dinucleotide, 5-mC)。正常人体仅有少部分CpG处于非甲基化状态并富集形成CpG岛,当它发生高度甲基化时会沉默抑癌基因进而诱导肿瘤的发生[1]。
TET(ten eleven translocation)基因对于调控甲基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TET家族包括TET1、TET2和TET3,TET蛋白可将DNA中5-mC氧化为5-羟甲基胞嘧啶(5-hydroxymethylcytosine, 5-hmC)、5-甲酰胞嘧啶(5-formylcytosine, 5-fC)和5-羧基胞嘧啶(5-carboxycytosine, 5-caC),通过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实现DNA的去甲基化[2]。TET家族蛋白的羧基末端包含1个双链β-螺旋结构(double-stranded β-helix, DSBH),DSBH与α-酮戊二酸(α-ketoglutaric acid, α-KG)和Fe2+结合形成TET的催化区域,催化过程需要α-KG、Fe2+与维生素C的参与,其缺少可能影响TET酶的活性。已有研究表明维生素C可使TET2的mRNA、蛋白表达和酶活性均有明显提高,地西他滨联合维生素C可以协同抑制肿瘤细胞和促其凋亡[3]。TET2基因有移码、无义、错义等多种突变,19%~26%的MDS中可见其突变[2,4-6],亦可见于AML、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monocytic leukemia, CMML)及骨髓增殖性肿瘤(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 MPN)。TET2对MDS患者的预后意义尚不明确[6-7],因此能否将TET2纳入危险分层因子尚需进一步分析。
由于TET2蛋白的活性受α-KG调控,α-KG是由异柠檬酸脱氢酶(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IDH)1和2催化异柠檬酸(isocitrate, ICT)产生的,突变的IDH可使ICT转化为2-羟戊二酸(2-hydroxyglutaric acid, α-HG),α-HG与α-KG结构相似,可竞争性与TET2的DSBH结构结合,从而抑制TET2蛋白的活性,导致DNA的高度甲基化[1-2];IDH在MDS中的基因突变发生率为4%~12%[8-9],IDH突变会导致α-HG的高水平积累,进而阻滞造血细胞的分化并促进MDS进展为AML[10]。MD Anderson癌症中心将1 042例MDS患者纳入研究[11],其中5.7%(n=60)发生IDH1/2突变(1.6%发生IDH1突变、4.7%发生IDH2突变),研究发现具有IDH1/2突变的患者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更低,PLT计数较高,骨髓原始细胞百分比更高,但IDH1/2突变的患者绝大多数核型良好或中危;IDH1/2突变少见于TP53、RUNX1、ASXL1、TET2突变的患者,这可能反映部分基因突变之间相互排斥的现象。在较低危的MDS患者中出现FLT3和RAS突变时,提示疾病可能进展为AML;IDH1/2突变也提示MDS可能向AML进展,而对于合并IDH1/2突变且已经进展为AML的患者,使用IDH1/2突变蛋白的靶向药物(Ivosidenib/Enasidenib),能否将患者逆转为MDS乃至完全缓解仍需研究和关注[9,11]。
哺乳动物DNA甲基化主要通过从头甲基转移酶DNMT3A和DNMT3B在CpG二核苷酸处建立,并由DNMT1维持,DNMT3L在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 ESC)中进一步调节DNMT3A和DNMT3B的功能;其靶识别区域(target recognition domain, TRD)保证了DNMT3A酶与CpG位点结合,因此当DNMT3A基因突变影响到TRD结构后DNMT3A活性下降,导致CpG低甲基化并促进造血细胞转化[12]。近年研究主要围绕DNMT3A进行报道,DNMT3B相关报道较少,MDS患者中DNMT3A突变率为5.9%~8%[13-14],具有DNMT3A突变的患者发生AML转化的风险更高,总生存期更短,且DNMT3A突变作为独立的不良预后因素,可能是监测治疗反应的潜在生物学标志物[14]。一项Meta分析纳入12项研究(合计2 236例患者),研究结果也支持DNMT3A突变对MDS患者的预后有不良影响,有助于疾病的风险分层和预后评估[15]。
1.2 MDS与核DNA组蛋白修饰组蛋白修饰的化学类型已逾25种,多种类型的组蛋白修饰及其排列组合构成“组蛋白密码”,参与表观遗传调控、肿瘤细胞凋亡、细胞自噬等过程。MDS中常见的组蛋白修饰基因突变为EZH2和ASXL1突变。
EZH2位于染色体7q36.1,全基因组测序研究发现MDS中EZH2突变多为无义或移码突变,表明其功能丧失在MDS发病机制中有一定作用。3%~13%的MDS患者EZH2基因功能丧失突变[16]。动物实验研究表明EZH2可能是抑癌基因,造血干细胞EZH2的缺失可能导致MDS的发生[17]。敲除EZH2的小鼠可见淋巴细胞减少、PLT增加和轻度贫血,中性粒细胞形态学异常(可见假性Pelger-Hu⊇t畸形和中性粒细胞分叶过多),EZH2突变与TET2和RUNX1共同存在,会加速造血干细胞向MDS或MDS/MPN转化[16]。上述研究发现提示EZH2对造血干细胞的分化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
polycomb和trithorax家族蛋白分别负责维持同源异型基因(Hox基因)的沉默和活化状态,共同维持基因表达稳态,果蝇中Additional sex combs(Asx)基因是polycomb和trithorax的增强子,人类拥有其3个同源基因,分别为ASXL1(additional sex combs like 1)、ASXL2和ASXL3,对转录具有激活与抑制的双向作用[16]。其中ASXL1是MDS的常见突变,MDS患者中ASXL1基因的突变率为11%~29%[18-19],ASXL1突变尚可见于AML、MPN、CMML及潜质未定的克隆性造血(clonal hematopoiesis of indeterminate potential, CHIP)等血液疾病;ASXL2突变常见于有RUNX1-ETO融合基因的AML中,在其他血液疾病中较少见;ASXL3表达则限制于淋巴结、眼、肺、皮肤、脑中,其突变在血液肿瘤中罕见[18]。ASXL1敲减或敲除的小鼠实验表明,ASXL1敲减可以导致MDS/MPN的疾病进展,而ASXL1敲除则由于失去与polycomb抑制复合物2(polycomb repressive complex 2, PRC2)的相互作用而导致造血功能受损,且大多数ASXL1突变存在于最后一个外显子(外显子12)中,并产生C末端截断的ASXL1突变蛋白,后者过表达时会影响髓系的分化[18]。ASXL1突变常与下列基因共存:DNA甲基化相关基因(TET2、IDH1/2)、剪接体(U2AF1、SRSF2)、转录因子(CEBPA、RUNX1、GATA2)、信号转导基因(NRAS、JAK2)、STAG2和SETBP1;ASXL1突变与DNMT3A、FLT3-ITD、NPM1和SF3B1突变相互“排斥”[18]。ASXL1突变常见于高危MDS,近期研究表明TET2突变者对去甲基化药物(hypomethylation agent, HMA)治疗反应良好,而ASXL1突变与HMA反应无关,且ASXL1突变向AML转化的风险更高,生存期短;MDS患者在发生ASXL1突变的同时常可伴发SETBP1突变,后者可能会促使ASXL1突变的MDS患者加速向AML转化[20]。ASXL1突变与HMA反应无关,可能是由于ASXL1突变主要影响Hox基因表达稳态,对基因甲基化的调控影响并不明显;或是由于其他基因突变的同时存在,影响ASXL1突变与HMA反应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2 MDS与核DNA其它突变
RUNX1是转录核心结合因子基因家族的成员,其突变率在MDS中占5%~15%,常提示MDS患者有向AML转化的高风险。RUNX1发生体细胞突变后编码的蛋白异常延长且无转录激活结构域,可能与MDS导致红细胞A抗原表达减少相关,RUNX1和ASXL1的体细胞突变见于MDS患者时,提示患者对HMA治疗反应差,患者生存率低[21]。RUNX1胚系突变的个体可能终生无症状,也有可能表现为家族性血小板疾病合并髓系肿瘤,表现为轻~中度的血小板减少和功能性血小板缺陷(出血时间延长),MDS等疾病的相关风险也会增加,但是并不能根据RUNX1胚系缺失来预测MDS的发病年龄[22]。RUNX1等转录因子对造血功能至关重要,而人类基因转录后的前体mRNA需要将内含子剪接后,才能将外显子拼接为成熟mRNA,因此剪接子(splicing factor, SF)突变会影响到前体mRNA的剪接机制,从而间接地影响转录因子的正常功能,LUC7L2、PRPF8、SF3B1、SRSF2、U2AF1和ZRSR2等SF基因突变在MDS的不同亚型中以40%~85%不等的频率出现,SF突变检测的结果表明,剪接异常及其对RUNX1等转录因子功能造成的影响在MDS患者病态造血过程中具有重要性[23]。
此外,近期研究[24]表明异常的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 HIF-1α)信号,可能是上述诸多驱动基因突变的共有信号通路,能够较好地阐释MDS中多种驱动突变产生相同临床表型的机制。在MDS小鼠模型中敲除HIF-1α能够消除MDS驱动突变的克隆增殖优势,减轻红系巨核系的分化阻滞,改善贫血和逆转MDS表型。该研究有可能在错综复杂的驱动突变中,为MDS的疾病发生找到关键的共性因素,有望为MDS患者的治疗提供新策略。
3 MDS与线粒体DNA
线粒体DNA是细胞内独立于核的遗传物质,由于缺少组蛋白的保护、暴露在活性氧簇(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环境中,且催化线粒体DNA复制的聚合酶不具有校读作用,易发生突变。线粒体DNA的突变可以导致电子传递链(呼吸链)上复合物的异常,在电子传递过程中Fe3+→Fe2+的转化也受到影响,Fe2+的生成受影响时可能导致血红素和血红蛋白合成障碍[25]。
既往研究表明多种肿瘤性疾病存在线粒体DNA拷贝数的异常[26-27],MDS患者线粒体DNA编码的基因表达低于正常,而拷贝数高于正常,经过治疗的线粒体DNA拷贝数明显降低,表明线粒体DNA突变与MDS的疾病发生可能相关[28]。近期研究表明线粒体功能/结构异常可能与血红蛋白合成障碍密切相关[29-30],MDS伴环形铁粒幼细胞(ring sideroblast, RS)并非绝对可见SF3B1突变或PRPF8突变[31]。此时,需考虑是否由线粒体DNA突变导致铁代谢障碍及其血红蛋白合成障碍。
从进化生物学角度分析,线粒体可能起源于细胞内独立生存的共生细菌,在正常条件下线粒体膜可使线粒体DNA与细胞质等相隔绝,当Ca2+超载和ROS堆积等原因导致线粒体膜破损时,线粒体DNA转移至细胞质内或细胞膜外,被自身免疫系统识别为体外异物[32],将通过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DAMP)等途径激活细胞免疫,导致MDS的免疫紊乱[33-35]。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甲基化调控、组蛋白修饰、剪接体、转录因子等驱动基因突变,均可能参与MDS的发生、发展;在错综复杂的驱动突变中,HIF-1α可能成为关键的病理因素,并为MDS患者的治疗提供新策略。线粒体DNA的突变可能影响铁代谢和血红蛋白的合成,并可能与MDS免疫紊乱存在联系。目前,线粒体DNA突变在MDS病理机制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