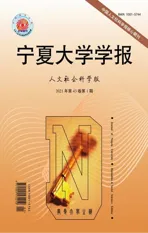城市空间正义探寻
——解读兰斯顿·休斯的《不无笑声》
2021-12-22舒进艳
舒进艳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喀什大学 外国语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如果说1893 年于芝加哥举办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将黑人向世界展示的良好形象与社会地位及以公民身份参与国家公共领域的资质作为吸引移民的有力拉手,那么广受黑人欢迎的《芝加哥卫报》则作为颂扬城市希望与潜力、积极鼓励移民的另一助力推手。芝加哥被描绘为“有着无限未来的愿景之城”[1],一度成为非裔移民摆脱南方压迫、寻求就业和自由的天堂。早期生活在芝加哥的黑人历经了南区由普通居民区到黑人聚居区再到贫民窟区的裂变,对敏于捕捉时代气息的兰斯顿·休斯而言,南区的街道、房屋及社区都成为他观照底层黑人真实生存样态的主要城市空间。
作为“第一部关于芝加哥黑人体验的小说”[2],《不无笑声》(Not Without Laughter,1930) 一经出版,便荣获美国哈蒙文学金奖。不过,评论界对此部小说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研究认为,该小说是关于主人公桑迪对社区经济、社会和种族现实认识的一部成长小说[3]。也有学者指出该小说是一部关于贫困、暴力的文学,一部关于所谓的美国梦的阴暗面的文学[4]。国内,已有研究者对该小说的叙事模式演绎进行了深度分析[5]。然而,对于小说表现出的城市特质与相关主题却缺乏关注。桑迪对有着“应许之地”神话的芝加哥的期许映射了休斯早年对芝加哥的追慕之情,桑迪的芝加哥入城经历再现了“大迁徙”浪潮下的黑人移民希望与失望交加的复杂城市体验。呈现于桑迪眼前的本应是一幅繁华无比的全景性都市图,然而,桑迪的大都市想象却随着入城后的现实灰飞烟灭。那么,为什么桑迪会对芝加哥如此失望呢?迁徙至城市的非裔群体将如何面对城市空间的既定秩序与边界?
桑迪的芝加哥之行不仅见证了囿于“城中城”的非裔群体城市生存的实状,而且他对这个落脚城市散发出的诡谲与隔阂气息发出了心底的质疑。休斯通过桑迪对芝加哥现实的深度考察与挖掘,将20 世纪初的城市黑幕展露无遗。以芝加哥南区为背景的城市书写成为休斯洞察和解读城市现实主义最犀利的武器。他对早期芝加哥黑人经历的真实叙述挑战了《芝加哥卫报》的许多文章将芝加哥描摹成“应许之地”的神话。在政治严威、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体制与固化结构中,芝加哥南区的“黑人带”成为种族主义社会形态下空间区隔与非正义的产物。文化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指出:“空间积极参与到生产和维持不平等、非正义、经济剥削、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压迫与歧视当中”[6],但他坚决反对空间隔离、空间歧视及空间资源的分配不均,并指出种族隔离是导致空间非正义或非正义空间的原因之一[7]。在他看来,隔离就像对公共空间的侵蚀一样,最初似乎是正义生产和城市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却是正义斗争的一个主要目标。在文化地理学的启示下,论文从底层黑人的主要城市生存空间来探析身处城市边缘的非裔群体在主流社会空间霸权的排斥与挤压下,竭力探寻城市空间正义及争取城市权利的实现,从而参与到美国城市的种族空间生产中。
一 公共空间正义与种族区隔
索亚指出,城市所有公共维护的街道以及十字路口、广场都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8]。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街道是不应以种族、阶级及性别等因素来进行划分与区隔。文化地理学家米切尔指出,公共空间必须被理解为任何特定时刻都存在着正义制度的标尺,公共空间不仅仅是城市权争夺的空间,它还是正义的空间[9]。在这一空间里,城市人享有以公民身份平等地实现城市权利的资质,然而,由白人社区团体及业主协会制定的限制性契约迫使黑人长期拘囿在城市限定的地区,1908 年成立的海德公园改善保护俱乐部等联盟组织组建社区将移民和其他族裔群体框定在城市某些地区的做法不仅强制地区隔了城市公共空间,而且褫夺了黑人作为城市公民的地理位置选择及居住权,从而致使作为公共空间的街道在小说中“呈现出种族性的一面”[10]。
对于初抵芝加哥的桑迪来说,映入他视线的本应是城市瑰丽辉煌的建筑及纵横交错的街道,但是,桑迪察觉到他所在的这条街道“渐渐地变得黑暗”。街道所呈现的地域特征,如索亚所言“在地方范围内,更细微的空间歧视体现在将城市空间划分成不同的街道”[11]。在“黑色”的街头,映入桑迪眼际的是“从窗户探出身子、垢面蓬头的黑人;或是坐在门口,叉着双腿,穿着随意,窃窃私语,以及闲逛着的黑人”[12]。他们成为桑迪路过城市全景的一部分,这些散漫的街边路人形象与休斯在自传《大海》中记录的国家大道到处都是工人和赌徒、妓女与皮条客,和罪犯的描述别无二致。在休斯看来,街道的“黑色调”不仅有违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期间为美化城市而形塑的芝加哥“白城”印象,而且这些街头路人也有损芝加哥非裔早前“以博览会作为种族进步的契机,积极参与其中并渴望在整个国家和世界中树立良好形象”[13]的声誉。博览会期间,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曾因白漆的仿大理石建筑而对这座白城印象良好并表达了自己仿佛置身于童话城市的感慨;芝加哥非裔的进步表现与良好形象也曾留给《芝加哥卫报》的创始人罗伯特·阿博特以深刻的印象。杰出黑人代表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B·T·华盛顿、保罗·劳伦斯·邓巴等均参与博览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他们既是19 世纪末以公民身份参与到国家公共领域的民族精英,又是为底层非裔渴望以公民身份融入主流社会而发声的与会代表。此外,成立三年的全国有色人种保护协会将其从计划中的大会地点圣路易斯迁到了芝加哥,该协会的初衷旨在打击南方的暴行如私刑、窥视和剥夺权利等,并反对任何地方的歧视和种族偏见。然而,即使有这样一个大背景的铺陈,芝加哥的非裔移民依然摆脱不掉被主流社会强制区隔的困局。
透过电车玻璃窗对城市街道的敞视性观瞻,饱含了这个小镇青年对城市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城市生活的华丽期待。然而,由于主流社会对地理空间及优势资源的争夺而施加偏见造成的地域歧视,使得呈现于桑迪眼前的城市景象是街道边“矗立着一排排肮脏的灰色大商铺”,“人行道两边既没有大型而漂亮的货栈与商场,也没有塔楼”,“街道两旁没有他所熟知的家乡的树、庭院及小草”[14]。入城后的瞬间印象使桑迪意识到城市与小镇环境、现实与想象的迥然差异,他透过车窗一面对城市街道进行详细挖掘,另一面他又游弋在芝加哥与小镇斯坦顿之间,正如厄里所言“在凝视特定的景致时,会受制于个人的经验与记忆”[15]。入城后的瞬间印象对桑迪产生的持续性作用使他深陷城市、无法抽身。雷蒙·威廉姆斯指出:“如果城镇里的景象差强人意,因为它使人们靠之生活的那些决定性关系变得明显而令人反感”[16],桑迪没有料想到这个想象中的大城市如此单调与丑陋。桑迪对城市街景的实幕揭发,是他进入城市、行使城市权利表达自身意志与情感的一种诉求。列斐伏尔指出城市权表现为自由的权利、社会化的个体性权利、习惯和居住的权利,城市的权利中还隐含着城市生活的权利、参与和占有的权利[17]。桑迪入城后,虽受限于主流社会为城市边缘的非裔群体而设定的空间屏障,但他却拥有了参与城市生活与建构城市想象的权利。
随着移民人口的持续增长,黑人并没有扩散到整个城市,而是被限制在一个不可撼动、居于隔离的地理空间。由种族隔离筑砌的歧视性地理位置导致了不平衡与非正义地理的产生,桑迪所见的沿街景观正是这种非正义地理的直接呈现。载着桑迪的电车沿着国家大道径直驶入黑人带,这一黑人带原本是沿着国家大道的22 街延伸到31 街的狭长走廊,后来从第39 街扩张到了第95 街[18]。内战时期芝加哥迎来了南方的第一波移民潮,在1900年时,仅有30000 人,不到总人口的2%;而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迁徙”运动,非裔逐渐取代了捷克、立陶宛、匈牙利等欧洲移民并从事一些无技术含量的工作,黑人带区的范围也扩展到城市中心[19]。母亲带着桑迪前往的沃巴什大街正位于黑人带的中心,牵引业巨头查尔斯·泰森·耶基斯建造的一英里长的高架铁轨便始于此,对地理位置的争夺成为他攫取城市空间资源与牟取巨额利润的主要方式。拔地而起的高架铁轨犹如一座巍然的瞭望塔,监视与规训着底层黑人的日常生活。地域歧视与空间非正义的交织,令黑人城市生存的地理选择权也因此复杂而微妙。
从国家大道到沃巴什大街,城市街道的种族化特征深化了桑迪对芝加哥南区的隔都印象。桑迪对街道的全景性审视不仅是其作为城市居民实现城市权利的具体表达,而且是回应其内心对城市空间正义的真实呼唤。在休斯看来,芝加哥南区的黑人带是主流社会对公共空间强加区隔而致的城市空间,以街道为代表的公共空间成为意识形态竞争的产物,阻断了底层非裔参与、融入主流社会的通道,从而形成了空间隔离的“城中城”。它所呈现出的种族“黑色调”与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着力打造的均质化城市空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南区的黑人带既是种族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空间产物,又激发了黑人建构城市空间正义与争取城市权利的能动性。
二 居住空间正义与身份认可
由于限制性契约在公共空间的约束效力,芝加哥南区与北区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城市空间。索亚认为,隔离或将特定人口限制在特定地区,不仅与空间非正义的产生有关,而且引发了边缘群体对居住空间权利的争夺。主流社会对黑人的空间排斥与隔离造成了芝加哥南区居住空间的种族化,黑人被迫长期囿限在南区的黑人带。格罗斯曼指出,黑人居民面临着“动态的选择和约束”,与其他移民不同,黑人居民更受限于按种族而非阶级划分的居住空间[20]。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社会的种族等级关系与权威,在其固化的排挤性逻辑中,黑人被压迫的从属性地位使作为城市居民的他们无法平等地享有城市空间最基本的居住权利。在列斐伏尔看来,居住权利意味着住房权利,并且他寄希望于日常生活领域发生一场都市变革以捍卫都市含居住权利在内的自由权利[21]。于底层非裔而言,为城市权利而战,成为他们寻求空间正义、抵制空间霸权的现实目标。
然而,在暴利的驱使下,房东不仅将房屋私自分割成带有简单厨具的小厨房单间,而且在没有租约的情况下便出租给多个租户,并从负担不起良好住房条件的黑人那里收取高额租金。为能立足城市,底层非裔只得忍受房东与主流社会经济上的盘剥,蜗居在黑人带拥挤的出租屋。小说中,母亲安吉租住的已是黑人带区最廉价的房屋,但她仍然为每个月的房租而愁眉不展,这也成为她鼓动桑迪前来芝加哥最切实际的理由。房屋位于有着漆黑走廊的二楼,房间里有一个带有白碗和水罐的洗脸架,一个大衣箱,一把椅子,一张专为迎接桑迪而铺设崭新被褥和浆色枕套的铜床。虽没有壁橱,但母亲告知桑迪可以在门后钉几个钉子;有两扇窗户,就可以在炎热的夜晚呼吸到足够的空气了,母亲安慰性的话语既表现了底层黑人的一种知足与委曲求全策略,又体现了黑人女性传统的持家智慧。然而,这并不能抵挡桑迪内心的压抑与对城市身份的质疑,房屋的狭仄与陈设的简陋让桑迪内心的失望感无处遁形,一种强烈的心理错位隐而不显。
为桑迪接风的晚宴虽设在饭店,但母亲却暗示桑迪在外用餐仅是极少数时候,她会把吃的东西带回家,放在房间里的燃油炉上,然后把纸铺在箱子上当桌子用。母亲的言语透露出第一代移民的坚毅与刚强,以及空间区隔下的城市家宅对黑人自我意识的束缚。微薄的收入无力承担起母子俩额外的城市消费,即使在漆黑的夜晚,也只能用汽灯照明。1879 年爱迪生发明电灯后,芝加哥全市住房都逐渐采用电灯照明,而在黑人聚居区的这些出租房里,房屋设施如家具稀缺,住房条件如照明、通风等的恶劣几乎成为常态,暴露了底层非裔居住空间的匮乏,以及被剥夺了平等地享有具有使用价值的资源的权利以及使用这些资源的机会。小说对芝加哥南区黑人聚居区住房问题的表征得到芝加哥种族关系委员会的调研佐证,“没有油漆过的两层楼框架的房屋排得很近,周围是一堆垃圾和灰烬。普通的便利设施常常是不存在的:厕所坏了或漏水了,电是罕见的,供暖和热水设施常常失灵”[22]。
此外,黑人带居民还受制于居住空间交通地理的钳制。曾带给桑迪无尽想象、促成了他入城梦想实现与流动自由的火车,而今却成为他的精神枷锁。穿黑人带而过的高架火车的轰隆声不仅时常袭扰他和母亲在屋内的谈话,有时甚至他都“听不见自己在屋内的说话声”。休斯不仅揭示了绕城穿行的公共交通作为公共空间对黑人私宅空间的渗透与入侵,而且暗示了底层非裔在公共与私人空间话语权的丧失。每当桑迪“听到长长的车厢声时,都坐立不安”[23],24 小时运营的高架火车成了桑迪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被资产阶级奉为圭臬的泰勒主义令人无处躲逃。公共与私人空间的融叠映射了黑人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状况。高架火车驶过后,桑迪在房屋里常能感受到火车残留的余震及窗户晃动的嘎吱声。工业化的现代生活不仅严重恶化了黑人的居住环境,而且业已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使他们无法抽离被压制的劣势空间,并被永久地剥离了有质量的生活方式。作为家中唯一的男性,桑迪也曾信誓旦旦地对母亲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24],顺从母亲意愿从事着电梯工的工作,领着14 美元的薪水以纾解母亲的愁容,然而桑迪在周而复始、异常沉闷与乏味的电梯工作中身心俱疲,他不甘于像其他轮班电梯工人那样40 岁了还只能操纵电梯,或像哈里斯先生那样一辈子以敲钟为生。最终,不拘泥于现状的桑迪放弃了电梯男孩这一资产阶级自诩为城市文明象征的稳定职业,他的这一决定极大地撼动了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黑人遭排挤的固化逻辑以及金钱至上的原则,作为实现城市权利的一种途径,他的拒斥逾越了主流社会的否定政治,彰显了边缘空间的抵抗力量。
作为城市居民,底层非裔本应公开公平地参与城市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所有过程,获得和利用城市中心生活的价值资源与地域优势,但事实是,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与自由,空间禁锢限制了他们对公共资源与服务的享有权。“阴暗的小巷”“单调的盒子式的公寓”“漆黑的走廊”等城市景观既是桑迪对城市化与现代化气息缺失的落脚城市极度失望的情感宣泄,又是他对遭受空间宰制的居住空间的愤懑不平。居住空间的种族化加剧了城市空间资本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深化与扩大了城市的两极化,拉开了社会差距,凸显了空间的非正义性问题[25]。休斯对底层非裔群体居住空间问题的密切关注烛照了他聚焦黑人性的民族立场与秉性,他既肯定了南区第一代移民为谋求生存而砥砺前行的可贵品质,又认可了他们为实现城市梦想、争取居住空间权利而付出的不懈努力。房屋作为他们在城市的安身立命之所,又是实现他们城市身份的精神家园,即使居住空间环境恶劣、设施破败,但这些都不足以成为他们逃离城市、退守乡土的理由,他们的顽强与隐忍实则是对主流社会空间剥削与压榨底层黑人的另类揶揄与嘲讽。休斯对城市黑人平民日常生活经历的书写反映出休斯“深沉的民族自信心和坚定的现实主义精神”[26]。
三 社区空间正义与阶层分异
芝加哥的黑人社区生活始于19 世纪40 年代末,来自南方的一小群逃亡奴隶和东部的自由黑人形成了一个黑人聚居地的核心,芝加哥曾被描述为“废奴的深坑”和“热爱黑人的城镇”[27]。圣克莱尔·德雷克等学者则将芝加哥南区的黑人社区描述为:“一个小而紧凑但迅速发展为三支力量的社群即‘受尊敬的人’,‘有教养的人’,‘乌合之众’”[28]。由于缺乏律法的干预,芝加哥南区的黑人社区常成为乌合之众窥探觊觎的城市空间。社区内部的阶层分化和外部的种族排斥,城市各种社会经济水平的黑人都集中到社区,使得20 世纪初的黑人社区成了经济和社会上遭受苦难的贫民区。此外,市政官员对黑人带的问题视而不见,芝加哥警方甚至有意把犯罪嫌疑人等引向南区的黑人带,以免打扰白人区住户的安宁[29]。
社区生活暴露了美国种族主义形态下空间生产模式的严重不平与失衡。桑迪的社区生活始于它的试探性融入,首先是一个身材矮小、用阴柔腔调向桑迪打招呼的男子,在递给桑迪一支波迈牌香烟后,便与桑迪寒暄,当桑迪介绍自己来自斯坦顿,这个怪诞的男子竟自以为是地说“是肯塔基,我去过那儿,那有漂亮的女人”[30]。陌生男子的浮夸举止让桑迪茫然不知所措,还未待他想出计谋,陌生男子就拍着桑迪的胳膊试图引诱桑迪到一个房间去看女人的裸照。当桑迪摆脱男子的纠缠后,行走在灯火通明的大街上,他感到莫名的惶恐。在他拒绝为一名又丑又瘦的女子买一张去蒙太克剧院门票的无理请求后,女孩便大骂他是小气鬼。只身行走在大街上的桑迪,还引来了看客的围观与嘲笑。归途中,桑迪暗衬:“这难道就是芝加哥,那里的建筑物像塔楼,湖面像大海......国家大道,作为最壮观的黑人大街,那里的人们总是快乐的,每一盏灯都亮着。在那里可以找到地球上最漂亮的棕色皮肤女人。这就是斯坦顿的人曾经说的”[31]。桑迪在社区的种种遭遇触动了他敏感而脆弱的自尊,从内心深处对芝加哥的层层诘问是他对黑人城市生活的质询与怀疑。路易·沃斯曾指出,都市人没有家,居无定所使他们缺乏传统和情感,几乎没有真正的邻居[32]。作为城市中的渺小个体,桑迪无从了解并明确自己在城市中的位置,这也促使他很难融入与邻舍互动与共居的社区大家庭中。对桑迪而言,黑人社区不仅是不良分子从事非法活动的广阔空间,而且是市政官员与警察角逐城市权力与夺取空间资源的有利场地。
黑人社区在接纳新来移民的同时又无形中将他们等级化。正如大卫·哈维所言:城市化一直是一种阶级现象[33]。已经在南区安定的非裔中产阶级对新来移民的行为颇感不安,他们思维中的“白人标准”令其“厌恶看到街上无所事事的人,因为闲逛被认为是街头景观的一个可怕特征”[34]。已经与该地企业建立起联系的黑人中产阶级为了摆脱歧视而有意疏远这些新来移民,甚至负责推动移民迁徙的《芝加哥卫报》创始人阿博特也用他的社论来批评新移民的不当行为。在一篇关于移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社论中,阿博特写道:“很明显,来到这个城市的一些人在公共场所的行为是严重错误的,令所有可敬的公民阶层蒙羞,他们对法律和习俗的一无所知……使他人有抱怨的理由”[35]。这种批评明确了居住在相同环境、维系社区共同体的黑人中产阶级和底层之间的剧烈冲突,同时也暴露了城市外来人口的集聚所带来的公共交通和环境恶化等城市问题。阶级冲突成为中产阶级排斥与驱赶城市外来移民的动因,也致使城市黑人低收入阶层、外来人口的生存空间不断被限制和挤压,城市权益日益边缘化;另一方面,意味着主动权与城市权更多地掌握在那些定居城市的黑人有产者手中。休斯借此表达了他对非裔中产阶级追求标准化生活的抵制与弃绝以及对种族内部阶级压迫的苛责与鞭挞。
种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与种族主义对社区的渗透常使非裔群体陷入内忧外患、孤立无援的困境。休斯在《大海》中写道:“我在黑人带外走得太远了,越过了温特沃思,遭到了一群白人男孩的攻击和殴打,他们说他们不允许黑人进入那个社区。我回家的时候眼睛发黑,下巴也肿了”[36]。白人社区的排他性与不可越界性构成了一种特权空间,这种强大的社区空间对黑人造成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威胁,他们既不能突破黑白对立的社区界线,也不能僭越既定的空间秩序。1919 年的芝加哥骚乱续写了种族暴力的历史,黑人必须恪守或明或暗的种族界线,即使在白人社区空间外,黑人也不能挣脱主流社会的空间钳制。社区作为黑人种族生活的大环境,本应该是凝结非裔集体意识、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公共场域,但却成为桑迪无法融入、有意避离的种族空间。对于社区中那些贫穷、未受过教育的底层黑人来说,他们自愿或乐意与有着相似背景的人聚集在一个固定的城市空间,在他们眼中,隔离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是有益的。休斯对社区中的种族压迫和歧视,以及非裔群体如何被迫应对这种遭遇的反应揭示了“偏见和种族隔离对黑人心理的破坏性和扭曲性影响”[37]。
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作为总体性革命的策源地,虽充满异化但又满载希望。桑迪从小在祖母海格的教诲下要成为B·T 华盛顿那样帮助黑人种族进步的领袖人物,一心到城市实现理想的他,对城市社区空间正义的缺失深感不安。作为祖母满怀期待的精神寄托以及母亲渴求改善城市生存现状的物质筹码,桑迪曾逡巡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但他最终却突破自我,果敢选择回归学校。虽然桑迪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但读者却坚信桑迪作为种族进步象征的希望空间的来临。桑迪的主动离开,不仅是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城市结构与秩序的公然挑战,而且是他寻求社区空间正义与实现城市权利的一种机智策略。在休斯看来,卑微的底层非裔群体要以公民身份被平等对待就必须通过教育来优化自我,提高民族自尊心与文化自信心,摒弃劣根性,这与华盛顿倡导的通过教育和道德的力量来助力种族提升的宣言有着相似旨归。
四 结语
《不无笑声》中,身处困境的非裔美国人并不是失却了笑声,而是笑是他们应对一切苦难的尖锐利器,是囿于城市的非裔美国人探索空间正义的信念支撑。街道、房屋、社区作为底层黑人生存的主要城市空间,它们见证了芝加哥南区的地理空间变迁及空间重组后的非裔群体城市生存实状。虽然城市化与工业化加剧了非裔群体在主流社会中的边缘化与贫困程度,但休斯却通过底层黑人对城市空间正义的探寻传达了他对建构非裔城市生存空间的想象与展望。休斯对非裔群体面临的空间区隔及空间非正义的揭露与阐发不仅是他对种族主义社会形态下白人特权及优势空间的敏锐批判,而且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结构与固化逻辑的深刻反思。休斯既意识到种族隔离与歧视将黑人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阻断了其参与并融入主流社会的通道,又觉察到非裔群体重塑公民身份与争取城市权利的必要性。休斯现实化城市空间正义探寻的审美格局是他勇敢面对现实、对底层叙事的执着坚守,他通过文学这一想象空间不仅再现了底层非裔对抗种族歧视的日常生活实践,而且预示了身处城市边缘的非裔群体在全球化下寻求城市空间正义及实现城市权利的理性呼声与现实意义,对当下争取种族平权而愈演愈烈的美国“黑命贵”运动不失为一种启示。休斯为建构边缘群体的城市空间正义开拓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