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出阳关
2021-12-21惠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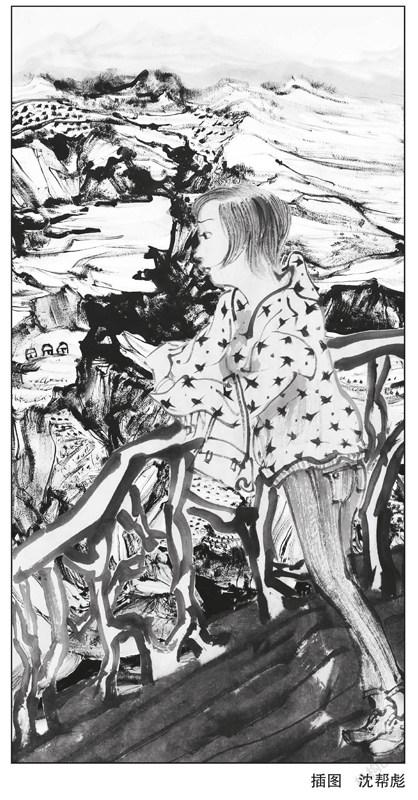
一
中午过后,天气渐渐转晴。
天空明净如洗,蓝得让人心醉。几片白云缓缓飘动,蓝天下显得更加洁白。
太阳已经偏西,但光线硬挺而嘹亮。这是七月高原的阳光。阳光下,方圆几十里的层层山峦灿若烟霞。山峦后面,苍苍祁连群峰高入云端,绵延千里。
这一带有个好听的名字:七彩丹霞。这个名字让人想到红色的火焰,还有天上美丽的彩虹。
大约四点,钟原与林小薇登上了最高的那座观景平台。他们气喘吁吁,汗水淋漓。
观景平台上挤满游人,他们头戴各式遮阳帽,身背各色旅行包。他们疲累而兴奋,脚步与说话声一样杂沓而匆忙。
一群游人走后,钟原与林小薇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来。他们拧开瓶子喝水,水在瓶中发出哗哗的响声。
风从山顶吹来,吹得他们衣服紧贴后背。风中带着冬天残雪的凉气,他们感到一阵清爽。
他們脚下,一条狭长的山谷,山谷对面,一条更为狭长的山脊。山脊层叠起深浅不一的红色,还有橙黄,阳光下发出耀眼而热烈的光芒。
一对老夫妇对着身后的山脊拍照。老妇人披着一条丝巾,丝巾映红了她幸福的笑脸。
老夫妇走了,最后一点吵嚷声随着他们蹒跚的脚步渐渐远去。下一拨游客还在半山腰,观景平台上只剩下钟原与林小薇两人。
钟原提议照个相。这么美的地方,拍个照留作纪念吧。钟原说。
林小薇站了起来,但却走到了镜头之外。
钟原从取景屏里看风景,取景屏里的风景看起来比现实中更鲜亮。相机快门咔哒咔哒响起,完整的山脊被切成远近不等的方块,存入相机黑暗的角落。
钟原偷偷调转镜头,拍下林小薇稍显忧伤的身影。
林小薇发现了,朝钟原笑了一下,她的笑容并没有她想显示的那样爽朗。
钟原朝林小薇走去。他右手不停按动相机上的按钮,把不满意的相片一一删除。
这地方真美,真想永远留在这个地方,林小薇说。
钟原看到林小薇双臂支在木头栏杆上,眼睛望着前方若有所思。栏杆被漆成红褐色,栏杆下是幽深的山谷。
钟原放下相机,相机在胸前晃荡。相机装着长焦镜头,镜头上有两个白色的光圈。
既然这么喜欢这里,今晚不走了,就住在这里。钟原说。
不,还是走吧,你有你的行程计划。林小薇说。
林小薇转身走向长凳,白色的旅游鞋踩在木条镂空地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长凳上放着两只旅行包,一只黑色,一只灰绿。林小薇走到灰绿色旅行包旁坐下。
游客的讲话声越来越大,当达到最大音量时,平台上又挤满了游客。林小薇背起自己的背包,钟原也背起自己的背包,两人一前一后走下山去。
一个小时后,钟原驾车行驶在通往嘉峪关的高速公路上。进入市区时,路灯刚刚亮起。
钟原感到很累,林小薇也一脸疲乏。他们没有刻意寻找,也没有胡乱将就,在街边一家还算干净的饭馆,吃了一顿比较可口的饭菜。
旅馆事先已经订好。与前两天一样,他们各自预订自己的房间。
他们的房间在同一层楼,进屋前,他们礼貌地道了声晚安。
天地一片荒凉,戈壁滩广阔得让人绝望。
高速公路像一条黑色的河流,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把枯黄的戈壁滩一剖两半。
一辆白色的越野汽车孤独地行驶在这条黑色河流上,它的身影起起伏伏,像一颗音符,在这片苍凉的荒漠上演奏雄壮的旋律。
祁连山仍伴随着道路而行。它在道路南边,已伴随道路行驶了近千公里。它切割蓝天后形成的轮廓线越来越低矮,越来越平缓,不远处就是它的尽头。
钟原手扶方向盘,眼睛从墨镜后望着前方。阳光很强,从正前方照进车里,照得钟原的脸像外面的山峦一样明亮。
钟原看看林小薇。林小薇蜷缩在副驾驶座上,仍在熟睡,黑色的安全带束缚着她纤弱的身体。
钟原感觉林小薇很缺乏休息,这两天在车上,她经常会睡着。
外面风很大,阵阵细沙滑过前挡风玻璃,发出嗖嗖的声音。
车内开着音响,显示屏上显示着乐曲名:《河西走廊之梦》。乐曲苍茫悠扬,很符合钟原此时的心情。
道路两旁渐渐有了草木,钟原看到前方绿色路牌上写着瓜州两字。这是河西走廊最西端的一片绿洲。
路往南拐时,钟原把车开进服务区加油。服务区空空荡荡,售卖瓜果的商店在暮色中亮着一盏孤寂的灯。
瓜果店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长期的风沙使她的面孔像双手一样粗糙。
钟原挑了三只哈密瓜,付钱的时候,中年女人说,你女朋友长得真好看。
林小薇脸上红了一下,转过身去。
钟原看了看林小薇,他没做任何解释。
他们决定到阳关去一趟。
这是他们在鸣沙山上做出的决定。做出决定后,他们看到鸣沙山下的月牙泉像一张微笑的大嘴
天气预报是晴天,抬起头来,却看不到太阳。旅店老板说,这是敦煌常见的沙尘天气。
汽车在混沌迷茫中穿行,林小薇却少有的好心情。
林小薇说,她最喜欢王维的《渭城曲》。
林小薇还说,她很小就幻想过浪迹天涯。
车载音响里播放着戴夫·考兹的萨克斯乐曲《I Believe》。乐曲轻柔如金色的丝绒,抚过钟原与林小薇微笑的脸庞。乐曲放完后,林小薇调回来,又重听了一遍。
他们先去看雅丹地貌,回程的路上经过阳关。
阳关早已荒废,只遗下一座残破的烽燧。烽燧是汉代的,见识过汉唐繁华,也经历过后世冷落。
游人很少,钟原与林小薇沿着护栏缓步行走。他们看到一只蜥蜴,蜥蜴也看到了他们。蜥蜴长着细长的身子,皮肤的颜色与沙土一样。他们蹲下身子,蜥蜴手忙脚乱地逃跑。这是他们一天中仅见到的一只动物。
他们在一处高台上坐下,远远望着对面的烽燧。烽燧往前,就是古代的西域。
林小薇低低吟诵《渭城曲》后面两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钟原说,不出阳关,也没什么故人。
他们起身往回走。晚上要赶到行程的下一站:阿克塞。
沙尘淡了些,夕阳露出了昏黄的轮廓。
这是一片真正的沙漠,钟原停下车,拍了好几张沙漠夕照。
钟原和林小薇下车,走到沙漠里。沙漠平坦松软,脚踩在上面几乎没有声音。
钟原提议上车,他要带林小薇体验一下沙漠越野。
汽车拖着烟尘在夕阳下奔驰。停车拍照时,汽车后轮陷入了沙里。钟原加大油门,车尾甩出长长的扬沙,汽车却越陷越深。
夕阳消失了,黑暗一点点吞噬光明,也吞噬钟原和林小薇模糊的身影。
再一次尝试后,钟原放弃了努力。他掏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手机却没有任何信号。
钟原靠坐在车头下,开始自责自己的草率鲁莽。林小薇哭了,钟原知道她是因为害怕。
钟原打开背包,取出自己的外套。他把外套披到林小薇肩上,披的时候,他感到林小薇的肩膀在瑟瑟发抖。
他让林小薇坐到车上。他从后备厢取出水和食物也坐到车上。
他们喝了点水,谁都没有吃食物。一包饼干滑落到座位下,黑暗中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天地一片死寂。钟原曾多次幻想过这种寂静,此时这种寂静却让他心生恐惧。
钟原扭开车灯,看到前方沙地上一片起伏的波痕,那是前天大风留下的印迹。
钟原关上车灯,他决定到路边去碰碰运气。
他们的眼睛已经适应黑暗,他们看到黑暗中有一种朦胧的灰色。他们能够看到彼此的身影,但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任何灯光。他们像行走在漆黑的巨型容器中。
钟原举着手机,终于在公路上捕捉到微弱的信号。
一小时后,两道雪亮的车灯刺破黑暗,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那是从城里赶来的救援车辆。
救援很顺利,半小时后,他们驶上了通往阿克塞的公路。为了这份顺利,钟原支付了很高的救援费用。
车到旅馆门口停下,钟原看到时间已是凌晨两点。
他们取下行李,去服务台办理入住。林小薇从后面把自己的身份证递给钟原。林小薇说,我今晚没订自己的房间。
钟原愣了一下。
钟原接过林小薇的身份证,接着办入住。服务员打着哈欠,给他们登记了一个三楼的房间。
放下行李,林小薇回身抱住钟原,在钟原怀里哭了。后来,他们亲吻,做爱。
事情结束后,林小薇背对着钟原,又哭了。
钟原看着林小薇,神情愧疚。
钟原打开柜子,把备用被子铺在地板上。林小薇走下床,阻止钟原在地板上铺被子。
钟原把林小薇抱在怀里,嘴唇贴着她冰冷的额头。
他们中午时分到达黑马河乡。
黑马河让人想到黑色的骏马,还有清澈的流水。
附近应该有条黑马河,但钟原没有看到。
他们住在小镇西北角一家私人旅馆,背后是青山,眼前是湖水。店主是一个胖胖的浙江女人。
下了十来天雨,你们一来天就晴了,浙江女人脸上挂着阳光般的笑容。
他们驾着车,沿着湖的西岸缓缓行驶。浙江女人说,西岸是青海湖最美的地方。
他们把车停在一处高坡,手牵着手在路上漫步。他们头上是青山,脚下是湖水。
有背包客迎面而来,有骑行者擦肩而过,他们或面带微笑,或沉思不语。
钟原与林小薇走到公路旁边,坐在一片开满红色和黄色小花的草地上。他们望着脚下不见边际的青海湖,湖水如天空般明净。
旁边有一群牦牛在吃草,长及腿腹的牛毛,随着有节奏的啃食不停地抖动。钟原和林小薇的到来没有影响它们,它们睁着见怪不怪的大眼继续进食。
林小薇靠在钟原的肩膀上,一绺长发被风吹起,遮在她微闭的眼睛上。
钟原接了一个电话。接电话时,太阳正沉沉西坠。
林小薇看到那个电话抹掉了钟原脸上的笑容。钟原说,公司业务上出了一点问题,老总让他明天赶回去。
林小薇感觉有些冷,她双手抱着自己肩膀。在她身后,暮色中的远山开始慢慢隐退。
林小薇说,明天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去塔尔寺。
晚饭吃得很冷清。没有笑语佐餐,饭菜显得很难下咽。
他们走在夜色中,默默地听着彼此孤独的脚步声。
他们有许多话想说,但几天的时间太短暂,他们还没形成无话不说的默契。
他们早早睡下。他们感到那条白天没有看见的黑马河,此刻正静静流淌在两人的身体中间。
钟原很久才睡着,醒来后太阳已经升起。他起床洗漱,发现林小薇的洗漱包不见了。他走出房间,发现林小薇的旅行包也不见了。他拨打林小薇的手机,发现她的手机已经关机。
钟原跑到楼下,楼下没有林小薇的身影。他驾车赶到街上,仔细搜寻街上的每个角落,仍没看到林小薇的身影。
钟原返回旅馆。他坐在床边,对着手机发呆。走道里一片吵嚷,早起看日出的游人正在陆续返回。
钟原感到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很空,心里也很空。
钟原到楼下餐厅吃早饭。浙江女人问,你一个人吃早饭,女朋友还没起床吗?
钟原埋头吃饭,一个人吃得无滋无味。
放下筷子,浙江女人又问,天气这么好,你们不再住一天吗?
钟原在门口站住了。不住了,今天我们到塔尔寺去。钟原说。
二
地铁像一串明亮的巨大盒子,穿行于深藏地下的黑暗管道中。那管道是城市的消化器官,每天都在不停地吞噬與排泄。
地铁开得很快,车厢拉起很大的风,发出呜呜的声音。
乘客已适应短暂的混乱,彼此挤靠在一起。随着车厢轻轻晃动,他们呼吸彼此身上难闻的气味。六点多的地铁永远都是这么拥挤。
乘客们大多戴着耳机,眼睛盯着手机屏幕。如果不是因为妨碍自己,他们没人理会站在身边的人都是谁。他们贴得很近,其实隔得很远。他们与这个世界所有的联系都在那方小小的手机屏幕,还有那根细细的耳机接线里。
钟原靠在车门边,与他耳朵相连的,是一个叫平克·弗洛伊德的摇滚乐队。
在我们儿时居住的地方,
在那地平线之外,
在一个充满吸引力和奇迹的世界,
我们思想一直迷失,没有边际……
他听到歌曲中如此唱道。
耳机之外,车厢广播叮咚响了两声,一个毫无生气的机械女声告诉乘客,下一站马上到了。
地铁钻出黑暗,进入虚假而短暂的光明。花花绿绿的广告灯箱在车窗外越跑越慢,越跑越慢,最终定格时,钟原看到一个身穿性感内衣的妖娆女人,站在自己面前微笑。那是一家内衣厂商的销售广告。
车门打开,车站上再次重复已进行过无数次的上下车混乱。
钟原随着人流走向出站电梯。
歌声中断了,钟原听到耳机中传来电话铃声。
手机屏幕显示的来电是一个大学同学打来的。那个大学同学与钟原上学时睡上下铺。他在电话中告诉钟原,他临时有事,明天的出行计划要取消。
钟原听出这是告知,不是商量。
前方道路施工,一块黄色警示牌指示钟原走别的道路。
钟原被迫变换行走方向。他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电梯门开了,吐出三个人,又吞进五个人。钟原是吞进去的五个人之一。
五个人都不说话,有的低着头,有的仰着头,看着不同地方。他们是邻居,但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姓名职业,也没有知道的打算。
电梯里很热,一个老人手拿印着药品广告的塑料圆扇驱赶面前的热气。热气被驱趕到钟原脸上,钟原闻到一股浓重的汗味。
钟原感到电梯是另一种形式的地铁,不同的是,电梯穿行的黑暗管道是竖直的,而且在地面之上。
钟原走出电梯。他走出电梯后,最后一个亮着黄色灯光的数字按键熄灭了。最后一个熄灭的数字按键是26。
一串钥匙在钟原手上转动,钥匙相互碰撞,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钟原打开房门,看到屋里一片黑暗。这种黑暗与他之前每一天看到的黑暗一模一样。
钟原啪的一声按下电灯开关,明亮的灯光立刻冲到门外,在楼道的地上和墙上形成一方被折立的方形光块。
两只蓝色的塑料拖鞋横躺在鞋架前,依然保持着钟原早上出门前的姿态。
拖鞋在钟原脚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击打声,那击打声一直响到阳台。
钟原看到城市的天空是浑黄色的,像草木燃烧时生出的火焰的颜色。那种浑黄带着温度,在夜色中缓缓流动,流过大街,流过楼群,流过钟原汗津津的胳膊和脸。
对面几栋楼房亮着参差不齐的灯光。钟原知道,那些亮着灯光的窗户里,许多人与自己一样,刚刚走进家门;那些还没亮起灯光的窗户,主人应该像他往日一样,还在赶往家的路上。
一个人住在一个人头上,一个家安在一个家上面,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生活方式。钟原想到不久前他的一个想法。
钟原还想到他头脑中的另一个想法:他像一只没有羽毛的愚蠢小鸟,巢穴建在空中,他却不会飞翔。
钟原开始吃晚饭。他的晚饭是一份牛肉炒面,还有一瓶可口可乐。
钟原打开空调,屋里很快凉快下来。屋里屋外像是两个世界。他咀嚼面条,嘴巴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筷子担在饭盒边沿,一只滑落到茶几上。茶几是钢化玻璃的,筷子滑落时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钟原靠在沙发上,嘴巴在做最后的咀嚼和吞咽。他望着头顶的吊灯。他感觉他回来得太早了,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让他有点不太适应。
他有半年之久没有这么早回来了。
他听到隔壁的电视机在播放天气预报。他还听到隔壁的孩子被大人训斥后哭泣的声音。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这套三居室今晚变大了,也变空了。
这套三居室是钟原三年前分期付款购买的。这套三居室本来还可以在另一座城市,那座城市有一个美丽的姑娘,曾向他发出深情的召唤。那个姑娘当时还没有结婚,曾与他恋爱过两年。
老总的话打消了他前往的念头。老总说,有才华的男人应该以事业为重。他后来才明白,老总所说的话有时并不都对。
钟原不停翻动手机通讯录。他在几个名字前做了停留,但最终还是翻了过去。他觉得与那几个名字只适合谈工作。
钟原最终拨通了一个叫艳子的电话。
钟原听到艳子的说话声很小,而且谨慎。艳子说,她丈夫下午回来了。
钟原与艳子相识于一次公司年会。他们在彼此的脸上读到了空虚与欲望。艳子对他的需要是性,他对艳子的需要也是性。
钟原再次抬头望着头顶上的吊灯。
钟原的视线转移到衣柜前的黑色旅行包上。旅行包的拉链敞开着,里面放着他昨晚收拾好准备出门的衣服。还有两本书和一张地图放在旁边的凳子上。
钟原拿不定主意,是把旅行包里的衣服拿出来,还是把凳子上的书和地图放进旅行包里。
半夜里,钟原梦见自己在加班赶项目。那个项目花了他和几个同事半年多时间。
梦醒后,钟原起床把书和地图放进了旅行包。他放得非常果断。
钟原觉得他不应该浪费难得的十天假期,还有他多年前存下的一个梦想。
钟原排在取票机前,他前面有两个人,后面有三个人。
钟原把身份证放在电子感应区,食指在显示屏上点击。取票机内部咕噜咕噜响了几声,扁平的出票口吐出一张车票。
车票是浅蓝色的,上面用黑体字打印着钟原此行的目的地:兰州。
入站口的护栏做成了回环形,这让钟原想起他去过的一些热门旅游景点。护栏是不锈钢做的,手摸在上面凉凉的,摸的人多了,上面还有一种黏黏的感觉。
排队的乘客在护栏内缓慢挪步,像一条效率低下的工厂流水线。他们终于走完护栏的第一段,然后调转方向,接着往下走第二段。
他们有的心平气和,有的一脸无奈,有的焦躁不安。
检票口自动闸机上有一块方形显示屏,显示屏上有一个人脸轮廓图。钟原把脑袋往右边偏了一点,让自己的脸与轮廓图重叠。闸机拦板哗的一声分向两边,钟原走入后,它又哗的一声合在一起。
这是入站过程中效率最高的一道程序,这道程序让钟原心里舒畅了一点。
乘客迅速分流涌向不同候车区域,他们有的缓步慢行,有的挟包快跑。
钟原随着人流往站台走。人流的步伐看起来协调一致,其实他们要去的是不同的地方。
列车离开城市,像一条白色的长龙,穿行于城镇、村庄,还有烈日炎炎下的山林田野。
城市是列車的目的地与歇脚点,在这种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的极速飞驰中,钟原很安稳地睡了一觉。
吃午饭的时候,钟原一眼看到林小薇出现在车厢门口。她背着旅行包,刚刚上车。
钟原当时还不知道林小薇的名字,他看她是因为她长得漂亮。
钟原放下饭盒,不再往嘴里扒拉米饭,他觉得在一个漂亮女孩面前那样吃饭很不雅观。
扔饭盒时,钟原在洗漱间洗了洗脸。他把脸上的水渍擦干,又把揉皱的衬衫拉直,才走回座位。
林小薇单独一人,坐在靠窗位置;她和钟原的座位之间隔着一条过道。
钟原几次往林小薇那边观望,有时是无意,有时是故意。
林小薇望着窗外,一只手托着下巴。她肩上的旅行包放在腿上,包正面有浅黄色的卡通刺绣。
列车很快又到了一座城市,新上车的乘客挡住了林小薇的身影。
钟原把视线转向窗外,看到列车一会儿明一会儿暗,钻进一个又一个隧道。
窗外渐渐草木稀疏,钟原看到视野中出现了广袤的黄土高原。
列车在漫长的黄色沟壑中穿行,最终来到它的终点——兰州。
列车缓缓进站的时候,钟原站起身来看了一眼,看到林小薇仍坐在她的座位上,等待下车。
中山桥上人来人往,钟原走在人群中。他的脚步走得悠然自得,不急不躁。
中山桥在黄河上矗立了一百多年,黄河在黄色土地上流淌了成千上万年。
钟原伏在桥栏上,看到河水带着黄土的颜色,泛起滚滚浪花,极速通过桥下。有些浪花撞在桥墩上,撞得水花四溅。
黄河将连绵的黄土山岭分开,也将林立的高楼分开。兰州就是一座被黄河分开的狭长城市。
钟原在树荫里走着,一边是缓慢的车流,一边是极速的水流。
风吹动树叶,吹到钟原脸上。风很清凉,钟原感到早上出门时,集聚在心里的暑热消散了。
有人招揽羊皮筏生意,钟原看到黄褐色的充气羊皮像一个个硕大的气球。羊儿本是温顺的食草动物,失去血肉后,却成了渡过激流的工具,钟原觉得这个世界充满神奇。
几个身穿红色救生衣的乘客登上羊皮筏子,瞬间穿过中山桥,奔向更远的下游。
钟原走向黄河母亲雕塑,在河边的一棵大树下,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们今天这是第二次见面,钟原说。
林小薇眼神中充满惊愕,还有防备。
钟原提起今天乘坐的那趟列车,还提起自己来自遥远的异乡。林小薇礼貌地笑了一下。钟原看到,林小薇笑起来比不笑更漂亮。
林小薇也是异乡人。她的口音让钟原想起一座熟悉的城市,他在那座城市里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时光。
钟原在林小薇身旁坐下来,他们聊了一会儿那座他们非常熟悉的城市,还聊了一会儿这座他们不太熟悉的城市。
又一只羊皮筏子在他们面前飞流而下。
那只羊皮筏子让他们想到了自己。他们在自己所住的城市独自漂流,却在遥远的异乡碰到了一起。
河对岸的路灯亮了,钟原邀请林小薇一起吃晚饭。林小薇犹豫了一下,起身去了。
一家中式餐厅,红色灯笼柔和的灯光中流淌着林海的《琵琶语》。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霓虹灯下,滚滚黄河浪花璀璨。
钟原说,他上学时非常喜欢历史,一直崇拜张骞、霍去病。
钟原还说,他已经把车租好,明天就将启程,独自走一趟他早就心驰神往的河西走廊。
林小薇望着窗外,神情黯然。
回到住处,钟原接到林小薇电话。林小薇说,我想搭你的车,也走一趟河西走廊。
三
外面在下雨。林小薇希望雨一直下,但雨又停了。
同事们准备下班。一位同事抱怨每天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太辛苦,林小薇从她的抱怨中听出一种炫耀。
林小薇走在大街上,她的步伐迈得缓慢而艰难。这样的缓慢而艰难,最近两年她已经历过多次。
林小薇对路人匆匆的行色觉得不可理解,不知他们为什么那么急于奔向前方。
林小薇还觉得那些路人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他们纷纷扰扰的脚步是对她形单影只的一种嘲笑。
路灯像一排没心没肺的瘦长怪物,肆意捉弄戏耍林小薇的身影,一会儿把它拉成可笑的细长,一会儿又把它压成可悲的粗短。
身影沉默不语,它与林小薇本人一样,早已习惯忍受。
那个男人已经到了,超过预计的等待让他神情焦躁,很不耐烦。
我可以养你,如果不想上班,你可以在家做全职太太。林小薇听到那个男人说。听的时候,她看到那个男人满脸的趾高气扬。
林小薇知道,他在用他的金钱弥补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以及他那充满破洞的离婚历史。
餐厅里灯光辉煌,林小薇觉得从那些人造水晶中透出来的光线非常刺眼。
服务员开始上菜,她们穿着合体的套装,把精美的菜肴放在林小薇面前。
林小薇起身走了。她觉得走进这个餐厅,在这个秃顶男人对面坐下,是她今晚不得不履行的义务。现在,这个义务她完成了。
公交车摇摇晃晃,像一个超级大块头,夹杂在一串个头矮小的汽车当中。
车流行驶缓慢,像流动不畅的河水。
空气依然闷热,夜色加深并没有让气温下降多少。
手机铃声第二次响起,来电显示是妈妈,林小薇再次把手机按掉。
公交车猛然刹车,林小薇没有抓稳扶手,身体向前打了个趔趄。
林小薇走下站台,失去了公交车的承载,她再次感到步伐的艰难。
街头拐角的空地上,一群大姐大妈在街灯下正随着音乐整齐地扭胯挥手。音乐充满动感,林小薇却没感到任何快乐。
小区里很暗,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使窗户的轮廓清晰可见。
林小薇看到自己家的窗户显现在三楼的灯光里。那灯光是苍白色的,她害怕那种苍白色。
林小薇抬脚上楼,楼梯在她脚下发出沉闷的踩踏声。声控灯像一个不辨好坏的势利小人,在她面前亮起,又在她身后熄灭。
林小薇把手伸进挎包,手指触碰到钥匙的金属冷硬感。
钥匙还没来得及插入锁孔,门已经开了。妈妈站在门口,脸上是林小薇早已预想到的那种气恼而又冰冷的神色。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母亲把她堵在门口责问。
那个男人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能交往一下?母亲让她进门,追在她身后,再次责问。
爸爸脸色铁青,一言不发。白色的烟卷在他嘴上化作一道道青烟,通过一个红色的火点,迅速向后退缩。烟灰积聚了很长一截,承受不住自身重量,从烟头掉落下去,在地上摔成一堆灰末,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林小薇走进自己的房间。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怜的软体动物,房间是保护她的外壳。
妈妈的责骂异常尖利,每一句话都能穿透遮挡的门墙,钻进她的耳朵里。
你以为你是金枝玉叶?也不看看自己今年多大了!林小薇听见妈妈隔着房门说。
林小薇感觉眼泪流下来了。那眼泪是冰的,带着透心的凉气。眼泪在脸上流淌时,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子,划过她悲伤的脸庞。
林小薇听到爸妈在争吵。
她知道他们的争吵是昨晚争吵的延续。
她曾在他们的争吵声中心惊胆战地度过了好多年,如今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争吵是爸妈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的生活内容。他们用争吵为幼小的林小薇铺设卧室的地板,又用争吵为成长后的林小薇扎下生活的高墙。
五年前,就是他们,曾用这道严密的高墙挡走了一个腼腆的青年,同时也挡走了林小薇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这个腼腆的青年当时与林小薇同在一所大学,他曾多次和林小薇手牵着手,走在校园朦胧的灯光里。
林小薇拉开窗帘,看到窗外依然延续着昨天的阴沉,也延续着昨天的闷热。
又是一个星期天,林小薇依然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她可以去,有什么人她想去见。
林小薇又躺下了,像许多个她不知所從的早晨一样。
林小薇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关得太久的小鸟,因为住惯牢笼,心中早已失去飞翔的渴望。
林小薇听到哗啦一声水响,那是鱼缸里的金鱼发出来的声音。
鱼缸放在书桌上,林小薇看到鱼缸是圆形透明的,绯红的金鱼摆动尾巴像悬浮在空气中。
金鱼是春天买的,原来是两条,前天死了一条。
金鱼圆形的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抱怨,又像是在哭泣。
林小薇觉得鱼缸里的水中满含金鱼的眼泪,金鱼生活在自己的眼泪里。
爸妈的争吵声消失了,林小薇知道他们上街买菜去了。买菜是爸妈的又一项生活内容,它与争吵相生相伴,却互不影响。
林小薇端起鱼缸走到厨房。她把鱼缸里的水倒掉,把金鱼连同剩余的水倒进塑料袋里。拎着塑料袋顺着街道往前走,一直走到尽头的公园。
林小薇把塑料袋打开,用手托着,将金鱼慢慢放入湖水中。湖中长着层层荷叶,金鱼游到荷叶的阴影中。
林小薇站在岸边,看着金鱼摆着尾巴在水中消失,她觉得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午饭与以前一样,三碟菜,一碗汤。
菜与汤摆在桌上,颜色分别是青、红还有酱褐,但在林小薇眼里,它们都是无色的。
林小薇坐在靠近自己房门的位置,爸妈分坐两边。小时候,林小薇觉得这种坐法是保护,现在她觉得是挟持。
爸妈像没有声带的进食机器,表情严肃,各自夹菜到碗中,再由碗中放入口中。
爸妈咀嚼食物的声音差别很大,爸爸快速而有力,像他暴躁的性格,妈妈缓慢而细碎,像她疼痛的腰腿。
空气仿佛失去气体形态,变成了无色的固体,让人呼吸困难。
电风扇在头顶转动,像只年久失修的搅拌器,发出沉重的吱吱声。
林小薇毫无食欲,几粒米饭在她嘴巴里艰难翻滚。
林小薇知道这种压抑的饭桌气氛会持续很长时间,直到爸妈再次打听到一个或秃头或凸肚的男人,要她前去见面,他们才会露出笑脸。
林小薇不明白,上学时那么年轻的同学上门,爸妈不让他进屋,现在却一次次让她去见那些俗气透顶的老男人。难道危险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小?她想问爸妈,但她没有问。
林小薇眼睛看着桌子。桌子上有一块黑色的烧痕,那是她小学时玩蜡烛烧坏的。
林小薇抬头看对面的墙壁,看到墙壁上挂着一幅工笔兰花图,那是她大学时画的。
林小薇觉得,她人生所有的美好都在回忆中,现实只让她万分痛苦。
林小薇决定说出她心里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上午她放走金鱼时想到的。
林小薇说,爸,妈,我决定搬出去自己住。
林小薇听到爸妈咀嚼食物的声音停了,接着看到爸妈夹菜的筷子停了。但只停了一下,一切又恢复如初。
只要有人愿意娶你,你随时可以搬出去住。林小薇听到妈妈说。
你是我们的女儿,不管你长到多大,我们都必须对你负责。林小薇听到爸爸说。
林小薇放下饭碗,往自己房间走去,走的脚步比吃饭前更加无力。
林小薇的眼泪又下来了,她觉得她与爸妈走在两条交叉的道路上,多年前他们就走过了交叉点,此后只会越走越远。
候诊室里摆放着三排长靠椅,每排长靠椅上都坐满病人。
长靠椅是金属制的,靠背上分布着均匀的圆形小孔。病人靠在靠背上,让许多小孔都带上了或红或黄或白的颜色。
长靠椅的正面墙上挂着一块黑色显示屏。显示屏很像电视机,但里面不播放电视节目,只滚动显示病人的姓名与就诊号。
林小薇坐在第二排第一张靠椅上,她觉得她与其他病人看病的目的很不相同,其他病人是想解决夜晚的睡眠问题,她是想解决整个人生的睡眠。
林小薇觉得很不相同的还有睡眠的地点,其他人是想睡自己的家里,自己的床上,林小薇是想睡在遥远的异乡,一个远离父母争吵的地方。
如果不能按自己的想法生活,那就彻底取消生活。林小薇想到她曾经在书上看到的一句话,这句话最近几天常常萦绕在她脑海里。
林小薇走进诊室,给她看病的是一个中年医生。
中年医生包裹在白色的工作服和口罩中,看不清面目,也看不到表情。
中年医生没有满足林小薇的要求,只给她开了她希望得到的一半用量的药品。
站在医院门口,林小薇犹豫了一下。她很快拿定主意,果断走向第二家医院。
林小薇没有去上班,她觉得上班对她此后的人生已失去意义。
她说她生病了,这是她编造出来的请假理由,也是她身心的实际状况。
她从昨夜就躺在床上,现在依然躺在床上。
她感觉此刻内心平静如水,但她知道这种平静来临之前,她曾经历过多少个日夜的心灵折磨。
一切都决定了,一切都不再更改。林小薇听见自己在心里说。
她的眼睛闭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她听到爸妈在房间里不停走动,还听到他们相互抱怨对方。
他们抱怨的声音很大,但林小薇对他们的抱怨内容已不再关心。
终于,林小薇听到房门哐的一声关上了,她知道时间已过八点,爸妈又如期出门买菜了。
林小薇打开柜门,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出门用的旅行包。把几件衣服放到包里,那几件衣服是她事先准备好的。又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两只白色的小药瓶。那两只白色的小药瓶是她昨天跑了两家医院才购买到的。
林小薇看到了抽屉里红色的笔记本,笔记本里记录着她曾经最美好的一段人生经历。她把笔记本拿在手上看了看,连同药瓶一起放在了衣服的下面。
旅行包的拉链合上了,林小薇的心也合上了。她看了看房间,看到房间里再没有什么让她留恋。
五分钟后,林小薇来到了大街上。她冲着车流招了招手,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停在她的跟前。
到高鐵站去。出租车司机听到坐在车上的林小薇说。
责任编辑 黄月梅
惠兆军,70后,安徽明光人,安徽文学艺术院第八届青年作家班学员,安徽省作协青年作家班学员,作品散见《安徽文学》等刊物,短篇小说曾获安徽省金穗文学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