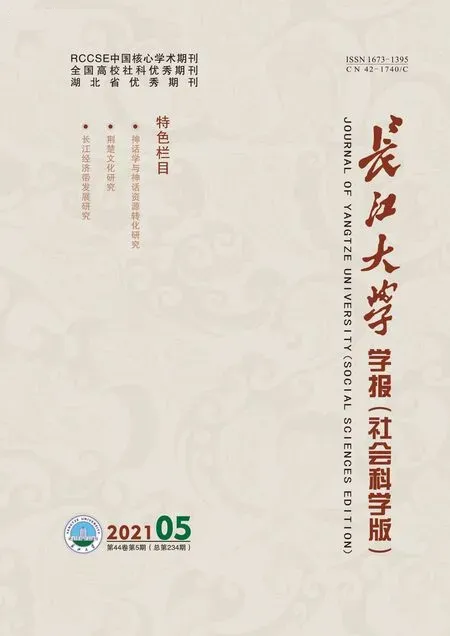戏剧性的闺怨:论镜卜风俗下的镜听词创作
2021-12-14庞明启
庞明启
(重庆邮电大学 传媒艺术学院,重庆 400065)
镜听是中国古代以镜占卜的一种风俗,由此诞生了一种特殊的诗歌题材即镜听词。中唐诗人王建的新乐府诗《镜听词》,既是该类诗歌的发轫之作,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镜听行为的文献,同时而稍晚的李廓也有同题之作,除此之外尚未见到唐人的其他相关文献。宋代没有镜听词,只有一些较为含糊的只言片语,如葛立方《韵语阳秋》曰“余观王建集有《听镜词》云‘重重摩挲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岂今听声之类邪”[1](P138),韩淲《浣溪沙·十六夜》词曰“荆楚谁言镜听词”[2](P2262),又有李洪《元夕书怀》诗曰“春冰夜市心空壮,听镜探官事更赊”[3](P27158),可以推知镜听行为在当时似乎并不常见。到了明清两代,镜听文献数量激增,并出现了22首镜听词,其中明代8首,清代14首。直到民国时期,还有一些作品见诸报刊,可谓绵延不绝。明代张懋修曰“(镜听)惟楚俗盛行,士人于科举之年咸有所卜”[4](P120),清代许起曰“镜听,每于除夕怀镜出门听人言,以卜吉凶,始于唐代……至今吾吴犹好为此事”[5(P530),可见当时该风俗已经较为流行。有研究者指出,“镜听占卜起源于王莽柄政时期或东汉时期……最为盛行是在唐宋时期。”[6](P41)这种说法似乎有待商榷。根据文献记载的情形,该风俗当始于唐而盛于明清,由荆楚等局部地区蔓延开来。又因为镜听往往是除夕讨吉利的一种行为,必须在夜深人静的户外进行,故而多流行于气候温暖的南方。镜听词的创作就是在这种风俗的逐渐流行中获得了历久不衰的生命活力。一般而言,镜听词所写基本为女子占卜丈夫归期,而笔记小说所写基本为士子占卜科举前程;前者侧重于对女子行为与心态的刻画,后者侧重于谶言隐语的神秘与谐趣,而前者在传统思妇的闺情范畴内加入了镜听民俗的戏剧性元素,适当吸收了后者的一些特点。目前关于镜听的研究多从民俗学研究出发,探究其起源、形式、发展,虽亦稍稍涉及镜听词,但并没有把它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在对镜听风俗的研究中,往往也是重响卜而轻镜卜。本文将先行探讨镜听程序以及镜卜传统,并以之为基础对镜听词进行专门研究。
一、镜听与镜卜风俗
镜听程序一般分为室内、室外两个部分。室内须在厨房灶台边进行,先拜灶神,祈祷心事;再在锅内水面上转动瓢勺,以勺柄最终所指为出门所走之方向;最后怀镜出门,听人言以占吉凶。这些程序中,包括三种占卜事物,一为镜,二为瓢,三为人言,故而镜听有时也称作瓢卦或响卜。其中包括一些具体的规定,如时间大多选在除夕静夜,整个过程都要保密,出听时禁言,人数上可一人,也可多人,但须以怀镜人所听为准,等等。还有在灶神前诵镜听咒的,如“贾子《说林》镜听咒曰:‘并光类俪,终逢协吉’”[7](P283),孔尚任《节序同风录》载“咒曰:‘四纵五横,天地分明。神杓所指,祸福攸分。’咒毕,以手揽水左旋抛杓”[8](P866)云云。第一种咒语是就镜光而言,祈祷的是夫妻团圆;第二种咒语是就转动瓢勺而言,祈祷的是能够指向听到吉言的方向。
以上这些规则不十分固定,有的时间并不在除夕,甚至不在半夜;灶神前的咒语有多种版本,或者根本不需要咒语;镜子可以出照以验所听,也可以一直揣着。之所以有这些不同的情况,也许是因为地域和时代的不同,规则会有所变化,或者因为有的占卜者较为严谨,而有的则视同游戏。整个过程的重点在于所听人言的内容如何,怎样解读,以及最后是否应验,这是响卜即听响而卜的关键,也是最为神秘且扣人心弦的地方,一板一眼的程式似乎都在其次。如下面两则镜听故事:
昆山徐大司寇(干学)昆季三人,未第时,除夕相约镜听。乃翁侦知之,先走匿门外,俟三子之出,揖而前曰:“恭喜弟兄三鼎甲。”诸子知翁之戏己也,不顾而走。则有二醉人连臂而来,甲拍乙之肩而言曰:“痴儿子,你老子的话是不错的。”盖以俳语相戏也。已而果应共言。又钱塘黄文僖公机未遇时,镜听闻二妇人相语云:“家有二鸡,明日敬神,宰白鸡乎?宰黄鸡乎?”其一曰:“宰黄鸡可也。”机鸡同音,遂以为谶。[9](P18)
两则故事的重点都放在了所听之语上面,讲究无心之言的谶纬效能,对如何怀镜、如何祷告等程序全不关心,和其他种类的响卜记载没有什么不同。镜听只是响卜或曰耳卜的一种,人们在进行响卜时所怀之物不一定是镜子,甚至能够不揣物品而径直出听。
在镜听中,镜子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乃至可有可无,似乎有点名不副实;但是镜子之所以能够用于该种占卜,且以之为名,根本还是在于其本身具有占卜的性能。有的使用者在出听人言之后还有“又闭目信足,走七步,开眼照镜,随其所照,以合人言,无不验也”[7](P283)的步骤,这就用到了镜子的占卜功能。同条文献还提到须“以锦囊盛古镜向灶神”,对镜的种类和包装提出了较为苛刻的条件,这也是看重镜卜作用的行为。
镜子虽是平常物件,却颇具神秘属性,可以作为佛道神仙的配饰与法宝,也可以作为祭祀与作法的器具,还可以治病、祛邪等等。孔尚任《节序同风录》中就记载了不同节日里与镜相关的不同风俗,如大年初一“家中大小镜俱开匣列之,曰开光明,或佩小镜曰开光镜”[8](P805);端午节“悬圆镜于中堂,曰轩辕镜,以驱众邪”,“是日江心铸镜,作葵花样,背蟠双龙,曰神鉴能照妖”,“用火镜取午时火,曰太阳真火”,“取大镜对日晃耀,光烛暗室,百邪远遁”;[8](P835)中秋节“磨镜,看玻璃宝镜,有面镜、眼镜、深镜、远镜、多镜、显镜、火镜、染镜”[8]848;而除夕之时除了镜听之外,还要“房中设穿衣大镜,照邪”[8](P861)。其占卜的性能,与其神秘属性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并不需要特殊的仪式,一般都是通过镜中异象的呈现、镜背文字的预测性、镜光与天象的感应以及梦镜的情形四个方面显示的。
镜中异象占卜,如元好问《姨母陇西君讳日作三首》其三注曰:
阳曲刘氏家大宝镜,能照天地四方,以前知休咎,其家埋地中,人不得见也。明昌、泰和中,北方兵动,渠父子欲卜之。一日,先以旃幕障中庭,乃扃闭门户甚严。及掘镜岀,光燿烂然,一室尽明,如初日之照。镜中见北来兵骑,穰穰无数,余三方都无所睹,因大骇曰:“不可,不可。”即埋之。[10](P541)
宝镜能预见北方兵乱,并活生生地呈现来,如同现在的电视电影,让人惊骇,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想象力。在流传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镜的故事中,有不少是照镜不见人头从而预卜败亡模式的,颇值得关注。明代徐应秋将其搜罗到了一起:
甘卓将袭王敦,照镜不见其头,寻为王敦所杀。义熙初,东阳太守殷仲文照镜不见其头,寻亦被害。梁河东王萧詧将败,引镜照面,不见其头,为元帝所杀,见《南史》。苍梧太守綦臣不恭王命,照镜不见其头,步隲斩之,见王隐《晋书》。石虎初衣衮冕,照镜不见其首,大恐怖,乃自贬为王。太和九年罗立言为京兆尹入朝,引镜自视,不见其头,为李训连坐诛死,见《宣室志》《集异志》。[11](P319)
当时天下纷争不断,政治凶险异常,一些政治人物经常朝不保夕,动辄即被杀害,此种极端恐怖的镜中异象的产生,恐怕与当时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
镜背文字预测,如明代正德年间江西巡抚孙燧被叛乱的宁王所害,谥号“忠烈”,其死忠之事早有预兆:“燧初至都宪行台,移后堂,向前数尺,于槛下故沟中得古镜,背刻铭二十八字,有‘昭明光运,忠扶日月’等语,盖天格之早已。”[12](P347)这种预测是十分隐晦的,需要在事情发生之后才能让人恍然大悟,其中不乏联想附会的成分。当然也有意思十分显豁的镜背文预测,如宋代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建炎二年,庐陵太守杨渊因城墙坍塌而兴工修缮,挖到一古墓,中有枯骨与石匣,匣中有镜,镜背有文字,言唐德宗兴元年间埋爱子于此,以镜陪葬,并将占卜文字刻在镜背,算出后来赵宋王朝的兴起、靖康之难与浙江兵乱的相继发生,以及南宋建国后此墓被发掘诸事,这让杨渊十分惊异。
镜光与天象感应,如唐代刘餗《隋唐嘉话》曰:“仆射苏威有镜,殊精好,曾日蚀既,镜亦昏黑无所见,威以为左右所污,不以为意。他日日蚀半缺,其镜亦半昏如之,于是始宝藏之。”[13](P852)隋代仆射苏威的镜子在日全食时全部变暗,日偏食时一半变暗,十分神异。接着又发生怪事,镜子在匣中发出钟磬一样的声响,前后两次,第一次响后不久苏威一子去世,第二次响后不久苏威的政治生涯遭受失败。隋代王度作有著名的《古镜记》,说苏威死后,这面神镜辗转到了王度手中,他发现无论日食月食,镜子皆有感应,若日月明朗,镜亦大放异彩。唐代长安城中有击鉴救月的习俗,曰“长安城中每月蚀时,士女即取鉴向月击之,满郭如是,盖云救月蚀也”[14](P35)。这种风俗的产生,想必应与认为镜与天象之间有某种神秘联系有关。此外,据说杭州城外有一面石镜,“在龙髯岭庙后,莹彻可鉴毛髪,明则霁,昏则雨,邑人以为候”[15](P88)。石镜虽非一般意义上的镜子,但其预报天气的功能与前述古镜亦有相似之处。
梦境的情形各异,分别预卜着不同的现实吉凶,看似纷乱却有规律可循,《梦林玄解》指出:“镜如满月,诸事分明。镜若蒙尘,事须整饬。镜如昏暗,将有磨难。好镜跌破,分离之符。缺镜重圆,夫妻会聚。大抵梦镜,明亮光曜者吉,破捐昏黑者凶。”该书中举了很多例子,如“对镜不见影,凶”“手内持镜,吉”“囊镜,吉”“气呵镜黑,吉”[16](P199)等等,每条下面都有详细解读。《梦学全书》曰“镜明主吉暗主凶,镜破主夫妻分别。镜破照人主分散,镜照他人主妻凶。将镜自照远人至,拾得镜者招好妻。得他人镜生贵子,他人弄镜主妻私”[17](P852),涉及到了镜子的明暗、圆缺、所照对象、得镜、弄镜等方面。当然了,梦境占卜重在梦卜,而非重在镜卜,但是它和现实中的镜卜在征候的解读方式上是一致的。
镜子因其日常性与神秘性,使得它被广泛用于各种占卜当中,镜听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前面已经指出,镜听的重点不在镜而在听,镜子并没有起到多少实质性的作用,而且可以被其他物品取代,甚至可以直接省略。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指出,镜听起源于响卜,也简化为到无需怀镜,仅凭言响而卜的单一形式,却没有看到镜卜本身也是镜听的源头之一。镜听有时候会被称为听镜,这就凸显了镜的作用,因为镜子发声的奇异现象是可以作为占卜依据的。如上面所说苏威之镜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唐中宗被武则天废后据说亦曾有此遭遇:“有人渡水,拾薪得一古镜进之,中宗照面,其影中有人语,曰:‘即作天子,即作天子。’未浃旬,践居帝位。”[18](P35)这类奇闻可以再往前追溯,传言早在周灵王之时,有外国使者前来朝贡珍宝,其中有宝镜名为火齐镜,“广三尺,暗中视物如昼,向镜语,则镜中影应声而答”[19](P88)。虽然在现实生活中,镜子并不可听,但镜听时怀镜的举动,应该会和相关的传说有关;再加上镜中的影像常常会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认为镜中或许真有一个人,能够发出声音,并有所预兆,这种心理在镜听词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二、历代镜听词创作的结构要素
镜听词是中唐诗人王建借由镜听风俗题材而创作的闺怨类新乐府诗,后世继作者基本不会脱离闺怨的限定,更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明言为拟王建原诗。这类作品的创作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而未断绝,究其原因,一是两首唐歌质量较好,能够引起后人的效仿热情,二是镜听风俗在民间逐渐流行,是一种比较有趣的诗歌取材对象。在该类诗歌中,女子对待镜听的态度远比笔记小说中男子的态度要严肃许多,其中所刻画的人物动作和心理可谓惟妙惟肖,因此多数皆可视为怀人之作里的佳品。先来看王建的《镜听词》:

明清的诗评家对此评价很高,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云“摹写儿女子声口,可云惟肖”,钟惺《唐诗归》在首句之下评云“‘嫁时’二字有意”,在“好语多同皆道来”之后评云“口齿情事在目”。[21](P1527)该诗对镜听的过程描绘得非常清楚,笔触极其细腻逼真。在谨慎与紧张的情绪下,女子明明希望得到丈夫早归的消息,却在祷告时退一步只求丈夫平安而不计较归来与否。当在月光下听尽好语之后,大喜过望,虽已深更半夜却激动得难以入睡,连给丈夫缝制衣服都反正颠倒了。前后的心理起伏可谓一波三折。这里面出现了两个神,一个是镜神,一个是灶神。最后她为了感激镜神,还殷勤地重绣锦囊,重磨镜面,尽管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镜子是她的贴身之物,是平日最为亲密的伙伴,而灶神就相对抽象一些,疏远一些。
同时而稍晚的李廓所作《镜听词》曰:
匣中取镜辞灶王,罗衣掩尽明月光。昔时长著照容色,今夜潜将听消息。门前地黑人来稀,无人错道朝夕归。更深弱体冷如铁,绣带菱花怀里热。铜片铜片如有灵,愿照得见行人千里形。[20](P5457)
该诗写女子处在一个没有月光,行人稀少的地方,最终没能等到任何好言语,与前诗所言“月明地上人过尽,好语多同皆道来”恰好相反。无论如何,两个女子虔诚紧张的情绪,以及对镜子所寄予的殷切期望都是相同的。可以想见的是,平日不出闺门的女子,在夜晚偷偷独自出行,其实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她们这种冒险行为背后是日常生活的孤单无聊,以及所承受的家庭生活的重担。不管所听言语吉祥与否,这都不大可能准确预卜丈夫的归期,只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在深夜镜听的游戏中,她们郑重其事,惶恐不安,百感交集,在夜幕下扮演着可怜又可笑的“偷听贼”。该种题材所展示出来的戏剧性和波折性,在传统游子思妇类型的作品中是相当突出的。
唐代两首镜听词是后世大部分镜听词效法的对象,它们给这类题材创作框定了四个需要注意的方面,第一是镜听的程序问题,第二是镜听的各种情形,第三是占卜结果以及女主人公相应的情绪反应,第四是女主人公对待镜子的心态。抓住这四个方面,就可以顺利开展此类作品的阅读了。
首先,镜听词的写作一般都是依据前面所说的步骤展开的,即取镜、拜灶神、出听、得到结果几个方面,只不过有些作品展示得完整一些,有些作品会有所省略,但出听与得到结果的核心要素是一定要保留的。如前引王建的作品所写过程较为完整,而李廓的则只有最后两个步骤。再如明代谢肇淛的《镜听词》:
蕙草摧严霜,云愁日易暝。行人岀门音息稀,欲归不归凭镜听。绿铜斓斑土花紫,一片清光匣中起。摩挲愿尔镜有灵,知我心中不言事。凝情端步兰闺外,自向灶前重跪拜。细语丁宁人不闻,时见香风吹锦带。祝罢深深抱镜行,但愿不闻哭泣声。前门后户都锁却,十二重楼空月明。街鼓绝静行人息,铜龙咽水群声寂。惟闻铁马语郞当,砌畔寒蛩鸣唧唧。入门自笑还自疑,未信分明争得知?别有侍儿来问讯,笑道郞归当郞时。两人相向各欢喜,抱镜重装香匣里。可可今日郞归来,为镜买取白玉台。[22](P800)
这首诗是现存镜听词中篇幅最长的,从时节交待、镜听缘起、取镜、求镜、向灶神跪拜祷告,到抱镜出听、获得结果、解读结果以及心情几个方面,展现得完完整整,可以直接作为研究该风俗习惯的研究材料使用。而清代陈作霖之作就十分简省:“灶前拜罢出门行,除夜迢迢无限情。怀里团圞抱月魄,耳边隐约卜风声。明识升沈有一定,吉语何妨先入听?来年欢喜胜今年,郎君稳会芙蓉镜。”[23](P555)其叙述部分主要是为后面的议论作铺垫,所以删繁就简,一笔带过。
其次,镜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都属于不确定的因素,也是镜听词中最有戏剧性的成分。有些诗会从该行为发生的缘由写起,如明代陈价夫《镜听词》曰:“忆昔与君生别离,镜似乐昌初破时。自嗟桂魄几圆缺,远人尚自愆还期。辘轳无绳瓶坠井,青灯荧荧照孤影。”[24](P221)离别的辛酸无奈,归期的无限拖延,让女子觉得如坠深井,形影相吊,实在是无计可施,她只好“含愁抱镜入中厨,呢呢低声自陈请”[24](P221),向镜子与灶台发出了祈请。明末清初的彭孙贻《镜听词拟王建三首》其一曰:“空床昨夜梦归婿,人传郎过黄花戍。”[25](P489)梦到夫婿归来的消息,让女子动了自行占卜的念头。清代永瑆《镜听词》写了一个以理性精神自命的女子,在无尽的孤独和等待的折磨下,聊且从俗进行镜听的思想转变过程:“今夕夫何夕,凛凛岁云除。居人怅独处,含意谁与语?嗟我多为恤,期逝渺所遇。檀车无音声,握粟出何去?昔闻阿姆说,镜听卜行路。少小不相信,谓当永欢聚。啁唧空仓雀,焉能逐鸡步?”[26](P134)其中所言“握粟”也是一种占卜手法,俗称粟卜,女子握粟出门,忽而忆及当年乳母关于镜听可以预卜行人归期的说辞,便改作此法,但内心却在自我嘲笑。
出门之后根据地点和时间的不同,所遇到的行人及其言语的多寡也会有所差异,甚至有时非常嘈杂而听不清楚,有时非常寂静而无话可听。吵闹的环境如明代凌義渠《镜听词》)曰“出门预愁人语譞,无情歌哭免浪传”[27](P382),彭孙贻《镜听词拟王建三首》其三曰“百虫夜号人语乱,报得平安刚一半”,清代赵希璜《镜听词》曰“东邻爆仗声轰天,西邻籸盆烟眯目”[28](P708),有人声的喧哗、百虫的鸣号、爆竹的轰隆等等。寂静的环境如前引谢肇淛之诗曰“前门后户都锁却,十二重楼空月明。街鼓绝静行人息,铜龙咽水群声寂”[22](P800),又如明代陈价夫《镜听词》曰“漏短不知夜几更,四邻已静无人声。忧疑未决心转苦,起步明月沿阶行”[24](P221)。挑选的时间过晚,除夕守岁的人基本都已睡去,所以有时得到的即便不是人语亦能充数,如彭孙贻《镜听词拟王建三首》其一曰“出门听得子规啼,已卜萧郎回马蹄。潜过西邻采药室,闻说当归喜倒剧”[25](P489),又如谢肇淛《镜听词》曰“惟闻铁马语郎当,砌畔寒蛩鸣唧唧。入门自笑还自疑,未信分明争得知?别有侍儿来问讯,笑道郞归当郞时。两人相向各欢喜,抱镜重装香匣里”[22](P800)。
再次,根据占卜结果不同,女主人公们有悲喜与达观等不同的情绪反应。遇到吉语喜不自胜,遇到凶语则倍添神伤,这是最为常见的情况,前面已经有了不少例子,但最让人无奈的是遇到吉语却不能应验的情形,如彭孙贻《镜听词拟王建三首》其三曰“镜听镜听奈镜何,年年归信成蹉跎”[25](P490),清代赵良澍《读张王乐府,喜其辞意新警,拟作四章》其四曰“年年携立街头月,听到红颜生白发”[29](P210)。如此一来,吉语凶语又有什么区别,欢喜悲伤都只不过是自作多情而已。当然也有十分达观的女子,如陈作霖《镜听词》曰“明识升沉有一定,吉语何妨先入听?来年欢喜胜今年,郎君稳会芙蓉镜”[23](P555),虽然命中自有定数,但是听一听吉语,想象一下郎君回来相会的情境又有何妨呢?清代女诗人郭漱玉看得更加通达,其《拟王仲初镜听辞》曰:“听来两字平安好,似慰妾心防妾恼。归房览镜满心欢,镜若有灵镜是宝。明年郎归共郎话,不须更卜桥头卦。”[30](P2)女子知道听来的吉语不可靠,只不过是心理安慰而已,但她并没有过于理智地拒绝这份欢喜,而且坚信明年郎君能够回家。而在面对凶语之时,这份坚信还能使人转悲为喜,如清代詹应甲《镜听词》:“恰闻浪子唱新曲,暮雨潇潇郎不归。掩耳回身泪如缕,掷镜绣床呜咽语。薄情铜片那通神?悔贴玉肌空抱汝。转思郎归终有期,何须镜听重伤悲?但求照我红颜艾,与尔重添合欢带。”[31](P271)女子听到了很不吉利的语言,泪水涟涟,伤心地将镜子抛掷一边,斥责它的无用,枉费了自己的一片赤诚,但后来仔细地想一想,郎君的归期本来就很确定,镜听不过是徒增烦恼,只要自己红颜尚在,终当夫妇合欢。与前述诗中大喜大悲的情绪相比,蔣士铨《镜听》则显得太过无情:“谶纬原难测,推求恐不经。菱花常自鉴,何必问冥冥。”[32(P46)其从破除迷信的角度出发彻底否定了镜听,认为有镜自我照鉴、自我修持就好,有了这份坚贞与德行,就无需那些子虚乌有的谶纬把戏,这就有些卫道士的气息了。
第四,镜听词中女子对待镜子的情感与心态是该类作品一个重要支撑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许多作品的叙事与抒情都无从铺展。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虽然同是镜听,但男子占卜科举前程与女子占卜夫君归期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前者可以轻视甚至忽略镜的作用,后者则视镜为举足轻重之物。镜子是女子朝夕相处之物,不是用来照面梳妆,就是贴身携带保藏,有如伴侣;而且女子在长期的闺阁幽居生活中,难免会因为寂寞无聊而对镜自语,从而有意无意间将镜子拟人化了,当做可倾诉甚至可交谈的对象。即如清代洪亮吉《转应曲》四首其二曰“明镜明镜,看了有时仍听。吉祥善事多般,顿觉愁颜喜欢。欢喜欢喜,侬与镜儿知已”[33](P6381),镜子已经被充分赋予了闺中密友的职能。这不仅是我们在读镜听词要注意的,甚至在怀人诗词、闺阁诗词的大范畴中,都是值得关注的心理现象。如明代韩洽《镜听词》:
夫婿经秋长别离,空留明镜照相思。含颦自启香奁看,分付愁心与镜知。归期不用金钗卜,潜挟菱花向神祝。整衣肃穆下阶行,踏碎花间乱月明。侧身暗傍门前立,良久不闻人语声。隔溪遥听人行处,依稀似道归家去。自疑自信还自庆,镜明镜聪堪作证。归时莫更诉离愁,唤取床前谢灵镜。[34](P196~197)
夫婿一去不回,空留镜子相照相知,那些难以辨识的含糊言语,也要靠眼明耳聪的镜子来作判断。它是整个镜听过程中女子仰仗最多的物品,得到好消息之后最要感谢的就是它的灵慧和体贴。前引郭漱玉之诗曰“归房览镜满心欢,镜若有灵镜是宝”[30](P2),表达的也是同样的心情,高兴地将灵镜唤作宝贝。如果得到的是坏消息的话,女子的埋怨也会一股脑撒到镜子身上,高呼“薄情铜片那通神?悔贴玉肌空抱汝”(詹应甲《镜听词》)[31](P271)。又如清代毛蕃《镜听词》:
匣中古镜青铜蚀,持向灶前重拂拭。敛衣载拜前致词,夫婿一别无消息。古镜千年会有神,重问归期真未真。山川险阻虎豹聚,丁宁细向镜中诉。拜罢回头窃自伤,绣带菱花什袭藏。他时夫婿重相见,更与摩挲祠灶王。[35](P54)
此处的镜子是面古镜,并不是平时的妆镜,用古镜是希望更加灵验。虽然不是常用之物,但女子勤加拂拭,细语叮咛,重复探问,什袭而藏,显得至昵至亲,仿佛须臾不能相离。跟高高在上的灶神相比,镜子是更加可爱的神灵。

三、镜听词的新变与衰微
镜听词在唐代出现以后,宋元两朝都没有继作者,直到明代才开始被仿效。明人的作品对王、李二人亦步亦趋,都采用了长篇古风的形式,在女子镜听行为与心理的刻画上下足功夫,围绕着思妇、妆镜、言响三要素命题立意,反复渲染女子盼夫归来的热切渴望。清代的作品当然也是以承袭旧制为主,但也出现了不少新变。有的作品为女性诗人所作,摆脱了男子作闺音的代言视角,如郭六芳的《拟王仲初镜听词》;有的作品采用了律诗的形式,如蒋士铨的五言律诗《镜听》;有的作品采用了词的形式,如洪亮吉的小令《转应曲(明镜明镜)》(按,《转应曲》即《调笑令》),余光耿的长调《倦寻芳·镜听》;有的作品借镜听词之名而无关风俗,乃写思妇对镜言语,如吴蹇《镜听词》二首。当然最富新变意味的是有人将该题材由闺阁孤怨引向了丰富多彩的大众民俗,如清代沈钦韩的《镜听词》三首,就完全没有闺怨之意而纯为节令风俗之作:
野云戏罢掩柴门,灯火星星出远村。约略丰年多好语,一壶白酒唤儿温。(其一)
籸盆已种火杨梅,乡里相呼劝一杯。圣得紫珍传此意,不须风雪上燕台。(其二)
明朝便唱连珠喏,此夜同分百岁钱。不把痴呆轻卖郄,消寒诗更续新年。(其三)[37](P58)
野云戏,即大傩,年终驱逐疫鬼的仪式。籸盆,除夕日祭祖送神时焚烧松柴的火盆。火杨梅,形似豆蔻,气味辛香,可作为豆蔻的替代品食用,用来佐酒。紫珍,镜精,典出于王度《古镜记》,此处代指镜子。消寒,即消寒会,为富贵人家的亲朋好友之间轮番举办以消磨寒冬,欢闹取暖的宴会。三首诗都描写了除夕之夜的热闹场景,乡里乡亲们驱鬼祭神,宴聚饮酒,期间举子们用镜听预卜举业前程并获得吉言。揣测诗意,这里的镜听和诗酒酬唱一样都是消寒会上的娱乐活动,并没有抱镜出门偷听人言,而是在聚会当中互相传递镜子,由其他人故作吉言让持镜者听到。这种吉言应该是带有隐喻、谐音等谜语特征的祝福之语,需要根据一定的规则当场创作,持镜者也需要配合表演,其目的就是图个热闹,讨个吉利。
清代孙原湘《琴川上元灯词》八首其七亦写镜听:“镜听时交鼓二更,条条僻巷似冰清。不须更约邻娃去,自有素娥相伴行。”[38](P154)乍看此诗并无蹊跷,只是说二更时分人潮退去,街巷变得冷落,女子独自一人借着月光进行静听活动。如果结合整组诗来看就不一样了,前六诗皆言元宵节灯会里一对相恋的青年男女以赏灯为由出来约会,但出于男女之大防,又不能过于明目张胆,只得偷偷地约定二更以后在某某地点幽会,因为灯会以后还有镜听活动,可以独自行动,此时已夜深人静,趁机幽期密会是再好不过了。组诗最后一首写皇帝下诏恭贺节庆,万民欢腾,共乐太平。当此之时,镜听也最容易听到吉言,所以是进行该活动的最佳时机。从《琴川上元灯词》中读书台、小三台、春风巷、文学桥、紫金街等地名来看,所写即孙原湘故乡常熟之风俗,紫金街即当地举办元宵灯会之地。而前引《镜听词》三诗的作者沈钦韩为苏州人,可见清代江南地区镜听词活动之频繁,形式之多样。清代王汝璧的《镜听词》也试图取法于这种讨吉利的民俗,虽不脱闺怨传统,却又加入了谀颂太平的成分:“铜街趚趚更鼓稀,笑声隐约多华词。宜蚕同功大如瓮,宜禾合颖兼双歧。萑苻无贼市无虎,长官不虐民无咨。吁嗟此语岂易得?听闻怳心然疑。”[39](P39)所谓的“华词”都是祥瑞太平、歌功颂德的词语,将该题材引向丰亨豫大的阿谀之风上来,几乎完全消解了闺情的意味。
与此同时,即便是拘囿于传统闺怨的范畴,也有一些作者试图扩大镜听词的表现领域,如引进传统民歌体的隐语元素,使之更具民俗色彩。彭孙贻《镜听词拟王建三首》其二:“道遇儿童捉嬉子,知定郎归先兆喜。归来胸冷菱花热,抱镜同眠数圆缺。应知镜破即归期,三更恰见月如眉。”[25](P489)这里面借用了两首诗的典故,一为唐权德舆《玉台体十二首》其九“昨夜裙带解,今朝蟢子飞。铅华不可弃,莫是藁砧归”[20](P3674),二为六朝《古绝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40](P469),“蟢子”“破镜”等隐语皆与夫君及其归期相关。相似的例子还包括陈价夫《镜听词》之“回身再问匣中镜,知汝何时飞上天”,蒲松龄《拟王仲初镜听词》之“无心好语有心问,却喜归期大刀折”。这些隐语的使用,与镜听所获之言的谜语性是比较搭配的,属于以古求新的手法。这里还需特别关注余光耿所作的慢词《倦寻芳·镜听》:
雁翎信断,鸳颈香孤,闲门深情,盼还刀头。人道事多先兆,晚爨烟昏。私语祝,翠奁影嫩,轻裾抱掩。金铺傍,红桥暗度,粉蟾低照。 渐迤逦,路临坊市,何处歌楼,喧呼佣保?侧听分明似,应一声来了。敛步潜归,邻女贺,引他兰炷花都笑。不荒唐,便今朝,起程犹好。[41(P]312)
虽然采用了词的形式,却基本上遵从了镜听词的传统写法。不过与一般作品不同的是,它在使用戏剧性情节的时候,还进行了喜剧化的处理,色彩鲜明,气氛欢腾,大大冲淡了传统闺怨诗词中孤冷可怜的情思。它将镜听视为乏味闺阁生活的调剂品,带有较多的游戏性质,这也许更符合某些女性实际的生活样态。
清代镜听词的这些新变并没有很好地延续下来,民国文人的作品一味因袭仿古,毫无开拓之功,没能让该类作品在旧文学退场的前夜发出应有的光彩。且看近代法学家谢冠生以簋笙为笔名在1915年的《小说丛报》上发表的《拟王仲初镜听词》:
宝镜光明秋一片,镜中之人不相见。欲凭神镜卜郎归,拂拭镜囊情系恋。绣幌珠帘月上迟,一灯红豆长相思。灶前暗祝还暗卜,郎去郎来知未知。不愿悲秋感离别,愿缔同心卍字结。闻说平安三日归,陌头杨柳春光泄。回身转傍镜台前,人影双时镜影圆。重磨镜面抽镜屉,珍重妆奁护宝钿。[42](P2)

四、结语
镜听是一个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民俗现象,也形成了诗歌表现领域饶有趣味的创作传统。中国古典诗词不仅仅记载了民俗活动的程序、规则、意义,而且以高超的描写与抒情技巧展示了一个个参与者的喜怒哀乐,若能够配合其他文献充分解读,就能够打开一个更加五彩斑斓的民俗世界。有些民俗活动有着性别的规约,比如端午节斗草、七夕节乞巧、中秋节拜月都专属于女性,还有学者指出元宵节里迎紫姑、祭蚕神、祈夫求子等活动也是女性所独专的[45](P129~133),即如罗时进先生所说:“从新正(初一)妇女盛妆出游拜年,初六(有的地方是初二)新嫁女子归宁到除夕守岁,儿女博戏玩耍,一年之中可谓月月有节,节节关涉妇女。其活动内容丰富,风情难以尽述。”[46](P245~246)镜听活动不分男女,但它也是有明显性别区分的。男女在该活动中所占卜的事情与遵循的规则都不尽相同:男子主前程,女子主婚姻;男子的规则十分宽松,重听不重镜,而女子的规则要严格许多,镜与听并重。在镜听词所构建的诗词世界里,几乎只有女主人公楚楚动人的孤独身影,用一个个戏剧性的独角戏诠释了相思驱迫下迈进黑夜,打探命运的千年闺怨。尽管有少数创作者试图突破陈规,用更加社会化的方式进行创作,却未能扭转整个创作局面,使得镜听词始终徘徊在闺怨的疆域,一遍遍回荡着女子向镜神的祈求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