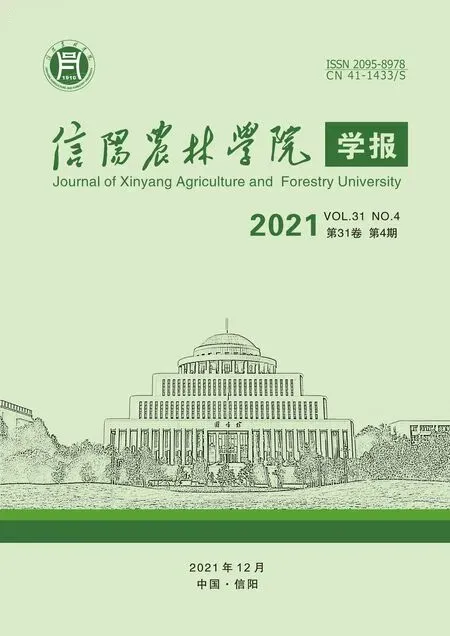论荒诞人的出路与抉择
——加缪《西西弗神话》对生活本身及其意义的诠释
2021-12-13申波
申波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
在任何时代,都有许多的个人在寻找和呼唤肯定性的价值理论和行为,加缪就是其中典型。加缪关注的核心是人,即人的存在与激情、苦难与反抗。从加缪整个哲学思想、创作史的形成和发展脉络来看,特别是从《局外人》中对“荒诞”(又译作荒谬)概念的首倡到《西西弗神话》的进一步阐发,“荒诞”无疑占据着非常突出的位置,烙印于加缪的思维视域及其哲学的理论框架。然而,在主体因意识的觉醒“思虑”到生活世界的荒诞、无意义而获得痛苦、厌倦又不断给予荒诞以确信背后,尤其是在那种充斥着战争、暴政、经济危机等满含疮痍的生存境遇和历史虚无主义、怀疑主义盛行的情形下,所要洞察和追问的绝不是生活的荒诞或值得与否,而是确立内嵌于生命活动本身的一条克服虚无和怀疑的绝对命令。换言之,必须在这样一种适逢和经受生活世界的荒诞、痛苦状况中勇敢地活下去。而反抗内在的含于生存的目的论当中,通过反抗表达主体存在的意义和所能获得的唯一明显事实。
《西西弗神话》作为加缪获诺奖后的一部哲学随笔,旨在考察经由外部世界的荒诞、陌生引起“思虑”及其牵动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生存本身尽管可能荒诞、无意义,然而生存本身却是人的自我呈现、存在方式和意义创生,生命的全部激情皆源于此;从对荒诞世界的承认和体验中借以其为底色阐释荒诞人的反抗和体验,表达对这世界最初和最后的爱,而荒诞、痛苦恰是主体沉迷尘世所必须的代价。加缪虽然远离我们,但他的思想和作品所关涉和蕴含的那种现代性荒谬、主体与世界关系的异化失衡仍旧愈发深刻表达和透析着现代人的生活常态,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加缪所关心的问题依然存在,如暴力、无序、死亡、战争乃至人在荒诞生活前如何自处等。
1 荒诞的认识
加缪作为上个世纪初期到中期一直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道主义思想家,饱受争议的同时也颇受国内外学者、思想家的关注。尽管有相当部分的学者、思想家在对加缪哲学及其著作进行深入研究并作出进一步阐释、剖析,但其落脚点无非是从荒诞哲学、存在主义以及荒诞与反抗、寻求生命意义几个角度。近几年甚至出现以思想互诠、文学创作、哲学文学化以及伦理学的视域对加缪《西西弗神话》进行阐述、研究,成果颇丰。在众多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关注的仍是以承认世界之荒诞为基础,试图详细论证西西弗与命运抗争的英雄形象,揭示加缪对于荒谬世界中荒谬人的出路的理论探索。然大多是沉浸在荒诞的世界和荒诞人中得出生活荒诞、向外求取意义和价值的结论,企图消除荒诞、寄未来以希望并在生存之外强化与不如意之生活、苦难之命运的反抗中以获得某种暂时的应对未来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希望、激情和斗志,忽视或遗漏了对主体意识、死亡的考察以及过分强调“反抗”而造成的作为全部活动最终目的的和人的根本存在方式的“生存本身”与荒诞、反抗间的微妙联系被搁置甚至忽略,这事实上是彻底走向了加缪哲学和反抗的反面。
《西西弗神话》(又译作《希绪弗斯神话》)作为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一部哲学随笔集,内容包括“荒诞推理”、“荒诞人”、“荒诞创作”以及“西西弗神话”。其中以“西西弗神话”最为人所乐道,其截取自古希腊神话,加缪对其进行了改编。在西方社会,它是一个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由于对众神的冒犯,西西弗被惩罚将一块沉重的大石头推到山顶。因巨石的沉重,再加上重力的影响,每次西西弗将巨石推到山顶,巨石都会再次跌落至山脚。因此,西西弗不得不重新开始,如此机械循环,永不停歇。众神相信没有比这徒劳无功、毫无希望的惩罚更严厉了。不过加缪并未直接建构和阐释“西西弗神话”,而是在开篇“荒诞的推理”中首先谈到荒谬与自杀,使用的还是西方哲学惯用的独断手法,把自杀作为仅此一个且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看待,并试图搞清楚自杀与个人思想之间的关系,自杀何以在某种确定性的范围成为荒诞的结果。究其根本,“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1]3。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加缪何以当且仅当将“自杀”唤作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并把对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回答归结为判断人生是否值得一过。虽说加缪所处的时代的哲学已然经历了本体论、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以及后来的各种普遍反形而上学思潮,可真正关涉荒诞的哲学或哲学体系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至少在加缪本人看来是如此,并且加缪似乎很排斥甚至急于与传统哲学的那种抽象性和形式化体系划清界限,譬如与萨特思想的分野。加缪认为那种习惯的推理和玩弄词句常常把问题复杂化,引人误入歧途。不仅否定生活意义的语言、思想和行动难以保持契合,就像叔本华在丰盛的餐桌前歌颂着自杀,在希望中“躲闪”,借以思想超越和规定生活的同时却也背离了生活的本意。而且靠希望而活的人与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加缪赞扬唐璜那样的人“知道其诸种局限的智慧,就是天才的所在”。还有“荒谬感并不因此是荒谬的概念”[1]26,尽管用理智的方法也能推导出荒诞的世界,但它却无法洞察、明晰荒诞的情感,更谈不上对荒诞的体验。形而上学的反抗或者思想的跳跃不过是确信了沉重的命运,那种属人的感受和激情、体验是其无能为力的。加缪果断地反对自杀和思想的“跳跃”,对荒谬世界进行事实分析,荒谬并不一定得到自杀的结论,默认和逃避都只是反抗的反面,从他赞扬唐璜主义和反形而上学的思维和活动方式就可以得知。也难怪熟悉两人的波伏娃在谈及两人的思想见解时一针见血的指出,彼此的相识不过是奠定分手的契机。面对人对统一性的渴望,以理性把握世界的企图与世界的非理性造成的二律背反,荒谬并不取决于意志的努力而是取决其反面,也就是死亡。不过“凭借意志的活动,可以把那些邀请人死亡的东西改造成生活的规则”,对荒诞生活的否定就是用意志和反抗与之相悖而行。死亡并不如同宗教所讴歌的那般,通往净土天国,而仅代表着个体生命的断裂。在谈到荒诞的自由时,加缪说,“如果自己是许多树中的一棵树或动物中的一种猫,那这种生活本身可能就具有一种意义”[1]45。可以清楚明白的是,加缪走的是不同于形而上学的理智道路,更多的关注人的存在与激情、苦难与反抗,而不是那种哲学传统的本体论或达尔文路线。摒弃他称之为游戏的那些东西,加缪在“荒诞的自由”部分更是由荒诞推导出了我的反抗、自由和激情(含假设的因素)。
《西西弗神话》延续了其早前在《局外人》中的一贯风格和态度,对“荒诞”的存在予以接纳和承认而非排斥和消除。在这部哲学随笔中,荒诞并非结论,而是这本书的出发点,只有持此立场,其创作才得以有意义和价值。必须强调的是,荒诞如影随形,具有持续在场性。绞尽脑汁地去验证和透析世界的荒谬或给予其以精确的定义是毫无意义的,并且加缪本人也承认其论述有暂定性,立场很难预判。我们只能从主体生活的荒诞遭遇暂且认定世界是荒诞的,在此基础上分析个体的处境和选择。虽然这种来自经验的荒诞曾被萨特大加抨击,但从加缪的视域,西西弗的人生毫无疑问是荒诞的,可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加缪在“西西弗神话”的第二段一开篇就坦言道“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一是源于他对大地的无限热爱,众神对西西弗的惩罚就是他对大地的热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一是源于他的激情和苦难、折磨,明知是一项无任何效果的事业,依旧乐此不疲地全身心投入。正是这种直面惨淡人生,正视荒诞的不放弃、不沉沦的创造和进取的精神使西西弗在完成推石事业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快乐,就像发现生活的荒谬性使精神得以更节制地沉浸于荒谬中那样。
2 思虑是一切的初始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2]虽说荒诞的产生更多关涉到主体的人和外部世界的存在,但不管是“荒诞的发现”还是“荒诞的结果”皆因“思虑”才成为可能,毋宁说“凭借意志的活动,可以把那些邀请人死亡的东西改造成生活的规则”[1]56。西西弗被迫接受这不可抗拒的命运,日复一日地做着无用而无望的工作,不停地推石上山。毕竟是巨石,人力不可能恒久的维持它在山顶时的那个状态,于是巨石再次滚下山脚,如此机械地循环反复。深陷其中无所谓胜利与逃离,因焦虑而消沉,陷入绝望所患的一种抑郁症,如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被物奴役和异化的状态。开始思想,就是开始设下伏雷。只有当西西弗开始思虑,发现了世界的厚实和陌生感甚至产生厌倦,他才清楚地知道这生活显而易见的荒诞。当西西弗开始“思虑”,然后一直往下延伸至自我的处境、生活值得与否这样的话题,一系列“为什么”的提出,更是留下足以抹杀他所有希望的痛苦、厌倦乃至烦,似乎“绝望与临死的光景有相似之处”[3]。
然而加缪却如此认为,“可是在这里,我们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厌倦有益。因为,正是厌倦唤醒了意识,而一切又都始于意识,只有通过意识才有价值,我们正好可以粗略地辨识荒诞的根源,‘思虑’是一切的初始”[4]。世界给予西西弗肉体上显而易见的规定、限制到感官意识到自己的离异状态,意识到生活显而易见的荒诞、无意义,这就是意识对荒诞的揭示和发现作用。这种源于意识运动所引起的厌倦、烦成为了荒诞的发现和意识的觉醒,这在“荒诞的推理”部分加缪就有明确指出。虽说荒诞的产生更多关涉到的是主体与对象、理想与现实的相互关系,但不管是“荒诞的发现”还是“荒诞的结果”皆是由于主体的意识才成为可能。换言之,所有关于这个世界的荒诞感和西西弗最后的抗争、胜利都无法脱离主体的意识,尽管荒诞可能取决于意志的反面。
意识的运动使西西弗变得厌烦、疲惫,甚至感到那种强烈的陌生感和无力感。如果主体性丧失,意识不足够知觉到自己的境遇,他实际上不会感到痛苦。“如果他对这个世界仍旧是一知半解的话,那么就算西西弗用手指顺着起伏的地势摸遍整个世界,他也不见得能了解更多。”而人主体地位的无法获得、主体性的缺失显著表现为在对象化中人与世界关系、人类本质、类生活的异化。用马克思的话说“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5]。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的异化导源于劳动生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资本论》中都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详细批判了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资本与劳动的一致性——的虚伪和保守性,总结得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价值的获取和创造并非产生于劳动,而是产生于工人劳动的异化。工人生产物,却反过来被自己生产的物所控制和奴役,导致了人类本质的丧失,彻底沦为物的奴隶。原先的货币占有者凭借其占有的生产资料和优势地位在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同时也使自己转变成了资本家,通过工业革命、开辟全球性的贸易市场和扩大生产使更多数的人被限制和固定在工厂,逐渐沦为工人并长期处于赤贫状态,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一无所有。另一方面,分工和私有制作为分属同一活动的过程与结果使得最初的货币占有者或者资本家凭借资本的运动为自身带来了财富积累和支配的权利,生产分配活动、经济关系的不平等还衍生或造成作为实质的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力的不对等。由此,资本家与工人、资本与劳动构成了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手稿》《共产党宣言》中接续揭示和描述了“有产”和“无产”这两大阶级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最终目标,并呼吁和倡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私有制及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除了生产劳动的异化,人的主体性的缺失还表现在人与其类生活的异化,特别是人在异己环境下的被奴役和被支配状态。马克思阐释的异化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劳动的对象化以及其活动过程和结果,异化包括劳动的过程、产品、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其周围人关系的离异。而西西弗的异化则表现为普遍的个体与世界、理性思维与非理性命运关系的失衡和对立,用加缪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所生发出的对于统一性的渴望。可能正是因为人本身并不就是像动物那般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简单的直接同一,所以人并不以此为满足。恰恰相反,人总是试图依仗其理性对外部世界的掌握以获取某种确定性并进而规定自我及其生活,可生活非但未能如其所待,反而造成了普遍的自我限制和个性压抑。生活的异化必须在对生活的异化的扬弃当中得到解决。人作为现存唯一“思想的芦苇”,势必要求重新处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包括通过人自身的活动所建构起的那些作为规范而造成限制的原则、思维方式的反思,于对象、现实、客体中寻求和获得其主体地位,扭转对象化的状态,心灵也在这世界中寻求重新链接。
3 回到生存本身的体验
人与其生活的离异就像演员与其背景的离异,意识的觉醒——对荒诞的认识——使得在这种情况下,摆在西西弗面前有三条可供选择的道路。第一条毫无疑问是“生理自杀”,即消灭自己的肉体,毅然放弃生命。既然人的类存在本身是不可逆转的荒谬、痛苦和无意义的,可能的选择是把它从存在转化为不存在,诚然这是一种消极的逃避。即使西西弗成功地实现了肉体的消亡,最终的结果是他确实逃离了这个满是荒诞、无意义的世界(命运),但也因此失去了他作为人这种类存在物的价值和意义。加缪明确反对持这种思想,他认为“自杀作为一种轻视自己的态度”[1]49,实际是和哲学的“跳跃”那般采取默许态度,“它恰恰是反抗的反面”。第二条路“哲学自杀”,这是一种区别于肉体自杀的精神逃避,类似于逃避到理念、上帝和宗教那里,有选择的相信和放弃某些东西以获取力量的沉沦。试图凭借自由意志的选择寄未来以某种希望并为自身建构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式的存在以便超越生活并于其外部寻求主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获取扭转、应对苦难生活的斗志和方法。在这里加缪把哲学归咎为宗教相似的形态,认为他们在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加缪论述到它们(以往的旧哲学)借助理性的手段从荒谬的概念出发,把概念、原则当作绝对去规定外部世界,已然背离了生活本身。尽管他们也能得到生活荒谬的同样结论,但抛弃了感性体验的逻辑推理、纯粹思维的活动,不仅离开了荒谬产生的事实状态、主客体的关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存在,得不到新的东西,还将那些极力压抑他们的东西奉若神明,并且在抛弃他们的世界里寻找希望的理由,甚至教导、怂恿人逃离。其本质不过是新的宗教,只不过起主宰、决定作用的神由原来的上帝变成了新的理念、价值原则。加缪对荒谬的存在予以充分肯定并不代表他认同和默认它的为所欲为。加缪认为,“荒谬只有在人们不同意它的时候才有意义”[1]29,这种形而上学的反抗“实际上不过是确信沉重的命运”。西西弗毅然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即反抗。众神施加在西西弗身上不是一次简单粗暴的惩处,而是永恒的机械反复的无意义工作,是西西弗永远不能摆脱的命运,这是西西弗的世界之所以荒诞的根本所在。“而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1]119反抗绝非你死我活的斗争,更非要消除世界、命运之“荒诞”,而是在以生存本身为目的的反抗当中实现意义的创生和确立主体存在之唯一事实。“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我们还应强调方法:贵在坚持。”在西西弗回身走向巨石的时刻,巨石开始与西西弗融为一体,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变成属于西西弗的东西,他的命运开始由他创造。进而区别于那种精神的“跳跃”或肉体自杀。加缪在结尾说道:“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这种精神的可贵,在于不拔一毛以利永恒,而仅以生存本身、必须活着为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和人生根本旨趣。反抗而非消极的对待或寄希望于来世、未来,寻求虚假空洞的乌托邦,因它抵不过活在当下真实的生活。加缪和萨特都在基于生活的荒诞开始对生活及其意义进行思索,然而,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萨特认为荒诞的世界对肉体的百般刁难、限制,并不能阻止意识作任何自由的选择和决定,“我的未来就是处女般未破损的,它为我允诺一切”。除了两人在政治路线方面的差异,萨特还在自由意志和责任的权衡当中,认为人的存在先于他的本质,经由自由选择人可以实现自己,并对未来抱以希望和充分肯定。“自由作为一个人的定义来理解,并不依靠别人,但只要我承担责任,我就非得把别人的自由当作自己的追求不可。”而加缪则更突出荒诞命运的无解并通过“反抗”造成的可以表达主体存在的意义和所能获得的唯一明显事实以实现对生活的胜利,“对荒诞人而言,问题不再是解释和解决了,而是体验和描述了。一切以英明的无动于衷开始”。通过驻足山脚和回到巨石的活动,加缪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关键是不抱希望,为了“希望”而生活,也只会给自己树起栅栏。这有悖常理的思维态势恰恰表达了荒诞人对荒诞的直面和反抗,最强有力的反抗也就是不为生理的和哲学的躲闪,也不为某种希望囚困和羁绊,而是仅为“生存本身”。值得庆幸的是,时隔多年,余华《活着》显露了同样的世俗奇葩,“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单向度的人及其活动的结果——内卷与躺平——是作为异化了的人和生活本身,是膨胀或猥琐、压抑了的意志(欲望及其实现的行为冲动)的盲目、极端安放,是建构于各式精美包装盒下的消极自我限定。这种奠基于犹太精神以货币、商品消费为其全部活动最终目的的价值趋向,向社会的各行各业、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必然导致人陷入消费主义陷阱、商品和货币拜物教的漩涡,造成更深层次、多重维度的荒诞和异化。
正如加缪所表达的那样:“一部作品的结尾已经蕴藏在开头里面了。”《西西弗神话》首页的诗句“吾魂兮无求乎永生,竭尽兮人事之所能”已经为这本哲学随笔的精神主干定了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并回到生活本身的体验使得荒谬人有可能从容应对甚至胜任任何一种形式的任务、工作、生活。更不必说从容应对已经内嵌于生命内部而必须面对的最后一块“巨石”,人一切荒诞和无意义的根本源头——死亡。可以想象,当一个被判永久监禁的人失去了除了监牢生活外的其他一切可能的生活形式,而不得不在这个狭小空间度过余生时,他可能感知到漫无天日的荒诞、孤独厌倦甚至痛苦,也可能完全享受这种足以支撑他长时间独处的闲暇氛围。西西弗成了自己生活的主人。加缪指出,在巨石与西西弗融为一体,使岩石成为他的一部分的时刻,命运是属于他的。按常理来说,冲出众神对他的限制,改变搬石上山的命运才是真正的胜利。尽管西西弗始终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说他的行动并不足以改变他的命运,每天仍旧在不断地面对荒诞命运即众神施与他的惩罚——推石上山。但若把众神对西西弗的惩罚看作死亡的必然,西西弗的所作所为似乎又是适宜的抉择。一切虚幻、美好的“镜子”都已破碎,唯有反抗(重新走向巨石的活动)是主体存在的意义和所能获得的唯一明显事实,正如加缪在《反抗者》引言部分描述得那般:“我反抗,故我在。”这显然和加缪在《局外人》中表达的那种纯粹的无能为力不同。面对母亲葬礼、女友求婚、死刑庭审,主人公默尔索有的似乎一直是被社会伦理、法律与价值规范等肆意左右的麻木、无动于衷,即便有意识的觉醒(对荒诞的认识)与不服从荒诞命运的安排,回归生活的反抗也因生命终结而抱憾;而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则更进一步阐释了其人道主义的思想,着重关注生存本身及主体存在的意义,而反抗就内在地含于生存的目的论当中,借反抗表达主体存在的意义和所能获得的唯一明显事实。反抗与其说是意识的、对立形态的斗争,毋宁说是关涉于生存实践的辩证法。这种生活的智慧在里厄医生(见《鼠疫》)那里被应用得更加炉火纯青,表现得也更为显著和突出。
4 结语
加缪通过笔下的西西弗,以荒谬为底色表达“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谬最有力的反抗”的理论内核和实践命令。虽然西西弗无数次的努力最终还是没能摆脱这荒诞重复的命运,但却将枯燥、无聊的惩罚变成了自由的事业和永恒的创造,并且传递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没有鄙视征服不了的命运”。向死而生,尤其是在饱受生活世界的荒诞、苦难之后,依旧能够怀揣对这世界原初的和最后的爱,这是西西弗精神的伟大之处,是导源自真正生活的荒诞的英雄主义。在荒诞的沙漠中开出自由、幸福的花朵,西西弗最有力的反抗和向上的行动富有意义正是源于重新走向巨石的活动。此外,加缪给予荒诞以充分确信背后乃是肯定荒诞的存在而非荒诞本身,反抗也不意味着你死我活的绝对对立和推翻,不是为了消除世界与命运之荒诞,而是通过意识的能动性把那些招致人死亡的东西转化为生活的规则,以及回归生活,使原本与主体对立的事物,如荒诞和死亡,与之达到微妙的和谐。会万物以成己者,实乃现实的生活辩证法。
加缪深受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追捧和欢喜,盖缘其哲学非是康德式的形而上学晦涩体系,而是扎根于现实生活世界的切实感言。诚然,时代的满目疮痍与个人的诸多悲惨境遇(贫穷、疾患缠身、婚姻受挫、无处容身、死亡威胁等)以及其老师格勒尼埃(特别是其《岛屿》一文)的影响,塑造了后来这只来自贫民窟的“高卢的雄鸡”。譬如对待贫穷,加缪虽然并不痛恨,但他仍旧坚持认为“贫穷让我相信并非一切都是美好的”。正是这种来自真正现实生活世界的人的荒谬与痛苦,使得他能够以更加细致的眼光审视和反思这个时代重大的基本问题。西西弗朝向众神的呐喊,毋宁说是映射了加缪本人向同时代的广大民众对生活、命运的不懈反抗和坚持的呼吁。始终根植于以生存(生活)本身为目的既重新建构了新的生活准则,也潜在地涵摄着对这世界原初的和最后的爱,带着病痛活下去的结果就是“而阳光又告诉我,历史并非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