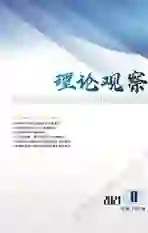我国离婚现状及对策研究
2021-12-08龙剑兴陈霖王玉学
龙剑兴 陈霖 王玉学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婚恋观;離婚;家庭
中图分类号:C91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8 — 0109 — 05
一、现阶段我国离婚现状
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而婚恋观的变化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我国的结婚人数不断减少而离婚人数却在逐年增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如表1所示),结婚登记数量自2013年呈下降趋势,数量由1346.9万对下降到2020年的814.3万对,而离婚登记人数从2013年的350万对,上升到2020年的433.9万对,且2019年离婚人数高达470.1万对。由表1可以看出,结婚率年年创新低,而离婚率却不断上升,离结率更是年年创新高。离结率从2013的25.99%上升为2020年的53.29%,这就意味着2020年每2对新人选择结婚的同时至少有1对旧人选择离婚。
另一方面,由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发布的《司法大数据离婚纠纷专题报告》显示,婚后2-7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而婚龄在3-4年的离婚人数最多,婚姻的持续时间在不断缩短,传统意义上的“七年之痒”逐渐发展为“三年-四年之痒”。离婚率的不断升高与婚姻持续时间变短显示了当代青年对待婚姻的态度不如以往谨慎,“闪婚”、“闪离”现象逐渐增多。因此,从马克思恩格斯婚恋观视角深入分析我国现阶段婚姻家庭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有助于从源头上解决当前婚恋中存在的问题,促使婚姻不断朝着“高质量、高稳定”方向发展。
二、我国离婚率不断上升的原因分析
离婚率的不断升高和婚姻持续时间的减少是受到社会、家庭、个人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一)从社会层面分析,受到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及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爱情应该是婚姻的基础。因而忽视双方的感情基础,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同时也具有不稳定性。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趋利性导致拜金主义盛行,也深深影响和改变着新一代青年的择偶观。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婚姻由以爱情为基础转变为以经济为基础,金钱的地位被空前地放大,青年一代在择偶时更加注重功利性和实效性,择偶观、婚姻观日趋功利化。择偶观的功利化使得部分女性想通过婚姻这一途径跃入豪门,对物质生活的渴望往往取代了对爱情的追求。这就导致了如今人们常会把爱情物化为各种经济指标,如户口、房子、车子等,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情感因素所占的比重逐渐被经济因素所取代,婚姻充满世俗性。有学者指出,“女性如今所关注的并非是男性的目光,她们关注的是社会的价值以及男性衣袋里的金钱。”〔2〕而以经济为基础缔结的婚姻其实质是物化的婚姻,是一方对另一方依附的婚姻,是极不平等的婚姻,具有不稳定性。

另一方面,受西方享乐主义、纵欲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变,在对待婚姻的观念上表现为更加注重个人感觉,过分追求个人自由与享乐。中国古代封建礼教“男女授受不亲”等思想逐渐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性解放”、“性自由”。在这种腐朽的思想的影响下,性道德观念和家庭观念被逐渐淡化,一方面,婚前性行为变得更加随意,婚前同居、未婚先孕,因怀孕而草率结婚的现象也逐渐增多,严重影响了婚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婚内出轨现象激增,婚姻忠诚度降低,“一夜情”、“包小三”等现象层出不穷。同时,在价值观的多样性和社会舆论环境的开放性的影响下,人们对待离婚的态度比以前更为宽容。在这种大环境改变的背景下,在面对配偶的不忠时,大多数人由以往迫于舆论压力而选择默默忍受转变为如今的果断离婚,这也是对以往“低质量、高稳定”婚姻模式的一种反抗。
因此,在市场经济趋利性及西方不良文化的影响下,以金钱等物质条件为基础而缔结的婚姻根基是不牢固的。同时过分追求所谓的“性自由、性解放”,导致婚姻的忠诚度不断降低,最终造成婚姻破裂。
(二)从家庭层面分析,受到家庭地位不平等及受原生家庭结构的影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2017年度140万起离婚纠纷案做了统计显示,家庭暴力是造成夫妻双方离婚的第二大原因,且90%以上都是男性对女性进行的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实质体现出夫妻在家庭地位中的不平等,是强势一方轻视或虐待弱势一方。恩格斯指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完全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结果。”〔3〕“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始分工模式源于男女性的生理差异,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使得私有制随之产生。男性由于参与社会劳动而获得经济回报,而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由于不产生剩余价值,家务劳动最终脱离社会劳动,变成女性在家庭内部的专门工作。家庭财富的积累使得男性在家庭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女性逐渐成为被奴役的对象。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4〕随着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走向了职场,投入到社会劳动中。这就使得女性实现了经济自由,同时也具备了摆脱丈夫和家庭的控制的能力,而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女性的社会及家庭地位不断提高,也使得其在婚姻关系中越来越具有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想要改变“男尊女卑”不平等的婚姻关系的欲望就愈强烈,这就有了当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时,由默默的忍受转变到选择离婚。
另一方面,家庭结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婚恋观。一个在幸福完整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和一个在离异家庭长大的孩子所形成的婚恋观是不一样的。有研究表明,经历过父母离婚的孩子在长大结婚后,会比关系融洽的家庭的孩子更容易经历离婚。〔5〕家庭的氛围和结构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婚姻观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完整且幸福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对婚姻普遍持有积极的态度,反之,在父母经常吵架或在单亲家庭或重组家庭长大的孩子对婚姻普遍持有消极态度。这种消极的态度也会被无意识地带入他们的婚姻生活,严重影响其今后的婚姻质量,低质量的婚姻进一步提高了离婚的概率。而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离婚率就开始不断上升,单亲家庭或重组家庭长大的孩子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由于经历了从父母的争吵不断到离婚的全过程,长大后这部分孩子对待婚姻一般都是持有消极的态度,而一旦他们的婚姻出现问题,他们会效仿父母的行为,把离婚当作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而不是坚持努力解决问题。在此背景下,他们做出离婚的选择会比他们的父母更果断而又显得更随意。
因此,在追求效率最大化及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在受到家庭暴力以及受到原生家庭结构的影响下,人们会把离婚作为解决问题最快且最优方式。
(三)从个人层面分析,受到“三观”不合及个人的任性的影响
根据《司法大数据离婚纠纷专题报告》显示感情不和是造成离婚最重要的原因。而“三观”不合是造成感情不和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相比于传统社会,人们的活动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就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多的依赖于家庭之外的世界,促进了个体化的加深。同时,夫妻双方由于生理特性的差异、原生家庭的差异、接受教育的差异等,也就很难以形成一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三观”不合及个体化加深的共同作用下,传统社会所提倡的个人的自我认同要服从家庭的认同的观念也逐渐瓦解。由此,夫妻双方的行动取向就变得越来越追求自我需求的满足与自我价值的实现。“个体化等多种因素使家庭关系与共同生活方式变得松散和不稳定。”〔6〕过去强调个体行为应屈从家庭需要的模式已逐渐减弱,如今强调的是家庭应满足个体的需求。一旦家庭满足不了个体的需求或抑制了个体的发展,家庭就有濒临破裂的危险。在这种“三观”不合与个体化不断加深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很容易会忽略夫妻一体的真理,而过分强调自我价值。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在《婚姻的意义》一书中说,我们忽略夫妻一体的真理,使配偶无法看到他们在我们眼中的价值,当我们将本是一体的夫妻关系一撕两半,各自以自我为中心生活时,我们就会变得没耐心,容易发怒,讲话刻薄,缺乏恩慈,嫉妒,怀怨,而对方也以同样的自我中心来回敬我们,夫妻关系就开始螺旋式下降,最终在自怜、愤怒和绝望中,感情被消磨殆尽。〔7〕夫妻双方在日常生活接触中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会由于在处理这些琐事的过程中总会不自觉地强调自我的感受,以自我为中心,忽略对方的感受,从而引发更多的矛盾,影响夫妻双方的感情。
另一方面,在“三观”不合及个体化不断加深的前提下,夫妻双方在为一些生活琐事发生争吵时,在互不相让的情况下,由于一时生气很容易做出离婚的决定。一言不合就离婚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对待婚姻的态度呈现出儿戏化的趋势。马克思指出:“谁随便离婚,那他就肯定任性,非法行为。”〔8〕这表明马克思虽然承认离婚自由,但他反对草率离婚。夫妻双方为一件小事争吵或意见不合,一时冲动而选择离婚,是极不理智的,也是对待婚姻及家庭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同时也显示出我国的婚姻法对于离婚过于宽容,婚姻调解力度不强。
因此,在“三观”不合及个体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再加上夫妻间的任性,离婚制度的过于自由,推动着离婚人数年年创新。
三、降低我国离婚率的对策
解决离婚率不断升高的问题,需要从个人观念的转变,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及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等方面着手。
(一)树立马克思恩格斯婚恋观
首先,抛弃功利性的择偶观。恩格斯指出:“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9〕因此,恩格斯认为,爱情应当成为婚姻的基础,而非除此以外的物质条件。婚姻缔结动机不纯,往往是由于夫妻双方或一方没有树立正确的择偶观,把婚姻当成改变命运的途径,希望通过婚姻一劳永逸地抵达幸福。功利化的婚姻缺乏一定的感情基础,通过一方对另一方的依附以实现经济自由,从而获得幸福的生活是不具有持久性的。只有抛弃功利的择偶观,树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才能持续把对方的幸福放在自己幸福之前,对方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从而大大增强婚姻的幸福感和稳定性。其次,恋爱要保持理性。在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下,性道德观念逐渐淡化,“偷尝禁果”、未婚先孕而草率结婚现象突出。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谦恭甚至羞涩的态度,而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应该在考虑结婚以前成为一个成熟的人。”〔10〕因此,在恋爱中保持理性,在我们还没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之前,避免过早发生如婚前同居等亲昵行为。我们可以以马克思和燕妮为榜样,通过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把过早的亲昵行为转化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目标。通过增加精神上的交流,深入了解彼此,在恋爱中把握爱的尺度,真正理解爱的本质。最后,正确对待婚姻的挫折。马克思指出:“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11〕马克思认为真爱的道路是曲折且不平坦的,而婚姻关系也一样。正确看待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挫折,用积极的心态迎接各种挑战并做好长期应战的准备。例如:在2020年春节期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病毒在全国蔓延,全国大范围内停工、停产,实施居家隔离。停工停产带来的“家庭经济危机”,居家隔离带来的“情感危机”无一不对婚姻家庭带来巨大的挑战。在面对突发事件给婚姻家庭带来的挑战,我们要正确看待由此而产生的婚姻家庭矛盾,以理解包容的心态对待另一半的缺点。正如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婚姻的道路也絕非平坦,正确看待婚姻中的挫折,有利于婚姻的可持续发展。
(二)构建和谐的家庭
首先,要建立平等的家庭关系。自封建社会以来,男性以及社会用“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同化女性,并且将这种封建思想进行代际传递。〔12〕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在家庭生活中很容易造成女性的压抑和男性的异化。马克思指出:“现代一夫一妻制家庭,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达到更高级的阶段,在那个阶段上的道德特点,将是达到真正的‘两性间的平等。”〔13〕在马克思看来,两性平等必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对于两性平等,恩格斯指出:“在结婚同居期间,双方在相互关系中必须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14〕平等的权利与平等的义务具体表现为对于子女的教育、老人的赡养、家务劳动等多个方面夫妻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共同承担,对于重大事情的决策拥有同等的话语权等。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家庭关系才能拥有和谐稳定的家庭生活。其次,加强家庭教育,建设良好家风。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此,在家庭教育中父母要发挥好榜样作用。父母恩爱,家庭和谐,有助于孩子形成正确的婚姻观,而父母婚姻关系不和谐,天天吵架,甚至父母一方有家暴行为,或父母离异等,很容易造成孩子形成扭曲的婚姻观,出现恐婚、不婚或离婚的概率会更大。所谓“身教胜于言传”,因此,父母要以实际行动向孩子传递正确的婚姻观。同时,建设良好的家风。在家庭生活中要营造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以及民主平等良好家庭氛围。家风建设好有利于家庭和睦,促进家庭的发展,有利于孩子形成正确的婚姻观,也有利于孩子长大组建家庭后家风的建设,使这种良好的家风得以代际传递,不断提高婚姻家庭的幸福感。最后,加强沟通,增强家庭责任感。沟通是化解矛盾的桥梁,因此,在产生矛盾时,夫妻间加强沟通。在进行沟通时要学会去除个体中心主义,尝试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争吵,促进夫妻间的有效沟通,达到化解矛盾的目的,不断增加家庭的幸福感。同时,在如今个体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闪婚”、“闪离”现象越来越常见,大多数人宣称结婚、离婚是对自身自由幸福生活的追求,他们更多的是关注个人的幸福与否,是出于个人的任性,而缺乏对家庭的责任感。马克思指出,“谁也没有被强迫着去结婚,但是任何人只要结了婚,那他就得服从婚姻法......所以,婚姻不能听从已婚者的任性,相反地,已婚者的任性应该服从婚姻的本质”〔15〕。一段婚姻的解散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离散,对家庭成员特别是未成年子女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因此,夫妻双方要增强家庭责任感,正确看待离异后对家庭成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婚姻可以离异,但不可任性。
(三)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婚姻稳定,家庭幸福的重要条件。首先,要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对我国的婚姻家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趋利性和平等性是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两大特征,而趋利性是造成婚姻观扭曲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通过弱化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功能,强化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功能以此来潜移默化地纠正人们的婚姻观。例如在就业市场上给予男女性同等的发展机会及薪资待遇,让女性在劳动市场上能够依靠个人努力实现经济自由和人格独立,从而摆脱对男性的依附,使女性从思想上改变“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扭曲的婚姻观,促使婚姻朝着“高质量、高稳定”的方向发展。其次,要建立合理的评价系统。在市场经济趋利性的影响下,经济条件成了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指标,评价指标逐渐单一化,物质化,这也是造成婚后夫妻双方感情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建立合理的评价系统,一方面,评价指标应该是多元化的,而非简单的“唯金钱论”。且每种指标所占的比例应该是合理的,情感因素理应作为首要的评价指标。另一方面,真善美应该成为评价的重要指标。再次,要加强文化自信教育。我们之所以被西方、“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等腐朽文化思想所左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中华文化还不够自信,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在我們的传统文化中,虽然我们常会强调“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腐朽的婚姻家庭观,但也不乏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积极的婚姻家庭观。儒家婚姻观认为婚姻具有神圣性,这也保证了婚姻的命定性、道德性、稳定性和持久性。〔16〕因此,我们要加强文化自信教育,提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人民群众的认知度、认可度。从而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明辨是非的能力,自觉分辨并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自觉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从而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最后,加强婚姻调解力度。面对如今的离婚现状,可以通过加强婚姻的调解力度来缓解夫妻间的关系。在离婚冷静期制度设立的基础上,建立“感情破裂”的指标体系,同时加强在离婚冷静期期间的调解力度,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任性而离婚的案件。
综上所述,要降低日趋上升的离婚率,个人、家庭及社会要形成合力,从多个方面着手。通过树立马克思恩格斯婚恋观、建立和谐的家庭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方式等方式来降低离婚率,建立稳定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
〔参 考 文 献〕
〔1〕2013年-201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BE/OL〕.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官网,http://www.mca.
gov.cn/article/sj/tjgb/,2021-04-26.
〔2〕殷国明.女性诱惑与大众流行文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82.
〔3〕〔4〕〔9〕〔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6,88,96,84.
〔5〕Gharaibeh Fakir M.Al. The Effects of Divorce on Children: Mothers Perspectives in UAE〔J〕.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2015,(56):347-368.
〔6〕薛红.在个体化浪潮之中的性别身份和婚姻家庭——贝克的《风险社会》中的性别和婚姻家庭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2001,(03):88-92.
〔7〕提摩太·凯勒.婚姻的意义〔M〕.上海:三联书店,2015:53.
〔8〕〔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83.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0.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9.
〔12〕李庭.从“两性平等”到“两性和谐”〔D〕.长春:吉林大学,2020.
〔13〕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45-46.
〔16〕孙长虹.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平衡——儒家婚姻观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05):14-19.
〔责任编辑:孙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