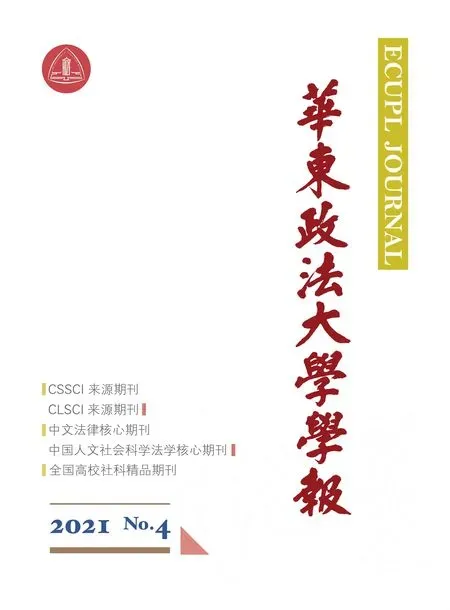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害人权利保障
2021-12-08王静
王 静
一、问题意识:认罪认罚改革与被遗忘的被害人
“认罪认罚从宽”乃决策层在我国刑事诉讼“案多人少”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制度设计与法治命题。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办案机关对所有案件皆适用“完全式”的刑事诉讼程序,既在制度设计上显得不经济,实践层面亦无可能达致。为了维持刑事司法系统运转、最大限度实现追诉犯罪之效益,采取“抓大放小”的制度建构策略,实乃当下刑事司法改革之应然路径。其中,“抓大”意指对重大案件、疑难复杂案件适用完整的诉讼程序,不仅侦查、审查起诉程序须做实做足,更应提高审判尤其是庭审程序的实质化程度,这便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面向;“放小”意指对轻微案件、被告认罪的简单案件采较略式程序,“尽可能地争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作,降低办案中的对抗强度”〔1〕秦宗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疑难问题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 年第3 期。,节约资源以供给“繁案”之实质化处理,此即为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刑事简化程序的目的。
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言,其之所以能够发挥资源节约的作用,无外乎因两方效应所致:其一,被告认罪认罚与检察机关签署具结书,有效减轻了控方的证明责任,使其不再将过多精力耗费于取证等环节;其二,认罪认罚随附程序分流之效果,通过适用速裁与简易程序,审判阶段亦因流程简化而节约司法资源。不过,制度运转并非徒法自行,法制改革向来都是价值权衡,认罪认罚从宽亦如此。理论上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取向与运转逻辑在于以从宽处理换权利放弃、以权利放弃换办案效率,即通过从宽处理引导被告认罪认罚,使其自愿放弃“如法庭调查与辩论等诉讼环节的诉讼权利”〔2〕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16 年第2 期。以及“获得无罪判决的机会”〔3〕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载《法学研究》2016 年第4 期。的实体权利,继而以此实现程序分流、效率提高、资源节约的效果。
虽然理论界大多以上述制度运转逻辑论证认罪认罚从宽之适当,但深究之,该逻辑仍存在明显疏漏——被害人被遗忘了。一方面,制度设计未妥善考量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运行可能导致的权利减损影响了诉讼程序的合法性。换言之,因流程简化所得诉讼效率之提高不仅需要被告放弃部分权利,同为诉讼当事人的被害人之权利让渡亦为其要素,在被害人未放弃任何权利的情况下,若仅因被告认罪产生程序简化并致被害人权利减损,显然缺乏相应法理依据。另一方面,缺乏被害人因素的从宽处理,其正当性颇显不足。学界大多概括认为,对被告从宽处理之依据在于其“认罪认罚”,即“通过程序的进一步简化来达致诉讼经济,并以此作为从宽的依据”〔4〕郭烁:《层级性:认罪认罚制度的另一个侧面》,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2 期。,但该观点实难证成。就结论言,认罪认罚可以获致的从宽处理,不论是报应刑减让还是预防刑减让,皆须在被害人参与的情况下才可能实质发挥制度的应然效果,而国家单方面对被告的从宽处罚应仅限于较窄之范畴内。
根据我国刑事司法的基本经验,仅仅重视被告人的自愿认罪和宽大处理,而无视被害人的诉讼请求和实体权益,这是根本行不通的。〔5〕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载《当代法学》2016 年第4 期。更明确地说,被害人在认罪认罚制度中的参与殊为重要,其不仅构成程序适用与从宽处理的正当性依据,更是纠纷解决、社会关系恢复之基础与核心。现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既导致了制度理论层面的疑难,也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涉诉信访等诸多问题。本文拟从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害人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入手,继而检讨现行制度下被害人权利保障之缺陷,最后提出完善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害人权利保障与有效参与之可能路径。
二、被害人权利保障之于认罪认罚制度的意义
现代刑事司法体系建立以来,被害人之地位似乎已越发次要,但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被害人却毫无疑问是国家追诉的主要权力来源与正当化根据。在“公共司法”时代的前期,由于国家权力欠发达,对犯罪人的追查通常只能由被害人自己完成,国家的追诉权往往只是一种象征,它隐藏在被害人身后,依靠被害人。被害人有权(或者说有某种义务)去追查并捕获犯罪嫌疑人,有权选择是否要求公权力介入,是否动用私刑。随着治理技术的发展,国家垄断了刑罚的权力——私刑被视为非法,除少量自诉案件外,刑事追诉权不再赋予被害人。在整个追诉期间,被害人更多地被视作司法权力的工具,仿佛仅为了证明加害人有罪而存在——犯罪被认为是公益之侵害,被害人被国家所代表。但不容否认,国家追诉原则源于被害人对国家的授权,即将自我防卫与复仇的权利让渡给主权者,由国家向犯罪者进行追诉。〔6〕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131-132 页。基于社会契约,对于存在被害人的案件,国家追诉行为的本质为代理,程序运行与刑罚执行皆以被害人为重要合法性来源。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程序参与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反过来说,被害人之权利保障也应为包括认罪认罚在内的诉讼制度设计必须考量的因素。〔7〕See Douglas Evan Beloof,“ The Third Model of Criminal Process: The Victim Participation Model”, 1999 Utah Law Review 289, 293-298(1999).
(一)作为程序正当性来源的被害人权利保障
被害人权利保障乃诉讼程序的正当性来源之一,缺乏被害人参与或损害其权利的程序,无论在追诉犯罪上多么有效,亦难被视为正当。按照正当程序的要求,与程序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均有权参加该程序并得到提出有利于自己主张的机会。〔8〕参见[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1 页。作为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其权利应得保障与恢复,这是刑事司法必须完成的任务。一方面,犯罪之处理应使被害人获得感情上的恢复,其主旨在于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应当有效保障被害人获得物质与精神上的赔偿,其既是恢复法益之前提,也应被视为最基本的正义。〔9〕反过来看,如果刑事司法未能有效保障被害人权利,则又将造成对被害人的“二次侵害”。See Douglas Evan Beloof,“ The Third Model of Criminal Process: The Victim Participation Model”, 1999 Utah Law Review 289, 294(1999).申言之,为了恢复被害人被犯罪侵犯的实体权利,就应当充分赋予并有效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使其成为实现此目的之手段。
从刑事法制的发展来看,我国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越发重视。1979 年《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定位为“诉讼参与人”,而1996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则将被害人提高到“当事人”地位。2012 年《刑事诉讼法》新增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并明确了审查起诉中被害人提出意见权,进一步保障了被害人权利、彰显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然而,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设计却一反上述法治路径,其对被害人权利之保障缺乏应有的重视,而这集中体现于程序分流机制中。在认罪认罚改革中,决策者更多地强调认罪认罚的程序分流功能,将其作为缓解“案多人少”矛盾的对策。〔10〕参见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载《法学》2016 年第10 期。基于效率价值的导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程序简化分流机制实际上处于某种“捆绑状态”,即“以从宽促认罪”“以认罪致分流”。但应当注意的是,程序的简化不仅限制被告权利,也会限缩被害人的权利。作为一项诉讼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必须在既有的诉讼权利体系下运转,程序分流所需的授权或弃权应由涉及的每一权利主体自愿作出。质言之,程序分流关乎被害人诉讼权利之实现,不应排斥或虚化其参与,否则制度的正当性便存有疑问。
(二)作为从宽合法性依据的被害人权利保障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从宽既是促使被告认罪认罚之前提,也是被告认罪认罚意欲达成的结果。对被告从宽处理的许诺与决定看似仅为司法机关之权力范畴,但事实上,对有被害人的案件而言,缺乏被害人参与和同意的从宽处理,则可能存在合法性依据不足的问题。换言之,制度设计欲在从宽处理上证成应然之合法性并取得跨越式发展,就必须重视被害人权利保障与程序参与。
探讨从宽处理与被害人之关系,首先有必要厘清“从宽”本身的概念范围。学界对从宽一般作两方面解读,即实体从宽与程序从宽,前者不难理解,而后者则主要体现为侦查机关变更、解除强制措施,检察机关可以适用不起诉或者向法院提出认罪认罚从宽的量刑建议等,〔11〕参见陈光中、马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探讨》,载《法学》2016 年第8 期。甚至,适用简化之诉讼程序也被视为从宽的范畴。〔12〕参见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16 年第2 期。但深究之,所谓程序从宽皆不是实质意义上的“从宽”:其一,程序简化并非从宽,其适用乃因当事人自愿放弃程序权利的一般性后果,若将之视为从宽,那么为何禁止对应普遍从宽处理的未成年人适用“程序从宽”之速裁程序?其二,强制措施之适用仅关涉被追诉人之社会危险性,〔13〕参见聂友伦:《检察机关批捕权配置的三种模式》,载《法学家》2019 年第3 期。之所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可能产生变更、解除强制措施的效果,乃因被告在认罪认罚后社会危险性降低使然,绝非认罪认罚制度本身应有的内涵。其三,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或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与程序并无关联,皆为实体层面定罪量刑之从宽。认罪认罚从宽本质上乃一种刑法规范,“从宽”亦仅为在定罪、量刑、行刑上的一种宽缓处置,〔14〕参见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载《法学》2016 年第10 期。它自身并无程序范畴内的意涵。
实体从宽,在大多数刑事案件中,其指向皆为量刑之从宽,即以法定刑为基准对被告从轻、减轻处罚。就量刑理论而言,报应的正当性和预防犯罪目的的合理性是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其中报应刑属于责任刑,而基于预防犯罪目的所裁定的刑罚属于预防刑。〔15〕参见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载《法学》2016 年第10 期。量刑从宽,不论责任刑从宽还是预防刑从宽,皆应引入被害人因素。就责任刑论,其源于“被害报应”,即犯罪使被害人遭受了具体损害,刑罚作为这种损害的代价或者补偿而具有正当性,〔16〕参见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6 页。若被告有效赔偿、取得了被害人谅解,作为结果的责任因素得以减少,因而降低了被告责任,应予在责任刑范围内从宽。对预防刑而言,被害人参与能够使司法机关充分了解案件情况与被告个人情况,〔17〕例如,对未成年人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的,检察机关应当听取被害人意见。立法机关工作部门指出,该规定的意义在于充分了解案情与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从而判断不起诉是否合适。参见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新华出版社2012 年版,第472 页。从而在预防必要性范围内准确裁量预防刑。因此,积极保障被害人权利,使其有效参与量刑协商或法院量刑过程,既可为量刑准确性提供标尺,更是量刑从宽的必要合法性依据。
(三)作为权力制约要素的被害人权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点位于审查起诉阶段,被告认罪、量刑协商、程序选择与具结书签署等核心程序皆集于此,后续审判阶段的主要内容仅为形式上确认被告认罪的自愿性与具结书内容的真实合法而已,最终判决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可以说,在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中,检察机关已事实上从以往侦查与审判之间的“二传手”变为了整个诉讼程序的主导者——不但负责与被告协商,最终的定罪量刑也基本由其决定——这极大扩张了检察机关的权力范围。〔18〕就检察官的裁量权而言,认罪认罚与辩诉交易对其存在相似的扩张效应。See Donald G. Gifford, “Meaningful Reform of Plea Bargaining: The Control of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1983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37, 40(1983).
检察权扩张的同时必须有相应的制约机制跟进,否则难以杜绝权力的滥用。〔19〕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载《法学研究》2016 年第4 期。普通刑事案件的办理存在一系列司法制约机制,审查起诉受审判制约、审判受抗诉与上诉制约,如此一来,权力滥用和司法腐败的成本实际处于较高水准。举一个可能不甚恰当的例子,若被告人欲逃避罪责,在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必须与承办检察官、法官都形成非法联系,否则很难达成其不法目的。但在认罪程序中,被告只需勾结承办检察官,非法具结认罪认罚协议并获得非法之从宽建议,大体就能实现目的——司法腐败的成本大大降低,此时若不引入有效的制约机制,司法制度可能存在极为严重的腐败隐患,同时也将极大地侵害被害人权利。
根据域外国家的相关法治经验,将被害人纳入认罪程序之设计,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检察权制约的效果,乃一条较为普遍的实践路径。如美国,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检察官在依法作出重大决定,包括达成答辩协议时,应通知被害人并征求其意见。若被害人强烈反对答辩协议之内容,法院必须允许被害人出庭并当庭发表其反对意见。〔20〕参见[美]伯恩敬:《“交易”还是“协议”—— 一个美国检察官眼中的辩诉交易》,载《法学》2008 年第7 期。德国法的强制起诉程序与日本法的准起诉程序更是赋予了被害人在检察官裁量不起诉后直接申请法院裁决之权利。〔21〕参见万毅:《刑事不起诉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04 年第6 期。此外,当案件进入审判阶段时,被害人的参与既能够帮助法官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审查判断被告人是否在自愿的基础上认罪认罚,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检察机关的恶意指控。〔22〕See Paul Cassell, “The Victims’ Rights Amendment: A Sympathetic Clause-by-Clause Analysis”, 5 Phoenix Law Review 301,(2012).总之,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引入被害人参与、有效保障被害人权利,不仅能够对可能的司法腐败产生制约作用,更是保证司法权力行使正当性的必要因素。
三、认罪认罚制度中的被害人权利:现状与困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2016 年9 月试点以来,支撑试点运作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两高三部”制定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等。时至今日,2018 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上升至法律层面,“两高三部”亦出台了旨在指引司法实践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围绕上述规定,对制度设计关于被害人的内容进行梳理与分析,乃探讨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的前提。
(一)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制度内容
就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制度内容而言,上述规范之规定包括: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将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退赔与取得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的考量因素,禁止民事赔偿事项未达成协议的案件适用速裁程序。虽然相关规定内容有限,但仍在理论与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分述如下:
其一,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保障了被害人对认罪认罚制度一定程度的参与。《试点办法》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意见”,在《刑事诉讼法》中,所听取的意见被明确为“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认罪认罚后案件审理适用的程序;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事项”。《指导意见》延续了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不论是认罪认罚、从宽之事项,还是程序选择的内容,被害人均可向检察机关提出意见,检察机关应当听取,其乃对被害人知情权与程序参与权之保障。
其二,将被告退赔与获得被害人谅解情况作为量刑的考量因素,使量刑从宽具备一定的合法性依据。《指导意见》规定:“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与被害方达成和解协议、调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方损失,取得被害方谅解,作为从宽处罚的重要考虑因素。”量刑从宽是从宽的实质内容,若被告不积极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其量刑从宽仅应限于如自首、坦白等法定降低预防刑的情节,〔23〕参见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274 页。所获之量刑减让程度有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要求的从宽,其意义在于通过扩大原有从宽之幅度,以鼓励被告认罪认罚,这就必须纳入被害人因素,使得量刑之进一步从宽获得合法性。
其三,禁止民事赔偿事项未达成协议的案件适用速裁程序,事实上部分赋予了被害人程序选择权。《刑事诉讼法》与《指导意见》皆规定,若“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不适用速裁程序”。实践中许多检察人员出于办案效率的考虑,认为应取消“未达成和解”这一禁止性条件,但却显然未考虑到被害人参与的因素。〔24〕参见李本森:《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研究报告——基于 18 个试点城市的调查问卷分析》,载《法学家》2018 年第1 期。正当程序禁止排斥被害人参与,一般而言,被害人不参与诉讼程序须以主动、自愿放弃权利为前提。速裁程序作为目前刑事诉讼中最简化之程序,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仅保留了听取辩方意见与被告人最后陈述之环节。前文已述,此程序所简化之内容不仅涉及被告人权利,被害人权利亦被限制,因而理论上被害人自愿弃权方为正当。对于被害人而言,由于其参与诉讼之目的在于获得因犯罪所致损失之赔偿,当此事项与被告达成一致时,其实体权利已得有效保障,无须再以保障程序权利达成该目的。
(二)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实践情况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情况直接体现在是否获得被害人谅解、是否与被告人达成调解或和解协议方面,一方面,就获得谅解、达成调解或和解协议的案件而言,被害人的赔偿要求一般得到了满足,这可以被看作一种实体权益的补偿;另一方面,既然案件已获得被害人谅解、存在调解或和解协议,表明被害人已经实质参与过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过程,被害人的程序权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然而,从笔者调研的情况来看,在调研地的认罪认罚案件中,获得被害人谅解、达成调解与和解协议的案件比例较低,被害人在认罪认罚案件办理中的参与度似乎并不高。
C 市是认罪认罚从宽的试点城市,自2016 年9 月到2019 年8 月,两级司法机关共办理认罪认罚案件2343 件,包括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1483 件,侵犯财产犯罪案件569 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案件198 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案件50 件,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案件27件,其他案件16 件。其中,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案件数共298 件,占所有认罪认罚案件的20.1%。危害公共安全类案件160 件,主要集中于交通肇事案、危险驾驶案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占该类认罪认罚案件总数的10.8%;侵犯财产类案件87 件,主要是盗窃案,占该类认罪认罚案件总数的15.3%;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类案件34 件,主要是轻微的故意伤害案,占该类认罪认罚案件总数的68.5%;妨害社会管理类案件15 个,主要是寻衅滋事案与妨碍公务案,占该类认罪认罚案件总数的7.5%。在J 市,2018 年检察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合计3026 件,3245 人,其中达成和解协议26 人,占比0.8%;2019 年检察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合计5133 件,5911 人,其中达成和解协议91 人,占比1.5%。在Q 市,2019 年检察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合计9528 件,10914 人,其中达成和解协议153 人,占比1.4%;2020年前4 个月,检察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合计1767 件,2103 人,其中达成和解协议38 人,占比1.8%。
在认罪认罚从宽试点的初期,有些地方司法机关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适用标准,要求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被告人必须与被害人达成调解或和解协议。事实上,这是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不当限制。《指导意见》专门规定:“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同意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的,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不过,从调研情况可以看出,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案件比率并不高,而被害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获得有效赔偿并与被告人达成协议的情况更是极为少见,为了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最高司法机关的上述规定未免有些过犹不及。更为重要的是,上述情况直接反映了被害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参与程度十分有限,这很难说明被害人的实体权益与程序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三)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困境分析
现行规范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仍存在一系列问题,使前文提及之程序正当性要素并未完全实现。一方面,在认罪协商阶段,听取被害人意见的规范意义阙如。按照现行规定之表述与学界通常之理解,此处“听取”仅为程式规范,应当“听”但不一定“取”,其产生的法定效果乃“记录在案”,并不必然对程序造成影响。退一步讲,即使不规定本条款,审查起诉阶段的承办人也应听取被害人意见,若不明确被害人意见的程序法效力,则该条款权利保障之意义将大打折扣。〔25〕实践情况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问题。实证研究显示,实践中听取被害人意见大多未能充分告知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目的、意义及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参见苏素专、洪文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害人参与的实证考察》,载《福建法学》2017 年第4 期。另一方面,对于可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被害人在程序选择阶段与被告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后,是否就丧失了程序参与权?获得民事赔偿本为被害人之固有权利,即除自愿放弃外,被害人皆有权求偿,而司法机关也应最大限度实现此权利,否则便为司法之不正义。然而,将获得赔偿与程序异议权挂钩,则混淆了被害人权利的性质与范围——获得赔偿权乃因被害人遭受犯罪之损失所生,具有实体性,程序异议权则是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根本不能等量齐观。换言之,即使达成了民事赔偿协议,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未经放弃也依然存在,其有权出席法庭并发表意见。〔26〕See Robert Fletcher, “Victims’ Rights in Criminal Trials”, 14 Criminal Justice Ethics 56(1995).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上述被害人权利保障条款极富弹性,使得权利保障的重视程度很大程度受控于承办检察官的裁量,最终难以实现被害人对检察权的制约。首先,被害人之确定受检察机关裁量,除犯罪行为明确指向的被害人外,其余受犯罪行为波及的权利损失人是否具有被害人地位,则基本由承办人确定,若认为其不属被害人,权利基础便不复存在。其次,检察官主导整个认罪认罚阶段,其既可因被害人异议而不同意认罪认罚,亦可不考虑被害人因素之影响而适用认罪认罚。再次,被告人退赔虽为法定从宽情节,但量刑从宽的“度”掌握在检察机关手中,被害人无法直接围绕量刑与被告人协商赔偿数额。有检察人员就认为,即便被害人未出具谅解意见,也不影响对被追诉人的从宽。〔27〕参见周新:《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从宽的实践性反思》,载《法学》2019 年第6 期。
不难看出,在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构建中,决策者依然奉行“被害人的利益仍由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的检察官代为主张”〔28〕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16 年第2 期。之思路,这造成了被害人主体性缺失、权利保障不彰的问题。不容否认,在当前既无法斩断刑事案件来源,也不能大幅度增加办案人员数量之现状下,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乃当下司法改革的必由之路。〔29〕参见陈卫东、聂友伦:《侦查视角下的刑事速裁程序效率研究——现状、问题与展望》,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6 年第6 期。但必须注意,诉讼效率提高应以维护司法公正为前提,而作为实现公正司法、正当程序之要素,略显边缘化的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在未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中尤应得到重视。
四、认罪认罚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完善方向
作为当事人的被害人,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不能因制度改革、程序简化而动摇,反而因其权利保障之程度关乎程序正当性与从宽合法性,更应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构中予以重视。被害人的诉求,一方面需要通过参与案件的处理过程得以疏导,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案件的处理结果得以满足。〔30〕参见李奋飞:《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以复仇愿望的实现为中心》,载《政法论坛》2013 年第5 期。在目前的制度体系中,被害人权利基本由承办检察官“代理”行使,其在程序中所能施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承办人保障其权利意愿的大小。法治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过分以依赖“司法能动”的机制并不可靠,要想真正维护被害人权利,防止权力过分膨胀,就必须针对认罪认罚的制度设计以及相关配套措施中被害人权利条款予以完善,构建被害人可参与、可影响、可救济的制度体系。
(一)明确被害人知情权与程序参与权
知情权是诉讼主体行权的前提基础,若缺乏知悉信息的途径,诉讼主体将“有权不知使”,其显然非正当程序之意涵。〔31〕See Press-Enterprise Co. v. Superior Court, 464 U.S. 501(1984); Globe Newspaper Co. v. Superior Court, 457 U.S. 596(1982);Richmond Newspapers, Inc. v. Virginia, 448 U.S. 555(1980).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听取被害人意见”,这意指在认罪认罚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当告知被害人相关情况,但也仅限于此。申言之,由于法律既未授权被害人实质参与,亦未设置相应的通知程序,被害人对认罪认罚的启动、诉讼程序的选择、从宽处理的情况以及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皆无知悉途径,甚至可能接到开庭通知时,始对案件的程序情况产生了解。
在知情权难以保障的情况下,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更无法实现。〔32〕程序参与是影响主体“公正感”的重要因素,有时它甚至比判决结果更为重要。See Tom R. Tyler,“ Procedural Justice,Legitimacy, and the Effective Rule of Law”, 30 Crime and Justice: A Review of Research 283(2003).应然层面看,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应当有效知悉程序信息并参与其中,否则既有的实体与程序权利皆可能遭受不当侵害。〔33〕See Sarah N. Welling,“ Victim Participation in Plea Bargains”, 65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 301, 305-306(1987).首先,在犯罪嫌疑人表达认罪认罚意向之初,被害人就应当得到通知,并给予其参与协商之机会。此机制既能有效保障被害人程序权利,亦可促使犯罪嫌疑人积极退赔、达成谅解,还能使承办人员直观判断预防必要性大小以供准确提出量刑建议,同时起到监督承办人员之作用。其次,应当赋予被害人提出异议的权利,根据现行规范,被害人虽可向检察机关提出意见,但并无刚性效力,该机制使得被害人权利虚化,无法得到保障与救济。考虑到认罪认罚制度的效率性,不宜直接赋予被害人程序否决权,可适当借鉴美国法的规定,当被害人提出异议后,将其意见记录在案并交由法庭决定,同时,不论案件适用何种程序审理,亦应明确被害人出席庭审并直接向法庭陈情之权利。
(二)将被告人退赔、被害人谅解与从宽幅度挂钩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未能就民事赔偿等内容协商一致并不影响对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从宽处理,只不过影响了后续诉讼程序的选择。〔34〕刘方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设路径——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经验的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 年第3 期。但应注意,获得赔偿乃被害人固有之实体权利,检察机关不得擅自处分,亦不得突破限度对被告人予以从宽。申言之,与被害人相关的赔偿损失、获得谅解以及达成和解协议为重要的量刑情节,若无以上情节,对被告之量刑从宽不得突破法定限度。
反过来看,此类与被害人相关的情节和量刑之间亦应设置某种对应关系,以防止量刑的随意性。虽然《指导意见》已经明确规定:“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与被害方达成和解协议、调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方损失,取得被害方谅解,作为从宽处罚的重要考虑因素。”但是,这里并未明确从宽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该标准既对几类典型情况划分了不同的从宽幅度,也在各幅度中预留了司法裁量的空间。对于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时,应参照此标准执行,防止量刑建议的过轻或过重。在未来,检察机关应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指导性意见,以保障量刑从宽的适当性与精确性。
此外,由于从宽标准的不明确,这里还遗留了一处问题。《指导意见》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并且愿意积极赔偿损失,但由于被害方赔偿请求明显不合理,未能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一般不影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据此,似乎一旦被害人的赔偿请求不合理,被告人只要表态积极赔偿,即不影响对其刑罚的从宽幅度。问题在于,其一,这里的“赔偿请求明显不合理”是否存在明确的标准且判断的主体为何?其二,一旦确认属于赔偿请求不合理的,即便未达成调解或和解协议,是否仍应按照存在协议的情形对被告人予以从宽,即“不影响从宽”应作何理解?就前者而言,事实上,犯罪行为尤其是侵害公民人身犯罪导致的损害赔偿,由于伴随着被害人精神方面的损失,其实很难通过金钱量化。在此情形下,“赔偿请求明显不合理”便无法被设置具体的标准。同时,从法律语境来看,“赔偿请求明显不合理”的判断主体很明显是检察机关,但作为与被害人平行的诉讼主体,其是否有权作出此决定,不无疑问。对于后者,在被害人不接受赔偿的情况下,从宽合法性来源便存在缺失,其无法在报应刑以及很大程度的预防刑层面减轻被告人刑罚,直接与存在赔偿协议的情况等而视之,未免有些矫枉过正。笔者认为,这里的“不影响从宽”主要是指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但相较于已经达成赔偿协议、获得被害人谅解案件的从宽幅度,仍需适当限缩,而较仅认罪认罚却不退赔的案件,从宽幅度则应适当提高。
(三)建立完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被害人权利保障之问题,不仅体现于认罪认罚制度,实则贯穿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被害人无法得到有效赔偿——大量被告人因将获刑罚处罚而不愿再予赔偿,法院对拒绝赔偿的被告又从严处理,如此便陷入了“以刑代赔”的陷阱。此情境下,被害人往往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即使获得了刑事附带民事的判决,亦很可能出现执行不能之结果。反过来看,被追诉人真诚悔罪、愿意积极赔偿,但被害人漫天要价,又将不可避免地影响诉讼流程的简化。〔35〕参见秦宗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疑难问题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 年第3 期。事实上,我国刑事司法一直遵循着“以刑促赔”的策略,将退赔作为重要的量刑情节、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皆可看作是此方向之努力。甚至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言,其目的之一同样在于促进被害人获得赔偿,将速裁程序的适用与赔偿协议挂钩即为体现。《指导意见》甚至规定,“对符合当事人和解程序适用条件的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积极促进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但是,对于大量缺乏赔偿能力的被告,“以刑促赔”必然将异化为“以刑代赔”,这根本无法从基础上解决被害人权利保障之问题。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完善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36〕早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许多州就已开始为被害人提供补偿金,全国范围内亦出现了大量被害人救助项目。See Leslie Ann Budewitz, “State Legislaiton in Aid of Victims and Witnesses of Crime”, 10 Journal of Legislation 394(1983).由国家对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被害人予以补偿,以最低限度弥补被害人损失、保障被害人权利。〔37〕参见赵恒:《认罪认罚与刑事和解的衔接适用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 年第3 期。尤其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诉讼效率的提高不仅是控辩双方达成合意的结果,被害人在其中亦放弃了部分诉讼权利。若认罪认罚制度无法有效保障被害人权利,其未来之发展前景恐出现更多问题。〔38〕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在发展进程中就曾因缺乏被害人参与而遭致大量批评,其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以补救。See David L. Roland, “Progress in the Victim Reform Movement: No Longer the Forgotten Victim”, 17 Pepperdine Law Review 35(1989).以此而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作为一项基础性配套措施,与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值班律师制度具有相同之性质,在未来的制度完善中须得到应有重视。具体做法可以参照国际通行标准,将补偿对象仅仅限缩为人身损害且需达到“重伤”和“死亡”的结果,将财产损失排除在外。考虑到权利义务的一致性,还可将积极协助追诉犯罪等作为补偿的前提条件。〔39〕参见贺红强:《我国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的实用倾向和路径选择》,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 年第3 期。
五、结语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其效率价值之达成应当以当事人权利放弃为前提,不仅包括被告,被害人之弃权亦是其中应有之义。换句话说,认罪认罚改革必须重视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与诉讼地位,这不仅对制度之程序选择、从宽处理与权力制约等方面的正当化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更是刑事诉讼之“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任务的根本体现。此前,我国认罪制度尚处于试点期,工作重点为制度框架建构,解决的是如何认罪、何以从宽等基础性问题,对被害人权利关注不足。然而,在“认罪认罚从宽”已载入法律的当下,应当将制度的完善化、精细化作为重点,被害人权利保障即为重中之重,应得到决策者的重视。在未来,可以通过明确被害人对案件认罪情况的获得告知权,完善其程序参与的途径与表达意见的渠道,在制度细化中明确获得赔偿与从宽幅度的关系,并探索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配套制度,从而在认罪认罚制度中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率与公正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