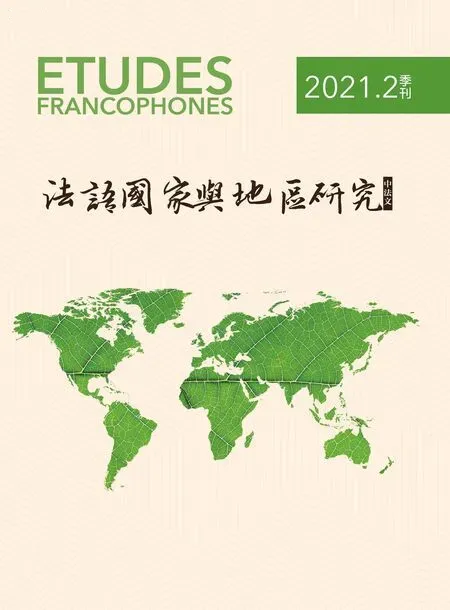米歇尔·图尼埃的摄影主题小说中的表征问题
2021-12-08王秀慧
王秀慧
内容提要 米歇尔·图尼埃在众多虚构及非虚构作品中一直延续着他对表征问题的思考,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短篇小说《维罗尼克的裹尸布》。小说主人公否定摄影忠实复制现实的模仿传统,她通过可将实在融于表征之中的“皮相摄影”,模糊了存在者与其表征之间的界限,使自己的摄影作品不再只是制造表征对象的在场效果,而是占据在场本身。图尼埃借小说的形式,具象化了表征内部“再现对象”的及物力量和“呈现自身”的自反力量之间的拉锯运动,并戏剧化了表征覆盖、篡夺现实的过程,从而提出表征虽不能还原对象,但它也不模仿对象,而是优先考虑取而代之;这种取代对象以呈现自身的倾向,实则是一种渴望代替上帝成为造物主的自恋欲望,但正是“人胜于神”的野心,才使艺术创造成为可能。
引 言
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 1924—2016)不仅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其业余摄影师的身份也广为人知。他曾主持过一档关于摄影的电视节目《暗房》(Chambre noire),并在1969年至1970年间与摄影大师吕西安·克莱尔格(Lucien Clergue, 1934—2014)共同创办了“阿尔勒国际摄影节”(Rencontres photographiques d’Arles)。图尼埃始终和摄影界保持着紧密联系,并与多位欧美摄影大师共同出版摄影评论集,比如“与我的天才朋友”①Arthur Tress, Michel Tournier.Rêves.Bruxelles : éditions Complexe, 1979, p.6.亚瑟·特里斯(Arthur Tress, 1940— )合作了《梦》(Rêves, 1979),后又与他最喜爱的摄影师爱德华·布巴(Edouard Boubat, 1923—1999)合作了《背影》(Vues de dos, 1981)和《加拿大游记》(Canada journal de voyage, 1984)。图尼埃研究专家贝文(David Bevan)直接称作家是个“摄影发烧友”②David G.Bevan.« Tournier’s Photographer: A Modern Bluebeard ?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1985, vol.15, no 3, p.66.。
有趣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与摄影师们合作愉快的图尼埃,却在自己的虚构作品里唱起了反调。在小说《桤木王》(Le Roi des aulnes, 1970)中,主人公迪弗热把相机当作阳具的延伸,靠偷拍来满足对男童的欲望;在小说《维罗尼克的裹尸布》(Les Suaires de Véronique, 1978)中,摄影师的“皮相摄影”实验导致模特的皮肤被层层剥削直至全身患上皮炎而亡;在小说《金滴》(La Goutte d’or, 1985)中,柏柏尔男孩伊德里斯离开绿洲寻找被法国游客拍下的相片,从而催化了他在图像泛滥的西方社会中的异化。这三部小说的叙事视角,从《桤木王》中的摄影师,到《金滴》中聚焦于被拍摄的对象,再到《维罗尼克的裹尸布》中转为旁观者,读者由此获得了摄影师的三重形象,且一律是恶毒的侵略性形象,似乎作家只是在小说中进一步印证了人们对摄影的刻板印象。其实,图尼埃最擅长为他的哲学思考披上小说的外衣,我们在其任何一部作品中都能找到作家暗渡哲学的痕迹。图尼埃在小说中如此频繁地拾起摄影主题,或借小说人物之口讲授摄影美学,实则暗含了作家对表征③“表征”(représentation)另有“再现”或“代表”的译法,现遵时译将其译作“表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其中最典型的是短篇小说《维罗尼克的裹尸布》,图尼埃在这部作品中以虚构形式演绎了表征的全过程,并试图恢复人们对表征的信心。在论证小说主人公克服物与其表征之间本体分离的尝试之前,我们先初步澄清“表征”一词的基本含义。
一、表征的双重维度
按普伦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的说法,表征基本上是“一个处于废墟中的概念,已被当代批评理论的强力武器进行过地毯式轰炸”④Christopher Prendergast.The Triangle of Representation.New York: Columbia UP, 2000, p.ix.。但对表征神话进行的无情攻击——以及比“反对表征”的口号更天真的“超越表征”——本身就陷入了表征的陷阱,因为“所有的语言都是表征性的”⑤德里达.《遣发——关于表征》.吴建平译.国外文学,1994(2):32.,任何对表征的批判只能重复表征的语言,表征就像“扎在尾巴上的认识论尖刺”⑥Christopher Prendergast, op.cit., p.13.,使试图超越它的人不断绕回原点。与其抵制表征,我们能做的只有与它所带来的持续挑战保持对话。
“表征”一词有着复杂难解的语义史。法语中的“表征”(représentation)可拆成re-présentation,即以空间上的在场和时间上的当下这两种相互关联的方式“使重现”。法兰西学院词典学家弗雷蒂埃(Antoine Furetière, 1619—1688)在其编纂的《通用词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 1690)中,将表征定义为“将不在场之物重新放回我们头脑和记忆中、并向我们描绘不在场之物原本模样的形象”⑦Antoine Furetière.Dictionnaire universel, contenant généralement tous les mots françois tant vieux que modernes, et les termes de toutes les sciences et des arts.La Haye, Rotterdam : Arnout et Reinier Leers, 1690, p.1793.。这层意义植根于“表征”在中世纪时的物质属性——葬礼上用来代替死者的浇铸形象⑧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黄迅余、黄建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8.。后来当表征被应用于政治和法律领域时,便有了代他人之位、手握其权的“代表”意涵。综上可知,表征不仅使缺场者重现,它还实行替代。
弗雷蒂埃指出了表征的另一层含义:亲自出现并展示演出。法语中“表征”也指“戏剧表演”,但这时我们并不是在复制或重复的意义上谈论戏剧,因为在演出中,是在场者(演员)构成了其自身的表征(角色),栩栩如生的形象与其指涉对象是一体的,彼此相互粘连。戏剧表演或可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相联系:角色虽在虚构中存在,但在现实中缺席,当它在舞台上得到演绎时,这场演出在某种意义上即该角色的第一次在场(présence);同样地,被压抑之物——比如影响某人一生的创伤——在无意识中存在,但对意识缺席,这些被压抑的事件会在生活中得到重复,也就是说,“就意识而言,重复就成了缺场的第一个在场、第一个表演”⑨Shlomith Rimmon-Kenan.A Glance beyond Doubt : Narration, Representation, Subjectivity.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P, 1996,p.9.。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一篇名为《遣发——关于表征》的文章中对表征内部的矛盾做了精辟论述,其中便谈到表征“也许没有代表性,不复制,不重复,而仅仅是简单地被呈现和放置在我们眼前,放置在我们的想象或心智的凝视之前”⑩德里达,前揭书,第31页。。事实上,“表征”在德语中的对应词vorstellung并不直接隐含représentation的前缀re所负载的意涵,正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世界图像的时代》(Die Zeit des Weltbildes)一文中定义的那样,表征是“把现存之物当作某种对立之物带到自身面前,使之关涉于自身”⑪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93.。因此,前缀re强调的与其说是重复,不如说是一种召唤至此时此地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返措自身,返指主体的力量”⑫德里达,前揭书,第34页。,于是表征不再从被模仿的对象中获得它的形状,而是把主体的形状强加给不在场者。
法国符号学家路易·马兰(Louis Marin, 1931—1992)通过对安托万·阿尔诺(Antoine Arnauld, 1612—1694)和皮埃尔·尼古拉(Pierre Nicole, 1625—1695)的《波尔·罗亚尔逻辑》(Logique de Port-Royal, 1662)的阐发,将上述的两面性统合进表征的概念之中。一方面,表征可从及物的透明维度(dimension de transparence transitive)来看:表征使缺席的对象呈现,换句话说,就是将无“装作”有,毕竟人们并没有面对着不在场的对象,但表征却使它发生了在场的效果。表征的这一维度往往是透明可见的,它的模仿性使表征的对象可立即被识别出来。另一方面,表征也可从自反的隐晦维度(dimension d’opacité réflexive)来看,即“任何表征都自我呈现为代表某物”⑬Louis Marin.Opacité de la peinture : Essais sur la représentation au Quattrocento. Paris : éditions EHESS, 2006, p.95.法语原文为:Toute représentation se présente représentant quelque chose.。也就是说,符号在表征某物的同时,也在呈现符号自身。
如果说“及物的、透明的”力量产生了“在场效果”,那么“自反的、隐晦的”力量就产生了“主体效果”。因此,我们看到了表征内部的双重运动,但第二种自反的、隐晦的运动是表征的潜在维度,因为在表征机制中,为了营造被表征之物的在场效果,表征行为的痕迹就不能回溯或显露,例如画布、画框通过保持隐蔽,使观画者暂时忘记眼前的形象背后还有支撑物的存在。因而路易·马兰指出,表征的惯常机制在于让人不去意识到它的第二维度而选择第一维度,让人在客体效果(表征对象的在场效果)与主体效果(表征的自我呈现行为)之间只见前者,即表征作为对缺场者的模仿,而后者则是“模仿性表征的非模仿方面”⑭Louis Marin.De la représentation.Paris : Gallimard, 1994, p.257,它往往隐藏自身、难以识透,但“正是支撑面的不可见性,才是被表征世界的可见性的可能条件”⑮Ibid., p.305.。
路易·马兰把注意力放在了对表征自我呈现运动的研究上,他指出,波尔·罗亚尔修道院(Abbaye de Port-Royal)的逻辑学家们之所以谴责绘画,是因为“图像符号中完全异化了的对象取代了对象本身”⑯Louis Marin.« Signe et représentation : Philippe de Champaigne et Port-Royal ».Annales.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1970, vol.25, no 1, p.2,也就是说,绘画替代了它的指涉对象、表征的第一维度让位给了第二维度,从而背离了表征的惯常机制。由此可见,图像符号一方面是典型的模仿,另一方面它又想突破模仿范畴,以获得自主,为此它不免要被指控僭越,或被更激进的圣象破坏者之流所禁止。因此,表征不应与模仿(mimesis)混为一谈,模仿的理想是在表现力与装置之间保持平衡,它要使所模仿的对象可见,就不能让人太过注意到它的装置,但同时它必须划定模仿的范围,以使人意识到自己在赏一幅画、在观一出戏;衡量模仿价值的标准还是基于它对模仿对象的唤起效果,且模仿者在秩序中附属于它所模仿的先在的对象,它既不能取代也不能将这一指涉对象包括在内。而表征的本性在于打破该秩序:处在“复制和替代的中间带”⑰Louis Marin.De la représentation.Paris : Gallimard, 1994, p.254的表征为了对象的在场效果而尽力淡化主体的表征行为,但它的野心却是实行替代以呈现主体自身,它将自己呈现成仿佛“作为代表的物”(représentant)即“被代表之物”(représenté)的客观真相,试图在行使表征的事物(认识论上的存在)与被表征的事物(本体论上的存在)之间建立等价关系。为达到这一目的,表征在其“强烈的、使自身天然化的内在倾向”下⑱Christopher Prendergast, op.cit., p.9.,将它所基于的人为建构,包装成根本不是人为的选择或约定俗成,而好像它是天然之所是。因此,当代理论在论述表征时,关注的重点是表征的过程,以及是谁在表征的问题,简言之,就是从表征对象向表征主体转移,以回溯表征的起源,更重要的是揭开掩盖这些起源的权力机制。
二、否定模仿,寻求超越
小说《维罗尼克的裹尸布》的背景即图尼埃熟谙的阿尔勒国际摄影节,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作为摄影节的常客,遇到了年轻女摄影师维罗尼克,后者不满足于以传统摄影为代表的再现真实,当她的同行们争相拍摄模特埃克托尔“漂亮丰硕的裸体”时,维罗尼克直言这些照片“没一张值得留下来”(图尼埃 1999:126)⑲文中该作品原文引文均出自:图尼埃.《皮埃尔或夜的秘密》.柳鸣九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因为“摄影师们要是愿意,就能拍出跟他本人酷似的身体和面孔,而且也会漂亮,但正如所有的复制品一样,用这种方法拍出来的照片显然比不上原物”(图尼埃 1999:127)。维罗尼克深谙黑格尔美学,若想通过模仿与自然竞争,艺术将永远劣于自然,所以她的摄影主张不是“漂亮”而是“上镜”,也就是制作比模特本人更美的照片、“制作超出真实物体的照片”,就好像它们“揭示出到那时为止一直隐藏着的美,然而这种美,照片并没有揭示出来,而是创造出来”(图尼埃 1999:127)。借维罗尼克之口,表征说出了自己的理想——“再现让位于呈现,复制让位于生产,再造让位于创造”⑳Shlomith Rimmon-Kenan, op.cit., p.10.,而实现这一理想的前提即让表征与模仿脱钩,以消除表征由来已久的因与模仿绑在一起而遭受的贬损。
维罗尼克在寻求超越传统摄影的过程中,移除了介于她和模特之间的摄像设备,她称相机等中介的调解是职业技术局限带来的“可耻的污点”,而“直接摄影”(photographie directe),也就是“不用摄影机、不用胶卷和不用放大器进行的拍照”,才是“大部分摄影家的梦想”(图尼埃 1999:138)。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开篇,叙述者“我”用“拥挤和重压”形容摄影师随身携带的摄影器材(图尼埃 1999:125),这样的描述预示着摄影设备这种负担将从摄影过程中被废黜,而实现了图像与人体彻底融合的“皮相摄影”将被引入:维罗尼克让埃克托尔泡在显影液里,然后让浑身浸湿的模特躺在泡过溴化银的亚麻布上,最后用定影液加以处理,以得到埃克托尔身体的皮相。本雅明指出,机械复制技术以“摹本的众多性取代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21]本雅明.《启迪》.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236.,维罗妮克的实验挽回了机械复制时代流失的“灵韵”,她的摄影没有底片,甚至就是原件——“真实的、独一无二的埃克托尔”(图尼埃 1999:128)。
再现的世界与实在世界的区别在于,再现是媒介化的,但只要人们“越不注意媒介,就越能专注于图像,仿佛图像是自己到来的”[22]David G.Bevan.« Image, Medium, Body: A New Approach to Iconology ».Critical Inquiry, 2005, vol.31, no 2, p.305.。因此,为了达到这种图像好似“自行给出”的效果,维罗尼克移除了相机,取消与实在世界的距离,但她移除的远不止这一个中介,为了使能指与指涉对象进入一种直接关系,所指的文化中介必须被排挤在外,于是所有为获得皮相所施加的暴力、所依赖的构造手段,这些痕迹都变得不可见了。小说中有一处细节:叙述者被邀请至维罗尼克在卡马尔格租住的房子时,描述室内的一切“都散发着手术室和刑讯室的气息”,而埃克托尔就是在这里经历了一年的驯化,包括缩减饮食和每日三小时的高强度肌肉训练,才成为维罗尼克所谓的“上镜”的模特,但叙述者在形容这所房子的外观时说,“这属于一种非常低矮的茅屋,又是用芦苇铺的屋顶,没撞见围墙的栅栏之前,在卡马尔格景区无法将这些茅屋分辨出来”(图尼埃 1999:127)。伪装成茅屋的工作室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直到人们接近它时才能被发现,这正隐喻了表征第二维度的隐蔽性,以及表征掩盖主体行为的“文化性”以使自己“天然化”的倾向。
小说最后,在维罗尼克办的摄影展上,叙述者质问她埃克托尔在哪儿,维罗尼克“以一种暧昧的手势指向从四面八方把我们包围起来的裹尸布”,说道:“埃克托尔?呶?他在……那儿。”(图尼埃 1999:140-141)通过对真实对象本身之外的任何所指的遮蔽,维罗尼克在她的摄影作品与被拍摄对象之间建起了等价关系,从而使她的作品不是埃克托尔栩栩如生的再现,而就是埃克托尔;不再只有在场效果,而就是在场本身。
三、取代对象,呈现主体
维罗尼克的裹尸布既是埃克托尔的在场证明,亦是他的死亡证明,叙述者暗示我们,埃克托尔是被化学溶剂腐蚀至死的。埃克托尔曾想要逃离维罗尼克的魔爪,他在给后者的诀别信中控诉道:“您给我拍了22 239张照片……22 239次从我身上剥去的东西落进了图像的陷阱……您把我像母鸡一样拔了毛,像安哥拉兔子一样拔了毛……现在我被掏空了,弄得筋疲力尽,糟蹋得不像样。”(图尼埃 1999:135)埃克托尔这头野兽落入了表征的陷阱,不仅被驯化成家畜,还被洗劫一空,这正呼应了西蒙·奥沙利文(Simon O’Sullivan)给表征所下的定义:“一项产生一种被掏空的实体的操作。”[23]Simon O’Sullivan.Art Encounters Deleuze and Guattari: Thought beyond Representation.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14.路易·马兰则借绘画指出表征的陷阱:“绘画把视线从起源(原型)、事物、世界的存在者(étant du monde)身上转移……以便用一种诱饵来吸引和捕捉目光,而这一诱饵即存在者的替代物。”[24]Louis Marin, op.cit., p.23.也就是说,表征以“行使表征的事物”覆盖“被表征的事物”,它并不引导观众回到表征对象,而是使观众的视觉停留在表面并阻止其进一步访问,因为表征以身体的缺席为生,它天然不愿让缺席的身体回归,且它的最终目的是用自己的存在取而代之。因此贝尔廷(Hans Belting)说道:“介入世界和我们之间的图像不是再现世界,而是阻挡世界,我们活在了我们自己创造的图像中。”[25]Hans Belting.« Image, Medium, Body: A New Approach to Iconology ».Critical Inquiry, 2005, vol.31, no 2, p.317.
同样,维罗尼克的皮相摄影并不指向埃克托尔,而是指向他的肉体解体,不过图尼埃暗示我们,裹尸布上还有维罗尼克的投影。在艺术评论集《他泊山与西奈山》(Le Tabor et le Sinaï, 1994)中,图尼埃提出:“如果一件艺术作品必须像什么的话,那么它必须像的不是它的模型,而是它的作者,就像一个婚生子自然会像他的父亲一样。相似在这里的意思即签名。”[26]Michel Tournier.Le Tabor et le Sinaï : Essais sur l’art contemporain.Paris : Gallimard, 1993, p.12-13.在《维罗尼克的裹尸布》中,叙述者“我”在摄影节上第一次见到维罗尼克时,形容她身材瘦小,身上带着令人着魔的智慧和疯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埃克托尔,他“肌肉发达,脸圆圆的,有点孩子气,小公牛似的前额上垂下一绺黑色的头发”(图尼埃 1999:125)。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者对埃克托尔的描述中,“智慧”是明显缺席的,由此我们可以说埃克托尔和维罗尼克之间构成了自然/文化、身体/头脑的二元对立。
小说的第二阶段,当叙述者一年后再次在摄影节上见到埃克托尔时,后者已经成了维罗尼克的专属模特。令人不安的是,“维罗尼克没变,至于埃克托尔,则变得认不出来了。他那有点孩子气的笨拙,他那漂亮动物般的狂妄,他那乐观的阳光样的奔放,已经荡然无存”(图尼埃 1999:126),他不仅身形日渐消瘦,还传染了维罗尼克的狂躁性情。总之,埃克托尔变得像维罗尼克了。但叙述者不得不承认,埃克托尔确实成了“很美的景象”(图尼埃 1999:134),一年前的照片尽管“漂亮”,但只是埃克托尔的劣质复制品,“现在他变得上镜头了”,足以“让认识他的、第一次见到他照片的人大吃一惊”(图尼埃 1999:127)。
在埃克托尔身上还发生了一个更大的转变:过去他只被当成一个身体或客体,在他不堪维罗尼克这一年的“洗劫”而想要逃离时,我们在他写给维罗尼克的信中看到他作为一个思考主体出现了。这要归功于维罗尼克,因为埃克托尔在信中坦言:“您给我拍了22239张照片。显然这让我有时间思考,而且我理解了很多东西……我欠您很多,亲爱的维罗尼克。您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图尼埃 1999:136)无论是埃克托尔在外形上从原始的“漂亮”,变成了现在的“上镜”,还是在思想上从野性不驯的动物,变成了有思想的、可以优雅写作的“另一个人”,都是受了维罗尼克的启蒙,或者说是由于文化向自然施加的作用,但结果便是,异化成维罗尼克形象的埃克托尔取代了埃克托尔本身,一件文化艺术品取代了一个天然的存在者,埃克托尔变成维罗尼克名下“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图尼埃 1999:134)。
表征内在的自反力量必然催生“主体效果”,而这是以牺牲表征对象为代价的。维罗尼克对叙述者说,理想的摄影需要“修炼(travail)和献身精神”(图尼埃 1999:126),“travail”来自拉丁语“trepalium”,意思是古代的一种酷刑用具,维罗尼克言下之意即:为了呈现表征主体自身,客体必须被暴力摧残直至消失不见。
四、扮演上帝,道成肉身
图尼埃指出:“艺术家被束缚在一种游牧式的自恋中,渴望在自我之外的世界中捕捉自己的影 子”[27]Judith Jeon-Chapman.Spirituality in Michel Tournier: Duality Aspiring towards a Perverse Cosmogony.Ph.D.dis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5, p.215.。对他来说,表征是用来投射主体隐秘欲望的手段,且这种欲望实际上是表征主体的自恋欲望,而非指向表征客体的侵占欲望。比如图尼埃否认《桤木王》里跟踪偷拍男童的迪弗热对孩子有任何生理上的性欲:“迪弗热与他的猎物/孩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性方面的。”[28]Michel Tournier.Le Vent paraclet.Paris : Gallimard, 2005, p.117.对迪弗热来说,摄影行为比性行为的占有更有成就感:
其目的在于使实在的事物上升一步,拥有新的力量,即想象的力量。摄下的形象,无疑出自真实的事物,但同时与我的幻觉又是不可分离的,与我想象的视觉处于同一位置。摄影术把真实推向幻想的层次,把实在的事物变成自身的神话。镜头是一扇狭窄的门,被召唤去充当受人支配的神祇和英雄的候选人通过这扇门神秘地进入我心间的万贤祠。[29]图尼埃.《桤木王》.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122.
在摄影中,迪弗热看到了超越性的可能,平庸的现实将被他的想象力提升到神性的维度。在《维罗尼克的裹尸布》中,图尼埃同样将摄影与神圣联系在一起。小说最后,维罗尼克在马尔特骑士教堂举办了题为“维罗尼克的裹尸布”的摄影展。借圣洁的宗教场所,维罗尼克提醒观众她的作品的超越性品质。事实上,维罗尼克的名字即来自宗教传说,图尼埃在《面具的黄昏》(Le Crépuscule des masques, 1992)中指出,Véronique源于拉丁语verus(真的)和希腊语eikon(图像),指《新约》(Nouveau Testament)中的圣维罗尼克,她是第一个向世人揭示耶稣形象的人:在受难的耶稣前往髑髅地的途中,维罗尼克“用自己的面纱擦拭救世主那张沾满鲜血、泪水和汗水的脸,然后奇迹发生了,维罗尼克的面纱上印着耶稣的面容”[30]Michel Tournier.Le Crépuscule des masques.Paris : Hoebeke, 1992, p.171.图尼埃在小说题目中用“裹尸布”(suaire)代替了“面纱”(voile),suaire现指耶稣尸体被从十字架上取下时包裹身体的都灵裹尸布,上面亦印有耶稣身体的形象。suaire一词来自拉丁语sudarium,意思是擦拭脸上汗水的布,而不是下葬时包裹尸体的布,因而小说的标题同时体现了suaire古今的两种含义。。据此,图尼埃追认圣维罗尼克为摄影的发明者。
至于埃克托尔,他像耶稣一样,留下的只是身体印在裹尸布上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是维罗尼克按自己的形象塑造的,因为埃克托尔在维罗尼克的调教下,越来越像后者。因此,我们或可说维罗尼克在扮演上帝,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他的形象反映在人身上,使人超越自身平庸的存在,步入神性。维罗尼克认为,是她将埃克托尔平庸、短暂的肉体存在升华为神圣、不朽的圣子形象,埃克托尔从此便如耶稣般存在,生与死的界限被取消了,“在创造/杀死埃克托尔的同时,维罗尼克成功地摧毁/保存了他的一切”[31]。
图尼埃将维罗尼克的展览设置在教堂中,暗示表征所渴望的呈现自身,实则是一种渴望代替上帝成为造物主的自恋欲望,而“人胜于神”恰恰是使艺术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却垄断了塑像权,被塑造的人类不能再塑身,上帝之后不再可能有创造者,而“只有带着相反的、大不敬的观点”,认为表征会比原型更有内涵,美学才可以设想,人才有可能成为艺术家,“艺术即颠倒的本体论,表现胜于存在本身,或说人胜于神,否则的话,人的手不过能模仿神的想法而已”[32]德布雷,前揭书,第159页。。这亦是图尼埃写作的终极梦想:文本渴望道成肉身,弥合词与物、形式与意义、身体与灵魂之间的差距,终结符号的任意性制度。这种文本和身体之间的理想关系是现实主义最疯狂的梦想——表征获得肉身,变成了“体现”(incarnation),文本不再现世界,其本身即它所言说之物的表演和呈现。这一理想背后的冲动是为了修复破碎的经验,使被时间和历史分割的东西完整起来,回归一种无中介的原始表达时刻,届时,身体和心灵没有被分割,表象与本质合为一体,符号中即存有它所指涉之物。
结 语
“表征”复杂的含义往往因各自使用语境之间的距离而被切开讨论,符号学家路易·马兰通过提出表征的双重维度——及物的透明维度和自反的隐晦维度,试图统合表征的复杂性;而小说家则可借虚构的优势,接受“表征”在政治、法律、审美等各个层面上的内涵。虽然《维罗尼克的裹尸布》中的“邪恶”摄影师是圣人维罗尼克的倒错形象,但图尼埃并不意在贬损摄影,而是将摄影这一表征的典型代表的可能性推到极限,以具象化、戏剧化表征在“再现对象”与“呈现自身”这双重运动之间的摇摆,从而揭示摄影内在的神圣与异化、创造与破坏并存的力量。正如大卫·贝文在评价图尼埃笔下的主人公时所说,摄影师以及与他一样也在实践神秘学的同道者们——食人魔、炼金术士和大祭司,“就像蓝胡子一样凶险,但我敢说,对他或她的潜在受害者来说,是‘迷人的’!”[33]David Bevan.« Tournier’s Photographer: A Modern Bluebeard ?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1985, vol.15, no 3, p.70-71.同样,尽管表征棘手的认识论困难是潜在的混乱来源,但它的多义性和多价性也是其持久魅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