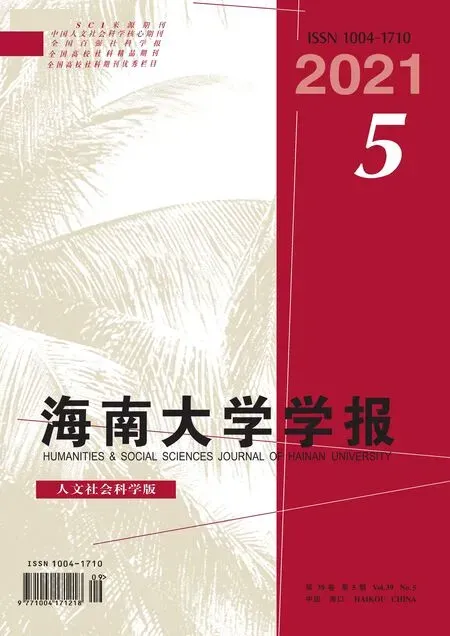海德格尔的“安提戈涅问题”
2021-12-08欧阳帆
欧阳帆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长久以来都是为文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所钟爱的一个题目,而海德格尔无疑是众多评论者中极为突出的一位。他不仅先后在1935 年的《形而上学导论》课程和1942 的第三次荷尔德林讲座中对其中著名的“第一合唱歌”进行过相去甚远的翻译和阐释,而且即便在学术之外也依然对之兴趣不减。例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就曾不止一次地从弗莱堡乘坐火车去慕尼黑观看由卡尔·奥尔夫根据荷尔德林的译文谱曲、由索尔蒂指挥的歌剧《安提戈涅》,直到饰演克瑞翁的男低音歌唱家乌德意外去世,他才表示不愿再看这一演出①Heinrich Wiegand Petzet,“Auf einen Stern zugehen:Begegnungen und mit Martin Heidegger,1929—1976”,Frankfurt am Main:-Verlag,1983,SS.168-172.。如此痴迷于一部希腊悲剧,这在西方思想大家中可谓绝无仅有,个中如若没有值得深思的缘由,恐怕很难说得过去。
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本人对《安提戈涅》的阐释又独树一帜到了离经叛道的地步。我们知道,此前黑格尔已经从家庭伦理与国家伦理之间的矛盾的角度对这部悲剧有过著名的解释,而海德格尔同时代的布尔特曼又从基督教信仰出发对之进行了“人道主义”的阐释,其中的“第一合唱歌”还被亨利希·维恩施托克称之为一首“文化的赞歌”②Otto Pöggeler,“Schicksal und Geschichte:Antigone im Spiegel der Deutungen und Gestaltungen seit Hegel und Hölderlin”,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2004,S.155f,169f.;时至今日,无论是从诗学、古典语文学还是从政治学、自然法角度对《安提戈涅》进行解释的著作仍然层出不穷③相关研究参见刘小枫,陈少明:《经典与解释19: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张巍:《西方古典学辑刊第二辑:〈安提戈涅〉里的合唱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此外较为特别的是林国华在“埋葬权”与“万民法权”脉络中对《安提戈涅》所做的解读,参见《埋葬权与战争法序言——格劳秀斯〈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第2卷第19章讲疏》,《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5年第2期,第76-87页。。然而,海德格尔的进入角度与上述所有做法都不一样。如果说,对于黑格尔等评论者而言,《安提戈涅》是一部可以分析的艺术作品——即便是“一切时代中的一部最崇高的,而从一切观点看都是最卓越的艺术作品”④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4页。——的话,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安提戈涅》毋宁说是一个谜、乃至一句谶语,其中蕴含的西方历史的奥秘并非寻常的视力所能洞穿。因此,不论是理解还是回答“安提戈涅问题”,都需要一种超出常规的命运性的直观——这或许才是海德格尔不得不采取与前人迥异的阐释进路的根本原因。
接下来,本文将具体阐明海德格尔对“安提戈涅问题”的进入角度,梳理其两次阐释之间的异同,并进而勘定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位置以及提出可能的启示。
一、悲剧精神为形而上学奠基
海德格尔曾多次翻译《安提戈涅》的“第一合唱歌”,并形成了两个差异很大的译本。在1935 年的《形而上学导论》讲座中,他首次翻译了这首诗;而在1942 年讲授《荷尔德林的颂歌〈伊斯特尔河〉》课程的时候,他又将这首诗几乎重新翻译了一遍,并于次年在稍加修改之后形成了一个私人打印稿,作为定本。而到了1953 年海德格尔正式出版《形而上学导论》的时候,他将1943 年的这个定本放在了正式出版的书中,但其中的解读却又是根据他的第一次翻译作出的,这无疑为理解海德格尔的相关解释造成了混乱。幸运的是,海德格尔曾于1935 年将他的第一个译本寄给雅思贝尔斯,这个文本因此被保存下来。我们将这个罕见的初译本移译如下①Otto Pöggeler,“Schicksal und Geschichte:Antigone im Spiegel der Deutungen und Gestaltungen seit Hegel und Hölderlin”,S.134f.:
《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1935)
(正转一)多种多样的恐怖者存在着/但是没有什么比人更恐怖的了;/他乘着冬季的南方风暴/在翻涌着白沫的浪涛上驶出——/又在撕裂到深处的/波浪之下穿行。/他也要耗损/诸神中最崇高者大地女神/这不可损坏和不知疲倦者/年复一年地改造她/翻来覆去地用马来/运犁。
(反转一)而且那轻轻滑翔的鸟群/也被他笼络,他还/用编织的网②这一行在后来的两个译本中都被漏掉了。/猎取荒野中的动物群/以及聚满了海洋的生物/这考量一切的人啊,/他还用狡计制服动物,/那在山上过夜与游荡的;/马匹的鬃毛粗糙的颈背/以及从未被驯服的山牛/被他套住脖子,逼它们受轭。
(正转二)而且进入词语的发声/以及风一般迅速的理解/他都找到路径,还能/进入统治城市的情绪。/而且他还想出了如何逃避/以便不暴露在天气的箭矢/以及不舒适的霜冻之下。/向着四面八方上路却又没有出路/他到达虚无。/唯独那个打击——死亡/他绝不能通过逃逸来抵挡,/他甚至在紧迫的重病面前/还能做到灵活的逃离。
(反转二)恐怖啊——掌握得超出/预期:那知识的制作性③海德格尔在这里用“知识的制作性(die Machenschaft des Wissens)”来翻译原文的to mechanoen technas,并在讲座中专门进行了讲解(GA40,S.168),但是在正式出版的《形而上学导论》中采用的却是1943 年的译文“能力的制作物(das Gemache des Könnens)”,这样一来相关的解读就完全落空、变得不知所云了。——/有时候他会跌入恶劣状态/另一些时候他又变得勇敢正直——/向中间穿行,进入大地的/法令与诸神发誓的接缝之间/在国家中高耸起来——他丧失国家④请注意,原文中的polis 这时是被翻译为“国家(Staate)”,而不是后来的“场域(Stätte)”,据称这一译名的改变与海德格尔对实际政治的疏离态度有关,参见Otto Pöggeler,“Schicksal und Geschichte:Antigone im Spiegel der Deutungen und Gestaltungen seit Hegel und Hölderlin”,SS.150-151.,/他为冒险行为之故/而让非存在者存在。/从事这样事情的人/不会是我的同灶伙伴/也不能与我共同商议。
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分三道程序来阐释这首诗。第一道程序特别指出构成诗的内在纯粹精神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在语言上将这一整体突出出来,具体而言就是选取了三个“关键句”进行详细阐释;第二道程序将全诗的内容逐段解释,并由此经验全诗的完整范围。这一部分是相对而言最具体、因而与原剧情节关联最紧密的部分;最后一道程序是在整体之中找到一个立足点,从而最终找到希腊人对人之本质的理解(参看GA40,S.157)⑤本文凡引用海德格尔原文,均由笔者译出,并直接在引文后标出海德格尔全集(Martin Heidegger,“Gesamtausgabe”,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76—2020.以下简写作GA)卷数及页码,须参见的内容亦然。。
第一个关键句即开篇两行:“多种多样的恐怖者(Unheimliche)存在着/但是没有什么比人更恐怖的了;”正是这两行诗说出了全诗的“内在纯粹精神”,亦即人之存在处于“双重暴力”之中。所谓双重暴力是指存在方面的“压倒性的支配力量”和人方面针对存在之支配力量的“暴力行事”:正因为人不仅从属于存在的支配力量,还能对这一力量行使暴力,人也就是to deinotaton〔最恐怖者或最暴力者〕。质言之,海德格尔此处的意图是要以其“另类形而上学”①这是海德格尔在其1935 年的第一次荷尔德林讲座中提出的概念,参见GA39,S.196.来回应康德先验辩证论中的二律背反难题,因而这里的双重暴力可以类比于传统哲学中自然与自由的悖论关系。正是这一关键的“前理解”,让海德格尔在接下来的译文中做出了特别的处理——他跟随荷尔德林的翻译,将接下来两个关键句理解为“逆喻/矛盾修辞(Oxymoron)”,并由此“在语言上将这一整体突出出来”。第二个关键句是第三段中的“向着四面八方上路却又没有出路”,大部分释读都将它同下句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间接肯定,一般译为“他事事都有办法,没有什么能让他束手无策”。但这一行的原文将意义相反“pantoporos”和“aporos”直接并置在一起,因此海德格尔将它理解为一个逆喻还是有一定根据的。下面情况也类似。第三个关键句是第四段中的“在国家中高耸起来——他丧失国家,/他为冒险行为之故/而让非存在者存在。”通常的译本都会将这句话与上面的句子关联起来理解,意即“如果他遵从地方的法令和他凭借诸神发誓要遵从的正义,他就会在城邦为尊(或他的城邦就会高耸);而如果他胆大妄为,做了不美的事,他就会失去城邦。”而海德格尔则根据原文中的“hypsipolis”和“apolis”的并置而将其同样理解为一个逆喻,并形成了上述翻译。实际上,这两个关键句都说出了人在存在者整体中的悖论姿态:一方面人在存在者中能够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另一方面人又不得不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人作为创造性的施暴者从历史境遇中耸立起来,但又恰恰因此而出离于历史境遇,因为一切规则法度都还有待于他们创建出来。正是通过这种矛盾修辞的语言造型表达,才更加准确地传达出了第一个关键句中的内在精神:人作为具有超出常态、离家、冲破边界的倾向的存在者乃是所有存在者中的最恐怖者(Unheimlichste)。下面的第二个步骤就是通过梳理全诗来具体阐明这一点。
海德格尔接下来从正面逐段解释了全诗的内容,这一部分篇幅最长,但意思并不令人费解。全诗的前半部分分别讲述了人类的各种能力和技艺,如果说“航海”“翻耕”和“驯养”所针对的是自然存在者的话,下面的“语言”“理解”和“情绪”等就是内在于人的能力了,上述两类能力无疑都是人所具有的能够针对存在的“压倒性支配力量”而施暴的强力,正是凭借这些强力,使得人能够在各方面都应付裕如。但是,有一条人类的所有技艺都无法突破的大限——死亡,因此人最终又不得不面临走投无路的绝境。海德格尔接着就在结尾的诗段中总结了三点:首先,全诗历数了人类的九种技艺,而这些暴力的行使范围就是诗中所谓“制作性(Machenschaft)”的整体范围,海德格尔用这个词来表达希腊词techne〔技艺〕的本质含义,后者也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技术,而是一种能够望出去把握整体的“知识”,犹如雕塑家在雕塑时要先能望出去看到作品的外观形象,然后才能将其生产出来;其次,如果techne 意味着恐怖者的“双重暴力”中的“暴力行事”方面的话,接下来的dike〔接缝〕就代表“双重暴力”中存在本身的“压倒性支配力量”,这是一种命运性的强力,无论人如何左冲右突,最终都会被它威临一切的强势所弥合包围以至于穷途末路;最后,恰恰因为命运的强力才逼得人不得不与之抗衡,因为如果没有人的制作与抗衡,自然的毁灭性的强力也根本无法显现。人的历史此在就处在techne 和dike 的极端张力之中,在两个极端中的人被抛来抛去,随时面临着成功和失败的险境。人作为行使暴力的创造者在孤注一掷中铤而走险,因为他要强迫未发生者、见所未见者(非存在者)进入显现(存在),而当他“冒险(tolma)”去支配掌握存在的时候,他必定四处碰壁,必定碰上非存在者的冲撞,碰得四分五裂。人就这样在“耸立出境遇”和“丧失境遇”②这里的解释与上列译文不尽相符,或许是海德格尔在正式出版时所做的修改。中来回挣扎。
第二个步骤对原诗的细致绎读在基调上与海德格尔同时期的著作完全是一致的,例如《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世界与大地的争执”就明显具有与此处相同的结构。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得出这种形态上的同类性,为此还必须深求一步,也就是对这一形而上学基本立场进行定位。实际上,完成了上述两个步骤,最后的程序已经呼之欲出了。海德格尔在文本中发掘出何种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呢?
但人就是在这样的此-在中被强迫、被投入如此存在的急迫(Not)之中的,因为这样一个压倒性的支配者,为了支配着地达乎显现,需要(braucht)一个为了它的敞开的场域。历史性的人类的此-在就是:被设定为裂口(Bresche),在其中存在的超强暴力显现着突袭过来,从而这裂口自身也在存在上毁灭。(GA40,S.171f)
有了上面的疏解,这里的表述已经不难理解,这里只点出两个要害。首先,人的历史性存在就在于充当存在的超强暴力的裂口——根据珀格勒的研究,这一论断的背后支撑乃是海德格尔在当时发展出的一套新的“模态学说”①Otto Pöggeler,“Übersetzung als Zwiesprache? Sophokles-Hölderlin-Heidegger”,Ulrich Stadler Hrsg.,“Zwiesprache:Beiträge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s Übersetzens”,Stuttgart/Weimar:Verlag J.B.Metzler,1996,S.77.此外参见Otto Pöggeler,“Schritte zu einer herme neutischen Philosophie”,Freiburg/München:Verlag Karl Alber,1994,S.227f.,其具体内容在《哲学贡献》中通过“存在的开裂”而得到论述,此处不赘述。其次,与本文目的更切合的是,如果我们将海德格尔在解读《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中所得出的对人之本质的希腊式理解与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揭示的“悲剧精神”进行对勘,就会发现二者在内在精神上若合符节!尼采回答康德“二律背反”问题的方式即是:在必然性的命运面前施展最高的违抗,以便同时在毁灭的快感中完成命运的强力——此之谓“积极的虚无主义”,这就是古希腊悲剧精神的要害所在②尼采:《悲剧的诞生》,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160 页。。甚至可以说悲剧就“是”存在的“裂口”——这一点构成了希腊对人的理解、以及希腊悲剧的独特性。抛开当时的时代氛围不论,尼采的影响对此时的海德格尔思想是决定性的。也正是尼采的思路,才说明了海德格尔为何要在一部以“形而上学导论”命名的著作的核心位置花费如此巨大的篇幅来解读一部希腊悲剧:因为正是悲剧精神奠定了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希腊世界观的基础。
总而言之,尼采的“悲剧精神”让我们获得了对海德格尔此时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准确定位,于是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勘探海德格尔接下来走了多远,是否到了能够走出悲剧精神这一基本立场的程度?
二、安提戈涅的特殊位置
海德格尔在1942 年再次讲授《安提戈涅》时,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第一合唱歌”译本③原文参见GA53,SS.71-72.。与翻译方面的改动相应,海德格尔在解释上也做出了重大调整。首先,如果说第一次阐释是为了回答希腊人对人之本质的理解的问题,而其中技艺和命运之间的张力构成阐释的核心的话,现在阐释的整体语境被转移到了“离家——还乡”的荷尔德林式主题之中。与此相应,海德格尔还撤回了之前解释中所有尼采式的“暴力话语”。其次,不仅整体语境改变了,解释的具体步骤也有改变。这次解释主要集中在对四个“关键句”的详细阐释之上——而在上一次阐释中,前三个“关键句”的阐释只构成第一道程序,接下来的两道程序在第二次阐释中付诸阙如。最后,虽然如此,这次解释涉及的范围却扩大了,不仅照顾到了前后的剧情,而且还引证了安提戈涅与伊斯墨涅以及克瑞翁的两段对话。归根结底,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差异关系到一个最根本的变化:第一次阐释要在合唱歌中寻找到希腊人对人之本质的普遍理解,而第二次阐释的重点则转移到了安提戈涅这一个体人物之上。具体的突破口正是这多出来的第四个“关键句”,而相关解释所占的篇幅也最大。
因此之故,为了将最核心的区别突出出来,我们略去这次阐释中可资比较的丰富细节,直接从最后的关键句开始:
做出这样行为的人/不会被我的灶火信赖,/我的知识也与他的臆想无关。(GA53,S.74)
在这一诗句中说话的“我”是谁呢?表面看来,自然应该是由忒拜长老们组成的歌队了。而他们要驱逐的人是谁?按照一种流行的解释,他们所针对的是作为僭主的克瑞翁,因为他在城邦中一意孤行、胆大妄为,因而属于开篇所说的“恐怖者”的行列;与此相反,其他生活在惯常状态中的人则是无害的,尤其安提戈涅更是无辜的,何况她最后还被克瑞翁处死。这样一来,安提戈涅就处在上文所说的“恐怖者”范围之外了。但海德格尔认为,这样的看法是完全不得要领的。为了弄清楚安提戈涅与恐怖者的关系,需要考虑此前她和她妹妹伊斯墨涅之间的一段对话:
伊:你有一颗热的心,却要转向冰冷的(死者)。
安:但我知道我是从何处而来受到问候,至高的急难落在我头上。
伊:尽管你能办到很多,但你所针对的却是不可违逆的东西。
安:那为什么不呢,因为显而易见,当我的力量消失,平静也已围绕着我生长起来。
伊:但是作为开端去追求那不可违逆的东西,终归还是不合适的。
安:如果你这么说,你会受到来自我的憎恨,
而且你还会遭到死者的憎恨,这是合适的。
就把它留给我和我身上建议危险艰难之事的东西吧:
将现在此处显现的恐怖者承担到自己的本质中来。
因为我无论在何处都不会经验到
我的死亡不是必须归属于存在这一事情。
伊:如果事情对你显得是如此,那就去!但要知道,你走却没有真理在你身边,虽然对朋友来说,你依然确实是朋友。(GA53,S.123f)
海德格尔认为,伊斯墨涅的话“但是作为开端去追求那不可违逆的东西,终归是不合适的”恰恰从反面说出了安提戈涅的本质。此处的“不可违逆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命运,而句首的“作为开端”并不是一个时间上的开始,而是“统治一切的出发点”,正是安提戈涅对这一不可违逆之物的“追求”才让它进入到统治一切的出发点。但是,一般将这句话翻译为“一个人不应该去追求不可能的事物”并不能传达这里的意思,而且这样一来伊斯墨涅所说的就成了某种处世智慧那样的东西,这同样贬低了伊斯墨涅——这位妹妹十分了解她的姐姐要去做的事情,虽然她的知识与安提戈涅的并非同一种知识。
接下来安提戈涅所说的“将现在此处显现的恐怖者承担到自己的本质中来”就从正面说出了安提戈涅的本质,即pathein to deinon〔承担恐怖者〕。这里的pathein〔承受、受苦〕构成了作为希腊悲剧“行动”的to drama〔戏剧性〕的基本特征,而这一承受恰恰与恐怖者有着根本的关联。安提戈涅承担的恐怖者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如下事实:她将不可违逆之物作为决定一切的出发点,因为这就是命运向她显现的东西,没有人知道它从何而来。这样一来,安提戈涅就被移出了所有人类的可能性,与一切存在者的场所相冲突,甚至否弃了她自己的生命。如果说,作为最恐怖者的人具有不在家的特征的话,安提戈涅就在这一不在家的领域中超越了所有其他的不在家者。她在一切存在者的场所中赫然耸立起来,甚至高过了同样耸立的克瑞翁——毋宁说她甚至完全走出了这一场所。她是彻头彻尾不在家的。恐怖者对她来说并非过早的死亡,那对她来说本来就“必须归属于存在”。她的死亡就是她的变得在家,但是是在这一不在家状态中并通过不在家状态而变得在家。如果合唱歌第一句说出了人在所有作为恐怖者的存在者中是“最恐怖者”的话,安提戈涅就不仅是这个意义上的最恐怖者,而且还是最恐怖者中的“至高恐怖者”(GA53,S.129)!从这一提法开始,与《形而上学导论》中的解释具有实质性差异的思想开始出现了。这一区别并非数量上的增加,而是本质性的差异。安提戈涅的恐怖之处就在于她是内在地不在家的。但是,情况会不会如此:亦即这一内在的不在家状态不仅与在家状态相隔最远,而且同时又最内在地归属于在家状态,因而是唯一本己的不在家状态?
海德格尔由此再次回到第一合唱歌的结尾段落。很明显,歌队对“恐怖者”的驱逐并非与安提戈涅无关,反而具有根本的关联。但是这一根本的关联绝非字面内容上的“相互拒斥”而已,值得我们深求一步。希腊人对遮蔽之物、亦即已说中的未说之物有着天生的敏感,那么在这句诗中未说的又是什么呢?首先,海德格尔通过引证赫西俄德、品达、毕达哥拉斯学派直至柏拉图对hestia〔灶火〕一词的使用来证明这个词在古希腊意义上意味着“家园”,而家园和“存在”有着本质上的关联,因为这时哲学和诗尚未分离,表示存在的真理的概念必须在神话的或诗意的词语中说出。而如果关于“灶火”的“知识”归属于“在家存在”,那么它必然对前文所说的恐怖者、亦即“不在家存在”已有所知。不仅如此,即便恐怖者被从灶火那里驱逐出去,他们也不会在存在之外,他们所具有的只是关于存在的“臆想”,但并非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们以一种遗忘和盲目的关系与存在发生关联。所以,虽然人“向四面八方出发着上路”,在各式各样的存在者中满世界地追逐,但却无法走出存在之外——因为死亡这一大限最终会让人“走投无路”。与此相反,安提戈涅的主动赴死所承担的就完全是另一种不在家状态。她的受苦、她对deinon〔恐怖者〕的承担乃是至高意义上的行动,这一行动才完成了“变得在家”的戏剧运动。“不在家状态”并没有在这一“变得在家”中结束,反而是首次在其本质中显现出来。因此,“结束语并不只是拒绝了不在家者,而毋宁说是使不在家存在变得值得追问了。……不在家存在将自身显示为尚未苏醒的、尚未决定的、尚未接受的‘能在家存在’和‘变得在家存在’”。(GA53,S135f)
通过上面的论述,海德格尔在结束部分自然得出了“不在家的歧义性”:不在家可以意味着一种放肆大胆,它要在存在者中逼出空间、寻找出路,而它只有在遗忘了家园、亦即遗忘了存在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人之为所有恐怖者中的“最恐怖者”的所在;另一方面,不在家存在也可以通过对存在的“追忆(Andenken)”和对家园的归属而打断这一遗忘状态,这才是本己的不在家存在——这却又是安提戈涅之为最恐怖者中的“至高恐怖者”之所在。这部分内容是《形而上学导论》所完全没有的,也就是他的第二次阐释主要突破所在。但是,安提戈涅究竟是如何成其为“至高恐怖者”的?海德格尔的上述提法与其说给出了答案,不如说呈现出了一个谜。安提戈涅究竟归属何处、又是从何处而来受到问候?她和克瑞翁的对话对此有所提示:
克:你竟胆敢公然冒险,越过这个(我的)法律吗?
安:不是什么宙斯这样要求我,
也不是那与地下诸神亲熟的狄克
在人类中设定这法则,
你的要求对我来说也完全没有显得
那么强,以至于它竟能凭人类的聪明去跨越
那未被写出的、不可改变的诸神的法令。
并不是从现在,也不是自昨天起,而是向来持续地
它本质性地现身。而且没人知道,它从何处而来显现。(GA53,S.145)
用对死者的崇拜或家族血缘关系来为安提戈涅在此的言语和行为寻找原因都是不合适的,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安提戈涅这里的话说的根本不是任何存在者。这个对安提戈涅的存在进行规定者超出了上下界的诸神,更不可能是任何人类的法律。我们不能在任何具体的场合遭遇它,但它总是已经先于任何具体事物而现身了,虽然无人知道它来自何处。安提戈涅必须在其本质中承担起来的东西只能是存在本身,是后者才首先给出了死者的特殊性和血缘的优先性的根据和必然性。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不同于任何现实的存在者,它就不能像存在者那样被发现,而是只能被创建。对存在的创建乃是至高意义上的纯粹创建,亦即作诗或诗化创建(Dichtung)。现在,海德格尔解释的内外两条线发生了有趣的交叠:从内容上说,在合唱歌中说话的当然是剧中的忒拜长老组成的歌队,他们的合唱说出了若干情节和实情;但从本质上看,被诗化创建出来的东西绝不是诗歌中的“一般内容”,而是其诗意的本质。因此,歌队的合唱就在本质的意义上是悲剧的核心,而在这一合唱中说话的是诗人索福克勒斯。如上面已经说过的,存在的真理只有通过作诗才能被说出,而索福克勒斯在这一诗作中创建的诗性真理又是什么呢?
在这一诗意作品中值得被诗化创建的无非就是在不在家存在中变得在家。安提戈涅她自己就是那首在不在家中变得在家的诗。安提戈涅是在本己和至高意义上的不在家存在的诗。(GA53,S.152)
为什么?因为她唯一地归属于死亡这一不可阻止的大限,因为她在她的向死而在中涤除了所有现实性,从而成其为纯粹的能在。她在不在家存在中变得在家,她的存在就是对在家存在的纯粹创建本身,而人类“在大地上”不在家的在家存在亦即“居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诗意的”。人们所以为的合唱歌的“一般内容”反而恰恰是“对独一无二的deinon〔恐怖者〕的言说的独一无二性”,它通过安提戈涅这一“独一无二的形象”而显现出来——“她就是那最纯粹的诗本身”。(GA53,S.149)
从而我们就可以对两次阐释的异同之处做一简单提示了。纵观两次阐释,第二次阐释的最大特点在于提出了“不在家存在的歧义性”,这是在第一次阐释对“恐怖者的双重暴力”的揭示中完全没有的。安提戈涅这一形象的出现,不仅完全满足前三个关键句中的所有规定,而且甚至超出了这些规定。从这些区别我们隐约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techne 的看法有了分殊——他似乎要将作为技术的生产制作和作为艺术的诗化创建做一彻底的切割:前者是不纯粹的、非本己的,而后者则反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安提戈涅作为“至高恐怖者”,她对不可违逆的命运的追求、她对死亡的归属以及她的大胆冒险,依然是从前三个关键句的逻辑中推出的,也就是说,她在受苦中的“没落下行”自始至终处在“悲剧精神”的基调之中。看来,为了更准确地评价海德格尔这两次阐释中的得失,我们就不能囿于海德格尔本人的思路,而要将语境置换到一个更大的视野才能做到。
三、区分三重思维方式
为了对海德格尔思想进行更加准确的定位,我们将已经隐含在上文论述中的三重思维方式清理如下:
(一)表象性思维
所谓表象(Vorstellen),就是将事物摆置在面前,将其把握为对象,这是传统形而上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追根溯源,是语言和意义的产生让人类首先能够看到和理解存在的事物,但我们很快就将这样看到和理解的存在者理解为事物本身,好像事物本身就是它们对我们呈现的那个样子。这样一来,意义的发生过程本身、事物在语言中出现的过程就被忽视和掩盖了。当我们以存在者为尺度来理解存在本身,也就是把事物的存在理解为存在性,亦即物性或在场状态,再通过这样一种物性来理解人和世界,形而上学的历史就开始了。这一思维方式在发展过程中当然经历过重大的变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通过意识的反思结构而将人设定为主体。这一主体并不是现实感性的人,而是一套形式化的逻辑结构,而正是绝对主体性为现代科学对世界的征服提供了保障①黑格尔为了克服以现代主体性哲学为代表的二元分裂世界观时试图诉诸古希腊逻各斯意义上的客观理性,但现代科学正是顺着黑格尔的“客观逻辑”而完成其世界统治的,这一点连列宁都看得很清楚,他在对黑格尔《逻辑学》最后一页关于逻辑观念向自然界过渡的论述进行批注时就说:“唯物主义近在咫尺。”参见列宁:《列宁全集》(第5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202 页。。这一“人”成其为现代无条件主体性的过程,被海德格尔称之为Aufstand〔起立〕,也就是人完全实现双脚站立,世界则完全变成摆在主体面前的客体,这样的绝对主体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为自己设定尺度。当今从北美发源、向全世界推行的科学主义机器人道路就是其直接后果。
(二)悲剧性思维
前文已经论及悲剧精神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内容,实际上,如果说整个形而上学史都是基于追问“存在者的存在”的主导问题(Leitfrage)的话,海德格尔的存在史思想则基于基础问题(Grundfrage),后者问的是“存在的真理”,也就是存在者在其中显现的自明状态或意义空间,而这又是奠基于并保存于具体的历史性人类存在之中的。由于任何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追问都无法脱离后者而独立自存,但又意识不到后者,因此后者就似乎作为“虚无”而被排除在形而上学追问之外、并恰恰因此而成为烘托形而上学的语境或地平线下的“基础”,此之谓“存在的遗忘”。那么,悲剧精神又是如何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呢?前文已经指出悲剧精神的要害就在于“在必然性的命运面前施展最高的违抗,以便同时在毁灭的快感中完成命运的强力”,这一“用技艺反抗命运”的思路的核心就在于将遭受的痛苦(pathos)转化为强力。尼采所谓的“积极的虚无主义”无非就是通过对“过去”的复仇而获得现世的“强力”,直至下一个新的“轮回”。这样一来,诅咒必然如影随形。而通过清理海德格尔的第二次《安提戈涅》讲座,我们看到,安提戈涅的形象属于在技术统治之外的极少数另类个体,正是通过她进入深渊的下行没落才开启出一种视觉,一种对命运的直观,由此她才能够说她所归属的地方“超出了上下界的诸神,更不可能是任何人类的法律”。这意味着与技术的现实性领域进行最深刻的切割:在时间中轮回的技术能够在可见的存在者领域呈几何数级地增长进步,但它并不能触及那个领域分毫——那就是安提戈涅知道她所归属的、从那儿受到问候的领域。触及这一维度,我们也就走到了悲剧性思想的边界。
(三)反身性思维
安提戈涅所归属的维度,类似于我们所理解的天道,它是最深的开端、最长久的先行、超越一切赶超者,任何人类的计算、制作和意向性投射都无法穿透它,因而它绝对不可被对象化。触及到这一维度,反身性思维也就开始了。然而要真正跨过这一步,绝非易事,因为这从根本上来说并非人力可办。在海德格尔思想与言说的穷竭处,我们想借助若干中国思想来说明这一问题,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思想的主脉即是反身性思维。以“存神过化”为例,“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长,顺焉可也”①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17 页。,因为一旦去思神,我们的神就已经外驰了,所以必须用“存”;而所谓“化”就更是如此:“大可为也,大而化不可为也,在熟而已。”②张载:《张载集》,第17 页。归根结底,“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后能穷神知化。”③张载:《张载集》,第17 页。因而所谓存神,也就是持不可持之灵台:“灵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④钱穆:《庄子纂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版,第203 页。。按照钱穆的解释:“有持而不知其所持,所存者神也;不可持,则所过者化也。”⑤钱穆:《庄子纂笺》,第203 页。但是这与上面说的不可对象化的维度有何关系?因为此处的“灵台”并非作为主体的人之意识,而是“天之凝于身”,因而“凝神”本身就是“合天”,而非用我们的心神去合一个外在的天。实际上,只有从反身性思维出发,我们才能够原原本本地理解中国思想中的很多关键概念。例如,关于“虚”这一概念,我们就甚至不能将其解释为“将身体或内心倾空”之类,因为“虚”本身即是反身!同样,所谓“德”乃是“道之得于心,天之充于身”,不存在与人之德性脱离的天道,而这也只能在反身性思维中才能理解。因而,如果有谁把“虚静”说成“道体”的某种“属性”,他明显是将表象性思维带入了反身性思维的领域。
四、结语
我们认为,海德格尔虽然触及了反身性思维,但并未跨过这一步。这对中国思想的意义在于,用包括海德格尔哲学在内的任何西方思想来“重构”中国哲学的做法终归是徒劳的。但是,海德格尔仍然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因为他前所未有地揭示出了西方人性中的技术性本质,因而一旦我们跟随海德格尔走到西方传统的边界、直观到西方的本质,返回我们自身的契机也就开始了。“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能否回复自身的人间正道、“天堑变通途”,我们今天也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