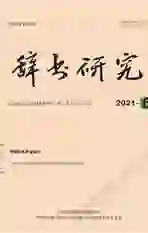才情未竟的词典学家
2021-12-06郑伟
郑伟
摘 要 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学,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他早年投身于包括汉字检索法、国语运动、汉语方言调查、中国古音学等语言文字方面的事业之中,所编《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饮誉中外。近来林语堂晚年致陈守荆的数百封书信公之于世,让学界更全面地了解到林语堂晚年在辞书编纂方面的功业和诸多史实的细节。
关键词 林语堂 国语运动 辞书编纂 袖珍词典 中文字典
一、 引 言
中国(香港)嘉德拍卖公司(China Guardian Auctions)為配合“尔意轩珍藏‘林语堂晚年书信”这一批珍贵藏品的展览(香港会议展览中心,2021年4月18—23日),编辑了一部名为《故纸清芬见真如:林语堂手迹碎金》(以下简称《手迹》)的资料集,其主体内容是林语堂(1895—1976)自1948年至1976年亲笔所写的477封书信(另包括语堂夫人廖翠凤女士及其友人书信数十封)和一些珍贵相片、文献等34件。除个别信件外,收信人均为尔意轩主人、语堂先生的甥媳、义女兼秘书陈守荆女士,故而此集亦可称之为“语堂晚年书信”。
《手迹》虽非公开出版物,但以精装书的形式印制,文质俱佳。《手迹》为32开本、精装彩印、繁体竖排,共1140页,包括“简介”“年表”“引言”“文章”“内容”五个部分。“简介”部分(14—19页)[1]对语堂先生作为作家、学者、发明家、语言学家诸方面的成果做了概述,并提供了林氏中、英文著作,作品翻译,发明专利,创办杂志的著述列表。“年表”部分(20—27页)则为林语堂生平大事记,从中可以对林氏的一生做一概观。“引言”部分(30—37页)是一篇题为“尔意轩珍藏‘林语堂晚年书信”的文章。接下来则是一组文章(38—77页),内容涉及林语堂的画作《双骏图》、为派克钢笔代言、作为词典学家的业绩、对《红楼梦》的研究与翻译、诺贝尔文学家提名等诸多细节。
《手迹》回答了学界迄今诸多未解之谜,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例如林语堂英译《红楼梦》为何没有直接出版,却先在日本出版了由英译本转译的日译本?《红楼梦人名索引》是否为林氏的唯一遗著?林语堂晚年还有多少未竟之作?作为“跨文化双语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林语堂1972;以下简称“《汉英词典》”),该书出版后的销售及版税情况如何?
至为重要的一点,如《手迹》编者在书前所介绍的:“尔意轩主人陈守荆(Francisca Shou-Ching Chen)女士是林语堂在世最后十年(1967—1976)在台北的秘书。她在1967—1974年间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协助《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的编务及后续工作。林语堂在该词典的Introduction中,也特别感谢守荆的协助。”(30页)又说,“这套书信的源起是词典的编纂,包括《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以及后续的两部词典。一部是以上述词典为基础,以《牛津简明英语词典》( 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为构想的《袖珍汉英词典》,二是《林语堂中国新词典》。因此这套书信是研究语堂作为词典学家(Lexicographer),特别是汉英双语词典学的重要研究资料”(32页)。
二、 林语堂对汉字检索法的终生情结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语言文字层面的核心问题,包括“文字改革”“国语运动”“汉字拼音化”等。文字改革的内容,涉及是否废止汉字,抑或如何将汉字由繁化简等;推行国语,则与如何处理文言与口语,以及如何制定共同语的标准,以何种方言为标准语等有关;汉字拼音化与文字改革相关联,涉及使用何种拼音化方案和其中的细节性问题。而林语堂终生最关心的语文改革层面的问题,恰恰都不是以上这些,而是“汉字检字法”的创制与改良。
1907年,林语堂入厦门鼓浪屿寻源堂读书,在这所教会学校学习期间,林语堂就已经“萌生了改良传统部首检字的想法”。中学毕业后(1911年),他到了上海,就读于圣约翰大学英文预科,一年半以后开始读本科,191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即北上,任清华学校英文教员。他公开发表的语文改革方面的作品,如《创设汉字索引制议》(《科学》3卷10期,1917年)、《汉字索引制说明》(《新青年》4卷2号,1918)、《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新青年》4卷4号,1918)、《汉字号码索引法》(未刊,1924)、《末笔检字法》(1925,此为专书,商务印书馆印行)、《图书索引之一新法》(《图书馆季刊》,1卷1期,1926)诸篇。
有鉴于“旧有字书,因仍不改者二百有余年,而检字法迂缓,隶部纷如,不适今用。当此普及教育之世,检字必有一简便捷速之新法,使学者尽知字典之用,而后自修有道,且检字不至于费时也”,林语堂在《汉字索引制说明》一文中提出了“首笔检字法”(即某汉字的首先笔画),并指出“首笔原系母笔所合而成。计汉字中,凡有十九母笔”。这十九种母笔分别归入横(6种)、竖(5种)、撇(4种)、捺(2种)、钩(2种)。(林语堂1933)271, 274该文另附有蔡元培序和钱玄同跋。林语堂曾在《忆蔡孑民先生》(1965)一文中回忆当时写作此文并征序于蔡元培的情形,“当时我编汉字索引制,对《康熙字典》首发第一炮攻击。这篇文章有钱玄同跋及蔡先生序,在《新青年》发表。后来诸新索引法,皆不出此范围。我当然求蔡先生的序。那时我未入北大,在清华教书,因此事去见蔡先生”(林语堂1994a)377。
据钱玄同1918年1月5日记:“黄昏撰林玉堂(语堂)之《汉字索引制》跋一篇,约千余字,亦预备登《新青年》者。”(钱玄同2014)327从林语堂后来的回忆可知,他对于钱玄同早期激进的语文改革主张并不赞成(林语堂1994b)297-298:
钱玄同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之一,也是力主改革的思想家。他专攻的学术是语言学。他倾全力提倡中文的拼音和中国文字的简化。在他反对儒家的一切思想,而且对一切都采取极端的看法这方面,我觉得他是个精神病患者。我认为在提倡社会改革上,应当采取中庸之道;但是在争论“把线装书都扔到厕所中去”,一般人听了确是心惊胆战,因此在宣传上颇有力量。
在那个文化界高唱“打破新世界、建立新秩序”论调的年代,林语堂自己也曾有很激进的主张。钱玄同1925年4月10日记:“林玉堂来信一通,拟登廿三期《语丝》,他赞同我那‘欧化的中国人之说,……这话甚是。”(钱玄同2014)632林语堂在1925年4月20日发表于《语丝》的《给玄同的信》中说:“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钱玄同认为这番话“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以前只有吴稚辉、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讲过这样的话”(钱锁桥2019)460。而且,钱玄同的思想很快也由激进归于冲淡,他在1927年8月2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我近来思想稍有变动,回想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今后大有‘金人三缄其口之趋势了。新事业中至今尚存自信为不谬,且自己觉得还配干的唯有‘国语罗马字一事,然而对于此事之努力,我远不逮元任、劭西两公,深为可愧!”(钱玄同2001)118
关于《末笔检字法》一书,《手迹》(422页)所收“语堂晚年书信”中,有一封为1972年9月28日致陈守荆函曾提及:“又Xerox(复印)旧书,海内孤本,1925年商务出版之《末笔检字法》,专以右旁排列,以便研究,如此则无左旁部首。”林语堂在编制汉字索引方面的功业,还对洪业(1893—1980)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3年8月,洪业先生回到中国,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代理主任。回国之前,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历史学硕士学位,但未能完成博士学科课程的修习。据洪业回忆,在美期间,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读到了林语堂关于汉字索引的书,该书“把中国字形分为十九类”,另外洪业“也知道图书馆员很多都用‘永字法”,于是“便采用各种检字方法,玩摩几千个卡片,创立了他自己的方法,名之为‘中国字庋撷法”。(陈毓贤2013)130
从内容上看,洪业读到的应是林语堂《汉字索引制说明》这篇文章,而非《末笔检字法》这部专书,因为洪氏在美期间,林书尚未刊印。洪业回国后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制了数十种中国古籍的索引。这一项蜚声宇内的成就,显然也得益于洪业早年对汉字索引方法的探讨。
林语堂晚年在汉字检字法上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上下形检字法”,并将其运用于《汉英词典》的编纂之中。《手迹》(591—593页)所见珍贵资料之一,是林氏于1973年6月19日致守荆函所附亲笔手写“上下形检字法的详细说明”,详细述及了林氏发明此种检字法的经过:
本人发明汉字索引制,起于1917(年)。五十年来,梦寐不忘(见1917《新青年》蔡元培序)。嗣经迭次改良,为中文打字机之键纽,第一架1932年。第二架为“明快打字机”。1948(年)(附件第四)嗣为美国国际商务机器公司IBM所采用,为中英翻译机器之一部(附剪報),又为波士顿ITEK公司采用,名CHICODER(二者皆美国空军出资制造之中美翻译机器)。1966(年)本人回台编辑中英词典,以字典与打字机性质不同,又得改良简化成为上下形三十三个根本笔形(以前打字机用六十八个),始成今日形式。此三十三个上下形打字机,此未曾见过,是一项发明。
从“语堂晚年书信”中可以看出,关于“上下形举例表”以排印还是手写方式出现在《汉英词典》,曾有过一番争论。1972年6月22日语堂致守荆函提到,“日本研究社人今日由东京至港,下礼拜一我拟过去九龙与他们讨论问题。……又上下形举例……拟令照相,不使日本重排,此亦一段佳话,可流传千古也”(345页)。几天之后,6月26日函中,之前的设想只得变更,“讨论结果,仍用排印,较为整齐,……我也不愿持之过急,所以让步,各种委屈,只有你知”(347页)。数月后日本方面印就《汉英词典》,将五十部样书寄语堂,仍采用了守荆的手写版本,“上下形举例一页,在词典封面底内页有宝墨,为词典增彩。这就是以前所争之点,现在成功,心里多快活,词典也宝贵起来”(460页)。语堂于1976年3月26日逝于香港,此前1975年2月至1976年1月间,他多次致函守荆,谈及“近日专心改制上下形的排法。却觉得很不容易,真心问你有何不良的地方”(931页),“现在把上下形重新改添一两字,加‘X号,余不改”(934页),“上下形我已作最后决定,如11、 12、 13、 21、 22等横格,又有删汰的……字样请寄来,完成此事”(959页)。最后一封论及上下形检字的信写于1976年1月21日,说“昨日用不少心血,定上下检字表文。分10、 20、 30及10、 11、 12之分别。虽然极简单,写法却不容易”(1090页)。可见,汉字检索方法的改良,无愧为林语堂的终生志业。
三、 作为语言学家的林语堂与赵元任
1932年以后,林语堂向语文学(语言学)挥手告别,除了次年发表《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林语堂1933)和将历年所撰相关论文编为《语言学论丛》(1933b)之外,他余生再也没有在语言学领域发表过研究性论文(纪念类、通俗类、序跋类文字等除外)。林语堂在自传、回忆类文字中,似乎没有明确提到过个中原因。他后来对早年的专业选择倒是有段回忆,“我初入圣约翰时,我注册入文科而不入理科,那完全是一种偶然的事罢了。我酷好数学和几何,故我对于科学的分析之嗜好,令我挑选语言学而非现代文学为我的专门科,因为语言学是一种科学,最需要科学的头脑在文学的研究上去做分析工作。我仍然相信我将来发明最精最善的汉文打字机,其他满腹满袋的计划和意见以发明其他的东西可不用说了”(林语堂1994c)16。
他将语言学当作自己的“本行”,在《重印〈语言学论丛〉·序》中说:“后来我走入文学,专心著作,此调久已不弹,然而始终未能忘怀本行,凡国内关于语言文学的专书,也时时注意。”(林语堂1994a)191马悦然(1924—2019)在《想念林语堂先生》(2015)237-238一文中回忆说:“高本汉给他的学生们讲汉语历史、音韵学和方言学的时候,有时提到林语堂先生在那些方面的著作。我那时发现林语堂不仅是一位精彩的作家和评论家,他也在汉语历史、音韵学、方言学、辞典编辑法、目录学各方面有重要的贡献,并发表在不同的学术杂志上。”
语言文字方面的“国故新知”,受众太小,完全不像写文学作品、时论杂文来得深入人心(包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林语堂弃语(言学)从文(学)完全在情理之中。有论者指出,“他早年研究语言学是受了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但是他的性情属于自然活泼的一派,不愿为‘汉学的清规戒律所束缚,更不能长期忍受其枯燥和琐碎,所以终于舍去不顾,转而提倡幽默,归宗于晚明公安三袁以至袁枚的文学性灵说。这一转变使他的性情和学问融合为一,他真正找到自己了”(余英时2006)462。但如果从当时学界的学人关系及实际情势的发展这些客观因素来看,我们并不难对其做一番合理推测。
此处不得不提到与林语堂年纪相仿、学习经历和专业相若、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1892—1982)。对于语言学,两人都可称得上“半路出家”,林语堂本科、硕士阶段的专业分别是英文与比较文学专业,博士阶段才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专研中国古音学;赵元任本科学数学,研究生阶段攻读哲学,博士毕业后曾在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教物理学。学成归国后,国语、古音、方言、辞书等,都是二人同时感兴趣并做过深入研究的领域。而且,二人都曾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差不多的时间去国赴美(林氏晚年则居留于台湾、香港两地),从此“不知梦里身是客”。同时,林、赵二人也是一生的朋友,从《赵元任年谱》(赵新那等编1998,以下简称《赵谱》)记录的信息来看,不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台湾,赵、林两家都有着虽然次数不多但却未曾间断的友好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两人在事业上的隐性竞争,也显而易见。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绝无“捏造”史实之意,更无意曲解二人关系,而是希望从学术史角度,说明对林语堂志业转向的个人及时代背景。从汉字拼音化、方言调查研究、辞书编纂等不同方面,均可比较出林、赵二人在学术追求上的异同。
(一) 汉字拼音化(拉丁化)
该设想自清末便已经开始,王照、劳乃宣等便是“切音运动”的支持者。章太炎评论说:“清末妄人,欲以罗马字易汉字,谓为易从,不知文字亡而种姓失。……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潘重规2016)37章氏特别强调了汉字对于国家统一、超越各地方言所起的作用,“废则言语道窒,而越乡如异国矣”(汪荣祖2008)139。不过,虽然章氏并不反对汉字注音方法的改良,“尝定纽文为三十六,韵文为二十二,皆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以代旧谱。既有典则,异于向壁虚造所为,庶几足以行远”(章太炎1908)62。
1923年,“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成立,所聘委员有钱玄同、黎锦熙、黎锦晖、赵元任、周辨明、林玉堂(语堂)、汪怡、叶虚谷、易作霖、朱文熊、张远荫十一人。1925年9月,刘复发起成立了“数人会”,在京成员有刘复、钱玄同、黎锦熙、汪怡、赵元任、林语堂六人。赵元任先后发表《讨论国音字母的兩封信》(1922)、 Ten Objection to Romanizing Chinese (1923)、 Principle of Romanization (1923)、《再论注音字母译音法》(1923)、《国语罗马字的研究》(1922—1923)、《新文字运动的讨论》(1924)、《国语罗马字与威妥玛式拼法对照表》(1929)、《罗马字母名称的练习句子》(1929)、《罗马字的行文》(1929)、《国语罗马字常用字表》(1930)、《国语罗马字》(1936)、《国语罗马字的特点》(1936),并以“数人会”名义发表 Gwoyeu Romatzyh (《国语罗马字》,1926),与钱玄同、黎锦熙合撰《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赵元任说:“中文之罗马字化是中国人自己为中国之需要而提出的改革方案。”(《赵谱》,121—224页)
《赵谱》(138、 153—159页)提到,“元任热心推行罗马字,那时写日记以及与钱玄同、林语堂等人的通信也都采用国语罗马字”。1928年9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并宣称:“兹经本院提出大学委员会讨论,认为该项罗马字拼音法式,足以唤起全国研究语音学者之注意,并发表意见,互相参证;且可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以便一切注音之用,实于统一国语有甚大之助力。”同时,“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部聘委员有三十一位,蔡元培、胡适、钱玄同、刘复、周作人、魏建功、黎锦晖、许地山、沈兼士、白涤洲、赵元任、林语堂等人均在其列。
自1937年开始,虽然赵元任仍在“从事民众教育和国语统一运动”(《赵谱》,216页),但当年没有再发表国语罗马字或注音符号方面的成果,这固然可能因为是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所任职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陆续迁往长沙,但这并非直接因素。1938年5月3日,赵元任致胡适信中说道:“近时拉丁化与G.R.(国语罗马字拼音缩写,下同)时有争论,我觉得这个在这时殊属无聊。我对于G. R.曾告假一年,现拟续假一年,对外仍用威妥玛,对内用IPA(国际音标),日记上漫无标准。以后想作一种国文罗马字,采Les Pères Lamasse et Jasmin的 Romanisation Interdialectique 之原则而不必如他们那末奴从高本汉之中古音。暂时维持汉字(你去年所谈)我相当赞成,但近日教部禁止中小学用钢笔铅笔(除理科外),我认为是病态心理。”(《赵谱》,232—233页)赵元任所谓的对于G. R.的“告假”及“续假”,其实就是要“告别”国语罗马字的意思。后来其在美从事中文教学,国语罗马字对外国人学习汉语帮助很大。
1938年8月1日,赵氏一家从云南昆明取道越南河内,再到香港,再度离境赴美,拟于夏威夷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接下来战事日紧,赵元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年的“告假”终成永久的离开。蒋梦麟对赵元任“故国可家”的殷殷期盼,亦终幻泡影。1940年2月22日、3月5日傅斯年曾分别致函赵元任和胡适,谈及“元任此去两年,有形之损失已大,无形之损失更大,……而元任身体不佳,虽愿与我们同甘苦,但恐身体不赞助其精神耳”,“目下最好是能为元任募到薪水留Yale。还有一好办法,即为元任募到一点薪水回中国。……总之,他们回来我们最高兴,其薪水及工作费用毫无问题”云云(王汎森等2014)808-809, 813。
我们不妨再看一看“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当时对汉字改良和汉字拼音化方面的意见,胡先生在《答蓝志先书》(1919年3月23日)里说:“我们希望——注意我们现在不过希望——将来能有一种拼音的文字,把我们所用的国语拼成字母的语言,使全国的人只消学二三十个字母,便可读书看报。至于‘古来传承的文字尽管依旧保存,丝毫不变,正如西洋人保存埃及的象形字和巴比伦的楔形字一样。”(姜义华1993)296可见,这里是主张推行拼音文字,同时原封不动地保留汉字。到了1923年1月12日所作《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卷首语,已经开始“褒扬破体字的改变”,即主张对繁体字加以简化,“采用这几千个合理又合用的简笔新字来代替那些繁难不适用的旧字”(姜义华1993)316晚年被问起对汉字拼音化的看法时,胡适不置可否,仅以“兹事体大”作答。(唐德刚2005)145
另一方面,同样是主张汉字拼音化的一派,内部也有若干见解的分歧。钱玄同1918年2月8日曾记录刘半农的意见:“半农对于注音字母不甚赞成,谓最好用‘福乃惕克(引者按:即英文phonetic音译)标注中国音。”钱氏的意见则是:“汉字未废以前,小学教科书非仿日本汉文旁注假名之法,实难正其音读。故吾谓注音字母在暂时尚用得着也。”(钱玄同2014)333
相较而言,汉字拼音化的工作,林语堂虽然参与其中,但远不如赵元任投入,也非他对汉字检索法革新的兴趣可比。早年仅有《国语罗马字拼音与科学方法》(1923)、《赵氏罗马字改良刍议》(1924)、《汉字中之拼音字》(1931)、《谈注音字母及其他》(1933)等少数几篇文章谈及此事。理由也不难索解,林语堂的一贯主张,是汉字不必打倒,主张汉字简化、俗化(周质平2013)22-23,且矢志不忘中文打字机的发明与改良。他晚年曾回忆说:“我对华文打字机及华文检字问题,可以说是自1916年起,经过五十年的思考,并倾家荡产为之。”(林语堂1994a)195
历史学家黄仁宇(1918—2000)对黎锦熙(1890—1978)、林语堂两位汉字改革的健将曾有一段风趣的回忆,“黎锦熙提倡汉文拉丁化,首先在福州路张开布幔,大书‘大炮响了,林语堂在北京还是循规蹈矩不离主流,及至上海才主张国难与否,人生总要追求生活之情趣,从此成为‘幽默大师”(黄仁宇2019)258。此处黄仁宇的表述容易引起误解。1926年9月,林语堂任厦门大学教授、文科主任,1927年3月辞职,北上至上海再到武汉,1927年9月,林语堂又回到上海专事写作。而林氏在《晨报副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一文,其首次将英文humor译为“幽默”是在1924年5月。(刘炎生2015)221932年,林氏创办《论语》半月刊,号召中国文化引进幽默,后又相继推出《人间世》和《宇宙风》两种刊物,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林语堂被奉作“幽默大师”。(钱锁桥2019)92《晚年书信》有一函(1971年11月2日)专门忆及此事:“《论语》时事短评最精警及婉讽刺中时弊文字,所以‘幽默大师之学皆由《论语》文字而来。”(445页)
(二) 现代方言调查研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林语堂先后发表《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1923)、《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1924)、《征求关于方言的文章》(1925)、《方言字母表》(1925)、《关于中国方言的洋文论著目录》(1925)、《闽粤方言之来源》(1928)等论文。
傅斯年1929年4月2日致林语堂函提及,有“令兄和清先生[引者按:即林憾庐(1892—1943),福建龙溪人,林语堂三哥]肯来助理先生调查闽语,至为欢迎”,“先生如何布置一时间,为我们研究所作某地(尤其是闽区)方音调查,当至感荷”云云,可见林语堂当时有展开闽语调查的计划。傅氏此函还提及助理员专业训练、相关薪酬及任职细节,“弟觉发音训练,似乎可请先生费神,留和清先生在上海多住些时,俾练习得有把握,然后所得材料,可免一大部checked之势”,“薪数因目下全所助理员薪最多者百二十元,只此一人,其余均百元以下,故只好请和清先生屈受此百二十元之薪”,“和清先生手续,须由元任先生签名,(他为弟勉为汉语组主任)由弟呈院长核准。现在元任未在广州,须待其返,办此公事,然只手续上事耳”。(王汎森等2014)145-146
但是,林语堂在闽语调查方面的志业,由于是年春天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广州迁址北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搁浅,而且从傅斯年于是年8月致林语堂函来看,之前傅氏所答应聘林和清为助理员并协助林语堂进行方言调查事已无法兑现(王汎森等2014)161:
先是先生提到和清先生事,弟正在广州,闹着搬家、改组等等麻烦,彼时全未虑到搬家后之自有搬家后之办法。先生来信,欢喜之极,马上答应。但彼时广州局面已是搨台,院中与弟之意见不一致,而广州同人闹意见,故原来在粤一所之精神虽折作二分而不止,而原请下之人物固皆在也。到平后,不啻重组织一所,两所共一费,焉得不生困难。费尚是其次,办法之变更尤大。在粤时,弟未有若何经验,何缓何急,全无充分之认识。到平后,大家以為如此少钱,如此名义,如此时局,如不切实收缩一下,简直不得下台,故决定:一、全所完全集中在北平。二、停止所外一切工作。三、专办几件事,凡在至少一年之内,不可以刊布之工作,皆停止。
虽然傅斯年言辞恳切,但其“出尔反尔”已成事实。当时林语堂受蔡元培邀请,任中央研究院的英文主编,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29年7月所定薪额为五十元)。在此封函件之前,傅氏应该已经跟林氏表达过类似的意见,而林氏也因此有所质疑,所以傅函后面才有“上述之决定,完全实行,来信云并未停止一切所外工作,想是传说者误”一说。关于方言调查事,傅函也曾与赵元任商议,有“他极赞成此举,……但后来大家商量,相约以不作一个例外为办法,故弟虽以心虚迁延又迁延,终不免发前一电也”云云(王汎森等2014)162。傅函透露的意思,只有“所内”工作(如赵元任主持的两广方言的调查),或者是应属“专办几件事”之列(如明清档案的整理),才能获得经费支持。林语堂非专任研究员,从事的研究又属于“至少一年内不可以刊布之工作”,自然也就无法进行了;而且,傅函已言明,作为同行的赵元任也赞成“照章办事”。
1925年4月下旬,赵元任一家从法国启程归国,5月28日到上海,6月9日到北京,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身份,入住清华园南院。赵氏讲授的课程包括《方言学》《普通语言学》《音韵学》等。1927年9月,开始计划吴语的调查工作,记录了33个方言点,12月下旬方完成。1928年8月,接受傅斯年的邀请,加入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主持语言组的工作,是年10月底到广州,旋即开始了两广地区粤(广州)、客、闽(汕头)等方言的调查。次年随研究所北迁后,实地调查无法开展,主要是做旧材料的整理,直到1932年2月赴美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主任。(《赵谱》,130—133、 147—179页)
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另一位专任研究员罗常培(1899—1958)在《厦门音系·自序》里说:“十八年(引者按:即1929年)余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自粤迁平,获与赵元任先生研讨语音,析疑辨微,受益匪浅。每思记录一地方音,以验个人审音之造诣,并就正于元任先生。……本书之成,承赵元任先生恳挚修订,林语堂先生精审校阅。”在该书“英文叙论”部分,罗氏还自陈其对语音的兴趣源自赵元任的指引。[For the completion of this monograph, I am indebted to Dr. Y. R. Chao (赵元任). He is the one who has inspired my interest most in the study of phonetics. This book may indeed be called the exercise work of his phonetic class.](罗常培1931)xiii
综上可见,在闽、粤方言的调查方面,赵元任、罗常培两位已“先拔头筹”,做了先驱性的工作。林语堂(1926)在《闽粤方言之来源》一文中,有专节论“闽粤方言之重要”,所以他有闽、粤方言调查的计划,自然在情理之中。但赵、罗两位的成绩在先,再加上出人意料地失去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支持,林氏后来心灰意冷放弃此业,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当然,正如上文所此指出的,客观因素固然存在,主观上的理由或许更为直接。
(三) 辞书编纂
汉字检索与辞书编纂密切相关,因为有用的辞书离不开精良的检索方法。出于不同的主客观因素,赵元任、林语堂先后投身于编字典这项事业中。区别在于,赵元任此举,主要是中年时期在美谋职的情势所需,而林语堂晚年投身此业,完全是对其终身关心的汉字检字法、中文打字机等自然延续的结果。
赵元任自1938年赴美后,先后在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短期任教。1941年7月,应哈佛燕京学社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教授邀请,到哈佛大学参加一项字典编辑工作,具体做法是“从若干(包括《佩文韵府》等)中国字典和两本外国中文字典剪贴1250000张卡片上这么一项工程”,以及“在字典上标古音和国语,以及粤语、福建、苏州和长沙等方音”(《赵谱》,260页)。次年着手进行R. H. Mathews所编写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汉英字典》)的修订工作。1943年,应战事需要,哈佛大学开办了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中文部由赵元任主持,为了配合中文的教授,他与杨联陞合编了 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 (《国语字典》,1945年完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
1972年3月29日,赵元任在第24届“亚洲研究协会”会议上做了题为 Problems in Chinese-English-Chinese Lexicography (《汉—英—汉词典编辑中的问题》)的演讲,正式发表时,赵元任已将林语堂于是年十月新出的《汉英词典》列入了参考文献(Chao 1972)。而林语堂尽管早年写过《分类成语辞书编纂法》(1918)、《编纂义典计划书》(1928)等专论,但是真正开始编字典,则要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
四、 林语堂晚年在词典编纂上的功业
《汉英词典》为林语堂晚年所编就,被誉为其“一生的巅峰之作”。正如《手迹》前附《词典学家林语堂先生:未完成的词典三部曲》一文所说:“这是在西人1892年翟理斯(Herbert A. Gilles)和1932年麦氏(R. H. Mathews)所编的两部汉英词典之后百年来的头一部汉英词典,也是华人所编的头一部汉英词典,也特别要反映出当代汉语的使用。……《语堂晚年书信》中的主题便是这部词典和两部后续词典的编纂过程,内容丰富,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44—45页)
《汉英词典》出版后的第二年,林语堂开始撰作《八十自叙》,为的是将“生平事业及少时至入大学,法德美国游记,做一总生平行述留与后人”(655页,1973年9月24日致守荆函)。他说:“《当代汉英词典》之完成,并不比降低血压更重要,也比不上平稳的心电图,我为那本汉英字典,真是忙得可以。我一寫完那好几百万字的巨册最后一行时,那最后一行便成为我脚步走过的一条踪迹。那时我有初步心脏病的发作,医生告诉我要静养两个月。”(林语堂1994b)313
但是,《汉英词典》尚未出版,林语堂便已马不停蹄地进行袖珍版汉英词典的编纂。他曾回忆早年就读圣约翰大学时对袖珍英文字典的偏爱:“我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这本英文字典,并不是把一个英文字的定义一连串排列出来,而是把一个字在一个句子里的各种用法举出来,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义,而是那片语,而且与此字的同义字比较起来,表现得生动而精确,不但此也,而且把一个字独特的味道和本质也显示无余了。……我就从这本字典里学到了英文中精妙中的片语。而且这本字典也不过占两双袜子的地方,不论我到何处去旅行,都随身携带。”(林语堂1994b)268六十年后,到了正式着手编纂袖珍版汉英词典时,仍然持此观点。《手迹》“特藏文献”部分收有“林语堂《汉英词典袖珍版》的说明(影印件)”(1972年6月30日函附件,109页)、“林语堂袖珍汉英词典样张(四页)”(118—119页)两份材料。
1972年3月4日语堂致守荆函,谈及《汉英词典》的海外销售代理,以及袖珍词典事宜,“现正去函小野及臧广恩,顺侯起居并提袖珍字典事,谅必不误。此事我甚关心,……潘光迥接洽全球代理事,Pergamon及McGraw-Hill、 Readers Digest及Longmans Green皆有此意,接洽条件,此是好消息。全球代理解决就有头绪,或者‘袖珍并可解决”(325页)。6月30日函说,“前两天正是无聊,以致精神不振,因为没有工作。……前天(廿八日)决定开始工作,乃一切复原”,同时亦谈及袖珍词典的编辑方式,“三年之内,不会出版,(否则)恐影响大本(引者按:即《汉英词典》)的销路。目前工作只是缩小,删除重复及不合现代之字句。以后再进一步,随时添补”(348—349页)。
是年7月至9月,林语堂有多封长函,与守荆讨论袖珍词典的编纂细节,如7月1日函涉及袖珍词典的注音体例,所举包括“一字有数音、数种读法”“两音皆可读者”“可轻声可不轻声”“两上声相接变为阳平及上声”等不同情形。至于词典的规模,此函说《汉英词典》“现估计1850页,袖珍本约1200页便可”。但随着编纂工作的推进,实际篇幅已不止于此。8月7日函说,“Pocket(引者按:Pocket和POD皆指袖珍词典)修改工作现初稿已改至1150页,其余共1450页,1150页后未改正。我要各复词联为一段及中文改在罗马字拼音之前,并以‘~代本字,系全书体例,不需逐字改正”(381页)。9月18日函提及“1973秋季以前,大学必跟我做合同(袖珍)”(414页)。
1973年3月23日函提及,“中文大学POD事来秋定夺,不致有误。不日当与宋淇商定”(533页)。3月26日函说,“我们计划之中文新字典到底能推销通行与否,须要我们的字典好不好及对此推销广告能否尽量做去。所以编辑须求尽善,……成语之例亦多入单字,如‘天高地厚多多举例。字典之好坏全在此等处”(535页)。4月4日,语堂收到日本研究社寄来的用日文回信,述及袖珍词典的编排问题,“其余样张系依我的信,重新排序,尽量省地方,以求合袖珍之用”;编辑体例问题,如“复词第一字改用‘~,一字两读音之破音字即拼全字而不用‘~号”等。总的预期是“中国袖珍字典篇幅力求小以致太厚,不如略放宽面簿,携带便利”(540页)。
是年6月,袖珍词典初稿已毕,6月20日语堂函说,“Pocket删订已完,今日按船邮寄去,如此以第二批。合上回寄去第一批及卷前卷后(序、英文附录等),并合为词典原书全部为一册”(594页)。后面的信函多涉及词典的修订(1974年7月12日、1975年2月18日、2月19日函)、编务(1974年6月20日、1975年1月19日、3月27日函)、抄录(1974年12月3日函)、人事安排(1974年5月15日函)、出版计划(1973年12月6日、1974年2月27日、1975年4月12日函)、版权(1975年4月26日函)、版税(1975年6月22日)等。“语堂晚年书信”中关于袖珍词典的最后一函,为1972年2月2日致美亚公司李瑞麟函,谈及词典的定价为9美元,而之前的《汉英词典》为200美元(1096页)。由于次月下旬语堂去世,袖珍词典的出版计划终成泡影。
另一部中文字典的编写过程,在“语堂晚年书信”这宗重要史料中,亦不难窥其全貌。1972年11月10日函提及“何容很赞成我字典之罗马字国语拼音办法及上下形检字法。将来开明出新上下形中文字典,已经讲好,详细再商定”云云(449页)。次年2月23日函说,“中文字典编纂大纲请留一份自用或复印。我此地不必。此大纲所以表明大意精彩之处,使此字典确有与众不同之好处。详细由编辑细加研究”(529页)。4月1日,林语堂亲笔中文字典编纂大纲(114页)。
1973年7月1日语堂致守荆函说,“我很想中华(书局)或美亞能出一中文词典”(609—610页)。8月27日函除涉及编务,还谈及其心目中理想的中文字典,“必须如牛津字典,称每一字之精华用处必须排列,使学者每一字可见到一字的精华”,并计划“大概一年又半可成”(639页)。9月5日函提及与开明出版社签订中文字典合同,“与刘甫琴复信及合约二纸,一纸交与开明,一纸自己保存,皆已签字盖章,言明各条”(646页)。9月14日、11月9日两函还都提到林语堂搜寻三哥林憾庐此前曾助其所编中文字典的旧稿(共13册),以便作为编写中文新字典的参考(651、 670页)。
关于编务方面,有一重要细节必须指出,即语堂决定在该字典中放弃他最钟情的“上下形检字法”,而改用“注音字母检字法”,是年11月30日函说,“我因为中文字典决定注音字母,就无上下形之必要。索引以注音字母排列,而上下形是为《汉英字典》所需要,可以省去”(690页)。
与前文所述袖珍字典类似,“语堂晚年书信”所涉中文字典编辑方面的事务,不外乎编务(1973年10月25日函)、人事(9月2日函)、费用(11月30日函)、出版(1974年2月27日函)、人员报酬(3月21日函)等。但有一点与袖珍字典不同的是,由于工作量太大,林语堂思虑再三后,最终决定放弃中文字典的编写,“至于中文词典,已经决定不做。因为一天要151000字,在我的岁数,实在吃不消,只好作罢”(784页)。
五、 余论与结语
作为文学大师和幽默大师的林语堂,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方面的杰出成就,无须多做强调。他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去世前两周还被告知,哥伦比亚笔会主席Maria Acosta向瑞典诺奖评审委员会提名他申请。1976年3月10日,语堂致守荆的最后两函便谈及此事(1100—1103页)。
林氏于1923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提交的德文博士学位论文 Altchnesiche Lautlehre (《古代中国语音学》),可以说是国人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的理念与方法,探索汉语历史语音问题的成果。
钱穆先生曾数度撰文纪念与林语堂先生的交谊,如《谈闽学——寿语堂先生八十》(1974)、《怀念老友林语堂先生》(1976)等[分别收入钱穆(2000, 2011)]。但始终未曾提及语堂在语文改革方面的努力与成绩。个中缘由,不妨试做如下推测:我们知道,钱穆毕生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在语文改革方面的理念趋于保守主义。如钱穆(1962/1983)9-10《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一文中说:
今中土学者,群学西文,少而习之,朝勤夕劬,率逾十载,其能博览深通,下笔条畅者,又几人乎?今既入黉序,即攻西语,本国文字,置为后图,故书雅记,漫不经心。老师宿儒,凋亡欲尽,后生来学,于何取法?卤莽灭裂,冥行摘埴,欲求美稼而希远行,其犹能识字读书,当相庆幸。而尚怪中国文字之艰深,遂有唱废汉字,创造罗马字拼音者,呜呼!又何其颠耶?
又钱先生在《维新与守旧》(1980/2000)19一文中说:“只读白话文,所收效果既不佳,乃进而求创新字体。先作简化汉字,继则废止汉字,求为罗马字拼音。……大陆简体字,海外识字人已不能读。然则务使中国人不识中国字,乃得成为一新中国人,除旧布新,岂诚如此之谓乎?”而有趣的是,林语堂恰好在这之前也作了一篇题为《论守古与维新》(1967)的文章,指出“知古而不知今,则昏聩老耄,自己不能进德修业,沉湎于古经古史,与时代脱节,而且阻挠时代的迈进。”(林语堂1994a)63我们自然不能认为,钱穆先生属于语堂所说的“沉湎于古经古史”的“昏聩老耄”之人,但如果说钱氏代表守古派,林氏代表维新派,应大致不差。
钱穆作为曾经和林语堂一样“烟具时时随身不离”的同道,他对林语堂最直接、最具体的赞誉之词,恐怕还是其在《怀念老友林语堂先生》(1976/2011)397一文中所说的“语堂早在三十岁前后,名满海内,举国皆知。尤其是他编行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诸杂志,乃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异军特起之一支,更使他名字喧动,‘幽默大师的称号,亦由此成立”这一句。而林氏此前也曾作《谈钱穆先生之经学》(1967)向钱氏的学术成绩致敬[2]。通观钱氏纪念林氏的文字,却没有一处提及林氏在语文改革方面的经历。从钱氏的立场出发,汉字简化、汉字拼音化并非他乐于见到的,但这终归没有影响钱、林二人“过了七十始成交,真是一老年朋友”的真情意。
当然,林语堂也不乏对其批评的声音。胡适在日记中(1943年1月10日)记载了一则美国文艺界对林语堂的评价,“到Arthne Train(A.特雷恩)家吃午饭,……Train对我说,‘有人问林语堂何以不能代表中国作家?他问我的意见。我说,前几天Charles Merz(查尔斯·摩斯)对我说,林语堂好像不会成熟(mature),这话似乎有理”(胡适2003)480。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1917—2012)曾回忆其清华旧同学丁则良(1916—1957)曾对他说的一番话:“我1945年秋出国之前数月,丁则良曾对我说,我们不要学林语堂,搞学问转以美国人为对象;我们应该学胡适之,搞学问要以自己中国人为对象。”(何炳棣2014)182但是,钱锁桥(2019)460在其《林语堂传》一书的后记里,有段意见相反的评述:“有一本流行的亚美文学教科书,一方面把林语堂当成‘华美文学作家的先驱,另一方面以激烈的语调批评林语堂,不光是因为林语堂不符合华美作家应该以美国为归依的主旨,还因为林语堂的‘政治不正确性。”
附 注
[1]下文括注页码,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此书。
[2]《手迹》(1113页)有钱、林二人于1965年在香港九龙宋王台的合影一帧,尤其珍贵。
参考文献
1. 陈毓贤.洪业传.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2.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北京: 中华书局,2014.
3. 胡適.胡适全集(第33卷).耿云志,欧阳哲生整理.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4. 黄仁宇.上海,Shanghai,シヤソハイ.∥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9: 257-269.
5. 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北京: 中华书局,1993.
6. 林语堂.汉字号码索引法.未刊,1924.
7. 林语堂.闽粤方言之来源.贡献,1926, 1(9).
8. 林语堂.图书索引之一新法.图书馆季刊,1926, 1(1).
9. 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六卷).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a.
10. 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b: 241-318.
11.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c: 1-35.
12. 林语堂.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国立中央研究院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海: 中央研究院,1933a.
13. 林语堂.语言学论丛.上海: 开明书店,1933b.
14. 林语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
15. 林语堂.故纸清芬见真如:林语堂手迹碎金.香港: 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内部刊印本),2021.
16. 刘炎生.林语堂评传.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
17. 罗常培.厦门音系.上海: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31.
18. 马悦然.另一种乡愁(增订本).北京: 新星出版社,2015.
19. 潘重规.章太炎先生之气节.∥章念驰编.章太炎的生平与学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30-37.
20. 钱穆.怀念老友林語堂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北京: 九州出版社,1976/2011: 397-462.
21. 钱穆.维新与守旧.∥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九).17-35.台北: 兰台网路出版商务股份有限公司,2000: 188-197.
22. 钱穆.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中国文学论丛.台北: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62/1983: 1-22.
23. 钱锁桥.林语堂传: 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24. 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书信).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5. 钱玄同.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6. 唐德刚.国语·方言·拉丁化.∥唐德刚.胡适杂忆.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24-151.
27. 汪荣祖.章太炎的中国语言文字之学.∥章太炎.章太炎散论.北京: 中华书局,2008: 138-146.
28.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9. 余英时.试论林语堂的海外著述.∥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余英时文集·第五卷).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60-467.
30.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民报,1908(21): 49-72.
31.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8: 121-224.
32. 周质平.林语堂的大关怀与小情趣.∥周质平.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3: 3-30.
33. Chao Yuen-ren. Problems in Chinese-English-Chinese Lexicography.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 1972, 7(3): 96-102.
34. Chao Yuen-ren. Review of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Usag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inguistics , 1978(6): 170.
35. Chao Yuen-ren. Further Problems in Chinese-English-Chinese Lexicography. Studies of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Academia Sinica , 1978: 9-38.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 刘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