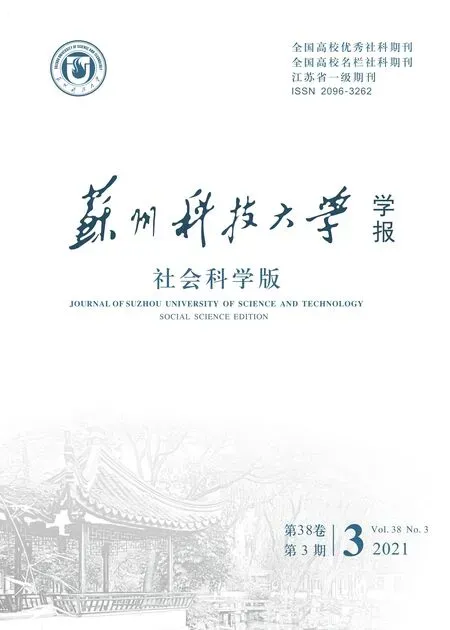汉宣帝时代的经学走向及其调整*
2021-12-05袁宝龙
袁宝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102488)
汉武帝之独尊儒术,引发了儒学的空前繁盛,公羊学的阴阳学理论因此由微而著,为汉代皇权的合理性阐释提供有力支撑。就在公羊学独盛的同时,因其对先秦儒学批判精神的吸纳与继承,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一统政权的潜在威胁。汉武帝去世后,公羊学的批判锋芒日益显露,时人开始以审慎、批判的眼光来回顾和评价武帝之政,儒学与现实政治的矛盾日渐激烈。汉宣帝亲政以后所面临的正是这样纠结复杂的理论与现实境况,如何应对汹涌澎湃的公羊阴阳学思潮,缓解公羊学兴盛对西汉帝国的理论侵袭等一系列问题亟待汉宣帝解决。
一、昭宣之际公羊学理论与现实政治的矛盾
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对于汉武帝之政已有微辞,只不过当时武帝初殁,余威犹存,且在霍光的蓄意安排与引导下,贤良文学的锋芒皆指向为汉武帝设计强国之策的桑弘羊等一干兴利之臣,未能触及武帝执政思想这一根本问题。《盐铁论·刺复》称:
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克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淮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1]
此即武帝朝群臣代君受过之明证。盐铁会议后,霍光尽败政敌,大权独揽,依然忠实地沿袭汉武帝时代的“有为”精神。但这种“有为”精神其实与公羊学以德治致盛世的主张背道而驰。霍光对汉武帝之政的沿袭,一方面使得西汉王朝继续保持着积极进取的“有为”态势;另一方面其对儒学理论的借重,又难免有饮鸩止渴、疗疮剜肉之嫌。也就是说,昭宣之际的当政者对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抵牾置若罔闻,甚至为矛盾的滋长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政治现实与公羊学学理层面的对立也因此日益尖锐,渐至不可调和。
至汉宣帝执政时,汉武帝的风评已然迥异于前朝。这无疑与儒学的进一步昌盛以及儒生对于现实政治认知的愈加深刻有直接关系。经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数十年的酝酿积淀,儒学理念已经成为西汉社会的精神归依。这一时期的儒生大多沉醉于儒学理论之中无法自拔,日益表现出张扬的个性与趋于极致的理想化特征。他们执卷沉思,回首儒学独尊以来的辗转历程,越发意识到汉武帝虽然外示儒术,但其实际的施政手段却与儒学意旨大相背离。儒生群体对于汉武帝的不满,也在这一时期毫无掩饰地表达出来。据《汉书·夏侯胜传》: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遗德,承圣业,奉宗庙,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循,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巨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于是群臣大议廷中,皆曰:“宜如诏书。”长信少府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于是丞相义,御史大夫广明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不举劾,俱下狱。……胜、霸既久系,霸欲从胜受经,胜辞以罪死。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胜贤其言,遂授之。系再更冬,讲论不怠。[2]3156-3157
汉武帝时代,董仲舒这般的纯儒仅具“缘饰”意义,无法走近权力中央,真正为汉武帝所用者实为公孙弘、倪宽这一类通知事务、达于权变的通变之儒。时过境迁,经积年尊儒,彰显儒学原则的察举制逐渐成为汉代的主体仕进机制,太学的兴建又为儒学的传承散播提供了制度化保障,昭宣时期的庙堂之上出现越来越多的纯儒,完全基于儒学视角的声音也在国家最高决策舞台上时常可闻。
夏侯胜以非议武帝获罪,著名的循吏黄霸亦以不劾夏侯胜之举而致罪: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将军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桀等与燕王谋作乱,光既诛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而霸独用宽和为名。会宣帝即位,在民间时知百姓苦吏急也,闻霸持法平,召以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守丞相长史,坐公卿大议廷中知长信少府夏侯胜非议诏书大不敬,霸阿从不举劾,皆下廷尉,系狱当死。霸因从胜受《尚书》狱中,再逾冬,积三岁乃出,语在《胜传》。[2]3628-3629
夏侯胜、黄霸于必死之际,犹能修习经典,正是道胜于君理念的鲜明体现。此举更与宣帝朝其余诸臣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诸臣强调“此诏书也”,其实就是强调圣意不可违背,这是汉武帝建构大一统集权帝国以来政治文化的重要遗产。此前数十年间,“君意不可违”这一文化意旨已经根植于西汉官员群体的内心深处。然而在公羊学“兴太平”“造盛世”这一宏大梦想的激励下,以夏侯胜、黄霸为代表的儒生们张扬的个性再度显露出来,这一长期以来似已牢不可摧的政治原则由此出现破裂甚至瓦解的可能。
换言之,公羊学曾是汉代君主集权制度的理论基石,但这一思想的理想化与极端化,又会对君主集权制度形成反噬。如果说夏侯胜与黄霸的个人持守与淡然生死,尚不能形成广泛的公共影响力,那么充满神秘主义的灾异理论则以其超乎寻常的群体威慑力成为公羊学反噬“霸王政”①汉武帝创设的政治体系以儒术为表象,实则彰显着强烈的法家精神,故称之为“霸王政”。参见袁宝龙《西汉中期“有为”精神下的“霸王政”体系建构及其传承演进》,《黑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第104~110页。的主要突破口。
至(本始)四年夏,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地动,或山崩,坏城郭室屋,杀六千余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吊问吏民,赐死者棺钱。下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托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术士,有以应变,补朕之阙,毋有所讳。”因大赦,胜出为谏大夫给事中,霸为扬州刺史。[2]3158
由董仲舒首创的公羊学灾异理论经后世学者的阐发,于汉宣帝时期盛极一时,成为时人揣测天意、研判时局的重要理论工具。夏侯胜以言灾异而获罪,最终又因灾异之生而得豁免,此事说明当时灾异理论的影响力之巨,上至天子,下及平民,无不深受其影响。而这种超乎世俗皇权之上的理论阐释,无疑是对大一统政权的潜在威胁。
汉宣帝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理论层面的变化趋势,并迅速找寻到应对之策,即通过有效的资源整合化解其胁迫性,使其为我所用。每当出现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宣帝多有罪己之诏,同时诏求贤良方正,减免租赋,以安黎民。金春峰指出,汉宣帝即位之初,大臣上书言事尚不称引阴阳灾异,但正是汉宣帝宣扬以后,大臣上书条奏,多以灾异为依托和根据,灾异谴告成为朝廷上一时风尚。[3]可以说,对于灾异理论的官方接受成为汉宣帝朝神学体系建构的重要特征。
最具典型意义的应对之策莫过于通过人为干预,使祥瑞与灾害交相出现,帮助时人于欣喜惊惧的交替侵袭中求得心安,效果尤佳。纵观史籍,汉宣帝一朝祯瑞迭现,祥兆频生,远多于前朝,此中缘由颇耐人寻味。《汉书》记载:
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故立三年,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告祠世宗庙日,有白鹤集后庭。又立世宗庙告祠孝昭寝,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筑世宗庙,神光兴于殿旁,有鸟如白鹤,前赤后青。神光又兴于房中,如烛状。广川国世宗殿上有钟音,门户大开,夜有光,殿上尽明。[2]1248
神爵元年(前61),诏称:
乃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国,神爵仍集,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九真献奇兽,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饬躬斋精,祈为百姓。东济大河,天气清静,神鱼舞河。幸万岁宫,神爵翔集。[2]259
又,五凤二年(前55),复诏称:
朕饬躬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并见,或兴于谷,烛耀斋宫,十有余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诏有司告祠上帝、宗庙。三月辛丑,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余刻,吏民并观。朕之不敏,惧不能任,娄蒙嘉瑞,获兹祉福。[2]266-267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史称宣帝一朝,“凤皇下郡国凡五十余所”[2]1253。祯瑞祥兆的频繁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天象异常带来的普遍性恐慌情绪,对于稳定局势、重建士人阶层与普通民众的信心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二、汉宣帝对阴阳学理论的转化与借用
汉宣帝对天意表述以及阐释方式的人为介入在宏观层面把灾异对大一统格局的消极影响化于无形,表现出高明的政治智慧与娴熟的帝王之术。除此之外,汉宣帝尝试把灾异理论引入政治实践,以此打击异己,彰显皇权,维护既有的大一统格局与尊卑秩序,这一点在对霍氏集团的处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霍光死后,诸霍专政,君臣关系日益紧张。张敞曾上封事称:
乃者大将军决大计,安宗庙,定天下,功亦不细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将军二十岁,海内之命,断于掌握。方其隆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月朓日蚀,昼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变怪,不可胜记,皆阴类盛长,臣下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宠故大将军以报功德足矣。间者辅臣颛政,贵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请罢霍氏三侯皆就第。[2]3217-3218
宣帝善其计。《萧望之传》亦云:
时大将军光薨,子禹复为大司马,兄子山领尚书,亲属皆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夏,京师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望之对,以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乡使鲁君察于天变,宜亡此害。今陛下以圣德居位,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万机,选同姓,举贤材,以为腹心,与参政谋,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陈其职,以考功能。如是,则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矣”。[2]3273
宣帝以过人的政治智慧和理国才能,把灾异理论转化为执政利器,在达成政治目的的同时获得了舆论支持,可谓一箭双雕,事半功倍。诛除诸霍之后,此范式被广泛应用于帝国政治实践中。可以说,汉宣帝对灾异理论的理解与运用皆达至境,频繁出现的灾异非但未能动摇帝国统治的根基,还成为高举“有为”旗帜、创制中兴格局的辅助工具。汉宣帝高屋建瓴,以过人的胆魄运筹帷幄,遂得于前所未有的理论困境中破围而出,乃至因势利导、化敌为友,开建盛世,蔚为西汉中期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奇观。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灾异理论得以内化于西汉后期的政治文化之中,再也无法剥离破除。宣元以后,西汉中后期政局日益沉沦于灾异学说的漩涡中不能自拔,整个西汉社会皆沉浸于末世惶恐与改制更化的缥缈希冀之中。这种风潮固然源自儒家思想的繁盛,亦与汉宣帝对灾异理论的放任、借用乃至激励不无关联,只不过此后的发展态势已非汉宣帝所能预料掌控。
如前所述,汉宣帝不仅接纳了阴阳理论,而且以过人的政治智慧将其转化为施政的辅助工具。汉宣帝一朝对于阴阳理论的借用乃至倚重在诸多方面皆有体现,尤以用人选官最为直接明显。宣帝朝达官显宦、元勋重臣多有精通阴阳学者。如宰相魏相,便是当时的阴阳学大师。
相明《易经》,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臣相伏念陛下恩泽甚厚,然而灾气未息,窃恐诏令有未合当时者也。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天下幸甚!”相数陈便宜,上纳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不上,相辄奏言之。[2]3137-3141
魏相之后,邴吉入阁为相,曾路遇逐牛而问其事,人不解其意,吉曰:“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2]3147此事表露出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邴吉于宣帝微时有恩,故备得圣心眷顾,然观其为相之风,则其得为相或非止有恩于上。魏、邴二人身居群僚之首,皆能自觉地把阴阳学理论与国家的治理之道相结合,宣帝朝西汉国家的最高决策也因此表现出鲜明的阴阳学特征。
毋庸置疑,汉宣帝对灾异理论的转化与借用,解决了汉代社会诸多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不过,这种借用也在无形之中认同了灾异理论的合理性,对其发展起到激励作用,使其锋芒辉耀于大一统精神之前,促使其向着极端化的方向演进,最终威胁到皇权的稳固。
盖宽饶目睹汉宣帝为政之道,上书直陈时弊:
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书奏,上以宽饶怨谤终不改,下其书中二千石。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指意欲求禅,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愍伤宽饶忠直忧国,以言事不当意而为文吏所诋挫,上书颂宽饶曰:“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司隶校尉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职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与,上书陈国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从大夫之后,官以谏为名,不敢不言。”上不听,遂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2]3247-3248
盖宽饶引《韩氏易传》之语阐明天下非一姓之私的观点,并以此作为进谏的理论支撑,隐然暗具胁迫之义。汉宣帝览奏后龙颜震怒,朝臣或有深知圣意所思者,以此进谗,果奏奇效。此事以盖宽饶横刀自尽告终。从盖宽饶的言行作为,以及自刭之后“众莫不怜之”的情景可知,尽管当时以汉宣帝的天子威权仍无人敢直撄其锋,但是极端化的儒学理论已经席卷整个汉代社会,阴阳学理论中关于“天命无常”的诸多观念已经为儒生群体普遍接受。
汉宣帝时期,公羊学与阴阳学的结合达到董仲舒以后的又一个高峰。班固称:“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睢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2]3194-3195
可以说,自董仲舒以后,阴阴学作为公羊学重要的理论构成不断发展进化,批判性与对皇权的威胁性不断凸显。尤其当汉代儒生意识到汉宣帝的施政风格与公羊学派的理想之间存在冲突,甚至与儒学经典描绘的王道理想背道而驰时,他们便自然而然引发了对汉室的极大失望,这种失望最终在阴阳学理论的鼓励下上升为对汉帝合法性的质疑。[4]盖宽饶的上书令汉宣帝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何抑制公羊学的阴阳学理论泛滥成为他亲政后思索的重大议题。正是在这样的求索过程中,同样以阐释《春秋》为主旨,且与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穀梁传》进入汉宣帝的视野,汉代学术思想与理论格局亦因此迎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整合与变革。
三、汉宣帝时代的经学调整及其影响
先秦以降,释《春秋》者非止公羊一家。据《汉书·艺文志》:“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2]1715《穀梁》与《公羊》皆于汉初以今文写就,公羊学系齐学,穀梁学为鲁学。齐学独尊之前,鲁学亦曾有凌驾诸学之上的机遇。实际上,即便在齐学取得独尊地位之后,穀梁学者亦从未放弃夺回儒学正宗地位的努力。据《汉书·儒林传》: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2]3617
此处提及,公羊学大兴之后,卫太子于贯通公羊学后,又私问穀梁之学,卒钟于此。从汉武帝与卫太子的性格截然两判可知,父子二人的学术取向大异亦在情理之中。只不过,此后卫太子身死,穀梁学亦从此湮没无闻。直到盐铁会议后,随着汉代统治政策的调整,诸如仁义、王道、民本等儒家主张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经学上则表现为由崇法主变、奇险诡异的《公羊春秋》学向温柔敦厚、具有浓郁的宗法人伦温馨的《穀梁春秋》学的转变,即由齐学向鲁学转变。[5]可以说,这种转变态势源自儒学独尊后诸多分支派系自我发展的内部需求,从学术层面而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汉宣帝亲政后,精准地把握这一学术思潮的新趋势,复以政治权力引领导向、推波助澜,为经学嬗变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据《汉书·儒林传》: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2]3618
事实上,汉宣帝对穀梁学的偏好显然不会如此段史料中所说的这样简单直接,此番由官方授意、引导的经学格局调整背后实具极为深刻的政治图谋与时代内涵。
汉武帝末年公羊学与现实政治的矛盾已经显露,汉宣帝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手段把公羊学的批判精神转换成推动帝国政治的辅助力量。此举的代价就是继续放任阴阳学理论与批判精神的滋长,实际只是把公羊学与“霸王政”的矛盾激化向后延缓而非根治。
这或可视为汉宣帝关于帝国政治宏大布局的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战略性延缓为根本性解决公羊学的威胁赢得时间。而这种根本性的解决之道就是以穀梁学取代公羊学,通过儒家思想的内部革易达成最终目的。杨树增先生指出:“《穀梁春秋》不讲‘受天命为新王’,宣帝正欲用《穀梁》来抵制《公羊》学的影响。”[6]以汉宣帝之英明睿智,在面临公羊学的长期理论威胁下,以同样阐释春秋义理而主旨相异的穀梁学来对抗乃至抑制公羊学,亦在情理之中。
弘扬大一统精神为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特质。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于阴阳灾变视域下对于先秦儒学“从道不从君”批判精神的承袭与阐扬,逐渐成为这一理论的显性特征,与现实皇权逐渐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相比之下,穀梁学更强调“亲亲尊尊”之道,注重宗法伦理,强调既有伦理秩序与君臣关系的不可侵犯性。与汉武帝时锐意进取的时局不同,汉宣帝治下的西汉帝国经济发展,民力恢复,显示出蓬勃稳健的发展态势,对于开拓进取的需求已经让位于稳定时局、巩固统治,穀梁学则刚好可以在摒弃公羊学弊端的同时满足这一现实诉求。
对于汉代经学嬗变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石渠阁会议,就是带着明确的政治诉求,以前述政治形势与学术思潮的变革为背景召开的。
宣帝甘露三年(前51),石渠阁会议正式召开,“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2]272。汉宣帝亲自称制临决,给这次会议赋予了浓重的官方色彩,也直接决定了这次会议的进程走势及最终结果。可以说,正是在汉宣帝态度鲜明的支持引导下,穀梁学得立于学官,一跃成为官方统治学说,地位甚至一度凌驾于公羊学之上,成为彰显国家意志的儒学正宗。穀梁学家自有其“以礼为治”的政治主张,随着穀梁学大盛,礼治的呼声日益高涨。穀梁学家们针对当时的形势,对《公羊》家所阐述的、已被人们认可的《春秋》之道进行修改,以期为解决“汉家制度”与儒生理想之间的矛盾提出一种折中方案。正是在公羊、穀梁兴替的背景下,宣元之际“以礼为治”取代“以德化民”成为儒学士大夫群体主导思想的历史痕迹。[7]这也是汉宣帝为破除公羊学咄咄逼人的批判质疑、求得现实政治与儒生理论之间的和解而做出的最后努力,其对学术思潮演进的顺应和转化正与其彰显“有为”意旨的“霸王政”精神相一致。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公羊学理论经此前数十年阐扬光大,其影响力已然贯彻于汉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人皆晓喻,深入人心,即便失去了官方统治哲学的地位,仍于民间有着极强的号召力。
实际情况是,尽管有汉宣帝的官方介入与引导,公羊学仍是西汉中后期《春秋》三传中内蕴最深厚、影响最大的一家。其作为西汉意识形态领域主导理论的地位并未受到根本性的触动,相比之下,穀梁学则始终处于从属地位。[8]公羊与穀梁出现明显的升降趋势,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汉宣帝于帝国治理的过程中,意识到儒与法相辅相成的特点,不能顾此失彼、厚此薄彼,亦能如武帝一般运筹帷幄,左右逢源,以个人能力掌控外儒内法的理论格局,其对穀梁学的吸纳与借助也与当年汉武帝之兴公羊学极其神似。
然而,无论汉武帝抑或汉宣帝,他们都试图以一己之力来把持儒、法的共生互融,却始终无法在儒学昌盛的学术气氛中为法家精神确立制度化保障。这种儒、法均势的达成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脆弱性。到汉宣帝末年,儒学益盛,双方共存之势时刻面临崩解之危,尤其太子的政治偏好与学术取向,令宣帝惧于身后之事。据《汉书·元帝纪》:
(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2]277
汉宣帝的这种无奈慨叹,正是源于西汉政治“外儒内法”的吊诡现实。从汉武盛世到昭宣中兴,在儒学思想蓬勃滋长的背景下,西汉帝国始终未能真正形成制度化的国家治理机制,这成为汉代盛世的最大隐忧。石渠阁会议虽然确立了穀梁学的正统地位,但此时已是汉宣帝统治晚年。不久,汉宣帝去世,他精心构筑的以穀梁学抑制公羊学进而求得现实与理论和解的宏大战略,也就此无果而终。公羊、穀梁两家之学并未如汉宣帝预想的那样不共戴天、盛衰异途,而是在频繁的互动共鸣中缔造了真正的儒学盛世。以好儒著称的汉元帝登基,引发了西汉儒生的群体振奋,最后也如儒生所料,儒学理论真正走进西汉帝国的最高舞台。与此同时,公羊学固有的理想化特征与批判精神重新涌动风行,充斥泛滥于汉末社会。这种思想层面的演变在政治现实中表现为对现状的质疑与不满,这也直接导致西汉帝国权力中央的剧烈变革,法家式微,儒家政治兴起,整个帝国由此陷入专一用儒的窘迫困境。
宣元之际思想格局的这一重大变化,开启了经学极盛时代。至此,首创于汉武帝时期、践行于孝宣之世的“霸王政”全面瓦解,儒生政治视野下儒学原则成为无可置疑的最高原则,其对汉代政治文化体系的影响至为深远。自此之后,西汉帝国的政治运作失去了法家的制度规约与效率保障,开始了满怀热情理想却又缺乏实践经验的儒生政治时代,历时近百年积极向上、蓬勃奋发的西汉“有为”时代正式终结,转而陷入经学时代对更化改制、复古效周的憧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