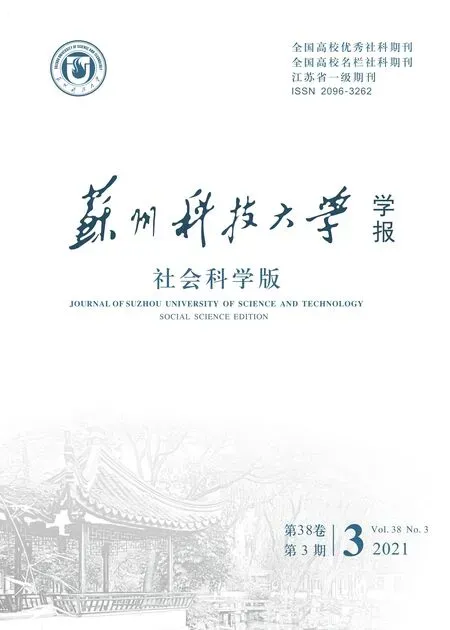跨越全球治理“筒仓式思维”的认知门槛*
2021-12-05陈绪新张晶晶
陈绪新,张晶晶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214122)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几乎一切文明的碰撞或宗教冲突都或多或少与复杂性问题的悬而未决有关。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在经济冲动力和权力冲动力的双重驱策下,沉迷于生产的无限扩大、财富的无限增长和消费的恣意狂欢,沉溺于无尽的征服感、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感。然而,指数级增长的事实、不饱和状态的假象、物欲背后的狂欢往往使得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个人对增长假象背后所积累的复杂性矛盾和问题视而不见。作为个体的普通民众,在物欲狂欢后略显孤寂和无助,不得不选择行为的“理性的无知”。妨碍人类应对复杂性问题的那些顽固且僵化的模式、思维、态度或信仰,即文化基因,如同生物基因一样流淌在人类文明有机体的血液里。当某种文化基因对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具有宰制性时,它就升级为“超级文化基因”,成为应对和解决诸如核威胁、恐怖主义、生态环境危机、高致病性传染病等全球公共危机与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巨大障碍。“筒仓式思维”就是其中最常见也是较为顽固的一种。
一、“筒仓式思维”:概念、缘起与后果
非此即彼、厚此薄彼或者“非我族类,虽远必诛”等狭隘的思维方式是“筒仓式思维”的典型特征。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在资源稀缺性或稀少性这个永恒的主题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习惯于紧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放,并试图制定各式各样的约定、规则和制度来规约彼此的行为界域,以确保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受外界的侵扰。久而久之,非此即彼、厚此薄彼,甚至你死我活的“筒仓式思维”就应运而生。
(一)“筒仓式思维”的规定性
“筒仓”是那些又高又厚并且没有窗口的密闭结构的统称。在管理学上,“筒仓式思维”是指那些阻碍部门之间共同协作或合作的——处理高度复杂性问题时所必需的——条块分割的思维和行为。[1]122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且形成固有的信息壁垒,使每个部门出现安于现状的“井底之蛙”;部门之间的信息或知识的绝缘,导致每个部门针对同一复杂性问题所指定的计划方案、法律法规出现低级的重复和相互的抵牾,复杂性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众人努力的结果。相对于“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知识和财富的累积速度而言,个体的我们永远是跟不上的。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和复杂性问题累积面前,在日常生活中,目光永远是那么短浅的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大脑还不能将那些复杂的联系进行关联”[1]122,每个人对某个公共事件背后的事实及其相关信息、知识的获得与理解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局限性,信息的壁垒、知识的鸿沟在所难免且很难打破。
(二)删繁就简的自然倾向
信息的壁垒和知识的鸿沟,使人类对自己生命存在的过程及这个过程存在的不确定性难以预测。我们既渴望自由、一路向前和狂欢,也希冀一路前行、自由狂欢的我们有更多的秩序、安全和庇佑。为了使不可预测的、极不确定的复杂性世界在自己面前变得有那么一点秩序、安全、可预测或可确定,删繁就简就像趋利避害一样成为人脑的一种自然倾向,成为人类解释自己生命存在的状态、意义,以及应对生命存在过程出现的各类矛盾和危机的惯习。在资本宰制下,人类习惯于将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简单化为“自然资本”、社会关系简单化为“社会资本”、生命个体简单化为“人力资本”、伦理道德简单化为“道德资本”。如果“1+1≧2”的话,那么把“2”分解成两个“1”又有何不妥呢?这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事实远非如此。
(三)过度“专门化”的后果
“随着领域被划分得越来越细,全才被‘专家’代替。”[1]122分工和部门的细化导致我们获取的信息或知识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以及该领域的专家对知识和信息的垄断地位。信息的不对称使今天的人们很难获得信息而且对信息难辨真伪,对“专家”的过分依赖,致使编造或歪曲事实真相的“专家”变成“砖家”。在事实真相没有曝光之前,我们对“砖家”所说的话还是深信不疑的。各个领域的那些具有战略眼光的“长期主义者”的领袖人物逐渐被那些急功近利的“短期主义者”所替代。过度、细化和“专门化”的后果就是,“战略性目标被划分为非常细碎的可测量的小目标”[1]122。这虽然有利于短期责任落实和绩效管理,但往往是内部问题解决了,外部问题被忽略了;短期目标实现了,长期目标被搁置了;局域性目标实现了,全局性目标被遮蔽了;工具技术性的外在手段实现了,精神价值性的内在意义被虚掷了。
二、全球治理的“筒仓式思维”现代性之隐忧
西方现代性道德谋划及其后果就是世俗化、去人格化、去传统化。人格、传统都是在从“我”到“我们”、从“私”到“公”、从“个体”到“共同体”的过程中形塑和获致的。优秀的传统、健全的人格都是“共同体”内部“共同的善”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2]99在“共同体”内部,因为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在共同体面临来自内部或者外部的威胁和危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挺身而出,采取一致的行动。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处于“共同体”内部的我们,可能会因为资源的稀少性或者性情的差异性而内讧,但是在危急关头,我们都会“一笑泯恩仇”,用“合作”代替“对抗”。
(一)各自为政的协作困境
随着人类复杂性问题的不断累积和公共性危机的不断升级,受根深蒂固的“筒仓式思维”影响,国家、组织、部门获取有关公共事务或危机方面的关键性知识、数据和信息变得更加困难;跨越“筒仓式思维”高墙并实现国家间、组织间或部门间合作的各种努力也会因为严重缺乏相互信任,以及相互协作的成本过高而变得十分困难。“相比于鼓励拥有共同目标的个人和团体一起合作,筒仓式思维会引起内斗、竞争和分裂。由于筒仓式思维阻止各组织之间共享信息和共同协作,本来就很难获取的复杂信息,变得更加难以获得。”[1]122当系统或组织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时,最起码也能够“一个和尚挑水吃”;当系统或组织被分解为两个隔空相望的部门时,当复杂性问题出现或者公共危机发生时,彼此的第一反应虽然是指责对方并将己方责任推卸给对方,但最终还是会选择“两个和尚抬水吃”;当系统或组织被分解成三个部门时,指责对方和“甩锅”的对象变成了密闭循环,演变成“三个和尚没水吃”;当系统或组织被肢解成孤立无援的一个个小部门时,毫无意义的争吵、连环性的相互推诿和扯皮、嘈杂的声音逐渐掩盖了有意义、有价值的正确发声,这些使得共同协作、共享信息变得几乎不可能。因为系统或组织被肢解后而形成的彼此孤立、各自为政的各个部门之间业已形成坚不可摧的边界。部门间的边界像一座座高墙,使得信息壁垒和知识门槛越垒越高,部门间的协作俨然形同虚设。久而久之,没有哪个国家、组织、部门会对整个问题主动承担责任——它们只关注自己的“日程”,甚至不惜破坏其他部门或组织的目标。当全球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之后,某些国家的一些政客只关注自己的目标——为了尽快从不利于自己的舆论旋涡中抽身,不惜编造假新闻来诋毁其“主观上的”敌人,玷污他们的名声。这些政客一方面是为了掩盖政府应对国内公共事务危机不得力的事实真相,转移国内民众的猜忌和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借此打压自己的对手,诱导或误导世界舆论导向,嫁祸于他人。那些只为达到本国目标的政客根本没有任何诚意在第一时间开展全球的共同协作,最终,不仅耽误了其国内公共事务危机应对的最佳时机,也错过了全球公共危机处理和全球治理的最佳时机。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捏造事实攻击他国的非理性做法,会在那些处于全球公共危机旋涡中心的国家和充满焦虑和恐慌情绪的普通民众心里埋下对其他民族国家的猜忌和不信任。
(二)自我保护的治理困境
生物进化论者认为,动物为确保生存,往往会通过“圈地盘”划定分界线以保护食物、饮水、配偶与幼仔不受侵犯,并为自己的利益而捍卫领地边界。社会进化论者则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交往与交换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个体一般都会选择寄身于某个组织,栖身于某个社会群体。每个组织或者社群为了组织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安全,就会本能地选择捍卫自己的“社会地盘”。出于对“自我利益最优化”的追求,个体行为选择的内部选择一致性向组织或者社群的内部选择一致性迈进。然而,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当自身的生存机会受到极大的威胁时,这种经济的理性选择行为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变成一种顽固的、近乎疯狂的保护自己“社会地盘”的非理性。“筒仓式思维”就是这种“出于为了提高我们的生存机会而捍卫‘地盘’的非理性本能”[1]130。
“圈层文化”既是动物性的自然选择的本能,也是社会性的内部选择的必然。无论是家庭、家族和宗族,还是城邦和国家;无论是社会阶层、阶级、其他利益集团,还是网络社会空间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圈层文化,都是人类为了应对生存困境、捍卫生存机会的自然选择结果,例如,古代人在城市或城堡的四周挖护城河,现代人出于财产权的边界保护而创制出诸如契约、协议以及为了确保这些人为设计能够得到某种强制性或非强制性保护而做的道德或制度的体制安排等。人类通过人为设计而建立一道道围墙——道德的或法制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都是为了能使生活在组织或社会内部的人们免于来自外部力量的侵犯。众所周知,以自我为中心、将自己封闭、与外部世界近乎隔绝的人们,不但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共同体内部的公共事务管理,而且缺乏与他人、外界交流和交往的热情,更谈不上对组织或社群外部的社会公共事务感兴趣。
执着于“社会地盘”的自我保护不利于组织或群体的长期利益和长远发展。一个组织或者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组织或群体内的团结合作。因为在复杂性问题和公共危机面前,任何个人、组织、群体都无一幸免。对自己的社会领地或地盘的执着保护,使一个个组织或群体变成一个个密不透风、难以逾越的“筒仓”,久居于“筒仓”的人们既不愿意进行组织或群体内部的合作,也不愿意进行组织或群体外部的协作。“保护数据、能力和各自的势力范围导致我们陷于目前的困境……由于每个机构都试图独自重复获取另一个机构的成果,浪费了时间和资源,这样一来,解决我们最复杂最危险的问题所需的协作方案越来越遥不可及。”[1]127因此,经济领域的重复生产、社会领域的重复建设、官僚机构的重复设置、学术成果的重复研究等随处可见,多部门共管变成没部门来管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对“社会领地”自我保护的另一个后果。当“筒仓式思维”获致的认知门槛越来越高且高不可攀的时候,它就演绎成为“超级文化基因”。信息的壁垒有时比贸易的壁垒更难打破,知识的门槛、信仰的门槛有时比珠穆朗玛峰还难翻越。
三、跨越“筒仓式思维”的认知门槛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世界已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花园。只要我们愿意跨越“筒仓式思维”的认知门槛,破除知识和信息的壁垒;在人生道路上疾步行走的我们就不是独步芳庭,在为人生目标奋斗打拼的我们就不是孤军奋战。
(一)并肩作战总是比单打独斗好
从某种意义讲,生态环境恶化、核安全、饥荒、恐怖主义、大流行病甚至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人类复杂性问题和公共危机,是“筒仓式思维”等“超级文化基因”的副产品,因为“筒仓式思维”阻碍了人类对复杂性问题和公共危机及时有效的解决,经年累月,复杂性问题或危机超越了人类社会可控的范围。“筒仓”越坚不可摧,“筒仓式思维”就越有宰制性,人类社会应对和解决复杂性问题和公共危机的集体行动策略和系统性科学方案就越来越远。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想象成认知能力有限的多兵种部队,如果这支部队的各兵种之间各自为政,不能很好地协同作战,那么在阻击经年累月累积起来的复杂性问题和突发性的全球公共危机等强大的入侵者时,他们很难有得胜的机会。阻碍人类社会创新复杂性问题解决方案的不是技术而是观念,今天的技术进步已经完全超乎人类自己的想象,但是信息的壁垒、认知的门槛、观念的隔阂等“筒仓式思维”并没有随着知识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而有所缓解。破除“筒仓”的壁垒、跨越“筒仓式思维”的认知门槛是人类社会应对复杂性问题或危机、开展全球科学治理的必然选择。“我们必须先拆掉自己的筒仓。……我们必须假定,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的人们应该共享信息和资源,而不是互相竞争。我们必须放下自我保护的原始本能,为了人类更大的利益而协同奋斗。”[1]129这是最大限度地促进个人利益的最佳选择,更是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利益和福祉的最佳方案。今天的人类需要共同应对很多复杂性问题和挑战,而成功地应对和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全人类共同协作或采取集体行动的广度和深度。面对复杂性问题,单打独斗总比不上并肩作战更好、更安全;恶性竞争总比不上协同合作更稳、更有效;自我保护总比不上资源共享更优、更经济。
(二)发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思维
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只有在这种“关系的存在”中,个人才能获得人格同一性认同,才能获致对自我生命存在的过程及其意义的理解和诠释;只有在这种“关系的存在”中,个人才能获得做人的尊严,获得身份和角色的认同及其基础上的成就感。概括地讲,我们每个人都寄身于不同层级的命运共同体,它们分别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命运共同体、以职业关系为纽带的职场命运共同体、以生活关系为纽带的社区命运共同体、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以安全共享为纽带的网络命运共同体、以和谐共生为纽带的生态命运共同体、以主权尊重为纽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复杂性问题和全球公共危机,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唯一出路。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条件向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张,世界各国人民只有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共赢代替独尊;才能化危机为生机,才能使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有利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国际核安全时指出:“在互联互通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所有国家都要参与到核安全事务中来,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努力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4]在全球性公共危机面前,世界各国需要摒弃成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从整体性思维的角度出发,人类文明总是从许多单个文明或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并生成无数的相互交错的力量,在这些无数个相互交错的力量所构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基础上就会产生一种合力。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文明乃是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互相发生牵制作用……这是处于生长过程中的文明的特点之一,它们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一切活动都彼此调合成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5]
(三)持守一种对话或商谈的视野
“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2]99传统脉搏和现时代的“重要的他人”共同塑造了一个可理解的“说话的语境”、一个“对话性视野”,这些语境与视野旨在使文化自我和文化他者在文化多元对话和交互融合的视景下,形成一种各种文明和不同的文化因子竞相生长的文化生态。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之间真正的建设性的平等对话,要求所有参与对话或商谈的行为者必须严格遵循三个有效性原则:“所作陈述的真实性”(真实可信而不是虚假捏造的事实)、“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是正确性的”(准确无误而不是肆意歪曲的表达)、“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心口如一而不是口是心非的真诚)。[6]也就是说,真实的命题、正确的言语和真诚的态度,一个都不可缺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其宰制下的各种文化形态,固守着非此即彼或主客二分的价值原则,以自我为中心,坚持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漠视文化他者的存在及意义,人为制造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对立,以文化自我的霸权行径对文化他者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经济制裁,甚至武装入侵,肆意侵犯他国公民的自由权。“未来有两个选择:死亡或者对话。……今天,如果沿着只顾自己说话而罔顾他人的路子走下去,那么离核战争、生态破坏或别的灾难也就不远了。我们必须竭力摆脱自我中心的自语之思想架构,而与他人进行对话,不是以我们在自语中猜测的样子来认识他人,而是按照他或她本来的样子来认识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这种毁灭性灾难。简言之:我们必须脱离自说的年代,进入对话的年代。”[7]人类文明从冲突逐步走向融合的基本趋势和客观规律不会改变。“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延续、壮大和成熟的,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和风格。”[8]站在跨文化比照的立场上,有着集体意识、家国情怀、天下观念等朴素情感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上展现出令人称奇的合作和冷静,在应对复杂性国际事务中始终持守一种对话或商谈的视野,在自我和他我的平等对话中进行国际间合作,与他国共同开展全球科学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