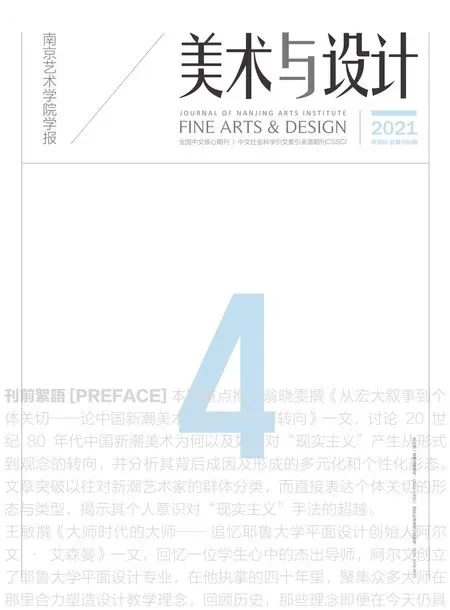虚拟现实艺术的美学探究①
2021-12-05李栋宁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李 剑 李栋宁(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提出的“数字化生存”在今天已然成为现实,人们也越来越习惯于将客观世界进行数字化表达。在虚拟现实技术逐渐成熟的背景下,虚拟现实艺术利用数字技术模拟并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环境系统,并让身处其间的体验主体与之产生多维度的交互,进而影响着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及其与人类关系问题的认知。虚拟现实艺术作为一种具有未来意味的影像形态,不仅是构建虚拟世界的重要工具,更是人类进一步自我数字化的重要环节。近年来, 虚拟现实艺术在娱乐、教育、医疗、商业、展览等领域的应用,正在迅速改变原有生态。作为艺术的VR影片,也开始走向世界一线的影像作品展会,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推出了VR概念影片,同时展出了近30部虚拟现实艺术艺术作品。2019年有五部VR影片获得艾美奖的提名。可以说,虚拟现实艺术已经在影像领域获得了一席之地,其美学特质和内涵也越来越受关注和研究。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形式,虚拟现实艺术以其对再现现实的极致追求、对身体和动作的介入以及对交互的审美体验,推动着影像技术与影像美学的双重革命。尽管一种成熟的影像语言尚未形成,但其对人们的美学认知的改变已然开始。
一、影像艺术:现实的投影与复制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了对现实世界进行再现性描绘的行为。囿于技术的限制,原始社会的人类只能运用简单的工具在洞窟、石壁等上刻画一些图案或符号,通常表现的是狩猎的场景或其捕获的动物。诚然,这些图像仅仅是象形或表义的结果,是对现实生活片段的模仿,但其作为人类在文化幼年时期的最初尝试,已然显现出“真实”再现现实的创作意图。古希腊时期的赫拉克利特在解释艺术起源时提出了“自然模仿论”的观点,认为“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1]模仿论明确地回答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为艺术是对客观对象的模仿。基于此,西方艺术极为重视艺术的“真实”问题,是否真实地再现现实,也成为判定艺术作品优劣的尺度之一。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得益于绘画透视原理的发现以及解剖学的发展,艺术家能够更精准地临仿现实的影像。光学原理的发现与对色彩关系的认知,也使得绘画艺术在光影表现、氛围营造等方面更加地贴近现实。
照相术出现后,人类的影像创作进入了机械复制的时代。本雅明认为,“复制技术使复制品脱离了传统的领域。通过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它以一种摹本的众多行取代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复制品能在持有者或听众的特殊环境中供人欣赏。在此,它复活了被复制出来的对象。”[2]在机械复制的时代,机器因素的作用逐渐增强,而人的参与度则明显下降。人们普遍认为照相术是一种比绘画具有更高“真实感”的手段,摄影的过程是对客观对象进行完全机械拷贝的过程,摄影也成为最“真实”的影像活动。鉴于机械复制的特性,“真实”似乎成了摄影艺术与生俱来的一种创作优势,以至于在很多时候对摄影作品的评价往往忽略其在真实再现现实方面的表现,反而更重视其风格化的追求。电影诞生后,影像纪录现实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因为时间的限制被突破了。诚如安德烈·巴赞所言,“唯有摄像机镜头拍下的客观影像能够满足我们潜意识提出的再现原物的需要。它比几可乱真的仿印更真切,因为它就是这件事物的原型,但已摆脱了时间流逝的影响。”[3]在巴赞的理论中,从静态摄影到动态影像,对客观世界的纪录无疑是更真实了:静态摄影终究只是对现实世界的瞬间纪录,是瞬间的真实,电影影像则实现了时间维度的复原,它提供的是一个完整而连续的时空纪录。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沙龙内放映短片《火车进站》时,观众感觉火车就像真实存在的实体向他们冲来,不由得慌忙躲避。这是影像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刻,也是对电影影像真实感的最好的诠释。
电影蒙太奇理论的提出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电影连续时空纪录的媒介特性的认识。剧情片的发展,意味着叙事性的表达取代了原初意义上的纪录。就影像而言,真实和真实感都被削弱了;但就艺术形态而言,电影蒙太奇推动了电影影像语言系统的形成,电影也被认为是最具真实感的艺术形式。巴赞甚至提出了“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的著名论断,巴赞在评论《温别尔托·D》这部影片时指出,“德·西卡与柴瓦梯尼力求使电影成为现实的渐近线,但是,他们始终还是为了使生活本身变为有声有色的场景,为了使生活在电影这面明镜中最终像一首诗呈现在我们眼前。电影最终改变了生活,当然生活毕竟还是生活。”[3]“渐近线”形象地比喻了电影与现实之间无限接近却永不相同的事实。电影应该也可以向现实不断靠拢,但又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现实。电影追逐并表征着现实,但电影作为艺术在根本上是虚构的,电影不是现实本身,它呈现于银幕之上。巴赞认为,“幕与镜子相似(我们必定同意,镜中影子反映被映入镜中的实物的在场),但是,它是带延时映象的一面镜子,仿佛有一层水银涂面会保留住它的影像”。[3]所以,我们从电影看到的现实,只不过是镜面反射的现实,镜子是不透明的,我们也永远不能看到镜子背后的现实。巴赞关于电影与现实关系的一系列论述,将电影艺术所追求的真实与现实世界的真实作了区分,也将电影媒介的艺术属性做了明确的定性。
计算机图形技术的发展,使得影像编辑成为可能,影像可以随心所欲地展现奇观化的图景。在计算机时代,“想象力的边界”成为比“现实的渐进线”更重要的命题。1968年,库布里克导演的《2001太空漫游》上映,该片是首部使用计算机特效的科幻电影,对太空场景、失重状态、真空音效等进行了细致逼真的表现,大量画面均是无法用摄影技术来实现的CG图像。电脑特效不仅提高了影像的表现领域,也提供了更为真实震撼的观影体验。再如,2008年首部3d电影《阿凡达》上映,开启了电影艺术的3D时代,观众佩戴3D眼镜后,能够观赏到纵深感更强、更具立体效果的画面。在一些特殊的影厅,如4D、5D影厅里,通过增设更多的机关来扩展和强化观影效果,提供更丰富多元的观影体验。如2017年,好莱坞版的《攻壳机动队》,片中大量的飞行镜头借助可转动的座椅、以及营造水雾、风扇等设备,营造出了一种具有沉浸效果的观影体验。更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和《双子杀手》这两部影片,导演李安坚持采用3D+4k+120帧的高技术规格来制作影片——尽管这种影片只能在为数极少的影厅内才能充分展现其效果,在视听感官层面力图达到极致,其根本目的是营造更逼真、更接近人眼感受的观影体验。
相对于传统影像而言,虚拟现实艺术的出现,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美学上都是一次巨大的颠覆与革新。传统影像的发展,一直在追寻着再现真实世界的完美方案。默片、有声片、彩色片、宽银幕、环绕立体声、CG技术、环幕、球幕、全景声、3D、I-MAX、4K影像、120帧,电影技术的演进,同时也是电影影像追求真实感的过程。传统影像最大的限制,在于它无法突破单向的“观看”行为,而这一行为从根本上定义了人与影像之间的关系。观众只能通过“观看”一个平面或曲面的影像,在脑海中获得一个虚幻的三维立体图景。虚拟现实艺术改变了这一规则,将人与影像的关系由“观看”变成了“对话”。体验者通过头盔式显示器获得近乎人眼的视角,身体的运动和摄影机的运动同步,观众的行为动作会在影像中有所反应,这些特点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体验。虚拟现实艺术的体验者往往并不认为是在观看一个画面,而是觉得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比如一个街心公园或朋友家的客厅,他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去观察、接触和熟悉这个空间,他需要与之进行全身心的“对话”。因此,从影像与现实的关系来说,传统影像只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投影,而虚拟现实艺术则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复制。
二、运动属性与身体介入
对于电影影像而言,运动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没有运动,也就没有电影影像。电影影像在银幕上的呈现,仰赖于放映机的存在。电影放映机控制着静帧胶片的间歇性连续播放动作,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在大脑中形成连续的运动感觉。电影的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幻觉,因为运动并不存在与银幕之上,而是形成于人的意识之中。柏格森把电影看作是静态切面和抽象时间的结合,瞬时是运动的静态切面,而运动是绵延的动态切面,即运动是全体的动态切面。电影区别于摄影的地方在于电影属于运动的概念。[4]德勒兹则认为,“运动不可以同被驰骋空间相混淆,被驰骋空间已是过往,可运动是正值发生的,即驰骋行动。空间是可被分化的,而运动不可分化,运动之间彼此互为独立,无法相互交化。”[4]显然,德勒兹并不认同柏格森对静态切面的“电影式幻影”[4]的描述,电影是同下述两种条件中相应而生的,一种是我们称为影像的瞬间切面,另一种是普遍性、统一性、抽象、不可见、无法感知的运动时间,电影展示给我们的是一种动态影像[4]。雷内·克莱尔说得更为直接,“如果确实存在一种电影美学的话,那么这种美学是在法国、在卢米埃尔兄弟发明摄影机和影片的同时诞生的。这种美学可以归结成两个字,即‘运动’。”[5]电影影像的运动包括三重含义:第一是被摄对象的运动,第二是摄影机自身诸如推拉摇移等运动,第三是蒙太奇造成的时空转换。
运动作为电影影像的本质属性,也是电影影像美学的核心,这与人的“观看”行为密切相关。人的眼睛似乎天然地对运动中的事物比较敏感,而一段静止的、监控式的影像记录,往往会被认为是枯燥乏味的。因此,很多创作者都非常重视影像的运动问题。事实上,除了上述三种影像运动外,包括构图、光线、色彩、明暗等元素的变化以及任何意在加强运动感的手法,也都足以减轻视觉上的枯燥感和隔阂感。正如贝拉·巴拉兹所说,“电影表现的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他只是运用了不同的手法,但结果却使得欣赏者和艺术作品之间的永恒的距离在电影观众的意识中完全消失了,而随着距离的消失,同时也消除了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距离,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一状态是电影艺术的组成部分。”[6]可以说,运动即使是在观众感受层面,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与基于“观看”行为的影像运动不同,虚拟现实艺术所营造的是一个基于“对话”行为的空间,它更像一个具有召唤意味的结构,需要体验者全身心地在这个空间里“漫游”。1968年,虚拟现实艺术之父伊凡·苏泽兰开发的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VR设备——“达摩克里斯之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泽兰设想:终极的显示是一个房间,通过电脑可以控制房间内的一切。椅子可以逼真到你想上去坐一坐,手铐简直可以拷人,子弹好像能置人于死地。苏泽兰认为,这一设计只要用适当的程序,就可能创造出文学上爱丽丝漫游的奇境。对于奇境的想象,或许是虚拟现实艺术后续发展的社会心理动机:创造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似的、完整而连续的虚拟空间,体验者可以“漫游”其间,充分调动身体的各种感官与这个环境“对话”,获得全新的身心体验。
虚拟现实艺术的运动,取决于体验者的身体动作,是高度自由而随意的。不同的体验者在虚拟现实艺术语境中,无须遵守某种特定的规则,只需要像在自家客厅里游走即可。虚拟现实艺术的构建,由计算机图形软件完成,颠覆了摄制影像的概念;360度的全景展示,突破了镜头和场面调度的范畴;虚拟现实艺术强调体验的整体效果,叙事似乎也变得可有可无;体验者依赖身体动作与环境之间产生互动,身体的介入和自由运动才是虚拟现实艺术得以连续呈现的前提。
身体的介入成为可能,端赖于空间定位技术的成熟。因为虚拟现实艺术是以体验者的视觉点为中心的三维虚拟影像,对体验者位置的实时定位是实现虚拟现实艺术运动的前提。动作捕捉以及空间定位技术是实现虚拟现实艺术的两个最核心的技术。虚拟现实艺术的运动方式和表现,与这两项技术息息相关:VR系统以极短的时间间隔来反复评估体验者的移动速率与方位,每两次评估就可以确定观众的准确位置。这种评估的频率越高,定位就越准确。动作捕捉的跟踪范围决定了体验者可以实现的运动幅度,跟踪范围越大,体验者就可以在更大幅度的肢体动作范围内与影像产生交互。
身体介入是虚拟现实艺术运动的最大特点。体验者的初始位置,就是身体介入的原点。体验者的每一个身体动作、手势或语言,经VR系统动作捕捉和定位技术处理后,反馈为虚拟现实艺术的运动和变化。而这些影像的运动和变化,又会进一步引发体验者的后续动作。这种以身体为媒介的人机“对话”关系,真正地将体验者置于一个由自身动作开启的虚拟世界中。在这个封闭、绵延虚拟时空里,体验者无时无刻不在用“身体”发出一个个指令,用“身体”接收这个被复制出来的“现实世界”的信息反馈,也用“身体”感受着从生理到心理的全方位反应。
三、环境交互与审美经验
虚拟现实艺术与所有的传统影像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交互性。虚拟现实艺术为体验者提供的,是一个可以与之进行平等“对话”和信息往还的与现实世界相似的语境。人们总是很容易区分影像与现实,因为影像无法与人产生实时的互动和交流,观众只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虚拟现实艺术则是构建了一个“真实”的模拟环境,这个环境中的一切都与人构成交互关系。观众在虚拟现实艺术世界中的表现,与置身于一个不太熟悉的现实空间的表现非常相似。
虚拟现实艺术的交互体验,具有“回到现实”的特点。在大量的交互行为中,人们需要通过某个媒介来进行交互行为。譬如智能手机的交互行为,便是人类与微型电脑之间进行交互的媒介,这种交互形式本质上是非现实的,因为体验者需要学习某个特定媒介的交互方式,才能获得良好的体验。而虚拟现实艺术的交互,旨在削弱这种媒介属性以及其所产生的学习门槛,实现“回到现实”的交互逻辑。这种交互逻辑,建立在虚拟现实艺术技术所具有的高度沉浸性与现实模拟的基础上。360度的全景呈现,与现实环境中的景象如出一辙。影像本身被环境化,直接投射到人的视网膜上,用以呈现影像的屏幕消失了。环境化后的虚拟现实艺术,使体验者的感知像处在真实环境中一样进行自由的浏览,只需要动一动脑袋就可以浏览四周的“环境”。与可穿戴设备配合后,可以像在真实世界中一样移动物品。所有的身体动作如移动、浏览、触碰,都可以实现与真实世界的高度相似,从而达到一种仿佛“回到现实”的交互形式。因此,体验者不再需要通过与特定媒介互动来达到了与影像的交互,而是直接面对影像,这种“回到现实”状态的交互体验,在人类影像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交互也成为虚拟现实艺术最具特色的审美体验和美学特征。作为体验主体的人,在虚拟现实艺术世界中通过身体动作与所处的影像环境之间进行信息交互,获得身心的愉悦感,这是虚拟现实艺术提供的前所未有的逼真体验,犹如在真实的三维空间中一般。虚拟现实艺术的交互形式,基于虚拟现实艺术中体验者的运动方式。通常体验者需要双手手持带有按钮和震动反馈的、能够自由定位的手柄,按钮和震动反馈,也是现阶段虚拟现实艺术的主流交互方式。体验者通过动作、手势等身体语言,与虚拟世界进行互动和沟通。体验者的手部动作和走动行为,在虚拟影像世界中产生能够让人理解的变化,其实是虚拟影像对体验者发出的一次反馈。体验者的身体动作和虚拟影像世界的信息反馈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交互行为和审美体验。
交互体验在虚拟现实艺术中最好的状态,就是让体验者感觉不到交互行为的存在,正如人们在现实空间中那样,与周遭环境浑然一体。VR交互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交互,它所营造的全景影像空间与现实生存空间高度相似,完全符合观众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与传统游戏相比,VR交互体验不需要停下来思考下一步的选择,那样会中断体验和信息的交互。体验者可以在VR交互游戏中获得高度的审美体验。Oculus Story Studio开发的《Henry》游戏,就加入了让玩家可以与小刺猬通过眼神进行互动的功能,增强了体验者和小刺猬之间的共情体验,该作品因而获得了艾美奖最佳原创互动节目奖。
虚拟现实艺术的交互特性及其独特的审美体验,也让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韩国MBC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遇见你》,利用虚拟现实艺术技术让体验者在虚拟世界中与逝去的亲人相见,创造了一次真实的情感体验。一位韩国母亲,7岁的女儿因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而离世。韩国MBC的创作团队为了弥补这位母亲内心的缺憾,耗时8个月,用小女孩的生前照片重建了面容,并设计了这场“久别重逢”,让妈妈和去世的女儿在虚拟影像世界中再次相见。当这位母亲戴上VR设备后,她不仅看到了女儿的影像,还听到了女儿的声音。通过手部佩戴的交互传感器,母亲还可以通过手势、触碰等的方式与离去的女儿互动。母女俩一起击掌,一起吹灭生日蛋糕的蜡烛,还拍了合影。可以说,虚拟现实艺术技术消融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实现了生与死的跨越。虚拟现实艺术的高度交互体验,足以使人忘却现实空间的存在,而沉浸于另一个虚拟现实艺术所构建的新的时空里,获得另类的情感与生命体验。正如诺兰在电影《盗梦空间》中展现的那个场景:老人们宁愿花巨额费用沉浸在人为营造的梦中,也不愿意醒来面对现实。虚拟现实艺术让人可以在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里与周围环境产生互动,这个空间与现实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完全可能在某一个瞬间产生对现实的怀疑。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更美好的事物才是现实,而人为营造的虚拟现实艺术空间由于能够带给人更完美更深刻的情感体验,其与现实空间的关系以及两者孰真孰假的问题,便越发地模糊了。
交互的审美体验,能够带给体验者强烈的自我认同,这种认同感则进一步将体验者“代入”虚拟现实艺术世界中。在创作中,越来越多的VR作品强调如何实现“代入”效果,而非仅仅拟造一个虚拟现实空间。在VR动画版《狼与辛香料》当中,动漫化的视觉效果、奇幻的场景风格、互动元素的加入实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让体验者更容易地“代入”到故事语境中去。再如刀剑神域的新作《刀剑神域:Alicization》,它描述了一个未来风格的VR世界,里面的角色均由人工智能生成,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人格,角色与角色之间也拥有着丰富的互动关系。这种设定的目的,无疑也是让体验者能够迅速地进入到虚拟现实艺术语境中,获得深度的审美体验。如果将这样的设定应用在某个特定的故事中,真正意义上的VR交互式电影或许就产生了。电影中的每个角色都能够与观众进行互动,这种观众与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像蝴蝶效应一样,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与每个角色之间的互动都有可能影响到故事的后续发展,每一位观众都将导演一出与他人截然不同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
虚拟现实艺术的交互,动作与行为只是表层,情感和审美的体验才是交互的真正目的,这也正是虚拟现实艺术美学的独特之处,基于真实,源于身体,诉诸情感。可预见的是,虚拟现实艺术的不断进展,会让人类有更自由的选择去进入一个另类的时空。虚拟现实艺术空间或许只是又一个“楚门的世界”,但对于体验者来说,在其身心灵上激起的震撼与回响,无疑又是真实的。当身边的场景真切如常,漫游其间自由自在,所有的感官全部打开,在触摸、感知和互动中,情感得以酝酿升华,心灵建立起了对话与交流,真实与虚拟的界限也便越发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