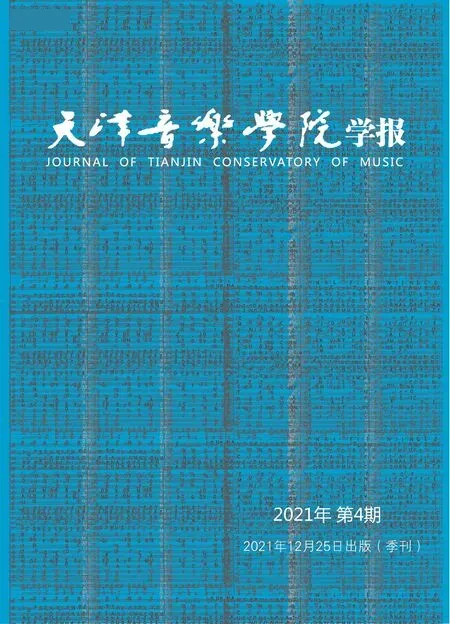暮景之下的“新世界”
——评《晚景与勃拉姆斯:维也纳自由主义黄昏中的音乐与文化》*
2021-12-05王梓路
王梓路
导 言
在艺术和人文批评中,将“晚期风格”引入文学、音乐和视觉艺术的现象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80)Gordon McMullan and Sam Smiles, “Introduction: late style and its discontents”, Late Style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而在西方音乐的历史进程中,对“晚期”这个概念的讨论与贝多芬的音乐有着最直接的关系。(81)David Beard and Kenneth Gloag.ed. Musicology The Key Concepts: “Lateness”,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6, pp.150-152.究其本质而言,“晚期”和“晚期风格”断然不是相同的概念。简单来说,“晚期”一词属于客观的时间范畴。根据萨义德的描述,我们很值得在“晚期”这个词语微妙地变化着的含义之上逗留,它的范围从未完成的约定、经过自然的循环、直到消失了的生命。(82)[美]爱德华·萨义德:《论晚期风格》,阎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XI页。同时,“晚期”并没有指定一种与时间相关的单一关系,它是一个相对的术语,但始终都会带来时间上的后果。(83)同上,第XII页。在艺术史长久以来的发展中,“晚期风格”更多地属于美学范畴。音乐中的“晚期风格”往往包含了诸如“怀旧”“简洁”与“抽象”等颇具审美意味的内在特质。因此,“晚期风格”一词意义指向含混:它既是一个 “批评性术语”,也是一个 “描述性术语”。(84)杨婧:《“晚期风格”在当代西方音乐学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136页。在“前阿多诺阶段”,所谓“晚期风格”,主要是作为一种描述性的时间概念,纯粹指称某位艺术家或某种风格类型的末期阶段的风格。(85)同上,第137页。因此笔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晚期风格”并非是一种一成不变的风格,它可以普遍存在于每位作曲家的艺术生涯中,但不受到某些共性特征的限制。换言之,贝多芬“晚期风格”中的“疏离破碎”、舒伯特“晚期风格”中的“死亡意象”,都不是形成一种“晚期风格”所必须包含的品质。随着“晚期风格”从这些刻板印象中逐渐脱离,对“晚期风格”的研究开始在西方当代音乐学界兴起。从此前的受冷到当代的备受关注,这一现象的转变无疑值得深省。
相比一直以来经久不衰、几乎占据统治地位的“贝多芬晚期风格”研究,玛格丽特·安妮·诺特里在《晚景与勃拉姆斯:维也纳自由主义黄昏中的音乐与文化》一书中所呈现的勃拉姆斯的“晚期风格”,为“晚期风格”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语境,也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话题的内涵,仿佛以一种自信的姿态向世人宣告:贝多芬的“晚期风格”并不是一种“规定性范式”,勃拉姆斯的“晚期风格”同样具有独一无二的个人特质。实现这一图景的做法即是将全书的论域置于社会学视野之下——在19世纪末维也纳复杂的背景中,通过重点关注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并以多种政治因素为线索贯穿全文,同时结合对其晚期室内乐作品的分析,深刻揭示了勃拉姆斯的“晚期风格”是如何在社会学场域中逐渐成形的。此外,集中于勃拉姆斯音乐本体的实证主义研究已臻全面,而对作曲家个人思想与作品之间相互关系的考量依旧匮乏,诺特里的《晚景与勃拉姆斯》中,融入了许多关于勃拉姆斯宗教信仰、政治倾向以及民族意识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缺。
全书共分为六章,作者开篇即阐明了立场态度,希望抵制一种普遍趋势——即以中立的、非历史的方式看待勃拉姆斯。对勃拉姆斯政治观点的探讨在第一章和结语中均有涉足,第一章通过关注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和勃拉姆斯周围派系之间的政治化冲突,将这位作曲家置于世纪末的维也纳,并指出“音乐逻辑”和“体裁”在今天的概念之外具有重要意义。从第二章开始,作者在“维也纳自由主义”的政治背景下引入“晚期风格”这个话题,并与后一章形成一体,详尽探讨了“音乐史上的晚期”和勃拉姆斯的“晚期风格”,对音乐本体的细致分析也集中于此。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了“体裁”概念在“衰落叙事”(narratives of decline)中的作用,以及勃拉姆斯晚期作品中采用“吉普赛风格”的做法与某些政治因素的关联。那么,“晚期风格”对勃拉姆斯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晚期风格”最终走向了何方?介于本书中的政治因素几乎贯穿始终,笔者将以此为主要线索,首先评述诺特里如何从政治视角来塑造作曲家的人物形象,进而阐述勃拉姆斯“晚期风格”这一话题及其内涵特质,最后对其“晚期风格”作出进一步思考。
一、 勃拉姆斯:作为中产阶级作曲家的“自由主义者”
众所周知,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德奥音乐在“勃拉姆斯阵营”和“瓦格纳阵营”之间发生了明显的两极分化,(86)Walter Frisch, “The ‘Brahms Fog’: On Analyzing Brahmsian Influences at the Fin de Siècle”, Brahms and His World, ed. Walter Frisch and Kevin C.Karne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17.尽管两个阵营之间存在分歧,但勃拉姆斯仍旧欣赏瓦格纳的作品。而布鲁克纳作为一位“精神上的”瓦格纳主义者,终其一生都在与勃拉姆斯对立。以此为出发点,诺特里带领我们将视线转向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维也纳。瓦格纳死后,音乐就与政治搅在了一起,盛行的“自由主义”世界观呈现出复杂的态度:亲德情绪、对天主教会的敌对以及对“反智主义”的极度不信任。(87)“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哲学,是以自由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于国教的对抗。本书中的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哲学,还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的冲突是在这种动荡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诺特里在书中指出,自由主义批评家贬低布鲁克纳和天主教堂的密切关系以及他明显的教养缺乏;同情反自由主义运动的评论家认为,勃拉姆斯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双方都指责对方搞党派斗争,都有超越音乐范围以外的动机。而随着公开的“反自由主义”批评达到高潮,勃拉姆斯甚至被贴上了犹太人的标签。(88)奥地利政治家卡尔·吕格尔将小市民对自由主义的嫌弃与反犹主义整合,奥地利天主教神学家阿尔伯特·维辛格同样将自由主义与犹太民族结合起来予以批判,使自由主义者越来越等同于犹太人。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感叹,勃拉姆斯为大众所接受的形象似乎向来都是“传统的维护者”“明确坚守古典—浪漫传统的最后一位大师”,即便是浪漫主义中的“反潮流”,也远不及被当作“犹太人”这样尖锐。
这种充满政治色彩的描绘,是诺特里通过对史料的大量搜集和梳理得来的。与以往对勃拉姆斯身份中政治因素的轻描淡写甚至根本不留笔墨相比,诺特里的叙述犹如异军突起。她明确表示勃拉姆斯当然不是犹太人,但他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作者认为与其音乐相关的主题的阐述更普遍地与自由主义精神相联系。这样看来,她似乎是在有意塑造勃拉姆斯作为中产阶级作曲家的“自由主义者”形象。一方面,作者认为勃拉姆斯以传统为导向的作曲方法显然符合主流文化中大众的趣味;另一方面,作者也强调其音乐的本质投射出了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此外,诺特里进一步指出,基于勃拉姆斯极为注重音乐理念中的“逻辑性”,许多作家都将他这种做法与中产阶级的态度联系起来。例如,德国作家蒂博尔·克尼夫(Tibor Kneif)就强调中产阶级通过努力工作实现个人成就的精神,正是勃拉姆斯创作方法的缩影,他认为这位作曲家将中产阶级的品质人格化到一个无与伦比的程度。(89)See Margaret Anne Notley, Lateness and Brahms, p.7.这样一来,“音乐逻辑”这一音乐理论范畴中的概念,就与“中产阶级”这样的社会学语词产生了关联。将“音乐逻辑”作为一种概念的极少提及确实出现在古典时代的巅峰时期,到十九世纪后期,将音乐作为一种语言的使用,以及对“音乐逻辑”这一概念的引用变得越来越频繁。在笔者看来,相比于福克尔将调性关系的和声规范称为“音乐逻辑”这样的音乐学表述,(90)参见[德]卡尔·达尔豪斯:《绝对音乐观念》,刘丹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1页。诺特里更倾向于申克和达尔豪斯的社会性解读。首先,申克认为复杂器乐的逻辑性和连贯性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这与达尔豪斯指出的音乐逻辑的历史性相契合。诺特里高度肯定达尔豪斯的解释,她认为在最近的音乐学者中,没有人比达尔豪斯更深入地探讨音乐逻辑的概念,特别是在关于勃拉姆斯的著作中,他就将重点放在音乐逻辑方面,认为“发展性变奏”即音乐逻辑的体现,而“发展性变奏”恰恰是阿多诺所认为的室内乐中至关重要的元素,也正是音乐逻辑和室内乐之间的关联,使勃拉姆斯成为这一体裁公认的“统治者”。(91)See Margaret Anne Notley, Lateness and Brahms, p.25.
用施密特的话来说,勃拉姆斯作为“室内乐作曲家”的身份,在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92)Ibid., p.9.随着布鲁克纳《F大调弦乐五重奏》的上演,他与勃拉姆斯之间的冲突再度爆发。从诺特里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勃拉姆斯的传记作者马克斯·卡尔贝克(Max Kalbeck)(93)马克斯·卡尔贝克:奥地利音乐评论家,勃拉姆斯传记的主要作者。他是勃拉姆斯的朋友,编辑了大量与作曲家有关的书信,并提供了关于音乐作品的诸多历史细节,在当今勃拉姆斯的研究中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认为,布鲁克纳缺乏对“音乐逻辑”的洞察力;而布鲁克纳的传记作者奥古斯特·古雷里希(August Göllerich)认为勃拉姆斯的室内乐不够纯粹,只有对与艺术相关的历史进行反思之后才能够被理解。在这种无休止的论战中,诺特里做出如下总结:表面上,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争论的中心是一场关于“旋律灵感”和“音乐逻辑”的相对价值的艺术分歧,然而,这种争论并不仅仅是美学上的。很显然,无论是“音乐逻辑”还是“体裁”,都被赋予了政治意义。达尔豪斯认为,至少在整个十八世纪,音乐体裁是在个人作曲家的风格倾向和社会阶层的要求和期望之间进行协调的。(94)Margaret Anne Notley, Lateness and Brahms, p.158.在十九世纪晚期维也纳狭窄的背景中,交响曲就在民粹主义情绪的推动下获得了更高的地位,许多维也纳音乐界的积极分子都认为音乐能够缓解阶级之间的紧张,较之室内乐,交响曲无疑能与更广泛的民众进行对话。而关于政治因素如何以及多大程度影响“室内乐”与“交响曲”两种体裁在公众话语中的接受,是作者在第五章中重点论述的。
由此可见,将“室内乐”这一音乐体裁作为某种政治工具对作曲家进行攻击就不难解释了。通过以上梳理笔者发现,勃拉姆斯是在维也纳居民生活条件极度不平等的时期居住在那里,他不但变得富有,还与这座城市的上层中产阶级精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其创作的室内乐体裁本身就具有私密的、无法普及全民的“精英主义”倾向。借此,古雷里希看似是阐述勃拉姆斯与布鲁克纳在室内乐创作中的艺术分歧,实则毫无理由地将勃拉姆斯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因为在许多反犹运动中,犹太人与自由主义被视为一体。(95)[奥]库尔特·舒伯特:《犹太史》,颜展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第193页。“反犹运动”中的犹太人和自由主义者都被视为原有经济秩序的威胁,犹太人更被当作时代精神的代表遭到迫害。也正如历史学家史蒂文·贝勒(Steven Beller)指出,在自由主义日渐衰落的年代,任何人都可能因为与犹太人有联系而名誉扫地,而自由派通常是攻击目标。(96)See Margaret Anne Notley, Lateness and Brahms, p.34.这些愈演愈烈的冲突最终在自由主义的崩溃中达到顶峰,诺特里在厘清史实的最后,坚定地避开了中立的态度,肯定了勃拉姆斯作为德国作曲家的身份。
二、 维也纳“自由主义黄昏”下的勃拉姆斯“晚期风格”
随着第一波现代主义浪潮的涌现,中产阶级自由文化开始日渐衰落,勃拉姆斯所处的维也纳环境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以此为基点,诺特里架构出一个更广阔的视角,观察到勃拉姆斯的风格转变与“黄昏”时期的维也纳自由政治和音乐文化相吻合。她指出,这为“晚期风格”的解读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背景,但也必须谨慎地加以解释。
从时间范畴而言,勃拉姆斯的“晚期风格”是在“音乐史上的晚期”中成形的,他在世纪末写下了最后的作品。诺特里强调,虽然“晚期风格”和“音乐史上的晚期”是基于不同的假设,但这两个概念都为考虑勃拉姆斯晚期的音乐提供了有效的框架,它们之间是辩证关系,彼此制约。随后,诺特里简要评述了一些学者对勃拉姆斯“晚期风格”的研究,在此仅举两例。首先是阿多诺,当阿多诺进行勃拉姆斯音乐的研究时,他通常把重点放在主题、动机和形式上,使勃拉姆斯成为广泛的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并将其描述为贝多芬和勋伯格之间的纽带。这样的做法似乎不能完整呈现勃拉姆斯风格中的全部复杂性,更不用说风格变化的可能性,但诺特里指出,这种零星的评论仍具有未开发的潜能。其次是尼默勒(Niemöller),他认为从《第四交响曲》到《管风琴前奏曲》都是勃拉姆斯“晚期风格”的表现。最后,诺特里提出自己的思考:勃拉姆斯“晚期风格”的变化、以及变化被感知的语境是什么?晚期音乐听起来有何不同?以这三个角度为基点,诺特里结合从1880年中期开始的室内乐作品,并依旧关注政治因素,对“晚期风格”背后的音乐文本(作品谱例)及内在特质进行了全面分析。在此仅举四类具有代表性的特质进行概述。
其一,诺特里指出了勃拉姆斯对“技巧”的重视,她认为二十世纪对作曲家“晚期风格”的讨论往往都是抽象的,或是倾向于一种精神上的感受,这种感受通过专注于作曲家的创作技巧而获得。而技巧只是他“晚期风格”的一个方面,这类技巧通常包括“将表达的复杂性集中于简洁的音乐语言中”,例如《c小调钢琴三重奏》。其二,诺特里更进一步谈到,对技巧的精湛运用——勃拉姆斯在某些作品中频繁地使用“等音转调”——甚至上升到了“矫饰主义”的层面,(97)矫饰主义又称“风格主义”,源于意大利语Maniera,最初用于绘画中,强调艺术家的内心体验与个人表现。在音乐领域,查尔斯·罗森认为:“1755年到1775年之间,缺乏一种在所有领域中都同等有效的整合性风格。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我们认为这一段时期具有‘矫饰性’”。例如《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就被贴上了“矫饰主义”的标签,诺特里认为这种矫揉造作与人们对自由文化的抱怨如出一辙。如果我们仔细回溯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格鲁克的新古典主义,有意拒绝诸多传统技巧;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任性武断的戏剧性激情转调与切分节奏;1760年代海顿交响曲中的暴力倾向——所有这些,都是‘矫饰性’的举动,为的是填补因为缺乏一个整合性的风格而产生的真空。”(98)[美]查尔斯·罗森:《古典风格》,杨燕迪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8页。其三,勃拉姆斯调性技巧的另一个方面是“调性的明暗对比”(chiaroscuro)手法,这一手法很好地体现在了《b小调单簧管五重奏》中,诺特里认为这部作品通过不断暗示主属之间的关系、频繁地在大调和关系小调之间移动,通过将一个无处不在的动机与几个和声性的意义相关联,并参照形式的界限和各部分的对比,最终暗示了一部晚期作品的“混合性质”(Verschmolzenheit)。作者进一步解释道,“混合性质”作为勃拉姆斯晚期音色特点的同时,也关联到一种风格倾向。她将这一性质联系到布林克曼(Brinckmann)对视觉艺术家晚年的研究,他们在晚年都呈现出一种“回归自我”的心理倾向,“混合性质”即用来形容这种心理倾向的客观关联。(99)Brinckmann Reinhold(1934—):德国音乐学家。其作品涵盖19—20世纪作曲家,包括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斯克里亚宾、艾夫斯等,尤其是勋伯格。除音乐分析,布林克曼还以关于音乐社会历史的著作及跨学科研究闻名。其关于勃拉姆斯的主要著作有Johannes Brahms, Die Zweite Symphonie:Späte Idyll. 由Peter Palmer英译为Late Idyll: The Second Symphony of Johannes Brahm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其四,作者认为这种“混合”风格传达出了“内省”,而“内省”是谈及勃拉姆斯“晚期风格”时无法避开的重要特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室内乐体裁似乎就是“内省”风格的天然载体,在勃拉姆斯致力于室内乐理想的过程中,自身年龄的增长以及与布鲁克纳之间政治危机的深化都是催生“内省”特质的诱因。布林克曼更是将内省的室内乐风格与“音乐史上的晚期”联系在一起,认为勃拉姆斯的音乐传达了中产阶级生活的忧郁。(100)See Margaret Anne Notley, Lateness and Brahms, p.75.
基于以上勃拉姆斯“晚期风格”的特质,诺特里认为,在维也纳内部,“晚期风格”问题已成为对作曲家进行论战攻击的又一工具,许多评论家都以一种偏颇的方式,甚至夹杂着“反犹情绪”来看待勃拉姆斯的“晚期风格”。因此,其风格的转变以及被感知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发生的,“晚期风格”的概念已经被政治化。相比那些认为勃拉姆斯“晚期风格”代表衰落的极端看法,诺特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留有赞誉,她认为勃拉姆斯晚期的音乐虽很少触及内心深处的灵魂,但他能赋予我们一种反思性的快乐,最重要的是,通过他对“音乐逻辑”的驾驭,以及他在陈旧的传统中寻找意义的能力,勃拉姆斯总能够创作出听起来既符合时代又与时代格格不入的音乐。
三、勃拉姆斯“晚期风格”的再思考
当人们谈及音乐时,有一种针对音乐社会学的异议一再被提出,这种异议就是:音乐的本质,它的纯粹存在本身(Ansichsein),与它在社会状态和社会条件中的复杂瓜葛没有任何关联。(101)[德]特奥多尔·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梁艳萍、马卫星、曹俊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第185页。虽然在非音乐领域中,艺术社会学早已变成对行为方式的解释,但在音乐中,我们似乎不能像在十九世纪的小说中所能做的那样去指责社会环境。(102)同上。尽管如此,笔者依旧认为,音乐家作为个体而言,本身就是社会存在,其作品的创作构想也就必然离不开社会因素的浸润。莫扎特的音乐就清晰地反映了从启蒙运动晚期的专制主义向资产阶级政治的过渡;(103)同上,第80页。瓦格纳更是指望“整体艺术品”能推动他所设想的德国人民的革新运动。可见,音乐及与其相关的一切皆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这也是诺特里为这部著作设定的基调。然而,本书在某些方面的叙述方法还是给笔者带来了些许困惑,也正是因为对叙述策略的重新审视,使笔者对“晚期风格”作出了进一步的思考。
首先,诺特里开篇便从社会学视角全面考察了勃拉姆斯所处的环境,这一社会学维度的探讨不仅涵盖了作曲家个人,还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体裁”概念。但这一涉及似乎并未真正触及核心,也没有达到作者所言的预期,即阐述“体裁”概念的特殊含义。换言之,作者是期望在自己设定的社会学论域中,通过讨论勃拉姆斯周围的政治环境,进而关联到“室内乐”这一体裁所承载的传统之外的意涵。但在具体实践中,作者仅提及勃拉姆斯作为室内乐作曲家的身份具有政治意义,除此之外,围绕“室内乐”这一体裁的论述均集中于音乐学范畴,并未读出所谓音乐之外的“特殊含义”。随着阅读的深入,笔者发现,诺特里在第五章设置了大量篇幅来探讨“交响曲”与“室内乐”体裁的概念、接受甚至意识形态等问题。这一做法看似与前文有所保留的论述相辅相成,但实际上并不利于论述这一概念所需的整体性,原因有二。第一,从章节设置来看,正文部分围绕世纪末的维也纳展开,一步步引出“晚期风格”的话题,最终在第二章点明勃拉姆斯“晚期风格”这一中心论域,第三章则进入微观层面,着眼于作品本身。然而第四章却突然将目光转向勃拉姆斯对各类关于使用“平行五度”手稿的收集,并对围绕这一技法的争论做了大量对比。一直到第五章,作者才重新将话题转入先前的设定中。因此,就阅读的连贯性和整体性而言,作者的布局策略不免会形成一种断层感。第二,虽然勃拉姆斯的交响曲享有盛誉,但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部著作是立足于勃拉姆斯的室内乐创作的。而诺特里在第五章中重新开始论述“体裁”概念时,给出的仅仅是室内乐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却将笔墨更多地留给交响曲的意识形态甚至是“纪念碑性”。然而,这种横向拓宽论域的做法似乎有些失控,毕竟书中有限的篇幅并不能很好地承载“纪念碑性”这一话题的厚重,以至于削弱了整体论述的纵向深度,甚至让人在这部分叙述中读出了“通史”的感觉。如果将作者的思路纵向延伸,应该进行的论述或许是“室内乐的繁盛和自由主义的巅峰时期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或是“室内乐是艺术与接受之间平衡的避难所,它通过消除公开性因素而建立起平衡,而公开性因素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同样属于这一观念的财产差别和教育特权却是与公开性因素相敌对的”。(104)同上,第101页。这样一来,室内乐体裁的概念便能更多地与社会学形成关联,从而使论述更加完整。
实际上,叙述策略造成的困惑渗透到了“晚期风格”的诠释中。很显然,诺特里向我们展示的勃拉姆斯“晚期风格”拥有众多的内涵特质,这些特质的论述多集中于第二章和第三章,既能让人感受到丝丝入扣的关联,也有让人耳目一新的跳脱。但还有一种极富代表性的特质——“吉普赛风格”,诺特里将其归入了最后一章中。在此,她将“慢板”作为一种“体裁”概念这一现象呈现给读者,同时也指出,贝多芬之后慢板的创作开始变得困难——慢板衰落了,而影射的则是整个时代弥漫的衰落感。这时的勃拉姆斯在晚期室内乐的慢板中,引入了“吉普赛风格”,无疑是为这种走向衰落的体裁带来了复兴。作者进一步谈到,勃拉姆斯此举是受到维也纳文化多元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是在十九世纪末,为了应对激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其他在帝国中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而产生的。由此可见,“吉普赛风格”的使用成为勃拉姆斯“晚期风格”中的又一亮点,且以《b小调单簧管五重奏》为代表,但在此前集中讨论“晚期风格”,甚至是对单簧管五重奏的音乐分析中,作者却对“吉普赛风格”只字未提。虽然在最后,作者将这一风格置于更深远的文化语境中论述,并实现了将“晚期风格”与社会背景相互关联的做法,但总体而言,这样的布局策略在对勃拉姆斯“晚期风格”的全面考量中还是造成了某种停滞感。
此外,笔者对勃拉姆斯“晚期风格”的另一个思考也来自于诺特里的启示。在谈到交响曲体裁时,作者提出疑问:为什么交响曲中的慢板通常不具有独特的性格特点?答案是这类往往与抒情性关联的特点更适合与钢琴独奏相关的自我表达,但交响曲必须表达一个群体的情感。由此可见,钢琴独奏为浪漫主义主体性的表达提供了天然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与勃拉姆斯晚期对“个人主义”、自我表达的追求相适应。虽然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他是出于这一目的而写下了几部晚期钢琴作品(Ops.116—119),但这些钢琴作品对其“晚期风格”的构成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一些更为明显的“晚期风格”特质,是在钢琴作品中体现的。遗憾的是,诺特里的选择并未涉及这几部钢琴作品。比如勃拉姆斯晚期时对“音色”的追求,在《be小调间奏曲》(Op.118)中得到深刻诠释——从天籁般的高音到浑厚的中音,再到昏暗的低音,勃拉姆斯的“完美低音”都笼罩在阴郁的音色中。(105)George S.Bozarth and Stephen H.Brady, “The Pianos of Johannes Brahms”, Brahms and His World, ed.Walter Frisch and Kevin C.Karnes, p.82.这是其晚期作品的理想音色,与室内乐中的“混合性质”不同,从作品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方面来看,勃拉姆斯亦追求声音的某种统一——这与现代钢琴中对于声音同质性和均衡性的追求是相符的;所以最终使得晚期钢琴作品既富有管弦色彩的多样性,又存在着更大的潜在的统一性。
结 语
无论是对“晚期风格”的探讨,还是对勃拉姆斯的研究,都是当今音乐学界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卡尔贝克的“传记式”研究,还是瓦尔特·弗利什(Walter Frisch)立足于作品的音乐分析,都在勃拉姆斯的研究中具有相当分量的学术价值。诺特里的《晚景与勃拉姆斯》更是因其富有新意的独特视角,在林林总总的史料著述中占得一席之地,为我们呈现了更多勃拉姆斯音乐之外的生活图景。
对于“晚期风格”,在阿多诺的用法中,“late”这个形容词没有让人安心或鼓舞人心的意思,它所包含的并非是乐观的预测,而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将灭亡。(106)Robert Spencer, “Lateness and Modernity of Theodor Adorno”, Late Style and Its Discontents, ed. Gordon McMullan and Sam Smiles, p.231.在萨义德看来,晚期作品会引起不满和警觉,使人拒绝安定、拒绝服从、拒绝与主流观点保持一致。(107)Ibid., p.222.因此,“晚期风格”更多地意味着不和解,意味着走向衰落;相比通常“晚期风格”中“碎片化”所带来的暴烈,勃拉姆斯的“晚期风格”更能触动内心深处的波澜,在他的“晚期风格”中,我们看到的是因其性格中的敏感和浪漫主义倾向所表现出的“忧郁”和“内省”,以及最后在“吉普赛风格”中的忘我,也正是这种忘我的沉醉,使勃拉姆斯不断探寻,实现了体裁的复兴,走入了属于自我的“新世界”。
最后,虽然诺特里的这部著作在叙述策略上存有不足,但其细致入微的音乐学分析、敏锐深刻的逻辑性思辨以及宽疏广阔的社会学视野仍是本书不可忽视的亮点。更为重要的是,相比于传记式的书写,诺特里的写作着眼于勃拉姆斯的“晚期”,加之作者富于洞见的批评性论说,就使得勃拉姆斯“晚期风格”的特质得以更大程度的展现,为其“晚期风格”的研究提供了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参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诺特里的长远目光和深远考量都与勃拉姆斯的“反潮流”精神相契合,二者都时刻警醒着我们——历史的浪潮不会等待流连沙滩的疲乏者,更不会淹没渴望觉醒的冲浪人,只有在历史的潮流中与时俱进而又不随波逐流,融会贯通而又能坚守自我,才能进行永无止境的探索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