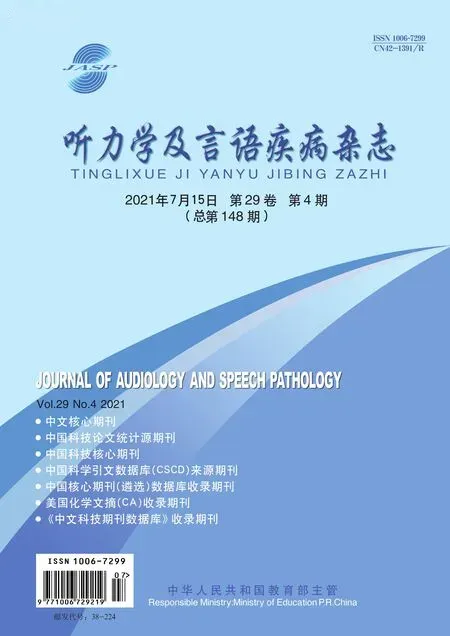近三十年国内汉语失语者的语言障碍研究*
2021-12-05赵妮莎姜孟
赵妮莎 姜孟
失语症(aphasia)是一种获得性语言障碍,即后天习得的语言能力因大脑局灶病变而受损,其主要分类为Broca失语、Wernicke失语、传导性失语、经皮质运动性失语、经皮质感觉性失语、命名性失语、完全性失语等[1]。近三十年来,对汉语失语症的研究从单纯的临床研究逐步发展为神经科学、影像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共同关注的领域。为分析汉语失语症患者的语言特点,本文对国内1990年~2020年发表的汉语失语症语言障碍的相关研究从汉语语言功能定位、汉语失语症患者词类损伤、汉语句法障碍、汉语语音损伤、汉语失语症量表的编制等方面进行综述。
1 汉语语言功能定位的研究
印欧语系的研究者们(Menon等,2001;Kuest等,2002;Poeppel David等,2004)认为:语言的优势半球为左侧大脑,颞叶、顶叶和额叶为经典语言中枢[2],细分为:①听感觉性语言中枢:听理解主要激活左颞叶(上回、中回、下回)、左楔叶、左额前区、左梭状回和左舌回;听分析主要激活左颞上回与中回;②阅读中枢:阅读激活左侧大脑皮质,包括颞枕交界下部、额中回、梭状回、颞中回、补充运动区,其中梭状回与词形处理有关,颞中回和额中回与语法、词汇记忆和语言组织有关;③运动性语言中枢:左额下区和颞上区是言语产出的处理中枢,且相关的皮质涉及两侧半球;④书写中枢:听写主要激活区为左顶上叶、左顶下叶的背面和左顶上叶的连接处,其他激活区还有左运动前区皮质,感觉运动区皮质和补充运动区。
而对汉语失语者大脑分区的研究发现,失语症类型与经典语言中枢并不完全相符,非语言区病变也可引起失语;但病变位于经典语言中枢的患者,其失语程度更为严重(张玉梅等,2005)。从语义加工入手,韩在柱等[3]发现左侧额枕下束、左侧丘脑前部放射和左侧钩束与汉语语义加工有着因果关系,为语义网络的解剖框架提供了证据。Zhao等[4]提出左前颞叶和双侧前扣带回皮层为语义中枢区域,进一步勾勒出大脑的汉语语义网络。从语法视角入手,毛善平等(2005)发现左额-颞叶神经网络系统损伤与汉语语法缺失密切相关,而右额-颞叶神经网络参与句法的辅助加工,提出完整的汉语语法认知需要左右两半球的协同合作。
对由皮质下结构(包括纹状体内囊区、丘脑、脑室周围白质及放射区等)损害导致的失语症研究逐渐兴起。毛善平、陈卓铭等(2002)将皮层下失语分为基底节性失语和丘脑性失语,其中,基底节性失语多表现为轻至中度口语流畅性障碍,词与词之间缺乏连贯性,说话费力、缓慢,韵律异常,构音障碍,但此类患者的语言功能恢复较快;而丘脑性失语则表现为低音调,找词困难,中度构音障碍,语流量减少,少数患者可出现错语及新语。大量临床病例报告就丘脑性失语的语言特征基本达成一致,但发病机制尚无定论[5],张玉梅等[6]发现除皮质外,多种白质纤维束和皮质下结构也参与其中,提出语言功能区皮质的低代谢、低灌注及纤维束的减少、移位和变形可能是皮质下失语症的发病机制;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症患者中,因此,孙学进等(2005)也认为,语言中枢的纤维量减少,尤其是前后语言区之间的弓状纤维束减少,阻碍了语言功能的完成。
失写症同样与基底节和丘脑损伤密切相关。高素荣[1]提出汉语书写障碍表现为构字障碍和字词错写,病灶集中在大脑后部。金梅等(2004)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语句篇章层级书写障碍,明确提出基底节神经节损害可导致汉语失写症,其发病机制有低灌注机制、整合中枢、环路受损、字形在脑内结构的记忆提取受损等可能性。
2 汉语失语症患者词类损伤的研究
2.1大脑词库 对大脑词库(mental lexicon)的研究,就是对词汇在大脑中的储存和提取方式的研究。崔刚(1994)首先提出:①与拼音文字一致,汉语词汇同样以整词的形式储存于大脑词库中;②汉语词汇的上下义关系相较于并列关系更为强烈;③汉语实词中,形容词和副词在言语障碍中更易丧失;④相似读音和同一语义场的词汇有可能储存在一起。周晓林等(1999)认为阅读时,汉字的词义激活主要是从形到义的直接加工,语音的中介作用有限。而杨亦鸣等(2000)否认了这种形义结合较牢固、形音结合较脆弱的结论,提出了形音性、形义性、形音义性三种失读的情况,声母、韵母或音调相同的词汇间联系更紧密,其中起首声母在词汇提取时的作用尤为重要;并否定了崔刚(1994)的部分结论,认为汉语的语义场储存才是词汇的重要储存方式,且词汇间的并列关系强于上下位关系。
2.2名动词分离 名动词分离即大脑在产出名词和动词时表现出不同的认知加工机制。Bates Elizabeth等(1991)发现Broca失语者和Wernicke失语者在词类理解上无差异,但图形命名时,Broca失语者均表现为动词特异性损伤,而7例Wernicke失语症患者中有5例表现为名词特异性损伤,如:Broca失语者对动名复合词(如,滑雪)亚成分中的名词(雪)比动词(滑)的产生能力好,而Wernicke失语者恰好相反。然而,周晓林等(1993)对Bates的实验材料分析发现,其中的大多数语料属于短语,只有少数为复合词,因此,对亚词汇水平上的名动分离现象提出了质疑。汪洁(1993)对失语症的词汇难度进行排序,发现最易理解的是物品名词,其次是动词、颜色名词和数词,最难理解的是拼音;而产出的表现不同,最容易的是动词,其次是数词、颜色名词和物品名词,最难的是拼音。王小丽等[7]发现一例仅颞叶受损患者句法保留较好,但词汇受损严重,具体表现为理解较好,但产出时存在名动分离的现象,且呈现名词特异性损伤。以上研究均证实在词汇的提取上,动词和名词确实存在显著差异。
2.3语义语法之争 深究名动分离的原因,争论的焦点在于是语义还是语法。杨亦鸣等(2002)认为语义标准可作为实词和虚词的划分依据,但不能作为整个汉语词类的划界标准,而名动分类以语法为划分标准不仅有神经机制的生理基础,且对语言学研究更有价值。柏晓利等(2004)发现2例出现大量语义错误的患者,其错误产生的原因却不同,患者一为语义后的输出系统受损,患者二为中心语义系统受损,因此倾向名动分离以语义为标准。而毛善平等(2005、2006)研究发现失语者大多能完成对实质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的操作,但对功能词(介词、连词、数词等)表现出缺失或者位置错放等,认为动词表达受损点为语法表征,且以语法为划分标准更为妥当。
2.4动词的复杂性 随着对名动分离到底是语义还是语法的争论愈演愈烈,动词的复杂性逐渐凸显。周统权等(2010)将动词的复杂性分为形态、范畴、语义和句法复杂性;在句法复杂性部分,尝试着用语迹删除假说、双重依存假说、结构凸显假说和句法树截断假说对失语现象进行解释。王洪磊[8]则对Broca失语者对一价、二价及三价动词的加工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动词价位越多,受损程度越重的结论,并验证了Broca区是加工动词配价的神经基础;同时还提到汉语中存在模棱两可的动词配价情况。
与语言学和心理学研究者不同,临床工作者更关注研究的临床应用价值,比如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s)、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对失语症患者进行检查,以期这些技术可以辅助失语症的诊断和治疗[9~11]。再比如,陈珍珍等[12]尝试依照国际失语症语料库的标准,构建命名性失语的汉语普通话语料库,以期为汉语失语者的动态语言分析提供工具,为其临床康复治疗提供线索。
3 汉语句法障碍的研究
句法为语言系统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崔刚[13]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梳理出五种可用于解释句法障碍的假说:①语迹删除假说:失语者的语迹被删除,导致名词短语或疑问词失去了题元角色的信息,或患者无法按照正常的语言处理给名词短语分配题元角色;②双重依赖假说:由于语迹和它的先行词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被破坏,导致患者无法分清名词短语应和哪一个同标;③映射假说:就“患者不能理解一些句子,却能对句子是否合乎语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一临床表现提供了两种解释,一是,失语者的理解障碍与句法本身无直接关系,而是由于表层结构中的句法表征与深层结构中的语义映射缺失,导致患者不能顺利地进行题元角色的分配;另一种是,在理解句子时需要同时处理句法和语义两个任务,相较单做语法判断占用了更多的认知资源,致使难度增加。基于认知资源受限的这一解释,进一步发展出④资源受限假说;Kolk等(2003)将注意力集中要时间这一资源上,提出了⑤时间匹配假说:句子表征的建立需要每一个要素都被激活并达到某个水平,若各个要素的激活时间无法匹配,则不能完成句子的建立。
3.1主被动句式障碍 主被动句式首先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杨亦鸣等(1997)发现汉语句法结构在听、阅读和生成这三种路径中存取加工是相对独立的,与词汇信息在大脑结构中的储存是相对分离的,提出主、被动句法结构在大脑中的“平行式储取机制”。崔刚(1999)发现失语者的句子结构的使用偏简单,以陈述句、肯定句和主动句为主。毛善平等(2008)发现汉语语法缺失患者存在较严重的“把”字句和“被”字句的理解障碍,认为其产生机制可能与语迹删除和工作记忆障碍有关。
3.2关系从句加工障碍 除了主被动句式,近十年对汉语关系从句加工的研究同样热门。围绕印欧语系研究者提出的“主语关系从句加工具有优先性”这一假说,周统权等(2010)发现汉语中主语关系从句的理解正确率低于宾语关系从句,否定了印欧语系的“主语从句加工优势论”。自此,不少学者采用ERPs对以汉语为母语的健康受试者进行实验,同样证明了汉语独特的“宾语关系从句加工优势论”[14,15]。但刘涛等[16]则发现在控制了从句动词的生命性与指称性后,汉语的主语从句依旧比宾语从句更易加工,继而对“汉语宾语从句加工优势论”提出了质疑。
4 汉语语音障碍的研究
4.1声调障碍 与印欧语系不同,汉语失语症有着特定的声调障碍。崔刚(1999)发现在声调障碍上,大脑损伤最易影响上声声调。而汪洁(2004)发现左顶叶、左顶深部梗死失语者双音节和三音节声调辨别错误较多, 认为声调感知的损害可以独立于音素而单独出现,且汉语一声调不需要加工,并初步认定左顶叶及左顶深部参与声调感知与产生的加工。
4.2语音的理解-产出机制 熊汉忠等(2004)从心理词典系统结构模型(语音输入词典、字形输入词典、语义系统、语音输出词典及字形输出词典)的角度,认为传导性失语者的语音错误并不是源于语音输出词典损伤,而是由词典后加工环节损伤导致的;而韩在柱等[17]报道了一例能理解所给材料(词-图、句-图匹配表现正常)但有大量语音和语义错误的患者,对阅读理解的语音中介假说(先激活词汇语音,再通达其语义)提出质疑,为探寻无需语音为中介的阅读理解机制提供了证据。
5 汉语失语症量表的研究
印欧语系的失语症量表主要有三个:波士顿失语症诊断量表(Boston diagnostic aphasia examination, BDAE)、波士顿命名测试(Boston naming test, BNT),西方失语症成套测验(Western aphasia battery, WAB),其中WAB的译版在我国临床和科研中使用最广泛。
与拼音文字不同,汉语的特点是一字能集形、音、义于一身,有严格的词序约束,但没有严格的词形变化。国内现已经公开发表并投入使用的汉语失语症评估量表有四个:①《汉语失语症成套测验》(aphasia battery in Chinese,ABC):借鉴WAB和BDAE,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改编,于1988年开始使用,失语部分的检查主要由谈话、理解、复述、命名、阅读和书写四个部分组成,而结构与视空间、运用和计算构成其他认知功能检查[1];优势在于计分和操作标准化,便于诊断和分类。就汉语失语症的特点而言,主要体现在阅读部分的“听字-辨认”(对形近字进行辨认)和“选词填空”(加入孙悟空等中国文化特有元素)。②《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汉语标准失语症检查量表》(China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center aphasia examination, CRRCAE):参考日本的《标准失语症检查量表》(SLTA),根据我国文化习惯设计,主要包括听理解、复述、表达、漫画说明、名词列举、自发谈话等测试项目(李胜利等,2000);除标准计分外,检查表还要求记录病人的“言语症状”,补充了标准化的量表缺失的主观细节描述。这两种量表是临床工作者基于西方失语症量表,结合我国国情和临床经验进行的编译,在词汇选取上存在着地域性(如,您家住在通县/延庆,对吗?)和时效性(如,皮尺)的差异,在句子翻译时存在歧义(如,木头在水里会沉,对吗?),图片使用不符合汉语使用者的生活场景等。③《汉语语法量表》(Chinese agrammatism battery,CAB):设计者们意识到了之前量表中缺失的语言问题,与语言学研究者一起合作,引用《西方国家语法量表》的框架和理论,根据汉语的文字特点和语法规则编写,由词类、语序、语用、句子-图画匹配和语言符号操作五个测试项组成,着重检查失语者的语法缺损(毛善平等:2002);但依旧忽略了名词、动词的理解产出及汉语句法的测验。④《中国失语症语言评估量表》(Chinese aphasia language battery,CALB):在《西北命名成套测验》(NNB)和《西北动词语句成套测验》(NAVS)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汉语语音、词汇、句法和语义开发,包括命名分量表和动词语句分量表。其中命名分量表包括听觉辨识、声调理解、听觉词汇判断、对证命名、听觉理解、语义关联、假词复述和真词复述八个分测试,而动词语句分量表包括动词命名、动词理解、论元结构产出、语句启动产出和语句理解五个分测试[18]。CALB是临床工作者、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者根据语言认知神经心理加工理论编制的,加入了之前量表从未出现过的声调理解和动词题元结构,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动词题元结构本身是一个语言学概念,对于需要使用量表的临床工作者来说,难以在短时间内掌握,更不用说测查病人时需要迅速且准确地记录;其二,量表中使用了我国患者不熟悉甚至忌讳的图片和词汇(如:祈祷、棺材),易让患者在测查过程中掺杂负面情绪,从而影响测查效果。
6 言语障碍的治疗
目前国内针对言语障碍的康复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基础训练(呼吸、发音、共鸣)和针对性训练(构音和韵律),再辅以传统中医康复疗法、物理治疗和心理治疗[19]。其中,呼吸训练、发声训练和构音训练以口部器官的主动运动为治疗措施,共鸣训练则对器官施行被动治疗,仅构音音位训练和重音训练是基于汉语普通话体系进行的。由此可见,对汉语失语者的康复治疗依旧以印欧语系失语者的治疗手段为主,鲜有针对汉语语言障碍特点的康复治疗措施。
7 小结
综上所述,汉语失语症研究者的关注领域主要集中在汉语语言功能定位、汉语失语症患者词类损伤、句法障碍、语音障碍及汉语失语症量表的编制这五个方面,与印欧语系的失语症研究相比,主要研究领域基本一致,但依旧存在以下不足:①研究团队结构相对单一,没有真正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取长补短;②对汉语失语症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临床症状的描述、分类及其病灶部位关系上[1],少有在系统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实证研究;③以个案或小样本研究为主,患者追踪时间短,鲜有更为深入的系统研究;④失语症检查量表以编译为主,本土化程度不够。
随着交叉学科的兴起,有关汉语失语症的跨学科研究已经将神经科学、影像学、康复医学、心理学与语言学结合在了一起,使临床研究有了更丰富的理论支持,语言学的研究也从理论走向了实践。后续研究需要结合临床工作者、心理学语言学研究者、失语症患者的实际需求,用科学的实验方法,验证和完善语言学的理论和假说,推动多学科发展,才能让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失语症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