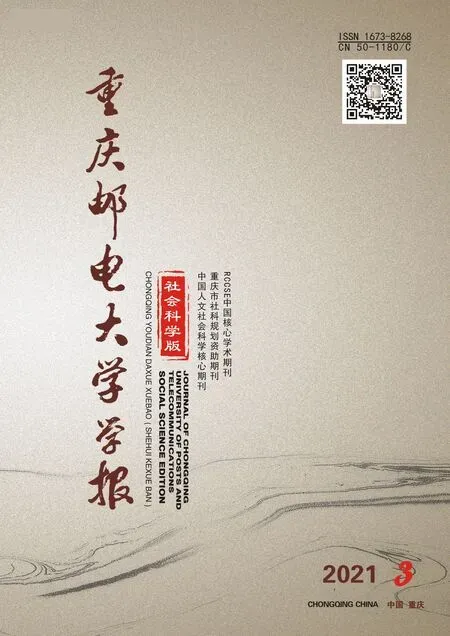戏剧性与情节性:电视剧审美接受的二元思辨
2021-12-04李轩
李 轩
(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北京 100024)
一出好戏的诞生,须达至“有戏”之意境,有立体可感的人物性格、激烈碰撞的矛盾冲突、意味深长的情境烘托等戏剧性场面,给人以净化心灵的审美冲击;也须成其“有看点”之奥妙,有合理可信的行动组织、细腻描绘的事件展演以及趣味性、悬念感等多重效果构成的情节性场景,给人以持续吸引的审美愉悦。过往相关的学术研究中,一方是就戏剧谈戏剧性,另一方是就情节谈情节性,因戏剧作为艺术形式和情节作为叙事单位这一概念由来上的不同,戏剧性与情节性常被分而论之。其实,戏剧性并不为戏剧所独有,情节性也不可完全与情节混同,叙事艺术的审美接受中二者本就互融互补、对立统一,因而不能一概割裂而谈。伴随着当代艺术形式化潮流的纷涌,不少艺术样式对戏剧性与情节性的体现已不如过往,尤其是在日趋先锋化和实验化的戏剧叙事和电影叙事中,戏剧性与情节性的“重量”愈发微薄。较之戏剧、电影,电视剧需要更“足量”的情节性场景和戏剧性场面,以维持内容体量、保持叙事弹性、体现作品精神主题、强化表现感染力,因而电视剧的戏剧性与情节性自然更具研究探讨价值。那么,戏剧性与情节性当如何界定、电视剧的戏剧性与情节性的概念及其关系为何、戏剧性与情节性间的失位失当是怎样影响电视剧的价值表达、当前国产剧内容生产中的相关现象又当如何解读?为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本文在对叙事艺术中戏剧性与情节性做简要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电视剧艺术的发生语境,探析电视剧戏剧性与情节性间强弱与优劣的辩证关系,分析二者对电视剧种种美学症候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与之对应的重塑意识,进而以此为理论基点解读当前国产剧叙事的“情节化转向”。
一、“审美接受”:叙事艺术的戏剧性与情节性
叙事艺术作品经典性的产生,离不开戏剧性与情节性的共同作用。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为例,唐僧师徒四人在西天取经过程中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劫难情境产生意味着新叙事单元形成,每一个叙事单元均须由特定情节线索和事件转折组合推动,《西游记》的引人入胜即来自险象环生又逢凶化吉的情节性体验。通过人物性格及冲突矛盾的塑造刻画,《西游记》令人难忘且最为人称道的戏剧性场面当属“大闹天宫”和“三打白骨精”。“大闹天宫”中,齐天大圣孙悟空与天庭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的冲突对抗产生出精彩绝伦的擒纵斗法情节,同时孙悟空桀骜不驯、刚直不屈的性格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三打白骨精”中,白骨精化身一家三口魅惑离间的情节惊异效果十足,由此导致大徒弟孙悟空和师傅唐玄奘的分道扬镳让人不免惋惜。相较于《西游记》其他章回,情节性与戏剧性俱佳的“大闹天宫”和“三打白骨精”堪称是传世经典中的璀璨明珠,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唯独这两个章回能在后世文艺改编中更受青睐。
(一)瞬息外现的戏剧性
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先民时期还是当下,戏剧性故事总是绵延不绝地发生。日常生活中戏剧性一词,便常被用以形容出乎意料的转折和饱含深意的事件。之于叙事艺术,凝练戏剧性相当关键,如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遭命运捉弄不幸陷入杀父娶母的人伦绝境,上演人与命运对抗的无奈悲剧;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因性格自大拒绝出战导致希腊联军惨败和好友身亡,暗显出英雄性格的因果注脚。回望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戏剧性诸成说更是各有所向,然而,其中关键还是在于把握戏剧性的“人性价值和审美内涵”[1],戏剧性“不是光在戏剧中得到体现,它还在所有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艺术门类中比如电影和诗歌文本中出现”[2],戏剧性体验也并非受叙事媒介严格约束。
正如萨塞在《戏剧美学初探》中所言,不管是什么样的戏剧作品,写出来总是为了给聚集成观众的一些人看的;这就是它的本质,这就是它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3]。威廉·阿契尔亦有与之相近的观点,他在《剧作法》中提出,能够使聚集在剧场中的普通观众感到兴趣就是“戏剧性”的[4]。而在《论戏剧情节》中,古斯塔夫·弗莱塔克写道:“所谓戏剧性,就是那些强烈的、凝结成意志和行动的内心活动,那些由一种行动所激起的内心活动。”[5]关于这种内心活动,乔治·贝克在《戏剧技巧》中认为:“外部动作或者内心活动,其本身并非‘戏剧性’的。它们能否成为戏剧性的,必须看它们是否能自然地激动观众的感情,或者通过作者的处理而达到这样的效果。”[6]由此可见,戏剧性的生成关键即在于受众审美感知,其真正达成须由体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戏剧动作激起受众的审美心理活动。
对于戏剧性的本质,黑格尔的认识及思考或许更为切近,他提出:“我们眼前看到的是一些个别具体化为生动的人物性格和富于冲突情境的抽象目的,这些目的在显示自己和实现自己的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制约——这一切都要在瞬息间陆续地外现出来。”[7]可以发现,作为一种审美特质的戏剧性,其本质是通过创造具有“瞬息性”特点的不同审美形态与受众完成审美交流互动。这一“瞬息性”并非指艺术客体要在尽可能短的瞬息之间呈现冲突,而是艺术客体通过尽可能巧妙的设计令受众可以在观赏过程中于瞬息间捕捉到性格、冲突、矛盾、情境等内容的深层意指和象征意涵,在内爆式的叙事信息接受获取中形成情感共鸣和情绪共振,并在体会寻味“陆续地外现”过程中对此细加品读。
(二)渐次延展的情节性
在《论情节》中,冉欲达曾为情节正名道:“对情节曲折的戏剧、电影,以所谓的‘情节戏’予以否定或贬低是不公允的,艺术作品没有动人的情节很难塑造出真正动人的性格,真正好的作品无一不是以曲折动人的情节而征服了千百万读者和观众。”[8]一般情况下,情节堆砌会被认为是艺术性匮乏的表现,故对情节功用的普遍理解也易流于负向,而当情节尚不能获得应有认可时,更勿论情节性。此外,因情节性与情节在一般使用上较为接近,故而使得情节性往往隐而不彰,多被视作情节的功能加以讨论,较少得到重视。但事实上,在叙事艺术中,不仅情节的形式功能不容替代,情节性的审美意义亦不容忽视。
然欲辨识情节性,必先对情节有清楚认知。早在《诗学》之中,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情节”是悲剧中最重要的成分;组合精良的情节不应随便地起始和结尾,而是应该符合完整划一且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模仿的悲剧构成的要求[9]88;情节有简单和复杂之分,构思精良的情节必然是单线的且应该表现人物从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9]97,并由情节本身的构合引发恐惧和怜悯[9]105。而对于情节的判定,黑格尔则认为:“主体性格对情境的掌握以及它所发出的反应动作,通过这种掌握和反应动作,才达到差异对立面的斗争与消除(矛盾的解决)——这就是真正的动作或情节。”[10]结合古典理论和当前艺术实践来看,情节不是动作而是行动,是一段完整的、由始至终的行动,且人物是构成和推动情节发展的中心;行动由人物执行,人物的性格、关系及与情境间的矛盾冲突是行动发展的动机;消除矛盾、回归平衡秩序是人物行动的归宿,由人物的情境反应动作形成的系列行动将产生冲突矛盾的不平衡因素完全消除,是一段情节真正完成的标志。在此,可将情节简单定义为:以性格鲜明人物的行动为基础,由若干行动事件组成,为冲突矛盾、因果承继等多重因素推动,并总是处于“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发展演进中,最终通过矛盾克服实现情节整一。
情节是一项叙事功能单位,是故事结构的基础组成部分。情节性不完全同于情节,相较于表意功能,它代表着观赏体验的审美效果,非情节、反情节叙事之中亦可存有情节性。略加辨析后即可发现,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同情、恐惧、怜悯,还是黑格尔意义上对立面消除产生的快感,其所指已超出情节的功能范畴,这种由情节激发的审美效果正是情节性。作为一种审美特质的情节性,其本质是通过创造渐次延展的审美体验,提供快感享受、满足认知意识渴求。受限于情节进展的流程脉络,受众难以在短时间内一窥情节全貌,只能选择跟随情节走向,在情节的构合与完成中得到娱乐。叙事艺术的情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情节组成构造的特殊性,内部各具特色的新奇事件可激发观看欲望,外部各不相同的情节主题可创造差异化的观赏体验;二是情节发展的整一性,首尾呼应、事件衔接、节奏控制等要素是情节成立的关键;三是多情节的结构性,即情节与情节之间的框架联系,关乎故事整体的完善。
(三)诉诸审美、趋于二元
戏剧性,如同令人难忘的瞬间,充斥着象征意味且满含诗意;情节性,如同人所必经的成长历程,曲折发展且运动变化。戏剧性与情节性之所以能共存于不同的叙事艺术样式,是因为它们不是特定艺术的独门手法,而是具有情感调动力的审美特质。如朱光潜所言,审美范畴往往是成双对立而又可以混合或互转的[11]。瞬息外现的戏剧性与渐次延展的情节性,是叙事手法的艺术升华和受众审美期待的产生源泉,二者共同构成叙事艺术的核心审美范畴。同时,叙事艺术中的戏剧性与情节性也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二元关系结构。一方面,基于审美特性差异,戏剧性与情节性相互区别,戏剧性注重“瞬息性”,情节性注重“延展性”;另一方面,戏剧性场面多呈点状分布,须依托情节线索串联才能贯通;情节性活动多呈线状演进,须借助戏剧性张力再造新变。
二、“关系辩证”:电视剧的戏剧性与情节性
电视剧作品中的“名场面”,多是饱含戏剧性的。以电视剧《亮剑》为例,该剧最为经典的桥段当属第14集李云龙率部“打平安县城”,堪称是对谭霈生先生以人物性格为中心,通过戏剧动作、戏剧冲突、戏剧情境、戏剧悬念、戏剧场面以及结构的统一性来呈现戏剧性的观念[12]的完美诠释。在人物性格上,李云龙选择攻打县城的直观动机是救妻报仇,充分体现出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在戏剧动作上,当八路军兵临平安城下,日军在城门楼上挟持李云龙妻子秀芹威胁撤军,李云龙不惧威胁大声下令开炮,饱含张力的动作中暗示着其内心抉择的巨大苦痛;在戏剧冲突上,八路军与日军斗争的激化,渲染出一触即发的大战氛围;在戏剧情境上,抗战时期中日双方尖锐的民族矛盾被重点突出,符合历史语境;在戏剧悬念上,包括李云龙能否救出妻子,李云龙部能否取胜,以及八路军及友军部队能否阻敌增援;在戏剧场面上,以李云龙部为明场,其他战斗为暗场,穿插战役双方的增援阻击,侧面呈现出整个晋西北战局的剧烈波动。此外,这一段落中也不乏情节性,其中八路军独立团六连、县大队与县小队、孔捷部、丁伟部以及国军楚云飞部等队伍阻击日军的场面即为各具特色的情节,全部围绕着李云龙部行动展开,以烘托战斗气氛、强化表现力。通过戏剧性与情节性的协调搭配,《亮剑》将顽强不屈的抗战意志和民族精神予以了完美呈现。
(一)电视剧的戏剧性
一般审美感知上,电视剧的戏剧性与其他艺术形式的戏剧性虽同构同源,但受自身艺术特征和媒介特性影响,必然具有相区隔的“电视化特质”[13]。就戏剧而言,舞台上人物所处的时空环境相对固定,动作直观可见,其戏剧性呈现自有其内在规律;但对于电视剧来说,若没有蒙太奇、长镜头等镜头语言,仅是单纯使用固定镜头拍摄,用纪实手法重现戏剧,电视剧的戏剧性就不能成立。而且,电视剧艺术的叙事时空相对广阔,景别、构图、调度等镜头语言能更好地表现人物动作的关联意指,为戏剧性表现提供新可能。基于此,有学者将电视剧的戏剧性定义为“剧中人物在屏幕艺术情境中展开有机的动作或行动,导致各类矛盾冲突或产生新的情境,让整个过程富有悬念,吸引着观众洞察人物的性格特征与精神世界”[14]。受众对电视剧戏剧性的审美感知生成,则需由以人物动作为中心的戏剧化手法和以镜头语言为基础的视听化技巧共同作用。作为电视剧艺术的一般审美范畴,戏剧性在电视剧中主要由因果性、悲剧性、崇高性、讽刺性、批判性等审美感知形态体现,如因果性给人以揭示、悲剧性给人以净化、崇高性给人以庄严、讽刺性给人以反思、批判性给人以力量等。
(二)电视剧的情节性
电视剧展现给观众的是可视的或可听的行动,即由人物、环境及人物与环境互动而产生的情节。考虑到电视媒介的传接习性,以及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受众争夺,电视剧很自然地会以对情节的进一步重视作为应对措施[15]。电视剧长篇化的叙事“高容量”,需要大量情节参与内容的构织填充。作为电视剧艺术的一般审美范畴,情节性是电视剧通俗化和娱乐化的征候,在电视剧中主要表现为生活性、传奇性、悬疑性、对抗性等审美感知形态,如生活性细构时空环境、传奇性强化故事魅力、悬疑性创造精神吸引、对抗性突出动作效果等。受众对电视剧情节性的审美感知生成,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结构性,电视剧的主线情节须脉络清晰,支线情节须枝繁叶茂、多重构合,如在悬疑剧、警匪剧等情节性依赖较重的类型剧中,多情节间的关系互动所产生的意义和价值势必远超单一情节,严谨合理有逻辑的情节结构作用突出;二是整一性,即情节构造必须是独立完整的才能创造意义,电视剧情节刻画的弹性空间较大,可通过镜头组接进行表意,也可由倒叙、闪回、拼贴等叙事形式间接呈现,或短或长的情节被赋予各异的强度、密度、曲折度;三是特殊性,电视剧情节的构成要素极为丰富,无论是剧本、画面、音乐,还是服装、布景、道具,任何与情节叙事有关的细节元素均可通过艺术加工表达特殊意涵,使情节别出心裁、独具一格。
(三)强弱之分、优劣之别
电视剧的戏剧性与情节性,存在强弱、优劣的辩证关系,既指审美表现上的强弱之分,又指审美价值上的优劣之别。强与弱、优与劣,出于文本、成于受众。戏剧性强,其审美价值可以是优,也可能是劣;情节性弱,其审美价值可能是劣,也可以是优。
其一,戏剧性强、情节性强。此类电视剧的突出特征是具有丰富的戏剧性事件素材和体量庞大的情节支线,代表类型是历史正剧。通过对历史史实的艺术再造赋予作品厚重史诗感,借助群像人物和系列事件增添情节性效果。
其二,戏剧性强、情节性弱。此类电视剧篇幅多精炼简短,如单本剧、电视短剧、微型系列剧等。受限于篇幅短促,此类电视剧一般不会大量增添情节线,而是将重心放在矛盾冲突集中的重场戏和高潮点上,细加营构戏剧性。
其三,戏剧性弱、情节性强。此类电视剧以情节表现为主要叙事手段,如在系列剧中,每集一个新故事的特点,使其对新生事件及情节存在依赖。此外,悬疑剧、推理剧等以情节化为主要特征的类型剧中,随着其情节体系和类型程度的提升完善,情节性也会随之增强。
其四,戏剧性弱、情节性弱,此类电视剧多以艺术化、纪实化为特征,作品文艺气息浓厚,常采用非戏剧性和非情节性手法进行叙事。事实上,电视剧并非完全与先锋探索绝缘,通过实验性手法创作的电视剧虽接受门槛较高,但通常也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相较于由艺术客体本身呈现出的表现强弱,审美价值的优劣判断更多由审美主体决定。戏剧性优、情节性优和戏剧性劣、情节性劣,代表着电视剧审美的两极,一边是“神作”,另一边是“烂剧”。诚然,达到“神作”标准的电视剧作品虽是少数,可这些作品却具有永恒的魅力与价值;而“烂剧”则不同,属于数量没上限、质量没下限,因审美价值寥寥故也毋庸赘言。多数电视剧作品均存在大大小小的瑕疵和不足,故戏剧性劣、情节性优和戏剧性优、情节性劣这两种情况较为常见,而当二者中任何一方的审美塑造出现匮乏空洞,即使另一方塑造得再完美,也注定是缺失的,整体艺术价值将大打折扣,意味着整部剧的失败。“神作”固然不能强求,电视剧生产创作却必须以戏剧性与情节性的优质呈现为目的,通过二者和谐稳定的良性关系构建,保证电视剧的内容质量和艺术基准。
三、“问题阐释”:电视剧内容生产的美学症候及意识重构
电视剧的审美价值,无非是娱一时之乐,还是娱一世之乐。电视剧中,戏剧性与情节性中的任意一方所能创造的都仅是一时之乐,如由情节性主导的电视剧在表现力、审美效果、市场盈利等方面均具优势,可惜经典性不足,多数作品仅是看第一遍时还行,看第二遍便乏善可陈,缺乏像《雍正王朝》《亮剑》《闯关东》等作品百看不厌的内涵与深度;另一方面,娱乐表达纵然路径多元却也有基本的底线和规律依循,对戏剧性的戏仿解构虽是无伤大雅的,但若一味嘲弄、不思建设,所迎来的必将是虚无不毛。因而,多数电视剧作品的品质失守、口碑崩坏,主因还是出自戏剧性与情节性的构造不足,或是戏剧性缺失,抑或是情节性匮乏,以及二者关系的失衡。
(一)从伪劣失实到优质互娱
伪劣失实问题,即故事内容的粗制滥造和失实构造,国产剧领域中的曾持续多年的“雷剧”现象即是此问题的典型反映。“雷剧”通过造型、台词、动作等方面的夸张失实效果,试图以逆向审丑方式点燃收视爆点,可实际带来的却是低质粗浅的视听效果和流俗媚俗的感官体验。目前而言,因创作意识失格和市场规则制约,粗制滥造的电视剧难以禁绝,导致电视剧行业整体口碑下滑,优质作品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伪劣失实般的创作虽然“短平快”,却无疑是在饮鸩止渴。内在来看,电视剧的伪劣失实问题主要体现在戏剧性与情节性层面。戏剧性上,此类问题剧是典型的外强中空、“雷声大雨点小”,在画面、台词、配乐等视听元素上极尽夸张之能事,外在表现上看似冲突激烈,实际却无一丝一毫效果,带来更深的受众审美心理落差,仅可视作“伪戏剧性”。情节性上,此类问题剧是“形式大于内容”,画蛇添足地谋求情节的“特异性”,尽管情节看似紧凑,实则节奏拖沓、不成体系,这些冗杂繁复的情节不仅毫无情节性可言,而且会引来尴尬、气愤、不明所以等反向观感,仅可视作“伪情节性”。
优质互娱意识,是指通过戏剧性与情节性的优质呈现创造深层次娱乐体验。在戏剧性层面,要放弃粗劣拙技,拆解拼贴式低俗娱乐多是无意义的消解,能一时流行却无法经典永存。当然,这并非指要放弃通俗化表达,一味追求高山流水,而是要用更精深的艺术技巧营构戏剧性场面,构建作品与受众的接受互动,激发受众审美心理活动。在情节性层面,易懂易感知是其优势,可这不意味着内容创作的肤浅化,而是保持叙事活力的剧作方法和娱乐化表达的必要途径。以奇幻剧为例,此类剧集多以异世大陆为背景,通常会面临故事失实的风险,因而一些作品会有意识地通过情节体现世界观设定,以细腻贴切的情节性支撑虚构域情境感知,激发物理质感,并以戏剧性事件强化精神情感勾连,以此实现整体的优质互娱。
(二)从断裂失衡到动态互融
断裂失衡问题,一方面是电视剧戏剧性与情节性的呈现与现实社会脱节,另一方面是指戏剧性与情节性固有联系的断裂和比例权重的失衡。当故事内容缺乏合理逻辑支撑,戏剧性与情节性将无从谈起,除荒谬外无其他,更勿论审美关照,国产剧领域中的“悬浮剧”即是此类问题的代表。“悬浮”,即飘在空中、不接地气,在本应表现社会现实状况和群众日常生活的现实题材剧中尤为常见,如在某些国产行业剧或职场剧中,因创作者对于特定职业工作方式的专业性塑造不足,故事人物的工作状态就会悖于实际,实难让人共情,明显违背电视剧艺术的现实性规律。此外,如果作品一味地迎合大众的低级的无意识欲望及趣味,亦会走向“伪现实主义”[16]。关系断裂方面,戏剧性与情节性相互割裂、难以衔接,矛盾冲突或情节表现两相互斥,作品如同“一潭死水”没有活性,审美感知方面存在不容跨越的鸿沟;关系失衡方面,戏剧性与情节性之间不均衡、不协调,过重过轻的两极化态势显著,缺乏串联过渡,滋生莫名所以的观感。此外,断裂失衡状态还可能瓦解戏剧性与情节性的点线结构关系,导致由点线及面的整体美感不复存在,阻碍受众移情认同。
动态互融意识,是指通过戏剧性与情节性的动态更新,回归互融互补状态。以国产情景喜剧为例,此类型剧在我国发展已近三十余年,虽留下一定数量的精品却也逐渐淹没于时间长河,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一般国产情景喜剧总是固守情节性一端,疏于戏剧性表现,尽管每一集都有新故事,但流水账似的日常生活故事实在难以讨喜。断裂状态下,电视剧戏剧性与情节性的故事效果往往光怪陆离、不知所云,审美主客体之间的接受鸿沟会持续加深,因此须强化戏剧性与情节性的有机融合意识,首先弥补叙事层面断裂,动态更新内容表现要素,进而缝合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裂隙,拓宽受众的审美感知向度。失衡状态下,戏剧性与情节性的动态结构体所能创造的并非两端互补共进的审美强化效果,而是单极垄断效应,完全隔绝另一极审美作用发生的可能。为规避此类问题,需要针对性地完成戏剧性与情节性的互补互通,在电视剧生产的前期、中期、后期均有相关把控,最终实现由此及彼的互鉴关照和价值递增。
(三)从同质失趣到多维互生
同质失趣问题,即由内容同质化导致故事丧失审美趣味和文化魅力,近年来国产的另类神剧便是此问题的代表。当一部剧第一次成功运用某一情节模式或戏剧手法时是创新、经典的,但当此模式出现后仍千百遍、不厌其烦地使用,就是套路化、流俗化的。电视剧市场中,一部热播剧往往可以带起一支题材流派,掀起同类作品制作潮流,因而容易滋生同质化问题。其实,若能把握艺术创作的“变与不变”规律,在共性上同质,于灵活处新变,是可以将同质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可惜知易行难。电视剧的同质失趣,可见于内容的各方面,从人物形象到剧情发展,每一处情节及冲突的雷同都是难以遮掩的。叙事层面拼贴复制和表意元素重复出现,会消耗故事内在的原创价值,令其所关涉的戏剧性或情节性受到波及,降低作品内在趣味性,影响审美活动发生。简而言之,内容同质的直接结果便是美感同质。
多维互生意识,是指通过戏剧性与情节性表现的多维向度,促进审美意义互生。电视剧同质失趣问题的主因是过度重复,其针对性应对策略即增强内容原创性。故事原创,讲求的是旧瓶装新酒,而非换汤不换药。电视剧领域中,某些创作者为避免同质化会选择走捷径式的刻意求新,为此就产生了诸如“抗日神剧”中武侠高手、逆天暗器、耍帅装酷、时空穿越等不合常理的奇观元素及恶俗桥段,其初衷虽是为创造效果,但却违背了戏剧性与情节性的产生规律,与其美学范畴不相兼容。电视剧戏剧性与情节性的多维互生,须坚持创新原则,积极开拓美学边界,从剧作技巧、人物表演、镜头画面、配音配乐、叙事剪辑等多重维度强化叙事文本的审美意涵,紧紧围绕核心人物展开创作,升华作品整体美感。
四、“现象读解”:当前国产剧叙事的“情节化转向”
2018年暑期档,电视剧《延禧攻略》热播一时。该剧讲述了魏家次女魏璎珞为替姐姐复仇选择进宫,在后宫中历经艰险,最终完成复仇并成为皇后的故事。不同于一般宫斗剧中后宫女子“白莲花”式的惺惺作态,魏璎珞更像是一朵“黑莲花”,她敢于反击、绝不吃亏,面对接连不断的生存危机,均凭借自身的机智勇敢化险为夷。“攻略”,原为攻城略地的简写,后衍义为游戏过程中的问题解决方案,指玩家在关卡设定中需通过特定的行为操作或方法指南完成通关。《延禧攻略》即魏璎珞的后宫生存攻略,该剧正是放弃了传统宫斗剧在人物、矛盾、情境等方面的复杂铺陈,转而采用游戏攻略式的副本结构法则,选择在新事件开端简略交代背景,快速抛出人物行动目标,任务完成后随即切换另一任务,循环往复。当人物战胜和消除对立客体的一系列行动成为电视剧审美效果的主要来源时,情节化即可视作其关键的叙事特征,这一特征在近年来的国产剧创作中日渐流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可惜的是,当前国产剧叙事的“情节化转向”,虽然情节性得到高扬,但却更多是以戏剧性的失位为代价,即外化为“戏剧性耗散”与“情节性熵增”。
(一)“戏剧性耗散”的成因
当前国产剧的“戏剧性耗散”,并非指戏剧性的消失,而是指戏剧性审美价值的大幅缺失。当作品的戏剧性表现呈“外强中干”“劣多于优”时,纵使行业整体的内容供给能力再充足,也难以抵御深描不足带来的根基失稳。其成因主要出自四个方面:一是演员表演,电视剧戏剧性产生的核心要素是人物,而人物塑造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演员表演,但近年来国产电视剧领域内“小鲜肉”“流量明星”等演技普遍低于及格线的演员当道横行,“老戏骨”等经验丰富、演技精良的演员群体则频频遇冷,当表演不足以支撑人物形象时,自然就会导致戏剧性弱化;二是剧情构造,此前国产剧领域的“雷剧”“悬浮剧”以及另类“神剧”现象即是明证,“狗血”“套路”“媚俗”等剧情设置问题,明显影响着国产剧的戏剧性审美体验;三是视听呈现,电视剧的戏剧性需要由画面、声音、造型等视听艺术手段的融合予以呈现,而在某些国产剧中,环绕、升格、降格等镜头的滥用比比皆是,花式配乐、人物BGM(背景音乐)等音乐效果密布杂乱,夸张、多余的视听表现直接影响着作品的戏剧性呈现,流于俗套、为人诟病;四是市场环境,在当前国产剧生产和收视市场中,作品价值的衡量标准还是以作品的预期收视和可能回报为中心,若利润获取相比无几,市场自然倾向选择周期短、见效快的情节化、娱乐化路线。
(二)“情节性熵增”的成因
当前国产剧的“情节性熵增”,表征为叙事段落内情节数量占比的增加、情节性程度的不断递增以及情节性效果的大幅提升。其成因主要出自三个方面:一是长篇化,国产剧的长篇化趋势属主导因素,目前国产剧平均集数已近40集,一些大剧形成60~80集的内容体量已是常态,叙事情节的数量需求也促进着情节性的提升,如《军师联盟》《庆余年》等剧集即是如此,但由此趋势引发的内容“注水”问题亟需重视;二是类型化,国产剧的类型化路线属辅助因素,特定情节元素集群是类型风格的必要条件,类型化程度与情节完善度成正比,如武侠剧需要有比武打斗、仙侠剧需要有修功练法等情节,而情节化叙事的高强度表现和高密度衔接,也有利于受众情节性体验的增强;三是网感化,国产剧的网感化走向属刺激因素,由网感化带动的内容情节性暗含着主体欲望幻想的意向性满足,以《回到明朝当王爷之杨凌传》为例,该剧的故事发展与原著小说的情节主线近似,主人公杨凌从普通秀才到异姓王爷的成长过程无比顺遂,上至朝堂、下至战场均无往不利,打怪升级般的情节模式虽提供出密集“爽感”,但不合常理、不合逻辑的因素也由之放大,因此该剧情节性虽强但审美价值却有所欠缺。
(三)戏剧性与情节性的关系重构
电视剧的戏剧性与情节性具有动态平衡的耦合关系,当其中一方有所疏漏乏匮时,即便另一方被呈现得非常完美,也注定无法掩盖作品整体审美价值的缺憾。短期内,由一方弱化留出的审美空洞会由另一方填充,即“戏剧性耗散”在一定程度上会助推“情节性熵增”。如演员表演上,以情节性为主导的国产剧对于演员演技的依赖度较低,人物只需要做出符合情节发展逻辑的行为动作,即可创造情节性效果;剧情构造上,情节性相对容易出新,不会重复“俄狄浦斯”“哈姆雷特”“雷雨”等千剧一面的戏剧性套路,可以用“新颖、奇怪、特别”的“新奇特”手法博取关注;视听呈现上,对于情节性手法要求相对简易,无需精致的画面和配乐,成片难度较低;市场环境上,《白夜追凶》《长安十二时辰》《隐秘的角落》等以情节性见长的国产剧集已受到市场认可和大众欢迎。客观而言,“情节性熵增”并非国产剧娱乐化发展的恶果,而是其在一段时间内的主导审美风格,是剧作观念、受众审美、市场选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阶段体现。然而,从长远角度看,国产剧的“情节性熵增”却是弊大于利的,如果内容生产一味地向单方倾斜,那么整体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必将无法实现有机统一。因此,国产剧优质生产的进一步实现,必须重视创作层面戏剧性与情节性的关系重构。
五、结 语
戏剧性与情节性的品质呈现和动态平衡,是电视剧艺术叙事精进的必经之途。一方面,通过经典叙事手段与现代视听方法的结合,以人物命运或际遇为主线的深描勾画,于各类冲突场面中持续激发戏剧性;另一方面,通过对人物传记式、视点化的表现,展示人物的个体行动、组合行动和交织行动,构织细密的情节网络,用丰富的情节演绎强化情节性。而对电视剧戏剧性与情节性的作用及关系的归纳、思辨、阐释,既可为电视剧艺术研究增添新的观察视角,也可为电视剧创作实践提供方向参照。未来国产剧的发展,可从戏剧性与情节性的角度出发,“采新规、用新策、走新路”。“采新规”,即依托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行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制度规划,如2020年2月6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生产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下发,通知中强调要加强源头引导、强化制作备案管理、反对内容“注水”、规范制作成本配置等,意在转变当前的剧集生产观念、压缩内容“水分”、规范演艺市场,对于重塑国产剧创作生态意义重大。“用新策”,即以“抛弃伪劣失实,走向优质互娱;避免断裂失衡,强调动态互融;警惕同质失趣,倡导多维互生”为中心策略展开。“走新路”,即在回归戏剧性与情节性并重的基础上,向戏剧和电影学习探索性的现代叙事手法和哲理性的文化辩证逻辑,吸取过往及当前热播剧集的创作经验,创作出具有新兴意蕴的故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