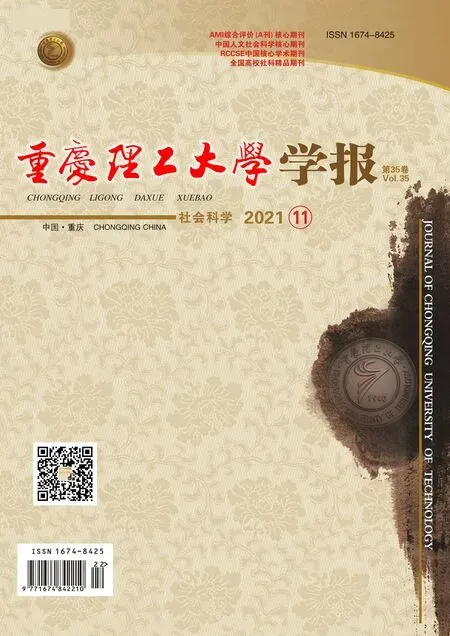西方真之理论的三次转向
2021-12-04邓彦昌
邓彦昌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真之理论的研究,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一直受到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关注,当前也是逻辑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哲学发展的不同时期,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们对“真”的定义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符合论、融贯论、实用主义真理观、冗余论、紧缩论等。在逻辑学里,“真”是判断逻辑推理有效性、可靠性和必然性的一个可靠依据。在整个西方哲学中,“真”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主题之一,正如帕斯卡·恩格尔(Pascal Engel)认为的一样:“真是一个核心的哲学概念,或许也是唯一的核心概念。许多其他重要的哲学概念或依赖于它或与它紧密联系……”[1]1不论“真”是不是第一哲学问题,但如果我们在哲学研究中,不能正确地掌握它,那么我们也不能正确地掌握其他的哲学核心概念。在逻辑学中,求真是逻辑学追求的终极目标,形式逻辑学家关心高技术的“真”的研究,而哲学家更关注与哲学相关的“真”的问题的研究。诸如,真是否有本质、真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关系问题,以及真的本质与意义理论是否关联等问题都是逻辑哲学所关注的问题。
一、本体论转向:真成为哲学约定的副产品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在哲学领域出现本体论转向,在真之理论领域也相应地出现了本体论转向。这一时期,真之理论研究的典型特点是真作为哲学约定的副产品。这一时期主要的真之理论类型主要有:真之原始主义、真之融贯论、真之符合论、真之实用论和真之冗余论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摩尔(Moore)和罗素(Russell)等人主张一种原始主义(Primitivism)真之理论,他们主张“真是命题基本的、不可定义的、不可还原的属性”[2]230,意义不能从所意谓的世界的真实事物中抽象出来,坚持意义是概念,真与假是命题最基本的属性。罗素跟随摩尔,主张命题及其组成部分是统一体的观点,认为真是命题一个不可分解的属性:真命题正好有它,假命题正好缺乏它[3]。有意思的是,20世纪晚期,真之同一论者主张真在于真之载体与真之制造者之间的同一性的观点同真之原始主义极为相似。但是,对于真之原始主义来说,对所有命题都给予同一性的解释是难以实现的,并且通过命题的诸要素得出的同一性对于命题的真假来说也是无区别的,因此不得不诉诸于真的进一步的属性。
20世纪早期,布兰夏尔德(Blanshard)、布拉德利(Bradley)和约阿希姆(Joachim)等人主张的真之融贯论是摩尔和罗素反对的真之理论形式。布拉德利把逻辑看作是对形而上学的不充分解决,他认为逻辑需要一种符合论。但是,他反对符合论,反对逻辑既能形式地又能充分地表现推理的观点。他自己对真的解释通过反对符合论而实现,他称这为“复制”理论。他的“复制”理论核心观点可以归结为:(1)我们只能复制现在的判断,关于过去和未来的判断不是复制的结果;(2)事实本身被复制作为我们假设的真,而事实本身却被看作是假理论的虚幻产物;(3)对于那些分离的、否定的和假设的判断我们不能把它们全部看作是假的,也不能把它们归属于符合于我们的真,也不能是普遍的、抽象的真;(4)反对“真外在于知识”和“知识外在于实在”这两个观点[4]107-111。但是,最终布拉德利受反实在论的影响而转向真之实用论,因为在他看来,真是不能超越现实的。布兰夏尔德和约阿希姆对真之融贯论几乎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赞同布拉德利“复制”理论的部分观点,认为真的本质在于融贯。并且他们也赞同布拉德利信念真正的融贯系统将与实在同一的观点,并且一个融贯的信念集必须不仅是一致的,而且要形成一个统一的解释系统,这明显带有奎因整体论的色彩。
20世纪初,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支持真之符合论的观点。罗素认为一个真判断所对应的复杂对象是这个理论呈现出来的相对独立于那个判断本身的东西。罗素在他的逻辑原子主义中认为,假判断和实际上真之符合论的可能性在于构成某个判断的实在对象和这个判断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某种不同。维特根斯坦批评了罗素的这个判断理论,但是,在《逻辑哲学论》中,他支持真之符合论,而对命题及真的解释又采取了区别于罗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直困扰罗素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的成分是名称,而不是罗素所说的对象,但是维特根斯坦承认对象是命题的真值承担者,并且承认命题是统一的。此外,维特根斯坦对真之制造事实有一个统一的融贯的解释,也就是说,他给出命题统一体本身一个融贯的解释。随着命题统一体问题的解决,我们能够给包含在真中的那种符合论本质一个确切的解释。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以皮尔士(Peirce)、杜威(Dewey)和詹姆士(James)为首的实用主义者坚持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格言:“考虑到那些有效的,可以料想是有实用意义的,我们认为对象是我们的概念所拥有的,那么我们这些有效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对象的概念的全部。”[5]258他们反对符合论者把真和假看作是外在于实在的东西,并且反对有确定的思想结构这种理论和实在可能是同一的理论。他们关于真之理论的观点是通过判断理论来实现的。皮尔士把实用主义的格言直接使用到真概念上,认为真是通过怀疑而无懈可击的真信念,探究目的的尽头是怀疑的终止,达到真信念集被证实。詹姆士和杜威则更倾向于把真等同于证实[6]。詹姆士把真概念看作是那些能被我们同化、能生效、能确证的东西,假命题则与之相反。
弗兰克·拉姆塞(Frank Ramsey)继承和发展了实用主义者关于“真”概念的观点,真被看出信念的一种有用属性,而真本身也成为一个有用的概念。此外,拉姆塞还赞同罗素“一个判断必须包括与许多对象多样地联系着的有思维的存在”的观点和维特根斯坦“A判断P确实具有‘P’表明‘P’的形式”的观点。但是,拉姆塞得出的结论却是一种成功的语义学——一个信念有P当且仅当P所包含的内容将导致我们基于那个信念与一些愿望相结合而履行的行动的成功[7]143。因此,拉姆塞认为,只要我们有了对判断的分析,那么我们就没有更深层次的真之问题需要解决的真之冗余论的观点。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看到:无论是真之原始主义的“真是命题一个不可分解的属性”,真之融贯论“真正的融贯系统将与实在同一”;还是真之符合论“给真之符合论本质一个确切的解释”,真之实用主义的“真等同于证实”的观点,很明显都带有浓厚的本体论色彩。
二、语言学转向:真之功用与意义
20世纪中期以后,伴随哲学领域的研究由本体论转向语言学,判断理论也逐渐发展成熟并可以规定相应的术语。当基于此的真之理论也能够被解释的时候,拉姆塞的冗余论把信念的语义问题与真之本质问题相分离开来。因此,真之理论的发展在“语言学转向”之后仍然坚持拉姆塞把信念的语义问题与真之本质问题相分离开来的基本方法论。虽然真之理论领域的语言学转向没有使真之理论究竟研究什么问题这一难题得到解决,但是真之理论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使我们对真之理论的焦点转变为关注真谓词的使用及其意义。这一时期,对真之理论研究的共同点是对语义学的关注:“几乎总有一个理论家的语义学概念主导了其研究真的框架。”[2]25这一时期,占主导的真之理论研究主要受被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影响的逻辑经验主义和被塔斯基影响的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有代表的真之理论类型主要有:真之逻辑经验主义、塔斯基的真之语义学和奎因的真之去引号主义等。
艾耶尔(Ayer)、卡尔纳普(Carnap)、纽拉特(Neurath)和石里克(Schlick)等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者深受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影响,他们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上来解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形式概念,坚持维特根斯坦的外延性论点——唯一有意义的命题是原子命题或由它们的真值条件构成的那些命题。他们进一步提出唯一有意义的陈述是那些可证实的陈述的观点。此外,他们也继承了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和有意义的证实主义标准——推出逻辑真或分析的真是无意义的观点。由此导致逻辑经验者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真概念。大部分逻辑经验主义者把“真”看作是与“证实”这一概念相关联的,他们对真之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要么把真看作一个形而上学的伪概念而加以拒斥,要么通过证实的方式来支持真之融贯论。同时,他们也认为,真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语义概念。对这样的一个语义概念必须获得其经验上的证据和描述,其对一种科学语言句子之间的关系是有用的。因此,我们从他们的这一观点中嚼出了经验主义者的真概念有实证主义的味道。
石里克的真之理论暗含着一种形而上学的色彩。石里克想寻求事实、语言和世界之间的语义关系,他支持基础主义的真之符合论的观点,他通过比较命题和事实来看一个命题是否为真。卡尔纳普和纽拉特先赞同石里克的基础主义的真之符合论的观点,后来在杜恒(Duhem)和彭加勒(Poincaré)的影响下接受证实的整体论的观点,转而支持证实的真之融贯论,但是他们也并没有致力于真之融贯论。纽拉特通过用证实的定义代替真概念的日常用法,从而使证实的融贯论走向真正的真之融贯论,他的真之融贯论的证实性和整体性特征使得他成为了一个实用主义者。卡尔纳普认为,一些句子的真、分析的真都仅仅通过观察它们的句法属性就能发现,并且认为在逻辑中不需要真谓词。因此,他好像支持“真不能被语法地定义”的观点。从这一点来看,他好像支持拉姆塞意义上的冗余论[8]53。艾耶尔和亨佩尔(Hempel)等人根据卡尔纳普的证实融贯论把石里克看作是真之融贯论者。艾耶尔追随拉姆塞的真之冗余论,认为不存在任何真理问题,对真的正确分析揭示出不存在能够怀疑其本质的真的属性问题[9]89。因此,逻辑经验主义者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真之理论观点,可惜这些关于“真”的观点没有被普遍采用。而塔斯基提出的真之语义学概念,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紧缩的真之理论能给逻辑经验主义者一个合理的解释。
塔斯基的真之语义学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拉姆塞紧缩的真之理论,但是,也有学者把他解释为真之符合论的一个观点。毫无疑问,塔斯基的真之语义学已成为当代西方真之理论的一个主流观点,时至今日,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定义“真句子”的恰当标准。
塔斯基放弃了为日常语言、自然语言提供真谓词的定义的打算,而改为为形式语言提供一个真谓词的定义,或提供一个定义真谓词的方法。并且,塔斯基只对为形式语言定义“真句子”这一术语感兴趣,而对任何使用到命题或信念中的真概念不感兴趣。因此,他提出了定义真谓词的实质上充分的条件,约定T。约定T断言真谓词的任何一个充分定义“T”必须蕴涵T图式(T)的所有实例:
(T)X是T当且仅当p
当它意味着明显的相关的图式(TS)区分真句子的时候,是对“真”充分定义的一个明显合理的限制:
(TS)X是一个真句子当且仅当P
根据塔斯基的观点,如果“T”的定义蕴含所有(T)的实例,那么,“T”至少一定程度上是实质上等价于“真句子”。事实上,这说明了句子的真属性与句子的判断本身是等价的。在塔斯基看来,这只是关于特定真概念的一个充分条件,换句话说就是语义学概念。正如塔斯基自己所说的一样:“一个真句子是认为事态是如此这般,而且事态确实是如此这般的句子。”[10]155因此,他进一步认为,这类陈述是对他所谓“真之经典概念(‘真——与现实相符合’)的必要的详细阐述”[10]153。
正如塔斯基的真之语义学被看作一种形式的真之符合论一样,奥斯汀(Austin)和斯特劳森(Strawson)对符合论和冗余论的争论逐渐演化为意义理论是否可以被合理地考虑为真之理论的一部分?奥斯汀坚持符合关系是绝对地、纯粹地约定的[11]154。对于奥斯汀来说,对语言的分析仅仅是形而上学问题的关键,真之理论应该在我们对“真”的日常使用的分析中体现出来:“我们在开始处理‘真’的上限和种类的时候:我们问自己,真是否是一种实体……或一种性质……或一种关系。但是,哲学家们应该接受某些更接近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来考虑。我们需要讨论的正是‘真’这个词的使用或某种使用。”[11]149也就是我们说真之载体是真的就是有一些约定决定了真之载体意味着p,而它是事实p。因此,奥斯汀给出了一个定义真的办法:通过指示的约定与陈述相互关联的历史事态来认定一个陈述是真的[11]152。根据奥斯汀的说法,陈述指向的总是实在的、真实的事态,虚假的陈述仅仅断言它们是一种它们不是的事态。
斯特劳森拒绝奥斯汀对符合关系以及语言约定、真之载体、真之制造者的说明,赞同拉姆塞的冗余论观点并且拥护拉姆塞对真之本质的探求方法。他明确地表达了紧缩论的主题:使真之理论变成知识、心灵或意义等的一部分。他认为,只有当真的事物被表达式在语词中以其他方式被表现出来的时候,词与物之间就获得了某种类型的约定关系,否则我们就不是真正地,或者不是彻底地理解“是真的”的意思[12]233。
奎因的去引号理论也许是另一个拉姆塞意义上的冗余论。奎因赞同约阿希姆和布兰夏尔德意义上的融贯论,认为只有整个理论能够与实在相符。他的真之理论的观点是由他对语义概念的怀疑形成的,他主张关于真,没有客观的、语言句间的同义词这样的东西,只有比较属于相同语言的表达式的意义这样的观点。奎因反对分析的和综合的真这样的观点,而坚持证实的整体论。他认为,真是“内在的”,真谓词只能被有意义地使用到说话者自己语言中的句子里,并断言真是去引号的——一个句子的真属性仅仅取消了引号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用引号来形成一个句子的名称。这样一来,在拉姆塞的意义上来看,在简单的语境中真谓词就是冗余的,在塔斯基的T图式中,奎因的去引号图式可以表示为:
(DS)“P”是真的当且仅当P
相比较而言,塔斯基的T图式允许句子有任意一个名称,而奎因的去引号图式只要求通过增加引号的方式来形成名称。按照奎因的观点,“真的”的去引号功能就允许我们去做一个技术的、语义的上升来谈论句子,虽然仍然是在谈论这个世界。
三、“日常”转向:何为真之本质?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真之理论的研究,哲学家们不再青睐于语言学方法,而是关注对“何为真之本质?”这一问题的追问,哲学家们进而关注“真的”一词的日常表现。这一时期,大多数哲学家都宣称他们对真之理论的研究都是对塔斯基形式上的真定义的回应与发展,对“何为真之本质?”这一问题的回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表面上来看,这一时期的真之理论的类型都表现出对已有的真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但是这些观点与已有的真之理论之间又表现出难以想象的差异。这一时期的真之理论的特点是为真之理论提供一个间接的、融贯的描述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艰难,因为这一时期的真之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真之理论类型主要有:菲尔德的没有事实的符合论、真之代语句理论、极小的符合论、没有紧缩的紧缩论、真之同一论和新实用主义的真之理论等。
20世纪70年代,哈特里·菲尔德(Hartry Field)意识到把符合论从诉诸事实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提出了没有事实的真之符合论的观点。他指出塔斯基的真之理论没有满足两个表面上合理的限制:(1)塔斯基的“真句子”没有抓住“真”的意义;(2)由于塔斯基真定义的语言相对性,因此他不能提供一个没有语义术语的真定义,进一步说就是,塔斯基没有给出一个物理主义上可接受的真之本质的解释[13]15-22。对此,菲尔德提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物理主义的真之理论,他使用塔斯基的“真句子”成功地去定义指示术语中的真,给出一个物理主义者可接受的真之理论。菲尔德认为,这一理论是符合论的一个类型,它恢复了对“真的”一词的传统的直觉解释。但是,将菲尔德的这一理论使用到自然语言结构的许多类型中还是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
以亚瑟·普莱尔(Arthur Prior)、C·J·F·威廉姆斯(Williams)、多萝西·格罗弗(Dorothy Grover)等为代表的真之代语句论者坚持一种极端的冗余论,他们坚持真根本不是一种属性。普莱尔的追随者C.J.F.威廉姆斯坚持极端的冗余论,他认为仅仅借助“真”来解释惯用语“……符合事实”。因为事实和命题都出于图像,因此“真”不仅是可取消的,甚至他坚持“真”根本不是一个谓词的看法。普莱尔和格罗弗认为“……是真的”不应该被当作一个谓语,并且包含“真的”的句子与不包含“真的”的句子是等价的,包含“真的”的结构发挥着有用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并没有把“真的”完全看作冗余的。因此,我们可以称普莱尔和格罗弗意义上的冗余论为没有冗余的冗余论。
普莱尔坚持命题是“逻辑结构”的观点,并且认为信念的属性不是关于命题的[14]8。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强拉姆塞式的紧缩论——“p”和“命题p是真的”在内涵上是等价的。从表面上看,普莱尔这个强紧缩论中“真的”是属于命题的,但是真的属性不是关于命题的。通过这种方式,普莱尔进一步强调“事实也是逻辑结构”的观点[14]5。因此,普莱尔建议我们把命题(句子)当作它们名义上的变项,也就是把它们看作日常语言中代词的形式有它们的对应物,因此命题变项被称为代语句的表达也有相应的对应物。正如普莱尔所认为的一样,我们“以完美地易于理解的方式延伸‘事物’量词的使用……”[14]37因此,当我们找到日常语言中某种类型的更常见的例子的时候,量词被恰当地理解。而这也正是真之代语句理论的断言的范例。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约翰·麦凯(John Mackie)、威廉·奥尔斯顿(W.Alston)和约翰·塞尔(John Searle)融合冗余论和符合论的立场创造出一种温和的真之简单理论,被学界称为“极小的符合论”。这一观点主要放弃了符合论中“符合是陈述对实在的任何形式的反映”或“符合是对真之载体部分与实在部分之间有某种一一对应的相互关系”这样的观点。麦凯的极小符合论主要来源于对奥斯汀符合论思想的批判继承。他认为:“说一个陈述是真的并不只是说X在类型Y中,而是说正如被陈述的X在类型Y中。”[15]48进一步,麦凯把这一观点概括为“说陈述p是真的就是说事实正如它所陈述的那样”。[15]49因此,麦凯的极小符合论承认真之载体,并认为真是一种关系。但是,为了避免进入一一对应的符合关系的符合论模式,麦凯采用可识别的紧缩论的方法来处理命题,以此避免命题或事实的实质性的说明[15]21。正如塞尔所说的一样,使得猫在垫子上为真的那种东西仅仅是猫在垫子上,并且任何真陈述都是如此[16]211。在极小符合论的意义上来说,“事实”和“命题”都是普遍词,但是它们没有一个能被称为做了解释工作的自然种类或实体。所以,似乎只有把真看作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麦凯和奥尔斯顿赞同霍维奇使用替换量化来概括的等值图式的方法:
(ES)p是真的当且仅当p。
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真之描述方式,说清楚了真之符合论的本质。
索姆斯(Soames)、霍维奇(P·Horwich)和赖特(C·Wright)把等值图式当作他的极小主义的核心教条,他认为极小主义有作为其公理的那个图式的无穷实例,用极小主义解释“真的”的意义,强调真是一个属性,这一观点被学界称之为没有紧缩的紧缩论。索姆斯为膨胀论和紧缩论的区别提供了一种不确定的情况——不确定的情况必须依赖于真谓词的先验描述来处理[17]245。他根据克里普克的“真之理论纲要”指出似真的真之理论构造的可替代模型。他认为根据克里普克的观点,真谓词应该捕获直觉的想法,克里普克的直觉概念为真谓词提供了一种扩展和反扩展,这意味着他给出了真谓词的部分解释。因此,他建议我们消除真谓词,直到在句子中不再出现“真的”。
霍维奇赞同菲尔德和赖特的观点,把等值图式当作极小主义的核心教条,因此霍维奇用他的极小主义解释“真的”的意义。他认为,当我们愿意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接受等值图式的所有非矛盾实例时,我们就掌握了“真的”的意义[18]35。但是,霍维奇没有给出一个“真的”定义,他仅仅是给我们指出是什么使我们拥有真概念[18]135-139。最后,霍维奇认为对真最好的描述是真是一种“逻辑属性”[19]321。此外,霍维奇赞同菲尔德的一个真之紧缩论者一定坚持与指称和满足相类似的观点。如菲尔德认为的一样,真谓词的这种功能需要“p”和“p是真的”的认知等同,从而使得哪怕是符合论者也需要这样一种去引号的真谓词。
当代紧缩论者强调真是一个属性。正如欧内斯特·索莎(Ernest Sosa)所说的一样:“基于这种观点(摩尔式原始主义),你不能用好的或黄的或真来定义它,从而给出一种有启发性的、紧凑的,至少一目了然的摩尔式分析。在这个意义上,你不能哲学地‘解释’任何这样‘简单的’概念。并且这就使得它是开放的,即你应该对由这样的概念基本构成的无限多命题有一种先验知识。”[20]11塞尔认为,当代紧缩论者这种析取性质可以看作一种哲学的反证法[16]215。
朱利安·多德(Julian Dodd)、詹妮弗·霍恩斯比(Jennifer Hornsby)和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等人支持一种真之同一论(the identity theory of truth),这种理论主张真是一种属性却可以没有定义。麦克道威尔认为“当一个人真地思考时,他所思考的东西就是事实所是的那样”[21]27。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真之同一论和真之原始主义极其相似,但是真之同一论在“所思考的东西就是事实所是的那样”这个自明之理之上添加了“真之制造者和真之载体是同一的”这样的解释。如此一来,真之同一论者的这个形而上学假设使得他们的理论貌似走向了布拉德利的融贯论。多德批判符合论者在采用真之制造者原则的时候出了错,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事态这个观点,符合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假设有某种东西使得真为真[22]。霍恩斯比强调我们不能独立于命题去证实事实恰好是真之同一性理论的观点[23]3。真之同一论者的这些观点并不是想提出一种真之本质的观点,而是想证明符合论的失败,他们的观点看起来像是支持某种形式的紧缩论。但是,他们的立场是:这一观点是不同于紧缩论的,而是离原始主义比较近的。
20世纪晚期,以唐纳德·戴维森(D·Davidson)、希拉里·普特南、理查德·罗蒂和C·赖特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者表达了对真之制造者这样的上帝之眼的观点的怀疑,他们不赞同20世纪大多数真之理论的观点,甚至包括实用主义者自己的——真是断定的标准的观点。正如戴维森所说的一样,“把真看作客观的,但是作为目标却是无意义的”[24]67。他们也不赞同詹姆士的“真是有用的”的观点,试图在真之符合论和真之认识论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方法来解决实在论与真的问题。对于新实用主义者来说,真在我们解释其他问题的过程中是一个核心概念,但是它在指导我们的行动中却不起任何作用。
新实用主义者表达与认识有关的理想的理论都可能是假的反符合论的断言,他们还通过坚持意义的整体论来拒斥菲尔德式的符合论。但是,事实上普特南和戴维森都曾经为真之符合论辩护,同时他们也表现出对认识论浓厚的兴趣,罗蒂也曾经赞同皮尔士的真理观。但是,新实用主义者已经提出了许多拒绝认识论的理由。普特南认为如果真是一个与认识相关的概念,任何把证实构建为真定义的理论都将承认真之载体在没有改变意义的情况下可能改变其真值,因此我们将不能获得真。此外,普特南还认为真是超验-认识的,这一观点导致普特南放弃了认识论的观点而转向“常识实在论”[25]510-517。但是,正如C·赖特主张的一样,我们不清楚是否需要放弃一种真之认识论观点来赞同真能被超验地认识到[26]335-364。新实用主义者对真之紧缩论持不同的态度。普特南和戴维森都持有一种紧缩论的态度却没有接受真之紧缩论,戴维森把紧缩论看作一种不同的给真下定义的尝试,而普特南认为紧缩论的真概念与他坚持的真是一种超验认识的真概念相冲突,但是罗蒂赞同真之紧缩论,并且他赞同真是一种属性的观点,认为真在解释理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赖特也赞同真之极小主义的紧缩论类型,但是他反对紧缩论的观点。
四、当代西方真之理论的发展趋势:多元化倾向
通过对西方真之理论的三次转向的分析,我们发现:
(1)真之理论的发展是伴随着哲学而发展的,这不仅仅体现在真之理论研究中,主题随着哲学研究的主题的转变而转变,还体现在整个真之理论的发展历史之中。综观整个真之理论的发展,我们发现,很多在20世纪初就出现的真之理论类型,在当代又焕发了新的活力,甚至成为真之理论的主流。比如,20世纪初出现的真之原始主义在当代又以真之同一论的身份活跃在真之理论领域。20世纪初期就出现的真之多元论思想在当代不仅作为一个真之理论类型被系统地研究,而且成为当今主流的真之理论类型之一。最初,罗素等原始主义者坚持真是最为原始的逻辑意义上的真和假的观点,而如今多德等人的真之同一论意义上的真之原始主义已经和真之紧缩论难舍难分,并且在真之同一论这里真是一种不可被定义属性。所以,真之理论回到真之原始主义(真之同一性理论)不是简单的轮回,而是真之理论已经实质性地发展了。
(2)在整个真之理论的发展历程中,真之理论从成为哲学约定的副产品到具有一个有意义的功能,再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其中有哲学研究主题的转变的因素,也有时代特征的因素。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这也同样适合于真之理论。真之理论的本体论转向时期,真之理论成为哲学约定的副产品,自然有形而上学的色彩和认识论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当代,我们更关注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在当前全球化的推动之下,文化多元化和多样化成为我们的时代特征,所以真之理论的研究自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3)在每一个时代,除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真之理论之外,每一个类型的真之理论也都有自己的市场。我们发现,不论是哪种真之理论类型的研究,我们都不得不考虑真之符合论的思想,可以说,真之符合论的思想贯穿在所有真之理论的研究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塔斯基的真之语义学理论既被看作是紧缩论的类型,也被看作是符合论的类型的原因之一。不论哪种类型的真之理论都有它的作用和意义,都有它存在的原因和理由;不论哪种真之理论类型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和困境;无论是哪一个类型的真之理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真之理论面对的困境;无论是哪一个真之理论类型都无法满足哲学研究对真之理论的需求。因此,某一单一的真之理论类型是不可能解决真之理论发展中面临的困境的。并且,在当今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某一单一的真之理论类型也不可能满足我们哲学发展对真之理论的需求,这就是真之理论走向多元化发展的原因,就如同C·赖特把历史上不同的真之理论类型都看作真之平凡话语为真之多元论服务一样。
(4)自近代以来,西方真之理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实质论和紧缩论两条对立的路线,这两条路线反映了当代西方真之理论研究者对真概念的特性以及真之理论的研究任务的根本分歧。实质论通过揭示真概念所表达的某种实质性的性质或关系来对之加以解释,认为真概念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形而上学或认识论内涵的概念;紧缩论关注说明真谓词的各自逻辑、语义概念功能,认为真概念是一个纯粹的逻辑、语义概念。
在当代,占主流的真之理论类型主要有真之相对主义、真之置换理论和真之多元论等。近几年来,凯文·夏普(Kevin Scharp)为解决诸如说谎者悖论之类的语义悖论提出了真之置换理论,这种理论虽然没有暗示有超过一种的成真方式,也没有暗示不止一个真概念,但是这种理论实例化在当代的真之理论里有一个多元化的倾向。真之置换理论主张真是一个不一致的概念,我们不应该依赖于它理论上的语境,它是一个多元性的不严格的真概念——上升的真和下降的真[27]。约翰·麦克法兰(John MacFarlane)为了理解某一类型的表达式(包括未来的偶然性、知识的归因、认知的模式、审美判断等)和“义务”的陈述的相对性发展了一个评定敏感性的概念的精巧结构。在他看来,我们应该假设两种不同的真概念:绝对的真和相对可评估的真[28]。C·赖特提出了一个关于真之本质的观点:真并不总是存在于相同种类的事物里,对于不同种类的主题,真可能要求不同的处理[29]。道格拉斯·爱德华兹(Douglas Edwards)、林奇对赖特的真之多元论提出批评,并进一步改进了真之多元论,使得真之多元论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当前,真之多元论形成了以赖特、林奇和吉拉·谢尔(G·Sher)为代表的实质真之理论研究,并逐渐占据真之理论研究的主导地位。不论是夏普的真之置换理论,还是麦克法兰的真之相对主义都有一个多元化的发展倾向[30]。
因此,在当代,不论是从整个真之理论发展的节点,也就是我们从追求某一真之理论类型的研究转向真之理论的多元化发展,还是在当前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和哲学背景之下,真之理论的发展趋势都倾向于一个多元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