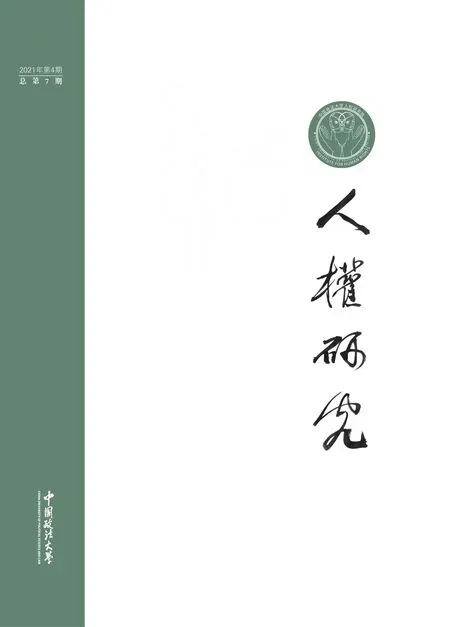多元社会中人权规范的解释路径
——以法国法院对外国休妻判决的承认为样本
2021-12-04朱明哲
朱明哲
一、面对休妻判决的欧洲人权法
在人权法的发展过程中,关于人权法规范的普世性和各种文化、宗教、社会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1See Neil Walker,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in Human Rights,in Cindy Holder & David Reidy eds.,Human Rights: The Hard Ques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39-58.其中,在欧洲各国的人权法实践中,伊斯兰身份认同的觉醒提出了如何在世俗法律的解释适用中实现平等待人的问题。1参见朱明哲:《司法中的政治理论脉络——从宗教符号判例看法国共和主义下的世俗性与平等》,载《法学家》2018年第2期,第88—105页。对于曾经在中亚和北非建立正式殖民地的法国而言,虽然伊斯兰教徒在人口中占的比例不高,2所有来自有伊斯兰背景之国家的移民及其后代在法国人口中占比5%左右。France Prioux et Arnaud Régnier-Loilier,« La pratique religieuse influence-t-elle les comportements familiaux? » , Population et Sociétés, no 447,2008,p.1-4.许多关于穆斯林身份认同的争议仍转化成了法律争议,在作为权威性定纷止争之途径的司法中寻求解决。3关于法国和欧盟法院有关判例的检讨,参见朱明哲:《司法中的政治理论脉络——从宗教符号判例看法国共和主义下的世俗性与平等》,载《法学家》2018年第2期,第88—105页;朱明哲:《论法国“世俗性”原则的斗争面向》,载《欧洲研究》2016年第6期,第117—135页。这两篇文章探讨了法国作为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在法国以及欧洲法层面,宪法和人权法如何规制基督教规范、如何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符号区别对待的问题。晚近判例涉及的法律领域众多,民法、社会法、行政法、宪法……几乎无所不包,自然也包括了人权法。而纷繁复杂的事实和精细扎实的教义学背后隐藏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在一个以世俗的规范保证普遍人权的法律体系中,如何安放具有明显宗教渊源的规范?
本文通过探讨法国法院在决定是否应该承认外国法院之有效休妻(Talâq/Répudiation)判决时对配偶平等的解释,讨论多元社会的司法应该如何处理普世人权和宗教特殊性之间的张力。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的法院作出的休妻判决是否必然违背配偶平等的问题,正是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规范与世俗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人权法领域的反映。源于《古兰经》第2章第228至243节和第65章第1节的休妻制度在不同的教法学派上有不同的实施细则,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法律规定。总体而言,该制度的核心内容在于允许丈夫依据其单方意愿解除与妻子的婚姻。虽然《法国民法典》允许分居满2年之夫妻中的一方单方申请离婚(第238条),但是仅承认丈夫解除婚姻权利的安排非但不见于现在欧洲各国的民法,也因为与《欧洲人权公约第七议定书》(以下简称《第七议定书》)第5条所规定之配偶之间的平等相违背而不可能出现。那么,如果一个外国法院通过合法程序作出了关于休妻有效的判决,法国法院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承认该判决的效力?专门研究伊斯兰法的德国学者罗厄(Mathias Rohe)把问题表述为:“一个法律操作如果与欧洲人权保护标准相悖,应该一概认定其无效,还是应该允许法院和行政机关有限考虑其具体实践结果,然后依据个案不同,决定相应的实践对于当事方而言是否可以接受?欧洲的‘公共利益’到底该彻底拒绝承认一切形式的单方离婚还是应该只在妻子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而且拒绝离婚的场合才不予承认?”4See Mathias Rohe,Family and the Law in Europe: Bringing Together Secular Legal Orders and Religious Norms and Needs,in Prakash Shah,Marie-Claire Foblets & Mathias Rohe eds.,Family,Religion and Law: Cultural Encounters in Europe,Routledge,2016,p.63.
对于外国法院的休妻判决,法国最高法院2004年以前倾向于考虑个案情况、以女性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路径,2004年以后转为强调《第七议定书》、一律拒绝承认休妻判决的路径。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此种转变:一方面,它体现了法国法院进入21世纪后在解释和适用私法规范时越来越重视一国公法秩序和国际人权法的趋势;5Cf. Geneviève Helleringer et Kiteri Garcia,« Le rayonnement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es droits fondamentaux en droit privé »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vol.66,no 2,2014,p.283-336.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法对法国国际私法上公共秩序概念的改造。1Cf. Sylvaine Poillot Peruzzetto,« Ordre public et loi de police dans l’ordre communautaire » ,Travaux du Comité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vol.16,no 2002,2005,p.65-116.本文希望展现这一转变背后的法哲学意义。对一个具体的社会争议,就可能有同样符合法律规定的解决方案,在各种方案中进行选择本身就是一个价值问题。依靠政治共同体的共识做一个权威价值判断,这在多元社会变得愈发艰难。于是,法律人更有必要发掘每一种法律解决方案背后的价值立场,然后就此进行辩难,寻求新的共识。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尤其如此。
究其根本,发生在2004年的立场转变涉及的是法国国内法院对于《欧洲人权公约》相关条款的解释改变。对国际条约的“演进解释”(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最近已经在国际学界引发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探讨。2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参见Eirik Bjorge,The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欧洲人权法院也在其裁判中承认,法律条款的解释必须考虑当时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条件”3SW v.United Kingdom (1996) 21 EHRR 363,para.34.。所以,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法国法院立场转变前后两种人权规范解释方法背后的法哲学基础。一概认定单方离婚无效的立场可以得到法律象征主义(legal symbolism)的支持,考虑具体裁判之实践结果的立场则可以得到法律实用主义(legal pragmatism)的支持。象征主义主张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实践作为道德上绝对的事物内化于法律体系之中,4See Jiří Přibáň, Legal Symbolism: On Law,Time and European Identity, Routledge,2007,p.X.实用主义认为法律概念和法学理论首先是实现目的之手段。5See Brian Z.Tamanaha,Law as a Means to an End: Threat to the Rule of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6.概括性的介绍亦可参见杨知文:《后果取向法律解释的运用及其方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3期,第167—180页。本文则主张2004年以前法国法院实用主义的具体考察方式更为可取。以下将在检讨分析相关判决的基础上,以欧洲人权法对宗教性规则的改造与包容程度为标准,评价两种不同模式。实用主义模式为宗教规范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对话准备了一种祛魅的宗教观,有助于实现法国法对伊斯兰宗教规范的转化。所以实用主义模式在处理人权普遍性和宗教特殊性之张力时是一种更优的法哲学立场。
二、休妻判决承认中的路径选择
我们选择的是一类司空见惯、在技术上不构成任何挑战的案件:对他国法院涉及婚姻关系判决的承认。国际私法长期以来为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即依据何种标准选择可以适用的法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理论和技术。国际私法提供的法律技术让国际私法学家在该类个案中既可以选择承认北非各国的休妻判决,也可以选择不承认。换言之,国际私法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知识。在不同的路径中选择终究涉及到法理论的问题。在这些案件中,法国法院要决定的是摩洛哥或阿尔及利亚的法院依据本国《民法典》(而非《古兰经》或“圣训/圣行”)作出的婚姻消灭判决在法国是否有效。如前所述,法国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在2004年前后出现了明显的路径转变。此前,法院更多聚焦于具体案件中当事人利益的保护;此后,最高司法机关则更坚持抽象性别平等。这一转变背后实际上是法哲学观念的变化。本文分别把这两种法哲学观念概括为实用主义和象征主义。
(一)具体利益权衡的实用主义路径
法国法院对外国法院人身判决的承认取决于公共秩序审查。根据法国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签订的司法互助条约,只要不违反当地的公共秩序,那么一个缔约国法院关于个人人格和身份的判决应得到另一缔约国的承认。1Art.1er d) de la Convention franco-algérienne du 27 août 1964; Art.13 alinéa 1 de la Convention franco-marocaine du 10 août 1981.与此同时,一个外国法院的判决在满足以下五种条件时,可以得到法国法院的承认:(1)外国法院的法官有权作出此种判决;(2)外国法院的审判程序不违背法国的程序公共秩序(ordre public procédural),即尊重两造之辩护权;(3)根据法国的冲突法规则适用外国法;(4)符合法国的国际公共秩序概念;(5)不存在规避法律(fraude à la loi)的情节。2Cour de cassation,Chambre civile 1ère,7 janvier 1964,no 302,Publié au bulletin; cf. Marie-Claude Najm,« Le sort des répudiations musulmanes dans l’ordre juridique français.Droit et idéologie(s) » , Droit et cultures.Revue internationale interdisciplinaire, no 59,2010,p.209-229.2004年以前,法国最高法院认为如果住所地在法国的夫妻同时具有另一国籍,那么该国法院即有权裁判,且裁判时不必适用法国法。换言之,在五项条件之中,对于国外法院管辖权和法律适用的形式判断方面,法国法院在婚姻关系案件中倾向于尊重国外法院的判决。所以,对于休妻判决之承认,重要的是如何解释“公共秩序”和“规避法律”。以规避法律拒绝承认在2000年以前很少出现,因为规避法律既需要证明当事人的恶意,又要证明其与作出判决的法院所在国之间的法律联结是为了避免适用对其不利之法律而为。而在相关案件中,夫妻双方的摩洛哥或阿尔及利亚国籍早在婚姻之前就已经取得了,以至于实际上没有太多讨论规避法律的必要。3相反观点,参见Jean-Yves Carlier,« La reconnaissance des répudiations » ,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familial,no 2,1996,p.131-140; Jean-Yves Carlier,« Volonté,ordre public et fraude dans la reconnaissance des divorces et répudiations intervenus à l’étranger » ,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Familial,no 2,1991,p.165-172.可见,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其实是对“公共秩序”的解释。
诉诸“公共秩序”路径因为允许国家过多干涉在观念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家庭关系而必须慎用。所以布赫尔(Andreas Bucher)才说公共秩序是一种“轻易不该拔出的武器”——在世俗国家中,婚姻关系或多或少有国家权威的介入,而在其他国家依照宗教或习惯规则缔结的婚姻或许未经国家的干预,即便如此,世俗国家也不能轻易以公共秩序之名不承认这种纯粹私人性质的安排。4Andreas Bucher,« La famill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vol.283,2000,p.113.为此,法国法院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情况:“在法国适用外国法”和“让外国法院适用外国法所为判决在法国发生效力”。两种情况与法国公共秩序的关系不同,在后一种情况下,法院一般不进行公共秩序评价——即为法国法上的“公共秩序例外”(l’ordre public atténué)。1Cf. Andreas Bucher,L’ordre public et le but social des loi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Martinus Nijhoあ Publishers,1994,p.47-52.基于以上考虑,法国最高法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倾向于承认外国法院休妻判决的效力。2Cour de cassation,Chambre civile 1ère,3 novembre 1983,no 81-15.745,Publié au bulletin.
在法官承认或否认休妻判决时,欧洲人权法提供了重要的规范基础。法国法院不时出于《第七议定书》关于夫妻双方平等的规定而拒绝承认休妻判决。3Cf. Andreas Bucher,« La famill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vol.283,2000,p.128.但是,法官在适用这一规范时,为了避免对外国法律是否尊重了基本人权进行实质评价,往往会把配偶平等进一步具体化为两种公共秩序考量。在程序公共秩序上,休妻不得出于避免在法国提出之离婚诉讼的目的而为;在生活公共秩序(ordre public alimentaire)上,休妻不得出于避免承担对女方之抚养义务的目的而为。4Cf. Hugues Fulchiron,« “Ne répudiez point...” : Pour une interprétation raisonnée des arrêts du 17 février 2004 »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vol.58,no 1,2006,p.7-26.换言之,如果承认夫单方解除婚姻之效力的司法程序没有妻的参与,那么自可以因为不符合程序公共秩序而拒绝承认;如果夫拒绝支付在法国离婚所必须支付的赡养费用,那么也自可以因为不符合生活公共秩序而拒绝承认。5Cf. Françoise Monéger,« Vers la fin de la reconnaissance des répudiations musulmanes par le juge français? » ,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vol.119,no 2,1992,p.347-355.所以,法国法官长期以来的做法是在适用欧洲人权法的时候尽量精细化为一系列技术性标准,而不是采取一种固定的价值立场。
在使用法律技术时,法国法院选择了更实质的评判标准:如何能保护妻的利益。在私人关系中,最简单的判断标准显然是个人的意愿。如果妻子本人同意让休妻宣告发生解除婚姻的效力,那么法院自然也无须坚持公共秩序的介入。6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Paris,Chambre civile 1ère,26 février 1992.同时,还存在着一些更客观的因素帮助法官考虑如何在面对这种似乎本质上歧视女性的制度时实现对妻子的平等保护。如果不承认判决会导致夫可以回国后再婚、而妻必须先在法国获得离婚判决方能在法国再婚,或者丈夫同意并支付足够的赡养费用,那么可以认为承认离婚判决有利于保护妻子的利益。7Cour de cassation,Chambre civile 3e,5 janvier 1999,no 671; Cour de cassation,Chambre civile 1ère,3 juillet 2001,no 99-12.859.可见,在2004年以前的各个判决之中,法官并非没有考虑配偶间的平等保护,但判断的标准是妻子的利益而非抽象的人权。
总结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承认外国休妻判决成为议题以来,法国最高法院长期贯彻权衡当事人利益的实用主义解释路径。这种做法意味着法院在进行合法性判断后,主要依据判决的合理性决定是否承认休妻判决。实用主义的法哲学立场又包括了三个附属性的主张。第一,法律概念和法律规范体系无法绝对决定个案的法律解决方式。8第二,法律在一定的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中产生与适用,法律的意义、功能、作用也都取决于特定的社会语境。1See Brian Z.Tamanaha,A Realistic Theory of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1; Benoît Frydman,« Le rapport du droit aux contextes selon l’approche pragmatique de l’École de Bruxelles » ,Revue interdisciplinaire d’études juridiques,vol.70,no 1,2013,p.92-98; Lawrence M.Friedman,American Law in the 20th Century,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p.ix.第三,包括法学与司法在内的法律活动都应该以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实现个案的正当分配为目标。2Cf.Benoît Frydman,« Le rapport du droit aux contextes selon l’approche pragmatique de l’École de Bruxelles » ,Revue interdisciplinaire d’études juridiques,vol.70,no 1,2013, p.92-98.2004年以前,法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一般不会抽象判断其他国家法律秩序的正当性,他们更愿意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费心理解到底妻子本身是否能因为婚姻消灭的结果获益。其结果是这些似乎在休妻制度中受到歧视的女性的利益可以得到更细致和具体的考虑与保护。
(二)抽象性别平等的象征主义路径
进入21世纪后,欧洲法院从整体上开始转向抽象地拒绝承认休妻能够产生离婚的法律效果,而不是强调每个个案的特殊性。3See Mathias Rohe,Family and the Law in Europe: Bringing Together Secular Legal Orders and Religious Norms and Needs,in Prakash Shah,Marie-Claire Foblets & Mathias Rohe eds.,Family,Religion and Law: Cultural Encounters in Europe,Routledge,2016,p.64.这种变化背后并非法律制度自身的发展,而是一种视法律为文化身份表达的“法律象征主义”思潮。换言之,决定法官对法律适用的不再是两造之间的利益分配,而是法律规则所彰显的身份认同。在本文所关心的判例中,是否承认休妻判决就成了适用属于“我们”的人权规范还是属于“他们”的宗教规范的问题。
法国最高法院民事庭在2004年2月17日的5个判决中,既改变了此前对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法院休妻判决较为宽容之态度,又改变了具体利益衡量的论证方法。4Cour de cassation,Chambre civile 1ère,17 février 2004,nos 256-260.这5个判例的共同点是居住在法国、拥有双重国籍的夫妇中,丈夫在摩洛哥或阿尔及利亚的法院取得了单方决定婚姻关系结束的休妻判决。在管辖权和公共秩序两方面,判例中都出现了无法忽视的发展。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法院是否因为当事人国籍而对此类案件有管辖权的问题上,法国最高法院依据新生效的《民事诉讼法》第1070条,判定在此类案件中适用管辖权的就近原则,即由居所地法院行使排他的管辖权。5Cour de cassation,Chambre civile 1ère,17 février 2004,no 260.在公共秩序方面,法国最高法院则认为休妻判决“因为与《第七议定书》第5条不符,所以与法国的国际公共秩序相违背”6Cour de cassation,Chambre civile 1ère,17 février 2004,no 256.。前者意味着婚姻关系消灭的案件将只能适用法国法,从而成为欧洲人权法审查的对象。后者意味着欧洲人权法上的原则构成了国际公共秩序的一部分,从而改变了此前把公共秩序分为两个较为具体标准的解释方法。这几个判例首先显示了《法国民法典》第3条所说的“强行法”(loi de police)在欧盟法背景下的新理解问题。一国必须参照欧盟法解释其国际公共秩序。1Cf. Sylvaine Poillot Peruzzetto,« Ordre public et loi de police dans l’ordre communautaire » ,Travaux du Comité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vol.16,no 2002,2005,p.65-116.休妻判决承认案件中的新公共秩序标准让法官不再需要考虑妻子实质是否希望婚姻关系存续,也不再需要具体分析赡养费的给付是否足够妻子生活,而只需要从抽象的配偶平等出发即可判断。
至于如何理解配偶平等,法国最高法院又采取了形式性的标准。休妻之所以不为配偶平等原则所容,乃是因为其仅因丈夫单方意志、在诉讼程序之外发生,不但妻子没有反对的权利,法官亦无质疑婚姻关系消灭和责任分配之权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夫妻并不是因为休妻之单方行为的特征而变得不平等,而是因为该制度把丈夫的支配地位结构化为法律制度。2Cf. Marie-Laure Niboyet,« Regard français sur la reconnaissance en France des répudiations musulmanes »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vol.58,no 1,2006,p.27-46.法国法院实际上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理解婚姻关系中夫妻权利平等。这种形式标准下,休妻制度确实与平等原则格格不入。以摩洛哥为例,2004年2月家庭与身份法修改才确定了休妻只有在法官介入和司法公证员参与下才能生效的制度,妻子为自己利益辩护的程序性权利也才得到承认。3Cf. Edwige Rude-Antoine,« Le mariage et le divorce dans le Code marocain de la famille.Le nouveau droit à l’égalité entre l’homme et la femme » ,Droit et cultures.Revue internationale interdisciplinaire, no 59,2010,p.43-57.所以,如果在人权法的视野内对休妻这一特殊的制度进行评价,认为其有违性别平等也并无不妥。
对一个外国制度的评价改变了,随之产生的是教义学应用的转变。此前,法国的法学家也同样批评休妻制度与性别平等的观念水火不容,但法院当时避免直接用抽象价值判断直接决定是否承认外国法院的判决。法官们曾以更为迂回的方式,使“公共秩序例外”变成常态,在系争判决本身能于实质上避免妻子的不利时小心地加以承认。现在,在法律制度本身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法国法院却采取了不同的立场。《第七议定书》第5条并没有让法国2004年的法律体系与上世纪80年代的法律体系产生本质区别。根据1958年《第五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55条关于“依法批准或者认可的条约或者协定,自公布后即具有高于各种法律的权威”的规定,法国在1985年批准加入《第七议定书》时,该议定书即在法国具有了国内法的效力。法国最高法院也并非在《第七议定书》具有法国国内法之效力后马上拒绝承认休妻判决。而且就算没有《欧洲人权公约》及其议定书,性别平等也自1946年《第四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以来一直是法国政府所保障的基本宪法原则。4“男女平等”首次出现在《第四共和国宪法》“序言”部分第3条。宪法委员会和学说都认为《人权宣言》和《第四共和国宪法》的“序言”是现行宪法的一部分。Cf. Pierre Pactet et Ferdinand Mélin-Soucramanien,Droit constitutionnel,Dalloz-Sirey,2008,p.517,532-534; Michel Lascombe,Xavier Vandendriessche,et Christelle de Gaudemont,Code constitutionnel et des droits fondamentaux,Édition 2017,Dalloz-Sirey,2016,p.4.显然,促成转变的原因在别处,而非议定书的规则。
从主张公共秩序例外到以性别平等作为公共秩序的核心而审查休妻判决,法国司法机关立场的转变暗示了一种对性别平等理解的变化。此前,法官更重视的是以性别平等原则保护在不平等的法律结构中弱势一方在具体个案中的利益。现在,重心落在了形式平等的名义价值上。法官不再问“她是否希望结束婚姻?她能否得到足够的经济补偿?”1至少从统计数字上看,妻子往往是更愿意提出离婚的那一方。Cf. Jacques Commaille et Yves Dezalay,« Les caractéristiques judiciaires du divorce en France » ,Population, vol.26,no 2,1971,p.173-196.法官论证重心的转变表明,在司法中更重要的不是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平衡,而是重申欧洲人权法所声明的价值。布赫尔曾经主张,在家庭法领域,“国际私法没有超越于个人利益的公共秩序需要保护”2Andreas Bucher,« La famill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vol.283,2000,p.128.。如今,形式平等的象征性价值确实超越了个人利益。从欧盟整合的背景看,其象征主义的特征更加明显。进入新世纪以后,对欧洲身份认同和欧洲统一政治的诉求也成为法学上不得不考虑的议题。3Cf. Jiří Přibáň,Legal Symbolism: On Law,Time and European Identity,Routledge,2007,p.119-124.无独有偶,法国无论是法院还是立法机关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一转此前对宗教符号的宽容态度,转而压制外显的宗教身份表达。4参见朱明哲:《论法国“世俗性”原则的斗争面向》,载《欧洲研究》2016年第6期,第117—135页。于是,他们把《第七议定书》第5条理解成了一道鸿沟,一边是尊重性别平等、普世人权的欧洲法律体系,另一边则是必定男尊女卑、否认人权的“穆斯林法”。
三、法国共和主义宗教观的不同表达
法国法院为了解决外国休妻判决之效力而使用的法律解释方式所折射出的人权与传统关系,只有在共和主义宗教观背景中才能理解。当“文明的冲突”在国际私法上表现为宗教规范与国家法规范的冲突时,必然会产生碰撞和交流,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模式。5托伊布纳(Gunther Teubner)在讨论法律移植的时候提出,一种制度引入到一个全新的法律体系中只能让双方同时出现改变,并产生全新的制度。本文借鉴他的思路,从一开始排除了用一个系统全面消除另一个系统的可能性。See Gunther Teubner,Legal Irritants: Good Faith in British Law or How Unifying Law Ends up in New Divergences, 61 Modern Law Review 11,11-32 (1998).法学家的工作是找出一个合适的观念,帮助我们谈论二者的交流以及所产生的新模式。为此,我们需要一种祛魅的宗教观念,从而让宗教系统可以与世俗的政治系统对话。实用主义和象征主义两种立场在法律观和宗教观上都有重要分歧。在法律观上,实用主义模式实际上把法律规则理解为实现个案中利益平衡的工具,而象征主义则把法律理解为一种文化整体性的表达。这两种法律观还伴随着两种不同的宗教观,以至于它们对世俗共和国如何处理宗教的问题有不同的答案。实用主义和象征主义都继承了法国共和主义的宗教观,把宗教视为一种社会机构和身份认同。区别在于实用主义承认宗教系统与世俗政治系统之间交流的开放性和身份认同的多元性。
(一)作为社会机构的宗教
法国共和主义传统视宗教为一种社会机构。宗教首先是一种与国家竞争着权力、同时可能对个人构成制约的机构。所以,在确立共和政体的斗争中,法国选择的并非美国式政教分离的路径,而是一种“斗争性”的世俗化路径。世俗国家既垄断社会与政治权力,又以个人自由的保护者面貌出现,限制宗教机构的活动范围。在法国,世俗性原则也正建立于打击天主教会的基础之上。在1880年《驱逐修会政令》后,共和国陆续引入了禁止教会私立学校的《费礼法》、禁止神职人员出任公共教学职务的《戈布莱法》等一系列法律,彻底世俗化初等和中等教育。1905年的《教会与国家分离法》最终实现了没收教产、教堂国有化等制度。上述举措和制度的象征意义是,同为社会机构的国家从此凌驾于宗教之上。于是,当私立幼儿园的副园长坚持佩戴头巾时,从世俗性的角度来说正意味着宗教出现在了教育机构之中,从而引发了世俗的和宗教的两种不同社会机构之间的冲突。1Cour de cassation,Assemblée plénière,25 juin 2014,n° 13-28.369; 参见朱明哲:《论法国“世俗性”原则的斗争面向》,载《欧洲研究》2016年第6期,第117—135页。出于类似的原因,当市政厅在圣诞节搭建耶稣降生场景时,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自然是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法》第28条的解释,但同时也是对于宗教在行政机关登堂入室的担忧。2Conseil d’État,9 novembre 2016,Fédération de la libre pensée de Vendée, n° 395223; Conseil d’État,9 novembre 2016,Fédération départementale des libres penseurs de Seine-et-Marne, n° 395122.2017年的判例进一步确认,只要是在公立机关的建筑及其附属空间内,就算可以竖立前任教皇保罗二世的雕像,也必须移除雕像上的十字架。3Conseil d’État,25 octobre 2017,Fédération morbihannaise de la Libre Pensée et autres, n° 396990.
透过以上一系列判决,可以看见法国以世俗性之名监督着作为社会机制的宗教和作为其组织机关的教会。国家不仅限定着宗教活动的范围,还干预宗教组织的管理。2018年2月1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出:“我们要努力改变伊斯兰教在法国的组织结构及其表达方式。”4« Macron veut “poser les jalons de toute l’organisation de l’islam de France” » ,[Le Journal du Dimanche : http://www.lejdd.fr/politique/macron-veut-poser-les-jalons-de-toute-lorganisation-de-lislam-de-france-3570797].Consulté le 13 février 2018.他相当明确地表明了政府随时准备干预宗教机构的内部治理。宗教和其他的社会机构一样,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目前,内政部的观点是法国伊斯兰教的宗教人士和宗教机构受到过多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的影响。5Cf. Didier Leschi,« Problèmes contemporains de la laïcité publique »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 https://www.conseil-constitutionnel.fr/nouveaux-cahiers-du-conseil-constitutionnel/problemes-contemporains-de-la-laicite-publique].Consulté le 20 février 2018.所以,马克龙的表态很可能意味着结束“治外教权”(l’islam consulaire)。除了宗教的组织外,宗教之表达也是政府所关心的事项。2017年3月29日,法国伊斯兰教委员会(Conseil français du culte musulman)发布了一份人们称为“伊玛目宪章”的文件,呼吁全国范围内的伊玛目和清真寺负责人签字。这份引发争议的文件要求宗教人士认可一种“开放而包容的伊斯兰教”“正道的伊斯兰教”(第2条),并承认“平等而具有尊严的男女,并给了他们不受干预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和信仰的自由”(第3条)。更重要的是,签名的伊斯兰神职人员全心接受“我们的共和国所建立的那些普世价值,以及确保信仰自由和对信仰与宗教实践多元性之尊重的世俗性原则”(第4条)。6Conseil français du culte musulman,29 mars 2017,Charte de l’imam.可见,宗教在法国虽然享有比其他社会组织更高的自主性并以宗教自由之名获得保护,却仍然是世俗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宗教组织活动界限、内部管理、信仰表达无法避免来自国家法律秩序的规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国法一直强调宗教的社会机构面向。
实用主义和象征主义在把宗教看作一种社会机构方面没有区别。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宗教与另一个社会机构——国家——可以、并且一直处于沟通中,后者则认为两者之间不可能存在有意义的交流。象征主义模式试图以性别平等之基本原则作为其正当性的基础,但本文认为这种主张是失败的。仅就对国外判决之承认上,象征主义模式至少有两个重要缺陷。在理论上,它持有一种僵化的观念,认为伊斯兰文化恒定不变,并进一步把穆斯林视为嵌入伊斯兰文化之中、不具备自我决定能力的被动客体。在实践上,它认定,休妻这一歧视女性的制度必然会造成妇女利益受损的结果,从而拒绝在个案中考虑妇女之具体利益诉求。相反,实用主义认为一切文化都处于与其他意义系统的交流与互动之中,随时出现新的形态和观念,个人也可以基于理念或实用的考虑宣称或放弃一种文化身份。这种立场促使解释者通过用法国法的标准和概念解释外国法,实现了对起源于宗教传统的法律规范的欧洲化。
实用主义把宗教视为世俗政治的一环,而非精神性的、外在于政治的现象。它并不认为宗教可以和世俗国家分庭抗礼。国家仍是组织公共生活的唯一场合,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何行使或限制国家权力以实现对宗教自由的平等保护。宗教在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因为每个人从事宗教活动的目的有所不同、宗教对于每个人的意义也有所不同,即便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专家也无法穷尽宗教在社会中的所有面向。牛津的政治哲学家拉博德(Cécile Laborde)提出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至少可以同时是关于美好生活的观念、自觉的道德义务、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联合的模式、容易受影响的群体、无所不包的社会机构、无可明言的理论。1See Cécile Laborde,Religion in the Law: The Disaggregation Approach, 34 Law and Philosophy 581,581-600(2015).除了最后一个维度,宗教与其他的社会现象并无实质区分,完全可以与世俗法律对话。
(二)作为身份认同的宗教
在宗教的身份认同维度上,象征主义比实用主义更好地体现了法国共和主义整治理论单一身份认同的困局。实用主义的多元身份认同为摆脱困局提供了一个可能方案。
在欧盟法院和法国最高法院最近几个判例中,共和主义的一元身份观体现得淋漓尽致:个人只能是共和国自由的公民(政治身份认同),而不能同时拥有其他的身份认同。近年判例中的女主角挑战的正是单一身份认同的传统。判例中坚持佩戴头巾的女性并不是刻板印象中穿着罩袍、认为女性不应该在公共空间抛头露面的保守人士。她们是职业女性(私立幼儿园的副院长、私立保安公司的接待人员、电脑工程师),是在公共沙滩上享受阳光的人,或者是在共和国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的女学生。但她们也坚持自己的宗教身份,而且需要把这一点明确地表现出来。2Cour de justice de l’Union européenne,14 mars 2017,Aあaire C-157/15; Cour de justice de l’Union européenne,14 mars 2017,Aあaire C-188/15; Cour de cassation,Assemblée plénière,25 juin 2014,no 13-28.369; Conseil d’État,ordonnance du 26 août 2016, nos 402742,402777.成员族裔多元的社会中,少数族裔在政治和社会冲突中要求主体族裔尊重其差异,并往往表现为对宗教和文化身份的强化。1Cf. Charles Taylor,Multiculturalisme : Diあérence et démocratie, traduit par Denis-Armand Canal,Flammarion,Paris,1992,p.44.这种宗教性的身份认同显然独立于同一性的公民身份认同之外。换言之,出于自愿而坚持在公开场合将自己宗教信仰外观化的行为意味着行为人坚持自己“是法国人,但同时也是穆斯林”。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双重身份认同挑战了法国共和主义。所以,当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要对关于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张扬的宗教符号发表意见时,它所要解决的并不仅仅是教育平等和信仰自由问题,还有是否允许在构建共和国公民身份的场合表现其他身份认同的问题。
法律象征主义坚持了传统共和主义的一元身份认同观,认为人只能主张一种身份认同,并由此凸显出传统法国共和主义的局限。2参见朱明哲:《司法中的政治理论脉络——从宗教符号判例看法国共和主义下的世俗性与平等》,载《法学家》2018年第2期,第88—105页。在涉及休妻判决承认、多偶制、女性婚前守贞义务等问题上,象征主义都惊恐地意识到,有些公民主张自己适用不同于其他公民的法律。象征主义把这种不同解释为不同于公民身份的其他身份认同在法律领域的外显。但人们完全可以在认为宗教是一种重要的身份认同的同时,承认个人可能有多重不同的身份认同。在他们希望于司法中保护自己的利益时,也完全可以坚持使用统一国家法秩序的规则、概念、理论来解释他们的诉求。象征主义无法理解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之间的区分。其结果是政治和文化的身份认同之对立体现在法律象征主义的思路之中,变成了“坚持自由、民主、普遍人权、共和政体的我们”和“屈服于蒙昧、不平等、文化特殊性、神权统治的他们”之间的对立。在涉及婚姻家庭的诉讼中优先保护抽象的性别平等而非具体的利益分配,本身就是这种对立的表现。
然而,公民身份优先前提下的多元身份认同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实现,在实践中也是对多元社会更好的回应。3See Will Kymlicka,The Rise and Fall of Multiculturalism? New Debates on Inclusion and Accommodation in Diverse Societies,61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97,97-112 (2010).换言之,一种更现实的立场是,承认人既可以是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同时也是某个宗教文化共同体的成员。那么真正的问题实际上不在于我们到底如何认识自己,而在于如何避免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多元威胁政治共同体的公共生活。就算承认共和主义对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担忧完全是合理的,也无需担心多元身份认同会导致所有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落空。反而是符号化特定群体的观念、拒绝世俗政治与宗教群体之间对话的象征主义策略更有可能导致对立和不宽容。
实用主义和象征主义都把宗教看作一种身份认同,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人可以有多种身份认同,后者则认为宗教身份认同必然排除政治身份认同。单一身份认同曾经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在建立统一民族国家、巩固共和制方面发挥了正面的作用。但是,随着现在地方分权加速、区域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国家不再是唯一的政治共同体。那么,每个人的政治身份认同已经必然走向多元。举例而言,一个法国人可以分别作为市镇居民、国家公民、欧洲人参与市政、全国、欧洲三个层面的政治生活。所以,单一身份认同的理念在当前政治实践面前已经变得苍白无力。既然如此,承认个人除了国家公民的身份认同之外保持文化/宗教的认同并无害处。
四、以世俗法律概念转化宗教规范
实用主义方案把宗教视为多元社会机构之一、多元身份认同之一,从而既拒绝神秘化宗教,又拒绝把世俗法律体系与宗教规范截然分离。它主张两种不同秩序之间的对话,既承认宗教作为一种基本善对于个人的重要性,又承认国家为了保护个人的利益干预宗教活动的必要性。采取实用主义的立场将允许法律的解释者在本国法律秩序的技术和概念中理解外国规范。它一方面实现世俗法律秩序对宗教规范的审查与规制,另一方面推动世俗政治对宗教生活的祛魅。
(一)国家法对宗教规范的转化
现代共和政体假设法律的内容和形式皆由世俗的国家机构决定。形成法律和适用法律的权力是主权的一部分,而且国家保证同样的法律适用于所有的公民。1参见朱明哲:《司法中的政治理论脉络——从宗教符号判例看法国共和主义下的世俗性与平等》,载《法学家》2018年第2期,第93—94页。随着现代社会多元化程度的增加和各种不同的群体认同的外显化,重振“法律多元主义”的主张再次出现。其核心要求是承认某个具体群体的特殊需要应该得到法律的满足,并因此免除该群体成员遵守一般法律规范之义务。2Bryan S.Turner,Legal Pluralism: Freedom of Religion,Exemptions and the Equality of Citizens,in Rossella Bottoni,Rinaldo Cristofori & Silvio Ferrari eds.,Religious Rules,State Law,and Normative Pluralism—A Comparative Overview,Springer,2016,p.63.在主权国家要求所有公民遵守的国家法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来源于宗教、习俗或传统的规范秩序。在此背景下,有的国家采取的做法是,只要这些规范秩序不与国家法所保证之基本价值相冲突,即允许特定群体遵守其群体规范而非国家法律的请求。另一些国家则更进一步规定国家法原则上接受这些非国家的规范秩序。3See Bryan S.Turner,Legal Pluralism: Freedom of Religion,Exemptions and the Equality of Citizens,in Rossella Bottoni,Rinaldo Cristofori & Silvio Ferrari eds.,Religious Rules,State Law,and Normative Pluralism—A Comparative Overview,Springer,2016,p.63.但这种多元主义的主张出于两个原因很难作为讨论本文所引判例之指导理论。第一,它只是一个法律渊源方面的理论,并不必然与实用主义或象征主义相容或互斥。4人们往往认为,多元的法律渊源理论会倾向于承认宗教规范。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多元主义者会认为实用主义误解了司法的性质,主张《欧洲人权公约》及其议定书在多元法秩序中的优先性。说到底,实用主义和象征主义表达的是一种“人们用法律做什么”的立场,而不是“法律以何种方式存在”的立场。第二,法国法政哲学所秉持的共和主义立场根本不允许宗教规范进入司法,从而难以与多元主义立场相容。5关于这一点,还是请参见朱明哲:《司法中的政治理论脉络——从宗教符号判例看法国共和主义下的世俗性与平等》,载《法学家》2018年第2期,第88—105页。如果我们不打算挑战现代共和政体,那么讨论的核心其实是如何在世俗法律上处理源自宗教的规范。
实用主义的立场在把世俗国家的法律秩序看作唯一有效的规范体系前提下,试图提供世俗秩序与宗教的对话。那些出于宗教理由或义务而为的行为、仪式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需要涵摄入统一的国家法内方能确定其发生何种法律效果。实用主义认为一套规则体系对于某个共同体的生活有何价值并不重要,人们希望通过这套规则体系实现何种目的才重要。在休妻的例子中,实用主义关心到底妻子本人是否也希望一段不幸的婚姻尽早结束、她又是否得到了合理的生存照顾。它不关心外在于国家法的社会规范到底隐藏着何种价值观,它只关心这一套规范中所要求的那些行为模式到底如何用国家法的概念予以表达。换言之,实用主义最关心的是那些出于宗教、文化、传统等目的而为的行为在获得法律意义后,是否能实现行为者所欲实现的目的。比如说,实用主义避免争论在公立学校中佩戴面纱是否一定意味着拒绝男女平等之基本价值。它更关心一名学生个体到底是出于美学考虑、宗教信仰决定自己的服饰从而应该受到基本自由的消极保护,还是出于传教的目的从而应该受到教师的制裁,又或者是因为受到了来自家庭、社群等外在的压力而不得不如此而为从而应当获得公权力的主动救济。1Cf. Didier Leschi,« Problèmes contemporains de la laïcité publique »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 https://www.conseil-constitutionnel.fr/nouveaux-cahiers-du-conseil-constitutionnel/problemes-contemporains-de-la-laicite-publique].Consulté le 20 février 2018.
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同于多元主义的融合模式。宗教规范与国家法并非两种分离的、平行的法秩序。在国家法的视野中,宗教规范根本不是法。虽然这种姿态在名义上似乎对宗教采取了否认的态度,从而在表面上拒绝保护当事人依据其所选择的规范而自治的意愿,却在实质上更能有效保护个人和群体在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由。个中原因,乃是实用主义立场并不认为个人是共同体的当然成员、无法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自己的文化与宗教认同。相反,它承认人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认识改变生活计划的能力,也承认宗教本身便时刻处于变动之中。
象征主义的立场则不然,它坚持一种本质主义的宗教观。于是,宗教规范成了一套独立于国家法的秩序,而且这种秩序包含一套坚实的内核,既不会因为人们的意愿而改变、又无法与国家法相融合。尼布瓦耶(Marie-Laure Niboyet)对休妻制度的评价可以代表象征主义的立场:“作为穆斯林社会中女性传统上较低地位的产物,休妻制度把女性置于服从者的地位,并在她服从丈夫的时候正当化丈夫对妻子的控制,而在她不服从的时候正当化丈夫对妻子的驱逐。”2Marie-Laure Niboyet,« Regard français sur la reconnaissance en France des répudiations musulmanes »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vol.58,no 1,2006,p.41.他认为,休妻制度不仅让妻子从属于丈夫,而且其存在本身是穆斯林社会中女性地位较低的体现。女性地位较低的传统特征造成了休妻制度的出现,休妻的存在又导致歧视女性的传统无法改变,所以性别不平等是伊斯兰教的内在特征,许多类似的歧视性观念以相似的过程在法国的精英群体之中建构起来。3Cf. Julien Beaugé et Abdellali Hajjat,« Élites françaises et construction du « problème musulman » .Le cas du Haut Conseil à l’intégration (1989-2012) » ,Sociologie, vol.5,no 1,2014,p.31-59.既然如此,在男女平等已然成为法国法基本原则和欧洲基本人权范畴的时代,再适用与之无法相容的伊斯兰法规范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实,用世俗共和国的统一法秩序转化源自宗教的社会规范的趋势,也体现在最近法国法院的判例中。1Cf. Stéphane Papi,« Normes islamiques et droit interne en France : de quelques zones de confluences » ,Droit et société, no 88,2014,p.689-708.不同于上文所提出的国际私法问题,在这些诉讼中,法官的任务并非仅仅判断一个在外国有效的判决是否应该在法国的领土上发生同样的法律效力,还要判断依据宗教要求所为之行为到底有何法律意义。典型的例子是在前往市政厅登记、举办世俗婚礼之前,两名当事人先依据伊斯兰教的规定举办宗教婚礼,否则二人无法单独外出,也无法在对方家中居住。这样的仪式当然不会让双方在法律上结为夫妇,但法国法院仍不妨认为该仪式令双方构成了同居关系,有时也认为双方因为宗教仪式而订婚。于是,在举行了宗教婚姻而未前往市政厅登记的情况下,一方仍可以因为另一方的死亡而请求财产和精神的赔偿,亲友也可以因为订婚破裂而要求他们返还订婚赠礼。2Cf. Stéphane Papi,« Normes islamiques et droit interne en France : de quelques zones de confluences » ,Droit etsociété,no 88,2014,p.689-708.同样,在涉及麦亥尔(Mahr)的判例中,我们也看到欧美各国法院更注重的是这种类似嫁妆的制度在分配正义方面的功能,而非其神学意义。3See Pascale Fournier,Flirting with God in Western Secular Courts: Mahr in the West,2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Policy and the Family 67,67-94 (2010).一系列判例显示,虽然“宗教规范”不是法律规范,但是假装依照这些宗教规范所为之行为从来没有发生过,无异于一种“鸵鸟策略”,也不符合正义的要求。法官真正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这些行为翻译成世俗法律秩序的语言,并从国家法律的角度出发,赋予其意义。
相反,象征主义的路径不但无法与这一司法潮流保持一致,还会提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法律解决方式。2006年,一名穆斯林青年在圆房当晚向亲友宣告因为女方向其隐瞒了此前的情史与性经验而必须撤销婚姻,进而以《法国民法典》第180条第2段所列“关于配偶之重要特征认识错误”为由向里尔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婚姻,并于2008年取得了婚姻撤销的判决。4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Lille,1er avril 2008,n° 07-08458.然而,此判决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许多批评,司法部长要求检察官提出抗诉。最终,在双方都希望撤销婚姻的情况下,上诉法院判决婚姻依然有效。5Cour d’appel de Douai,Chambre civile 1ère,17 novembre 2008,n° 08-03786.究竟对妻子过往情史的无知是否属于法典中说的认识错误、究竟妻子隐瞒情史是否属于欺骗,在法律上自然可以争论。但初审法院的判决之所以引起如此争议以至于司法部长认为必须介入,无非是因为人们觉得宗教规范对女性婚前贞洁的要求侵犯了女性自主,从而不见容于男女平等的观念。普罗大众和司法机关捍卫普世人权的努力固然令人动容,然而从当事人的角度看,不惜动用国家司法资源也要阻止他们离开不幸的婚姻,实在令人费解。诚然,他们仍然可以选择通过离婚程序离开对方,正如那些发现实际上休妻判决对她们有利的妻子一样。但是离婚在任何一个法律制度中都是一个漫长而充满消耗的过程,我们不妨问自己:把国家的司法资源和人们的精力浪费在这些诉讼中,真的值得吗?
在社会分化加剧、群体身份认同的大时代背景下,6Cf. Tzvetan Todorov,La peur des barbares : Au-delà du choc des civilisations, Robert Laあont,2008,p.129.不难理解为何此前依据个案利益权衡来决定的休妻判决承认问题会引起激烈讨论。实用主义和象征主义体现了世俗法律体系处理宗教规范的两种极端方式。实用主义只把宗教规范以及出于宗教目的所为之行为理解为事实,否定任何群体豁免一般公民之守法义务的要求。象征主义则不但认为法律规范与宗教规范是两个无法交流的意义体系,更认为宗教规范是一个静态的、不能因为国家法而变化的系统。相比之下,还是实用主义模式更有利于世俗的国家法转化和吸收源自特定宗教的社会规范。
(二)世俗政治对宗教生活的祛魅
实用主义模式除了有助于国家法律秩序吸收和转化宗教等非国家的社会规范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功能,那就是实现世俗政治对宗教生活的祛魅,使任何活动都无法借宗教之名逃逸于公共权力的监督之外。目前人们往往从美国的司法实践出发,认为世俗国家理念主要是避免垄断世俗政治的国家干涉属于精神领域的宗教活动。1参见李松锋:《政教分离的准绳——“莱蒙法则”的前世今生》,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第59—69页;刘碧波、李一达:《从教派之争到文化战争——美国政教分离的宪法实践》,载《学术月刊》2017年第1期,第92—103页。至于什么是宗教在法律上的核心含义,又有两种主流观念。第一种认为宗教的要旨在于个人的良心自由;第二种则认为宗教涵盖了一系列与之相连的活动,包括信仰、结社、表达,乃至经营行为。2See Cécile Laborde,Religion in the Law: The Disaggregation Approach,34 Law and Philosophy 581,581-600(2015).联系世俗国家的理念,两种观念都认为存在一些领域或活动,因为与宗教相关,所以免于国家的审查和干预。流行的观念假设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存在清晰的区隔,国家权力的行使停留在公共领域,宗教则作为个人事务,在私人领域获得保护。3Cf. Olivia Bui-Xuan,« L’espace public : l’émergence d’une nouvelle catégorie juridique? Réflexions sur la loi interdisant la dissimulation du visage dans l’espace public » ,Revue française de droit administratif, no 3,2011,p.551-559.流行的观念还假设在世俗政治与宗教信条之间不存在对话的空间,所以国家只能听任宗教自我发展,只有在出现了违法事由的时候才有权干涉。
上述两种流行的假设在最近的法律实践中摇摇欲坠。一方面,国家权力可以干预的“公共空间”在立法和司法中一再扩大,以至于不但包括政府和公立学校,还包括了沙滩、道路,并在一定情况下包括了私人机构甚至私人住宅。4参见朱明哲:《司法中的政治理论脉络——从宗教符号判例看法国共和主义下的世俗性与平等》,载《法学家》2018年第2期,第88—105页。如此一来,我们便发现了一种空间公共化倾向:只要不是彻底对外封闭的排他性场所,都可能因为其成为不同的公民展开互动、形成公共意见之场所,而变成象征性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开始实质性地审查宗教因素与现代政治原则的符合程度,判定罩袍5Conseil d’État,27 juin 2008, 2ème et 7ème sous-sections réunies, no 286798.和休妻制度置女性于受支配地位的判例都体现了国家对宗教事务的评价。既然国家可以单方面决定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的分野,那么指望公私领域的划分能够有效限制公权力、保护个人的自由本身就不现实。
换言之,传统观念中认为把世俗政治与宗教生活完全隔开的墙已经不复存在。与上文所说国家法秩序对宗教规范的评价与规制一脉相承的是,人们不再视宗教为神秘的、不可知的、完全独立于世俗政治的领域,以宗教信条之名所为之行为也不再仅因此前日益扩大之宗教自由理念而避免国家法秩序的评价。诚然,在欧洲人权法的框架内,国家直接干预教会组织仍不合法。但现在完全可以想象国家与宗教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对话关系,对话的空间包括但不限于司法场域。1Cf. Pierre Bosset et Paul Eid,« Droit et religion : de l’accommodement raisonnable à un dialogue inter normatif? »,Revue juridique Thémis, vol.41,2007,p.513-542.世俗政治与宗教生活之间良性的对话关系应该既能够回应不同群体对法律上实质平等保护的要求,又能够实现国家无差别适用法律的义务。
象征主义的路径虽然承认宗教属性无法阻却世俗政治对某种社会机制的评价,却无法满足对话的需求。那种静态的宗教观和一元的身份认同观甚至会加剧不同群体的冲突。现在法国乃至全欧洲都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基督教是与现代共和民主相容的宗教,而其他宗教不是。保守主义者强调:因为宗教原因,外来移民不可能接受共和价值观,所以不会是好公民。2参见崇明:《教法与自由——当代欧洲的伊斯兰教挑战》,载《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第132—151页。进步主义者则要求:对西方式民主的否定内在于他们文化,我们需要包容。两方虽然结论不同,错误却是一样的:他们假设“宗教”和“文化”都是僵化且无法发展的事物,而且可以简化为一两种信念和实践。以上同样是持象征主义法律观的学者常犯的错误。他们轻易把普遍人权、性别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观与欧洲文化相连,并认为外来文化是传统的、地域性的、歧视性的、不自由的。3Cf. Ali Mezghani,« Quelle tolérance pour les répudiations? »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 vol.58,no 1,2006,p.61-71; Marie-Laure Niboyet,« Regard français sur la reconnaissance en France des répudiations musulmanes »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vol.58,no 1,2006,p.27-46; Fatna Sarehane,« La répudiation,quels obstacles pour les Marocains résidant en France? (Exercice au Maroc et reconnaissance en France) »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vol.58,no 1,2006,p.47-59.不管有心还是无意,当尼布瓦耶指责穆斯林社会有把女性置于受支配地位之传统时,她似乎忘记了性别平等即便在西欧也是在20世纪通过一系列渐进法律改革落实的法律原则。相反,她暗示了存在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尊重女性,另一种则不然。于是,捍卫一种确实值得珍视的价值就在学术话语中转化成了在“他者的生活方式”面前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斗争,并进一步演变为在“他者”的威胁面前捍卫“我们”的斗争。4类似的转化,参见Julien Beaugé et Abdellali Hajjat,« Élites françaises et construction du « problème musulman».Le cas du Haut Conseil à l’intégration (1989-2012) » , Sociologie, vol.5,no 1,2014,p.31-59.如果一种宗教意义体系的发展取决于其传统而不取决于今天的信徒们的理解,那么无论国家对这一体系持有何种评价,人们都无法改变其内容。其结果就是对宗教的静态理解。所以,象征主义法律观其实仍然视宗教为绝缘于世俗政治自主发展、不能为国家所渗透的一个整体。
实用主义路径则更能回应两个不同领域之间对话的需要。与其视宗教为一个以个人信念为基础的、无法分割的、静止的整体,不如承认宗教具有多个面向,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产生不同的认知。 在面对以宗教为名的诉求时,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此种诉求在何种维度上具备宗教的属性,然后决定世俗政治可以与之对话的限度。如在休妻判决的承认上,涉及的本就是安排人际生活关系的社会机制,摩洛哥或阿尔及利亚法院的判决本身又是根据其本国的成文法而为,那么国家法律秩序作为另一种规制社会生活的机制,干预的限度自然可以更大。所以,无论认为休妻制度本身违背了性别平等,还是决定依据个案对妻子利益的保护程度而判决,均可成立。只不过实用主义路径会选择后者而已。类似的还有可以类比嫁奁的麦亥尔制度。换言之,实用主义问的是:“如何对待国外的判决能更好地实现两性的实质平等?”如果一个看上去歧视妇女的判决在个案中恰恰满足了受歧视一方的需求,不予承认反而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做法。而在公立学校是否可以佩戴表现宗教归属之饰物的案件中,依据教义穿着某一类型的服饰就涉及身份认同和道德义务的层面,需要更谨慎的权衡。在身份认同方面,需要考虑是否有必要坚持单一的公民身份认同,还是说可以容忍多重身份认同的可能性。1关于多重认同讨论的新发展,参见Will Kymlicka,The Rise and Fall of Multiculturalism? New Debates on Inclusion and Accommodation in Diverse Societies,61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97,97-112 (2010).至于道德义务层面的问题,则需要更深入地理解人们选择某一种服饰的动机到底是出于美学考虑、义务感还是社会压力。可见,实用主义的路径虽然无法提出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却为更复杂和深入的对话创造了空间。
五、结论:艰难的融合
人权法往往发挥着限制国家权力的作用。但晚近的发展也表明,以人权的名义同样可以要求公权力有所作为,避免个人成为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受害者。最近宗教在欧洲法学界引起的关注反映了身份认同的政治在世俗法律秩序与宗教之间产生的紧张关系。随着全球治理的发展,非国家行动者的作用和地位愈发受到重视,除了国家公民身份以外的多元身份认同也本应水到渠成地发展为当代政治的基本元素。然而在关于宗教仪式和服饰的司法判决中,我们却更多看到法国共和主义传统所坚持之单一身份认同悄然复兴。与此同时,对外来文化和宗教采取片面、单一、僵化理解的主张也出现在司法之中,强化了教条的法律问题解决模式,而阻止人们以更灵活、更务实的态度,从当事人利益平衡的角度解决社会纠纷。在我们讨论的判例中,可以看到,对待休妻的不同方法都可以在教义学上找到足够的理据。所以,起决定作用的只可能是法教义学之外的因素,比如主导规则应用的不同法哲学立场。当解释者对公正的分配结果、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持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法律规则和法教义学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工具以实现其目的。易言之,即便面对的是同样的规则和技术,法律观不同的法学家所为之法律解释仍可大相径庭。
在这样强调不同意义系统之间的对抗性和优劣高下之别的时代背景下,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都岌岌可危,建立在博爱理想上的社会融合显得尤为不易。关心妇女地位不再是一种领导解放的运动,而成了一种标榜自身优越性的方式。对于休妻判决之承认问题的司法论证体现了法律象征主义的兴起,其代价是关注具体个案之分配结果的思维方式让位于“我们”和“他者”的区分。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共同点是把宗教规范理解为一种无异于其他社会规范的意义系统,并且尤为强调其作为身份认同和社会组织的面向。但实用主义对国家的世俗法律体系渗透与转化作用于宗教规范更有信心,所以也更有利于把宗教生活置于世俗政治生活之中。相反,教条的象征主义路径则让我们只能对宗教实践采取或听之任之、或坚决打压的极端态度,不利于现代公民社会的整合。与此同时,实用主义对个人的多重身份认同采取了更现实的开放态度,而非强迫个体只能选择单一的国民身份。所以,相比于象征主义,实用主义更能促进两种不同规范体系之间的对话而非对抗。从法国的语境中看,实用主义也是更能够实现“博爱”承诺的路径。确实,相比于“自由”和“平等”,人们往往忽视这一同样铭刻在所有公共建筑之上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