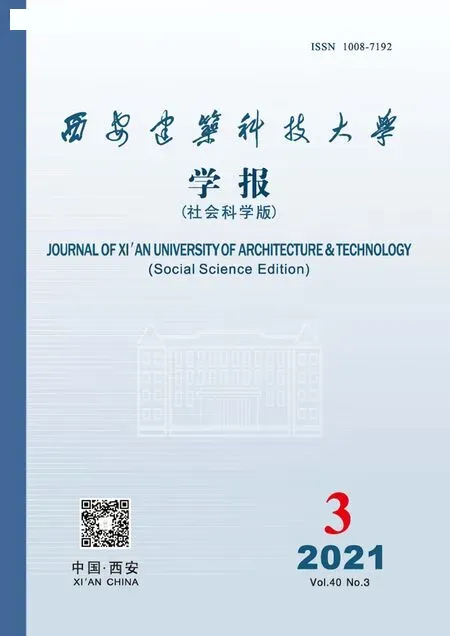犹太难民视角下的上海记忆与中犹文化交融
——以自传《上海船票·流亡隔都》为例
2021-12-04唐洁
唐 洁
(西安外国语大学 欧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奥地利犹太女性弗兰西斯卡·陶西格(Franziska Tausig,1895-1989)曾在二战期间流亡上海,回国后在《社团》《维也纳工人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关于流亡经历和回忆上海的文章。1987年,她根据流亡经历创作的自传《上海船票:一个维也纳女人的逃亡和避难》由维也纳社会评论出版社付梓出版。1989年,陶西格在维也纳去世。2007年,维也纳米雷娜出版社将其自传更名为《上海船票·流亡隔都》((Shanghai Passage·Emigration ins Ghetto)再版,这一版本更新了部分内容,并增加了新版前言和作者之子奥托·陶西格①为自传撰写的后记。为了纪念弗兰西斯卡·陶西格与奥托·陶西格母子,2013年维也纳维登区(第四区)设立了陶西格广场。
德国当代女作家乌尔苏拉·克莱谢尔(Ursula Krechel)的长篇小说《上海,远在何方?》(Shanghai fern von wo?)以弗兰西斯卡·陶西格为原型,融合虚构元素塑造了女主人公陶西格夫人。该小说以极富诗意的语言和打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深受评论界好评,接连荣膺约瑟夫·布莱特巴赫奖、德国批评奖莱茵高文学奖等众多文学奖项。与之相比,《上海船票·流亡隔都》更为真实地还原了陶西格夫人的人生经历。
一、犹太难民自传《上海船票·流亡隔都》
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爆发后,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惨遭纳粹迫害,被迫逃亡国外。美国法国等众多西方国家,面对纳粹惨绝人寰的暴行,采取了限制性移民政策,几乎令欧洲犹太人陷入绝境。中国上海,这座当时被置于殖民管辖且不需要签证的东方大都市成为犹太人最后的避难地。从1938年到1941年,大约有两万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远渡重洋来到上海,尽管他们在贫困与饥饿中苦苦挣扎,生活与文化的巨大差异使他们无所适从,但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犹太人的援助下,犹太难民在上海得以幸存。
二战结束后,为了纪念流亡上海的艰辛岁月和战争中遇难的亲友,不少幸存者开始书写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他们想要将独一无二的流亡经历和在远东经受的创伤传递给下一代以及感兴趣的读者。从二战结束至今,已有30余部犹太流亡难民自传问世。《上海船票·流亡隔都》是其中颇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这部自传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弗兰西斯卡·陶西格既是叙事者,也是主人公。她用细腻质朴、略带幽默的语言描绘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塑造了一位勤劳乐观、坚强勇敢的独立女性。陶西格夫人1895年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蒂米什瓦拉,从小与父母居住在维也纳,家境优渥。原本幸福的生活在纳粹德国不复存在。面临死亡威胁的陶西格夫妇最终流亡上海。在上海的漫长岁月中,夫妻俩忍受着与儿子骨肉分离的痛苦,在异国他乡经历着种种磨难。面对陌生的环境,丈夫日益消沉,最终客死他乡。陶西格夫人独自艰难熬到战争结束,并最终回到满目疮痍的故乡维也纳。
《上海船票·流亡隔都》共分为三章:“无忧无虑”的时光,自1938年以后的故事以及上海岁月。第一章讲述了弗兰西斯卡从出生到流亡上海之前的家乡生活。弗兰西斯卡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与年轻的匈牙利律师阿拉达·陶西格一见钟情并结为夫妻。短暂的甜蜜之后小家庭卷入了一战的旋涡。丈夫奔赴前线,在一场战役中被爆炸击中造成严重耳疾。弗兰西斯卡冒着生命危险探望受伤的丈夫,不久后将丈夫接回维也纳。之后陶西格夫妇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并在维也纳度过了二十年衣食无忧的美好时光。第二章描写了陶西格一家在纳粹统治下的悲惨遭遇。为了躲避纳粹铁蹄的践踏,弗兰西斯卡将儿子奥托送上了由基督教教友会组织的逃往英国的火车。奥托在此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也开始了与母亲的八年之别。正当弗兰西斯卡不停地寻找出逃机会时,她的丈夫被纳粹从家里逮走了。这使得她的处境更加恶劣,心境更加绝望。对于身处险境的犹太人来说,外逃的船票就像茫茫苦海中的救生圈。弗兰西斯卡花高价买来了一张伪造的船票,使丈夫得以暂时脱离危险。陶西格夫妇不断寻找离开维也纳的出路,但始终遭遇“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遇。在弗兰西斯卡对未来绝望之时,她在旅行社橱窗里偶然发现前往上海的“乌萨拉莫号”邮船还有最后两张船票,便倾其所有将其买下。弗兰西斯卡在自传中写道:“现在我把‘天大的幸运’——两张前往上海的船票,紧紧握在了手中。”[1]60在《逃亡与拯救——二战中的犹太难民和上海》一书中也有关于“乌萨拉莫号”邮船的论述:“有两艘专门租赁的德国邮船将运送犹太难民经南非和爪哇来到上海。这一路线的选取是为了避免支付苏伊士运河费用,因为这一费用只接受英国英镑,不接受德国马克。6月28日德国乌萨拉莫号邮船到达的459名难民也得到了安置。这批人中有114对夫妇,150名孩子,142名单身男子和33名单身女子。”[2]77-78其中也包括陶西格夫妇。1939年,经过9个星期不同寻常的海上之旅,弗兰西斯卡和丈夫终于抵达遥远而陌生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第三章“上海岁月”讲述了陶西格夫妇在异国他乡生存的艰辛。为了养活生病的丈夫,弗兰西斯卡在“科里布瑞”西餐厅烤制维也纳苹果卷和萨赫蛋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犹太难民的境遇雪上加霜,在犹太人被迫迁入虹口隔离区之后,弗兰西斯卡原先工作的西餐厅倒闭。她在犹太人隔离区租下一间面包房分店,然而面包房的生意并非一帆风顺,故事情节一波三折。陶西格先生病情逐渐恶化并最终离世,这彻底击垮了弗兰西斯卡,但是想到远在英国的儿子,弗兰西斯卡不得不继续生活下去,她在医院厨房做帮工直到回国。二战结束后,弗兰西斯卡在儿子的劝说下最终决定回到家乡维也纳,成为第一批返回欧洲的犹太难民。1947年,弗兰西斯卡在朋友们的欢送中踏上了返回欧洲的“猎鹰号”军舰,告别了居住八年的第二故乡上海。经历了漫长的旅途终于抵达维也纳火车站,弗兰西斯卡百感交集。
二、自传中的上海城市记忆
犹太人流亡上海的历史在弗兰西斯卡·陶西格的自传中得以回忆、解构与重构。德国学者瓦格纳·艾格尔哈夫指出,自传并不完全等同于过去生活的写照,它更多的是在文本基础上对过去的构建,这种构建从它的叙事形式中获得大部分的重要意义。作为文学记忆体裁之一的自传不仅与个人记忆,还与文化记忆紧密相关[3]217。作为时代见证者,犹太难民对亲身经历的故事进行了文学叙事,将个人记忆用文学形式传递给后世。与此同时,犹太难民的个人记忆往往以某种形式从集体记忆中提取,并受到社会群体集体记忆的支配。作为文化记忆的媒介,自传对上海历史形象、价值结构以及自我和他者的想象进行了解构与修正[4]375。本文的立足点并非对上海进行历史叙述,而是作为东方“他者”的上海在犹太难民自传中如何构建和重现。
弗兰西斯卡以下面这段叙述开启了对上海的记忆:“上海岁月让我饱尝人世间的苦涩滋味。日子就像高脚杯,盛满了残酷无情的命运之酒,直到我饮尽最后一滴。”[1]99对犹太难民而言,这段饱含伤痛的经历注定会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上海作为最后的避难地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在此之前,大部分犹太难民都未曾来过中国。“上海”这个名词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也是一个差异性的、边缘化的他者空间。在弗兰西斯卡未到达上海之前,她认为身无分文且毫无生存技能的自己根本无法在千百万的中国人中生存下去;而她的丈夫——一名匈牙利律师——在中国也毫无用武之地。经过九个星期的海上航行,搭载着四百多位欧洲犹太难民的轮船终于接近了目的地。弗兰西斯卡以流亡者的视角审视上海这个陌生的世界:“之前深蓝色的海水,现在突然变成了脏兮兮的黄褐色。”[1]91当难民们获悉可以上岸时,不由得欢呼雀跃起来。弗兰西斯卡第一次见到“奇怪的墨汁瓶和细如发丝的毛笔”[1]92。
抵达上海后,弗兰西斯卡被移民局登记为女厨师并幸运地获得了一份工作,因为她会烤制真正的维也纳苹果卷和萨赫蛋糕。她开始接触中国贫苦大众的日常生活,并对上海有了进一步的认知。每天凌晨五点,西餐厅老板会接弗兰西斯卡去市场采购食材。她在市场上看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食物:“泛着银光的小鱼、埋在土里的鸡蛋、堆积如山的菠萝、干瘦如柴的火腿等等”[1]101。在弗兰西斯卡看来,中国市场是“一副热闹非凡的宏大场面”[1]192。与此同时,她也目睹了成群结队沿路乞讨的乞丐,“每个乞丐手上都拿着一个破旧的讨饭碗,上下来回晃动。人们扔给他们肉、鱼的下脚料、一把米饭或者是半腐烂的水果。一口铁锅和身上背着的一个竹席就是这群乞丐的全部家当。情况稍好一点儿的乞丐会随身携带一个大的保温壶。我从未见过像中国一样有这么多热水壶的地方。它们成为生存必需品。对于人们而言,半瓢热水比整顿饭还要重要。谁的碗里盛有米饭,就会再浇上一些热水。我看见许多人用手指将生肉或者生鱼块从垃圾里拣出来放进锅里然后狼吐虎咽地吃下去。这种贫穷难以想象,但是人们却必须承受。老弱病残沿街乞讨,大批死亡”[1]102-103。彼时的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整个城市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造成了上海历史上空前的大劫难,穷苦老百姓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由于饥寒交迫,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行乞为生,还有些人铤而走险偷抢害命,许多女性沦为娼妓。上海沦陷后这些混乱的社会状况通过弗兰西斯卡笔下的细节描写得以真实再现。
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曲折,犹太难民们逐渐适应了上海的生活环境,在基本解决温饱之后,便开始试图在这个客居地构建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生活氛围。犹太难民乔治·赖尼希在回忆录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难民们虽被本地文化逐渐融化,但也极力保留他们源自欧洲中部的生活方式。”[5]89犹太难民们在虹口提篮桥地区开办了许多咖啡馆、餐厅、杂货店、面包房、理发店、鞋帽店等,一时间虹口地区德文招牌林立,奥式露天咖啡馆也出现在街头和屋顶露天平台。中国的土地上生发出一种柏林和维也纳亚文化,“小维也纳”和“小柏林”由此而生。在被迫迁入虹口隔离区后,弗兰西斯卡失去了原先的工作。她被阴险狡诈的亚美尼亚人玛通茨欺骗,被迫租下了一间面包房分店,取名“欢迎面包房”。精心装饰后的面包房充满浓浓的维也纳风情,犹太难民惊喜地喊道:“这不就是上海的得美尔甜品店吗!”[1]117面包房门庭若市人来人往,不仅吸引了犹太难民,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前来品尝维也纳的咖啡和甜点,弗兰西斯卡和丈夫也因此收获了许多友谊。
自传中的上海记忆也体现在反复提到的亚热带炎热的气候上。每天晚上陶西格先生都会在餐厅门口等弗兰西斯卡下班,然后两人一起去黄浦江边散步,享受江风吹来的丝丝凉意。“水面上帆樯栉比,覆盖整个江面。就像在巴达维亚,人们干着脚就可以走到河对岸。往来船只千里不绝,气势如虹。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令每个人都心情愉悦,所有人都涌向江边。那里甚至有一个小公园和一艘报废的旧船,在船上建有一个茶馆。”[1]104陶西格夫妇在面包房不分昼夜地工作,偶尔也会早点关门去江边散步,因为客人们十点多就离开了。“这个得归功于炽热的夏日夜晚,人们在封闭的房间里几乎无法度过。”[1]119就算穷苦中国人家也会有电风扇,因为上海的夏天到深夜依然酷热难耐。当弗兰西斯卡被玛通茨先生解雇时,玛通茨让人把她房间里的电风扇拆除。弗兰西斯卡写道:“他的做法无异于用东西堵住一个原本就即将窒息的人的喉咙。”[1]148
三、自传中的多国人物记忆
上海记忆不仅存储在城市空间的文学叙事中,也蕴涵在对生活在同一时空下的25 000名苦难同胞们的情感回忆里。德国奥地利犹太流亡者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如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理发师、建筑师、记者、作家、演员、画家、音乐家等,他们在困难中相互扶持,同舟共济。犹太难民在极其艰苦的岁月里,仍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追寻一种根植于本我文化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尽可能地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6]131。美军的空袭结束之后,弗兰西斯卡工作的医院厨房上演了“一生中最值得关注的宴会”[1]141。“男士们,每天一律带着粗糙的亚麻围裙干活,今天都穿上了黑色的西装甚至是晚礼服。几乎所有人都有金色的袖口纽扣,真丝的领带甚至金色的烟盒。女士们身着小晚礼服或者下午穿的连衣裙。所有人都在手艺精湛的维也纳理发师那里做了发型,他在上海也经营着一家不错的理发店。人们几乎认不出这个精心打造的团队,旧貌换新颜。”[1]142
犹太难民在上海创作了许多具有维也纳风格的轻歌剧等各种剧目。通过建立戏剧社和创作鲜明时代特征的戏剧作品,犹太艺术家们鼓励困境中的上海犹太难民坚定生存意志,维持和修复自我社会文化身份。1938年,犹太业余剧社在上海建立:“新组建的剧社积极创作意第绪语的轻歌剧和音乐剧,因为轻歌剧这种半古典、半通俗体裁比音乐会和歌剧在犹太难民中更受欢迎。”[7]204犹太难民在业余时间自导自演轻歌剧,通过这种方式化解精神苦闷、追忆故土情怀。“吃完饭大家把桌子打扫干净,将值钱的东西放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开始卡巴莱表演和跳舞。鲁迪模仿了一个宴会之后想要借给邻居假牙的妇女。他站在那里,吧嗒嘴、咕哝、抱怨,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这里不是维也纳,忘记了战争的存在,也忘记了他不是那个真正的摩泽尔。”弗兰西斯卡觉得那个夜晚十分幸福,在没有美军轰炸的璀璨星空下,人们可以做一个有关“回家的梦”[1]143。
在漫长的流亡岁月中,陶西格夫妇还结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上海洋人”:心地善良的白俄难民斯克里亚宾“阁下”、阴险狡诈的奸商玛通茨先生、为人仗义的瑞典船员汉内斯、乐于助人的维欧医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匈牙利人特里比西·林肯、通情达理的工部局官员凡·惠更斯先生、沉静寡言的高本夫妇、收养穷人小孩的犹太难民等等。弗兰西斯卡所描绘的生存故事不仅生动地刻画出德国奥地利犹太流亡者的众生相,并且折射出一幅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全景图。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汇集在上海,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汇造就了上海“华洋杂糅”的城市性格。
四、自传中的中犹文化交融
在共患难的岁月里,犹太难民与中国百姓相识相知、和睦相处、真情相助。弗兰西斯卡在自传中讲道:“我丈夫总是将多余的面包分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孩子们称他为‘善良的面包大叔’。几百人来询问他的情况,当大家得知他离世的消息后,许多人都潸然泪下。”[1]131在《上海船票·流亡隔都》对文化记忆的书写中不乏对旧中国传统女性和传统习俗的记叙。很多年过去了,弗兰西斯卡并没有忘记她与一位中国女孩结下的友谊,这段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更加刻骨铭心。女孩因家境贫寒被父母卖给妓院,弗兰西斯卡将这个美丽的女孩称为“娜芙蒂蒂”:“高颧骨和黄皮肤构成了女孩棱角分明的侧脸轮廓,亚光面的中国丝绸长裙凸显出女孩高贵和苗条的身材,这让我不禁想起那位年轻的埃及女王,她的美丽在几千年后仍让人无法忘记。”[1]110女孩由于强烈的自卑心而不敢与弗兰西斯卡说话,当弗兰西斯卡和她讲话时,她用洋泾浜英语说道:“女士,请您不要跟我说话。我太卑贱了。”弗兰西斯卡不顾旁人的眼光坚持和她成为朋友。弗兰西斯卡的丈夫去世后,“娜芙蒂蒂”陪她度过了人生中最孤单的日子。中国人对逝者传统的悼念方式在自传中反复出现:“娜芙蒂蒂”将纸钱和其他用纸糊的东西点燃,充满敬畏地向死去的陶西格先生深鞠躬。回国后的弗兰西斯卡听说“娜芙蒂蒂”自杀的消息后,在维也纳选择了同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位美丽的中国女孩。在犹太难民与中国邻居接触的过程中,文化碰撞和误解不可避免。邻居的妻子沈荷绿因不能生育四处寻医问诊,然而街里的中国医生只通过眼睛诊断,开的药方则是加入蟑螂的药草。弗兰西斯卡好心找来妇科医生,沈荷绿的丈夫却不能接受陌生男子为妻子做妇科检查,治疗以闹剧收场。沈荷绿最终遭到了丈夫无情的抛弃,含泪目睹丈夫张灯结彩地迎娶新妻。通过对“娜芙蒂蒂”和沈荷绿两位旧上海传统女性生动形象的刻画,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女性在旧社会毫无地位的生存现状和女性顺从式付出的封建礼教束缚,从中折射出中国传统家庭观念。
当得知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时,弗兰西斯卡与中国人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胜利,伟大的胜利终于来了。大部分房子都太小,不能举办庆祝活动,但是中国人很乐于帮助我们。”[1]150岁月流逝,犹太难民早已将这座陌生的他乡城市视为第二故乡,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在离别之际萦绕心头。二战结束后,犹太难民纷纷开始寻求可以永久居留的新家园,大部分人选择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四国,很少一部分人回到欧洲。弗兰西斯卡拒绝了多位犹太难民的追求,因为她心中始终惦念着多年未见的儿子。长久以来,正是这份深深的思念之情给予弗兰西斯卡生活下去的勇气,维也纳成为弗兰西斯卡最终的归宿:“如果我去了澳大利亚、美国或者其他地方,那我一定已经窒息而死了,因为我儿子回到了维也纳。我会因为永远的思乡之痛离开人世。”[1]1481947年,弗兰西斯卡登上了返回欧洲的轮船,告别了居住八年的城市。医院厨房所有人前往港口送别。轮船启航时,朋友们一起合唱古老的送别歌曲“明年再相见,耶路撒冷再相见”[1]179。故事的结尾令人动容,儿子与母亲见面却不敢相认,年轻人礼貌地问道:“仁慈的女士,请问您是我的母亲吗?”[1]192弗兰西斯卡在自传结尾写道:“这个问题为我的流亡生活画上了句号,也成为故乡新生活的开始。”[1]192
五、结 语
作者在回忆最为艰难的虹口隔都岁月时说道:“生活越是艰难,生命就越渺小,留下的回忆越来越多。我们中许多人更多的是生活在回忆里。这些回忆不会随着时间的磨灭而变模糊。正好相反,人们越是打磨它,它越加光芒四射。”[1]113《上海船票·流亡隔都》首版发表两年后,弗兰西斯卡离开了人世,没能再回到记忆中的故土——上海。她的自传作为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对城市空间、人物、气候等方面进行了文学书写,解构和重构了上海的历史形象,重新塑造了自我和他者的想象,承载着上海犹太难民的集体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