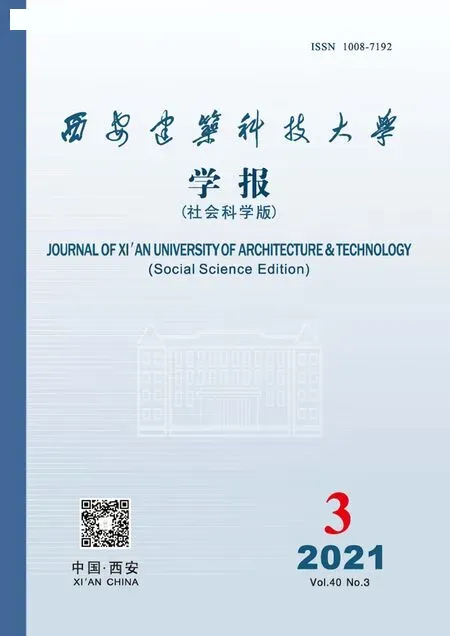文化诗学视域下贾平凹乡土叙事探究
——以《山本》为例
2021-12-04刘秀哲
刘秀哲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作为陕西的本土作家,贾平凹对甘陕大地有着浓郁的故乡情结与执着之爱,而甘陕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奇异的民俗风情也为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在《山本》中,作者聚焦于巍巍秦岭,通过对乡土文化、民俗文化、宗法文化的叙述,为读者构建出一个深度的精神空间,即涡镇人民在血雨腥风中所铸就的拼搏精神。而在对这一精神空间审视的过程中,也让读者领略到其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同时,作者将秦岭的“文化意蕴”与文学的“艺术价值”巧妙结合,使文本升华到了文化诗学的高度,即“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俗气的、丑恶的和反文化的东西”。因此,从文化诗学的角度反观贾平凹的乡土叙事便使其创作显示出独具特色的文学品格。
一、社会生活化的乡土叙事
《山本》以亘古苍茫的秦岭为依托,以风云诡谲的涡镇为基点,讲述了各色人等在乱世之中的命运沉浮,而这一切之于苍茫巍峨的秦岭就如同沧海一粟,最终化为乌有。作者以灵动的笔法将秦岭博物风情通过森罗万象的世事传递出来,又将世事置于秦岭这一壮阔的背景中,“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悲喜剧”。恰如作者所言:“秦岭里就有那么多的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1]541在动荡不安的人世与巍然屹立的秦岭中所蕴含的是命运的无常与自然的永在,更蕴含着多元而厚重的乡土文化、民俗文化、宗法文化。作者将这种文化无限地延伸、拓展,为乡土叙事开辟了深层而广阔的意蕴空间。
乡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在乡村世界中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山本》将全面而丰富的民俗文化、宗法文化寓于乡土文化之中,通过社会生活化的叙述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涡镇世事的改变与陆菊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起因便是十三年前那三分陪嫁的胭脂地。由最初风水先生对这三分胭脂地的预言,到陆菊人将其作为自己的陪嫁,再到井宗秀父亲阴错阳差的葬于此处,以及随后井宗秀的发迹均与此相关。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关于这三分胭脂地的传说并未就此而止,文本在叙述的过程中多次提及此事,它将井宗秀的命运、涡镇的盛衰全都牵系于此。这种风水文化在乡村社会十分常见,特别是在文本所叙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平普遍低下,对外界的自然现象认知有限,所以对风水文化深信不疑。于他们而言与其说这是一种迷信,莫不如说是一种信仰,正因为陆菊人深信风水先生的所说:“啊这地方好,能出个官人的。”[1]002并在井宗秀父亲葬于此处后将这一“机密”告知井宗秀,从而激起了井宗秀的雄心壮志,最终井宗秀也成功的证实了这一预言,由一个普通画师变为了涡镇的“霸主”。从这一点而言,风水文化在乡土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仅凭风水先生的一句预言就能够成就井宗秀的一生显然是无稽之谈,它所起到的作用是支撑井宗秀在人生的道路上奋斗不止的信念,给予了他奋斗的勇气,是一种精神力量。但这种精神力量又只是一个起因,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神秘文化推动着井宗秀走向人生之巅。
《山本》中对于神秘文化的建构是纷繁而复杂的,然而又不是无中生有的杜撰,它们作为风水文化的补充具有清晰的指向性,既指向文本以内的世界,也指向文本以外的世界。作者以大量的笔墨对这种神秘文化进行了描写,如那棵高大而挺拔的皂荚树,它作为涡镇的象征屹立于街巷之中,见证了涡镇由萧条破败走向光鲜亮丽,但在熊熊烈中火皂荚树被付之一炬,也暗示了涡镇的风光不再,既指物也指人,伴随着涡镇的衰落是井宗秀的离世;再如周一山以井宗秀的“军师”角色出现在文本中,此人并非有手眼通天之力,而是因为他能够通灵,通过梦境能够未卜先知,并且能够听懂禽言兽语,这在井宗秀实现“霸主”的路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仅成就了井宗秀的传奇人生也使自己煊赫一时。作为神秘文化的代表非陈先生莫属,他将世事玩弄于股掌之中,在他身上既体现了儒家的仁义,又彰显了道家的风骨。不问世事不涉红尘的陈先生如同《白鹿原》中的朱先生一般,能将世间的一切看淡,也能够一语惊醒梦中人。在小说的结尾,陈先生用一句话将人世的一切沉浮俯仰归因于“时运”,在突出主题意蕴的同时又与前文中的风水文化互相照应,“二者神秘而又难以言明的关系构成了《山本》最基本的故事基础,也成为其基本主题之一”[2],可见作者对神秘文化的叙述更多地指向了文本以内的世界。对于文本外部世界的指向更多地凸显在他对秦岭民风民俗的迹化,将这些神话传说由外在的形态转化为内在的文学性书写,在此基础上实践了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
涡镇作为秦岭的一个缩影,涵盖了秦岭的万事万物,在这一生死场中不仅展现了人性的较量,也蕴含了丰富的民俗文化。为秦岭作志原为作者的初衷,既然是秦岭志就必然会包含秦岭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风土人情,在文本中作者借麻县长这一人物对秦岭大地做了细致的描摹,又通过百姓的日常生活展现了这里的烟火气息。在官场上举步维艰的麻县长,只能将自己的情趣寄托于秦岭与秦岭中的风物,他留意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为官数载却无所作为的麻县长想在这世间留下些什么,那便是自己所撰写的《秦岭志草木部》与《秦岭志禽兽部》。然而纷飞的战火使涡镇变得满目疮痍,麻县长的两部著作也荡然无存,但无论秦岭志的存在与否,都不能抹杀秦岭的存在;无论世事如何沧海桑田,秦岭的黛青山色苍茫依旧。诚如陈先生所言“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的一堆尘土”,在变与不变中静观着世间的离合悲欢和人事的兴衰荣辱。此外,作者对秦岭脚下百姓日常生活的描摹也是可圈可点,文本充满了地道的陕西方言口语,如写人们“圪蹴在那儿吃饭”;写土匪“把吃饭叫填瓢子,把路叫条子,向导叫带子,人质叫票子,打人质叫溜票子,打死了叫撕票子”。写陕西的各色民俗,如对民间手艺铁礼花的叙述,对姑娘婚前各种习俗的刻画,对人死后各种礼节的描写。所以作者在文本中所展现的除了亘古不变的秦岭与秦岭中的花木草石,还呈现了这方土地上的饮食男女及风俗习惯。具有秦岭风味的自然和人事,构成了这一独特而又平凡的世界,成为这段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爱情作为文学叙述的永恒主题,其中不仅蕴含着深刻的人性思考,也蕴含了深厚的宗法文化。宗法文化在中华大地绵延数千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也影响了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山本》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陆菊人与井宗秀那种“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愫,三分胭脂地将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牵连起来,但二人却并未越雷池一步,“一直是扑面而来的游丝般的不即不离的关系——是亲密、亲情、暗恋、暧昧似乎都有”[3]。正是这样一种韵味悠长的情愫,让我们看到了宗法文化对于维系社会结构稳定的重要性,作者将二人的关系从最初的相识叙述到最终的相知,却始终没有让读者见证他们的相爱,可见这份情愫在作者心中同样是神圣的、弥足珍贵的。同时作者将这对世俗男女的这种“暧昧”进行了升华,升华到没有一丝杂念与邪恶的亲情。陆菊人以她地母般的情怀给予井宗秀无私的支持与帮助,但对于井宗秀的爱意却并未言说,只是将此深深地埋在内心深处。“她恪守传统女人的妇道”,将这种情感由外在于形内化于心。即使就井宗秀而言,他也清楚地知道,得到的也许并不比守望者更为幸福与长久,他知道如何去遵守这一规则,并持久地守望下去。作者抛却世俗的眼光去考量这份“爱情”,使“枭雄井宗秀和女杰陆菊人‘英雄爱英雄,叔阳爱管仲’的惺惺相惜又渐行渐远的人生经历”[4]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也不难见宗法文化对天理伦常的规范作用,而对于陆菊人和井宗秀来说,这种宗法文化是渗透在骨子里面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无意识在时刻提醒着、支配着他们去践行它、遵守它,从而使整个生命形态达到圆融的状态。
秦岭作为华夏民族的地标式景观,“积淀了古老而厚重的民族历史文化”,见证了千百年来甘陕大地上人们的绵延生息;而《山本》作为一部秦岭志,一部地方文化史、民族文化史,集中浓缩了秦岭大地上的各种文化形态,“其深刻的文化意蕴是其他小说难以比拟的”。作者对于这种文化形态情有独钟的表达,不仅彰显了对这种乡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更是体现了“文化诗学”所特有的轩邃、丰厚的文化特质。
二、充满哲思的乡土叙事
“文化诗学”的另一特质便是对人性的弘扬与生命的关怀,使文本在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的同时,彰显出浓厚的人文情怀。新世纪以来,贾平凹以《秦腔》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都蕴含了这样一种情怀,“都是带有原创性的、本土的,具有中国民族审美精神与中国气派”[5]。在《山本》中,作者以其充满哲思的笔调展现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善良淳朴,他们身上不仅仅具有乡土中国的温良恭俭,同样具有狭隘的小农意识与狡黠的性格特征。在文本中作者并未一味地去弘扬人性的温柔醇厚,对他们的自私庸俗也进行了细致地描摹刻画,这种鞭辟入里的叙述所传达的是对人性的诘问、对生命的感喟,更是对人文精神持久而深沉关注后的反思。
在《山本》中作者并未刻画浩繁而宏大的历史场面,而是围绕陆菊人与井宗秀等人琐碎的日常生活展开了对历史的敷陈与阐释,描绘秦岭大地上人们“生如禽兽般惜懂,死如草木般寂静”[6]的坎坷人生,其中对于人物多元的叙述无限延展了文本自身持久的美学张力。陆菊人这一地母般的形象显然是最为作者所称道与赞扬的,她带着三分胭脂地的陪嫁来到涡镇,并参与到涡镇的历史风云变幻之中。初到涡镇的陆菊人显然代表了乡土中国的传统女性,她勤俭持家、孝顺长辈,对于丈夫杨钟放荡不羁的行为选择性地隐忍,她并未对丈夫给予厚望,或者期望他有所作为,她所希冀的是一家人的团圆和睦。此时的陆菊人并非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千千万万的妇女形象,而这一形象显然符合作者的价值观,也就是大地母亲的形象,她们从容、善良,以自我生命的坚韧去面对生活的艰难困苦、酸甜苦辣,所以在文中我们会看到作者对此细致的描写,使得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富饱满。但寓于共性之中的是生命的个性,在陆菊人身上所彰显的生命个性主要体现在对井宗秀人生的塑造上。阴错阳差的三分胭脂地令二人结下一生的情缘,井宗秀从一介草莽逐步走上“霸主”的宝座与陆菊人的帮助难解难分,陆菊人以其自身的智慧与深明大义的品性辅助井宗秀崛起,也令井宗秀心存感激。在井宗秀崛起之后她所做的一切更是不可小觑,尤其是将茶生意做得蒸蒸日上,为井宗秀的预备团提供了源源不断地供给,保证了井宗秀在实现“霸主”路上走得更加顺畅。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死于战乱,陆菊人自己出资为这些亡灵设立往生牌进行超度,这种悲悯情怀令我们看到了另一面的陆菊人,是在从容、善良、智慧背后的普世情怀。陆菊人作为《山本》中理想化的人物,认命却又不屈服于命运,带给这片荒凉的世界一丝光与温暖,她不仅见证了井宗秀的崛起与衰败,也见证了秦岭世事的沧桑巨变。作者通过陆菊人的视角,将世间的生死展现出来,传达出了对生命的无常感叹与对人性的关怀。
如果说陆菊人是善的化身,那么井宗秀便是被善感化的对象。井宗秀作为涡镇的核心人物,与涡镇生死相依,涡镇给了他新生,也腐蚀了他的灵魂。在文本中井宗秀很难被定义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作为英雄本应造福一方、守护安宁,而井宗秀所挑起的是无谓的争端与流血牺牲,作者展示他英勇无畏的一面,也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他的阴鸷、冷酷。井宗秀从一个籍籍无名之辈成为涡镇的预备旅旅长,在他成长与奋斗的路上充满艰辛,但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当他觉察到妻子与土匪五雷私通,竟悄无声息地让她失足坠井而亡;通过挑拨土匪内部的争斗除掉了盘踞在涡镇的土匪;他通过自己的势力将麻县长从平川“请”到涡镇,并逐渐掌握了政权,借此巩固自己的范围;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他开始了更疯狂的行动,不仅大动土木而且对百姓横征暴敛,更是惨无人道地剥活人皮制鼓,尽显人性的苍凉。井宗秀本是被众人奉为一方的守护神,最终却变为了独裁的统治者。井宗秀最终“完美”地蜕变成了涡镇的“霸主”,但也逐渐失去了本心,迷失了自我。贾平凹用真实而客观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也将井宗秀“还原到历史和生活的本然状态”中去打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一个战火纷飞、军阀混战的年代,想要求得生存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与牺牲,甚至要不择手段,而作者所展示的正是井宗秀的这一面。作者对井宗秀人性的沉沦并未进行大量的批判与回避,反而是以陆菊人的善良无私去不断地感化他。在这条充满刀光剑影的成长道路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沦丧,更看到被善与温暖环绕的人性之光。贾平凹在“后记”中也曾说:“这一切还留给了我们什么,是中国人的强悍还是懦弱,是善良还是凶残,是智慧还是奸诈?无论那时曾是多么认真和肃然、虔诚和庄严,却都是佛经上所说的,有了罣碍,有了恐怖,有了颠倒梦想。”[1]543由此可见,作者将对于人性的诘问放置在了更广阔浩渺的宇宙之间,韵味绵长,引人深思。
“苦难是人类无法规避的一种生存处境,在现代性话语里还被设定为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本质,同时也是文学历史长河里艺术表现的一个基本情感类型。”[7]《山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众生的苦难史,塑造了众生在人世所经历的各种苦难,但随着文本的叙述也让我们看到了众生对苦难的消解。杨掌柜一辈子与世无争,在井宗秀父亲死后他秉承着与人为善的处事之道帮助井宗秀料理后事,他的乐善好施让人在那慌乱而薄凉的人世不再感到生命的荒寒;陈先生作为涡镇的郎中,他虽没有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却内心澄净,用心感悟乱世之中的生死存亡之道,以精湛的医术呵护众生的生命周全,他总能以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解开他人心中的疑团,这也是陆菊人为什么将自己的儿子剩剩送到陈先生身边学医的原因,希望他能如同陈先生一般睿智而坦荡,而不因这世间的苦难懊恼;宽展师傅遁入空门远离红尘,她以自我的慈悲与善念设立祠堂为众生祈祷,宽展师傅与尺八相伴一生,尺八苍凉的乐音不仅表达出了她内心的落索,也展现了世间的凄苦,更让人体会到了凄苦中所蕴含的慰藉。涡镇的天下终究是凡人的天下,在时代的洪流中,演绎着人生的无奈与悲凉。作者对这些芸芸众生的塑造可谓匠心独运,以陈先生与宽展师傅为代表的尘世与空门都未能在乱世之中得到解脱,但是他们却得到了超越苦难的良方。陈先生本为盲人却终生行医济世,宽展师傅本为聋人却整日余音绕梁,本非常人却胜于常人,其中蕴含了深奥的生存之道——“悲苦是蜜,全凭心酿”。众生都觉得生活悲苦、人生残酷,唯独陈先生与宽展师傅不以为然,在炮火纷飞的涡镇依旧傲然独立,在苍凉与光辉并存的秦岭大地上注视着苍生。作者以极其坦然的心态重现历史与往事,伴随涡镇消逝的是人们对痛苦与磨难的消解,而这种痛苦与磨难的消解又寓于陈先生与宽展师傅身上,足见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哲思与作者对于人性与生命形态的思考。
贾平凹倾注了自己的满腔热血书写着秦岭大地上的人事。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每个人所必备的技能便是于乱世中求得生存,所以作者去刻画他们的善、他们的恶以及他们的蝇营狗苟,如牟宗三先生所说:“现在的人太苦了。人人都拔了根,挂了空。”[8]2在涡镇的世界中生存是最大的善,谁也无法用善恶的标准去衡量存在这里的每一个生命,所以面对陆菊人、陈先生、宽展师傅的善,作者有所讴歌,但是对于井宗秀、阮天宝的恶,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批判,所传达的正是作家深沉的生命关怀和人文情怀。
三、文化内涵与诗学价值
童庆炳先生曾言:“文化视角无论如何不要摒弃诗意视角。我们要文化,但也要诗意、语言等等。大可不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是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的守望者。”[9]显然,在童庆炳先生看来,对于文学的研究应该是文化与诗学兼而得之,不可偏废,这一点在贾平凹的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商洛文化对于贾平凹的熏陶与浸染犹如高邮之于汪曾祺、香椿街之于苏童。作者将包罗万象的文化因子寓于文学文本之中,并通过诗情画意的书写呈现于读者面前。在《山本》中作者对于秦岭大地的乡土文化、民俗文化和宗法文化的描写,让读者更多领略到的是甘陕大地的淳朴醇厚,同时也在这一文化场域内看到了众生对于诗情画意生活的守望,这也便是《山本》的文化内涵与诗学价值之所在。
地域文化对于作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贾平凹的乡土叙事立足于地域文化之上,构成独特的叙事内容。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秦岭大地,为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决定了他文学叙事的特异性。就贾平凹的创作而言,《废都》之后的文学作品相较以前明显少了那种清新空灵的乡土韵味,而显得更加浑厚苍茫,这与作者的生活阅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对生活体悟的不断深化,对于地域文化的认识不断加深,那种理想化的乡土叙事逐渐淡出作者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着重揭示在这一文化场域中众生的真实生活图景。《山本》中对于乡土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的描写叙述,远不止于为了增加文本的趣味性与可读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于地域文化的描写叙述,揭示其中深厚的文化韵味,让读者透过文化的面纱去体会深刻的生命意识。在写《山本》时如何让历史文化进入文学是作者所思考的问题,此时作者将自己置于广阔的秦岭大地,细细地去体味百余年前发生在这片大地上的生生死死,关注这里的一草一木,并将他们细化到文本之中。《山本》中虽然充斥着不绝于耳的枪声与无处不见的死人,但秦岭的文化形态并非体现在这些大的争斗之中,反而是浓缩于那些小的争斗与生活之中。这些丰富的细节描写、生动的人物刻画,集中体现了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与内涵,“为文学叙事奠定了一种生活基本基调,构成了作品生活的基本内容及其思想倾向,体现的是一种共性原则”[10]。
《山本》的艺术世界中体现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文本集中浓缩了天、地、人,儒释、道等文化特征,构成一个斑驳庞杂的世界,并在这一世界中体现出历史的本真与现实的无奈。文本充斥着大量的神秘文化描写,对于主流文化而言,这些神秘文化显然是虚无的、玄妙的、难以被接受的,但对于乡土中国的普通民众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作者通过对神秘文化的描写叙述,展现的是一种信仰的力量,例如高大神秘的皂荚树,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够接受它的恩泽;陆菊人做事会得到某种神秘预兆,并根据预兆作出自己的选择;对井宗秀是老虎托生的暗示,因此要盘踞在依山傍水的涡镇;周一山能够未卜先知,以此来对世事作出独特的判断等。这种神秘文化对于涡镇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有着某种支配力量,推动着众生去探索生命的奥秘,也正是这些看似荒诞而诡异的神秘文化,支撑起了这方土地上民众的生生死死。贾平凹在《山本》中不仅对这种独特的神秘文化进行简单描绘,而且通过这样的描写折射出乡土中国民众的生存状态。当然,在《山本》中我们所看到的神秘文化是乡土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的综合体,作者通过对这些文化的呈现,让读者看到了“普通民众与历史生活纠缠在一起的实实在在的生命生存过程”。
文学艺术源于生活,但远远高于文学,它既不是对生活的简单描摹,也不是对于生活的简单再现,它所塑造的世界比现实生活更高、更圆满,更富有诗情画意。贾平凹所处的三秦大地人文意蕴深厚,在当代涌现出了以路遥、陈忠实等一大批著名作家,虽然他们所构建的文学世界各异,但对于诗意生活的追求却从未停止过。在众多的作家中,贾平凹的创作力是强盛的,也是独特的,他“始终植根于沉实、淳厚、坚韧、空灵、传统的俗世文化系统和底蕴之中,叙写秦岭商洛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人们近百年来的世道人心、生活和行为衍变”[11],这对诗学价值的彰显也具有持久的美学张力。在《秦腔》中作者通过描写白雪对秦腔的演奏与传承,展现了作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记录对已逝故乡的缅怀,对“家乡已经消逝文化的祭奠,对记忆里家乡的怀念”这种诗意的生活伴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但是对于这种诗意的追求却从未止息。作者用文学的方式记录在文本之中,让更多的人体会到了这种诗意。《极花》塑造的是一个极其简洁的故事,主人公胡蝶抱着对大都市生活的憧憬逃离农村,却不曾想被拐到更为偏僻的农村并结婚生子,当她被解救后才发现自己已不被都市所接纳,于是毅然决然回到了被拐的乡间。在所有人看来胡蝶的命运是悲惨的,但相对于城市的冷漠与荒寒,被拐之地已然成为了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了自己诗意的栖息地,这其中纵然饱含着无奈与辛酸,但更饱含着她对儿子的爱与牵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山本》中同样如此,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并非一派霁风朗月,而是充满了血雨腥风,但是存在这里的每一个生命都没有放弃对于诗意生活的追求。
《山本》在现实与超现实之中展开叙述,以抒情的方式吸引读者走进涡镇的世界。涡镇是各派势力的竞技场,在这里既有军阀、匪患,也有逛山、刀客,各派势力“在残杀与争斗中,生命瞬间被毁灭,意义和价值被消解”[12]。由此可见,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这一世界都并非一个诗情画意的世界,读者看到的只有满目疮痍。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人们依然没有放弃对诗意的追求。首先,作者以诗意的笔触展现陆菊人与井宗秀这种“发乎情、止于礼义”的情愫,陆菊人与井宗秀之间的这种情愫是涡镇黑暗之中的一缕光,让我们感受到无论世事多么艰难,都无法阻止人们去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逐,对人性最本真的流露使小说弥漫着一种诗意般的韵味。其次,作者生动而真切地描绘了涡镇的众生相,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一生所追求的只是安稳度日,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望,即便如此,人们依旧相信人世的美好,在涡镇稍显安宁之时,以铁礼花这一传统技艺来庆祝这片刻的美好。当然,作者对于诗意的描绘并不限于人世,也体现在对自然的书写,秦岭中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在作者笔下显出别样的生机,也令读者在涡镇这一乱世之外感受到大自然独特的生命力。诗学在《山本》中是一种氤氲的缠绕,作者并未去讴歌什么,也并未去批判什么,但在掩卷之余依旧令人相信人世美好,人间值得。
秦岭山关雄奇,人文奇特,贾平凹以此为背景为读者构建了异彩纷呈的自然景观与人生往事,在现实的书写与奇幻的叙述中阐释着“文化诗学”的内涵。将文化寓于文学之中的独特书写,令人在感受到文化的魅力的同时,更令人体会到了文学的品格,而将诗意寓于文学中,令人体会到的是一种悠远的审美魅力与诗般情愫。
四、结 语
作者在《山本》的后记中写道:“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没改变的还有感情,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慨叹万千。”[1]541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对秦岭进行了详尽的描绘,从“文化诗学”视域内考察《山本》的创作,毋庸置疑,其中既饱含了厚重的文化意蕴,又体现了深沉的人文情怀,同时兼有诗情画意的艺术品格,饱满而深刻地体现了文本的文化内涵与诗学价值。这一文本叙述与当今国内文论界所倡导的“文化诗学”观正相吻合,是“文化诗学”在现实意义上的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