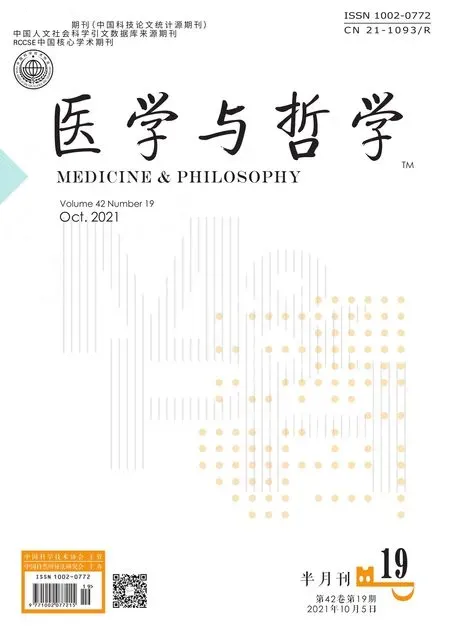多元文化对儿童安宁疗护实践的影响*
2021-12-03周英华
周英华 庄 严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来自不同国家及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迅速增加。日益加剧的多元文化社会对医务工作者提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对具有不同生活经历、信仰、价值体系、宗教、语言及观念的个体提供恰当的照护。在患者和家属的疾病痛苦经历中,文化信仰和习俗尤为重要,然而医务人员往往不太了解它们,尤其是当医务人员与患者的文化背景不同时。研究发现,近40%的儿科医务人员认为文化差异是儿童安宁疗护有效实施的一个常见障碍[1]。高质量的照护需要医务人员具有对文化的敏感性和文化胜任力,在儿童终末期的照护中更是尤为重要。同时,文化可能影响儿童安宁疗护的恰当实施。例如,研究发现拉美裔美国居民倾向于一个首要的、支配一切的信念,即要尽所有努力来挽救孩子,这个信念使得父母即使知道疾病的严重性也对采纳安宁疗护很犹豫[2]。目前国内缺少关于儿童安宁疗护中文化考虑的研究。因此,本文在简要介绍文化与多元文化护理、文化敏感性与文化胜任力及儿童安宁疗护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阐述文化对儿童安宁疗护实践的影响,为多元文化背景下儿童安宁疗护的开展提供参考。
1 相关概念
1.1 文化与多元文化护理
文化(culture)是指一个特定的群体所学习、共享、代际传递的价值观、信仰、规范和生活方式,其影响和引导一个人的思维、决策和行动模式[3]。美国护理学理论家Leininger[4]提出了多元文化护理,又被称为跨文化护理,它是一个侧重于整体的文化照护、健康和疾病模式的研究及实践领域,关注人们在文化价值观、信仰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目的是能够提供与文化一致的、富有同情心的护理。因此,多元文化护理是以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为基础,结合关怀理念、文化照顾形成的理论体系,主张将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融入到护理实践中[3]。
1.2 文化敏感性与文化胜任力
文化敏感性(cultural sensitivity)是指对文化如何塑造价值观、信仰、世界观等的认识,以及对存在的文化差异的承认和尊重,其要求医务工作者对不熟悉的信仰和实践保持不带偏见的态度,并在出现冲突意见时,愿意协商和妥协[5]。缺乏文化敏感性可能会导致错误的观念,从而阻碍医务人员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有效互动,以至于达不到预期的临床结果或目标[5]。
文化胜任力(cultural competence)是指能够更好地融入不同文化,或与不同文化的人建立关系的技巧和能力[6],它不仅指文化实践知识的积累,而且要求医务工作者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偏好和信念的构建[7]。在临床环境中,文化胜任力是指医务工作者掌握、理解、重视不同世界观的观点[8],获得能够加强文化问题管理的知识和技能[9],从而在跨文化情境下,可以实施和达到正确的临床结果或目标[10]。现代对文化胜任力的要求包括强调它的动态性,以及在与患者和家属的沟通中,将照护和患者需要视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联系并进行连接的过程[11]。综上,文化敏感性和文化胜任力描述了在提供文化照护方面应具备的知识、恰当的态度和技能,处理和尊重文化差异可以增加信任,提高照护质量。
1.3 儿童安宁疗护
安宁疗护是采用多学科协作模式为临终患者和家属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社会支持等,以尽可能地减轻临终患者的痛苦,提升其生命质量[12]。儿童安宁疗护特别关注患儿和家庭的需要。同时,随着患儿的成长发展,疾病对患儿的影响不仅包括生理上的改变,还有情感和精神上的变化,因此,对新生儿与对青少年的安宁疗护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儿童心理发育常不成熟,对死亡缺乏认识,而青少年具有了复杂的思维,这使得他们对于死亡的看法和愿望有了更多的思考。此外,儿童安宁疗护中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在父母和医生的眼中,儿童的安宁疗护看起来不符合自然规律,因此,他们很难接受孩子无法治疗的现实[11]。
面对日益加剧的多元文化社会,在2002年,国际儿童姑息照护倡议组织(Initiative for Pediatric Palliative Care,IPPC) 专门强调了文化敏感性照护,并提出了怎样为患儿及其家庭提供文化敏感性照护,框架包括:(1)最大限度地让家庭参与决策和照护计划,让每个家庭成员感到舒适。应初步评估患儿家庭的宗教信仰、仪式和饮食习惯,以避免照护过程中产生冲突,询问他们对疾病和预后的看法和恐惧。(2)对于患有生命威胁性疾病的儿童,在了解他们的发展能力和愿望下,应尽可能地告知患儿病情并让他们参与到照护决策中。在此过程中,医护人员要注意避免与患儿照顾者之间发生冲突,因此,应在照顾者的同意下与患儿进行坦诚和开放的沟通。(3)减轻患儿的疼痛和痛苦的症状。需评估家庭对于减轻疼痛和痛苦的态度与信念,询问过去如何管理疼痛和痛苦,以及是否存在与治疗有关的一些强烈的信念。(4)为患儿及其家庭提供情感和精神上的支持,以应对因危及生命的状况而造成的多方面的丧失。在儿童安宁疗护中,精神的评估是尤为重要的,然而,应注意的是,有些文化认为情感是家庭的隐私或把接受精神健康服务误解为患有精神疾病。(5)促进住院和出院后护理的连续性。在患儿死亡前后,为患儿及其家庭提供哀伤支持,但应注意询问患儿家庭的传统及其意愿[11]。
2 多元文化对儿童安宁疗护实践的影响
2.1 病情告知及决策
知情决策是安宁疗护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心肺复苏和特别治疗措施等问题的决策方面。在分享信息和决策过程中,与文化相关的最有力的决定因素之一,是个人与家庭的相对重要性。在西方文化和宗教中,个人是首要考虑因素,如果患者有能力,总是首先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13]。但在一些传统文化尤其亚洲文化中,家庭的福祉是第一要务。在俄罗斯、韩国、中国和日本文化中,基于家庭的决策很常见,疾病被认为是家庭而不是个体的事情,希望了解患者的病情并以家庭的最大利益为重,为患者做出治疗决定是非常常见的[5,14]。同样,在拉丁美洲文化中,以家庭为中心的决策模式受到高度重视,而且可能比患者的自主权更重要,这被称为“家庭观念”(familismo),其特点是相互依存、联系和合作[15]。 因此,家属可能希望在通知患者之前先获得医疗信息,以便他们能够保护患者或逐步告知病情[15]。
在安宁疗护中,医务人员与患儿的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交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除患儿的年龄外,关于病情告知的一些文化因素也是尤其需要关注的。当患儿是青少年,但其父母反对病情告知时,即使其中的文化规范受到尊重,医务人员与患儿父母的冲突可能也会产生。在西方国家,鼓励患儿父母从患儿的诊断确立起就开始病情告知,倡导开放的、与患儿年龄相适宜的交流方式[11]。不愿讨论死亡可能说明了患儿父母的痛苦和不能接受患儿患病的事实,一些家庭决定不去讨论死亡,即使他们的孩子很可能因为疾病而死亡,这样往往导致不能做好死亡的准备。在有些文化中,对患儿隐瞒病情是可接受的,如美国拉美裔居民及亚洲家庭可能要求医务人员应在患儿不在场的情况下交流病情[13-16]。在我国,通常父母会向孩子隐瞒病情,以防止死亡带来的恐惧使孩子失去希望,从而使病情变得更糟。在韩国,对患者隐瞒病情也是常见的,家属认为患者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做出恰当的决策,同时坏消息会使患者丧失希望[17]。此外,患儿性别也可能影响人们对于疾病的看法,性别常在治疗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有些传统文化中,家庭对男孩维系家庭的血脉具有更强烈的希望[18]。
宗教信仰也会影响病情的沟通。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是指患者在自己意识清楚的情况下,对自己将来进入临终状态时的治疗护理意愿进行沟通和明确的过程[19]。然而,服从上帝的意愿是伊斯兰教的核心信仰,在阿拉伯语中,“伊斯兰”一词的意思是(向上帝)投降,穆斯林是向上帝投降的人。因此,医务人员如果试图将一些问题如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生命支持技术,传达给某些患者,尤其保守的穆斯林患者,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反感[20]。类似地,菲律宾患者也不愿讨论安宁疗护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些讨论会违背他们关于个人命运是由上帝来决定的信仰[21],所以需要一定的沟通方法。有时把问题以假设的形式陈述出来可能会让人感到更舒服和具有更少的威胁性,尤其是对于把直接谈论死亡看作是不尊重或不可接受的人[11]。因此,认真了解患儿及其家人的愿望,尤其当有些愿望与种族文化密切相关时,对避免交流中产生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2 语言与非语言的交流
在儿童安宁疗护中,医务人员与患儿家庭之间需要有意义、深入的交流。而交流的失败可能会导致不正确的诊断、对疼痛管理的不足、药物的使用或利用不足及获得知情同意的困难等。口头交流会牵涉到语言,语言可能是一个关键的障碍。当语言障碍使得家庭不能获取关于孩子健康状态或医生推荐治疗的完整信息时,一些家庭可能会产生失望。因此,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尤其移民国家,训练医学翻译者是非常重要的,以帮助患者家庭和医务人员的深入沟通[21]。此外,我国部分少数民族患者仍不能熟练使用汉语,患者承受着痛苦但又不方便向医务人员直接表达,医务人员也不能直接通过语言对其进行疏导,语言障碍成为不可避免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在我国少数民族较多地区的医院,应具备一定可以熟练使用民族语言的医务人员,医院也可定期开展少数民族知识讲座,增强医务人员对少数民族患者的了解[22]。在医患沟通中,对词语的选择也会产生交流障碍,例如,在美洲土著居民、菲律宾人、中国人和波斯尼亚人的文化中,强调一旦一些词语说出来,那可能就变成事实[21]。因此,有些父母认为谈论或认同安宁疗护,就会使患儿的死亡到来,所以不愿谈及安宁疗护。
此外,一些非语言交流的文化差异也可能影响准确的交流。在不同文化中,一些姿势可能意义不同,甚至差异很大。例如,在中国文化中,点头、微笑或说“是”,仅仅表明倾听,而不是理解或同意医务人员所说的,直接目光接触可能被认为是具有攻击性或敌意的[16]。在韩国文化中,握手在男性间是恰当的,女性是不握手的,轻轻地鞠躬代表尊敬[17]。有些文化比较喜欢碰触[11],在美国,交流较棘手的信息时,常伴随着一些姿势如触摸手或手臂,来表达温暖、同情或安慰。在欧美文化中,触摸孩子的头,是一种喜爱的表达方式,但在其他文化中,这可能是不尊重的表现。例如,美洲土著居民有一些关于头和头发的传统,因此更喜欢尽可能地避免碰触头部[11]。同样,泰国人、印尼人认为头部是宝贵而又神圣的,也忌讳他人触摸自己的头部。因此,在这些文化中触摸和轻拍孩子头部不是建立友善关系的方式。此外,宗教的教条也应受到尊重,如在犹太教中,即使是为了表达对患儿父母的同情,触摸异性也是被禁止的,伊斯兰教中也有类似的观点[23]。而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中,特别是年长者,也忌讳异性碰触他们的身体[24]。
2.3 对疼痛的理解和管理
为患者减轻疼痛是安宁疗护的重要内容,然而,患者对疼痛的耐受性和表达、对于身体存在疼痛的看法及对自我承受疼痛的理解,在文化上是有差异的。有些文化可能较其他文化坚忍,如西班牙裔男性往往不抱怨疼痛[20]。韩国患者可能非常重视情绪上的自我控制,表现得很坚忍,因此,可能不会表现出疼痛或者要求止痛药[17]。而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会更倾向于表达疼痛并寻求帮助[25]。在中国文化中,癌症患者对疼痛的看法常受到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影响。儒家思想把疼痛看作是一种磨练,因此患者常会选择忍受疼痛。道家认为疼痛是由气血不畅引起的,要去除疼痛,应把不畅去除,患者必须回到与万物和谐的状态。佛教认为疼痛是一种修炼,通过修行才可解除疼痛[26]。拉美裔人会把疼痛和痛苦看作是一种精神惩罚形式,患者需要忍受疼痛,这样死后才能进入天堂[25],同时,这也能测验一个人的坚韧性[27]。在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也有类似的转世或轮回痛[11]。此外,加勒比海地区对于一些患有癌症的患者,身体上的疼痛被认为是对信仰的考验,所以应忍受而不是用药物掩盖[28]。因此,来自上述文化中的患者可能更倾向于不报告疼痛或认为自己必须去忍受它,但这些发现对于儿童和成人是否是一样的,还并不清楚。
文化还会影响对改善疼痛药物或疼痛管理的请求。在俄罗斯,给患者使用吗啡会被误解为患者可能正处于无望和放弃的病况下[14]。越南人常把对医生或医务人员说“不”,看作是不尊重或会导致医患关系不和谐,因此,即使他们所接受的止痛药剂量不够,也可能会遵守医生的医嘱而不去反驳[29]。一些中国患者认为向护士要求止痛药物会让护士从更重要的职责中抽身,他们认为护士是专业人员,护士知道患者需要什么,因此,他们会被动地等待止痛药的给予,因为他们认为患者需要的,护士都会给予[25]。同时,在一些强调面对疼痛应自控和坚忍的价值观文化中,对于无法控制的疼痛的抱怨表达可能会大大降低,常造成疼痛管理的不足[16-17,29]。此外,宗教信仰也会影响疼痛的治疗。例如,大多数西班牙裔拉丁美洲人是天主教徒,他们可能会求助于宗教活动,如通过祈祷、集体聚会、涂油礼、牧师的祷告以减轻或忍受痛苦[25]。此外,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治疗痛苦比对待痛苦本身更糟糕,这在东南亚佛教徒中比较常见,由于他们对保持警觉高度重视,因此,他们抗拒由于止痛药的影响而产生模糊的感觉[20]。在上述这些文化影响下的患儿,可能也会用相似的方式来描述或认知疼痛以及对疼痛管理的需要。医务人员在对患儿进行疼痛评估和干预时,应具有文化敏感性,从而更好地提供与患儿文化一致的照护。
2.4 对治疗的选择及精神照护
患儿家庭对于治疗的选择,尤其在临终阶段,如认为医院的治疗是不合适的还是补充性的,可能也反映了文化的差异。在一些研究文献中,患者寻求的常见的辅助性治疗方法有驱邪物、药草和自然疗法。在中国,患者可能用特殊食物和草药来恢复阴阳的平衡,除此之外,患者可能会使用其他中药作为初步的治疗方法,特别是在疾病的早期阶段。一些传统的中医疗法,包括按摩、针灸和灸术疗法,通常被用作西医的辅助治疗[16]。日本人可能会采用灵气疗愈“Reiki”,“Reiki”寓意“普遍引导”或“精神能量”,其来源于两个日语词“Rei”(指引导宇宙的创造和运作的高智能)和“Ki”(指流经所有生物的生命能量,包括植物、动物和人类),它是一种通过减少压力和促进放松来达到自然愈合的日本传统方法[30]。韩国人可能会向经常使用草药的传统治疗师寻求帮助,草药中人参尤其常见[17]。此外,在中国和韩国,人们可能会认为西药药效太强了,从而改变服用的药物剂量,只服用一半或在医务人员告知之前停药[16-17]。美洲原住居民可能会先在汗蒸屋治疗,然后结合医院的基本治疗以净化身体中的毒素,这也是欧裔美国人用来修复个体在身体和精神上损伤的常用方法[11]。不同传统和习俗对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理解会显著影响家庭寻求和遵从治疗的程度。
在西方的犹太教及基督教信仰人群中,神职人员被视为宗教、精神关怀、舒适、知识和智慧等的支持者和提供者。神职人员定期访问医院、疗养院和患者之家,可以为患者和家属解除精神困扰和提供安慰,但并非所有宗教都是如此,如来自大多数佛教教派的神职人员,在患者死亡之前不会去医院或患者家里[20]。此外,越南、拉美裔家庭可能不希望精神健康师参与到悲伤过程[15,29],因为他们认为这表示他们的悲伤是病态的[15]。因此,这些来访在执行前,应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和解释。
2.5 对疾病和死亡的理解
患有威胁性疾病的儿童或年轻人常须面对的问题是对疾病、痛苦和死亡的理解,而文化影响着人们对它们的理解。在中国和韩国文化中,认为当身体中相互冲突的能量失衡时,疾病就会发生,这些能量包括但不局限于阴、阳、冷、热[16-17]。很多亚洲人信仰佛教或印度教,他们可能会把疾病和痛苦归因于坏的因果报应,并把痛苦视为对自己前世犯下的罪过的赎罪,逃避痛苦会把痛苦转到下辈子[13]。类似地,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认为疾病是由于此生或前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疾病可以洗去一个人的罪恶[11]。因此,来自于这些文化中的危重患者可能会受到指责或污蔑,而不是受到富有同情心地对待,他们被认为应承受痛苦的折磨[31]。
此外,人们对死亡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西方人受宗教影响,认为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相比肉体更重视灵魂,对死亡的认知较为理性,加之生死教育的广泛开展,西方对死亡比较淡然,能够坦然面对和接受,医患沟通更为直接[32]。而在美国,死亡常被看作是敌人,应尽所有努力去避免。因此,患者可能会避免去谈及即将到来的死亡,但美国中的少数种族文化对死亡的看法和态度可能是不一样的,例如,非洲裔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常常具有强烈的宗教和精神基础,这种基础包含在死亡和死亡的过程中,死亡被视为生命中的自然结果,家人会因为死者现在平静、快乐地与上帝在一起而感到宽慰[8]。在我国,儒家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处于核心位置,其死亡观是好生恶死的。长期以来,在儒、道、佛、迷信、民间习俗相交融的思想体系下,形成忌讳死亡、重生轻死的观念[32],往往把死亡看作是不详的征兆,对死亡持逃避、消极的态度。特别是孩子的死亡,家长会采取尽量回避的态度。然而,中国民族众多,文化习俗差异大,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对死亡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羌族人认识到生、老、病、死是人不可逃避的自然法则,倡导顺其自然,相信人死亡后,便离开了现实世界到了祖先居住的鬼神世界,把死亡看作“回老家”,显示了羌族文化与道教文化的融合[33]。藏族把生死看作正常的轮回,死亡只是肉体的消亡,而人的灵魂是不朽的,认为人死后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生活[34]。回族人从小就受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伊斯兰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生命包括人类,都是真主安拉创造的,人类生命的长短由安拉决定,自己是无法改变它的,死亡是连接今世和后世的桥梁,死亡是人的必然归宿,只有虔信真主的人才能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进入天堂[35]。因此,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应了解患者对死亡的理解、接受程度,开展个性化的死亡教育。
2.6 死亡仪式和死亡地点的选择
在不同的文化与宗教中,死亡仪式和风俗是不同的。在日本,在移动逝者身体之前,可能会先念“枕经”,家庭成员会聚集在床边,并让牧师吟咏祷文[36]。菲律宾家庭可能会清洗患者的身体,并希望每个家庭成员能向垂死的人道别[13]。信仰佛教的家庭,可能会为病重的患儿念诵咒语或使用药物疗法,当患儿病得很重或快要死的时候,使其尽可能多地保持平静和安宁是很重要的。其次,死亡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转入下一个生命的过渡点,这时会祈祷,或由佛教神职人员或家属诵读一个专门的文本。死亡后,孩子的身体不可被触摸,而是被带回家,在埋葬前,会举行祈祷以使逝者更容易地转世[23]。我国藏传佛教认为,应为临终者摆设佛龛和供品,把死亡看成是一个神圣的过程,家庭成员要围绕着临终者,为之念诵六字真言,祈祷临终者来世幸福[34]。信仰伊斯兰教的可能要求在患者逝去后,立即把其尸体转向东面,即他们的圣城“麦加”的方向,会给死者全身清洗3次,并在24小时内进行埋葬,禁止火化[11,13]。我国信仰依斯兰教的回族传统中,一般会将临终患者接回家里,家属会通知患者的亲朋好友前来道别。临终者希望能进行“讨白”,“讨白”是帮助临终者进行“忏悔”的仪式,以帮助其认识到自己一生中犯的过错,弃恶从善,在临终者忏悔和反省自己的同时,阿訇(主持伊斯兰教的各种仪式,讲解古兰经的人)和亲属们会在一旁为其祈祷,祈求真主饶恕临终者的罪过。此外,他们主张土葬,认为真主用泥土造出人,人死后躯体应贴近大地,变成泥土,这样才是自然的[35]。信仰印度教的希望家人和朋友能围在垂死者旁边,唱着神圣的赞美诗,并祈祷或吟诵垂死者的咒语,当死亡临近时,家庭精神领袖需做最后的仪式,逝者的身体应尽可能靠近地面,以帮助灵魂被吸收入土地[11]。信仰犹太教的会在24小时内埋葬死者,除非死亡发生在星期五的日落、星期六、犹太教节日或等待家庭成员到来的过程中[14]。信仰天主教的家庭,患者的傅油圣事是由牧师来完成的,以帮助患者做好死亡的准备,念珠、蜡烛和宗教勋章是安慰垂死的人和其家人的常用方法[8]。
关于最佳死亡地点的想法可能是基于文化的,与相关人员的宗教、教养程度、疾病情况、家庭情况或其他问题有关。在菲律宾、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越南和拉美裔文化中,患者主要死在家里,亲人陪在身边[13,15,29,37]。一些美国本土文化认为,死者的灵魂留在死亡之地,对生者有害,因此,家是一个不适合死亡的地方;知识渊博或经验丰富的人往往希望控制局面,并认为有了足够的支持,如医务人员的指导,家里可能比医院更适合死亡;有的知识贫乏的人认为现代医学可以治愈一切疾病,因此拒绝离开医院[20]。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寿终正寝”的说法,中国人普遍认为在家中离世是非常重要的[38]。例如,藏族人希望患者在家中离世,以使患者人生的最后时刻不被陌生人打扰,心灵会尽可能地保持平静。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蒙古人也是倡导安详死亡,在患者病情加重的时候,常常会放弃治疗回到家中,让患者在死前尽可能地保持宁静[38]。一项关于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传统上“最后一口气在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落叶可以回到它的根上,死者的灵魂可以在它自己的地方休息,而不是成为一个孤独的灵魂或精神流浪者[39],有些人可能会严格遵守社会传统,而另一些人则承认这种信仰并尊重家庭成员的决定,但也有一些中国人认为死在家里会带来霉运[13]。人们经常用自己的宗教视角或个人价值观来看待人生和世界,这些都为人们把握人生的复杂性提供了意义、希望和指引,这样的个人价值观和宗教信仰可以促进生命终末期的讨论和准备[39]。然而,无论家属选择让患儿在何处离世,都应确保对患儿的照护质量。
此外,当死亡到来,不同文化、宗教中对悲伤的表达也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讲,在西方的葬礼上,哭泣常是不被允许的,例如,在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下,基督教的葬礼是为死者祈祷,祝其早日升入天堂,即使亲友对逝者不舍和哀痛都不能大声哭泣,仅会默默地流泪[40]。在伊斯兰教中,哭泣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信仰者认为悲伤跟生活中的任何其他事一样,应坚忍地去面对,大声痛哭或哀嚎意味着对伊斯兰教的不满[11]。而在拉美裔文化中,在患者死亡前后,家庭成员常守在患者床旁,悲伤的过程会以公开的方式表达出来[15]。类似地,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菲律宾人在公共场合下的悲伤表达是被期望的[13]。在中国的葬礼上,大声哭泣也是非常常见的,人们用哭丧表达对逝者的不舍和哀痛,这也是子女孝顺的表现。同时,人们认为哭声能够使逝者感受到亲人对自己的不舍,甚至可以唤醒逝者的意识[40]。但我国藏传佛教认为,整个丧葬仪式期间,即使人们非常悲伤,也不能在临终者床边大声哭泣,以防止亡者的灵魂听到亲人的哭声后会留念亲人而难以转世[34]。因此,对于文化差异总体的认识是重要的,但医务人员也应明白来自于相同文化的人也可能有其他的隶属的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等,每种宗教可能有不同的实践。医务人员应询问每个家庭关于他们的传统、信仰、宗教仪式及他们的喜好,以了解他们特定的需要和期望,使得所有的照护能充分体现对患儿家庭的尊重,减少模式化和刻板的可能性。
3 结语
儿童安宁疗护中存在着许多障碍,其中文化障碍可能不会由患者或其家属公开表示出来,但会造成对医疗信息及安宁疗护选择的曲解。多元文化护理要求结合患者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世界观、价值观等,为患者提供照护,因此,对医务工作者的文化胜任力和宗教素养的培养尤为重要。在儿童安宁疗护中,应评估患儿的希望、梦想、价值观、对生命和死亡的看法,评估患儿及家庭对患病期间祈祷和仪式作用的看法。轻柔探问他们对于疼痛和痛苦的理解与应对,询问家庭成员是否需要牧师或其他精神方面能起到帮助的人的在场,以减轻家庭成员在患儿疾病和死亡过程中的抑郁和痛苦。与患儿及其家属谈及死亡时,应具有文化敏感性,注意了解他们的文化特征,使用恰当的沟通方法。
在日益加剧的多元文化社会的趋势下,在一些发达国家,对医务人员的跨文化培训受到极大重视,如何实施多元文化教育也成为当前的任务。基于儿童安宁疗护文化的研究可以帮助医务人员改善安宁疗护模式,为患儿和家庭提供高质量的照护。但由于国家起源、文化、宗教和传统的多样性,同时,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安宁疗护的研究较少,本文不可能将所有文化差异均进行描述。理解种族多样性仅仅是个开始,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希望此文使更多研究者关注于如何实践来促进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儿童的安宁疗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