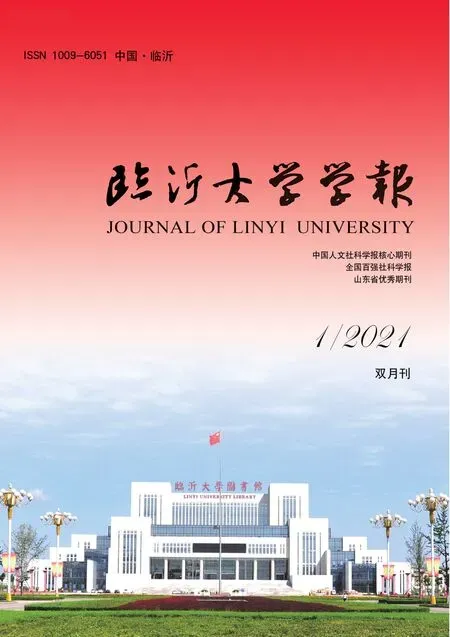清代司法视角下家谱证据的价值局限性
——以《平平言》中“张氏坟冢”案为例进行分析
2021-12-03石泉
石 泉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810000)
《平平言》是方大湜①在晚年写给其弟子的为官手记,其中卷二、卷三两部分详细记录了方氏本人在为官期间所承办的各种民事纠纷案件二十余例。通过对作者在审理“张氏坟冢”一案时的整个思考过程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发现本案中承审官员无法借助证据层面内容的客观性和数量的充分性来实现对矛盾问题背后事实真相的探寻。加之受“告诉不受理”“断罪不当”等律文内容本身在行为和思想层面对官员的导向和规制作用,导致了审理者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动”地依靠个人能力从社会常理、常情、常识等角度对案中人原本为自证诉求且主观表征很明显的文字材料(书证、口供)或实体物品(物证)进行证据价值评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该诉求是否给予“法律支持”的个人态度。此处以案情材料所涉及的家谱证据为例进行典型性分析,以明确官员在实际应对此类问题时会具体表现并遵循怎样的思考方式和路径。
一、案件还原——证据缺失下的承审困局
“张氏坟冢”案的情节过程并不复杂。起因于方大湜在担任广济县令之时,当地韩家湾后山有一名为郑张氏的坟冢。不过案发前该坟冢已多年无人祭扫,只在该坟碑石上留刻有“孝子(郑)秉福、(郑)秉谦;孙(郑)知先、(郑)知明;曾孙(郑)圣有、(郑)宗鲁、(郑)维高、(郑)书玉”字样。尽管时间久远,但地方官员却先后收到了济邑生员郑昭和薪州民人郑炳礼的具呈控争,二人均认为郑张氏是自家祖坟,并请求官府予以确认。[1]
尽管作者在史料文字中并没有明确二人是在何种目的下做出了争认祖坟的行为,但基于案情并结合常理思维不难发现,案中人实际上有通过建立与逝者的亲缘关系来获取经济利益的现实考虑。②换言之,如果能够借助案件审理这一“手段”实现判决内容中对自己与该土地间权属关系的认可,便能够在得到现实经济利益的同时利用具体的司法裁断排除日后可能出现的其他人对该土地权属问题的破坏和侵夺。③另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案中存在该坟冢年代较为久远这一现实情况,所以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该处土地最后归属权法律认定的难度。因为民事案件一般采取纠问方式进行审理,呈控者必须首先对己方诉求承担充分的证明义务和举证责任,以期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权益的有效维护或对方责任的必要承担。如果出现证明力不足或被承审官员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况,就会导致其原本的诉求得不到法律层面“国家权力”的支持,甚至还极有可能会遭致“诬告反坐”的追责处理。[2]不过本案却是一种完全与此相反的外部表征,区别在于呈控人郑昭和郑炳礼即便无法在证明自身与坟冢逝者间亲属关系问题上达到证据提供的充分、客观标准,但只要承审一方无法对其诉求内容给予足够有说服力的“驳斥性”反证,或者准确而言,无法发现其举证材料中的“伪诈”之处,④就势必要在最后对该诉求内容予以承认。具体而言,该坟冢存续时间较为久远且多年无人祭扫,表明了至少在当地不可能有人会在案发时与二郑间出现关于身份关系以及地产利益的纷争,⑤这也意味着二人在取得该处土地权属过程中所面对的唯一障碍就是地方官府怎样进行审理并如何得出结论的问题。假设二人确与逝者郑张氏间存在亲属关系,自然无需赘言;反之一旦二人有冒认宗亲谋取土地的目的考虑,所需要做的也仅是让提供的主(张)证(明)材料得到承审官员的认可(何种方式、手段在所不论),就可以将该处土地据为己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事实真相能否恢复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民间司法博弈后的定案结果,而影响该结果的关键环节就在于对纳入审理程序中的具体举证材料如何进行证明力的价值认定。
最后必须特别说明的是,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清代通常以地籍内容作为权属合法性认定的首要依据。特别是鱼鳞册中所记录的土地形态、面积、科则业主等信息,将会直接反映具体土地的权属关系。[3]如发生诉讼纠纷,除对地籍内容进行核对外,官方还需进行实地勘察,以便做到证据确凿。至于坟田的所有权争议,《大清律例》中明确规定:“凡民人争告坟山,近年者以印契为凭,如系远年之业,须将山地字号、亩数及库贮鳞册并完粮印串,逐一丈勘查对,果相符合即断令管业。若查勘不符,又无完粮印串,其所执远年旧契及碑谱等项,均不得执为凭据,即将滥控侵占之人,按例治罪。”[4]这实际上也解释了为何二郑会将诉求内容集中指向确立与逝者的亲缘关系而非直接去主张自己对坟田拥有土地所有权。因为一旦亲缘关系成立,自然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实现获取土地所有权的目的,同时还能够相对减轻审理过程中己方的举证难度。⑥
二、案件审理——家谱内容的证据价值
虽然郑昭和郑炳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埋葬郑张氏处的土地所有权,但正如上文所述,实现此目的的前提条件是必须首先让官府认可其与逝者间的亲属关系能够成立,因此二人在案件实际审理过程中选择以家谱作为举证材料。作为记载家姓源流和重要人物的谱籍,不管其本身属于何种类型以及修订完成的具体时间,都会有一个最基本的原生特征:记录一家一姓或一族的血缘世系。而这个固有的基本特征,就决定家谱必然存在“明血统,辨昭穆”的价值功用。[5]所以在本案中通过家谱所记录的文字内容来证明二郑与郑张氏亲缘关系的成立,是一种较为符合当时社会常理性思维逻辑的稳妥选择。另外家谱内容具有很强的隐秘特点,私家修谱“一般是本族人自己修,而且是挑选受过一定教育,在本族有一定威望的人撰修。”[6]同时,家谱通常被其成员视为是“私家历史”的记述,即便是在修成以后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随便给他人观看。特别是在族内发放和领取家谱时,“为防止家谱外传,一般在谱后都有顺序号,然后登记注册,某人领某号,定期抽查。”[7]因此在本案中对于二郑提出的家谱证据,其内容方面首先毫无疑问是为举证方谋取利益服务的;同时,承审方想要从家谱以外进行切入并形成有效质疑实际上也存在着很大的难度。⑦
因此,本案审理的焦点自然就转而集中于对家谱内容本身的思考和查核。方大湜首先查阅郑昭提供的家谱,认为其中仅记载“张氏葬魁伯山”,与现在所葬山名不符的同时又无子孙可考,所以断不可因此认定郑张氏坟冢为其祖坟。至于郑炳礼提供的谱内虽载有“张氏葬广济韩家湾后山右侧”字样与事实情况相同,但方氏却对谱中另一处“其子字秉福、秉谦,孙字知先、知明、曾孙字圣有、宗鲁、惟高......”内容产生了疑问。虽然与案中墓碑本身所刻同样,但没有说明此处立碑后人的称呼究竟是“名”还是“字”,但就一般情况而言,古人的“字”主要是在成人后用于朋友、同辈之间的称呼,以示平等和尊敬,也即“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8],而“名”一般在“子生三月则父名之。”也就是说,名和字是古人在一生中两个不同时段的称谓,名起于出生,标志着一个人的降临;字起于冠礼或笄礼仪式上,标志着一个人已进入成年。所以在墓碑书写这种非常强调与尊长亲近之人情感表达的环境中,使用字就显得后辈在礼法制度下和逝者间的关系过于疏离。所以郑炳礼在谱内指明碑文内容皆为“字”,自然就会让承审官员对该谱本身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其次,方大湜进一步指出郑炳礼所提供的谱中郑张氏名目下先注“子善”二字,后尾却又复注“子二”,自相矛盾的同时还与家谱基本的编修体例不符。作为家谱修撰内容的主体部分,世系图(表)通常会占据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至于具体的世系人名会根据其在整个家族中的辈分和嫡庶情况进行排位,名目下则会依次细书辈序、字、某人子、生、殁、葬(坟茔地点)、娶(婚姻情况)、子女(后代情况)各项,使观者明白易晓,便于考核。[9]简言之,子嗣的数量、姓名情况一般应列于该家庭成员介绍的最后部分,但谱页中却独在郑张氏处出现了明显的书写错误。由此方氏认定“名为争坟,实为争地”,而此谱亦是造假无疑,故断令将二郑戒饬责惩,其山地归公,交与贤庄首事经管,招佃承看。
实际上,出于对本家族在特定区域内“正统”源流地位的塑造和现实情境下为维护既得权益而寻求历史依据等目的的考虑,将家谱内容通过假托始祖、歪曲事实、牵强附会等方式进行伪造的社会现象并不鲜见。但考虑到家谱本身属于文字内容,不会对他人权益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缘故,通常情况下权力机关并不会对其编修过程和主观目的进行过多地干预。只不过一旦家谱作为客体脱离纯粹的社会背景转而纳入证据视角下进行考量,其真伪性的认定问题就变得极为重要。作为诉讼环节的“无冕之王”,证据本身需要通过审理官员的“鞫狱断刑”并依靠其自身的客观性和证明力来实现恢复事实真相的最终目的。所以无证据和伪证据很可能就会导致疑案、悬案或不能受理案件情况的出现,同时被害人或利益诉求人的合法权益亦将因此无法得到有效维护。[10]故一旦承审一方无法以“审慎”之态度剥离家谱本身所固有的“社会性”特点,那么在后续的司法过程中很可能就会导致其异化为完全服务于个人主观需要的工具,[11]并在丧失“证据价值”功能的同时给主观决断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三、结语——司法程序下证据的特点及现实功用
证据是承审一方在审理过程中了解与掌握案情的基础。不过官员出于最大限度降低自身“事实审”的复杂程度,也即减少自己重构案件事实难度情况的考虑,通常会选择将举证责任推给原告并尽可能要求原告提供证明力最强并几乎完全可以确定案件事实的证据。[12]但现实情况却是很多案件的证据掌握程度到最后根本无法满足充分性、客观性、关联性这些最基本的标准要求,正如文中所涉及的情况,除去当事人所提供的两份家谱,方氏根本无法获取关于该坟冢归属权的任何其他有效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官员就可以此为理由回避审判,或为确保结果的公正性而无限延长案件的审理时间。⑧而只能在最后被动地选择“进入”案情,并在审理过程中依靠主观态度和个人能力去尽可能扭转既有客观条件的“不利”局面。
“审慎”,意指做事周密而慎重,偏重于对人行为态度的评价。具体到主审官员则要求其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对案情的分析必须达到毫无疑义的程度;对案中人物的相互关系必须做到确实明了;对证据的搜集和掌握必须实现完整齐备;对相关法条的选择和运用必须能够准确熟识等等,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接受来自内心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的质疑进而“超越并排除合理怀疑”。只有如此方能在实现“结果正义”目的的同时又不违犯“程序正义”的要求,并使最后的裁决尽可能达到古代司法语境下“信谳”的标准。只不过证据本身并不会自动显现,且“表达”的信息也并不必然保证绝对的真实性。以家谱为例,其在内容、体例、时间、装订、纸质等方面都可能会存在不真实的情况,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案件的审理进程和审定结果。虽然不可否认无论家谱内容的真伪与否在社会学角度都有其历史意义,但在法律领域则必须要对其进行证据价值的评判,因为这事关当事人权益的保障和国家法律的公信力。由此也决定了如果官员不具备对相关法外知识、社会情理和礼法制度的掌握和了解,其很难完全依靠律文本身实现对案件的公正审理。
注释:
①方大湜,字守一,巴陵画眉湾人,咸丰五年(1855年),以诸生身份入仕,先后历任湖北广济、襄阳等地知县。为官期间“兴学校,课蚕桑,事必亲理,胥吏无所容奸,民亲而信之”,后因樊口毁堤事件受馋贬归。回乡后稀见宾客,著述颇丰,代表作有《方氏世德录》《辨惑录》《团防章程》《修防刍言》《捕蝗纪要》《桑蚕提要》《桑馀提要》《平平言》等,其中《平平言》据作者《自序》中载:“所言平平,无甚高论”,故名。关于方大湜的生平经历请参阅[清]赵尔巽.清史稿(第四十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082-13083。
②李哲在其《中国传统社会坟山的法律考察——以清代为中心》一书中从社会学角度指出:墓田虽然在法律层面属于土地所有权的客体,但同时也是维系家庭乃至家族成员间相互关系的纽带,墓址位置的选择可以有效向外界表明此处地域的“私属”性,并通过安葬逝者这一行为来实现该处土地所有权的代际传承。
③《大清律例》中明确规定:“凡盗卖、换易及冒认(冒认他人田土作自己者),......田一亩,屋一间一下笞五十,每田五亩、屋三间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徒二年。系官者,各加二等。”具体到本案,假设郑昭和郑炳礼无论谁最后在官方判决下得到了该处土地的所有权(手段方式的合法与否在所不论),都有利用该律文内容保护自身既得(即便是通过欺骗手段获取)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可能。
④此处需要明确的是清代伪证现象具有比例高、种类多样、手段高明等特点。究其原因除去部分民众将诉讼作为一种谋取利益的工具和途径外(讼棍),更有当时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缺陷;清代讼状规则中存在很多无证据不予受理的情况,而当事人为了符合官方的应诉标准,便会在特定情况下选择伪造证据以实现其目的。具体请参阅蒋铁初.清代民事诉讼中的伪证及防治[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3)。
⑤原因在于扫墓、祭祖是宗族团体的重要社会活动,自然每年岁首、祖先生辰、清明、四季节日都一定会有后人亲临墓地,这也意味着宗族后嗣与墓田的接触在正常状态下应该是频繁且不会在时间上发生中断的。所以“多年无人祭扫”这一情况背后传达的信息表明至少在当地范围内,该墓中逝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已经失去了与其后人的必要“联结”,由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即使出现第三方且能够有效否定呈控人亲缘关系诉求的可能性很低。
⑥本案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在于原本看似“居中裁断”的审理者在实际承审过程中却处于略显“被动”的位置上。一方面举证环节对官员提出了极高的个人能力要求,因为呈控者单向所提交的证据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迷惑性);但同时逝者本身又已经不可能对这些主张提出对等的反证材料;所以就导致了官方只能“接替”逝者的“职责”去面对具体的证据内容。另一方面清代对审理期限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同时非特殊情况不许无故告诉不受理。这也决定了官员更是只能将案件承接且必须给出具体的审理结果;而一旦被证明出现审理有误的情况,官员自身将可能会面极为严厉的追责处罚。
⑦从族谱本身进行质疑的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郑张氏真实的家族后人对二郑进行指正,即通过另一份血缘证明(实际上在当时也很可能同样是家谱类证据)对二郑所提供的举证内容进行有效否定;其次,乡里周邻有年高德劭之人出现证明,即与逝者郑张氏存在密切的联系且对其后人情况有清楚了解的;再次,对该土地的归属情况有不同的主张(比如遗嘱分配、抵押买卖情况等)并有充分的证明材料;最后,便是通过二郑关系密切之人予以说明,将其归入其他宗族(除去嫁娶、过继、收养等极特殊情况,一人同属两个宗族的可能性很低)自然就可以否定其案中主张的成立。不过由于该案所涉时间较为久远,实际上无形中降低了上述情况出现的可能性。
⑧清《六部处分则例》中要求:“若州县官在扣去初参(两个月)分限之外,尚有延迟,逾限不及一月者,罚俸三个月,逾限一月以上者,罚俸一年。”同时《大清律例》中规定:“凡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论。若增轻作重,减重作轻,以所增减论;至死者,坐以死罪。若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并以吏典为首,首领官减吏典一等,佐贰官减首领官一等,长官减佐贰官一等科罪”;“......凡斗殴、婚姻、田宅等事不受理者,各减犯人罪二等,并罪止杖八十。”这些条文内容直接否定了官员应对案件时的差异情况和困难程度,也就是要求承审官员必须受理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得出正确的审理结果。但“必须受理”“规定时间内”“正确的审理结果”三项同时符合标准要求的情况,实际上在“据证断案”的司法程序下,官员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追责压力,往往很难依靠个人能力和职业操守来保证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甚至为谋取利益,会有意识地阻挠外部力量在后续审理过程中对案件真相的探寻。具体请参阅:石泉.正义的分歧——以清代“杨乃武”案为例分析中央与地方的司法博弈[J].宁波大学学报,20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