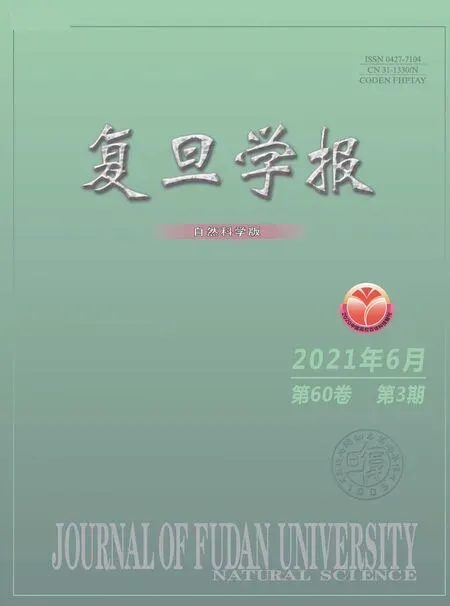基于神经认知科学的音乐对情绪诱发的机制研究综述
2021-12-03田佳宜许敏鹏
甘 霖,田佳宜,许敏鹏,3,明 东,3,周 鹏,3
(1.天津大学 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天津 300072;2.天津大学 国际工程师学院,天津 300072;3.天津大学 医学工程与转化医学研究院,天津 300072)
音乐被广泛用于使听众产生不同情感状态的变化,了解人类大脑对于音乐的响应机制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和分析音乐与情绪之间的关联.不同种类的音乐对于大脑情绪的诱发规律存在一定差异,规律呈现也十分复杂,因此对音乐的情感反应的响应机制研究是一个较为复杂且亟待解决的问题.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EEG)、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等脑成像技术十分有助于研究者逐步探索音乐对于情绪诱发的神经机制.EEG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适用于音乐变化对于情绪影响的及时性捕捉,音乐情感与特定频段之间的关系多通过脑电技术发现;EEG所产生的脑电图是利用头皮上的一系列电压探针进行电位测量,脑电的产生是由于大脑中的电位振荡,即兴奋性突触后电位引起的,电流由丘脑的皮质传入激活顶叶树突[1].fMRI是一种神经影像学方式,具备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其原理是利用磁振造影来测量神经元活动所引发的血液动力的改变,适用于研究音乐诱发情绪过程中不同脑区的响应规律[2].此外,在对于情绪的评估方法上,价值-唤醒环形图表最常使用,作为情绪情感衡量的2维模型,它的横坐标代表对事物感情的效价,纵坐标代表感情的觉醒程度.情感效价是消极到积极的分类,区分正性和负性的情绪,唤醒度是从平静到兴奋,表征情绪的唤醒程度[3-4].
本文旨在探究音乐诱发情绪的机制,分别从音乐诱发情绪在不同频段产生脑电差异、音乐诱发情绪在不同大脑区域中的电生理相应规律以及音乐中不同和弦诱发情感的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效应这3个角度来归纳当前神经认知科学方法对于音乐诱发情绪机制的客观研究成果.
1 采用EEG技术研究音乐诱发情绪所产生的神经机制
1.1 不同情绪效价在额叶区域诱发脑电的不对称性
目前有多项研究结果表明,额叶的脑电不对称性与音乐诱发的情绪处理有着密切关系.
Daly等[5]的实验选择了两段音乐,分别是电脑生成的音乐和古典音乐作为刺激材料,Mikutta等[6]让被试完整地聆听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这两项研究都要求被试受音乐刺激后在价值-唤醒环形图表上报告他们的情感状态来作为评估情绪的依据,之后都发现了当被试报告高情绪效价时,前额在α和β波段都呈现较为显著的不对称性,并且在高唤醒过程中右前额抑制了低α波段活动;其中,Daly等[5]还发现无论是听生成音乐还是古典乐,当被试报告较高的情绪效价时,观察到的α和β不对称性明显更高.Lee等[7]则只选用了悲伤音乐作为刺激材料,分别在被试听悲伤的音乐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时间点测量了前额叶脑电,之后让被试对音乐的“喜爱程度”进行评分(1——完全不喜欢,2——不喜欢,3——不确定,4——喜欢,5——非常喜欢).最终发现,无论初始状态下左右脑的功率分布情况如何,在悲伤音乐刺激下的脑电在大脑中都会发生不对称性.Schmidt等[8]同样对被试的静息状态下的脑电进行了测量,并使用3种表达(产生中性、积极或消极情绪情感)的音乐作为刺激材料,同时请被试对“表达的情绪”和“享受的程度”进行评价.最终发现,左侧额电极位点上具有相对较高的α功率的人比起右侧额电极位点上具有相对较高的α功率的人,对所有刺激的“喜爱程度”的评价都更高.Sushma等[9]让被试分别在第1天和第6天完成贝克的焦虑量表和状态-特质焦虑量表,之后21名男性被试中的11名听了“变化的音乐”(节奏和八度有增量变化的印度传统器乐),另外10名听了“稳定音乐”(没有这种变化的印度传统器乐),每天3次,连续6天.研究发现,在“变化的音乐”中观察到焦虑评分显著较低,并且在α和β波段出现较为显著的额叶不对称,并且α波段更加活跃.
1.2 左右脑对快乐(正向)、悲伤(负向)音乐的敏感性不同
一些研究显示,大脑的左右脑区对快乐和悲伤这两种类型的音乐具有不同的敏感程度:左脑对快乐音乐更为敏感,而右脑对悲伤音乐更为敏感,音乐引起的积极或愉悦情绪由左额叶区域进行处理,而悲伤或不愉悦的情绪由右额叶区处理.
Schmidt等[10]让被试聆听4个管弦乐音乐片段,作品经预评估后其情绪体验分为:强烈不愉快(恐惧)、强烈愉快(欢乐)、沉着愉快(快乐)和沉着不愉快(悲伤).研究发现,不对称额叶的脑电图活动的模式可以区分音乐片段诱发的正负性情绪:在情绪中呈正性态的音乐段落(欢乐和快乐的音乐片段)引起相对较活跃的左额叶的脑电活动,而呈负性态的音乐段落(恐惧和悲伤的音乐片段)引起了相对较活跃的右额叶的脑电活动.在另一项研究中,彭金歌等[11]让被试分别在两个房间里先观看5 min的紧张视频用来诱发紧张情绪,之后一个房间放快乐音乐,另一房间放悲伤音乐,观察在不同音乐作用前后被试的EEG波形能量的变化.研究发现,不同脑区对不同类型音乐刺激的敏感程度不同:聆听快乐舒缓音乐前,左脑区与右脑区的能量变化近似;聆听快乐舒缓音乐后,左脑区能量增强幅度明显大于右脑区的能量变化.同样,在聆听忧伤舒缓音乐前,左脑区与右脑区的能量变化近似;而在聆听忧伤舒缓音乐后,右脑区能量增强幅度明显大于左脑区的能量变化.由此可推断,在紧张情绪的刺激下,左脑对快乐风格的音乐较敏感,右脑对忧伤风格的音乐较敏感.
1.3 音乐诱发情绪过程中大脑在不同波段的能量变化与差异
Hou等[12]根据价值-唤醒环形图表将音乐分为4组,“欢乐”和“平静”组有22个样本,“悲伤”和“愤怒”组有20个样本.研究发现,当被试在听愤怒或安静的音乐时,额叶的各波段能量较高;聆听欢乐音乐时,枕叶皮层区域的θ和α波段能量较高,额叶的β波段能量较高;当听悲伤的音乐时,枕叶皮层区域的α波段表现出更大的活动范围.Naser等[13]探讨了人们对于音乐的喜爱程度对大脑情绪的影响,结果发现,当被试者聆听高喜好程度的音乐时,在α波段中大脑的功能性连接增加;对于低喜好程度的音乐,在γ波段中大脑功能性连接增加.而Balasubramanian等[14]则发现,被试聆听喜欢的音乐时,额区的θ波段能量增加;而当听到不喜欢的音乐时,额区的β波段能量增加.
1.4 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诱发情绪时所产生的脑电差异
在音乐与情绪相关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了本民族的古典音乐作为刺激样本,与西方古典音乐对情绪的诱发结果进行了比对研究,均发现本民族音乐在α、θ等波段所产生的功率变化与情绪的相关性.
卢英俊等[15]发现部分特定种类的中国音乐可以通过诱发α波段的脑电来使这部分被试感到放松和愉悦.他们的实验中要求被试先观看带有悲伤情节的电影片段,诱发悲伤的情绪状态,然后聆听4种不同类型的音乐(中国古典音乐、流行乐、班得瑞音乐和摇滚乐)以及保持静息态(不聆听音乐).研究发现,聆听中国古典音乐时α2(9.0~13.4 Hz)的脑电功率谱重心频率(Gravity Frequency,GF)最高,且显著高于静息态及聆听其他3种音乐时的;此外,被试在安静放松状态下的脑电重心频率是以α节律为主导的,悲伤影片状态下的高频α节律(α2)活动减少且移向θ波,而在聆听中国古典音乐时,整体脑电节律又以α波为中心,α波的节律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外,卢英俊等[15]从功率谱百分比总变化图中还发现,在聆听4种音乐类型时,α1波段(7.5~8.9 Hz)和α2波段的功率谱百分比显著高于观看悲伤影片时的;且α2波段功率谱百分比的变化极其显著,观看悲伤影片时α2波段功率谱百分比约为10%,而在听4种音乐及静息状态下时α2波段功率谱百分比约为40%.此外,聆听4种音乐时α2波段的功率谱百分比排序如下:中国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摇滚音乐>班得瑞音乐.由此可见,使用中国古典音乐舒缓情绪后的α2波段的功率谱百分比最高,与保持静息状态时的最为接近;而以上各种状态时θ波和β波的功率百分比均显著低于观看悲伤影片时的.由于α波功率变化与大脑活动呈反相关,即α功率愈大代表脑活动愈少;同时,α波段功率比其他波段更能反应大脑行为的变化(Fried[16]指出音乐可以使得低代谢的、与觉醒相反的状态加强,即α波增多).因此,综上所述,该项研究表明,对于中国被试群体,部分中国古典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相比,能够使被试更加放松,脑部活动显著减弱.Toropova[17]等研究了俄罗斯民族音乐对脑电信号的影响.实验记录了51名被试(包括30名俄罗斯人和21名中国人)在静息状态下聆听俄罗斯民族音乐时的脑电信号,最终发现两个国家的被试在聆听俄罗斯民族音乐时都展现出α波段功率的增强的情况.Banerjee等[18]探究了聆听印度斯坦尼音乐时脑电信号变化的规律,在3个实验条件(休息、有音乐和无音乐)下,对额叶位置的α,θ和γ脑节律进行频率分析发现,听具有浪漫/悲伤情绪的印度斯坦尼音乐时,被试情绪在α波段的唤醒程度得到了增强,而在γ和θ频率范围内未观察到明显变化.在另一项关于民族音乐引起情感效价的研究中,Tandle等[19]让41位被试聆听了印度古典器乐并记录他们的脑电信号,被试在音乐结束后给出主观评分(0是非常不愉悦,5是非常愉悦),之后通过评分将被试分为欣赏者和非欣赏者两类.研究发现,与右脑相比,欣赏者左脑的额中线θ波段功率显著增加;此外,非欣赏者的左半球的额中线θ波段功率明显下降.该项研究认为,印度古典器乐音乐所唤起的积极或愉悦情绪是由左额叶区域处理的,左额叶区域的激活与否取决于被试是音乐欣赏者还是非音乐欣赏者.一项旨在研究印度传统音乐特性的抗焦虑作用的实验中,Kadir等[20]研究分析了马来西亚传统音乐和摇滚音乐对脑电信号的影响差异.该实验同时记录了被试的静息态、聆听马来西亚传统音乐和摇滚音乐时的脑电信号.结果发现,与摇滚音乐相比,聆听马来西亚传统音乐时,被试大脑的α波段功率增强.
2 使用fMRI技术研究音乐诱发情绪的机制
2.1 音乐诱发情绪时所激活的大脑边缘系统
我们通常认为大脑的边缘或旁边缘系统是涉及情绪加工的核心结构,这些结构的损伤或功能紊乱与情绪障碍有关[21].在有关fMRI的研究中,一些研究发现音乐可以对大脑的边缘结构进行激活,并且音乐的愉悦性会对边缘结构的不同部位产生影响.
Zatorre[22]让被试听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并且将被试听其他被试喜欢的音乐作为控制条件,实验结果诱发了震颤(震颤与大脑边缘或旁边缘系统的核心结构相关).Baumgartner等[23]探索了视觉和音乐刺激对大脑加工的影响,实验选择了高度唤醒幸福、沮丧和恐惧3种情绪的图片作为视觉刺激,以及3段古典管弦乐音乐样本(分别激发幸福情绪、沮丧情绪、恐惧情绪).实验过程中,在观看图片的同时播放诱发相同情感类型的音乐,让被试将自己置于所呈现的情绪刺激所表达的相同情绪中,通过回忆适合情感的生活事件,并看着呈现对应情感的人脸(Schneider等[24]、Tim等[25]、Esslen等[26]在情绪诱导实验中都使用了类似的方法).结果显示,在所有4个电极簇(左前F7/F3/FT7/FC3、右前F4/F8/FC4/FT8、左后TP7/CP3/P7/P3和右后CP4/TP8/P8)中,单独呈现声音刺激的条件下α波段功率活动最大,单独呈现图像刺激的条件下α波段功率活动为中等,而音乐图片组合时α波段功率活动最低.由此认为,音乐与图片共同呈现时要比单独呈现图片或音乐时产生更大的情感激活.此外,从脑的地形图中可以看到在音乐图片组合条件下大脑的枕叶、顶叶、额叶和颞部具有最低的α波段功率活动,表明大脑的枕叶、顶叶、额叶和颞部的皮质激活最强,情感激活最强.Koelsch等[27]用愉快和不愉快的音乐作为实验材料唤起情绪,并且使用fMRI来确定情绪处理的神经相关因素.实验中使用的愉快音乐片段是音乐家演奏的欢乐的器乐乐曲,而不愉快的音乐片段是原始音乐片段的不协和延续版本.结果显示,与聆听愉快的音乐相比,聆听不愉快的音乐时,t映射图在在左侧海马、左侧海马旁回和右侧颞极表现出更加显著的激活;此外,不愉快音乐激活了左杏仁核,愉快的音乐则激活了腹侧纹状体以及脑岛的BOLD(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信号.这项研究表明了杏仁核、海马结构以及腹侧纹状体可以被不同类型的音乐所激活.Cheung等[28]采用fMRI的方式来探讨和弦与诱发大脑愉悦度之间的联系.首先,使用了马尔可夫模型得到音乐中每个和弦的不确定性和惊讶程度值,根据拟合得到的与音乐的愉悦度具有显著相关性的变量.结果发现,音乐的高惊讶程度伴随着低愉悦程度、低惊讶程度伴随着高愉悦程度,而这种愉悦度和惊讶程度相关关系与杏仁核、海马前部和听觉皮层有关.已有的研究表明[29],不确定性和惊讶程度是大脑皮层信息传递中预测-编码模型的主要成分,该项研究认为音乐正是通过鼓励个体对其和弦产生预测并对预测进行核对来诱发情绪的.
2.2 音乐诱发情绪与多巴胺的释放有关
一些研究显示,聆听愉快音乐会激活负责奖赏以及愉快体验的脑结构,引起多巴胺的神经活动,从而达到缓解情绪、减压放松的效果.
Salimpoor等[30]要求被试在fMRI环境中聆听自己喜爱的音乐片段,之后在每个音乐片段结束后,做出愿意花多少钱购买这些音乐的决定.实验结果发现,人们在聆听自己喜爱的音乐时,中脑边缘的纹状体区域得到激活.而且,在聆听那些愿意支付更高价格购买的音乐片段时,伏隔核的激活水平更高,伏隔核与听觉皮层、腹内侧前额叶等音乐加工脑区的功能连接也更强.该项研究认为,由于纹状体与伏隔核是大脑奖赏系统的一部分,对增强生物适应性行为有重要作用,大脑的奖赏系统会激活并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从而获得愉悦感.因此,人们在聆听自己偏好的音乐时,奖赏脑区的激活以及由此诱发的愉悦感可能就是音乐减压的重要原因.Fritz等[31]发现腹侧纹状体的激活与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VTA)和下丘脑的激活有关.而这表明腹侧纹状体的血液动力学变化反映了多巴胺的神经活动,研究认为这是由于伏隔核部分受到脑干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支配,是“奖励环路”的一部分.
3 音乐诱发情绪响应的ERP研究
通过ERP方法可分析与刺激任务相关的锁时EEG信号变化来研究大脑皮层中信息处理的动力学机制[32].
Brattico等[33]开创性地采用音乐家制作的180个简短的音乐片段作为刺激材料,每个片段由5个和弦组成,其中前4个和弦持续500 ms,最后一个和弦持续1 000 ms.根据西方音调音乐理论[34]最后一个和弦可以以3种方式作为结束,分别是与前面的和弦一致、不一致以及模棱两可.这样得到的音乐材料不会与特定的音乐流派直接关联,避免实验结果受到个人音乐喜好的影响[35-36](在此之前,有关音乐诱发ERP的研究[37-38]通常会选择已有的西方古典音乐作为刺激材料).在实验过程中,被试需要完成正确性判断任务和喜好判断任务:正确性判断任务为“正确”、“不正确”;喜好判断任务为“喜欢”、“不喜欢”.实验结果表明,对音乐片段的喜好判断要慢于对相同音乐材料的正确性判断,这是因为被试对于喜好的判断需要对音乐的感知和情感内涵进行评估,这个过程涉及前额叶皮层,而不是自动快速的皮层反应,直接将外围听觉过程与边缘系统联系起来[39-40].研究还发现当被试对听到的音乐表示“不喜欢”时,大脑右半球的ERP会在大约280 ms时出现负电位峰值.除此之外,对于喜好的判断任务会在大约1 200 ms时引起晚期正电位.
音乐中,和弦可以说是保留情感信息的最小音乐构件.大和弦通常被认为是产生正向情绪的声音,小和弦则被视为产生负向情绪的声音,但这些情绪在早期是如何形成的一直有所争议.Bakker等[41]给被试同时呈现面部情绪刺激和音乐和弦刺激,被试在看到开心、悲伤和中性的面孔图片时会同时听到大和弦或小和弦音乐.研究发现,当呈现给被试的音乐和弦和面部刺激属于同一情感类别时(如开心的脸配上大和弦或伤心的脸配上小和弦),ERP中P1和N2成分的振幅减小,这代表着情感的处理过程更加便利.这表明和弦确实具有情感内涵,可以让听众在听到音乐的最初的200 ms内进行处理,也证实了大和弦和小和弦具有深厚的情感联系——小和弦可以引起消极的情感,而大和弦可以引起积极的情感.
之前的一些研究[42-43]发现听众能够根据音乐规律预测特定的音乐事件,并能够发现和弦序列中的不适宜的和弦.Koelsch等[44]发现早期右半球优势的负电位可以作为对和弦序列中不适当的和弦的响应.该项研究从商业CD中摘录古典钢琴奏鸣曲的节选,在和弦序列的末尾会分别出现预期的和弦和意外的转调和弦两种情况.在每次试验后,要求被试按下响应按钮,以指示上一个音序是否包含转调和弦.该实验的ERP数据结果表明,与调内和弦相比,转调和弦的负电位出现在180到350 ms之间,在转调和弦开始后的250 ms内最大.这种作用广泛分布在中央颞叶上,并在右半球占主导优势.负电位出现后,正电位开始于额叶出现于约320 ms时,于顶叶出现于约370~400 ms时.这些电位在前期窗口(350到450 ms)以及后面的潜伏期窗口(从大约500 ms开始)中都会出现峰值.这表明转调和弦的效果在两个时间窗之间的头皮分布不同.
4 结 语
音乐治疗是计算机音频在医疗健康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子领域,其中,音乐对于情绪的作用是音乐治疗的基础,而音乐的种类非常复杂,针对音乐神经认知研究涉及的维度较多,学科交叉性与专业性较强,国际上兼具神经认知与音乐理论学科交叉能力的研究团队较少,如果想实现音乐对于情绪的调控,诸多基础科学问题仍需完善.与此同时,随着神经科学的不断进步,有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可以帮助人们探索音乐对情绪影响的神经机制,可以利用不同技术的特点多角度进行研究.例如:通过EEG技术我们可以捕捉神经信号的特点,而fMRI技术则让我们更清晰更直观地发现大脑的生理变化.目前,在EEG、fMRI、ERP等类型实验过程中,对于音乐情绪的研究多使用演奏家的音乐作品或商业CD中的歌曲作为刺激材料,如果能够进行更为具体的音乐结构和元素对于大脑和情绪的影响以及效能音乐的研究,这些发现将对脑认知与发育、音乐教育、心理治疗等应用领域产生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