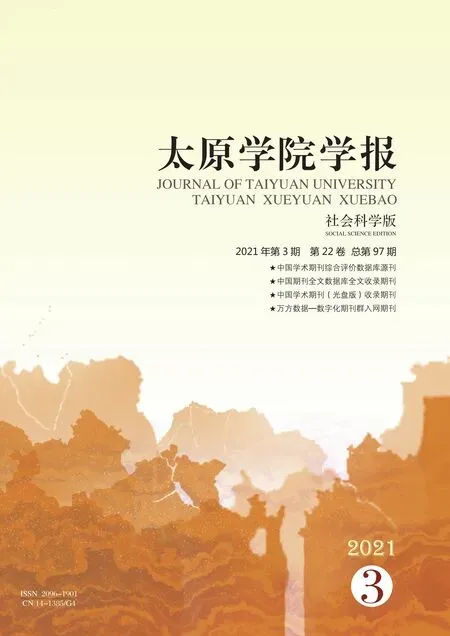谈鲁迅加入左联的四个问题
2021-12-02管冠生
管冠生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一、为什么要联合鲁迅?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立三路线’时成立的”[1]337,李立三在叫停与鲁迅论战、团结鲁迅筹建左联这件事情上是发挥了关键作用的。那么,他是出于何种动机与目的要联合鲁迅呢?
一种新观点认为,与此前中共高层轻视文学活动不同,1928年下半年负责中共中央及宣传部工作的李立三重视文学工作,对鲁迅尤有兴趣,“在‘革命文学’论争极大紧张了鲁迅与中共关系的背景下,李立三主动向鲁迅伸出橄榄枝,固然服从于中共文艺发展的目标,仍然需要面临不小的党内压力。这一决策的制定,可能同样植根于李立三较深层次的个人志趣。据1946年任李立三秘书的蓝漪回忆,李立三当时曾向其表示,特别喜欢鲁迅《二心集》中的作品,其中《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篇,‘从前我都能背出来’。而《二心集》所收,正为1930至1931年间鲁迅的作品”[2]。
据此,李立三的“个人志趣”是喜爱鲁迅的作品,故此才与之前的领导人不同,要团结鲁迅。这看上去有道理,细察则论据与论点并不匹配。团结鲁迅、筹建左联是李立三1929年下半年便有的设想,如何以他喜欢1930—1931年间的鲁迅作品来例证1929年及之前的“个人志趣”呢?假若能提供李立三爱读《呐喊》《彷徨》等作品的证据,那才是有说服力的。
不妨说,李立三联合鲁迅是要利用鲁迅的名人效应来为自己的路线主张服务。
二人有过一次会面,时间是1930年5月7日晚(1)王锡荣《鲁迅与“左联”》(载《上海鲁迅研究》总第78辑)认为使得鲁迅愿意加入左联的原因之一是“李立三亲自找鲁迅谈话,明确表明创、太二社对鲁迅态度的错误,并希望与鲁迅联合”,并认为“这对鲁迅是有说服力的”。此处需考虑:李、鲁见面是在左联成立之后,以左联成立之后的事情作为鲁迅愿意加入左联的原因是否合适?(同样的问题出现于本文前面所谈论的“新观点”)。据冯雪峰回忆,李立三希望鲁迅公开发表一篇宣言,表示拥护当时的各项政治主张,鲁迅则和他“各人谈各人的”,没有同意[1]250;据胡愈之回忆,李立三要在上海搞大规模示威游行,对鲁迅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在周建人的回忆中,李立三说的是“你在社会是个知名人物,有很大的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1960年3月1日许广平见李立三,请他回忆一下和鲁迅见面的情况,李立三谈到了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认为“鲁迅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这是事实;但创造社有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个别人也有骂名人藉以出名的思想”[3]。
对会面谈话的内容,冯、胡、周、李四人的回忆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皆以鲁迅是名人为意识中心,尽管冯雪峰的回忆没有明确出现李立三说鲁迅是名人(2)在《回忆鲁迅》中,冯雪峰就说得明白了:“为什么鲁迅先生改变了阶级立场,影响会那么大呢?当然因为他在文学上的地位高,他的名誉大,他拥有广泛的群众”。(见《冯雪峰全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61页)。几十年后,李立三以为创造社个别人“有骂名人藉以出名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那么,当年他团结鲁迅时是否超越了、摆脱了这个“思想”呢?本文认为,无论是骂鲁迅,还是联合鲁迅,实质都是拿鲁迅做“梯子”。这虽然亦只是一种“可能”,但看起来更符合历史情境、更可信一些;对李立三来说,可能还是他联合鲁迅的最重要的心理动机。
二、鲁迅“错了”的到底是什么?
在研究鲁迅“向左转”的时候,“人们特别喜欢引用”[4]或“被征引最频繁的”[5]一段话,出自《三闲集·序言》(引文一):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而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若查阅相关研究文献,我们很难见到能完整引用并解释这段话的。大概是为了节约篇幅,常用“……”代替某些话,如代替“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这样,引文一前两句话就变成了“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于是“错”就直接指向了“相信进化论”,于是引文一就被解释为“经历过1927年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鲁迅对进化论和‘青年’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也动摇了他启蒙的信心”[6];简言之,进化论被“轰毁”了。
对自己的文章,鲁迅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3)见《答北斗杂志社问》,《鲁迅全集》(四),第373页。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又说:“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见《鲁迅全集》(四),第526页),那么,为什么我们引用时用“……”代替的字句鲁迅不删去呢?难道鲁迅遣词造句、表情达意的能力不如我们?这个疑问可以排除。情况只能是:我们用“……”代替的字句是不应该删去的,它表明我们对引文一的理解还不全面与准确。
仔细看引文一,鲁迅对青年先后用了“敬重”和“敬畏”这两个词(可视为同义词):先前“敬重之不暇”,后来“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因为他在广东看到某些青年坏起来、杀起人来更可怕。如是,鲁迅说“我明白我倒是错了”,哪里错了呢?按其本意,是先前那样“敬重”青年错了,意即先前不该那么看重珍惜青年,当他们给“我”十刀的时候,就应该还他们十箭。
因此,错了的是敬重的态度,而不是进化论思想。另一个证据就在《三闲集·序言》的最后,鲁迅这样写道:“因此译了一个普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意思很明确:进化论可以信,但不能“只信”。“只信”就是“偏颇”,而鲁迅不再偏颇了。换言之,“进化论是不够的”(4)冯雪峰《鲁迅回忆录》,原载1946年10—12月《文汇报》。(见《冯雪峰全集》(5),第203页)说“进化论是不够的”显然并不意味着进化论错了。事实上,没有一种理论思想是万全的、万能的。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而加以发展充实,鲁迅进化论思想亦是如此。。
“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鲁迅本以为青年才有将来,然而青年之间对立杀戮的事实告诉他这个思路有问题。那么,它轰毁之后变成什么了呢?可以肯定,不是反过来,以为“过去必胜于将来,老人必胜于青年”。答案应该从《二心集·序言》里寻找。
《三闲集·序言》作于1932年4月24日,4月30日鲁迅完成《二心集·序言》,两者应合而观之。后者写道:“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据此,不是青年而是无产者才有将来。原先的区分与对立是“老人/青年”,如今是“资产者/无产者”,鲁迅的视野已经注入了阶级斗争的新内容。
那么,进化论被阶级斗争学说完全排斥出去了吗?不妨认为进化论仍然发生作用:既然无产者是“新兴的”,按照进化论的思路,新兴的会战胜、取代旧有的,那么“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作为一个信念就更容易被接受,而阶级斗争则为鲁迅提供了新的思想斗争的武器。在鲁迅那里,进化论与阶级斗争学说可以并存且互相取用,并非你来我必去、水火不相容。
但鲁迅不是无产者,不是“一个普罗列塔利亚作家”(5)这是鲁迅1930年9月17日在自己五十寿辰庆祝会上的演讲内容之一。(见于史沫特莱《追念鲁迅》,原载《文学》1937年第9卷第4号,收入《鲁迅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第200页),他确信无产者才有将来,但他并不和无产者生活、战斗在一起,他与之战斗的是青年。虽然说思路已毁、乐观不再,遇到那些需要帮助、值得帮助的青年,鲁迅仍然提供帮助与支持。其实,鲁迅最愿意与志同道合的青年结成亲密的战斗的小团体。当柔石向冯雪峰介绍鲁迅时,冯雪峰“第一个感觉是柔石好像完全浸在慈父所给予的爱里了,而在这一个被爱者的心中所反映出来的鲁迅先生,也竟像是一个近于老年的万分恳切慈爱的父亲似的”[7]。
只是,像柔石、冯雪峰、瞿秋白这样的青年可遇而不可求。
三、如何理解“梯子”之论?
普遍认为,“梯子”思想是鲁迅加入左联的重要原因。它出自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信:
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华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学界对此解释颇有不同。有研究者择取部分(尤其是“倘使后起诸公……也无几了”),“明白地看出,鲁迅决定这一行动(指加入左联——引者注)时的清醒的自我牺牲意识,没有什么冲动。受一种神圣使命的召唤,为他人,为中国,牺牲个人,而且似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正符合他的一贯精神”(6)见曹振华《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的对立统一——关于鲁迅与左联关系的思考》。(《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期)另有研究者的表述——“鲁迅对左联的事业有一定的牺牲心理”——就婉转宽松了。(姜肖《论晚年鲁迅与后期左联青年的矛盾》,《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有研究者则看到了鲁迅对左联内部严重宗派主义倾向的反感,认为“鲁迅在不断的委曲求全中,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与冷静,试图和‘左联’一些人物保持团结合作的关系,尽自己的梯子之责,从而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奉献力量”[8];有研究者则单独拈出“茄花色”,认为“在鲁迅的内心深处,他实在以为于左翼文化内部,只有自己的意见或观点才会符合现代中国进步文化的发展方向,其他人的意见那就不过尔尔,皆‘茄花色’了。‘茄花色’乃绍兴方言,系鲁迅在‘左联’成立会上对于另外一些成员的观感,是并不怎么好看或者不过如此的意思,这个观感其实在鲁迅晚年已经形成了一个深刻印象,而且随着他对周扬等人反感的加强,这个判断就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思维定势了”[9]。
让我们仔细看待鲁迅的原话。首先注意“熟虑”这个词,它表示细致、认真、反复地考虑,那就意味着鲁迅对自己加入左联做梯子的事既不是一时冲动,也很难看出有什么“神圣使命的召唤”(既有“神圣使命”召唤,又何必熟虑?)。其次,注意鲁迅前面说“应青年之请”,后面则说“上海的革命作家”。意思很明显,“青年”和“上海革命作家”不是一回事。鲁迅所说的“青年”大概只是出席左联成立大会的柔石和冯雪峰等少数几个,而“上海革命作家”包括鲁迅点名批评的曾向自己进攻的创造社和太阳社诸人,认为他们“力量实在单薄”“专事于吹擂”。“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表明鲁迅并不心甘情愿为之作梯子(“险”字表明鲁迅有疑虑、抵触之情绪),“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表明鲁迅其实看得明白,虽然现在坐在了一起,但“他们”也未必瞧得起自己——“他们”所指不是“青年”,而是“上海革命作家”。
甘为人梯、助力青年成长,固然是大好事,但鲁迅所说作梯子、爬梯子,有被别人使用或利用之意。这种感觉总是叫人不爽快,且不说有人爬得高了,就忘了梯子,撤了梯子,甚至毁了梯子(所谓过河拆桥或卸磨杀驴),令人心寒。可以说,鲁迅不愿作这样的梯子。举个小例子:以鲁迅《我的失恋》被抽调为导火索,孙伏园辞去了《晨报副刊》编辑,接下来办了《语丝》杂志,鲁迅是竭力呐喊的一个,使前者颇受了打击,孙伏园乃对鲁迅说“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鲁迅就觉得“这‘炸药’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而粉身碎骨”,虽然以后继续投稿,但“对于意外的被利用,心里也耿耿了好几天”。孙伏园和鲁迅关系一直不错,觉得被利用尚且不痛快,被前年乱咬自己的创、太社使用,心里能痛快吗?鲁迅吸引人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能实话实说,能把自己的复杂感受真切不遗地表达出来,他不是一个“不断的委曲求全”以便让自己做一个好“梯子”的人。
鲁迅绝不希望与青年结成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他提供帮助,但不愿意从此被绑定(7)有些刊物要求老作家每期投稿,鲁迅说:“新产生一刊物,由老作家稍为帮助一下,三两期后,便能自己办起来,像《译文》初时情形一样,那是对的。如果每期都需要帮助,好像背着一个人走钢索,不但走不动,而且会有使背的人跌下去的危险”。(见许广平《片段的记录》,原载1936年11月5日《中流》第1卷第5期,收入《鲁迅的写作和生活》,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他更希望与青年彼此汲取力量,并从青年那里获得新鲜的东西。如冯雪峰所说,鲁迅待柔石如爱子,同时又从柔石那里获得教益,得以自我省思、自我振作、自我成长:“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并“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使他反省到柔石这“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他“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再如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秋白同志在上海的两年半中,著译工作那么勤勉,是因为革命文学运动的战斗的需要,但同时鲁迅先生的热情的鼓舞也曾经分明地起了作用。在鲁迅先生方面也同样,他那几年的战斗性的昂扬,就不能不说和这个战友的热情的鼓舞多少有一些关系”(8)《回忆鲁迅》,见《冯雪峰全集》(4),第293页。限于篇幅,本文对二人关系的良性互动不作展开。。就此来看,认为鲁迅觉得“自己的意见或观点才会符合现代中国进步文化的发展方向,其他人的意见那就不过尔尔”就是一种偏颇了。
四、加入左联的心理关节如何打通?
可以说,面对广东青年屠杀青年的事实,鲁迅并没有走向自我封闭的极端,而是仍然在采取敞开的行动与斗争。只是在加入左联这个问题上,鲁迅有一个心理关节需要打通,这个关节就是:创造社与鲁迅本要合作,但不久反过来掉头攻击鲁迅,后来党叫停了这场论战,要求创造社等联合鲁迅筹建左联,尽管有柔石和冯雪峰施加影响,但鲁迅总要“熟虑”跟这些反反复复的人合作到底值不值得、有没有用?换言之,到底以什么样的理由与态度跟这些人合作?因为鲁迅对创造社等人早就有了“茄花色”的认识,如1929年4月7日致韦素园信中便说:“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有些则简直是军阀脑子”(9)1928年4月9日致李秉中信中亦写道:“此地有人拾‘彼间’牙慧,大讲‘革命文学’,令人发笑。专挂招牌,不讲货色,中国大抵如斯”。关于创造社与鲁迅的分合,可见朱正《一个人的呐喊》第223-238页。。
在对历史与人性深刻洞察的基础上,鲁迅以一种包容原则解决了这个心理问题。在左联成立的前一天,1930年3月1日的《萌芽月刊》发表了鲁迅的《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其中写道:
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行进。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10)见《鲁迅全集》(四)第231页。1933年6月26日致王志之信中亦说:“这大约无论怎样的革命,都是如此,倘以为必得大半都是坚实正确的人们,那就是难以实现的空想,事实是只能此后渐渐正确起来的”。
这是鲁迅“熟虑”的结果,并以此说服自己再次加入团体:不必过分担心个体的动机与目的之分歧,只要团体在行进与战斗,那就会成长为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1933年6月26日致王志之信中亦说道:“这大约无论怎样的革命,都是如此,倘以为必得大半都是坚实正确的人们,那就是难以实现的空想,事实是只能此后渐渐正确起来的”。《语丝》提供了一个先例。按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所说,《语丝》创办时“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十六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顾颉刚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说,和《语丝》的喜欢涉及现在社会者,倒是相反的”,后来,“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个人,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成为一支“纯粹,精锐的队伍了”。鲁迅对《语丝》经验的叙述表明他充分认识到了战斗团体养成过程的曲折性与复杂性。
《我和〈语丝〉的始终》发表于1930年2月1日的《萌芽月刊》,和3月1日发表的《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共同见证了鲁迅对加入左联进行自我心理说服的过程。当然,这个自我说服的工作早就开始了。在1928年3月12日发表的《“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中,鲁迅质问创造社“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后者一直没有回答,鲁迅好几次与冯雪峰谈到这个问题,说:
明白了真理之所在,如马克思所说,转移了阶级,自然是好的;或者为了自己也受压迫,为反抗起见,或者只为了良心,愿意帮助被压迫者,自然都是好的;但从自身将来的利害计,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道破了利害,不算就是揭穿了小资产阶级的灵魂!(11)见《回忆鲁迅》,《冯雪峰全集》(4)第240页。鲁迅接着说:“只是要问,果真相信自己看准了么?……何况还要看更切近的利害。最后胜利是必然的了,然而倘若还很遥远,眼前却是性命交关的斗争,——怎样呢?这就真的要看小资产阶级的灵魂了”。鲁迅看问题是透彻的。
对人心、人性的认识是如此真实而深刻,才能包容不同的动机与目的。但同时,鲁迅也应该看到了左联与语丝社不同。《语丝》的投稿者是孙伏园“独力邀来”的,而鲁迅一开始就介入了左联的成立事务;《语丝》的成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而左联一开始就存在着斗争。表现之一便是鲁迅三番两次点名批评成仿吾是一个“纸张上的革命家”,“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东窜东京,西走巴黎”。在鲁迅看来,成仿吾不只是成仿吾,而是代表了“上海革命作家”这个群体。对他们就要斗争,及早打预防针,尽量避免“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的情况出现。故此,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演讲就很刺耳。演讲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核心观点是“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今后应注意的几点”,无论是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还是“战线应该扩大”,还是“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还是“在文化上要有成绩,则非韧不可”,还是联合战线要有共同目的,皆可视为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防止左翼作家变成右翼作家,如何防止左联成为右联。
事实证明,左联远比语丝社要复杂,尽管鲁迅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恐怕其复杂性还是远远超过了鲁迅在先的评估。只是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就略去不提了。
结语与补充
李立三做出联合鲁迅的决定乃是借重鲁迅的声望与社会影响力,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却可能是最重要的。而鲁迅并不是纯思辨型的思想家,他的思考基于并来源于自身体验,如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信所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同样,1927年的“清党”使他不再相信“青年必胜于老人”,但也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所有青年都失去信心,因为人心不齐,有好的青年,也有坏的青年。即便只为请他出面的“好的青年”,他也应该加入左联(12)在1933年8月1日致胡今虚信中,鲁迅写道:“好的青年,自然有的,我亲见他们遇害,亲见他们受苦,如果没有这些人,我真可以‘息息肩’了”。。尽管鲁迅在左联过得并不愉快,但他的选择表明:行动和斗争仍然是最值得考虑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