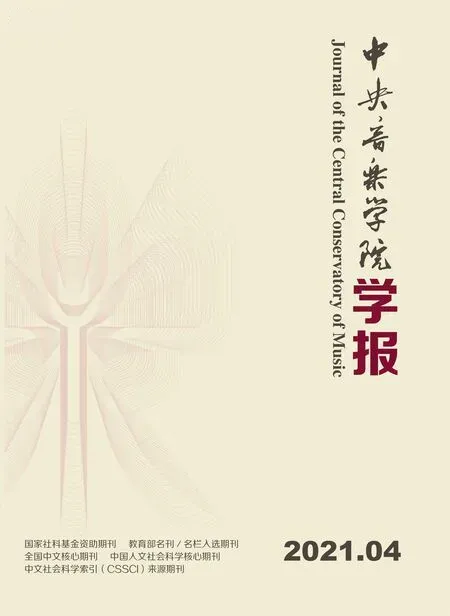《离散、认同与融合:印度尼西亚华人表演艺术的文化语境与演出形态》
2021-12-01杨民康
杨民康
蔡宗德教授的新书《离散、认同与融合:印度尼西亚华人表演艺术的文化语境与演出形态》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作为新世纪以来台湾学者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音乐民族志理论著作,该书在海上丝绸之路与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领域无疑有其不凡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我与该书作者虽然是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学者,但在学术研究经历和学术偏好上有不少相似之处:我们的博士论文都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他研究北方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音乐,我研究云南傣族的南传佛教音乐;我们面对的都是异文化,继而都转向了东南亚音乐的研究。当然,他由于研究伊斯兰教音乐的缘故,一开始转向了东南亚外圈——海岛国家印度尼西亚音乐的课题研究;而我因为研究的是南传佛教音乐,便转入了东南亚内圈——陆路国家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的音乐研究课题。此外,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工作期间,曾经经手了他的多篇印度尼西亚音乐研究论文的编辑工作,通过对他的著作、论文的了解,我发现他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学术视野非常宽广,研究对象多种多样,对于印度尼西亚音乐,从古典到现代,从宗教到世俗,从传统到变异,从传承到建构,从离散族群到文化认同,他都有细致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联系到以往自己从事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或与之对象相近、有更多人从事的世界音乐研究,我始终抱着一个期望,即这些研究在得出自身结论的同时,也能够对中国自己的音乐文化研究有所帮助,起到一点反哺的作用,那就最好不过了。看了宗德教授的这本书,感觉我的上述期望在书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下面,我想结合蔡著对我的研究给予的启示,来谈谈它所拥有的学术贡献和理论性特点。
第一,蔡著的印度尼西亚华人音乐研究是中国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外向性拓展,在东南亚文化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拥有特殊的学术地位和文化意义。
蔡著研究的印度尼西亚华人音乐与我研究的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分布在东南亚的外圈和内圈,在地理上分别具有海岛和内陆的特点。两千年前印度文化大举南下,兵分两路,其中一路便由海路,经马六甲海峡前往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另一路经由陆路到达缅甸,再到内圈的其他国家。而我们的学术追踪,也一样是循此“由内向外”的途径来到自己的学术目的地。就此来说,蔡著的印度尼西亚华人音乐研究与我目前所从事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有密切的交集。但是,我们的研究起点和终点与同样是研究印度尼西亚本土族群音乐的孔斯特(J.Kunst)、胡德(M.Hood)和研究泰国音乐的米勒(Terry E.Miller)等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不一样。相对于我们的“由内向外”,带有跨界族群比较研究课题性质的研究视角,他们做的是具“世界主义”和“客位”的眼光,带有定点个案课题性质的研究。由以上课题性质和出发点的不同,带来了研究策略和方法上的区别。
蔡著提出,印度尼西亚华人历史与社会文化一直是国际学界重要的研究领域,除了因为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占有一定程度的人口数外,华人在印度尼西亚无论在经济、社会与政治等层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加上近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影响力,也确实提升了许多印度尼西亚华人的社会地位,因而让更多的学者投入印度尼西亚华人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移民史、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等方面,至于表演艺术相关研究则相对不足。再从我们局外学者的角度看,以往由于西方学者多年来在印度尼西亚音乐文化研究领域的深耕细作和不遗余力地推广传播,以加美兰为代表的印度尼西亚本土音乐文化在世界学坛已家喻户晓,广为人知。而华人音乐文化的情况,却如蔡著所言,尽管华人人口只占3%,经济文化上却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以致人们一般只知道印度尼西亚华人有经商的才能,对其包括音乐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却一无所知。对此,从蔡著引述国际知名跨性别舞者郭俊安(Kwee Tjoen An)的一段话里便知端倪:“华人也不只是在商业上有成就,很多华人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传统文化艺术上的精彩表现,并不亚于商业上的成就。只可惜,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受到应得的关注。”(第3页)而华人以其经商的头脑和能力,帮助印度尼西亚本土音乐文化广泛传播并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和作用,亦如印度尼西亚民族音乐学者苏玛山(Sumarsam)所言:“爪哇艺术与文学透过华人出版商得以传播,事实上华人在对印度尼西亚传统音乐甘美朗与戏剧演出的支持与维护上不遗余力,华人在发展商业性戏剧演出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大大促进了爪哇宫廷艺术被一般大众接受的可能性。”(第78页)在此情况下,尽管华人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重要的成员,民族音乐学界也已经注意到印度尼西亚华人研究的重要性,但实际以印度尼西亚华人表演艺术研究为主的欧美学者并不多见,蔡著在此研究领域据有的学术贡献和所发挥的作用便十分的难能可贵。在本书中,蔡著以8个章节的篇幅,讨论了华人带到印度尼西亚的音乐戏曲品种如布袋戏、八音的传播、传承和发展变迁;印度尼西亚华人通过爪哇皮影戏、中爪哇舞剧瓦扬翁(wayang wong)的参与建构,对印度尼西亚音乐文化整体建设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新时期产生形成的新的城镇通俗音乐卡拉OK音乐的产生和生存状态等,为上述印度尼西亚华人音乐文化的研究填补了知识性、资料性和学术性观照等多个层面的空白。
第二,蔡著通过对印度尼西亚华人音乐进行的广泛、深入的田野考察,细致入微的观察了解,全面、完整的音乐民族志描写和丝丝入扣的阐释性分析,对华人音乐艺术文化在海外的创造性发展及汉文化与周边国家和民族跨区域文化交融提供了很好的解释。
根据蔡著的介绍和分析,再加上我本人的认识和解读,长期以来,印度尼西亚华人为了在陌生的异土他乡保持和传承传统文化历尽艰辛,排除万难,一路行走至今。在其本地文化适应过程中,华人在其固有原生文化顺向传承的基础上,再经过无数次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催生了现有的华人艺术文化体系。就此而论,华人布袋戏与爪哇华人皮影戏都属于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仅从表层现象看,两者最大的不同可能就在于,华人布袋戏是在来自闽南布袋戏的基础之上,添加了印度尼西亚传统艺术元素;而爪哇华人皮影戏却是在印度尼西亚传统皮影戏的基础上,吸收来自于华人布袋戏中的故事与戏偶形态等元素。其中,布袋戏是一种来源于中国华南地区广东、海南、福建的,历史较悠久、影响较大的华人戏剧。我接触蔡文以来,一直有两个满感兴趣的问题:一个是中国流入东南亚的华人戏剧种类甚多,为何只有布袋戏能够流传下来?另一个是为何如今布袋戏的操偶师除了个别人外,与乐队伴奏人员一样,其表演活动多由印度尼西亚当地人掌控。我在爪哇岛考察期间初见其事,就觉得十分好奇。进一步接触蔡著之后,所受的启发是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在印度尼西亚华人文化的本土适应及文化交往过程中,布袋戏一定会存在来自内部的舞台表演环境下,由艺术表现手段和语言操作能力带来的文化沟通、学习和相互理解的问题;同时也由于外部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条件的影响,会对这种表演手段和语言能力的发挥和运用及转换带来影响和不同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下,布袋戏和皮影戏不需要真人上台表演,其“演员”及器乐和戏曲伴奏音乐都不涉及直接的语言表达问题,这种“无身份、性别”的符号表现形式,便为华人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为了保存其传统文化内核,而对表现形式加以伪装、履行甚至隐匿提供了方便。所以,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应该首先是同这些表演类型不像其他戏剧在表现形式上有那么大语言障碍,易于在异文化族群之间传承、传播有关?而在此表象背后,却还有着更深的社会和政治原因。
据蔡著介绍,受20世纪60年代印度尼西亚“新秩序”排华运动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华人艺术文化当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真空,存在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像华人布袋戏那样,以换人(将华人操偶师和乐队演奏员改换为印度尼西亚人)和换语境(因前述做法而将华人剧种的“族性”暂时改换为印度尼西亚人,以掩人耳目)的方式暂时生存下来(第6章);另一种是像华人皮影戏那样,由于受制同样外在环境影响的原因,在此期间彻底消失了一段时间。若从表现形式上看,如果华人布袋戏的这种形态变异是属于易芯——“旧壶装新酒”的话,华人皮影戏的变异就属于借用——“换汤不换药”。究其根源,这两种发生在艺术形态上的变异,都与在印度尼西亚推行的“新秩序”排华运动有关。在这次运动中,华人表演大型戏剧的活动受到官方禁止,只有依靠本地人的参与传承和主持表演,畸形地维持本地的就业水平,才能通过官方的审查,亦间接地保证了这项华人演艺文化的异地传承。所以,他们以布袋戏为代表的传统戏剧能够传承至今,是与印度尼西亚本地人的参与性传承有很大的关系。当时遭到禁止和排斥的,还包含华人的各种宗教信仰,而佛教是其中唯一幸免于难的。因为印度尼西亚政府认为佛教来源于印度,不是源自于华人。于是,“聪明的华人就只能在佛教的掩护之下,在佛教的寺庙当中供奉其他华人所信仰的神祇,例如妈祖与观音等等,并且仍旧维持华人以当地信仰中心的所在地,为联系维持感情交流之场所的传统。”(第17页)其实,从蔡著中披露的以及我自己考察的情况看,亦有相当多的华人传统音乐和戏剧表演艺术,也是借助于佛教寺院乃至带有伊斯兰教性质的宗教或民俗场所,变相得到保护和传承的。此外,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如今主要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尼西亚,如同我曾经关注过的大乘佛教遗址婆罗浮屠塔寺、印度教遗址普兰巴南神庙等能够长期留存下来一样,既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又因为其中隐含的对于其他宗教文化相对的理解和包容,而给人以些许欣慰之情。想想,若此类事件发生在泰国、缅甸、柬埔寨这类全民信仰佛教的东南亚国家,就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奇怪。记得我在缅甸景栋做田野考察时,就看到那里有一些华文学校,就因此以佛教做掩护;也有由华人主持的佛教寺院里,包括汉传佛教音乐和其他寄寓于此类文化场所表演的戏曲(如布袋戏、皮影戏)在内的传统艺术,也都因为其佛教“外壳”的“源自印度”和所在国全民崇尚佛教的原因,而躲过了一次又一次针对华人文化的文化清洗,最后终于熬到了社会开放,华人文化重获尊重的那一天。由此看,对于佛教的利用,显现了印度尼西亚华人于戏曲表演形式之外,对其他文化表达方式同样加以借鉴、“挪用”的“聪明、机智”之举,或曰某种突出的文化适应能力。
再就已故著名华人江段新所创造的爪哇华人皮影戏来说,这是一种在爪哇皮影戏基础上衍化而成的戏曲类型。在表演方式上,“华人皮影戏操偶师一样要在演出前念诵爪哇传统经文(mantra),并深入理解爪哇传统喀嘉文(kejawen)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操偶师也必须完全理解爪哇甘美朗(gamelan)演奏曲目(gendhing)以及爪哇传统歌曲,也因此所有华人皮影戏操偶师也都必须要会演奏或演唱传统甘美朗音乐。”(第177页)从以上华裔艺术家借用和改造印度尼西亚本土戏剧形式的做法看,无疑同华人布袋戏一样,最初也是带有某种保存华人传统文化的性质和目的的,即如蔡著所言:“如同爪哇皮影戏(wayang kulit)一般,爪哇华人皮影戏也具有传承华人宗教、娱乐、教育,甚至是政治、社会、经济等功能,特别是使用于神祇与祖先祭拜的宗教仪式当中,无论是华人寺庙(klenteng)神祇诞辰、各种宗教节庆,甚至是一般华人婚礼、生日纪念、新居落成、房屋净化等仪式中都有可能会演出。”(第177页)
第三,以华人移民传统音乐文化为研究对象,参与建构印度尼西亚当代音乐文化史,在大中华文化非核心区华人音乐文化的历时民族志研究中独树一帜。
长期以来在整个东南亚外圈,在晚近以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非印度源流宗教为主要信仰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些以印度古代史诗为代表的“印度化”色彩甚重的古代文化因素,通过古典戏剧和音乐舞蹈等艺术表演方式存留下来,并且深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隐层。这其中显然经历了一个不同宗教与社会文化由冲突、排斥到和解、包容,以及社会关系由紧张、一元到和谐、多样的发展过程。否则,我们很难去相信并解释这种现象:从其祖先开始便接受了佛、道、儒等传统文化的华人,何以才能在一个以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度里相对融入、和谐地生存下来。然而,有关上述对象领域的研究,做起来是有很大难度的。从敦煌乐舞壁画为代表的研究得来的经验看,文字、实物和图像三者在此类研究课题中缺一不可。而在上述东南亚国家,有关上述领域的研究,至今除了存有部分实物和图像和非常少量的汉文史料外,几乎没有任何详实的编年史文字材料可供参考。因此,借鉴音乐民族志方法,通过田野考察去获取必须的研究资料,就是势在必行的任务了。在蔡著里,通过对华人艺术家参与以中爪哇舞剧瓦扬翁创作表演和改革推广活动的例子,活态地揭示了上述印度尼西亚当代艺术史中的局部发展过程。我于2017年在印度尼西亚日惹考察期间,曾经看过整场哇扬戏《罗摩衍那》(Ramayana)的表演,其场面豪华、宏大,表演细腻、精致,整场都用了大型加美兰乐队伴奏和声乐伴唱,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对于这类表演的来龙去脉,中国学界已往有一些研究资料,较多集中于讨论其印度历史和文学的文化背景,而对其真实的发展状况人们知之甚少。对此,蔡著予以了比较详细、深入的分析和解说,并且揭示了诸多与华人艺术家相关的文化建构情节。按蔡著所言,瓦扬翁原属中爪哇梭罗与日惹宫廷的一种舞剧型态,是以人来模仿古皮影戏的一种舞蹈性质的戏剧演出,又称“人偶戏”。与古皮影戏一样,瓦扬翁也是以演出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与《罗摩衍那》为主。瓦扬翁舞剧的演出保持了皮影戏的架构,由演员自行对话,而操偶师往往与加美兰演奏者同坐,起到参与故事内容的旁白、以木槌敲击木盒发出声音提示舞者动作和伴唱皮影戏歌曲等作用。根据本地学者的研究,瓦扬翁的前身是印度爪哇舞剧瓦扬望(wayang wang),其艺术形象早已经出现在公元907年勿里洞(Balitung)的浮雕上(第8章)。另据相关考古图像资料,在公元8—9世纪修建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婆罗浮屠大塔寺石雕中,也包含了许多同《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有关的舞蹈、戏剧形象内容,可以作为佐证之一。①其后,表演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内容的瓦扬望舞剧便在不同的王朝一再上演,中爪哇瓦扬翁舞剧又受到中国戏曲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瓦扬翁舞剧从宫廷流传到民间,在华人艺术家的参与下,从其表演形式上由皮影戏操偶师转换为演员本人表演到化妆和舞台布景的应用,都受到华人剧种的影响。如今,瓦扬翁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结合舞蹈、戏剧、音乐、舞台设计、文学等的综合艺术形式,体现了印度尼西亚包括华人在内的各民族共同建构、复兴当代印度尼西亚艺术文化的愿景,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华人艺术家的参与和共建行为,因而受到包括蔡氏在内的不同研究领域学者的关注(第8章)。
华人传统艺术在当代东南亚获得发展和复兴,存在多种途径和可能性:其中一种如上文所提及的,由于当代华人通过文学艺术来塑造族群身份认同的意识往往要甚于其先辈,因而萌生了许多主动的音乐文化建构和重构行为;另一种则是本土人以对异文化形式的借用,来获得艺术风格多样化的灵感,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印度尼西亚音乐家通过重建华人皮影戏的努力(第7章)里得到印证。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艺术创作思维和手法,这在不同国家、民族的本土艺术中都已经屡见不鲜。
第四,通过离散族群研究、文化与身份认同研究和“去领域化、再领域化”②等学术研究方法手段,既达到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解释的目的,也为同类研究课题中音乐人类学学科方法论的运用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案例。
前面讨论了印度尼西亚华人音乐的表演形式和乐种类型,如果说它们涉及传统艺术的内部条件因素的话,这里将要讨论的内容,就会涉及到该类传统艺术与外部政治、社会环境因素的关系。
东南亚内、外圈华裔族群的文化处境既有共同点,也有相异之处。仅就差异性来说,距离远近的差异、陆路与海路的差异、华人离散族群来源及其迁入的时间、条件的差异等等,都能够为他们带来外部政治、社会和宗教信仰环境的巨大差别,也能够为他们带来与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相关的种种条件差异。近年来,当我们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丝路华人音乐后,便能够看到外圈居住的华裔主要是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迁入的汉族,而内圈的华裔很大一部分是由云南、广西等西南省份迁入,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是由外圈内移而来的汉族。东南亚外圈的汉族华人主要的五个方言群(闽南人、潮州人、客家人、广东人与海南人);内圈的华人主要是讲汉语西南方言,华人中的少数民族与本地族群同属汉藏语系藏缅、壮侗、苗瑶诸语族和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由此看,相比起内圈族群与文化认同的多样性和多层性来说,东南亚外圈的华人所维护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的认同,更是区域性华人文化符码的呈现”(第4页),而印度尼西亚华人随着社会变迁的过程而改变或创造新的华人文化,可谓是以汉族为主的华人文化的外向延伸。尽管,这些华人在国籍上大多已经不再是中国籍,然而他们仍然努力地在维护着华人文化传统,同时结合华人与印度尼西亚各种表演艺术形态,创造出属于华人与印度尼西亚的共同文化,使得印度尼西亚华人表演艺术成为华人与印度尼西亚的文化桥梁。而身为华人的一分子,无论是对于大陆或台湾以及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艺术研究,都有着一份深厚的使命感。而华人音乐文化在其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诚如蔡著所言:“或许,我们也可以这么说,音乐本身是一个有效的认同符号,可以用来建构其从孩提时期至成人之后就已经在无意识之中所形成的‘民族认同’,而这样的民族认同有其快速性且具有双倍的有效性,不仅成为不同民族或社会认同的角色,而且在一个独特的方式中,是具有情感内涵以及作为被用来主张认同的方式。”(第39页)
在蔡著里,除了文化与身份认同,“去领域化、再领域化”③是又一个出现较多的方法论概念。作者指出,“去领域化”原本是在讨论现今资本主义社会面对全球化过程中,可能会慢慢抽离(disembedding)了其原生地的文化空间(cultural-spatial)关联性,其中包含了原有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环境、文化活动、文化经验与文化认同的连结,而走向所谓的“现代化”的社会型态。因此当离散社群在面对一个移民国新的文化空间的改变时,导致其从母国所带来的传统文化,慢慢地抽离了其原来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空间,开始进行适应、融合的过程。当印度尼西亚华人将其来自中国母国的文化系统带到印度尼西亚移民国之后,由于所带来的文化系统已经远离了原属于中国母国的文化空间,同时也为了要融入与适应印度尼西亚文化、社会体系,导致其来自中国母国文化形态的转型(transformation),而产生所谓文化“去领域化”的离散现象。就以爪哇华人皮影戏而言,虽然原始的概念来自华人传统布袋戏,其戏偶创作概念与故事内容都是来自华人布袋戏,但在演出场域、演出方式、使用语言、后场音乐等方面都结合了印度尼西亚皮影戏的元素,因此无论是在演出环境、演出形态、演出内涵上都有所改变。事实上,这样的一种“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也很明显地呈现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离散社群的文化现象之上。然而在此一“去领域化”的过程中,并不代表此一新的爪哇华人皮影戏就已经受到当地华人、爪哇原住民族以及当地政府的接受,特别是在1967年之后的“新秩序”(Order Baru)排华运动,对于爪哇华人皮影戏的发展更是一大政治冲击;更何况还要受到印度尼西亚学者专家的认同,甚至受到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肯定,而成为印度尼西亚爪哇皮影戏的一种类型,这些都必须经过长期“再领域化”的过程,才能使爪哇华人皮影戏成为印度尼西亚华人特有的重要文化遗产,甚至被爪哇原住民族与印度尼西亚政府认同。
蔡著又继续讨论说,在“去领域化”的过程中,“再领域化”也随之应运而生,当一个文化系统面对媒体的传播影响或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同时,改变后的新的文化系统往往也要透过整合新旧文化符码而进行部分领域的“再在地化”(partial territorial relocalizations),也就是基于移民后的新文化空间的基础上,再建构、再定义、再诠释此一整合后的文化产物,这一文化产物已不再是来自母国或移民国原有的传统文化,而是专属于离散社群的文化形态。这样的“再在地化”或“再领域化”也可说是一种旧文化符码的转型。就此而言,蔡著述及的华人艺术家对于中爪哇舞剧瓦扬翁创作表演和改革推广活动的种种贡献,已经从相对绵长、延续的当代艺术发展史角度,体现了上述印度尼西亚华人文化由建构、交融、整合到身份认同的过程(参见168—170页)。而在蔡著里,又专辟一章,可以说从更新的层面上讨论了卡拉OK音乐在不同华人地区的广泛传播。在这类通俗音乐里,涉及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意识形态的歌曲,在一种“娱乐至上”的氛围里,都被抹平了。在东南亚国家中,我对新加坡的情况认识较早,缘起于20世纪末与新加坡学者的交往,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圈子里,中国大陆的红色音乐无论对其左倾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对其多层性的华人社会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建构与推动作用。笔者在印度尼西亚日惹亦曾参加过华裔社区的卡拉OK演唱活动。如今印度尼西亚的此类活动内容,比起笔者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要更为多元一些。台湾歌曲为首选,其次为大陆流行歌曲,也会有带一定民族认同色彩的大陆歌曲如《爱我中华》、陈红的《常回家看看》等,此外还包括马来西亚的本土歌曲。在东南亚地区,器乐曲,尤其是民乐,只要是音乐流畅抒情,通俗易懂,就能够接受和流行,并且相对来说很少避讳带有政治色彩的标题内容。而在中国大陆,包括红色歌曲在内的华语流行音乐,已经进入了包括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在内的几乎所有日常生活领域。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半个多世纪以来,华人文化的发展被分布在不同洲际的多种畸形政治漩流隔断,未能够以渐进、平稳的方式演进,从而形成明显的断层有关。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卡拉OK这种艺术与工业文化的混合产品,随着大陆华人的世界性流动,成了整个国际华人文化圈内,一种能够超越不同国族身份、年龄代沟和意识形态而突显共同的族群身份标识与人伦色彩的重要文化符号。
随后,再谈谈蔡著对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几点启示:首先,东南亚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在族群成分和社会文化上有诸多的相似性,以致东南亚音乐研究里也可以寻找到不少南方民族音乐研究的踪影,且很自然地涉入了南方跨界族群音乐的学术研究范畴。同样,宗德教授的印度尼西亚华人移民音乐问题研究,让我联想起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以往也一度习惯于把它看作是“非汉”文化区域,只注重去做异文化和文化濡化的研究,而忽视了那里的汉族移民文化发展及涵化的问题。对此,我与宗德教授也算是“心意相通”,看到了这方面的契机,我便在2019年12月于云南艺术学院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跨界族群音乐文化论坛的主旨发言里,提出了在边界两侧比较研究、路带研究、环岛(海南与台湾)研究、环山(喜玛拉雅山)研究之外,将海外华人音乐文化研究作为第五个研究方向纳入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框架的主张。
其次,从历史音乐人类学角度看,由于文字史料的缺失,数千年来的云南与东南亚音乐发展史中留下了许多悬案。联想起蔡著所提示的那样的情况,既然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来往能够追溯到公元前,历史不过千年左右的婆罗浮屠大乘佛教与中国的大乘佛教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呢?同一时期存在于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以及更早镌刻在斯里兰卡、印度的石窟壁画里,各种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民间乐器相关的资料,也有待于我们去做比较。另外,印度尼西亚华人文化中狮舞等民间歌舞对本土文化的影响,在宗德兄的书里,依据相关资料,进行了较为详实的梳理。据我自己在巴厘岛看到的情况,当地各种狮舞中,也能看到许多中华文化影响的痕迹。联想起云南傣族、布朗族等地区,也有不少各种类似的采用竹木道具的民间歌舞和歌舞戏,其与汉族文化的关系,尚有待于再做进一步的认识和梳理。
再者,离散族群并不仅仅涉及中国中心地区汉族文化的迁移和扩散,也同样涉及其他本土族群文化自身的受化和变异。蔡著中涉及的许多印度尼西亚本地人接受、消化和发扬华人艺术文化的传奇性经历,也让我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我的具有白族身份的祖父、父亲对汉族京剧的由衷喜爱和对汉文文化的高度接受。看到印度尼西亚的第四代华人舞蹈家吴俊安和其他“侨生华人”能够取得并拥有那么高的印度尼西亚舞蹈文化成就时,我也在想,我们这些中国的“混血”族裔(我的母亲是内地汉族),是不是也在由边疆城镇到内地都市的远距离、跨地域的迁居过程中,取得了某些当初未曾料及的异文化艺术发展成绩了呢?在我的40年学术生涯里,我写过很多别的离散族群或族裔的个例,但还是第一次这样来反观我自己,这没准会让我拓展“自我民族志”的学术思路,为今后的研究打开另外一扇窗户呢!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中爪哇舞剧瓦扬翁(哇扬戏)的例子,进一步联想到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傣族的傣戏,侗族的侗戏,壮族的壮剧等,既是少数民族文化建构的结果,同时也几乎都体现了汉族文化横向传播及本地化的过程。以往这些民族的艺术家在发展自己的戏曲艺术时,除了唱腔上能够借鉴本民族的说唱性质的唱腔之外,在伴奏乐队、表演程式和表演方式上,同样是较多借用汉族的表演形式,但是像瓦扬翁那样,仍然保持自己独有的加美兰音乐伴奏、伴唱形式的,能找出多少例子来呢?此外,瓦扬翁里保留了印度史诗内容的情况,在云南傣族舞剧《婻木诺娜与召树屯》里,也通过佛教仪式中本生经的唱诵,保留了同样的来自古印度文化的故事性因素,从而让这两类具有完全不同的宗教社会背景的舞剧创作和表演抹上了相似的隐喻性文化色彩。
蔡著里包含的文化内容和学术观点十分丰富,在此难以一一而足!从中可以归结出一点:本文提到诸多的印度尼西亚华人音乐文化事项,尽管其中多数我都有过聆听体验,但是通过蔡著的启发之后,方使我获得了联想的依据,产生了理性的归并和导致了某些学术灵感的迸发。最后想说的是,鉴于蔡著拥有的较为突出的学术成就和显著的文化意义,希望它的正式出版,能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同、推广和普罗大众阶层的欢迎、喜爱!
(本文在为蔡著所写序言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① 杨民康:《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佛塔的乐舞石雕图像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3—24页。
② 在大陆学术界,又习惯称“去语境化、再语境化”。
③ 同注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