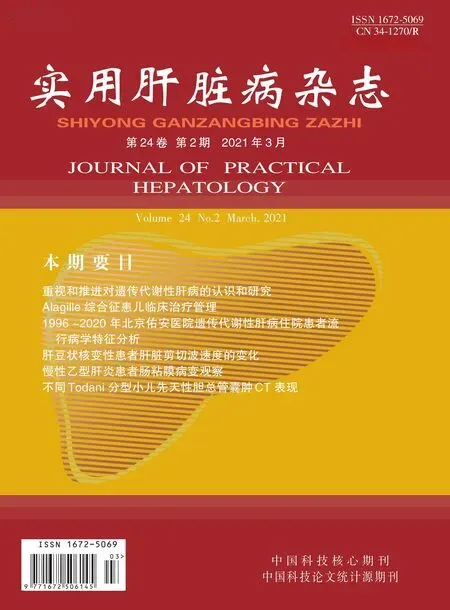Gilbert综合征研究进展
2021-12-01邓玉婷魏民华周俊英
邓玉婷,魏民华,周俊英
高胆红素血症是临床常见的症候群,而胆红素是血红素分解代谢的最终产物。在正常情况下,由脾脏巨噬细胞释放的血红蛋白分解为血红素和珠蛋白,血红素被血红素加氧酶(heme-oxygenase,HMOX-1)的限速同工酶复合物氧化降解,释放胆绿素、一氧化碳和铁。胆绿素在胆绿素还原酶(biliverdin reductase A,BLVRA)的作用下促进未结合胆红素(即间接胆红素)的产生。血液未结合胆红素与白蛋白结合被运送至肝脏,通过弥散作用或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1B1(organic anion transporting polypeptides 1B1,OATP1B1)进入肝细胞,在尿苷二磷酸葡糖醛酸基转移酶1A1(uridine diphosphate glucuronosyl transferase 1A1,UGT1A1)的作用下,与葡萄糖醛酸结合成胆红素葡糖苷酸(即直接胆红素),最后通过ATP依赖性的多药耐药相关性蛋白2经肝细胞小管膜分泌到胆汁中[1,2]。由于溶血作用、HMOX-1/BLVRA酶活性增强致胆红素的过量产生、肝细胞对胆红素摄取障碍以及肝细胞对胆红素的结合障碍导致高间接胆红素血症。
临床上,根据UGT1A1酶活性水平的不同,可将高间接胆红素血症分为三种,即Gilbert syndrome(GS)、Crigler-Najjar综合征Ⅰ型(CNS-Ⅰ)和Ⅱ型(CNS-Ⅱ)。GS患者UGT1A1酶活性降至正常的30%左右,其临床症状轻微,主要表现为轻度、波动性黄疸,总胆红素(TBIL)波动于17~103 μmol/L。在禁食、体育锻炼、腹泻、情绪紧张、感染、妊娠或月经异常等情况下黄疸加重,一般不伴有肝脏器质性改变,通常认为是良性过程[3];CNS-Ⅰ患者UGT1A1酶活性严重缺乏甚至消失,黄疸严重,TBIL >342μmol/L,易进展为核黄疸,病死率极高;CNS-Ⅱ患者UGT1A1酶活性约占正常值的10%,TBIL多波动于103~342μmol/L,给予苯巴比妥60~120 mg.d-1治疗后胆红素水平较前降低超过25%[4,5]。目前,遗传性高间接胆红素血症以GS多见,发病率高达5%~10%[2]。本文就GS最新研究进展进行阐述。
1 GS的概述
GS在1901年由Gilbert和Lereboulet[6]首次报道,被认为是一种胆红素代谢障碍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2],但也有研究认为GS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4],具有不完全外显率。其特征是在无溶血及肝脏疾病状况下反复发生血总胆红素升高,且以间接胆红素为主。先前认为GS的病变基础是UGT1A1基因突变所致的酶活性降低超过正常60%~70%[2],引起间接胆红素的结合障碍。目前,大量研究表明GS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是环境因素(种族、年龄和性别)和基因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1.1 环境因素对GS的影响 GS在不同种族地区的患病率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2],例如,中国人和日本人呈现出较低的患病率,大约占2%,而印度、南亚和中东的患病率可高达20%,白种人的流行率大约在2%~10%,其患病率的差异可能与基因突变位点不同有关。Mooij et al[7]发现肝转运蛋白的表达与年龄显著相关。在对OATP1B1 mRNA水平分析研究发现,新生儿肝脏OATP1B1 mRNA仅为成人的1/500,婴儿为成人的1/90。在对80名2月至12岁的儿童的肝脏样本分析发现,OATP1B1在6岁之前一直处于低水平,7岁后其蛋白水平处于稳定状态,并且与OATP1B1基因型多态性有关。此外,GS以青壮年男性发病多见,男女发病比例为1.5∶1~10∶1,这可能与雄激素对葡萄糖醛酸化的抑制作用有关[8],这一结果在Mucara[9]的实验中得到了解释,但性激素在GS发生发展中的潜在作用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1.2 GS患者常见的UGT1A1基因突变类型 UGT基因超家族编码催化各种底物葡糖醛酸化以促进其排泄的系列酶。UGT1基因位于2号染色体长臂37区,该基因由四个常见外显子(外显子2/3/4/5)、13个独特的启动子和第1外显子(可变外显子)组成,仅仅包含可变外显子A1的基因参与胆红素的结合过程[1]。因而,UGT1A1是催化肝细胞中水溶性胆红素葡萄糖醛酸生成的唯一酶,该基因的突变可导致胆红素结合缺陷。通过检索人类基因突变库可知,已知该基因突变位点为151个,GS中较常见突变位点是调控区域具有启动子TATAA元件和苯巴比妥反应增强元件(phenobarbital-responsive enhancer module,PBREM)[10]。UGT1A1基因突变最常见的是TATA盒的插入突变和第1外显子的错义突变。TATA盒的插入突变是指A(TA)7TAA(又称UGT1A1*28)序列取代正常的A(TA)6TAA,重复的碱基对降低了结合蛋白与TATA盒的亲和力,致使基因表达减少,进而降低UGT1A1酶的活性[1]。A(TA)7TAA的纯合突变可使UGT1A1酶活性降至正常25.5%,而杂合突变使其活性降至50%左右[5]。第1外显子的错义突变是指第211位的鸟嘌呤(G)突变为腺嘌呤(A),即211G>A(UGT1A1*6),突变后第71个氨基酸从甘氨酸变异为精氨酸,故又称p.G71R,即其纯合突变可降至正常酶活性32%,杂合突变约占正常活性的60.2%。目前研究认为UGT1A1酶活性40%是区别正常人与GS患者的很好标志[5],因而在GS患者,p.G71R突变通常以纯合状态出现。GS患者UGT1A1基因突变多态性在不同种族之间存在差异[8]。在西方人群中,以A(TA)7TAA的突变更为常见,其等位基因的频率约为0.4,而在东亚人群,例如日本、中国、韩国等,以p.G71R突变更为流行,因其在p.G71R突变点有更高的等位基因频率[1]。此外,研究还发现1号外显子的686C>A(又称p.P229Q,UGT1A1*27)、4号外显子的1091C>T(又称p.P364L,UGT1A1*63)和5号外显子的1456T>G (又称p.Y486D,UGT1A1*7)等位点的突变也可引起高间接胆红素血症[5]。因此,对UGT1A1基因进行全基因检测有助于明确GS的病因。PBREM是长290bp的UGT1A1基因的增强子序列,其表达可以提高GS患者对苯巴比妥的反应能力,位于启动子TATA盒的上游[10]。位点-3279T>G (UGT1A1*60)的纯合突变可使UGT1A1酶降至正常的60%左右,而杂合突变约占正常酶活性的77%[5],单纯的-3279T>G位点突变可引起血清胆红素水平的轻度升高,但并未达到GS的标准,其一般和TATA盒的突变或编码区域其他突变点联合引起GS[11]。对中国人GS研究中显示-3279T>G 突变约占36.3%,A(TA)7TAA突变约占30.6%,而p.G71R约占14.5%[12]。
2 GS与其他疾病的关系
以前研究认为胆红素是一种脂溶性有害代谢产物,用于评估肝脏损伤严重程度。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大量的研究显示胆红素不仅仅是一种体内的代谢废物,还是一种天然的内源性抗氧化剂,具有抗自由基、抗炎、抗免疫、调节代谢、保护血管内皮等功能,可能在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药物代谢、结肠炎等疾病中起到保护性作用,可作为慢性疾病良性预测的生物学标志[4,13]。
2.1 GS对心血管疾病和代谢综合征起保护作用 研究发现肥胖伴有高危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短期减重,胆红素水平随体质量的降低而增加[14]。与胆红素正常的糖尿病患者相比,糖尿病合并有GS患者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更低[15]。在哺乳动物,轻度的高胆红素血症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和MS有积极作用[16]。一项Meta分析显示,胆红素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血清胆红素水平升高会使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disease,CHD)的风险降低[17]。MS是一组包含肥胖、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高胰岛素血症等在内的代谢紊乱的症候群,氧化应激为其主要的发病机制,有结果显示GS患者氧化应激标志物降低[18],提示轻度的高胆红素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抗氧化应激反应。另一项Meta分析也证实了血清胆红素水平与MS成分(如中心性肥胖、高甘油三酯血症、空腹胰岛素、高血糖)呈负相关[19]。深入研究胆红素与心血管疾病、MS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能为未来疾病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2.2 GS缓解NAFLD的进展 NAFLD是MS在肝脏中的主要表现,肝组织脂肪酸的积累能提供线粒体氧化应激的来源,进而造成损伤、炎症甚至纤维化。研究表明高间接胆红素血症与肝脏损害的组织病理学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与无NAFLD或NAFLD尚未进展到NASH阶段人群相比,NASH患者血浆高胆红素可显著降低肝硬化的发病风险[20]。关于高胆红素缓解NAFLD进展的作用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清楚。有研究显示胆红素可激活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α)的转录活性,PPAR通过增加肉碱棕榈基转移酶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的表达,诱导肝脏和脂肪组织的脂质代谢[21-25]。PPAR介导的脂肪酸氧化的这一结果也在Landerer的实验中被证实。此外,胆红素还可清除过氧自由基、羟基自由基、单线态氧、活性氮,并减少α-生育酚基自由基,从而促进维生素E的循环利用来降低氧化应激。
2.3 GS与药物代谢的关系 肝脏是具有解毒功能的器官,许多药物经过肝脏多种酶代谢后排除体外。GS患者UGT1A1酶活性明显降低,可能影响某些药物(如吉非罗齐/依折麦布、他汀类药物、炔雌醇/氟维司群、非甾体类药物、抗HIV病毒药物、干扰素、利巴韦林、伊立替康)代谢,增加患者对药物的暴露时间,更易造成药物性肝损伤或其他严重的不良反应。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为伊立替康,后者是转移性结肠癌的标准治疗选择,其在羧酸酯酶的作用下转变为SN-38发挥抗癌活性。SN-38经过UGT1A1酶灭活后由胆汁和尿液排出体外。由于GS患者UGT1A1酶活性低下,造成伊立替康的蓄积从而导致严重的骨髓抑制和腹泻。在GS合并子宫内膜癌和霍奇金淋巴瘤患者,轻度升高的间接胆红素对患者具有保护作用,可能与药物代谢时间延长有关,但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此外,在应用阿扎那韦或茚地那韦抗HIV治疗过程中,由于药物抑制UGT蛋白质,GS患者更易观察到不同程度的高胆红素血症。
2.4 GS对结肠炎的保护作用 胆红素,尤其是间接胆红素除了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外,还具有免疫调节和抗炎作用。有人[26]通过对体内外结肠炎的研究中发现,在低水平的外源间接胆红素作用下,疾病的恢复期可观察到结肠炎患者血生化学和组织病理学的改善,伴有脾脏、肠系膜淋巴结、固有层IL-17+T细胞频率较低,而结肠上皮细胞IL-10+淋巴细胞比例更高。当芳基烃受体(AHR)水平降低或存在功能障碍时,会降低辅助T细胞17(Th17)的免疫应答,证实间接胆红素通过AHR促进Th17高表达CD39胞外核苷酸酶来缓解结肠炎的活动性。因而,我们推测GS对结肠炎起保护作用。此外,在Gila et al研究发现,胆红素可通过清除TLR4受体介导的NADPH氧化酶衍生的活性氧来阻止低氧诱导因子-1α(HIF-1α)的活化,从而抑制诱导性一氧化氮合酶的上调来发挥其抗炎作用,缓解症状。但有研究表明,GS以p.G71R为主要突变位点的患者发生结直肠癌的风险更高[27]。
3 小结与展望
GS是最常见的非溶血性遗传性高间接胆红素血症,其肝脏生理功能正常,不会进展到炎症、纤维化等阶段,因而一般无需特殊治疗。GS具有异质性,了解其在不同人群的患病率及基因突变位点对于及时诊断具有重要作用,对该病及早的诊断和基因检查可以避免过度治疗,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GS依赖其轻度的高间接胆红素血症对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NAFLD、药物代谢、结肠炎等疾病具有保护作用,但具体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仍需更深入的研究来探讨疾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了解GS真正的病理学意义,从而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
利益冲突 无。
作者贡献声明邓玉婷为论文的主要撰写者;魏民华为论文进行了辅助修改;周俊英指导研究选题、设计和指导论文的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