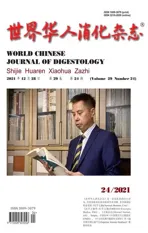STING信号通路参与NAFLD的研究进展
2021-12-01吴锦婷贺博武曹婕露严峻彬陈芝芸
吴锦婷,贺博武,曹婕露,严峻彬,陈芝芸
吴锦婷,贺博武,曹婕露,严峻彬,陈芝芸,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 310006
0 引言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一种与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和遗传易感密切相关的代谢应激性肝脏损伤,其疾病谱包括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simple fatty liver,NAFL)、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及其相关肝硬化和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它不仅是代谢综合征的主要肝脏表现,还影响着肝外器官和调节途径[1].近年来,NAFLD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迅速上升,已成为慢性肝病最常见的病因之一[2],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NAFLD发生发展的潜在机制是复杂的、多因素的,研究发现免疫机制在其发生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STING)作为机体免疫系统的一个关键性接头蛋白,起初主要注重其相关信号通路在细菌病毒等感染性疾病中的作用.近些年发现该信号通路也可参与NAFLD的发生和发展,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结合相关报道和最新文献,对STING信号通路在NAFLD中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以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药物开发等提供参考.
1 NAFLD与免疫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识到生物的新陈代谢和免疫之间有很强的联系.不仅在免疫细胞中,在代谢细胞中也发现了明显的免疫信号及相关信号通路.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它不仅维持糖和脂肪的体内平衡,还参与免疫调节(先天免疫、获得性免疫和免疫耐受),所以肝脏也被认为是一个免疫器官.
肝脏免疫耐受和有效免疫反应之间的平衡对组织的正常功能和体内平衡至关重要.在NAFLD中,肝脏中出现不适当的免疫反应或炎症持续的情况,使这种平衡被打破,进而观察到NAFLD/NASH的肝脏病理[3].肝脏非实质细胞在NAFLD的进展中起关键作用.它受到脂质抗原、脂肪因子等因素的刺激,分泌的免疫因子可改变SREBP-1c、ChREBP、PPARγ等关键蛋白的表达,调节脂质代谢,从而影响NAFLD的病理过程;某些ncRNAs(包括miRNAs和lncRNAs)也可以通过改变体内脂肪稳态来参与NAFLD的病理过程[4].炎症被认为在促进单纯性脂肪肝发展为更严重的肝损伤(如脂肪性肝炎、肝硬化和HCC)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免疫机制也主要在NASH的进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多种类型的先天(自然杀伤细胞,自然杀伤T细胞,和Kupffer细胞/巨噬细胞)和适应性(T细胞和B细胞)免疫细胞在肝脏内富集并参与了脂肪肝疾病的炎症反应[5,6].近几十年的实验和临床数据表明,不同的肝先天免疫细胞和适应性免疫细胞对NAFLD/NASH的作用也并不一致.一般来说,CD8+T细胞、M1巨噬细胞、B细胞、1型NKT细胞、中性粒细胞和NK细胞分泌的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会导致ALD和NAFLD/NASH的发展.相反,M2型巨噬细胞、2型NKT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似乎与肝损伤保护有关[5].
2 STING信号通路
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NG,又称为TMEM173、ERIS、MITA或MPYS),在免疫调节相关的细胞和组织中高度表达,是STING相关信号通路中的中枢免疫分子,也是Ⅰ型干扰素(interferon,IFN)产生和先天免疫系统的主要调节因子.在正常的真核细胞中,DNA从细胞质中被严格包装和分离,以避免自身炎症.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导致病原菌源性DNA、自身DNA在细胞质中被异常定位.这些外源双链DNA(double-stranded DNA,dsDNA)存在于胞质中,对先天免疫系统是一种危险信号,可被环鸟苷单磷酸(guanosine monophosphate,GMP)-腺苷单磷酸(adenosine monophosphate,AMP)合成酶(cyclic GMPAMP synthase,cGAS)及时感知和检测.随后dsDNA与cGAS结合导致cGAS的激活,并由鸟苷三磷酸(guanosine triphosphate,GTP)和腺苷三磷酸(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催化合成2,3-环GMP-AMP(cyclic GMP-AMP,cGAMP),cGAMP高效结合并激活STING.然后激活的STING从内质网(endoplasmic reticulum,ER)转运到高尔基复合体,在那里它招募TANK结合激酶1(TANK binding kinase 1,TBK1)和IκB激酶(IκB kinase,IKK),并将它们迁移到细胞的核周区域.随后,这些激酶磷酸化并激活干扰素调节因子3 (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3,IRF3)、干扰素调节因子7(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7,IRF7)、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等转录因子.激活的IRF3/7和NF-κB等途径刺激触发Ⅰ型IFN和许多其他促炎细胞因子等的产生,从而触发先天性免疫反应和适应性免疫以维持体内平衡[7-9].
上述是STING的典型激活通路.最近也有研究发现STING的激活可以不依赖于cGAS和cGAMP的产生.Dunphy等[10]研究发现角质形成细胞和其他人类细胞在依托泊苷诱导的DNA损伤数小时内产生先天免疫反应,这涉及到DNA传感适配器STING,但独立于胞质DNA受体cGAS.这种非典型的STING激活是由DNA结合蛋白IFI16、DNA损伤反应因子ATM和PARP-1介导的,导致了一个替代的STING信号复合物的形成,其中包括肿瘤抑制因子p53和E3泛素连接酶TRAF6.TRAF6催化STING上k63连接的泛素链的形成,导致转录因子NF-κB的激活,并诱导一个替代的STING依赖的基因表达程序.
STING信号通路在机体免疫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在对抗各种DNA病毒、逆转录病毒和细菌等病原体的免疫防御以及内在抗肿瘤免疫反应中发挥关键作用,而且在许多涉及炎症的常见病中发挥作用,如心血管疾病、炎症性肠病、糖尿病、纤维化等[11].
3 STING信号通路与NAFLD
STING信号通路能介导免疫细胞中的Ⅰ型干扰素(IFNs)炎症反应,以防御病毒和细菌等病原体感染.最新的研究表明[12],该通路也可被异常定位于细胞质中的宿主DNA激活,导致无菌性炎症、IR和NAFLD等的发生发展.NAFLD以肝脏脂肪变性为特征,也是一种涉及炎症的代谢性疾病,可发展为NASH.许多证据表明机体的免疫应答有助于NAFLD的进展,然而,其促进NALFD的潜在机制仍不十分清楚.近些年的研究发现STING免疫信号通路与NAFLD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
3.1 STING信号通路与NAFLD和/或NASH Wang等[13]发现NASH患者的肝脏中STING细胞的数量增加,并且与肝脏炎症和纤维化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另外两项研究也发现[14,15],肝脏STING信号通路的激活可能介导营养过剩诱导的NAFLD和/或NASH.而STING缺乏可减轻蛋氨酸和胆碱缺乏饮食(methionine-and choline-deficient diet,MCD)或高脂饮食(high-fat diet,HFD)喂养的小鼠肝脏的脂肪化、纤维化和炎症[14,15].的确,与非NAFLD患者相比,NAFLD患者肝脏组织中STING水平更高;NASH小鼠肝脏中cGAS和STING的mRNA水平也比正常小鼠高[14,16].此外,在HFD喂养的NAFLD小鼠的肝脏中,STING信号通路的两个下游靶点TBK1和IRF3的磷酸化状态也显著升高[14,17].研究发现[18]NASH患者肝脏线粒体功能异常,胞浆mtDNA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当肝吞噬细胞吞噬凋亡或死亡的肝细胞时,其自身DNA进入细胞质,激活cGASSTING通路[19].小鼠肝脏吞噬细胞中STING-TBK1-IRF3和IKK-NF-κB通路的激活可产生多种细胞因子,包括干扰素(IFNs)、炎症因子、α平滑肌肌动蛋白(aSMA)、TGF-β和IA型胶原蛋白A1(Col1a1).其中,干扰素和炎症因子主要作用于小鼠肝细胞,引起肝脏异常炎症[13-15,17];而aSMA、TGF-β、Col1a1主要通过旁分泌激活肝星状细胞(HSCs),加重肝纤维化[13-15].此外,NAFLD患者肝脏中脂质过度沉积导致内质网(ER)氧化应激损伤,从而激活STING-TBK1通路[20],STING-TBK1通路的激活不仅会引起肝脏代谢紊乱,包括肝细胞胰岛素抵抗和脂质沉积[14,17],而且促进了不溶性p62/sequestosome 1(SQSTM1)聚集物的形成,这是NASH的关键标记物,在NASH形成中起重要的致病作用[21].
STING在肝脏中分布不均匀.与肝细胞相比,STING主要在肝非实质细胞(NPCs)中表达和激活,包括Kupffer细胞、窦状内皮细胞和肝星状细胞(HSCs),从而发挥相应的作用来维持肝脏的稳态[22].在全身或骨髓细胞特异性敲除STING的HFD或MCD小鼠中,其可能通过影响NF-κB及IRF3的表达从而减轻肝脏的脂肪变性、炎症和/或纤维化[14,15].此外,将对照组小鼠的骨髓细胞移植到STING敲除小鼠后,可加重HFD喂养小鼠肝脏脂肪变性和炎症的严重程度[14],这表明STING敲除小鼠的代谢表型改善是由于小鼠肝内缺乏STING巨噬细胞而不是肝实质细胞.这些结果与STING不存在于人类和小鼠肝实质细胞但存在于肝非实质细胞中并大量表达的发现一致[15,23,24].有研究发现[13],STING主要在巨噬细胞中表达,包括单核细胞衍生的巨噬细胞(MoMF),库普弗细胞和CD163巨噬细胞等.一项对98例NAFLD患者肝脏样本的研究也显示,Kupffer细胞和MoMF细胞中的STING表达与炎症和纤维化密切相关[13].然而,另一些报道却表明STING也存在于肝实质细胞中,并且敲除STING或IRF3均可减轻脂质积累、肝脏炎症和细胞凋亡[17,25].这些发现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在全身STING敲除小鼠中观察到的一些NAFLD表型可能是由于小鼠肝实质细胞STING缺陷所致.另外,Bai等[26]还发现cGAS、STING和TBK 1等STING通路组分在脂肪细胞中也存在高表达,抑制该信号通路可以减少肥胖诱导的炎症并改善代谢稳态.
IRF3和IRF7都是先天免疫反应中的关键转录因子,均参与Ⅰ型干扰素依赖的免疫应答.其中IRF3是公认的STING信号通路的下游信号分子,目前很多关于STING信号通路参与NAFLD的研究也是围绕STING-IRF3开展的.然而最近Cheng等[8]发现尽管鸡中缺少IRF3,但它们却能使用IRF7来重构相应的IFN信号,以响应DNA和RNA病毒感染,并发现了通过STING激活IRF7的机制.进一步的研究则指出[27]IRF7由STING激活的方式虽然与IRF3高度相似,但IRF7的调节似乎受到更严格的控制:尽管单个磷酸化事件足以激活IRF3,但激活IRF7至少需要两个磷酸化事件.所以,IRF7也是STING的下游游信号分子.早先有报道指出[28]IRF7参与代谢异常,并在饮食诱导的能量代谢和胰岛素敏感性改变中起作用.同时在NASH患者和高脂高果糖(high fat/high fructose,HFHFr)饮食诱导的NAFLD小鼠中IRF7表达也均出现上调.结合这些发现,我们不难推断出STING-IRF7通路似乎也参与NAFLD的发生发展.但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提供更多证据.
综上,STING信号通路可能通过介导肝脏炎症、脂质代谢以及细胞凋亡等影响肝脏的代谢稳态从而参与了NAFLD和/或NASH的发生发展.
3.2 STING信号通路与HCC NAFLD最终可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NASH肝硬化患者中肝癌的年发病率估计在0.5%至2.6%之间;非肝硬化NAFLD患者中HCC的发生率较低,约为0.1-1.3/1000人每年[29].
STING信号通路同样参与了HCC的发生发展.大量证据显示,STING信号通路的激活能抑制肿瘤的发展,而DNA损伤和癌症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实[30].与正常细胞不同,肝癌细胞胞浆中含有大量的异位DNA,如肿瘤来源的DNA、mtDNA和核染色体片段[31].当细胞质DNA被cGAS识别时,STING-TBK1-IRF3和IKK-NF-κB通路被激活,产生IFNs、促炎因子和趋化因子,能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这些细胞因子还召集肿瘤组织周围的DCs和NK细胞,形成肿瘤特异性淋巴细胞浸润的抑瘤微环境,作为抗肿瘤免疫的一线防御[7].此外,干扰素-β不仅提高了DCs的终末分化,加速DCs的成熟,促进DCs中肿瘤特异性抗原肽到MHCI类分子在CD8+T细胞中的交叉递呈并激活它[32],也会增加CXCL9、CXCL10和其它趋化因子的表达、进而诱导T淋巴细胞转移到肿瘤组织,杀死肿瘤细胞并启动适应性免疫反应[33].此外,STING激活还能产生自噬、凋亡、坏死等非免疫功能,有效清除外源性病原体和肿瘤DNA,促进抗原呈递给T细胞,介导T细胞免疫应答[34].
然而,也有证据表面STING信号通路可能促进肿瘤的发生和进展.例如:STING-TBK1-IRF3通路产生的IFN-β刺激免疫关卡分子的产生,如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1,PD-L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 (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 4,CTLA-4),这些分子与T细胞表面受体结合,抑制T细胞的激活,可以导致免疫逃避[35,36].此外,Ⅰ型IFNs在化疗和放疗过程中可诱导持续的DNA损伤,进而异常激活STING,导致长期炎症[37],进而引起组织破坏和免疫抑制,延缓癌细胞衰老,使癌细胞“永生”[38].另外,STING诱导的T、B淋巴细胞凋亡也会损害细胞免疫功能[39],从而促进肿瘤的发展.
所以,STING信号通路在HCC中似乎有着互相矛盾的作用,虽然大多数研究认为其能抑制肿瘤的发展,但在某些条件下其也可能会促进肿瘤的发展,这可能与肿瘤所处的环境和阶段有关,其中具体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去阐释.
4 讨论
目前关于NAFLD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多重打击”学说被认为是比较符合NAFLD发病机制复杂性的解释,其中免疫因素在NAFLD发生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以STING为中枢的免疫信号通路是新近的研究热点,该通路可能通过介导炎症和脂质代谢等参与NAFLD的发生发展.但是,STING在肝脏中的表达仍然存在争议.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在NAFLD中,STING的表达和激活只发生在肝脏非实质细胞(主要是巨噬细胞)中,但也有学者发现在肝细胞以及脂肪细胞等实质细胞中同样存在STING的表达和激活.所以进一步研究STING信号通路在代谢相关细胞(如肝细胞、脂肪细胞)和组织驻留免疫细胞中的相对贡献,以及STING信号通路激活引发这些细胞之间的潜在交叉对话,将是值得的.不仅可以更全面地认识STING信号通路以及其在NAFLD的作用机制,还可以为开发治疗NAFLD的新型治疗药物提供帮助和思路.所以,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STING信号通路与NAFLD之间的复杂关系.
当前,关于STING信号通路的临床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因和蛋白水平上,重点是在蛋白质水平上开发临床应用的靶向药物,包括激动剂和抑制剂.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STING信号通路中的关键蛋白是潜在的药物靶点.目前,关于STING信号通路在肝脏疾病的临床应用的研究主要集中病毒性肝炎和HCC上[40].考虑到STING信号通路在NAFLD中的重要作用,我们不难推测它也是开发有效治疗NAFLD的一种很有前景的潜在药物靶点,是治疗NAFLD的一种新的思路.事实上,已经有报道指出一种新型广谱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通过抑制STING信号,意外地减轻了NAFLD中的炎症和脂质功能障碍,可能是一种治疗NAFLD的候选药物[41].鉴于STING通路是一把双刃剑,可以通过激活或抑制来达到预期的效果.一方面STING信号通路的激活可以增强肝脏的免疫监测能力,另一方面STING信号激活引起的炎症反应也可导致更大的肝脏损伤,更严重的肝脏炎症甚至纤维化.所以虽然通过调控STING表达治疗和预防NAFLD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考虑当激活或抑制通路时产生的副作用是否会干扰预期的治疗效果或者尽可能地避免这些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