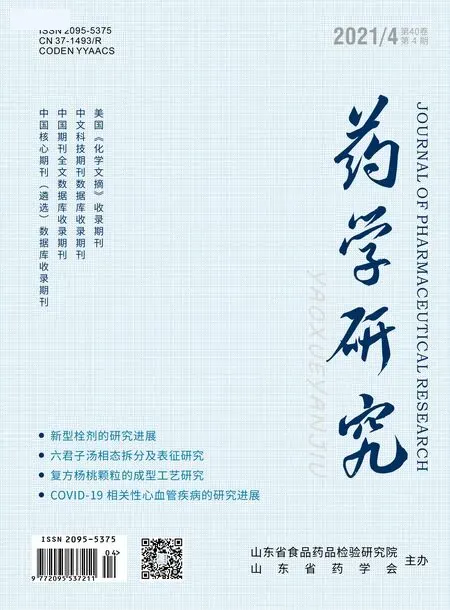COVID-19相关性心血管疾病的研究进展
2021-11-30宋双孙大康李洋程艳丽
宋双,孙大康,李洋,程艳丽
(1.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心内科,山东 滨州 256603;2.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临床医学实验室,山东 滨州 256603)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4月30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COVID-19)的大流行已导致累计超1.5亿人次感染,并造成超过300万人死亡,对全世界公共卫生、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影响。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是导致COVID-19全球爆发的病原体。起初,人们认为COVID-19涉及的器官主要是肺脏,临床表现从无症状亚临床感染、轻度上呼吸道症状、肺炎到进展为需要重症监护、机械通气等治疗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疾病严重程度各不相同[1]。目前研究表明,SARS-CoV-2可累及胃肠道和肝脏,并伴有心肌炎等心脏并发症。
1 SARS-CoV-2生物学特征
SARS-CoV-2病毒属于巢病毒目冠状病毒科(Coronavirus),病毒粒子多呈圆形,病毒直径在80~120 nm之间。SARS-CoV-2病毒为具有包膜的单股正链RNA (+ssRNA),基因组全长在26~32 kb 之间。冠状病毒科分为α、β、γ和δ 4个属,α、β属冠状病毒感染哺乳类动物,而γ、δ属冠状病毒感染鸟类。目前已知有7种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类,其中α属冠状病毒HCoV-229E、HCoV-NL63和β属冠状病毒 HCoV-OC43、HCoV-HKU1仅引发轻微病变。而β属冠状病毒SARS-CoV、SARS-CoV-2及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可引发人类严重的呼吸道病变。
SARS-CoV-2的基因组主要编码4种结构蛋白,包括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S)、包膜蛋白(envelope membrane protein,E)、膜蛋白 (membrane protein,M)以及核衣壳蛋白(nucleocapsid protein,N)。SARS-CoV-2的S蛋白是该病毒的主要抗原成分,是病毒与受体结合的部位。S蛋白分为S1和S2结构域,其中S1结构域具有受体结合区(receptor binding domain,RBD),能与呼吸道上皮细胞、肺脏、心脏等部位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ACE2)受体结合,这种结合有助于病毒附着于靶细胞表面。S蛋白的S2结构域则主要介导冠状病毒与感染细胞的融合。与SARS-CoV相比,SARS-CoV-2的S蛋白与ACE2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宿主细胞跨膜丝氨酸蛋白酶TMPRSS2可以激活病毒S蛋白,是SARS-CoV-与ACE2结合的先决条件。
2 SARS-CoV-2的复制、传播及侵入
SARS-CoV-2的复制需要RNA依赖性RNA聚合酶的参与,病毒至少含有6个开放阅读框。由于SARS-CoV-2具有较高的基本繁殖率(R0=2~2.5),其传播性远远高于2003年SARS-CoV引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和流感。某些COVID-19患者体内病毒载量非常高,每毫升痰样品中RNA病毒复制本可以达到10亿,并且痰液污染的表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具有传染性。与铜或硬纸板界面相比,SARS-CoV-2在塑料或不锈钢界面更加稳定。在抵达这些界面72 h后,病毒活性依然可以检测到。由于COVID-19病情严重的患者具有很高的病毒载量,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病毒播散能力,因此SARS-CoV-2病毒载量是判断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重要指标。
为了更好地了解心血管疾病与COVID-19的相关性,明确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基本病理变化是非常重要的。SARS-CoV-2可以与肺泡Ⅱ型上皮细胞、巨噬细胞等的ACE2受体蛋白结合进入细胞。在此过程中,细胞跨膜丝氨酸蛋白酶TMPRSS2对S蛋白的切割非常关键。由此看出,SARS-CoV-2感染的宿主细胞需同时表达ACE2蛋白和TMPRSS2。ACE2除了在肺泡Ⅱ型上皮细胞高表达外,在血管周细胞中亦呈高水平表达。血管周细胞在全身毛细血管及微血管广泛分布,因此血管周细胞高表达ACE2会导致严重的心血管功能异常,这很好的解释了COVID-19患者易发急性冠脉综合征的原因。心力衰竭会引发ACE2表达上调,这可能是心力衰竭患者SARS-CoV-2感染率、致死率较高的原因。了解冠状病毒引起机体的病理改变及病毒的传播特点,为我们寻找新的治疗靶点提供有力帮助。应用ACE2阻断型抗体或者抑制TMPRSS2的表达,会阻断SARS-CoV-2侵入细胞,阻碍或减缓COVID-19的病理进程。
3 COVID-19的主要临床表现
SARS-CoV-2潜伏期通常为1~14 d,研究发现在存活者中病毒核酸脱落时间最短为8 d,最长为37 d,中位持续时间为发病后20 d;但在非存活者死亡之前均可检测到病毒。COVID-19主要临床症状包括发热、干咳、乏力、肌痛和呼吸困难,其中发热、咳嗽多伴随出现,随后可出现呼吸急促和严重疲劳(与发展为重症肺炎有关);少见症状包括头痛、鼻塞、咽喉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和腹泻等。胸部CT以磨玻璃样影和双侧斑片状影最常见,在一些严重的病例中,也曾并发纵隔气肿和气胸。同时死亡患者的肺部病理检查显示:支气管及细支气管可见大量黏液堵塞,支气管上皮细胞损伤;肺泡间隔可见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浸润;肺泡腔内充满纤维素渗出物;多核巨细胞增多;Ⅱ型肺泡上皮细胞明显增生。COVID-19临床表现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而宿主本身最有可能是造成这种异质性的原因。虽然该病的临床症状主要是呼吸系统,但直接或间接累及其他系统也很常见,尤其是心血管系统。既存心血管疾病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严重感染的风险。
4 COVID-19炎症反应的特征
在COVID-19中,除了肺脏之外免疫器官是受影响最重的器官。病理检查发现,COVID-19患者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肾脏萎缩,伴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数量下降、坏死及全身性出血。同时淋巴结中的淋巴细胞出现耗竭,CD4+、CD8+细胞数量显著下降。这与某些重症病例中表现出的外周血淋巴细胞减少症相吻合。有意思的是,在COVID-19患者中IL-2、IL-6、IL-7、GSF、CXCL10、CCL2、TNFα等细胞因子或趋化因子会系统性升高,表现出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的特点。CRS的发展进程与COVID-19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相对应。CRS细胞因子表达谱与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ocytosis)比较近似。COVID-19可能是继发性嗜血细胞综合征(HLH)所导致的血细胞减少的原因之一,骨髓中可出现吞噬血细胞及纤维蛋白原含量降低。流式细胞术检测发现:COVID-19患者T细胞出现过度活化的现象,其HLA-DR+或 CD38+的CD8+和CD4+T 细胞比例显著升高,同时CCR6+的Th17细胞比例亦显著升高。T细胞过度活化会导致严重的免疫损伤,类似于动脉粥样硬化。
IL-6表达水平升高常见于CRS患者。对武汉150多名COVID-19病例进行多中心回顾性分析,发现外周血IL-6含量可作为判断COVID-19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预测指标。在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中,IL-6是重要的生物标志物和致病靶点。Tocilizumab(托珠单抗)作为IL-6受体抑制剂,常用于肿瘤治疗或HLH的辅助治疗,治疗或预防CRS的发生。在一百多个国家Tocilizumab也广泛应用于类风湿关节炎、幼年特发性关节炎、Castleman病(血管滤泡性淋巴结样增生)、巨细胞或大动脉炎等疾病的治疗。其他的IL-6受体靶向药物,譬如Sarilumab(沙利鲁单抗)也具有同样的潜在功效。
IL-6受体靶向药物可应用于COVID-19治疗,以缓解CRS的病理进程。COVID-19在中国爆发之初,Tocilizumab被用于该病的治疗,以缓解严重的CRS所导致的器官衰竭和死亡。在21例严重的COVID-19患者应用Tocilizumab进行治疗后,19例患者在2周内治愈出院。在中国,Tocilizumab已被批准用于伴IL-6水平升高的严重、复杂的COVID-19病例。在意大利某医疗机构,Tocilizumab被用于6名COVID-19患者的临床治疗,其中3名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显著改善。这大大推动了多家机构的研究规划,开展针对IL-6拮抗剂的单克隆抗体研究,用于COVID-19的治疗。
某些COVID-19患者在出现细胞因子风暴,IL-6细胞因子水平升高后,会伴有多种较明显的心血管改变,譬如心动过速、高血压、左室功能异常。CRS相关的心脏毒性亦会显现,主要表现为传导异常、房颤、BNP和cTnIs升高。COVID-19患者中、长期的心血管病理改变与IL-6信号通路的异常活跃相关。大量实验研究表明IL-6和其他CRS相关细胞因子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也可引发心肌纤维化和心力衰竭。体外实验表明:细胞因子会促进上皮细胞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同时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会激活巨噬细胞,促进后者产生大量的IL-6。在动脉粥样硬化小鼠动物模型中,高血脂组小鼠主动脉中IL-6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注射重组IL-6,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28]。应用IL-6反式信号传导抑制剂可溶性糖蛋白(gp130),可显著缓解LDL受体缺陷小鼠的病理改变。由于IL-6可影响小鼠体内脂质的稳定性,因此血浆IL-6水平与腹主动脉瘤的进展有很高的相关性。IL-6反式信号通路活化可促进实验性心肌纤维化的形成,而在肺动脉高压模型中IL-6受体上调会导致血管重构。另外 GM-CSF、TNF-α、IL-17、IL-18、IFN-ϒ等细胞因子亦通过多种特定的信号通路,参与、影响COVID-19的病理进程。
5 COVID-19与心肌炎和心肌损伤
心肌损伤和急性心肌炎是急性病毒感染常见的并发症。在最近的一例COVID-19患者心脏尸检样本中,发现心肌坏死及单核细胞浸润的现象。这与其他暴发性心肌炎病例报道相一致,提示心肌炎是导致COVID-19患者心肌损伤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临床上,COVID-19患者的心肌炎主要表现为轻微的肺部不适和心悸,这些表征难以把COVID-19与其他疾病相区分。在合并心肌炎的COVID-19患者中,常出现心肌损伤标志物(如cTnI、CK)水平升高和短暂的心电图改变,有助于明确心肌损伤的存在及评估病情严重程度。心肌炎会导致传导阻滞、室性心动过速及左室功能减弱等。
在临床工作中,当发现有心肌损伤表征但缺乏急性冠脉综合征证据时,多怀疑心肌炎可能。通过心脏的核磁共振检查,急性心肌损伤可明确诊断[32]。心内膜心肌活检作为检测的金标准,可直接明确心肌坏死及单个核细胞的浸润[33]。在欧洲对急性心肌炎患者进行活组织检查发现,病毒起源的病例范围大约在37.8%~77.4%。大量研究表明,暴发性心肌炎是COVID-19的重要临床指征之一,但其具体的发病率目前尚不清楚。从当前COVID-19的流行趋势以及其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威胁程度来看,心脏核磁共振检查及心内膜心肌活检作为常规检测手段是不太合适的。
从病毒介导的肌细胞溶解开始,可将病毒性心肌炎动物模型分为多个发展阶段。心肌损伤可激活固有免疫系统,释放大量的炎性细胞因子[35]。心肌细胞裂解后释放的蛋白质具有某些与病毒抗原类似的表位,与MHC分子结合后可进行抗原提成。肌球蛋白是一种心脏肌节的结构蛋白,可能以“分子模拟”的方式发挥抗原作用。虽然在此阶段心内膜心肌活检显示有炎症反应变化,但机体固有免疫应答系统已有效清除病毒,导致病毒颗粒无法检测到。获得性免疫应答是该阶段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抗体升高和T细胞活化。CD4+辅助性T细胞和CD8+细胞毒性T细胞可激活,导致炎症级联反应和细胞裂解,巨噬细胞迁移至心肌损伤部位。在病毒性心肌炎末期,亦称为恢复期或低水平炎症反应期,伴有继发性左室功能下降。有意思的是,COVID-19患者在出现首发症状之后心肌炎可持续较长时间(10~15 d)。目前一个关于治疗选择的核心问题尚不明确,即心肌细胞损伤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由病毒复制(细胞毒性)造成的,亦或通过其他途径实现。考虑到急性心肌损伤一般出现在COVID-19症状发作2周后,心肌细胞损伤进程开始启动,T细胞介导的适应性免疫应答及固有免疫效应分子失去有效控制,在心肌细胞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重症病例中出现CCR6+Th17细胞显著升高,产生大量的炎性细胞因子介质,加速病毒性心肌炎的发展。
6 COVID-19中的其他心血管疾病
6.1 COVID-19与心律失常 SARS-CoV-2感染后出现的代谢功能障碍、心肌炎症和交感神经兴奋,均易导致心律失常,包括房颤、传导阻滞、室性心动过速和室颤等。一份关于138名COVID-19住院患者的报告[12]显示,16.7%的患者合并心律失常,在COVID-19常见并发症中居ARDS之后的第二位。在36例因并发症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患者中,有44.4%的患者出现心律失常;而不需要转入ICU治疗的患者中有7%出现心律失常。有趣的是,在最初暴发期间,一些患者就诊的主要原因是心血管系统症状,如心悸、胸闷,而非呼吸道症状。
6.2 COVID-19与高血压 现有数据显示COVID-19患者高血压患病率约15%~40%,与普通人群中的高血压患病率(33%)基本一致。一份包含191例COVID-19患者的研究报告显示,91例(48%)COVID-19患者出现并存疾病,其中高血压最常见[58例 (30%)]。而重症COVID-19患者中,58.3%的患者合并高血压。另一份关于COVID-19的报告显示,约23.7%的重症患者、13.4%的普通患者合并高血压,因此高血压可能在重症感染患者中更为普遍。目前认为COVID-19合并高血压可能与ACE2有关。SARS-CoV-2最初通过ACE2进入靶细胞,随后还可下调ACE2的表达。由于ACE2是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中的一种关键的负向调节酶,可将血管紧张素Ⅱ降解为血管紧张素-(1~7),减弱其对血管收缩、钠潴留和纤维化的影响,因此SARS-CoV-2下调ACE2表达会增强血管紧张素Ⅱ的活性,出现高血压、心肌纤维化等情况。
6.3 COVID-19与心肌损伤和心力衰竭 研究表明血清肌酸激酶(CK)和乳酸脱氢酶(LDH)在大部分COVID-19住院患者中表达升高。而在首次确诊的41例COVID-19患者中,有5例出现心肌损伤,主要表现为超敏肌钙蛋白Ⅰ水平升高(>28 pg·mL-1)。一份包含138名COVID-19住院患者的研究报告指出,需收入ICU治疗的重症患者中,心肌损伤标志物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患者。研究还发现NT-proBNP、cTnI、hs-CRP的升高与疾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应通过监测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超敏肌钙蛋白Ⅰ等心肌损伤标志物,综合评估患者的病情状况。
SARS-CoV-2感染后可导致包括暴发性心肌炎在内的心脏并发症。一份关于COVID-19住院患者的报告显示,23%的COVID-19患者出现心力衰竭,其中包括52%的死亡患者,12%的幸存者。其他报告显示,约7.2%~17%的COVID-19住院患者合并急性心肌损伤,可能表现为急性心肌炎或心肌梗死等。在分析武汉市68例COVID-19死亡病例时发现,36例(53%)死于呼吸衰竭,5例(7%)出现心肌损伤最终死于循环衰竭,22例(33%)死于两者。
6.4 COVID-19与冠心病 目前认为病毒性疾病通过全身炎症反应、细胞因子风暴以及向不稳定表型分化的免疫细胞,可能潜在地破坏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稳定性。人类心脏单细胞图谱显示,COVID-19患者心脏中周细胞的ACE2表达水平升高,SARS-CoV-2感染周细胞时可能发生局部微血管炎症,出现严重的微血管功能障碍,最终导致非阻塞性冠状动脉心肌梗死。此外,细胞因子风暴可以导致内皮功能障碍[42]。
6.5 COVID-19与凝血异常 以D-二聚体、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升高为主要特征的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和肺栓塞,在COVID-19中非常普遍。研究发现大约71.4%的死亡患者中合并DIC,同时亦有大量关于肺栓塞的报道[44]。值得注意的是,D-二聚体水平升高对COVID-19的不良结果具有很高的预测性。在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中发现,D-二聚体水平升高(>1 g·L-1)与住院死亡率密切相关。
7 总结
COVID-19感染与心肌损伤有关,而心肌损伤与更严重的病情进展甚至死亡相关。通过对COVID-19相关性心血管疾病进行综述,我们发现本次非典型肺炎的暴发易出现肺外表现,因此即使患者没有呼吸道症状,临床医生也应保持高度的怀疑,以确保最大限度地减少社区和医护人员的接触。同时我们在综述中发现目前对COVID-19相关性心血管疾病的认识仍有很多不足之处,如既存的心血管疾病是否增加SARS-CoV-2感染及病情恶化的风险、宿主感染SARS-CoV-2后不同反应的决定因素以及COVID-19患者继发心肌损伤的具体机制,还需要深入的实验研究。而且关于COVID-19的治疗,目前仍缺少特异、有效的治疗方案,需要进一步寻找治疗和预防的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