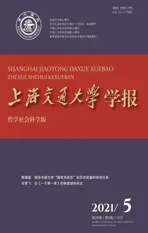论《一千零一夜》的嵌套结构形式
2021-11-30宗笑飞
宗笑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引 言
目前,国内关于《一千零一夜》的研究已有诸多成果,但大抵集中在故事类型、人物形象、社会意义方面的评析,或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世界各国文学的影响。而聚焦于套盒式或嵌套式框架结构本身的研究论文并不多见,且已有成果主要讨论有关结构形式的叙事功用,如徐娴的《一千零一个山鲁佐德》(1)徐娴.一千零一个山鲁佐德: 《一千零一夜》的隐含作者与连环穿插式结构的关系[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3(4): 96-100.、张莎的《析〈一千零一夜〉的框架式故事结构》(2)张莎.析《一千零一夜》的框架式故事结构[J].语文学刊,2009(17): 135-136.等采用叙事学中的“隐含作者”理论分析其嵌套结构的叙事技巧。
关于这种嵌套式结构的来历或源头,国内现有成果大多止于对民间传说的泛泛而论或简要评述,如2017年赵建国发表的论文《〈一千零一夜〉的框架式故事探源》,在谈及印度《五卷书》的创作结构时肯定了它对《一千零一夜》的启发和影响,但对其框架构成及美学价值没有深入展开;(3)赵建国.《一千零一夜》的框架式故事探源[J].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 55-57.穆宏燕的《〈一千零一夜〉主线故事探源》从波斯、印度两处分析这部民间故事集的嵌套结构源头,认为其印度源头与《五卷书》密不可分,有些故事明显源自《佛本生故事集》;(4)穆宏燕.《一千零一夜》主线故事探源[J].国外文学,2015(1): 135-142.李俊璇在其《影响与再创造——〈五卷书〉与〈一千零一夜〉之比较》中也分析了印度《五卷书》在结构、内容、思想、手法等四个方面对《一千零一夜》的影响。(5)李俊璇.影响与再创造: 《五卷书》与《一千零一夜》之比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3): 108-112.
一般说来,学界的基本共识是,《一千零一夜》这部民间故事明显受到波斯和印度文化的影响。埃及学者苏海勒·卡拉马薇(Suhair al-Qalamwi)在其专著《〈一千零一夜〉研究》(AlfLaylawaLayla:Dirsa,1959)中也谈到了《旧约·以斯帖记》、波斯的《赫扎尔·艾夫萨那》以及印度的故事对其结构的影响(6)Suhair al-Qalamwi.Alf Layla wa Layla: Dirsa[M]. Cairo: Dar al-Ma‘rif, 1959: 44-48,73-92.。此外,以笔者正在从事《一千零一夜》学术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尽管西方《一千零一夜》最早的译本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研究起步较晚。18世纪和19世纪,辨别《一千零一夜》手稿真伪的研究成为焦点,如佐登堡(H. Zotenberg)的《神灯中的阿拉丁故事》(Histoired’Alal-Dn,ouLaLampemerveilleuse,1888)(7)H. Zotenberg. Histoire d’Al al-Dn, ou La Lampe merveilleuse[M].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88.、邓肯·布莱克·麦克唐纳(Duncan Black Macdonald)的《纽伯利图书馆中的阿拉伯和土耳其手稿》(TheArabicandTurkishManuscriptsintheNewburyLibrary,1912)(8)Duncan Black Macdonald. The Arabic and Turkish Manuscripts in the Newbury Library[M]. Chicago: The Newberry Library, 1912.及其一些相关文章等,均或多或少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贡献。穆赫辛·马赫迪(Muhsin Mahdi)也颇耗心力,在其《一千零一夜: 依据阿拉伯原本》(KitbAlfLaylawaLaymin’Usulihal-‘Arabiyahal-’la,1984)(9)Muhsin Mahdi. Kitb Alf Layla wa Lay min ’Usulih al-‘Arabiyah al-’la [M]. Leiden: Brill,1984.中,对《一千零一夜》的可能母本和故事层进行了梳理。一个普遍的现象是,19—20世纪的西方学者大多出于马克思所说的“双重殖民需要”,将《一千零一夜》当作猎奇和“他者化”工具,直至20世纪,纷纷攘攘的各种主义将其适用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诉求。尽管也有学者,如罗伯特·厄文(Robert Irwin),曾在其《一千零一夜: 导读》(TheArabianNights:ACompanion)(10)Robert Irwin. The Arabian Nights: A Companion[M].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94.中对《一千零一夜》的波斯、印度、希腊等源头进行了细致的类比,但对其审美维度未做过多涉及,而审美维度恰恰是我国传统文艺批评之所长。
就印度这个源头来说,毋庸置疑,《一千零一夜》受《五卷书》(11)后汇入《故事海》(Katha Sarit Sagara)。除《五卷书》外,《故事海》中的其他故事也大多使用框架结构。后者成书于11世纪,但其口传期可追溯至7世纪前。参见月天.故事海选[M].黄宝生,郭良鋆,蒋忠新,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1.影响很大,而它同时也有《罗摩衍那》(Rmyaa)重要的结构形式。本文除了补充《一千零一夜》的另一重要渊源——《罗摩衍那》外,还着重分析其框架结构的美学价值。
一
敦煌学者仁欠卓玛在《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的框架式叙述结构分析》一文中指出:“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属于纵向发展式结构,但也有其特殊之处。纵观全文,以罗摩和悉多故事为框架,其中穿插了鸟国的故事、猴国的故事和罗婆那的故事,形成了纵向发展的框架式叙述结构。”(12)仁欠卓玛.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的框架式叙述结构分析[J].北方文学,2016(6): 211.而敦煌古藏本《罗摩衍那》作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早期中译本,不仅内容丰富、故事动人,并且在我国境内流传了一千三百多年。(13)仁欠卓玛.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的框架式叙述结构分析[J].北方文学,2016(6): 211.
先说《罗摩衍那》的框架结构,它以罗摩的英雄事迹以及罗摩与悉多的情感纠葛为主线,串联起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对人物的性格塑造产生了影响,而且起到了推动情节、烘托气氛的作用。《罗摩衍那》由七篇组成。第一篇是楔子,虽内容庞杂、线索众多,但关键情节无疑是大神毗湿奴化为罗摩下凡,以及随着罗摩诞生、成长所衍生的其他故事。而在这些故事中,悉多的诞生以及罗摩与她结为夫妻无疑至关重要,可谓故事的主线。季羡林先生在分析《罗摩衍那》时认为,“这一篇是后来窜入的”。(14)蚁垤.罗摩衍那(一): 童年篇[M]. 季羡林,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同样,季先生谓最后一篇(第七篇)也“是后来窜入的”。(15)蚁垤.罗摩衍那(一): 童年篇[M]. 季羡林,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和第一篇类似,最后一篇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罗刹的起源,以及罗波那和哈奴曼的故事;二是罗摩与悉多的第二次离合。在此,罗摩的性格几乎完全改变,他听到一些风言风语,竟然派人将身怀六甲的悉多遗弃在荒山野林之中。幸好蚁垤仙人救了悉多,使她得以平安生下罗摩的一对孪生子。母子三人在仙人的照拂下度过了十几年的时光。后来,仙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罗摩宫,让他们当着满朝文武朗诵《罗摩衍那》。罗摩终于明白,眼前的两个少年就是自己的儿子。罗摩于是请蚁垤将悉多带来。众神也于此时降临,悉多当众向诸神发誓,如果自己是贞洁的,那么就请地母不弃。这时,大地忽然裂开,悉多纵身跃入地母怀抱,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罗摩追悔莫及,遂传位于儿子,自己化为毗湿奴升入天堂。
从罗摩和悉多的主干故事来说,第二篇至第六篇的确构成了史诗《罗摩衍那》的主要情节;但若从叙事结构来看,第一篇和第七篇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第七篇,作为框架结构的主要枢纽: 那一对孪生兄弟(恰似《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敦娅佐德姐妹),起到了贯穿作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摩衍那》的首尾两篇很可能是文人窜入的,从而结束了作品的口传时代,擢升了史诗的艺术表现方式。所谓散为千珠,聚则一贯,无论是《一千零一夜》《罗摩衍那》,还是《五卷书》,它们的框架结构都是聚起千珠的金丝银线。
如果说,我国的传统载道论与西方的模仿说异多同少,那么因承较多老庄学说的《文心雕龙》与西方形式美学的关系则似乎恰好相反。前者侧重于形式(风格)与想象(神思),所谓“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文心雕龙·体性》),或“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神思篇》)。同样,西方形式美学从古希腊到康德的一元论和黑格尔形式/内容二元论,再到20世纪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历时两三千年并最终衍生出“形式即美”,以至于无论在文学还是语言学层面,形式(能指)凌驾于内容和真实之上。(16)Theodor Adorno.Aesthetic Theory[M]. London: Continuum, 2002: 159.然而,《一千零一夜》的形式却服从于内容,嵌套是为了接续,动听是为了劝诱,并且用我们的话来说,终于“文以载道”: 善恶有报,恶有恶报,当然,《一千零一夜》还加上了“一切自有天定”的宗教思想,这是题外话。
二
一如《罗摩衍那》中的孪生兄弟,山鲁佐德姐妹在《一千零一夜》中既是叙述者,也是重要人物。而她们的长老师傅又恰似蚁垤仙人,是显性作者(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何尝不是隐性的荷马?或者他们与荷马一样,本身也是大写的。史诗或民间传说,其真正作者往往是复数的,是由无数无名口传者(吟诵者)经年累月完成的艺术结晶。当《伊利亚特》吟响:“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致命的愤怒吧……”(17)荷马.罗念生文集·第五卷: 伊利亚特[M].罗念生,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5.荷马便诞生了。尽管这一个“荷马”常常被学术界冠以引号,诚如罗念生先生所言,“荷马”是一个“问题”——简称“荷马问题”。(18)荷马.罗念生文集·第五卷: 伊利亚特[M].罗念生,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3.本人无意就荷马是否曾经存在探赜索隐,但无论如何都认为他是标志性的,不仅十分重要,而且不可或缺,因为自他以降,古希腊神话传说终于摆脱了口传形态,开始成为成型(定型)的史诗。至于荷马他(她)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或一群人、几代人,于我而言并不重要。同样,当《罗摩衍那》唱出“仙人魁首那罗陀,学习吠陀行苦行,擅长词令数第一,苦行蚁垤问分明”,(19)蚁垤.罗摩衍那(一): 童年篇[M]. 季羡林,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由此大写的或复数的蚁垤便产生了。
以此类推,《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可谓承担了“作者”“叙述者”“人物”三重角色:
很久很久以前,相传在印度和中国的众岛屿间,有个萨珊王国……(20)Alf Layla wa Layla[M].Cairo: Matba’ Bulq al-Amīrīyh,1860: 2.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就这么开始了。但起初我们并不知道山鲁佐德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讲那么多故事,直至作为楔子的《山鲁亚尔及其兄弟的故事》接近尾声:
晚上,国王正想和山鲁佐德亲热,不料她却哭了起来。国王问她原因,她说:“国王陛下啊,我有一个妹妹,我想要和她道个别。”
国王于是派人请来了敦娅佐德。……妹妹对姐姐说:“姐姐,看在安拉的份上,给我讲个故事吧,咱们好打发长夜。”
国王本来也觉得心烦,听了这话不由觉得高兴,也想听听故事。
于是打那晚起,山鲁佐德开始讲一个又一个的故事。(21)Alf Layla wa Layla[M].Cairo: Matba’ Bulq al-Amīrīyh,1860: 7.
这显然是个楔子,是由荷马或者蚁垤似的编纂者窜入的,从而串起了一千零一个故事。当然,在不同版本中,故事并不都是一千零一个(22)关于《一千零一夜》这个书名的最初出现时间,学界有不同说法。厄文(Robert Irwin)教授的观点是该书名第一次出现于12世纪开罗犹太人旧书冢目录中,当然也有可能上溯至更早。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而众多版本中故事数量也远未达到1 001个,个中情由本文不再赘述。;即使按大故事套小故事,小故事套小小故事算起,也不是所有版本都凑得齐一千零一夜(或一千零一个故事)。譬如在马德鲁斯版本中,不仅第六百一十七夜至七百夜的故事残缺不全,而且第六百七十九夜至七百夜是完全付之阙如的。马德鲁斯竟称那是因为山鲁佐德生了孩子,而且是替国王山鲁亚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23)Ulrich Marzolph, Richard van Leeuwen. The Arabian Nights Encyclopedia: Vol.2[M].Oxford: ABC-CLIO, 2004: 637-638.大多数版本则是以夜为分界,凑齐了一千零一这在博尔赫斯看来是“无穷尽”(24)Borges J L.Siete noches[M].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80: 65-66.的神奇数字。
由于是故事套故事,《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也平添了许多悬念,仿佛我国章回小说或说书人口中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套盒式的框架结构还明显有利于“节外生枝”: 大故事暂且悬置,小故事不断衍生。这与中国说书人吊人胃口的某些“机关”(欲知张三如何,必先说明李四如何)十分相似,譬如《渔夫与魔鬼》《脚夫与女孩》《国王与王子》《王子与公主》《女蛇王》《太子与王妃》《王子与宰相》等故事中都嵌入了若干个小故事,
此外,一如中国套盒或俄罗斯套娃,小故事中的小小故事又为小故事制造了悬念。这样一来,山鲁佐德便不仅是令人牵挂、命悬一线的人物,而且也是故事的叙述者和套盒的制造者。于是,她的命运一定程度上又攥在了自己的手中,直至国王山鲁亚尔这个人物和普通读者一样忘却了烦恼(仇恨),彻底为故事本身所感染。
同时,也由于是套盒式框架结构,故事的现实情景被不断打破,亦真亦幻、有虚有实,古往今来、天南海北被赋予了更多的色泽——虚构色彩。法国学者罗歇·凯卢瓦(Roger Caillois)曾致力于建构幻想美学,并在其《幻想文学选集》(AnthologieduFantastique,1966)中历数了古来十余种幻想文学形态,《一千零一夜》自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幻想文学形态之一,遗憾的是他仅仅列出了一个: 神秘移动或神秘消失的物体。(25)Roger Caillois.Anthologie du Fantastique[M]. Paris: Gallimard, 1966: 12.然而,事实上《一千零一夜》不仅形态丰富多彩,而且其中的一些故事元素还是绝无仅有的艺术珍品,除了神秘移动的物体,如飞毯或乌木马,更有镇锁魔鬼(巨人)的小瓶子和瓶盖上的所罗门封印、两个相反相成的梦、神秘的宫殿等等。至于魔戒、魔杖、魔法、仙女、巫师等,更是数不胜数。可以说,世界文学史上罕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幻想作品。我国《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聊斋志异》中的狐仙女鬼、《镜花缘》中的大人国小人国,以及《搜神记》《述异记》《山海经》《封神榜》等,通常都指向一种或一类幻想(或幻象)。外国文学中也是如此,除了少数童话集可勉强与其比肩,实在找不出第二部像《一千零一夜》这么奇谲灵异的作品了,真可谓一骑绝尘。
诚然,无论多么诡谲灵异,也无论是妖魔鬼怪还是动物世界,《一千零一夜》借以表现的仍不外乎人事。除了家喻户晓的魔鬼或者妇孺皆知的魔法师,《一千零一夜》还有大量以动物为主角的故事嵌套在各色故事之中,譬如来自《五卷书》或《卡里来与笛木乃》的许多寓言。这些故事被赋予了强烈的教化功能,一些阿拉伯学者,如苏海勒·卡拉马薇、艾哈迈德·穆罕默德·沙哈兹(Ahmad Muhamad Shahhz)等,均强调《一千零一夜》不仅具有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教化色彩,而且它并非简单的低俗故事,其宗教宣扬的意味也非常明显。(26)Suhair al-Qalamwi. Alf Layla wa Layla: Dirsa[M]. Cairo: Dar al-Ma‘rif, 1959; Ahmad Muhamad Shahhz. Malmiha as-Siysah fi Hikyt Alf Layla wa Layla[M]. Baghdad: Dr ash-shuwūni ath-thaqfah al-’mma, 1986.它里面的一些篇什还与希腊故事交织缠绕,例如《狐狸与乌鸦》。尽管在《一千零一夜》中令人欣喜的是最终乌鸦比狐狸还聪敏,不仅识破了狐狸的诡计,而且给它讲了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故事——《麻雀与老鹰》。后者说的是麻雀自作聪明,想学老鹰去抓小羊,结果反被羊毛缠住了爪子,牧羊人将它逮个正着,并拔掉它的羽毛、送给儿子当玩具了。然而,在这之前,狐狸刚刚给老狼讲过另一个故事,说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农夫与蛇”。当然,在《一千零一夜》中,农夫变成了路人,他为了搭救一条仓皇逃遁的毒蛇,好心将其藏于口袋之中,结果待捕蛇者走远后,毒蛇露出本性,咬了恩人一口作为“报答”。而老狼和狐狸掉进陷阱时,狐狸也曾以它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前者作为梯子让自己跳出陷阱,然后它不但没有回去搭救老狼,还幸灾乐祸地给后者讲了那个路人与蛇的故事。依此类推,老鼠和猫的故事同样讲不该怜悯蛇(对于老鼠而言是猫)一样的恶人,否则后患无穷。
而另一方面,由女蛇王统治的蛇王国,其臣民都是硕大无比的巨蟒,只有女蛇王是蛇身人脸,而且面目十分靓丽。她向来客讲述古老的传说和天堂地狱的故事。鸟王国三仙子(或谓羽翼仙子)与王子的邂逅则不仅讲述了爱情的奇妙,而且揭示了人类因贪欲所引发的战争以及战争的残酷无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可见,《一千零一夜》中几乎所有幻想和丑恶的反面依然是作品(那个大写的、复数的作者)试图彰显的真善美。与此同时,《一千零一夜》昭示的人物往往不是西方哲人黑格尔所谓的“这一个”,而是“这一类”,这保证了作品主题的一贯性和一致性。即或个别故事因为大量嵌套而显得形式上长短不一,甚至“残缺不全”,但这种“残缺的美”宛若断臂维纳斯,似乎格外受到20和21世纪读者的青睐,其中的非对称性更是现代造型艺术的重要选择。
三
回到《一千零一夜》的结构,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现代派文学曾挖空心思地进行形式探索、结构创新。如今,当我们蓦然回首,却发现他们的许多形式,其实在《一千零一夜》中俯拾即是。
时代的变迁往往导致文学内容、文学观念发生变化,而文学内容、观念的变化又会直接影响文学形式和创作方法的演化。虽然在文学作品中,内容和形式、观念和方法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但是从以往文学作品的产生方式看,形式却常常取决于内容,方法取决于观念。因而,传统的说法是形式美的关键在于适应内容,为内容服务,与内容浑然一致。然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随着形式美学的兴起,传统的美学观念遭到颠覆。至于形式主义,更是强调审美活动和艺术形式的独立性,将内容决定形式倒转为形式即内容,进行非对象化纯形式表现。这显然是美学观念中的另一个极端,难免失之偏颇。从结构形式看,纵观现代派小说,我们大抵可以发现以下几个路径:(27)陈众议.拉美当代小说流派[M].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1995: 63-95.
(一) 以时序为突破口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也是时间的艺术,这早已成为一个普遍的命题。举凡小说都有人物、场景、情节、情绪、氛围等,这些都包含着时序、时值、时差的变化因素,直接影响着小说的形式和形态。
但是,最初的小说(以及小说出现之前的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和古典戏剧等)几乎无一例外地遵循着一维时间的直线叙事形式,以致莱辛、黑格尔等艺术大师断言同时发生的事情都必须以先后承续的序列来描述。中国古典作家则常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与莱辛、黑格尔如出一辙。所以,时间的艺术性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顺时针和单线条是几乎所有古典小说的表现形式,由于时间尚未成为一个“问题”,因此自始至终从容道来便成为一种习惯。
然而,人的心理活动并不完全遵循自然时序,按照先后的程序进行。首先,时间是客观的,但人们感受时间时却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同样的一个小时,可以“瞬息而过”,也可能“度之如年”。即便是同一个人,对同样长短的客观时间也会有“时间飞逝”或“时间停滞”之感,这些感觉是人们受不同情景刺激所产生的心理现象。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曾诙谐地比喻,一对恋人交谈一小时,比一个心烦意乱的人独坐炉前被火烤十分钟,要“短”得多。其次,时间是客观的,但艺术时间却具有很大的可变性、可塑性。千里之遥、百年之隔,尽可一笔带过;区区小事、短短一瞬,写不尽洋洋万言,文学对时间最初的艺术加工就从这里入手。再次,时间是客观的,但速度可以改变时值。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科学地论证了时间与运动的关系,譬如飞速行驶的列车之内的时间值不等于候车室里的时间值,尽管其差甚微,倘若能以超光速运行,将会产生时间的倒流和因果的颠倒,梦就更不必说。
因此,作为文学描写对象的人和自然是复杂的,事物并非都是循序渐进的。除了直线以外,存在着无数种事物运动形式。于是,现代小说开始在时序上大做文章,不仅有倒叙、闪回,还有穿插、并行、错乱等。而《一千零一夜》中这些均已存在,虽然并不极端,但各种迷宫般的窜入和交叉、闪回和平行、枝蔓和省略所在皆是。
(二) 以结构为聚焦点
文学是语言和时间的艺术,同时也是结构的艺术。虽然时间与结构密切相关,但并不能完全涵盖结构。20世纪以来,尤其是拉丁美洲小说崛起后,作为西方现代小说的集大成者,拉丁美洲小说的结构形式越来越成为一种艺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或可以说是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尽管在具体作品中,它们愈来愈同内容完美统一,成为内容的骨骼。
不言而喻,结构是小说内容和形式(指总的形式)最终达到完整统一的契机,是小说形式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小说的构思过程也即小说结构形式的设立过程。因此,结构不等于单纯的故事框架,它意味着作家对生活的审美把握,是从产生内容的构思中诞生的,是具有实在内容的形式。
但是,传统的小说结构一般比较单一,大致仅有三种,即顺叙、倒叙或插叙。而20世纪的小说,尤其是现代派小说讲究开放、追求变化。于是,各种结构形态应运而生。其中较为常见的有“蒙太奇”结构,如一些意识流小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科塔萨尔的《跳房子》等当在此列。
同样,在《一千零一夜》中,由于故事中不断嵌入其他故事,或可称那些不断嵌入的小小故事为有关人物的独白,尽管它们并不像意识流那么任意和跳跃。反过来说,无论意识流的蒙太奇如何支离破碎,其终极目标依然是为了传达人物潜意识或无意识状态的某种感觉、心境,归根结底也还是作家刻意传递的某种意识形态。
和“蒙太奇”结构几乎一样常见的是平行结构或套盒结构。后者在《一千零一夜》中更可谓比比皆是。拉美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加斯·略萨曾多次谈到套盒结构,并在创作中身体力行。他在评价博尔赫斯时也曾强调这种结构形式,遗憾的是他并未就博尔赫斯同《一千零一夜》的关系留下评骘,倒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其实应该以乌尔苏拉讲述的故事为开端,同时并行的便是奥雷里亚诺第二和作者自己同《一千零一夜》的遭遇”。(28)Mario Vargas Llosa.Gabriel García Mrquez: Historia de un deicidio[M]. Barcelona: Barral Editores, 1971: 183.
(三) 借叙述者开枝散叶
鉴于传统小说大都具有圆满的情节结构,所以总是有头有尾、循序渐进。与之相适应的叙述者则是典型的全能第三人称叙事,陈平原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对此叙事的特点进行了全面分析。在传统小说中,叙述者通常是作家的传声筒,往往可以与作家本人画上等号。
20世纪的小说家则出于形式的需要,开始拿叙事者做文章。于是,由人物担任叙事者的作品大量涌现。无论是“对话”还是“复调”,归根结底是作家退隐、人物凸显的结果,以至于罗兰·巴特宣布零度写作或作者死了。然而,即使是在新小说派那里,人物也依然是作者选择的人物,是作者的木偶。纯客观或纯自动写作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人、物的叙事者,还是多角度叙事或多人称叙事,最终传递的也还是作者的意图。一如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即内容”仍是作者的取法、审美或审丑意图使然。
巴尔加斯·略萨曾把拉美当代小说的主要结构形式分门别类为“连通式”(也即“平行式”)、“组合式”(也即“复合式”)和“套盒式”三大类;其中,又以套盒式为甚。所谓套盒式,其本质是“剧中剧”,乃是《一千零一夜》中最典型、最原始的框架结构形式。在《一千零一夜》中,叙事者之多可谓绝无仅有,除了山鲁佐德,还有许许多多的叙事者,从国王到大臣,从正人君子到贩夫走卒,无不是叙事高手;就连动物也会说话,也会讲故事,而且常常是故事套故事,叙事者引出叙事者,借以设置悬念、传递思想,达到教化和娱人之目的。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里,美是人类社会实践使对象主体化、主体对象化,是真与善的规律性统一,是自由和谐的形式;“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97.《一千零一夜》正是东方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和文化交流中积聚的艺术宝库。从形式美学的角度看,它既像一串色彩艳丽的珍珠项链,也像一座重楼叠翠的华丽宫殿。按照福柯的假说,话语就像狱卒对犯人的环形凝视。人们被话语所形塑,又反过来形塑别人。山鲁佐德先用故事说服父亲,走向死亡冒险。诚如爱娃·萨利斯(Ewen Sallis)所言,她不仅要拯救自己和其他无辜的少女,还要拯救陷入复仇魔障的国王山鲁亚尔。“山鲁佐德以非凡的叙述技艺开始了她的故事,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催眠术。它每一次都迫使被国王开启的现实痛苦之门随着黎明的到来关闭记忆、陷入沉寂。当国王从催眠状态中解脱出来,时间已经流逝”,第二夜的故事又开始了。这样,夜复一夜,日复一日,奇特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催眠”国王。三年左右时间积累了大量形象、比喻、寓言,它们恰似心理治疗中的暗示。(30)Ewen Sallis.Sheherazad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M]. London: Routledge,1999: 91-93.换言之,对故事(接下来又将如何)的渴望,以及对最终解决(最终将发生什么)的渴望,开启了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山鲁佐德以此摆脱了山鲁亚尔受辱之后报复行为的循环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山鲁佐德用各种各样的故事取代了各种各样的女孩(或妻子),从而她自己也成了集众多女性特征(尤其是优点)于一身的女人,尽管作品对她的外貌有意采取了类似于我国国画的留白方式,盖因美貌对于阻止国王的报复毫无作用: 毋庸置疑,他的王后是美丽的,三年中上千名被他选中并杀害的少女也一定是美丽的。
需要强调的是故事——文学的魅力: 它们不仅感化了人物(譬如听故事的国王),同时也感化了读者。虽然在《一千零一夜》中死亡是男人对女人的最大惩罚;反之,背叛是女人对男人的最大还击。就像《魔鬼和女郎的故事》所说的那样,男人(魔鬼)用暴力,女人(俘虏)用欺骗,但这个魔咒最终被文学所化解,而后者承载的便是真善美。至此,可以说用无数少女性命攸关这么大的悬念牵出一千零一个故事,实在不是《五卷书》和《罗摩衍那》的框架结构能比拟的。这是文学化境之美,也是审美形式不断演进的这把金钥匙“救人赎己”、屡试不爽的终极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