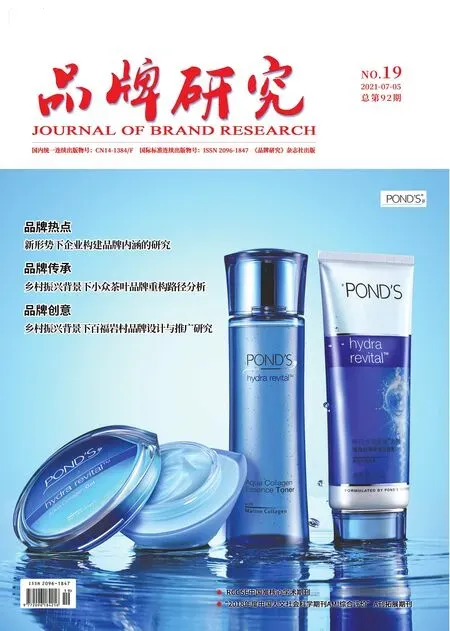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医务人员的权力保障研究
2021-11-30朱婉婉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
文/朱婉婉(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
一、医务人员紧急公权力法律定性
回顾范围广、传染性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非典、埃博拉病毒、SARS等,相关国家的行政紧急权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紧急权行使容易越过法律红线,例如,动摇对权利、秩序等元素的保障,影响对公正、自由等价值的选择,应急冲突因此就显露出来。以2020年春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不仅来势猛、危害性大,而且传播快、传染性强,医务人员第一时间冲在防控一线,他们成就战役成果的同时亦承受着防控疫情的压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务人员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执业医师法》,代表国家行使紧急医疗处置的公权力,成为患者人权保护与疫情防控任务的冲突焦点。此时,为保障防控一线,国家也应设法缓解此冲突,而法律赋予的权力无疑是最硬核、最直接的支持。
紧急状态的宣布是此处探讨的医务人员公权力的先决因素,此权力的行使正当性依赖于紧急状态宣布,因此属于广义的行政紧急权范畴。紧急权的属性是对抗的,适用时间是紧急状况,如新冠肺炎疫情,紧急权也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在时间限制上,它随着紧急状态的结束而失去作用;在体系上,紧急权力根植于紧急状态法律体系下,而紧急状态法律体系是与正常法律体系相并列;在规制和调整上,它无疑不存在超宪性和超法性之说,必须要受宪法和法律的规制,受到宪法精神和法律原则的束缚。即使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此权力的裁量亦如此。
二、医务人员紧急公权力实施缺陷
我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务人员的权力只有零星的法律规定。如在《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法律中有所提及,对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捉襟见肘。
(一)特殊干预权立法缺位、程序缺失
紧急状态下,医师的特殊干预权与常态化是截然相反的。一般而言,医师的一般权利总是迁就着病人的要求和人权,这样利于平常治疗工作的开展,而特殊干预权体现着对病人根本利益的负责,为完成对病人的义务,医师特殊干预权需要暂时限制其自主权,这也是一种为长远目标服务的权利。医疗中基于医事共同体授权的权利有强制治疗权、隔离诊疗权、强制检查权、公共卫生检查监督权、计划免疫接种权等。
特殊干预权是医师的基本权利之一,但我国尚未对该权利以明确的法律形式予以立法肯定。《民法典》中在抢救危重病人的行为中提到该权利,但这项规定更侧重于利益保护,并没有赋予权力的趋势;《执业医师法》中仅以强制义务形式出现。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均对医师的特殊干预权以强制义务的形式予以规定。但由于缺乏可行的操作细则和执行标准,在实施中并未体现其作用,临床实践中,新冠病情未知元素很多,医师面对的病情复杂多变,并且许多患者会有许多并发症,如何能在有效的时间内快速制定治疗方案,最大限度地挽救患者生命,除了有赖于法律对特殊干预权的明确,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规范。然而,我国卫生设施及资源分布不均衡,且疫情突发各地很难建立高度统一的可操作性单一程序。
(二)医疗裁量权制度上界定不明
医疗裁量权也是一种医疗特权,在医疗工作开展过程中,病患病情变化,医师相应的可调整治疗方案,从用药到治疗方法,从药疗到手术治疗,以及手术的技术和方式等内容。而在紧急状态下,这些现有的医疗裁量权范畴捉襟见肘,且模糊不清。
在现代新的医学模式下,各国立法或判例一般都倾向于将医疗裁量权的范围严格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以避免重新回归到父权主义的医学模式。所以,医师医疗裁量权往往限于对告知内容的裁量,而此范围的授权显然应付不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张状态。除此之外,对于紧急状态下医方的告知义务,法律也没针对性的规定。疫情期间,许多人的思想和个人状态是未知的,当被告知患病时,有一些人慌乱之下采取极端做法,各个城市间游走传染病毒,引发严重后果。对这种行为虽有刑法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名”予以惩戒,但造成的局面已然发生,事后惩戒起不到预防作用。此时,需要医方的自由裁量权项下的“告知”发挥机动预防作用,但现有法律规定并未对告知义务的时机进行说明,换句话说,可否在行使强制隔离后再告知以避免上述情况?
三、医务人员紧急公权力保障建议
(一)特殊干预权
1.完善特殊干预权的立法内容和实施程序
特殊干预权作为医师的基本权之一,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医师和医疗机构享有特殊干预权。新冠病毒传染快,范围广,所以在发现第一时间进行隔离,限制患者自由行动是有必要的,特殊干预权理应包括这一权利。除此之外,医务人员对隐瞒病情的患者应该依据比例原则享有特别干预权,如若只事后追究责任,为时已晚。唯有使权利有法可依,才能缓解权利与伦理、人权的冲突。完善实体法律规范不能一劳永逸,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是密不可分的,避免错误和偏私的程序规则不可或缺。
完善的特殊干预权的实施程序,有利于对特殊干预权加以判断和控制。因为建立切实可行的操作细则和程序规范是保障医师行使特殊干预权的重要手段。因此,明确权利主客体,才能使医方面对紧急情况有法可依,有权做出抢救行为。明确特殊干预权的行使范围、行使依据、对行使权力后产生结果的责任分配等要件,才能使患者对医疗机构的做法予以理解或者主动配合医方的各种符合医疗精神和伦理规范的处理。
2.建立司法监督评判小组
行使特殊干预权的依据是患者利益的最大化,医师的决定往往仅基于专业的医学考虑而未涉及伦理、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因素,特殊干预权在适用过程中必须考量各种相关因素。医师的专业判断是否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患者的利益需要被确认。同时,为了制约医师对特殊干预权的滥用,也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督、评判。所以,可以借鉴英美等国家的普遍做法,在紧急状态下建立一个第三方。它的作用为,一方面,权利冲突出现时,权衡利弊,做出科学的裁决,当然,其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应当被执行;另一方面,医师专注于医疗,而且还可以提前解决矛盾,稳定医患关系,避免纠纷扩大。它的组成人员应是多方面的专业人才,如医学、法学、心理学、伦理等,并且由法官主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法律效力。它的性质是独立于医疗机构和患者的第三方,如此,才能裁定医师行使特殊干预权的复杂情况。
(二)医疗裁量权
1.明确紧急状态下医疗裁量权范畴
对医疗裁量权界定不明,在常态下就导致医师行使该权利时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发生冲突。在紧急状态下,病理等存在未知区域,医方被赋予足够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有必要的。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大多伴有传染性强以及变异的特点,医方需要与时间赛跑,尽快研究并临床试验。因此,应当尽量减少医方的顾虑,赋予其适当的自由裁量权,常态化医患关系本就紧张,更何况积极状态下?常态下的小范围裁量权显然不够应付防控一线的医疗工作进展,因此,立法上应明确紧急状态下的医疗裁量权的界限,并适当增加权利范畴。
2.完善告知制度
告知是作为权利还是义务,是两种不同的解法。当如实告知病情会导致不利后果时,医师有自由裁量的权利好过于有不告知的义务,同时意味着,医师也可以免除告知义务。这个逻辑下,因告知而产生不利后果的就代表医师不符合违反注意义务的法定事由,亦不用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由此,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紧急状态下医师的不告知权利,注意的是不规定医师去避免产生不利后果的义务。另外,其他国家已有经验和结合本土特色的实践,可结合我国当下紧急状态下医患关系的新特点,去粗取精,增订我国现有的针对性法律,换句话说,医师有告知义务,也有不告知的权利。告知与否属于医师的自由裁量权,关于以上提到告知后会对患者造成极大打击,甚至对社会造成隐患,医师有选择告知时间的自由,即可以在采取针对性措施之后再告知,再者,即使医师未发现隐患,告知患者后导致患者病情恶化或其他不利后果,只要医师在治疗过程中遵循了相关医学职业标准,则不必为告知的后果承担责任。该立法规定既对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进行了保护,又避免了医师告知与否的两难选择,有利于紧急状态下医疗防控行为的进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生的合法、合理的特殊干预权和医疗裁量权等为防控的坚实性提供了保障,但需要提及的是这些权力依旧在行政紧急权之下,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除此之外,被赋予的权力具有机动性,必须以紧急状态的宣布和消失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