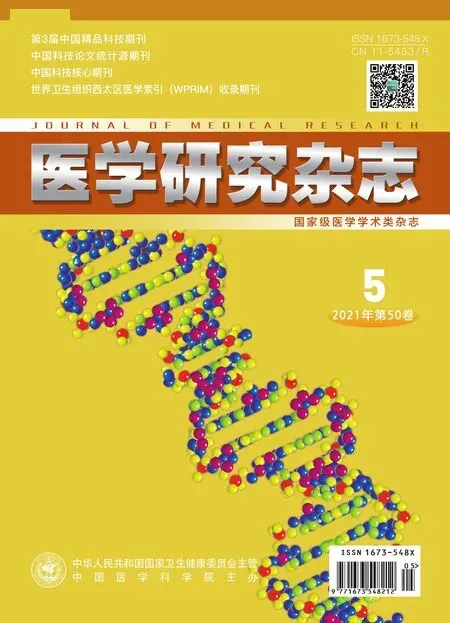抑瘤素M在炎症性肠病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2021-11-30陶美慧
陶美慧 张 颖 付 妤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是一组胃肠道非特异性慢性炎性疾病,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的腹泻、腹痛、便血,并可能并发肠道狭窄、脓肿、瘘管、癌变等,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21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IBD发生率不断升高,有研究预计2025年中国的IBD患者将达到150万例,给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带来极大挑战[1]。目前观点认为IBD发病关键可能是肠黏膜屏障破坏及免疫紊乱,然而具体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抑瘤素M(oncostatin M, OSM)属于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家族成员,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近年来研究表明OSM可参与上皮屏障功能,促进肠道炎性因子分泌和纤维化,并可以预测IBD患者对抗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治疗的应答,与IBD发生、发展关系密切。本文将综述OSM在IBD中的研究进展,以期进一步研究其在炎症性肠病中的作用及具体机制。
一、抑瘤素及其受体
1986年Zarling等[2]从佛波醇12-肉豆蔻酸盐13-乙酸酯活化的U-937淋巴瘤细胞上清液中分离纯化得到OSM,并发现其可以抑制A375黑色素瘤和其他肿瘤细胞增殖。OSM属于IL-6家族,该家族成员还包括IL-6、IL-27、IL-11、IL-31、心脏营养素-1(cardiotrophin 1, CT-1)、白血病抑制因子(leukaemia inhibitory factor, LIF)、睫状神经营养因子(ciliary neurotrophic factor, CNTF)以及心肌营养蛋白样细胞因子(cardiotrophin-like cytokine factor 1, CLCF1),其中OSM和LIF基因位点相邻,在蛋白结构、结合受体及生物学功能等方面具有相似性[3]。基因组DNA分析显示,编码人源OSM的基因位于22号染色体q12 区。人源OSM多肽经蛋白酶裂解后,产生由196个氨基酸残基构成的成熟分子,其中包含5个半胱氨酸残基,形成四螺旋束二级结构,并且半胱氨酸残基之间构成两个二硫键[4]。肠道组织中,OSM主要由包括CD4+T淋巴细胞和抗原递呈细胞在内的造血细胞表达[5]。
作为IL-6家族成员,OSM以低亲和力结合家族共有受体亚基gp130的同时,必须与第二受体LIFRα或OSMRβ结合才能发挥生物学活性。其受体包括两种类型:Ⅰ型受体为gp130/LIFRα复合物,可以结合OSM和LIF;Ⅱ型受体为gp130/OSMRβ复合物,是OSM特异性受体[3]。研究表明,在人类肠道黏膜组织中,OSMR主要表达于基质细胞,而上皮细胞、造血细胞、内皮细胞的表达较少甚至无表达。IBD患者中OSMR增多主要是由于表达OSMR的肠道基质细胞累积,而非单个基质细胞上OSMR表达量增多[5]。
二、抑瘤素的作用机制及生物学功能
OSM通过OSMR活化细胞内信号分子来发挥生物学功能。受体激活的第一步是OSM配体结合gp130受体亚基,使得gp130和OSMRβ受体亚基同源或异源二聚体化,进而相互磷酸化,活化结合于受体胞质区的Janus激酶,从而磷酸化酪氨酸残基,最后选择性激活下游多种信号转导通路,包括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子(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STAT)、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磷脂酰肌醇-3-激酶/丝苏氨酸蛋白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serine-threonine kinase, PI3K/AKT)等,启动细胞内的信号级联反应,调节基因表达,介导相应效应[3,4]。目前的研究表明,OSM是一种具有多效性的细胞因子,通过在不同的组织和细胞中激活相应信号转导通路,参与免疫和炎性反应、造血、骨代谢、纤维化以及细胞增殖分化等多种生物学功能。
有研究报道在细菌性肺炎中,OSM特异性作用于肺泡上皮细胞,激活转录因子STAT3,诱导趋化因子CXCL5产生,募集中性粒细胞,参与固有免疫反应[6]。另有研究显示在慢性自身免疫性荨麻疹中,OSM-OSMR通过JAK/STAT通路介导自身免疫反应,促进IL-1、IL-6和IFN-γ等炎性因子产生[7]。此外,OSM可磷酸化MAPK信号通路,诱导肌成纤维细胞分泌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1,促进肝脏纤维化[8]。总之,OSM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参与机体重要的生理过程及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目前越来越多研究关注OSM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性疾病中的作用。
三、抑瘤素与炎症性肠病
近年来研究显示,OSM与IBD关系密切。Jostins等[9]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和Meta分析发现,22号染色体上OSM的单核苷酸多态性(rs2412970)与IBD易感性相关。OSM在急慢性结肠炎小鼠模型的炎性结肠组织中表达显著增加,且在血清和粪便中也发现表达上调[10,11]。此外,在IBD患者的血清和炎性肠道黏膜中OSM蛋白表达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12]。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OSM在多个方面参与IBD的发生、发展,并且对选择IBD的治疗方案以及探究新的治疗靶点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OSM与肠黏膜屏障:肠黏膜屏障功能破坏是IBD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肠黏膜屏障包括机械屏障、化学屏障、免疫屏障及生物屏障,其中机械屏障由完整的肠上皮细胞和细胞间连接构成,occludin、claudin-1、ZO-1、cadherin及连接黏附分子等紧密连接蛋白对维持屏障功能的完整性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表明OSM对上皮屏障功能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Pothoven 等[13]使用重组人OSM刺激呼吸道上皮细胞后,上皮跨膜电阻下降,异硫氰酸荧光素葡聚糖4(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 dextran 4, FITC-dextran)水平升高,紧密连接结构破坏,并在体内研究发现OSM水平与上皮渗漏标志物α2-巨球蛋白的表达呈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说明OSM可诱导上皮屏障功能障碍。另外,OSM可通过介导上皮-间充质细胞转化,使上皮细胞获得某些间充质细胞的特性,进而上皮细胞极性、细胞间紧密连接和黏附连接丧失,导致上皮屏障功能受损[14]。
遗传关联研究指出,IBD易感基因OSMR与肠道上皮屏障功能和修复有关[15]。细胞和动物实验都发现OSM可以影响肠黏膜屏障功能。有研究显示OSM以浓度依赖的方式下调Caco-2细胞紧密连接蛋白ZO-1、occludin和claudin-1的表达,诱导肠道屏障功能障碍[10]。除此之外,Li等[11]使用可以干预OSM途径的小檗碱处理慢性结肠炎小鼠,结果显示血清中FITC-dextran下降,ZO-1、E-cadherin和occludin等紧密连接蛋白升高,肠黏膜屏障功能改善。这些发现表明OSM通过破坏肠黏膜屏障,使肠道直接暴露于外界有害物质和病原体,最终导致不受控制的肠道炎性反应。但也有研究发现OSM通过STAT3依赖的途径,促进肠上皮细胞增殖,并抑制其凋亡,调节肠道屏障功能紊乱[16]。
2.OSM的促炎作用:IL-6可上调促炎性细胞因子产生,并抑制T细胞凋亡,是介导慢性肠道炎症的重要介质之一。OSM属于IL-6家族,该家族成员的受体大多含有亚基gp130糖蛋白,因此在生物学活性上有相似作用。研究证实在肠道基质细胞中,OSM与OSMR结合后驱动下游通路,促进IL-6、细胞间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 ICAM 1)、趋化因子等多种促炎性分子产生,增加肠道炎症活动度,并且OSM和OSMR的表达水平与IBD患者组织病理学严重程度密切相关[5]。此外,Vossenkamper等[12]使用抗OSM抗体处理IBD患者肠道外植体,发现IL-1β、IL-6和TNF-α等促炎性细胞因子减少。尽管部分研究表明,OSM是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细胞因子,作用形式很大程度依赖于其细胞来源、靶细胞类型及周围的免疫微环境。但目前在IBD中研究证据显示OSM主要发挥促炎的作用,通过上调趋化因子、黏附分子及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促进肠道炎症,阻断OSM对这一效应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3.OSM与肠道纤维化:IBD患者肠道纤维化是长期炎性反应和异常损伤修复导致过度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 ECM)沉积的结果。OSM可以调节基质金属蛋白酶与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的平衡,影响ECM沉积,并且可以诱导的上皮-间充质细胞转化,在多种器官中具有促纤维化的作用。研究显示在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的肺泡灌洗液中,OSM蛋白水平显著上调。研究者进一步通过动物实验发现经鼻腔给予小鼠重组鼠OSM后,出现剂量依赖性的胶原沉积,提示OSM在肺纤维化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17]。另外,OSM可通过刺激肝巨噬细胞,上调转化生长因子β1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促进肝星状细胞Ⅰ型胶原分泌,参与肝脏纤维化形成[18]。
研究表明,OSM对肠道慢性炎症纤维化也发挥重要作用。Haberman等[19]在儿童CD患者中发现,OSM炎症基因与ECM/胶原炎症基因标志紧密相关,这与将来肠道狭窄的发生有关。研究证实OSMR主要表达于肠道基质细胞,并且OSMR的表达与成纤维细胞产物Ⅰ型胶原α1链(collagen type 1 alpha 1 chain, COL1A1)、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α(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α, FAP)、平足蛋白(podoplanin, PDPN)及ICAM 1呈显著正相关,其中COL1A1是ECM的主要成分,FAP和PDPN表达于成纤维细胞表面,ICAM 1是伴肠道狭窄的CD患者成纤维细胞上表达增高的黏附因子,提示OSMR可能参与ECM沉积、成纤维细胞激活及聚集[5]。此外,Li等[11]提出小檗碱可能通过抑制OSM通路,减少胶原沉积,下调FAP、PDPN和α平滑肌肌动蛋白的表达,从而减轻葡聚糖硫酸钠诱导的慢性结肠炎肠道纤维化。这些证据表明OSM可促进IBD患者肠道纤维化,进而引起肠腔狭窄、肠梗阻等并发症,但是目前具体机制研究较少,进一步研究OSM在IBD中的促纤维化作用,以期寻找治疗肠道纤维化狭窄的新靶点。
4.抗TNF疗效预测:目前,抗TNF是对IBD患者治疗有效的一线生物制剂,但高达40%的患者对抗TNF治疗耐药,迫切需要可以预测抗TNF疗效的生物学标志物,以期在治疗前识别疗效不佳的患者,实现个体化治疗。West等[5]提出治疗前肠道黏膜高水平的OSM与IBD患者对抗TNF治疗应答下降密切相关,OSM可作为抗TNF疗效的预测标志物,其预测患者对英夫利昔单抗不良初始应答的ROC曲线下面积达0.99,敏感度和特异性分别为100%和91.7%。中国IBD患者,OSM和OSMR在炎症和溃疡部位的结肠组织中高表达,且其表达水平与抗TNF 治疗耐药有关[20]。然而肠道黏膜OSM水平检测是侵入性的检查,在临床运用上有所局限。另有研究发现血清OSM水平也能有效预测抗TNF疗效[21,22]。Bertani等[21]通过对接受英夫利昔单抗单药治疗的CD患者进行疗效预测标志物研究,发现第54周黏膜愈合患者的基线血清OSM基本为0,而黏膜不愈合患者的血清OSM水平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且当基线血清OSM水平临界点取14pg/ml时,预测黏膜愈合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1,敏感度和特异性分别为96%和89%,与肠道黏膜OSM水平预测效果相差不大。OSM除了可以预测抗TNF治疗疗效,对于IBD其他生物治疗也有一定的预测价值。Zhou等[23]在TURANDOT临床试验中发现UC患者外周血和肠道炎性组织中OSM mRNA表达、以及血清中OSM浓度与抗MAdCAM-1单克隆抗体(PF-00547659)治疗疗效相关,提示OSM是预测PF-00547659临床疗效的生物学标志物。总之,血清OSM是一种非侵入性、价廉、可靠的评价IBD生物治疗疗效的生物学标志物。患者血清OSM水平有助于评估生物制剂的选择及优化,以利于实现个体化治疗,提高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降低医疗保健负担。
此外,OSM可能成为IBD治疗新靶点。West等[5]使用Fc标记的可溶性OSMR-gp130融合蛋白处理Hh+α-IL-10R模型小鼠,有效中和OSM,同时OSM相关的炎性因子减少,对抗TNF治疗耐药的小鼠结肠炎严重程度减轻。Bordon[24]提出对于抗TNF治疗耐药的IBD患者,靶向OSM-OSMR途径可能是潜在有效的治疗策略。Du等[25]探究OSM-OSMR相互作用位点和三维结构以及OSM-OSMR药物干预位点,发现包含两个“热点”残基Phe160和Tyr214的3个药物结合靶点,为设计阻断OSM-OSMR相互作用的小分子抑制剂提供思路,以提供更安全有效的靶向治疗。因此,OSM可能是IBD新的治疗靶点,但是目前的证据较少,期待进一步开展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以证实其疗效。
四、展 望
综上所述,OSM作为IL-6家族中的一员,通过影响肠黏膜屏障功能,促进炎性反应和肠道纤维化,参与IBD肠道炎症的发生、发展。此外,OSM可以作为预测IBD患者抗TNF治疗疗效的生物学标志物,有利于实现患者的个体化治疗。但目前有关OSM在IBD中作用的研究尚不足,OSM对肠道屏障的影响存在争议,并且对其具体分子机制的研究不够深入,有待于进一步探讨IBD中OSM的信号转导通路及OSM与抗TNF治疗相互联系的网络。抗OSM治疗可能开拓新的生物制剂,为目前40%对抗TNF治疗耐药的患者提供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