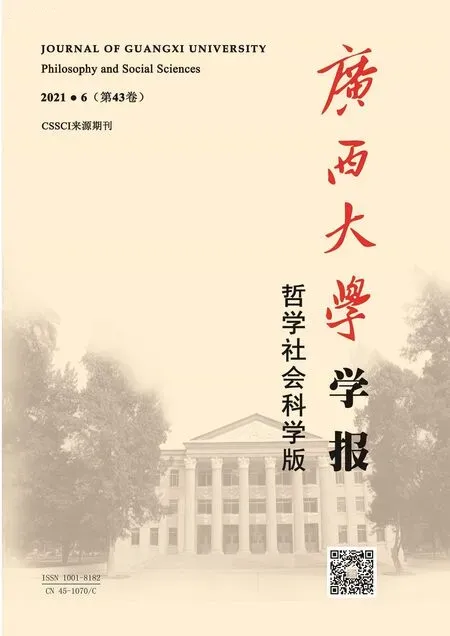邵雍诗歌中的哲学意蕴探析
——以《击壤集》为中心
2021-11-30尚荣
尚 荣
邵雍是“北宋五子”之一,也是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与其他理学名家相比,邵雍的思想在今日学界所受到的关注是相对较少的。这主要是因为邵雍之思想以易理为根基,故一方面有其晦涩难懂之处,另一方面则与理学主流略显隔阂。但有趣的是,邵雍的理学诗则非常浅白——不仅与其他诗词相比之下显得浅白,与其他理学名家的诗词相比也是如此。本文拟从邵雍诗歌集《击壤集》入手,探寻邵雍诗歌中所反映的哲学意蕴,以此从一个别样的视角理解邵雍的哲学思想。
一、理学诗与《击壤集》
所谓理学诗,从大的角度而言,即以理论入诗。当然,一切诗歌之中,都有理论的反映,但不能将一切诗歌称为理学诗。就中国诗歌之历史发展而言,可以在广义上称之为理学诗的,有魏晋玄言诗、两宋理学诗以及历代禅诗。可以看出,这些诗歌流派的共有特色有三:第一,这些诗歌所阐发的理论是形而上化的。第二,这些诗歌的产生是与其时思想界的主流哲学思想保持一致的。第三,这些诗歌与主流诗歌是存在隔阂的。当然,不能否认有少量理学诗在文学的评判标准下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但这毕竟是凤毛麟角。狭义上的理学诗,则单指两宋理学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儒学、尤其是两宋理学思想为论述核心的诗。
对于理学诗,古人与今人的评价都不甚高,多有批判之语。刘克庄《跋恕斋诗存稿》言:“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1]并不把理学诗看作诗。袁桷《乐侍郎涛集序》云:“至理学兴而诗始废,大率皆以模写宛曲为非道。夫明于理者,犹足以发先王之底蕴。其不明理,则错冗猥俚,散焉不能以成章,而诿曰吾唯理是言,诗实病焉。”[2]甚至认为理学诗对中国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钱锺书也说:“此乃南宋之天行时气病也。”[3]虽然这是玩笑话,但也能够看出钱锺书对理学诗的负面观感。但是,并不是所有诗评家都秉持着这样的态度。唐顺之就这样评价邵雍的理学诗:
近来有一僻见,以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者。然文莫如南丰,则兄知之矣,诗莫如康节,则虽兄亦且大笑。此非迂头巾论道之说,盖以为诗思精妙,语奇格高,诚未见有如康节者。知康节诗者莫如白沙翁,其言曰:“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后来操翰者,二妙罕能兼。”此犹是二影子之见。康节以锻炼入平淡,亦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者矣,何待兼子美而后为工哉!古今诗庶几康节者,独寒山、静节二老翁耳,亦未见如康节之工也[4]。
这番论述中,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唐顺之是知道自己的观点并非主流的,所以会自称“僻见”,又有“虽兄亦且大笑”之语。其次,唐顺之对邵雍诗作的极大推崇,并不是站在理学层面,而是站在诗歌层面的,故称“此非迂头巾论道之说”。最后,唐顺之认为邵雍的诗歌成就在杜甫之上,尤其是在“工”的层面上。这样的观点确实令一般人难以接受,但唐顺之有其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在唐顺之看来,杜甫的工整是“后天之工”,也就是说是通过文学技巧达成的。而邵雍的工整则是“先天之工”,是“以锻炼入平淡”,亦即本然而发者。这里的“锻炼”,其指向不在于诗歌,而在于诗人本身;是诗人本身的境界,成就了诗歌自然而然的工整。
理学家之诗,往往以境界为先,绝不炼字,于文辞雕琢、隐喻、通感等技巧方面非但不愿为之,乃至不屑为之。今人有时会觉得理学诗“纯粹说理,苦涩难懂”[5],这话固然没错,但这是以大多数今人的知识构成来判断理学诗的理解难度。事实上,对于一生研读四书五经的古代文人而言,理学诗在理解上绝对谈不上困难,甚至可以说是过于浅易直白了。比如邵雍有一首《生男吟》,其诗云:“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我,寿夭贤愚系于汝。我若寿命七十岁,眼前见汝二十五。我欲愿汝成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6]188诗中的“鞠育教诲”“寿夭贤愚”可能对今人而言略显晦涩,但在古人的眼中,这首诗的浅白程度恐怕胜过大多数的打油诗。那么,像这类看似游戏之作,朴实若俗语、直白如口号的诗歌中,唐顺之所言的“工整”究竟体现在何处呢?这就涉及对理学诗的核心理解问题。
理学诗的核心并不是以理学入诗,也就是说,不能将理学诗理解为理学与诗的合并。事实上,理学诗应当被纯粹理解为理学——不仅是理学的一种表达形式,而且是理学本身。当将“诗”重新以理学定义之后,这里的“诗”与我们日常经验中的“诗”是截然不同的,在审美取向与精神内核上都是如此。但想论述清晰这一点,还要从理学本身谈起。
所谓理学,又称性理之学,又称天理之学,又称道学。其名虽异,其实一也。理学思潮的形成,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对其时佛老思想大兴的反动。从思想内容来看,是将佛教本体论的思维模式纳入儒学之中,以此重新解读先秦儒学,依靠儒家经典构建一个可以与佛老相抗的形而上体系,并且依靠这一体系来解释世间万物的存在与流行演化。因此,从理学本位而言,理学显然不单纯是一种哲学思潮,而且是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是道德的存在模式,是人生的运行范式。总而言之,理学是包含容摄一切的,诗歌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对于不同的理学家而言,其理学观点——或者说他们最以之为本位的先秦儒学经典——是有差异的。对于邵雍而言,他的理学框架之构建,所围绕的根本文献是《易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邵雍理学诗的独有特色。
邵雍的理学诗集名为《击壤集》,其中收录了邵雍一生所作的3000 余首诗。所谓击壤,是一种投掷游戏,即用手中之物投掷而击远处之物,击中为胜。投掷之物,后期以石竹之属为多,早期应是土块,故名之为击壤。但邵雍这里所用的是击壤的典故:
壤父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7]
帝何德与我哉,所体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正是《易经》性的。天地万物,自有规律,运转不息,而个体所能做的,便是合乎天道,令自己的行为契合于其中。“何人不饮酒,何人不读书。奈何天地间,自在独尧夫。”[6]356这种安然自得的状态,与在这种状态背后对世界的理解模式,是邵雍《击壤集》的理念背景。
二、皇极经世:邵雍理学诗中的世界理解
邵雍一生所留下的作品不少,但最能代表其思想体系的,毫无疑问是《皇极经世书》。“皇极”一词,最早见于《尚书· 洪范》,孔颖达疏:“皇,大也;极,中也。”皇极经世,即大中治世也。邵雍这部大部头的作品试图以易数推究阐释世界万物之起源演化、人类历史之动荡变迁。简而言之,即以易理推演一切。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从中也能看出邵雍对自身哲学体系的自信。邵雍言:
《皇极经世书》凡十二卷。其一至二则总元会运世之数。易所谓天地之数也。三之四以会经运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帝尧至于五代历年表。以见天下离合治乱之迹。以天时而验人事者也。五之六以运经世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自帝尧至于五代书传所载。兴废治乱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验天时者也。自七之十则以阴阳刚柔之数。穷律吕声音之数。以律吕声音之数。穷动植飞走之数。易所谓万物之数也。其十一之十二则论皇极经世之所以为书。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焉。[8]
可以看到,在邵雍的描绘中,《皇极经世书》的结构是由总而分,层层推衍。这样的结构,事实上也就是《易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模式。邵雍在此处所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万事万物之存在发生有其合理而必然的根源,而且是可以推而知之的,即“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这样的世界理解方式,在邵雍的诗歌中比比可见。其中最明显的,是邵雍为《皇极经世书》所写的《安乐窝中一部书》:
安乐窝中一部书,号云皇极意何如。春秋礼乐能遗则,父子君臣可废乎。浩浩羲轩开辟后,巍巍尧舜协和初。炎炎汤武干戈外,恟恟桓文弓剑余。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铺舒。几千百主出规制,数亿万年成楷模。治久便忧强跋扈,患深仍念恶驱除。才堪命世有时有,智可济时无世无。既往尽归闲指点,未来须俟别支梧。不知造化谁为主,生得许多奇丈夫。[6]318
安乐窝,是邵雍为自己居住之所所取的名号。其中所藏的一部书,正是集其思想之大成的《皇极经世书》。由诗歌内容可以看到,邵雍提举极高,包容极广,有以寥寥数句总括历史、点拨宇宙之意。这样的气度,如果不是有其背后的易理世界作为思想基础,是难以表现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邵雍诗歌的这种宏大气势,与其他诗人的气势是有所差异的。其最根本的不同,在于邵雍的诗歌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宿命感。因此这种气势给读者带来的感情并不是振奋或者激动,而更多的是一种“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掌控感。在邵雍的所有诗歌中,都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味道。其《秋怀三十六首》之三云:
明月生海心,凉风起天末。物象自呈露,襟怀骤披豁。悟尽周孔权,解开仁义结。礼法本防奸,岂为吾曹设。[6]218
其《书事吟》云:
天地有常理,日月无遁形。饱食高眠外,率是皆虚名。虽乏伊吕才,不失尧舜氓。何须身作相,然后为太平。[6]229
天地、日月、山海、风雨,这些宏大的意象在邵雍手中,有一种信手拈来的味道。邵雍与其他诗人不同,他并不为这些天地伟力而震撼,当然也并没有轻视之意,而是以中性冷静的笔触,描写着世间一切。邵雍对“天地”一类宏大意象的书写,核心是对天地规律的透彻认知,所以“天地有常理,日月有常明。四时有常序,鬼神有常灵”[6]476。这样的世界理解构成了邵雍诗歌中独有的哲学特色。
三、以物观物:邵雍理学诗中的处世哲学
在《皇极经世书》中,最能代表邵雍哲学思想精华的是《观物内篇》与《观物外篇》。所谓“观物”,即对物质世界——或者说是对“非我”——的认知与理解方式。当然,这种理解的最终目的不是理解本身,而是通过理解来安顿自身。邵雍这样阐释“观物”:
天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虽圣人无以过之也,而过之者非所以谓之圣人也。夫鉴之所以能为明者,谓其能不隐万物之形也。虽然,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又未若圣人之能一万物之情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6]49
虽然邵雍言“又安有我于其间哉”,但这并不是对自我的消弭。邵雍在这里所排除的“我”,不是主体与存在意义上的“我”,而是有所喜好、有所偏私的小我。而如果达到了圣人的境界,能够“反观”而“一万物之情”,就会合天地与我为一,达成生命境界与精神体验的内在超越:“奇花万状皆输眼,明月一轮长入怀。似此光阴岂虚过,也知快活作人来。”[6]274“风花雪月千金子,水竹云山万户侯。欲俟河清人寿几,两眉能着几多愁。”[6]301在邵雍的诗歌里,自然万物是自在的,但同样也是为我所用的,但此“用”,是各安其位而互不相伤的。“是知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然犹未离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6]180便是此意。
“以物观物”的处世哲学,是邵雍对待万物的态度,也是其对待诗歌的态度。《毛诗》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9]邵雍对此点评道:
是知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发其志则谓之言,扬其情则谓之声,言成章则谓之诗,声成文则谓之音。然后闻其诗,听其音,则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谓身也、时也。谓身则一身之休戚也,谓时则一时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则不过贫富贵贱而已,一时之否泰则在夫兴废治乱者焉。是以仲尼删诗,十去其九。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盖垂训之道,善恶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泆。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6]179
邵雍认为近世诗人的诗歌“溺于情好”,也就是偏重于小我之私情,而未能观物之本然。但是邵雍自己的诗歌,也同样有着个人情感的抒发,那这与他所批判的“溺于情好”有何不同呢?如果单独看邵雍的某篇诗歌,这个问题怕是不易回答,但如果将邵雍的诗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答案就跃然而出了。与普通诗人相比,邵雍没有将抒发个人情感作为第一要务,而是在“以物观物”的理念指导下“以诗观诗”。邵雍有《首尾吟》一百三十四首。所谓“首尾吟”,即首句与尾句同为一句,更为有趣的是,邵雍的这一百三十四首诗,首尾竟然都是同一句“尧夫非是爱吟诗”[6]517。如此强调自己不爱吟诗,却写了一百三十四首之多,这看上去多少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如果仔细一一读来就会发现,在邵雍这里,诗的定义已经非常模糊,范围已经非常宽广了。在这组诗作中,以“诗是”开头的诗句有一百二十七句,以相当全面的角度解释了邵雍会在什么状况下写诗。其中有时间上的限定:“十月时”“春尽时”“秋尽时”;有情绪上的限定:“无奈时”“乐事时”“得意时”。事实上这所表达的是,时时皆可写诗,一切皆可为诗,作为表达主体的邵雍对诗并没有偏私之情,而是主体安处大化之中自然显发的结果。
四、观化一巡:邵雍理学诗中的生死态度
熙宁十年(1077),邵雍的生命进入弥留之际,友人与亲属纷纷前来探望。此时的邵雍,在生死面前表现出了非常超脱的态度。在司马光前来问疾时,邵雍以“观化一巡”表达了自己对生死的看法:
熙宁十年夏,康节先生感微疾,气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谓司马温公曰:“某欲观化一巡,如何?”温公曰:“先生未应至此。”康节先生曰:“死生常事耳。”[10]221
生死问题是人类关心的终极问题之一,对于生死问题的解决,儒家一向是讳莫如深的。这与佛道二家大相径庭。道家言尸解升仙,佛教言寂静涅槃,都对死亡问题给出了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但自孔子以来,儒家一向“未知生焉知死”,将生死问题置而不论。这也导致在宋明理学家处,虽然普遍具有解决生死问题的自信与实践,但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以及解决方式大有差异。所以对于邵雍的生死观,同为北宋五子的张载与二程都大不以为然。张载与程颐去问病时,也发生了一番对话:
张横渠先生喜论命,来问疾,因曰:“先生论命,来当推之。”康节先公曰:“若天命则知之,世俗所谓命则不知也。”横渠曰:“先生知天命矣,某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它人无以为力,愿自主张。”康节先公曰:“平生学道,岂不知此?然亦无可主张。”[10]221
因邵雍病重,张载并没有针锋相对地激烈论辩,只是以一句淡淡的“某尚何言”表达了自己不赞同邵雍看法的态度。程颐也同样在略提一句后便闭口不言。但在私下里,二程与张载对邵雍的生死态度是颇有微词的。
伯淳(程颢)言:“邵尧夫病革,且言‘试与观化’一遭。”子厚(张载)言:“观化他人便观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观得化?尝观尧夫诗意,才做得识道理,却于儒术未见所得。”[11]
张载这里对邵雍生死观的点评有两个关键词,一是“道理”,二是“儒术”。在张载看来,“观化”的理论是没问题的,但只有以主体为根基,观察客体之演化,这“道理”才是成立的。但在生死之际,要立得住的是主体,主体不能“观化”主体,所以邵雍认为张载的“观化”之说在生死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张载所说的“儒术”,即生死面前对主体的主动性把握。从本质而言,张载与邵雍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差异是,邵雍在“物我一体”的程度上比张载——也可以说比其他所有理学家都更为彻底。
在“未知生焉知死”上,邵雍的观点与其他理学家没有差异。“先能了尽世间事,然后方言出世间。”[6]407“日月无异明,昼夜有异体。人鬼无异情,生死有异理。既未能知生,又焉能知死。既未能事人,又焉能事鬼。”[6]423但在世界观与生死观的结合上,邵雍则与其他理学家大为不同。邵雍《逍遥吟》云:“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向其间一事,须是自诚明。”[6]279而《人物吟》又云:“人盛必有衰,物生须有死。既见身前人,乃知身后事。身前人能兴,身后事岂废。兴废先言人,然后语天地。”[6]477前者先言“天地”,后谈“死生”。后者却先言“人事”,后谈“天地”。这观点看上去是截然相反的,但事实上在邵雍这里,天地与生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只要通晓了其中一件,另一件也便豁然贯通了。正因此,邵雍才能用“观化”来解决生死问题,因为他相信 “人生固有命,物生固有定”[6]357,所以“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听于天,有何不可”[6]513。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邵雍作《病亟吟》云:“病亟吟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6]514体现了对践行自己哲学理论的极大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