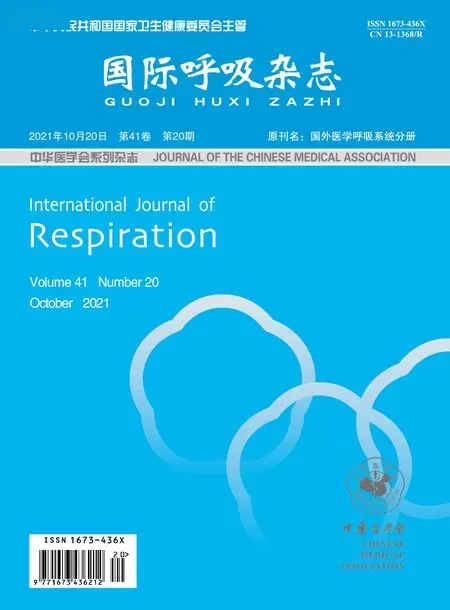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在肺癌免疫抑制中的研究进展
2021-11-30朱慧琦应可净
朱慧琦 应可净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呼吸内科 国家呼吸疾病区域医疗中心310016
在肺癌发展和侵袭的早期,细胞外基质激活,激活的基质中含有被激活的成纤维细胞[1],这种激活状态的成纤维细胞即为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 (tumor-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s)。CAFs是一种呈大纺锤形的间充质细胞,具有平滑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共同特征。根据细胞的形态和功能将CAFs分为前体CAFs和激活态CAFs,目前已知CAFs的前体包括正常组织成纤维细胞、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造血干细胞和周细胞[2]等,但多数CAFs前体细胞对肿瘤的免疫抑制影响甚微。激活前体CAFs的因素包括多种细胞因子和胞间相互作用等,其中以损伤上皮和免疫反应中单核细胞释放的活性因子最常见[3-4]。
在多数炎症反应中,成纤维细胞可以被损伤组织释放的炎症因子激活[3-4],参与促进邻近细胞增殖[5]和损伤后免疫反应。正常情况下,当修复过程中损伤引起的刺激逐渐减弱,成纤维细胞的激活也能及时停止。但在肺纤维化和肺肿瘤中,成纤维细胞过度激活,引起了微环境中一系列免疫调节反应紊乱失衡和损伤部位组织过度纤维化[6]。失去正常调节的免疫反应和组织纤维化又能不断刺激激活CAFs,使得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调节不断朝着促肿瘤的方向转变。
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中的基质细胞类型在遗传上相对稳定,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如果将基质细胞作为肺癌治疗靶点有望降低耐药性和肿瘤复发的风险[7]。尼达尼布 (Nintedanib)作为一种最初用于癌症开发的酪氨酸激酶受体抑制剂,近几年也被批准用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这也提示成纤维细胞和肺癌发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8]。在本篇综述中,将总结肿瘤微环境、特别对于肺癌肿瘤微中的CAFs与TME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1 肺癌TME与CAFs的激活
静息状态的成纤维细胞在损伤的上皮细胞和单核细胞等释放的肿瘤生长因子β(tumor growth factor-beta,TGFβ)、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MCP-1)、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和蛋白酶等因子[3-4]的作用下发生激活。除此之外,成纤维细胞也能通过细胞间直接通讯[9]、活性氧、补体因子C1或改变细胞外基质成分激活[10]。
TGF-β在富含CAFs的肿瘤中不仅对免疫抑制状态下游的诱导者起关键作用,也是CAFs功能的上游调节因子。肺癌患者肺上皮细胞表达突变型肺表面活性蛋白A2(surfactant protein-A2,SP-A2)能够增加细胞内质网应激的错误折叠蛋白,未折叠蛋白应答的激活是最大限度分泌TGF-β1所必需的[11]。作为TGF-β的亚型,TGF-β1和TGF-β2在CAFs中均上调,TME的CAFs可以激活Smad2/3通路以自分泌方式形成TGF-β正反馈环[12]。
TME 中表达的免疫调节性多糖蛋白半乳糖凝集素-1(Galectin-1)不仅可以调节CAFs 的活化,也可以控制MCP-1的表达。MCP-1可以通过参与化学趋化因子受体2(C-C chemokine receptor,CCR2)阳性免疫细胞 [如单核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 (dendritic cells,DC)和T细胞]的募集介导乳腺癌的肺转移[13],也能不断激活CAFs参与肿瘤相关免疫抑制反应。
肿瘤诱导的骨软化 (tumor-induced osteomalacia,TiO)是一种罕见的副肿瘤综合征,临床上常导致磷酸盐损耗和骨折,主要致病因素中就包含由非恶性间充质肿瘤异位产生的FGF-23。肿瘤局部产生的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是FGF-23的直接转录激活剂,TiO 中HIF-1α活性上调是导致FGF-23产生异常的原因之一[14]。全身和局部产生的FGF-23不仅可以促进CAFs的激活,还能够通过与髓系细胞 (包括巨噬细胞和多形核白细胞)的直接相互作用来调节免疫功能,从而损害免疫细胞功能[15]。
吸烟是肺癌特别是肺鳞状细胞癌的高危因素,香烟烟雾中各种有害成分不仅会直接损伤气道上皮细胞,激活气道一系列的炎症反应,也会导致损伤局部缺氧微环境的形成。缺氧3~6 d可促进细胞的G1/S期转变来介导正常人肺成纤维细胞增殖,这个调控过程主要通过激活HIF-2依赖的NFAT 信号实现的[16];增殖的成纤维细胞介导的局部纤维化则进一步激活微环境中的缺氧相关信号通路,形成恶性循环。
2 CAFs与抗肿瘤免疫
2.1 CAFs与髓源性抑制细胞募集活化 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主要是指粒细胞、巨噬细胞、DC等免疫细胞的前体构成的一大类细胞,这些前体缺乏成熟T 细胞、B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s,NK)以及巨噬细胞的膜标志物,能够显著抑制免疫细胞相关免疫反应[17]。CAFs不仅能通过调节IL-6/STAT3 通路促进其他细胞类型向MDSCs转变分化,还可以通过分泌趋化因子12 (C-X-C motif chemokine 12,CXCL12)将肥大细胞招募至TME[18],后者进一步动员MDSCs向肿瘤浸润[19-20]。
2.2 CAFs与非特异性抗肿瘤免疫
2.2.1 CAFs与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募集 活化肿瘤发生初期,机体出现外来致癌因子或者自身异常激活的肿瘤细胞,体内的巨噬细胞能够吞噬提呈相关抗原,活化多种免疫细胞,产生肿瘤相关免疫反应。TME 中CAFs能通过分泌的趋化因子、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IL 来促进单核细胞向TME募集并分化为M2免疫抑制表型[21-23]。M2巨噬细胞在肿瘤进展中起重要作用,它不仅促进组织修复和血管生成,还能产生多种免疫抑制因子如IL-10、精氨酸酶、吲哚胺-2,3-双加氧酶 (indoleamine-2,3-dioxygenase,IDO)和TGF-β,抑制TME中细胞毒性CD8+T 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24]。
2.2.2 CAFs抑制自然杀伤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 在人体固有免疫中,NK 细胞可以通过自身的细胞毒性、分泌细胞因子和促进抗原呈递细胞成熟等参与早期免疫。2013年一项CAFs与NK 细胞的共培养实验结果提示,前者能够直接抑制NK 受体、穿孔素和颗粒酶B的表达[25],随后Inoue等[26]的研究进一步揭示CAFs可以通过下调细胞表面的NK 细胞激活受体表达来抑制NK 细胞的杀伤活性。此外,CAFs参与分泌的TGF-β不仅可以降低NK 细胞活化和细胞毒性活动[27],还能通过减少NK 细胞分泌的干扰素γ (interferon-γ,IFN-γ)来影响CD4+Th1 细胞对肿瘤的清除。
2.2.3 CAFs抑制DC 对抗原的有效提呈 免疫应答中激活的成熟DC可以有效激活抗原特异性T 细胞,启动肿瘤特异性细胞毒作用。在CAFs衍生的TGF-β的作用下,DC可以下调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Ⅱ,MHC Ⅱ)分子和共刺激分子CD40、CD80、CD86 m RNA 的表达,继而影响抗原的有效提呈[28]。有研究对肺癌手术标本进行免疫组织化学分析发现,癌旁成纤维细胞中色氨酸2,3-双加氧酶(tryptophan 2,3-dioxygenase,TDO2)表达增加,给予TDO2抑制剂可显著改善小鼠的DC 功能和T 细胞应答,并减少肿瘤转移[29]。
2.2.4 CAFs与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 TME 中,巨噬细胞活化产生一系列趋化和促炎因子,可以吸引中性粒细胞聚集、黏附,吞噬杀伤肿瘤坏死因子和细胞。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 (tumor-associated neutrophils,TANs)是一种TME中存在的肿瘤源性中性粒细胞,与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类似,TANs也有2种表型,即亲肿瘤N2型和抗肿瘤N1型,目前CAFs对TANs的募集和TANs表型的极化等影响尚不明确[24]。但是,TANs与CAFs共培养的实验中,TANs 能够表达更多的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以STAT3-PDL1途径损害免疫T 细胞在肿瘤中的作用[30]。
2.3 CAFs与特异性抗肿瘤免疫
2.3.1 CAFs促进调节性T 细胞的免疫抑制作用 调节性T 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在抑制人体免疫反应和维持免疫耐受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有研究结果提示主要存在于肺腺癌肿瘤间质中的Tregs与CAFs关系密切。在高Treg密度基质来源的CAFs中,TGF-β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均显著上调[31]。CAFs和Tregs可以通过TGF-β介导的环状调节方式同时增加CAFs和Tregs的活性。临床上表达叉头转录因子箱 (forkhead box P3,FOXP3)的Tregs与CAFs共存确实与肺腺癌的不良预后相关[31]。肿瘤区域调节性DC自身高表达的IDO 不仅可直接抑制抗肿瘤免疫反应[32-33],也可以通过诱导Treg增殖参与肿瘤细胞的免疫耐受和抑制[32]。此外,TME 中Tregs功能还受癌症局部环氧化酶2 (cyclooxygenase 2,COX-2)及其产物前列腺素E2 (prostaglandin E2,PGE2)的调控[34]。在肺癌细胞与间质成纤维细胞共培养试验中,被肺癌细胞诱导的CAFs的COX-2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后者能以非细胞接触途径促进CD3刺激淋巴细胞的增殖、上调Treg细胞特异性FOXP3基因的表达,增强Treg细胞的发育及Treg细胞介导的免疫抑制作用[35]。
2.3.2 CAFs增强促肿瘤辅助性T 细胞免疫反应 CAFs及其分泌的趋化因子 (如CCL2、CCL5、CCL17)、极化细胞因子 (如IL-1、IL-6、IL-13和IL-26)还能直接增强促肿瘤辅助性T 细胞 (如Th2、Th17)免疫反应,抑制抗肿瘤性Th1反应[36-37]。靶向FAP+CAFs的DNA 疫苗可以促进Th2 细胞向Th1 细胞的极化转变,抑制TAMs 和Tregs的功能,同时激活细胞毒性T 淋巴细胞 (cytotoxic T lymphocytes,CTL)发挥肿瘤特异性细胞毒作用[38]。
3 CAFs与TME的基质重塑
在肿瘤中,控制细胞外基质 (extracellular matrix,ECM)合成和更新的稳态受到干扰,导致异常的血管形成,不同硬度和组织的过度纤维状胶原积聚[39]。
TME中CAFs激活后可以通过胶原纤维的增厚和线性化使ECM 刚性增加,这种改良的ECM 蛋白网络起到了物理屏障的作用,限制了T 淋巴细胞等免疫细胞对癌细胞的访问[40-41]。肺肿瘤患者组织切片活体细胞成像显示,T 细胞在疏松的纤维连接蛋白和胶原区域活动活跃,而在瘤巢周围的致密基质区域迁移较少。无论是添加胶原酶来降低基质刚性,还是由肿瘤细胞实验产生趋化因子CCL5,都会增加T 细胞从间质区域移动至癌细胞的速度[42]。
在纤维化程度较高的肿瘤中,功能性血管数量有限,肿瘤组织往往氧合不良,导致存在较多被称为 “缺氧区”的低氧压区域[43-44],影响TME[45]的氧气供应、酸碱度以及免疫细胞从血管向TME[46]迁移等过程。CAFs还能通过在肿瘤基质中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隔离物来削弱DC细胞表面MHC Ⅱ类标志物的表达和抗原摄取能力,这样不仅抑制DC 的生成和成熟[47-48],也可以通过抑制DC 介导的T 细胞分化生长来发挥免疫抑制作用[49]。
虽然多数研究认为肺癌中CAFs主要参与促肿瘤的免疫抑制反应,但其他病理类型中某些来自激活的肌成纤维细胞的因子可能会产生与前述相互矛盾的影响。例如,胰腺癌中α-SMA+CAFs 的缺失会通过增加肿瘤中CD4+Foxp3+Tregs的数量来诱导免疫抑制,从而加速肿瘤生长并降低生存率[50]。这可能和肿瘤的组织类型及分期有关。
4 抗CAFs治疗
TME内的CAFs能够通过多种机制损害抗肿瘤免疫,同时其遗传上相对稳定,不太容易受到传统治疗耐药机制的影响,这样一来靶向调节间质细胞功能的免疫治疗有望成为现有免疫治疗方案的重要补充。
基于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 (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FAP)在CAFs中表达的相对广泛性[51],目前靶向抗CAFs的免疫治疗的主要治疗靶点即为FAP。在L12小鼠肺癌模型中,经修饰表达FAP的全肿瘤细胞疫苗能诱导针对肿瘤细胞和CAFs的抗肿瘤免疫,并增强CD8+T 淋巴细胞的浸润,减少免疫抑制细胞在TME 中的聚集[52]。针对FAPα的疫苗在诱导FAPα特异性CTL 杀死CAFs,破坏TME中免疫抑制成分[40]的同时还能降低免疫逃逸的风险[38]。但是,一项研究将FAP 反应性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转移到携带各种皮下肿瘤的小鼠体内,只介导了有限的抗肿瘤作用,却在两个品系的小鼠中诱导了显著的恶病质和致命的骨毒性[53]。因此,靶向耗竭CAFs的治疗方案的确切效果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试验明确。
5 总结
尽管成纤维细胞在肿瘤中相对丰富,但几十年来一直被忽视。近年来它们在肿瘤生物学和肿瘤学领域的关键作用逐渐显现。TME 中CAFs 的激活受免疫细胞的调控,CAFs也可以通过释放各种趋化因子、细胞因子等调节多种免疫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反应的改变,参与构成TME的炎症表型。因此,靶向消灭或抑制CAFs治疗可能可以有效改善肿瘤中CAFs介导的免疫抑制。但既往以TME为靶点、旨在耗尽基质细胞的治疗,结果都提示疗效有限[54],原因可能在于TME功能的可塑性,单一消除TME中某一促肿瘤机制并不能完全阻断肿瘤的生长发展。因此全面了解CAFs对于肿瘤相关免疫反应的具体调控方式至关重要,适时调整CAFs的功能状态可能比单纯的消除更科学有效。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