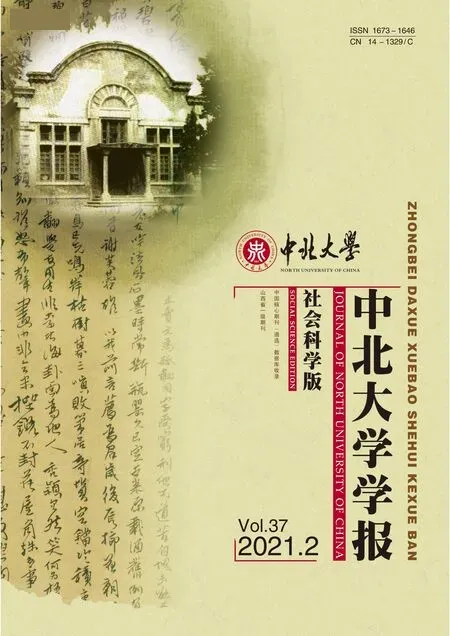和而不同: 中国诗学“实境”论与克罗齐“直觉”说
2021-11-30韦拴喜
韦拴喜, 柳 靖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实境”作为艺术实践活动的一种审美追求, 它要求创作者以浅显明了的构思、 晓畅直白的用语, 描写即目所见的真景, 抒发自然生发的性情, 在真情与真景的相“遇”相融之中, 尽显意境之美而自成佳作。 “直觉”作为艺术和审美活动的本质要素, 其呈现的是主观心灵(情感)赋予客观“物质”(物象)以形式载体, 将其上升为可供观照的具体形象, 从而达致心物统一、 情景相融、 “使情成体”(鲍桑葵语)的过程。 尽管“实境”属于中国古典诗学的独特范畴, 而“直觉”是现代西方表现主义美学的核心概念, 但无论是作为一种艺术本质论, 抑或是作为一创作方法论, 还是作为一种风格境界论, 两者之间都存在着互融互通、 对比阐发的空间。
1 “实境”释义
1.1 《二十四诗品》“实境”论解读
所谓实境, 乃相对于虚境而言, 顾名思义, 即真切实在的境界。 唐人司空图在其《二十四诗品》中, 专列“实境”品以详加阐释:
取语甚直, 计思匪深。 忽逢幽人, 如见道心。
清涧之曲, 碧松之阴。 一客荷樵, 一客听琴。
情性所至, 妙不自寻。 遇之自天, 泠然希音。[1]128
显而易见, 实境是指真实描写所见事物, 加以真实情感抒发所构成的诗歌境界, 实境一品, 关键在于“浅” “直”二字。 与“含蓄” “委曲”品相异, 不同于“含蓄”所求之藏而不露, 亦有别于“委曲”所言之曲折委婉。
首先, 就用语构思而言, “实境”讲求“取语甚直,计思匪深”。 《二十四诗品》之“实境”首句开门见山, 点写了用语构思之要领。 所谓“取语”, 即指书写诗句时所选取的语言。 “直”即直质, 其意为语言不求华丽繁琐, 隐晦幽暗, 但求明白晓畅, 质朴真挚。 “计思”即指诗篇的谋划构思; “匪深”, 不要求深奥繁琐, 其意为构思不求曲折反复, 变化无穷, 只求构思浅显, 直截了当。 “忽逢幽人,如见道心。”“幽人”, 乃高雅脱俗之人, “履道坦坦, 幽人贞吉”, 得以与幽人相逢, 倾心畅谈, 方得修道之精髓。 其意为心思仅在用语构思上是远远不够的, 幽人仿若写作时的灵感顿悟, 艺术创作讲求妙手偶得, 方可参悟道之本心、 事之本心。
其次, 就写景状物而言, “实境”追求即目直书, 将心中所想所感辅之以真实具体的事物景象和盘托出, 正如“清涧之曲,碧松之阴。 一客荷樵,一客听琴”。 实境讲求所写全为实景, 所感皆为实情, 即使描写虚空飘渺的精神道理, 也须得依托实在事物彰显表现, 强调即时即景。
最后, 就抒情写意而言, “实境”强调设身处地体悟真实景象, 自然通畅地抒发真情实感, 反对苦心孤诣的蓄意谋求。 正所谓“情性所至, 妙不自寻”, 即指真实的情感源自于心灵的妙悟, 诗之所至, 情之所至, 不自寻而自得。 明谢榛有云: “自然妙者为上, 精工者次之”[2]127, “诗有天机, 待时而发, 触物而成, 虽幽寻苦索, 不易得也”[2]127, 即是主张灵感触发后的自然妙得。 “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天”即天机天意, “泠然”出自《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 泠然善也”[3]10, 为“清和之意”[4]34。 “希音”出自《道德经》“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实指绝妙的诗篇。 显然, 就直抒情意而言, “实境”集中体现了道家哲学思想——天机所致, 道法自然。 诗人触物感怀, 心物相应, 捕捉刹那间迸发的灵感, 真情实意地将其描绘刻画, 任情适性, 浑然天成。
1.2 “实境”论之例释举隅
作为一部以诗评诗的诗论专著, 《二十四诗品》以自然淡远为审美基础, 对24种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美学意境进行了分类品评。 “实境”品辞用语浅直, 在即时即景中追求“思与境偕”的审美境界, 即注重客体形象与主体灵感相融合、 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审美意蕴, 在古典诗词中俯拾皆是, 此处特举两例典型“实境”之作。
昔闻洞庭水, 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 凭轩涕泗流。[5]579
杜甫《登岳阳楼》一诗, 此诚司空图所言之“实境”也, 清秀实境如在目前, 触目感怀, 心物相应。
首先, 诗歌开门见山、 直截了当点写出登临岳阳楼之所见, 在写作手法上与“实境”讲求之“浅” “直”不谋而合。 其次, 在表达方式上, 颔联“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 将洞庭湖水势的汹涌磅礴和宏伟壮丽真实地描绘出来, 寥寥数笔刻画出洞庭湖风光, 此为“实景”。 “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 诗人触景伤怀, 眺望眼前浩瀚无边的洞庭湖水, 触发了创作灵感, 联系自身居无定所, 孤苦无依的凄惨身世, 此乃“真情”, 诚如实境所求之即时即景, 即景即情。 最后, 在风格境界上, 诗人直抒胸臆, 仿若脱口而出, 信手拈来。 颈联表现自己政治生活坎坷, 漂泊天涯, 怀才不遇的心情。 尾联抒写出诗人眼睁睁看着国家离散而又无可奈何, 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凄伤。 诗人触目感怀, 即景会心, 方得此佳句。
再如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6]971
首先, 在写作手法上, 诗歌语言清新流畅, 淳朴素淡, 开头四句运用白描手法, 契合了“实境”品辞中所倡导的诗作语言应明白晓畅, 质朴真挚。 其次, 诗歌的表达方式上也彰显着“实境”的主要特征。 主要体现在诗歌的前部分再现了母子分离时慈母缝衣的真实生活场景: 母亲为了连夜赶制儿子出行的行装, 针线与衣服本为司空见惯之物, 诗人在这里却用这两种最简单的东西描绘勾勒出了母慈子孝的美好画面。 生活实景的刻画与真挚情感的抒发也是体现其“情性所至,妙不自寻”, 游子发自肺腑的感恩之情, 自然生发, 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可谓“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2 “直觉”考辨
2.1 克罗齐“直觉”说阐释
“直觉”是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的核心范畴。 克罗齐将精神视为世界的本源, 认为一切事物和人类行为皆是精神活动的产物, 其中, 直觉是基础和根本。 审美和艺术活动即为直觉活动, “美学只有一种, 就是直觉(或表现的科学)的知识。 这种知识就是审美的或艺术的事实”[7]177。 克罗齐将人类知识分为直觉和逻辑两种, 直觉是前提和基础, 对直觉的理性思考形成概念, 进而上进到逻辑层。 逻辑知识需以直觉为基础, 但直觉却并不依赖逻辑。 因而, 直觉和逻辑是上下级关系, 绝非主从关系。 直觉不依赖概念, 不由概念而来, 这不仅反驳的是黑格尔的美是理念感性显现说, 还暗含了克罗齐试图以直觉冲动来摆脱概念世界, 与本体论美学决裂的理论构想。
所谓“直觉”, 通常是指不必进行理论分析便可直接领会事物真相的一种心理能力。 不同于这种惯常的理解, 克罗齐给予“直觉”以审美维度的阐释。 克罗齐在其《美学原理》开篇, 便将直觉与理性、 知觉、 感受等概念列举分析。
首先, 与源于理智, 关乎共相, 产生概念的理性不同, 直觉来源于想象, 关乎的是个体, 产生的是意象。 其次, 直觉可以是知觉, 反之, 直觉也可以不是知觉。 知觉是关于现前实在知识的是非判别, 而直觉则没有实在和非实在之分, 没有真与伪之别, “对实在事物所起的知觉和对可能事物所引起的单纯形象, 二者在不起分别的统一中, 才是直觉”[7]4。
在分析了直觉与诸相关概念差异的基础上, 克罗齐阐明直觉的表现本质。 “心灵只有借造作、 赋形、 表现才能直觉”[7]9, 感觉或印象, 借助文字或非文字(线条、 颜色、 声音)等各种表现形式, “直觉与表现是无法可分的。 此出现则彼同时出现, 因为它们并非二物而是一体”[3]10。 从中可窥得, 克罗齐所谓的“直觉”本质上是一种心物交融的直观意识和使情成体的赋形能力。 直觉的过程即为主观心灵(情感)赋予客观物质(感受或表象)以形式, 使其上升为审美观照中的具体形象的过程。 这样一种心灵为物赋形和心灵创造的过程, 也是一种直觉表现的过程, 大抵类似于“形象思维”。 克罗齐美学之核心原则“直觉即表现”, 也体现出了他认为直觉与表现是不可分离的。 “心灵只有借造作、 赋形、 表现才能直觉”[8]14, 即就时间顺序而言, 二者几乎同时发生。 直觉唯有表现出所赋形的物质, 才能掌握这些形象。
基于对“直觉即表现”的阐释, 克罗齐进一步提出“艺术即直觉”的观点。 对此, 克罗齐在《艺术是什么》一文中以五个关于艺术的否命题来专论之。
第一, 艺术不是物理事实。 克罗齐认为一切直觉活动在心灵中完成, 无须借助外在媒介。 凡借助于外在媒介传达的产物, 皆属“心外之物”, 只能称其为记录艺术家创作灵感的备忘工具, 不能称之为艺术。 当我们在艺术创造中, 意志或灵感突现的瞬间, 构思在脑海内完成, 表现与艺术也就已产生。 第二, 艺术不是功利活动。 功利活动属于实践活动领域, 以追求实效为目的, 是趋近于追求个别利益的经济活动。 克罗齐否认将感官快感直接等同于美感的思想, 抨击了审美快感主义的传统“游戏说”, 以及将快感奉为至上原则的弗洛伊德“泛性欲论”。 第三, 艺术不是道德活动。 道德活动作为追求普遍利益为目的的精神活动, 属于实践活动类别, 与隶属认识活动的直觉有着很大差异。 第四, 艺术不是概念。 概念与直觉皆为认识活动, 克罗齐认为直觉先于概念且可独立于概念而存在。 直觉来源于想象, 产生意象, 意象性是艺术最根本的特性。 第五, 艺术不可分类。 克罗齐曾指出, 在艺术分类准则要求下的艺术家仿若“受到一切奴役性的束缚”[9]21。 克罗齐反对艺术的传统分类法, 既然艺术为直觉、 表现, 而表现与直觉并没有具体的形态以及程度, 因而无法分门别类。
基于以上关于艺术的否定性论述, 克罗齐认为“艺术即直觉”, 并进一步得出艺术即心灵赋形活动; 艺术是抒情的表现; 艺术是想象活动等观点。 可见, 克罗齐在关于直觉问题的阐述上, 强调心灵活动, 注重感情的抒发以及灵感、 意志的瞬间突发, 与《二十四诗品》中“实境”中所追求的真情流露、 灵感顿悟、 即目所得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这为我们进一步探究二者的互释互通性奠定了基础。
2.2 中国诗学“直觉”说相关命题辨析
纵观中国诗论, 虽未有“直觉”一词的原词复现, 却存在着极其相近的理论表述。 事实上, 就某种程度上而言, 中国古代艺术偏于主体、 内敛、 表情、 写意的审美范型和基本走向(1)与西方“模仿论”艺术观偏重客体、 外倾、 理智、 写实的审美理念不同, 中国古代艺术和诗学长于言志表情、 畅神写意的审美理路。 从发端于先秦两汉的“言志”说, 到兴起于魏晋之际的“缘情”说, 再到晋宋而盛于唐宋的“尚意”说, 尽管对主体情感、 内在体验的强调程度略有不同, 但中国艺术偏重主体、 内向、 情志、 写意的主导性审美意趣和审美范式一脉相承。, 与克罗齐的“直觉”说在艺术本质、 创作方法乃至风格境界上, 都具有一定的契合度, 这也为“实境”与“直觉”二者间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基础。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为陆机的“缘情”说与“应感”说以及严羽的“妙悟”说。
1)“缘情”说
“缘情说”的兴起意味着时人初步意识到情感在艺术创作主体中的重要作用, 乃是“情”进入中国文学视野之萌蘗发端。 “缘情说”一语出自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 赋体物而浏亮”[10]240。 实则最早始于《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缘情”之意有三: 其一为任情而动, 意为借由情感之萌发而彰显出诗歌之绮丽华美; 其二为因情而生, 其意为诗歌能将寄托于其中的情感与万物顺应并显现出绮靡之美; 其三为蕴含真情, “缘”有点缀、 装饰之意, “缘情”即强调诗歌创作要通过情思的浸染, 尤其是真情的作用, 方能使作品具有含蓄生动之美。 诗人将真挚内敛的情感熔铸于整个诗歌创作过程, 使得诗人的个人情感与诗作和谐统一。
这三层涵义从不同角度显现出情感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反观“直觉”范畴中, 克罗齐所言艺术即心灵赋形活动, 艺术是抒情的表现, 二者皆注重艺术与抒情的交汇共通, 可窥得其中的相似性。
2) “应感”说
“应感”作为中国诗学与文论关键词之一, 指有感于物而兴发创作灵感, 亦称“感兴” “天机”。 陆机《文赋》有云: “若夫应感之会, 通塞之纪, 来不可遏, 去不可止”[11]183, 即强调艺术创作中的灵感妙悟。 陆机借由“应感”一词, 强调了灵感的存在及其在艺术构思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正所谓“来不可遏, 去不可止”, 灵感顿悟并非创作客体所能自觉把握的。 “古典文艺学认为感兴源于感物”[12]29, “应感”其实就是一种心物交感和心物感应, 并非对客体的镜面模仿或直观反映, 而是心物感应时的一种微妙而具有诗意的心理活动。
“应感”与“直觉”虽在具体内涵与作用上存在差异, 但又具有相互融通的可能。 克罗齐认为, 艺术作为心灵的想象活动, 其完成场所只能是艺术家的脑海, 灵感迸发瞬间在脑海内便完成构思, 这种构思即直觉与表现, 一旦构思完成, 艺术成果便已在心灵中表现出来。 这种将艺术创作诉诸“灵感”触发的看法, 无疑是过分强调感性思维而导致的直觉审美绝对化的体现。 然而, 不可置否的是, 审美创造与审美欣赏中都存在直觉性。 在审美欣赏中, 的确存在不假思索的直觉判断; 在审美创造中, 也的确存在着淡化理性全凭灵感的直觉表现。
3) “妙悟”说
“兴趣”作为《沧浪诗话》的核心范畴, 其释义与“兴”这一概念内涵联系密切。 “兴”, 有感兴、 兴发之意, 即外物形象触发创作主体的内心情感, 而这种触发往往是自然而然的触发, 即感性直觉的触发, 排除了理性思维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 正所谓“不涉理路”, 诗歌的意象即在此种审美感性中自然生发。 这种审美感兴, 即为“妙悟”。 “‘妙悟’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晋僧肇的《涅磐·无名论》里: ‘玄道在于妙悟, 妙悟在于即真’”[13], 乃禅宗的重要范畴之一, 后被严羽引至《沧浪诗话》, 特指心物相应后的感发过程。 这种“妙悟”被严羽上升为诗人的创作本质, “诗有别才, 非关书也”, 这种妙悟别才在某种程度上与克罗齐的“直觉”说存在相似之处。 与严羽几无差异, 克罗齐也排斥一切理性思考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 将感性直觉置于首位。 此外, 严羽将妙悟视为天赋灵感, 与克罗齐“直觉说”中强调艺术家个人的灵感构思颇为类同。
3 “实境”论与“直觉”说的互释互补
克罗齐的“直觉”概念经由朱光潜翻译引介至国内,初识“直觉”,朱光潜从反映论的角度试图阐释理解, 直至他通读翻译克罗齐《美学原理》后,才在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与克罗齐美学之间找到沟通的桥梁。 此外, 他还提及: “诗的境界突现都起于灵感。 灵感亦并无若何神秘,它就是直觉。”[14]52由此可见, “直觉”与“实境”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吸收、 双向阐发的可能性。
3.1 “实境”论与“直觉”说的异中之同
第一, “实境”论与“直觉”说均强调艺术创造活动具有客观实在性。
“实境”讲求以真言写真景、 真景表真情的构思创作之法, 认为诗歌创作应做到即时即景, 所写之景皆为实景, 所抒之情皆为真情, 情景交融, 一触即发。 “实境”论将诗境置于实境之上, 首先要将“物象的本样复原”[15]91, 强调应目会心而合乎自然英旨, 由此直致所得。 在主客体关系层面, “实境”论所追求的艺术创作境界实为物我一体的创作境界, 其所理解的艺术本质实为主客和谐统一的艺术本质, 所言之真情实为强调主体能动, 所言之真景即为强调客观实在。
克罗齐的“直觉”说强调艺术无须借助各种形式的外在媒介, 诸如文字、 颜色、 声音等包括自然和人工的外在传达媒介, 艺术创作在心灵中即可完成。 然而, 这并非意味着“直觉”说所言之艺术创造是脱离了客观实在的空想, 其仍是依托客观实在进行创作。 艺术创作过程其实是主客体相互交融、 互为表里的过程。 “直觉”说虽强调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创作过程中的独特地位, 但并非彻底逾越了客观实在性, 因而, “直觉”说是在客观实在的基础上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
“直觉”范畴还强调意志突现的瞬间, 认为艺术创作过程具有“具体而微地迅速”的特点, 这种创作具有的即时性, 使得艺术家不得不借助于各种“备忘的工具”来暂存保留。 而所谓“备忘的工具”, 实指客观物质的外在传达, 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直觉”说对艺术创造具有客观实在性之肯定。
第二, “实境”论与“直觉”说均强调了主体在艺术创造活动中的能动作用。
无名氏于《皋兰课业本厚解》有云: “盖实理实心显之为实境也。”“实境”并非单纯的实景, 它虽然是依托真实物景, 但要义在实景与主体遇而进于境, 情因境生, 法因境生。 “‘情性所致, 妙不自寻’——情由性出, 故此情性为真, 以此‘真’之‘情性’为诗, 便成佳绪。”[16]因而, “实境”实为表现实有的客观实物及作者的主观情思。
“实境”以“真切为贵”, “实境”乃真实切在之境界, 诸如直抒胸臆、 即兴感言, 皆为实境, 意指在艺术创作时在真情与真景的相“遇”相融之中, 情真意切, 尽显意境之美。 《二十四诗品》“实境”品辞“情性所至,妙不自寻”二句强调了创作主体通过亲身体验, 以及设身处地体悟真实景象, 进而抒发自身的情感, 强调了创造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 诗歌本是人的产物, 诗中所呈现的具体意象, 所描绘的意境, 脱离了主体情感的表达, 意象与意境本身的存在就失去了价值与意义。
克罗齐的“直觉”说无论是对直觉本身的界定, 还是对艺术的进一步阐发, 皆与人本身脱不开关系。 “直觉”作为艺术和审美活动的本质要素, 其呈现的是情感赋予物象以形式载体, 将其上升为可供观照的具体形象, 从而达致心物统一、 情景相融和“使情成体”。 克罗齐认为直觉是心灵的主动赋形活动, 其内容也是关于个体的内容, 甚至认为直觉活动无需外在客观物质媒介, 便能在艺术家脑海中完成。 而克罗齐对于艺术的界定同样强调所谓心灵赋形活动, 并宣扬艺术即为抒情的表现, 强调艺术的表现总是体现为情感的表现, 进而产生了美。
第三, “实境”论与“直觉”说均强调灵感顿悟在艺术创造活动中的特殊作用。
“实境”论提倡创作主体在心物相应、 灵感勃发刹那, 真实地摹写出脑海中的实境, 促使真情实感地自然流露与抒发。 《二十四诗品》“实境”品辞: “忽逢幽人,如见道心”, 忽逢隐逸的高雅之士, 就好似瞬间迸发的创造灵感, 诗人置身实景之中, 其创作要义就在于捕捉刹那触景所及之情, 继而真情实意地将其书写记录。 同样的, “情性所至,妙不自寻。 遇之自天,泠然希音”四句也体现了灵感顿悟在创作时的独特地位, 主张灵感触发后的自然妙得, 继而做到浑然天成。
克罗齐“直觉”说在论及艺术与物理事实的差异时提到: “审美的事实在对诸印象作表现的加工中就已经完成了……如果在此之后, 我们要开口说话, 或提起嗓子唱歌, 这就是用口头上的文字和听得到音调, 把我们已经向我们自己说过或唱过的东西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实践的事实, 意志的事实, 而不是心灵的事实。”[8]50在此处, “起意志”即意志突现瞬间, 实质意味着艺术创作要诉诸于灵感, 这种灵感“具体而微地迅速”, 具有即时性, 然而一旦发生, 创造便发生, 表现便发生。
3.2 “实境”论与“直觉”说的同中之异
第一, “实境”论与“直觉”说对于外在语言文字媒介的态度存在差异。
“实境”注重情感的外化传达, 艺术创造要借助语言文字, 因而要求创作主体提升艺术修养。 “实境”论还重视作为外在媒介的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 《二十四诗品》“实境”品辞中, 开篇便提到了对于文字语言的要求, 即“取语甚直”。 所谓“情性所至, 妙不自寻”, 也需要借助文字作为媒介物。
克罗齐则与之相反, “直觉”说更多强调艺术创造, 人人皆有直觉活动, 人人皆为艺术家。 克罗齐侧重艺术创造而忽视了传达, 认为直觉活动无需外在客观物质媒介, 便能在艺术家脑海中完成。 就此而言, 司空图的“实境”论更加贴合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 克罗齐的“直觉”说却摒弃技巧等“心外之物”, 认为艺术无需琢磨技巧, 具有天生性, 人人皆为艺术家。 这与其对于直觉的根本界定有着密切关系。 当我们在艺术创造中, 灵感迸发瞬间在脑海内完成构思, 表现就已发生, 艺术就已产生。
第二, “实境”论与“直觉”说对艺术创作主体的能力要求不同。
“实境”论要求创作主体在完成艺术创造之前, 创作主体首先需了解并参透一定的艺术创作规律及技巧, 正所谓“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17]58。 此外, 还需提升自己的文化以及审美修养, 否则, 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成艺术创作。 掌握了基本的艺术创作规律, 方才明白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 提升了内在审美修养后, 方才积累了艺术经验, 进而使创作主体具备了相对敏感的艺术觉察力,从而使诗人在触及情感, 灵感迸发时足以敏锐察觉并准确把握客观对象深刻的审美内涵。
克罗齐“直觉”说则非如此。 克罗齐将“直觉”视为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艺术创作能力, 无须具悉艺术规律, 亦不必锻炼艺术技巧。 “直觉”指导下完成的艺术创造, 其审美价值之于创作者而言亦无高下之分。 显然, 如此为之, 克罗齐便彻底否认了艺术创作规律与技巧的基础性, 以及主体内在审美感觉力的重要性, 甚至泯灭了“直觉”引导下艺术创造的独创性。
第三, “实境”论与“直觉”说对艺术创作具体过程的复杂程度的要求有别。
“实境”论虽然力求即目直寻的艺术创作方式, 但并非一味纪实, 即非平铺直叙地记录便可完成创作。 创作主体所书之景已然是经由其审美过滤后之境, 犹如“清涧之曲,碧松之阴。 一客荷樵,一客听琴”。 流水淙淙之清涧, 亭亭如盖之碧松, 有江渚渔樵, 亦有聆音幽人。 入画之景, 以淡雅幽远的境界展现在创作主体眼前, 施以具体可感的生动形象, 辅以油然而生的真挚情感, 创作过程相较“直觉”说而言更为复杂。
克罗齐视直觉为最基层的心理活动, “直觉”的获得无须铺垫前因后果, 好似先天凭空得来, 唯一前提基础即为“感受”,这一前提人人皆备。 如此, 与“实境”论不同, “直觉”说强调创作过程相对简单直接, 瞬间即可在脑海内完成创作。
4 结 语
具言之, 作为西方表现主义美学核心范畴的“直觉”, 虽从未在中国古典诗学史上原词复现, 但却在内涵旨趣上与中国古典诗学的相关命题遥相呼应、 不谋而合, 尤其和“实境”概念在构思创作、 取境抒情等层面存在着交互印证、 相互补充的诸多可能。 在现代跨文化语境中, 将“实境”论与“直觉”说并而论之, 以阖合性思维、 对话性姿态对其相似之处及同中之异进行比照阐发, 或可为中西审美形态的互识、 互证、 互补、 互通提供一个可供参照性的研究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