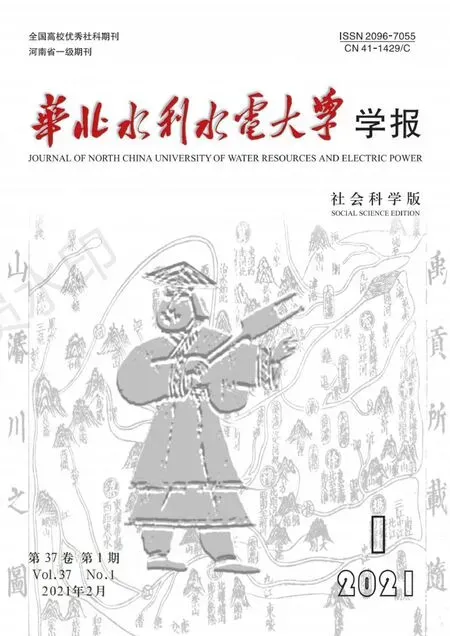永定河变迁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2021-11-29张连伟
张连伟
(北京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永定河属于海河水系,上游为桑干河和洋河,流经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宋元以降,永定河因流短水急、泥沙含量大,有小黄河、浑河、无定河之称,并影响到下游生态安全和水系变迁;又因流经京津冀腹地,威胁到京畿安全,所以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近几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永定河成为京津冀等省市的重要水源涵养区、生态屏障和生态走廊,涉及雄安新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国家重要地区和基础设施的生态安全,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生态领域率先突破的着力点。近些年,围绕永定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变迁和治理,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林学、水利工程学、水土保持学、环境科学等许多领域学者展开了相关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历史学视角,梳理永定河演变的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变迁的驱动因素,反思永定河治理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一、永定河的历史演变
永定河最早载于《山海经》,称为“浴水”,班固《汉书·地理志》称其为“治水”,许慎《说文解字》又称其为“水”[1]43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水》第一次对永定河水系进行了详细叙述,桑干水、桑干河、清泉河等名称也见诸记载。永定河的第一次开发是在三国时期,当时永定河水被用于灌溉农田。三国时期,魏国征北将军刘靖于嘉平二年(250年)造戾陵遏,开车厢渠,导高梁水,“灌田岁二千顷”[2]340。其后,景元三年(262年),樊晨更制水门,水流乘车厢渠,扩大了灌溉面积。晋元康五年(295年)六月,洪水冲塌了位于梁山(即今石景山以北的四平山)附近的戾陵堰,“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2]340。刘靖之子刘宏按照旧制,重新修建了戾陵遏和水门,复兴灌溉之利。北魏孝明帝时期(516—528年),裴延儁出任北平将军、幽州刺史,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对督亢陂和戾陵堰进行了修复[3]。及至隋朝,《册府元龟》载,裴行方任检校幽州都督,引卢沟水,广开稻田数千顷,百姓赖以丰给。
隋唐以至宋辽金时期,永定河及其上游桑干河成为中原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拉锯争夺的地区。隋炀帝、唐太宗征伐辽东的时候,都曾途经永定河。宋辽对峙时期,宋军与辽军在永定河流域展开拉锯战。辽国占领幽州以后,于天会元年(938年)升幽州作为陪都,改名为南京,又称燕京[4]4。辽统治者曾“猎桑干河”“观渔桑干河”,最后甚至“遗传国玺于桑干河”[4]5。金灭辽后,海陵王迁都燕京(今北京),改燕京为中都,流经都城西南隅的永定河地位日渐凸显。
金元时期,统治者定都北京后,毗邻永定河,称之为卢沟水、浑河,曾尝试在今石景山附近向东开凿金口河,引永定河水直通京城。然而,这条人工河并没有起到理想的作用,不仅航运未成,最后连灌溉的功用也被迫放弃,原因在于永定河日益浑浊,泥沙含量增大,河道淤积问题突出[5]。但就永定河及其上游桑干河而言,在木材的采伐和运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元朝时期,为营建大都、修造战船和兵器,开始通过永定河大规模采伐上游的森林资源,“西山兀,大都出”。这也加剧了永定河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导致永定河水泥沙含量不断增加,成为名副其实的“小黄河”。
元明清时期,都曾在永定河下游修筑水利堤防,用以防洪和灌溉,但真正大规模地修筑堤防则是在清康熙时期。清朝初期,永定河多次决口,威胁到京城安全和百姓生活。1698年,康熙皇帝责令于成龙负责永定河治理。于成龙采取加筑堤防、疏浚河道的方式,在永定河两岸大规模修筑堤防,固定了永定河下游河道,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京城和永定河下游的安全。但是,由于永定河水含沙量大,下游河道平缓,泥沙淤积日趋严重,致使永定河堤防维护工程日趋繁重,在清朝中后期逐渐陷入困局。晚清时期,整个永定河下游河堤越筑越高,成为地上悬河,风险越来越大。永定河在官厅山峡出山以后,基本上失去了蓄水能力,一旦遇到强降雨冲决堤坝,就会引发水灾。根据笔者对官方奏报的统计,晚清时期永定河共漫决29次,其中1867至1873年更是连续7年8次决口,漫决频率之高令人难以置信。
20世纪初,永定河水患仍然是京津冀地区的重大生态威胁,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水灾,而1913年、1917年、1924年、1925年、1929年、1939年为特大水灾[6]367。为了根治永定河水患,在政府和民间的推动下,顺直水利委员会和华北水利委员会先后负责永定河治理,展开了永定河水文资料的调查和测量,以及永定河水利工程的勘查和研究,并尝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对永定河进行治理,发布了一系列治理和研究成果,如《永定河疏治研究》《永定河治本计划》等,为永定河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时局动荡,战乱频仍,这些研究大都没有能够落到实处。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开始大规模治理永定河,力图根除永定河水患,保障北京的城市安全和用水。官厅水库是我国建造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它的建设受到了政府的空前重视,并得到大力支持,1951年10月动土,1954年5月竣工投入使用,在防洪、发电、灌溉、供水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根据1995年的统计,永定河及其上游桑干河、洋河河段仅水库就有200多座。这些水利工程遏制了永定河水患,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需要,保障了下游河段的安全,但也导致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即由多水变为缺水,由水灾为主变为风沙灾害为主。
2001年,北京市政府联合水利部制定《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北京市政府投资18.27亿元对官厅水库进行综合治理,并在三家店建设净水工程。2010年,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建设实施,启动多项治理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北京西南部的城市景观,涵养了水源。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中央将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作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领域率先突破的重大工程,编制了《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设立了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2019年,为了恢复永定河生机,国家开始对永定河进行跨流域补水,黄河水经山西万家寨引黄工程进入永定河水系。2020年6月,断流25年的永定河实现全线通水,“浴水”重生,这又是永定河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二、永定河变迁的驱动因素
历史上,永定河流域曾经水量充沛,森林茂密,资源丰富,为京津冀晋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从早期的泥河湾遗址、北京人遗址,到山顶洞人遗址、东胡林遗址,都留下了原始人类活动的足迹;从传说中的黄帝、炎帝、蚩尤的板泉、涿鹿之战,到“合符釜山”“邑于涿鹿之阿”[7]6,这些都奠定了华夏民族发展的基础,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数万年前永定河塑造的北京小平原、北京湾,到数千年前永定河上的古渡口,奠定了北京城市发展的基础,进而演变为蓟城、燕京、元大都、北京城,永定河不仅为北京的城市发展提供了丰沛的水源,也塑造了北京的历史地理空间,使北京逐渐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北京城的建立和发展,大大提升了永定河的地位,历代统治者都不断强化对永定河的治理。人类活动对永定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永定河变迁的重要驱动因素。
第一,秦汉以来永定河上游地区的农业垦殖是永定河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推动力。永定河上游的桑干河和洋河两大支流,分别处于黄土高原区和内蒙古高原区。从地貌来看,自流域边缘至中心依次为黄土台地、冲积洪积倾斜平原和冲积平缓平原[8]2,边缘区域土壤疏松,一旦进行大规模农业垦殖,地表植被很容易被破坏,造成水土流失,进入桑干河和洋河,进而影响下游的永定河。从区域位置来看,永定河上游地区处于农牧交错地带,先秦至西汉初期,永定河上游的桑干河流域主要为游牧民族所控制,农业垦殖较少。西汉建立以后,先后在桑干河流域设置了定襄、云中、雁门、代郡等郡县,为了加强对边境的控制,开始移民垦边,进行农业开发。东汉以后,桑干河流域成为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争夺的地区,长期战乱,人口减少,农业垦殖停顿,大批乌桓、匈奴游牧民族进入桑干河流域。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拓跋部落崛起,其以平城为中心,不仅建立起日益强大的政权,而且迁移人口,发展农耕,平城附近的人口曾达到百万之多,使桑干河流域的农业垦殖达到了高峰。南北朝后期,突厥逐渐强大起来,多次进入桑干河流域,长期的战乱导致人口迁离,城镇废弃,桑干河流域的农业垦殖再次陷入停滞。及至隋唐时期,整个永定河上游的桑干河流域因疏于管理,成了游牧民族的游猎之地,地表植被得到一定恢复。到了唐末五代以至辽宋时期,桑干河和洋河流域的农牧业再次发展。元朝时期,农业垦殖与森林植被的大规模采伐加剧了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也使永定河迅速成为浑河、小黄河。进入明朝,长城成为农牧地区的分界线,长城内侧桑干河流域的居民曾在明朝初期内迁,政府为加强对边境的统治,开始在桑干河流域驻兵屯垦。在明清时期,随着人口增加,永定河上游地区的农业垦殖日趋频繁,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严重。
第二,魏晋以后海河流域的漕运发展改变了永定河下游区域的河流生态。海河水系形成于战国时期,但早期规模较小,仅限于今大清河、永定河和北运河三个水系[9]393。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征讨乌桓,运送军需物资,遏淇水入白沟,又开凿平虏渠和泉州渠,连通滹沱河与沙河、泃河与潞河,成为海河流域漕运的重要发端。隋朝时期,隋炀帝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入白沟,循清河东至天津,由天津北达涿郡(今北京西南),其中在天津到北京之间利用了永定河(桑干水)下游河段[9]401。永济渠沟通了海河与其他水系的航运,形成了大清河、南运河、子牙河、永定河、北运河汇流入海的水系结构。这种水系结构便利了航运,对促进南北交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为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变迁埋下了伏笔[10]。魏晋至隋唐时期,海河流域的漕运主要是为了打通向东北地区的通道,方便军粮运输,所以持续时间不长。元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大运河成为南北经济交通的大动脉,漕运与永定河泥沙下泄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此造成的环境压力也日渐凸显。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过卢沟桥》诗注:“下口运河为之阻,浑流既不可入运,惟使荡漾于淀池及洼地,自乾隆元年以来,已三易其处矣。今之下口,据方观承以为可行,二十余年知其非长策,而实无计可图也。”[11]1566在永定河治理上,清朝统治者既要防范永定河水患,又要保持运河畅通,但实际上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兼顾。为了解决永定河泥沙淤积问题,清朝前期开始,就通过束水攻沙、蓄水刷清,使平原河道的泥沙向下迁移,利用下游湖泊湿地的蓄洪蓄沙能力,吸纳上游洪水和泥沙。但是,随着下移泥沙的不断增加,一些原有的低洼处逐渐消失,河流失去蓄洪能力,造成了更加频繁的水灾[12]。
第三,宋元以降,永定河中上游森林植被的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根据于希贤、尹钧科、吴文涛、李红有等人的考证,永定河中上游流域曾分布着茂密的森林,生态环境良好。魏晋以后,特别是宋辽、金元、明清时期,随着城市的发展,宫殿、城池、寺庙、衙署、民房、薪炭等所需的木材,大量取自永定河中上游流域。尤其是元朝以后,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城市发展迅速,所需的木材、薪炭也多源于永定河两岸的森林。元代的《卢沟运筏图》形象地再现了永定河流域森林采伐的盛况。明朝时期,京城奢靡之风渐盛,“官民之家争起第宅,木植价贵,大同宣府窥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筏木”[13]776。明朝政府为了抵御蒙古族的侵扰,在长城沿线实行“烧荒”政策,宣府、大同、延绥等地是烧荒的重点区域[14]。近边诸地,经明嘉靖时胡守中斫伐,宋元以来古松殆尽[15]。清朝所需的木材薪炭都由近京州县负责采办,顺治初年,永定河中上游卫所每年负责采办杨木长柴15吨,其后不断增加,到咸丰三年(1853年)达到每年18.9吨[6]151。这些采伐和破坏都导致永定河中上游地区森林资源锐减,土壤沙化,水土流失严重。以地处永定河上游中段的大同县为例,到新中国成立时,森林覆盖率下降到了0.7%[16]。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重视林业建设,开始在永定河流域植树造林,但林木成活率较低,效果不明显。随着“大跃进”等运动的开展,毁林开荒,林农争地,都加剧了永定河上游地区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第四,明清以来,永定河流域持续的矿业开采也对山体和植被造成严重破坏。矿产资源的开发不仅使环境污染,也造成矿区水土流失,诱发塌陷、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地表植被、景观、生物群落的破坏[17]。永定河中上游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煤炭资源有着悠久的开发利用历史。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已经有永定河上游地区利用煤炭的记载,其中说:“水发火山东溪,东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热同樵炭也。”[2]316明清以来,随着永定河流域人口的增加,森林资源减少,煤炭被越来越多地用作生产生活燃料,开采日盛。以地处北京永定河畔的西山为例,它曾是北京燃料的主要供应地。《檐曝杂记》云:“即如柴薪一项,有西山产煤,足供炊爨。故老相传‘烧不尽的西山煤’,此尤天所以利物济人之具也。”[18]131煤炭在给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煤矿开采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总体而言,古代生产工具简陋,开采规模小,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还比较小。近代以来,随着煤矿开采技术的不断进步,开采规模日益扩大,对环境的影响也愈加明显。以永定河流经的门头沟一带为例,有数百个煤窑,上百个采石场,挖煤、采矿持续了数百年,对永定河水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山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19]。
第五,清代以来,水利工程建设对永定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永定河早期的水利工程主要用于农业灌溉。金代以后,统治者开始在今石景山到卢沟桥之间筑堤固岸,防止水患。明代以后,政府又开始在卢沟桥以下筑堤。这些水利工程要么规模较小,要么持续时间较短,对永定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影响较小。永定河真正大规模筑堤始于清朝,从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到晚清时期的同治、光绪,历代统治者都在永定河治理上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堤的长度、规格,工程的复杂性、系统性,管理制度的专业化和完善程度等,都远远超过前代”[20]。永定河堤坝的修筑,固定了永定河河道,改变了永定河下游河道摇摆不定的状态,但也造成严重的泥沙沉积、土壤沙化、湖泊淤废,增加了永定河下游水灾的风险和频率,对下游流域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清代以后永定河下游的防洪抗汛压力不断增大,水灾频仍。1949年以后,为了根治永定河水患,化害为利,以官厅水库的修建为起点,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永定河中上游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以遏制永定河水患,保障永定河的生态安全。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永定河出现长期断流,上游地区水体污染加剧,下游地区则风沙灾害增加,整个流域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三、永定河变迁的历史启示
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演变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从早期的清泉河、卢沟河到后来的浑河、无定河以及当代的污水河、无水河,都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反映了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变化。对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演变及其治理的研究,不能仅仅从水灾、水污染或风沙灾害、植被破坏等单个问题去研究和治理,还要充分考虑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多角度、多层次探寻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和原因。从历史角度反思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演变和治理过程,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要加强永定河上游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永定河上游处于黄土高原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早期以游牧为主,保持了较好的生态环境,但随着人口增加,农耕发展,森林被砍伐,地表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日趋严重,致使下游水灾频发。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曾在永定河沿岸大规模地植树造林,用以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但与此同时,在永定河上游的桑干河和洋河流域,又存在着大量毁林开荒、盲目发展工矿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以至地下水超采,水源涵养不足,污染严重。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对永定河上游水源保护的过程中,往往采取行政主导的方式,忽视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导致许多保护措施难以为继。因此,新时代要使永定河成为一条流动的河,必须加强源头保护和治理,尤其是植被恢复、水源涵养方面。要正确处理农业生产、工矿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打破河流的地区分割,进行区域间、产业间的生态补偿,推动经济发展的转型和升级。
第二,要发挥永定河中游区域的生态涵养功能。自官厅水库至三家店出山口间的峡谷,称为官厅山峡,全长108.7 km,属于永定河中游地带,也是北京俗称的“大西山(即西山)”区域。历史上,永定河的水源,除了上游的桑干河和洋河外,西山森林茂密,泉源众多,对永定河也发挥着水源补给的作用。西山良好的生态环境与永定河丰沛的水源相互依存,为北京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先秦至汉唐,永定河中下游地区一直人口较少,森林植被破坏程度也较小。《新唐书·张旭传》记载:“北平多虎,(裴)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21]5764野生虎豹等大型食肉动物的生存对生态系统的质量要求很高,而当时该地区多虎,说明当时的生态环境非常好。辽金以后,西山一带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不仅失去了其生态涵养功能,水土流失也非常严重。近些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门头沟地区列为生态涵养区,但从永定河中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来看,这是不够的,它应该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结合起来,扩大范围,封山育林,立足于生态涵养,促进文化发展。
第三,要注重永定河下游流域水灾的预防。千百年来,永定河以水灾而著称,下游地区深受其害。以北京地区为例,从元朝至今共发生水灾320余次,“属于永定河泛滥成灾的比例无疑最高,危害也最严重”[22]117。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上游地区大量水利工程的修建,下游地区水灾消失,河水出现长期断流,河道湮废,名存实亡。但是,受季风气候影响,永定河流域的降水季节性变化非常大,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降雨时间短而急促,很容易引发水灾。近些年,随着永定河断流,下游大片河道被占用,甚至被开辟成高尔夫球场,沿线工农业设施不断增加,这都形成了潜在的风险。未来,随着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永定河上游水量必然会逐渐增加,中上游山洪暴发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也会增加。历史上,一旦山洪暴发,永定河在三家店出山口处的下泄就极为迅速。特别是永定河在三家店出山以后,落差较大,如果上游来水过于迅猛,很可能威胁到下游地区的安全。因此,永定河下游地区的防汛工作始终不能松懈。
第四,要遵循永定河治理的生态规律。河流不仅是水利或自然资源,它还是一个生命体,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只有恢复河流的自然生命,才能保持它的活力。回顾永定河治理的历史,从顺其自然到人为地操纵控制,从下游筑堤固坝到上游大规模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在兴利除害的过程中,发生过许多违背生态规律的事情。历史经验证明,单纯以人类利益为中心,从局部出发,无法根治永定河,只有在遵循生态规律的前提下,把山水林田湖草看作一个生态整体,进行系统治理,才能达到人类与河流的共生共荣。当前永定河治理,最重要的是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进行生态补水,从而恢复永定河的自然生机。在治理过程中,不同部门、不同区域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做到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协同推进,使永定河逐步具备自我生态修复的能力,真正成为一条流动的河、绿色的河、清洁的河、安全的河。
第五,要完善永定河治理的制度和机制。历史上,永定河的管理制度是随着永定河的治理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设立总河,并设永定河南岸分司、北岸分司,司署衙门设在固安城内,这是永定河首次建立管理机构。康熙之后,雍正、乾隆等也都曾谋划永定河治理。雍正四年(1726年),永定河实行专职管理,设永定河道一名,先归属河道总督,后隶属直隶总督,下设石景山同知、南岸同知、北岸同知、三角淀通判等,其下又设汛员、河营等。此后,永定河的管理虽然名称、隶属关系不断变化,但基本上都实行了统一管理。1954年初,河北省各专区分别成立水利局,永定河河务局被撤销,两岸堤防分别由北京市和河北省沿河各县负责管理,从此永定河被分而治之。永定河被不同省市区分而治之后,不同部门之间往往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沟通,山、水、林、田的管理各自为政,不同河段管理方之间争水夺利,导致永定河的治理顾此失彼,缺乏系统性,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难以兼顾。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生态领域率先为永定河的区域合作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在永定河生态修复和治理过程中,京津冀应加强与山西、内蒙古两省(区)的合作,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建立动态的生态补偿机制,破解永定河治理中的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