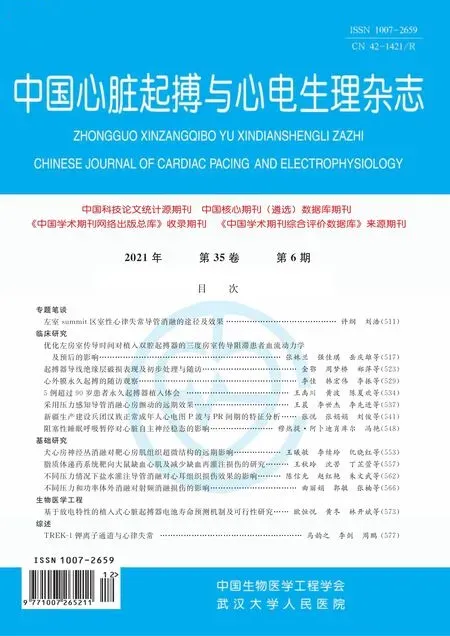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术后的复发与优化管理
2021-11-29陈居刚黄彦生董淑娟楚英杰
陈居刚 黄彦生 董淑娟 楚英杰
导管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catheter ablation,RFCA)已成为防治阵发性和持续性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AF)的重要策略,但复发率仍然较高,尤其在持续性AF术后晚期。近年来RCFA 技术和策略的进步并未显著提高手术的成功率,降低AF复发显得迫切需要[1]。最近的研究显示:优化管理生活方式和危险因素对AF 有潜在益处,被认为是AF的无创上游治疗[2]。加强AF 的综合管理对改善RCFA 术后的复发有重要意义,笔者综述这些方面的研究进展。
1 AF的病理生理机制
AF的发生机制相当复杂,目前学者已提出了众多假说包括转子学说、多发子波折返学说、局灶触发学说及AF 的巢学说等,但尚无一种假说能解释所有类型AF 的发生[3-4]。近年有学者提出“AF病理生理三角”可能是AF触发和维持的重要机制,包括:引起AF 的触发活动(启动AF)、纤维化基质(维持AF)以及众多调质(多种潜在机制)[5]。
在临床上,众多心血管危险因素或疾病与AF的发生相关,如高血压、肥胖阻塞性呼吸暂停(OSA)、糖尿病、炎症、肿瘤、外科手术、耐力运动等[2]。这些因素充当“调质”作用,它们通过多种潜在机制参与AF 的发生和维持。但这些因素参与AF的具体机制仍不明确,探究这些因素的机制可能是AF防治的一个重要方向。
2 RFCA与AF术后复发
RFCA 成功可改善AF患者的症状、降低卒中风险及改善心脏功能,即使复发也能为患者带来诸多益处。AF 预后与其类型(阵发性、持续性或长期持续性)、消融技术、心脏基质、随访时间、随访期间监测次数以及复发的定义等相关[6]。阵发性AF预后较好,但随着随访周期延长,复发率也增加。RFCA 第1年,阵发性AF成功率在70%~90%,持续性AF的65%~75%;然而RFCA 术后第5 年,阵发性AF 降至55%~65%,而持续性AF降至40%~50%[7]。
AF术后复发一方面可能由于消融技术的限制[7]。常见原因如下:①肺静脉窦部恢复传导是肺静脉隔离后复发的常见原因;②先前心律失常未被消融:术前AF 伴心房扑动或房性心动过速,由于检测技术受限未被识别,或者术中麻醉过深可能使局灶性房性心动速动未被诱导出来;③致心律失常位点未被消融指数识别:非肺静脉致心律失常性位点对触发方案(包括异丙肾上腺素、猝发起搏、程序性刺激)可能不明显,而一般临床实践不支持经验性隔离其他部位如上腔静脉、左心耳、马歇尔韧带[8];④靶向心律失常复发:损伤位点的持久性是当前消融的主要限制之一,尽管RFCA 后再传导与心律失常复发非正相关,但有研究表明至少40%患者出现再传导[9];⑤消融后新基质的产生:消融后可产生疤痕,包括心房基质周围、临近损伤位点及消融范围均可产生新的传导区,从而促进微折返或大折返。
AF术后复发另一方面可能由于致心律失常心房基质的存在,而这些很难被单纯RFCA 所改善[7]。在长期AF患者RFCA 术后随访中发现心房基质也发生演变。心房纤维化是AF的基本组织病理学变化,也是肺静脉隔离消融后复发重要预测因子。在AF 患者RFCA 术后随访中,高血压、OSA、糖尿病、吸烟、饮酒等多种心血管危险因素或疾病有助于心房纤维化[5]。这种非固定性质的纤维化可能成为未来AF新的起源点,而其无法被先前的RFCA 识别。
3 AF患者RFCA术后优化管理的危险因素
众多心血管危险因素可通过影响致心律失常心房基质而参与AF发展。优化管理这些危险因素可能是降低AF患者RFCA 术后复发的有效途径。
3.1 高血压 高血压是导致AF发病率高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与AF发生及发展密切相关[10]。动物实验已表明高血压可影响心房异常重构,包括心房异质缓慢传导、间质纤维化及炎症增加,从而使心房致心律失常性增加[11]。此外,高血压患者右房电解剖图中也发现传导减慢、低压区和AF易损性增加[12]。而一项动物实验也发现:在自发性高血压大鼠,灌注奥美沙坦可显著降低Ang-Ⅱ诱导的传导阻滞以及左房心肌纤维化,说明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可通过降血压发挥非抗心律失常药物对AF的抗心律失常作用[13]。
有证据表明高血压是AF 患者RFCA 术后复发的一个强有力、独立的预测因子[14]。在肾动脉去交感神经(RDN)早期前瞻性随机试验表明:RDN 可能有助于持续降低血压以及减少AF患者RFCA 术后的复发[15]。2020年一项大型多中心、单盲、随机临床试验(ERADICATE-AF)显示:与单独AF患者RFCA(肺静脉隔离)相比,RDN 显著增加阵发性AF和高血压患者12个月无AF的可能性[16]。然而有研究显示应用药物积极控制血压并不能减少AF 患者RFCA 术后的复发,但是其治疗时间很短(术前0~6个月和术后3个月),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逆转重构和改善预后[17]。此外,目前AF患者尚无明确的高血压治疗目标。一项随机开放临床试验(SMAC-AF)表明:与阵发性或持续性AF 患者标准治疗(血压>130/80 mm Hg)相比,RFCA 前平均3.5个月积极的血压控制策略并不能降低RFCA 术后AF的复发,但可导致更多低血压[18]。但仍有学者对此研究有异议:①在积极控制血压前,本研究并未显示高血压持续时程以及可能对心房的影响;②综合危险因素管理包括血压、体重、血糖、OSA 等可明显改善RFCA 术后AF的复发,而单独管理血压有一定影响但作用可能有限。
3.2 OSA 大量研究显示OSA 是AF 发生和进展的重要危险因素,防治OSA 可降低抗心律失常药物、电转复和RFCA 治疗AF的有效性[19-20]。OSA 增加AF 的风险机制包括[21]:①间歇性夜间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②呼吸暂停时交感神经张力增强,血压升高,进而通过压力和容量负荷导致左心房牵张;③增加氧化应激和炎症应激。
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是OSA 的一线治疗方法。2013年Felin等[19]进行的小型非随机研究发现CPAP 治疗OSA 可降低AF 射频消融术后复发,但仍需进行随机对照试验。2018年一项荟萃分析显示:OSA 增加AF 患者RFCA 术后复发风险,而CPAP治疗可能会显著降低AF 复发的风险[22]。CPAP能否提高OSA 患者AF治疗的成功率仍存在争议。OSA 心血管终点(SAVE)试验发现:CPAP治疗并不能预防中度至重度OSA 患者的心血管事件,包括新发AF的发生率[23]。最近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也表明:CPAP在减少OSA 患者AF成功电复律后复发方面并无益处[20]。因此,单独的CPAP 治疗可能并不足够预防OSA 相关性AF。此外,CPAP在OSA 患者中的依从性相对较低。
近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主神经激活参与了OSA 相关AF的发展[24]。急性OSA 发作可导致交感迷走神经共激活,缩短心房有效不应期以及促进AF 发生。慢性OSA诱导的交感神经激活在心房自主神经重构、结构重构和电重构中起关键作用,从而为AF的维持和复发提供基质。众多慢性OSA 犬或猪模型研究[24-26]发现:自主神经调节策略(如β受体阻滞剂、肾去神经、神经节丛消融、低水平迷走神经刺激、低水平压力反射刺激和颈动脉体消融等)可通过抑制交感迷走神经过度激活、心房重构降低AF可诱导性和持续时间,但未来仍需要大量的临床研究进一步明确。
3.3 糖尿病 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发生AF的风险比非糖尿病患者高40%,总风险每年增加约3%[2]。糖尿病和AF关系相当复杂,目前认为糖尿病通过血糖波动、氧化应激和炎症触发结构重构、电机械重构、电重构和自主神经重构,从而促进AF的发生[27]。
在一项糖代谢异常和AF 患者RFCA 的单中心研究发现:糖代谢异常可影响心房内传导延迟和低电压,并增加RFCA 的复发率[28]。2019年一项纳入298例AF伴糖尿病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根据RFCA 前12 个月糖化血红蛋白(Hb A1c)趋势分为三组(Hb A1c<7%、7%~9%和>9%),术后随访(25.92±20.26)个月表明AF伴糖尿病患者积极控制血糖(Hb A1c<7%)可明显降低RFCA 术后AF 的复发,因此RFCA 前应尝试一切方法优化血糖控制[29]。但糖尿病与AF患者RFCA 术后疗效仍有一定争议。在一项1 121例患者的队列研究显示:糖尿病不会增加心房扑动消融后AF发生的风险。德国的一项登记研究也发现: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糖尿病患者并未增加心房扑动或AF射频消融的围手术风险以及心律失常复发[30]。有荟萃分析表明:糖尿病伴AF患者行RFCA 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与一般人群相似,尤其血糖控制满意的年轻人[31]。
然而有关糖尿病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的数据主要局限于小范围和单一中心的报道。2019年一项纳入2 504例AF射频消融患者的欧洲多中心观察研究发现:234例AF伴糖尿病患者行RFCA 是相对安全的,但术后复发率较高(32.0%vs 25.3%,P=0.031)尤其是持续性AF(P=0.003),而阵发性AF伴或不伴糖尿病术后复发率无明显差异(P=0.554)[32]。但目前最佳血糖控制与AF 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的研究仍甚少。此外,2019年Kim 等[33]在一项纳入9 797 418人的全国人口研究中发现肥胖、超重、低体重及糖尿病的人群有较高的新发AF 风险,体重的状态和糖尿病有协同效应,新发AF随糖尿病的进展而增加。这项研究表明维持最佳体重和血糖状态可能会预防新发AF。因此任何进一步的研究都应该澄清糖尿病、血糖和AF之间的联系是否与体重状态无关。
3.4 其他 肥胖越来越被认为是AF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一项meta分析(包括16项观察研究)显示:体重指数每增加5个单位,AF 射频消融术后复发则增加13%。这些发现逐渐得到大型国际队列研究的支持[14,34]。目前关于体重控制对改善AF射频消融效果的研究甚少,但观察研究表明:中心性肥胖和高血压、血脂异常、糖耐量异常、吸烟、饮酒等其他危险因素的管理可以改善AF射频消融后的症状和复发[14]。此外,有一项纳入267例AF射频消融患者的回顾性研究表明:非酒精性脂肪肝与AF患者RFCA 术后心律失常复发率显著增加相关[35]。因此,识别和逆转这些危险因素可能会提高AF患者RFCA 术后无心律失常生存率。
4 结语和展望
AF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年龄、性别、遗传、种族和共病(如吸烟、高血压、OSA、肥胖和糖尿病)等均发挥作用。目前RFCA 已成为AF防治的重要策略,优化及综合管理心血管疾病相关危险因素可降低AF 基质尤其心房结构重构和电重构,从而减少RFCA 术后AF 的复发。因此,RFCA不应被视为AF单独的治疗方法,而应作为一种综合治疗方式。抑制或消除现有AF 发生的基质并防治AF 发展的基质将是未来AF管理的一个重要趋势,而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将为临床管理AF提供循证医学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