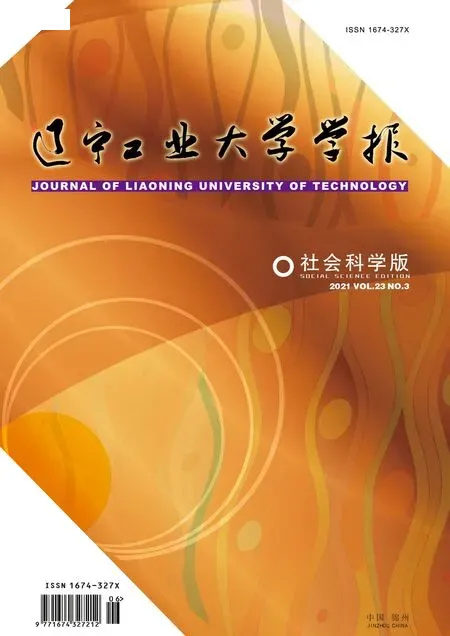三体并峙:咏史诗的内涵界定与题材分类新论
2021-11-29王帅
王 帅
本刊核心层次论文
三体并峙:咏史诗的内涵界定与题材分类新论
王 帅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 100005)
本文分析了咏史诗中“咏”的不同方式和“史”的不同含义,在此基础上对咏史诗的内涵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咏史诗是指诗人通过诗歌对于真实历史、历史信息载体、文学史历史形象三个层次的内容所进行的记录、评论和颂赞。根据咏史诗创作的实际,咏史诗又可以分为:传体咏史、论体咏史、赞体咏史三种具体的类型。
咏史诗;历史;历史信息载体;文学史历史形象;诗歌题材
汉魏六朝诗歌中有一大批优秀的咏史诗,这些作品有的直接题为《咏史》,比如班固的《咏史诗》;有些则以所歌咏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作为诗歌的题目,如曹植的《三良诗》;更多的则直接题为“览史”“览古”“咏古”等;有些诗歌的题目,虽然题为“咏怀”“感遇”“感兴”“古风”“古意”等,其题材仍然是咏史。本文通过三种咏史诗的研究,希望重新提出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咏史诗的问题。咏史诗这一题材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哪些诗可以算作咏史诗?咏史诗具体分为哪些类型?
一、“咏史”概念的提出和相关讨论
“咏史诗”的名称出现于东汉,但第一次对咏史诗题材提出明确界定的是六臣注《文选》。吕向于王粲《咏史诗》的解题中曰:“谓览史书,咏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1]1267吕向认为咏史诗的咏,有两个含义:一是评论历史事件的得失;一是寄托自己的怀抱。吕向这一观点,为后来的诗论家所继承。清代学者何焯有言:“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抒胸臆,乃又其变。”[2]他认为,咏史的“咏”包括“隐括本传,不加藻饰”和“多抒胸臆”两种情况,并分别称之为正体和变体。袁枚同样认为咏史分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出之”和“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两类,基本都是按照吕向的解释。
近现代学者也从现代的诗歌题材角度对咏史诗的内涵进行了解释,但基本上还是原有的思路与框架。以下是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①“咏史诗,是以歌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题材的诗歌作品。”[3]
②“咏史诗,顾名思义,即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诗歌。”[4]
③“咏史诗,是直接采取史实进行构思的一种诗歌样式。”[5]
④“咏史诗是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吟咏对象,藉之以述怀叙志,寄托感情的一种诗歌体式。”[6]
⑤“咏史诗,自古有之。诗人借咏史抒发自己的怀抱,以古人自况或对前人往事进行评议褒贬,借以表示对今人今事的称颂与讽刺,这也是一种广义的比兴手法。”[7]
这些定义,基本上还是从“咏”的角度对咏史诗的内涵加以界定和分析,但对于咏史中的“史”为何物却缺乏深入说明。近年来,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李翰指出因为史学的传统,咏史诗之“史”是具有演绎和传奇性质的广义的历史[8]。
纪倩倩等引进历史学“历史信息载体”的概念,进一步界定咏史诗所歌咏的范围。这个研究思路的开拓对于咏史诗研究很有启发,但二者的研究仅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问题,没有紧密结合汉魏六朝咏史诗的具体情况。
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结合汉魏六朝咏史诗的创作实际,进一步分析“史”的概念和范围。笔者认为,咏史之“史”的具体含义应该有三层,咏史之“咏”的具体方式也有三种。相对于咏史诗,应该有广狭两种定义。
二、从“史”的含义看咏史诗的内涵
诸家学者关于咏史诗的定义,都没有侧重分析“史”的具体含义。因为“史”就是历史,这本无问题。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咏史诗中的“历史”的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从汉魏六朝咏史诗创作的实际来看,咏史诗的“史”应该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个层次,就是正史所记载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是咏史之史最标准、最直接的含义。所谓咏史诗,就是指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歌咏。萧统《昭明文选》所编选的咏史诗足可以证明这一观点。《文选》共收咏史诗21首,其中王粲的《咏史诗》和曹植的《三良诗》,所歌咏的是《左传》所载的“秦穆杀三良”的故事。左思的《咏史诗》8首,先后歌咏了贾谊、司马相如、金日蝉、张汤、冯唐、段干木、鲁仲连、张安世、扬雄、孔子、司马相如、许由。荆轲、主父偃、陈平、司马相如、苏秦、李斯等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及其生平事迹均见诸《史记》《汉书》等正史典籍。张协的《咏史诗》描写的是《汉书》中记录的“群公祖二疏”的历史事件。卢谌《览古诗》歌咏的是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智慧和勇气,取材于《史记》。谢瞻的《张子房诗》根据《汉书》的记载歌颂了张良一生兴刘安汉的功业。颜延年的《秋胡咏》描写秋胡戏妻的故事,取材自《列女传》。其《五君咏》则分别歌咏了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位贤士,均是取材于正史的记载。鲍照的《咏史》则歌咏了严君平安贫乐道,不慕富贵的高尚品格,严君平其人其事亦见诸《汉书》。虞羲《咏霍将军北伐》描写的霍去病征匈奴也是《汉书》所记载的正史。从萧统所编选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出,在编选者心目之中,咏史所歌咏的对象,一定是正史所载,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第二个层次,是传说中的古代事件和人物。仔细检索汉魏六朝咏史诗的创作,就会发现,诗人所歌咏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并不局限于真实发生的历史。正如清人李重华所论:“咏史诗不必凿凿指事实。”比如,曹操诗歌中反复歌咏尧舜禹汤等上古贤王,就是经过儒家历史化的传说中人物,而非真实人物;再如阮籍《咏怀》诗中所歌咏的湘妃等人物,是舜之二妃故事的神话化,在诗歌中也被当历史典故来使用;再如,王昭君的故事,虽然在《史记》《汉书》中有所记载,但咏史诗所侧重的“画工受贿”事件却出自小说家的《西京杂记》而非正史所载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诗家之“史”比史家之“史”的范围更加宽泛。这个历史的范围,可借鉴葛剑雄先生所提出的“历史信息载体”的观点加以理解。葛先生指出:“历史不仅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图画符号、语言文字、遗迹遗物、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都是历史赖以存在的手段。如果从广义上讲,这些都是包含着记载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人与事的信息载体,称为历史信息载体。”[9]
虽然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认定为历史信息载体,还需要具体分析,但咏史诗之“史”的第二层含义,应该包括广义的历史——历史信息载体。
第三个层次,咏史之“史”还可以指文学史上因为历代文人反复歌咏而形成的虚构的艺术形象,即文学创作传统堆积出来的“历史”。比如,齐梁之际,诗人所歌咏的“刘生”。刘生为何人?《乐府解题》曰:“刘生,不知何代人。齐梁以来为《刘生》辞者,皆称其任侠豪放,周游五陵三秦之地:或云抱剑专征为符节官,所未详也。”[10]通过详细研读现存的齐梁诗,可以知道,这一形象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根据汉代历史虚构出来的历史人物。但由于乐府和文人反复的歌咏,成为一个创作传统,也进入了咏史诗所歌咏的“史”的范围。这一层次的历史和神话传说是有所区别的。“历史信息载体”中的神话和传说,均有一定的历史根据或依托。比如前文提及曹氏父子乐府中歌颂的尧舜禹,虽然其真实性可能存疑,但在当时知识分子的思维体系和学术架构中,都属于真正的历史,是正史的一部分。再如王昭君和班婕妤的故事,虽然经后世加以想象发挥已经失真,但仍是以一定的历史人物为根据加以演绎的。这是和第三个层次所说的“文学历史”最不同的地方。如刘生、王昌,没有历史依据,完全是文学创作传统积累而成的形象。
综上所述,咏史诗之“史”,有三个不同层次的含义,对这三个层次“历史”的“咏”都应该算作咏史诗。这是咏史诗的内涵。接下来,我们从“咏”字入手,结合汉魏六朝咏史诗创作的实际,具体分析一下,咏史诗有哪些类型?
三、从“咏”的方式看咏史诗的类型
“咏”同“詠”。《说文解字》云:“詠,歌也。从言永声。”[11]本义是吟诵歌咏的意思,含有咀嚼不尽之意。前人解释咏史诗之“咏”多为记述和评论,并将直接铺叙历史的咏史诗视为“正体”,将评论历史、寄托自己怀抱的咏史诗视为“变体”。刘熙载概括为“传体”和“论体”两类。但是,这样的分类存在一个问题,有些咏史诗的创作,没有简单的铺叙历史事实,这就当然不能属于传体。但也很难说这些诗歌内部寄托了创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类咏史诗就很难归类。已经有学者看到这一问题,并且试图弥补其中的缺陷:如孙立将咏史诗分为传体咏史、论体咏史、比体咏史三类。李真瑜将咏史诗分为为感史诗、述史诗和议史诗这三种主要类型。但是,二位学者所分的类别的外延之间有所交叉,如比体咏史和论体咏史之间,感史诗和议史诗之间都很难区分。根据咏史诗创作的实践和当时文体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这一时期的咏史诗应该根据“咏”的不同角度划分为传体、论体、赞体三个类型。以下分别进行论述。
(一)隐括本传的传体咏史诗
传体咏史诗,是指采用纪传体的方法撰写的咏史诗。其基本的创作方法就是用诗歌的形式详细地复述历史事件的原委,可以看作是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的诗传,其中间或流露出作者个人的意见和判断,但并不占主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类咏史诗的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班固的《咏史诗》,此诗以叙事为主,细致描述了缇萦救父的过程:先叙太仓令有罪,被押长安;次写缇萦痛感父言,遂诣阙陈辞;再写文帝生恻隐之心,下令废除肉刑,后以感慨结之,赞扬缇萦胜过男儿。此诗以大量篇幅铺陈史事,过程详备,细节毕现,把缇萦救父事在七联十四句中娓娓道出。“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如果我们对比班固的《咏史诗》《汉书·孝文本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就可以看出“传体咏史诗”的特点。见表1[12]。
表1 班固《咏史诗》《汉书》《史记》中关于缇萦救父的歌咏与记载对比
班固《咏史诗》《汉书·孝文本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 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淳于意受赂,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 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于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 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 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路莫由。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 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文选》注引刘向《列女传》,缇萦伏阙上书时,曾“歌《鸡鸣》《晨风》之诗”。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上闻而悯其意,此岁即除肉刑法。 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仔细对读上表可以发现,班固此作,就是用五言韵语叙述史料。虽然,最后一句可能包含作者自己的情感在内,但根据篇幅的比例来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卢谌《览古》[1]1282的写法也是这样,这首诗主要描写的是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其诗云:
赵氏有和璧,天下无不传。秦人来求巿,厥价徒空言。与之将见卖,不与恐致患。简才备行李,图令国命全。蔺生在下位,缪子称其览。奉辞驰出境,伏轼径入关。秦王御殿坐,赵使拥节前。挥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连城既伪往,荆玉亦真还。爰在渑池会,二主克交欢。昭襄欲负力,相如折其端。眦血下沾襟,怒发上冲冠。西缶终双击,东瑟不只弹。舍生岂不易,处死诚独难。棱威章台颠,强御亦不干。屈节邯郸中,俯首忍回轩。廉公何为者,负荆谢厥諐。智勇盖当世,弛张使我叹。
该诗36句,前34句都是根据《史记》所记,用诗歌的形式叙述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的故事。甚至有些诗句都是直接化用《史记》的原句。虽然最后两句,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于蔺相如智慧和勇气的赞叹。但是从诗歌的整体来看,史传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传体咏史诗,是咏史诗最基本的类型,即所谓“正体”,这一做法肇始自班固,一直绵延不绝,成为咏史诗一个最主要的类型。
(二)寄予感怀的论体咏史诗
论体咏史,是指采用论说体的方法撰写的咏史诗。这类咏史诗的创作特色是,诗歌中不再单纯的叙述历史事件,而是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将历史事件的要点或人物的基本特点提炼出来,简要地表达自己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咏史的目的是借助历史事件或人物抒发自己的情感和寄托。也就是说,咏史,并非是为了记录历史,而是为了咏怀。这一类型的咏史诗最早可以追溯到曹操的《短歌行》[13],其诗曰: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崇侯谗之,是以拘系。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专征,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齐桓之功,为霸之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赐与庙胙。命无下拜,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圭瓒,秬鬯彤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威服诸侯,师之所尊。八方闻之,名亚齐桓。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
曹操在诗歌中,赞美周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而犹能臣服于殷朝的功德;宣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绩;称赞晋文公称霸不凌王室的功勋。其真正的目的,就是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这就是论体咏史的关键所在。如果说,曹操此诗中的个人情感还是隐藏在对于历史人物功业的评述之中,而左思所作,则将个人的情感倾注在各种历史人物之中,正式开创了论体咏史诗的艺术规范。左思的八首咏史诗,褒贬了古往今来许多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但他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完全都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程千帆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诗中史事,分然杂出,而细加条理,则友纪较然。析而言之,冯唐、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为一系。潜郎终身汩没,四贤初仕屯蹇,则作者所因为况譬者也。段干木、鲁仲连一系,佛酿成伸腿,爵赏不居,则作者所因为仰慕者也。许由、杨雄一系,当时尊隐,来叶传馨,则作者所因为慰藉者。苏秦、李斯一系,福既盈矣,祸亦随之,则作者所引为鉴戒者。独荆轲之事,若无关涉,殆可为寂寥中之奇想,而归本于自贵自贱,是与他篇固亦相通。”[14]咏史诗中的议论,与其说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感慨,毋庸说是左思的自况或者借以鞭策、鼓励自己的榜样和引以为鉴的对象。这类论体咏史诗,经过左思之手,成为后世咏史诗最常见的类型之一。
(三)起于“赋得体”的赞体咏史诗
赞体咏史,是指采用颂赞体的形式撰写的咏史诗,其写法起自南朝的赋得体咏史。之所以单独列为一类,是因为这类咏史诗具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和传体相比,这类咏史诗的区别在于,并不采用史传的方法仔细叙述历史的细节,而是用概括的语言一笔带过,具体说来,一般多采用对偶的句式,用高度凝练的词汇概括历史事件。
其次,与论体咏史相比,这些诗歌虽然也会表达出作者自己对于历史事件的意见、观点和看法。但是,这些情感只是在同题共作的情况下单纯地评论历史,表达对于历史人物的赞美或者评点,很难说寄托了作者个人的思想。
最后,这类咏史诗的创作场景,一般都是同题共作的集体场合。在南朝则多见于“赋得体”。赞体咏史虽然在中古咏史诗中所占数量不多,但也具有很鲜明的特点。如周弘直《赋得荆轲诗》[15]2466,其诗云:
荆卿欲报燕,衔恩弃百年。市中倾别酒,水上击离弦。匕首光凌日,长虹气烛天。留言与宋意,悲歌非自怜。
这首诗是歌咏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但诗歌的重点并没有放在易水送别、图穷匕见等具体情节的描写上,只是用概括的语言选取人物事迹中的几个典型特征组成对偶句虽然也体现了荆轲的“悲歌”慷慨之气,但很难说这和作者本人的情感寄托有什么联系。检点周弘直一生,历任国子博士、庐陵王长史、尚书左丞、兼羽林监、中散大夫、秘书监,职掌国史官署。升任太常卿、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而且得享天年,寿终正寝。他对于荆轲的歌咏,只是在“赋得”情况下的“命题作文”。很难看出自己寄托的情感。再如张正见的《赋得韩信诗》,其诗云[15]2491:
淮阴总汉兵,燕齐擅远声。沈沙拥急水,拔帜上危城。野有千金报,朝称三杰名。所悲云梦泽,空伤狡兔情。
诗中也是简要地赞颂韩信一生的功绩和英名以及知恩能报的品格,惋惜其“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但是,检点张正见的一生,诗人并没有这样的经历,《陈书》载张正见的仕宦经历:“幼好学,有清才。梁简文在东宫,正见年十三,献颂。简文深赞赏之……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国左常侍。梁元帝立,拜通直散骑侍郎,迁彭泽令。属梁季丧乱,避地于匡俗山……高祖受禅,诏正见还都,除镇东鄱阳王府墨曹行参军,兼衡阳王府长史,历宜都王限外记室,撰史著士,带寻阳郡丞。累迁尚书度支郎、通直散骑郎,著士如故。”[16]张正见一生虽然经历了梁陈易代之乱,但其仕宦经历确是一帆风顺,并无韩信式的遭遇。所以,他诗歌中结尾的两句,也只是人们对这一史实的常见议论。
根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除以上两首之外,南朝的“赋得体”咏史诗还有张正见《赋得落落穷巷士》、刘删《赋得苏武》、祖孙登《赋得司马相如》、阳缙《赋得荆轲》和徐湛《赋得班去赵姬升》。这些诗歌的创作场景基本类似,都是同题共咏。士人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赋咏普遍有一种“咏物化”的倾向,他们往往采用咏物的方式,摘取人物身上若干特点组成对偶句以扣住赋得的主题。诗歌缺乏对于历史人物事迹感同身受的情感。所以,他们对于历史人物的歌咏往往不具有“传体”的铺叙和“论体”的点评,而只停留在“赞体”的描绘上。
由上述作品可以看出,赞体咏史诗的创作,主要是要求扣住赋咏的题目,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基本特征概括出来,使人一望而知所赋为何人何事,结尾的评点和议论并不包含个人的情感,只是在同题共作场景下的命题作文而已。虽然在咏史诗的创作过程中,这种类型出现较晚,而且数量较少,但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型,对于唐代近体咏史诗有一定影响。
四、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根据“咏”的不同方式和“史”的不同含义,对咏史诗的内涵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本文认为应该从两个层次来界定咏史诗:狭义的咏史诗是指诗人用诗歌的形式,记录或者评论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广义的咏史诗是指,诗人通过诗歌的形式,对于真实历史、历史信息载体、文学史传统塑造的历史形象进行记录、评论或颂赞。
根据咏史诗创作的实际,咏史诗又可以分为:传体咏史、论体咏史、赞体咏史三种具体的类型。事实上,这种“三体并峙”的情况,在咏史诗的发展阶段中是一直存在的。
[1] 萧统, 吕延济. 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2] 何焯. 义门读书笔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893.
[3] 黄筠. 中国咏史诗的发展与评价[J]. 中国文化研究, 1994(4): 35-39.
[4] 郭丹. 论《昭明文选》中的咏史诗[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3): 67-73.
[5] 古远清. 论咏史诗及其创作艺术[J]. 青海师专学报, 1985(1): 57-61.
[6] 江艳华. 魏晋南北朝咏史诗论略[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4): 51-55.
[7] 缪钺. 略谈杜牧咏史诗[J]. 文史知识, 1985(7): 8-13.
[8] 李翰. 汉魏盛唐咏史诗研究——“言志”之诗学传统及士人思想的考察[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5.
[9] 葛剑雄, 周筱赟. 历史学是什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1.
[10] 郭茂倩. 乐府诗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790-791.
[11]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48.
[12]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05.
[13] 曹操, 夏传才. 曹操集校注[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3: 23.
[14] 程千帆, 莫砺锋. 程千帆选集[M]. 沈阳: 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6: 1208-1215.
[15]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G]. 逯钦立, 辑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6] 姚思廉. 陈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469-470.
10.15916/j.issn1674-327x.2021.03.022
I207
A
1674-327X (2021)03-0082-05
2021-01-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ZW050)
王帅(1989-),男(满族),辽宁沈阳人,博士。
(责任编校:叶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