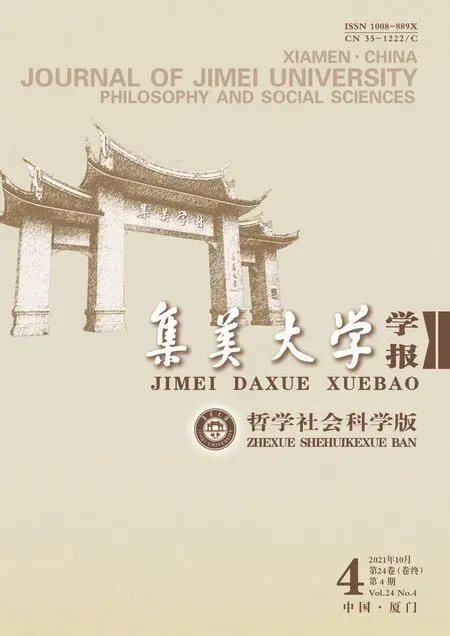跨学科视野下女性研究的新尝试
——兼论《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的借鉴意义
2021-11-29周海琳
周海琳
(集美大学 师范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中国古代女性的生活状况,在儒家经典著作的表述中常有矛盾。一方面,她们被描绘成处于高度封闭、遮蔽的状态;另一方面,在许多外部场所中又总有她们的身影。如《礼记》中虽有“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外内不共井”“男女不通衣裳”等区隔男女内外;但在祭祀仪式、日常居家生活或路途中,男女又难免会有交集:“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1]。这种矛盾并非偶然。许多研究在体例之外突兀存在着的古代女性,如宋朝的李清照,唐朝的上官婉儿,汉朝的班超、蔡文姬等,在历史“空白之页”[2]的表述中也是矛盾的存在。她们既有悖于主流叙述——女性在古代常被拘于闺中;又以自身的独特性不能被埋没,最后只能成为多数史著中的“特例”[3]。
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主流表述下,中国古代女性的生活与生存状态到底如何?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许曼博士,在其学术著作《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1)华人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历史学系副教授许曼,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英文著作Crossing the Gate,并于2016年在海外出版。该书2019年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刘云军译为中文——《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在国内出版。中创新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研究指出:尽管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整个帝制中国所有的女性,无论其所处阶层与时期如何,都有明清精英女性“由内向外的空间延伸,对个人、社会及公共领域界限的跨越”等能动性[1]。许曼的研究在中西方文化参照下、跨学科视野下进行史料梳理、空间建构与话语整合。通过阅读与比较原典,重新审视“闺阁”,尽量冷静客观地寻找门闾之外宋代女性的生活痕迹。她的这部著作试图从多个维度对已有研究进行反思与重构,审慎地得出结论。其成功探索给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以诸多借鉴。
一、整合史料,跨学科视野横向拓展
古代女子拘于深闺、足不出户的刻板印象源于许多男权意识较强的主流文字表述。实质上,要绝对化地实行起来却很难。文字表述只是考察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仅依据一类文字材料来断定古代女性的生活与生存状况,是片面的。史学研究需要多种材料的支撑。《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的视野并未拘于史学,或史学的近邻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除了广搜史学领域内地方志、考古报告等,它还构筑了一个巨大的跨学科群。这至少涉及建筑、交通、宗教、绘画、法律、经济、民俗等领域。由其参考文献即可见一斑:《黄泉下的美术》《中国绘画史上的女性》《性别的物质化》《性别和死亡考古学》《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近代中国妇女史》《礼记正义》《毛诗正义》《朱子文集》《朱熹的〈家礼〉》《宋刑统》《宋代的家族与社会》《福建宗教文化》《营造法式》《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等。另外还有大量未出版的“福建宋墓发掘报告”等。
它并非平行地堆积史料,而是跨界组织素材、整合史料,寻找突破口与交集。如,内室与外室、家与外界的结合处——中门、闾;男性对女性的柔性评价处——私人书信、墓志铭、墓室绘画;女性嫁妆与陪葬品的关联;以女名命名的井、路、桥、果等;官府中女性作为原告、被告、主犯或从犯的案件;杀婴习俗中的杀害者与被杀者等等。其视野之宏大,体量之惊人,至少在门里门外、地上地下、官方民间、世俗宗教、理念实际、今生来世等六个方面实现了贯通。在如此视野下,研究者既进行了传统的实打实的史学田野考察,又进行了宏观的设计、史料组装,成功构建出宋代福建女性在家庭内外的生活状态。无怪乎美国学者高彦颐从多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这题目的难处,不光是文献史料缺乏,更因为过去研究者往往对理学的伦理规范过于重视,抱了先入为主的成见,无法对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所享受的自由空间有正确的认识。许曼从墓葬壁画、陪葬品等图像和实物材料,结合大量零散的各类文献,清楚显示了宋代女性实际生活和儒家理想之间的落差,也让读者认识到文献史料本质上的局限。”[1]跨学科多维视野的史料收集与整合,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
二、创新思维,多种经验纵向对话
就学术研究而言,各时代学术研究自有其建树。已有研究被发现不足且被更新,也在情理之中。但对已有研究不足的指陈之“破”是起点,并非最终解决之道。在新的视野下,冷静地质疑、理性地兼收并蓄,是一种学术担当。许曼的研究并未完全解构、推翻关于中国古代女性研究的结论,而是在对话中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其研究既不钻中国古代史研究埋头考据的牛角尖,也不以“洋气”的理论虚张声势。兼收并蓄中,处处体现出传统研究重史料“密针线”、中外理论“巧结构”两结合的扎实功底。新旧研究间互通款曲,不截然对立。既显示原有研究的历史性,又显示新研究的时代性;既是新研究本身,又有研究史述的意味。
(一)整体思维赋予“日常生活”尊严
该研究赋予日常生活史料以尊严,并借助这些史料结构起了一个丰富的女性想象空间。除了精英女子,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其他女子。如,杀婴行为中的婢女、稳婆;捐桥、捐路、捐井的女人;冠名荔枝的女人;享受祭祀的女神;女恶霸;诉讼中的女原告和女犯;教育儿子或丈夫当官的女人;通过纺织挣私房钱的女人;化身尼姑复仇的女人;财产继承争夺中的寡妇等。她们是具有能动性的,与多数文献中所描绘的拘于家门之内无主张的、少智慧的女性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有相当大的反差。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日常生活诗学的核心内涵,是揭示日常生活内部所蕴藏的各种微妙繁富的生命镜像,重构人类身与心、人与物的统一性。”[4]研究者从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而非纯粹的文字表述入手,目光由象征着家庭荣耀的“中堂”转向了为人进出的“中门”等,“解围”了多学科研究中“被困”的古代女性。日常生活小中见大的视角,规避了观念先行的宏大研究弊病,给人以启发。
(二)创新思维引领新研究与新思考
该研究中处处可见创新,如跨学科研究方法、性别研究视角、比较研究视野等。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打破边界”[5]的跨学科研究是时代的趋势。从追求日常生活史实,到合理推导心理世界、来世想象,由此岸世界过渡到彼岸世界等,该研究巧妙地吸收了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跨学科重构女性生活与生存史,重视日常生活实证与推理研究,修正了原来对于女性生存状况等的表述。性别研究视角虽已不再新鲜,但大量存在于古代文化研究中的性别偏见赋予了其创新性。因为新的研究不得不跳出原有轨道去寻找新风景。而比较研究视野,使得已被研究过的原典、已被叙述过的“深闺”等具有了重新被研究、阐释的可能。
这部断代的区域女性史以创新思维,着眼于整体研究,着手于细部史料,两种方法杂糅,既避免了整体宏观研究的大而无当,又避免了微观研究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它对多地域多时代同类史学研究很有启发。又因史学研究的基础性,它也将影响到许多方面。如文学研究因此获得了更多重新判断、阐释、归类女作家文学作品的契机。文学史研究者也可反思古代“空白之页”的表述与“例外”女作家在体例上的悖论。此外,它还拓宽了女性角色在文学创作中的生存空间。作家们可对古代女性日常生活场景有诸多补充,可以表现更多更丰富的主题。
三、融汇理论,打开研究新局面
从“空间”的角度探索宋代妇女的日常生活,营造多重“空间”对话,使该研究极富特色。上述门、闾、墓志铭、井、桥、文本等不同空间的实物,构建了许多物理空间和想象空间,给人以无尽的生成性构想。
空间这个日常存在,时刻与人息息相关。20世纪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它“超越了这种单纯的、物理性的、自然的涵义。”[6]实际上,空间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学者陆扬在《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一文中梳理了西方学者对空间认识发展的三个阶段。概言之,“第一空间认识论”偏重于客观性和物质性,力求建立关于空间的形式科学,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与环境的地理学等。“第二空间认识论”注意力集中在构想的空间。它从构想的地理学中获取观念,进而将观念投射向经验世界,因而更多是反思的、主体的、内省的、哲学、个性化的活动。“第三空间认识论”既解构又重构前二者的认识论,在质疑它们思维方式的同时,又向它们注入新的可能性。它既不同于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又包容两者,进而超越两者[7]。美国当代空间理论学家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有着无穷的魅力和“开放性”[8]。它重新认识了既在全体之中又在主体之外的“边缘”;打破了此前中心与边缘、里面与外面的二元对立关系;通过发现边缘性,进入另一个压迫者看不见的第三世界;而边缘是一种主动选择,它可以保持本色,而不指望他者来承认自己;在边缘坚持自己,体现自身的主体性,从而实质上颠覆压迫者的中心地位[8]。
带着这种对空间理论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清醒认识,便能发现许曼研究中的“空间”秘密。研究者既竭力搜罗家庭、建筑、邻里、村落、城市等传统空间理论所着力的考察对象,又从哲学、文学、宗教、法律乃至经济的、政治的文本中去探求和对照、反思各时代人们的想象空间。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建筑空间与文本空间、理念空间与现实空间、封闭空间与开放空间、单一空间与多维空间之间产生了多重的对话关系。既处处有冲突和反叛,又具有互文性,共同生成无数新的内涵。作者又通过关注与挖掘那些边缘性的存在,重新展示了宋代那些中门之后静室之中思考、写作、生活的女性,或者游走、行动于门闾之外的诸多日常生活中的女性。她们虽无进入主流的入场券、未被打上主流的印记,却保持着一种自在的状态,很多时候与主流性别文化相安无事。
耐人寻味的是,该研究中还多次反复呈现了一些富有同情心和较有开放思想的男性如朱熹的研究材料。反讽的是,作为官员和鸿儒的朱熹在男权主流性别文化中,是一个建构者,是女性居内生活和被动生存方式的规约者。但在非官方的私人生活空间,如私人信件、宗谱序文、墓志铭等中,他却是一个自我的反叛者。他同情女性的际遇、包容女性的行为,甚至以自己的实践鼓励或影响别人在处理涉及女性的事务中保持开明或妥协。这些矛盾得以相融且解释合理,得益于“第三空间”开放性的魅力。可见,融汇理论,可以给研究带来意想不到的新突破。
四、文明互鉴,探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话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9]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包含学术交流在内的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的广度与深度。但中外文化交流却难说是平衡的。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输入远大于中国文化向西方文化的输出。其原因,向归于近代以来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时间上的先进,却缺少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学术研究)现代转型应有的理性反思。其结果,是在当代中外文化交流对话中显示出了同样的不平衡性。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中西方都不乏市场。崇洋媚外,体现在各种文化交流中。这与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定位是不合拍的。
2020年,中国实现全面脱贫进小康后,精神“脱贫”——文化自信建设刻不容缓。2017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就颁布了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其中“研究阐发”被置于首位[10]。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研究和再阐释,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系统工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如何重新阐释从而复兴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继续在居高临下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中复制、模仿、套用已不合时宜。百年前由胡适及北大学者等倡导的“以西方的哲学框架,形塑中国的历史资料”[11]的“整理国故”运动,终因内忧外患的国情,在学术研究方面未达到理想的境界:“启蒙与学术交叠变奏,最后启蒙压倒学术”[12]。今日研究能有条件借助多学科的深耕研究以及新的技术整合史料,展现新貌,可以有所作为。许曼的研究个案,以贯通的宽阔眼界、纵横的精心结构、中西合璧的整合叙事,既丰富了宋史与女性史的研究,又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研究,在视野、理念、方法等方面都具特色,能给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诸多有益启发。学者们应立足本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以平等的文化心态与文化自信广泛吸收和充分利用海外汉学研究的新成果、新方法,在跨学科的视野下探索、活用,建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学术研究话语。是为新时代学者应有的学术自觉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