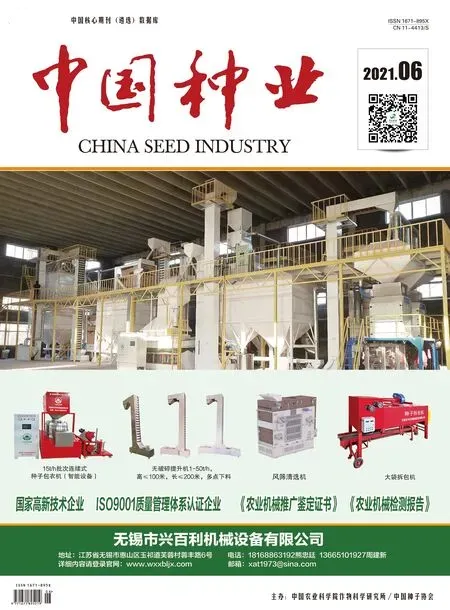论品种出口权的域外效力
——以新西兰Zesprit 案为视角
2021-11-29李东海李佳禹
李东海 李佳禹
(1 青岛农业大学,山东青岛 266109;2 东北农业大学,哈尔滨 150030)
UPOV 公约1991 文本增加了品种权的内容,规定出口受保护品种的行为需要征得品种权人的许可。虽然出口权并非品种权所独有之制度,如专利权、商标权中均有关于出口权的规定,但是Zesprit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将行为人的域外收益作为计算赔偿数额的依据,在某种程度上使品种出口权具备了域外效力。该案将成为国内法域外适用向植物新品种保护领域渗透的标志性事件[1]。在国际种子贸易日益发达的背景下,有必要对品种出口权的适用条件、效力范围、救济措施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种子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支持。
1 案情概要
Zesprit 公司为G3 和G9 猕猴桃品种的权利人。2016 年Zesprit 公司向新西兰法院起诉高浩宇、薛琴以及Smiling face 公司,称3 被告未经许可向中国境内出口G3 和G9 的繁殖材料。目前查明在中国G3和G9 的种植面积已达174.2hm2。
新西兰高等法院在判决书中承认在新西兰现行法律框架下,品种权人并不享有专有的出口权,但是考虑到新西兰已于2019 年底批准了CPTT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新西兰将在3 年内批准适用UPOV 公约1991 文本,而该文本中规定了品种的出口权。同时,法院援引Cropmark Seeds Ltd v Winchester International(NZ)Ltd判例,认为:“任何具有削弱权利人专属效果的行为都构成品种权侵权行为”。任何未经Zesprit 公司许可出口G3 和G9猕猴桃品种的行为都有可能(Potentially)损害其品种权,所以本案被告出口G3 和G9 猕猴桃品种的行为侵犯了Zesprit 公司的品种权。
考虑到Zesprit 公司在中国同样拥有G3 和G9猕猴桃的品种权,Zesprit 公司的损失可以在中国获得救济,最终新西兰高等法院以Zesprit 公司在新西兰许可费标准的50%确认了总额为$14894100 的赔偿数额。
新西兰Zesprit 公司案件的特殊性在于法院不仅对发生于新西兰境内的行为进行了评价和定性,同时还对发生于中国的相关行为进行了评价,并以此作为确定侵权赔偿数额的依据。本案判决突破了知识产权独立性和地域性原则,在我国以UPOV 公约1991 文本为修法目标的背景下,品种出口权的效力及救济措施尤其值得关注。
2 值得思考的问题
2.1 品种出口权的效力分析知识产权的独立性和地域性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基本原则。一般而言,知识产权不具有域外效力,一国政府授予的知识产权仅在该国地域范围内有效,同一知识产权客体在不同国家所受保护是相互独立的。作为知识产权体系中的一员,品种权同样受到地域性的限制,一国授予的植物新品种权仅在授予国的地域范围内有效。由于品种的出口涉及到受保护品种的跨国界流通,品种出口行为的效果通常发生在进口国境内。如果品种出口权仅针对发生于出口国境内的行为,并且仅在出口国市场范围内计算品种权人的损失,那么基于品种权的独立性和地域性,进口国与出口国为相互独立的市场,品种权人在进口国市场所蒙受的损失就不能够通过在出口国的司法系统获得赔偿。如果品种权人基于品种出口权可以对发生于进口国境内的损失获得赔偿,那么就涉及到品种出口权域外效力问题,即品种出口权在何种条件下、何种程度上具有域外效力,这种域外效力是否会对品种权的独立性和地域性构成冲击?在制度上应当如何予以协调?在实践中应当如何应对?
2.1.1 品种出口权制度的立法目的从品种出口权的立法目的来看,出口权制度并不以国内市场为主要关切对象。因为如果要保证品种权人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保证品种权人的国内市场利益,既有品种权保护制度的规定已然足矣。品种出口权的直接调整对象是出口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该出口行为不会对品种权人在国内市场的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由此可见品种出口权制度所关注的必然是品种权人在国外市场的利益,为实现对品种权人国外利益的保护,品种出口权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具备域外效力,能够就品种权人因品种出口而在国外所蒙受的损失提供救济,否则品种出口权的规定便失去了意义。
UPOV 公约第14 条规定了品种出口权,但是并未对出口权的效力范围进行解释。为明确品种出口权的域外效力,UPOV 公约在第16 条“权利用尽”条款中特别规定了出口权例外条款:“品种的繁殖材料经品种权人许可投放市场之后,针对该繁殖材料进一步的生产、销售以及进出口等行为不再受品种权的限制;但是将该品种的繁殖材料出口至不保护该品种所属植物或种类品种的国家时,除非是以最终消费为目的,否则该出口行为依然需要获得品种权人的许可。”
2.1.2 品种出口权的适用分析从UPOV 公约的规定来看,品种出口权的效力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理解。
首先,从出口品种繁殖材料的来源看,虽然公约对用于出口的品种繁殖材料来源的合法性并未加以限定,但是非法获取繁殖材料的行为本身即具备违法性,针对非法取得的繁殖材料的出口行为其违法性自不待言。因此,在UPOV 公约的语境下,用于出口品种的繁殖材料其来源应当是合法的,即是由品种权人或经其许可投放于国内市场的。
其次,从出口的目的国来看,就合法取得的品种繁殖材料,品种出口权所涉地域范围是不保护品种所属植物种属的国家,已有相关品种权保护制度的国家不受出口权的限制。只要进口国对相关品种提供保护,那么无论出口品种在进口国是否获得授权,针对该国的出口行为不受品种出口权的限制。
最后,从出口的目的来看,当合法取得的品种的繁殖材料出口至不保护该品种所属植物种属的国家时,除以最终消费为目的的出口行为外,其他任何出口行为均应征得品种权人的许可。此一规定不仅排除了以商业应用为目的的出口行为的合法性,同时也排除了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出口行为的合法性。换言之,此种情况下品种出口权不受农民特权和科研行为的限制。
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澳大利亚育种者权利保护法案以及日本种苗法关于品种出口权的规定与UPOV 公约基本一致。韩国品种保护法关于品种出口权的规定与UPOV 公约略有不同,授权品种的出口仅在为非繁殖目的的出口时,才适用品种出口权用尽;任何繁殖目的的品种出口行为均构成对品种出口权的侵犯。与UPOV 公约相比,韩国品种保护法并不考虑进口国的品种权保护情况,明显扩大了品种出口权的适用范围。
从UPOV 公约和各国立法情况来看,立法者并未直接限定品种出口权的效力范围,只是将品种出口行为置于品种权人的控制之下。至于品种出口权是否会对出口人的域外行为产生影响,或者出口国是否对域外侵犯品种出口权的行为具有管辖权,则取决于国际司法的一般规则和各国所承担的国际条约义务。
2.2 品种出口权的救济所谓“无救济,无权利”,品种出口权的效力还表现为当出现侵权行为时,授予品种权的国家的司法体系能够为权利人提供怎样的救济手段。品种出口权的域外效力与救济途径和救济效果密切相关。UPOV 公约并未涉及具体的或者特殊的针对品种出口权的救济方式,在规定了品种出口权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也并未对侵犯品种出口权的救济方式做出特别规定。从这一事实来看,侵犯品种出口权的救济模式与其他类型侵权行为救济模式并无二致。
一般而言,侵犯品种权主要有两种责任承担方式,一是停止侵害,二是赔偿损失。停止侵害关注的是对侵权行为的事先预防和事中阻止;赔偿损失关注的是对权利人所受损失的弥补和对侵权行为人的制裁。
2.2.1 停止侵害与品种权的域外效力停止侵害针对的是正在发生的侵害行为以及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侵害行为的制止,时间性要求较高。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对《侵权责任法》的释义都明确说明,停止侵害针对的是行为人正在或者继续侵权的情形,对于已终止的侵权则不能适用[2]。品种出口权针对的是受保护品种的出口行为,由于出口行为持续时间较短,品种权人行使停止侵害请求权的时间窗口十分有限,品种权人存在难以及时发现、及时制止的现实困难。
此外,品种出口行为虽然发生于出口国境内,但是出口行为对品种权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却发生于进口国境内。如果品种权人能够及时制止非法出口行为,那么损害结果尚未发生,自然没有赔偿损失存在的空间;如果品种权人未能及时制止非法出口行为,出口行为已经结束,那么停止侵害就没有适用的余地。对于发生于进口国境内的损害结果,停止侵害不具有弥补品种权人损失的效力。
品种权的地域性决定了如果一品种未曾在一国被授予品种权,则在该国有效管辖范围内即不存在针对该品种的品种权,自然也没有依据进口国法律予以制裁或者救济的可能性。如果一品种已在进口国被授予品种权,则品种权的独立性决定了该品种权与出口国的品种权并非同一财产权,而应由进口国的品种权人就其进口行为行使权利。由此可见,无论出口的品种在进口国是否受到品种权的保护,作为出口国的品种权人都没有在进口国主张权利并获得救济的资格,即便品种权人在进口国和出口国同时享有品种权,其在进口国寻求救济的权利基础也不是其在出口国的品种权,而是其在进口国享有的品种权。行为人侵犯的也不是品种出口权,而是品种进口权。由此可见,如果品种出口权不具有域外效力,那么其救济措施就只能停留在停止侵害阶段,无法提出损害赔偿的诉求,因为损害结果并非发生于出口国境内。品种出口权的效力若仅止于此,其作用聊胜于无。
因此,如果品种出口权不具有域外效力,不能够就域外损失主张赔偿,那么品种出口权的停止侵害至少不应当仅限于正在发生的出口行为,还应当指向未来可能发生的非法出口行为,使得品种权人可以通过诉讼确立一项面向未来的针对侵权行为人的出口禁令。
2.2.2 赔偿损失与品种权的域外效力就赔偿损失而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行为人的域外收益是否可以一并计入权利人的损失,如果将行为人的域外收益计入到权利人的损失数额当中,则出口权变相地拥有了域外效力,有违司法礼让的一般原则。如果行为人的域外收益不能够计入到赔偿损失的数额范围内,那么出口权救济措施仅仅是在海关阶段的停止侵权,品种权人难以获得实质上的救济,品种出口权名存实亡。
依据UPOV 公约的规定,如果品种出口权所涉进口国对相关品种不予保护,那么出口行为在该进口国不被认为是侵权行为,也不存在就品种权人在该进口国市场所蒙受损失获得进口国司法救济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品种出口权仅限于在出口国境内对出口行为的限制,因出口行为导致的品种权人的损害是否可以以品种出口权为依据进行赔偿,则涉及到品种权的域外效力问题。如果出口权不具有域外效力,那么就无法实现对于出口权的救济,有关出口权的规定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从逻辑上分析品种出口权天然地应当具有域外效力。
在出口的品种来源合法的情况下,无论在进口国是否存在有效的品种权,也无需考虑进口国的品种权人与出口国品种权人之间的关系,只要该进口国保护进口品种所属植物种属,按照UPOV 公约有关权利用尽条款的规定,此时相关品种的出口权已然用尽,既不存在侵犯出口权的问题,也不存在赔偿损失的问题。只有在进口国不保护进口品种所属植物种属,且出口并非为最终消费目的的情况下,才有出口权适用的空间,此时品种权人在进口国市场上因出口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应予赔偿。
在出口品种来源非法的情况下,则无需考虑进口国的品种保护情况,可以直接适用出口权予以规制,品种权人因出口行为所受域外损失应予赔偿。
在域外损失的计算方面,如果进口国已有相关品种权,且与出口国品种权人相同,则根据司法管辖权国际礼让原则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应允许品种权人以放弃进口国索赔权为前提,由出口国判令赔偿。如果进口国已有相关品种权,但与出口国品种权人相异,则出口行为在进口国不会对出口权的品种权人产生实际损害,故不存在域外损失也不存在损害赔偿问题。
法律的域外效力一般是指法律在本国管辖范围之外产生确定拘束力。从实践情况看,国内法域外适用一般表现为国家针对本国管辖领域之外的私人主体适用本国法的行为。而一旦国家通过国内法确立对域外行为的管辖,域外适用就有了国内法依据,其结果就是本国国内法产生域外效力[3]。而划分法律域内效力与域外效力的标准是被规制行为的发生地[4]。品种出口权体现的是权利人对于品种出口行为的控制权,其本质尚属一国国内法管辖范围。但是本案中新西兰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将发生在中国境内的行为作为计算依据,从结果上看使新西兰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具有了域外影响力。由于新西兰是判例法国家,此一判例开品种出口权域外效力之先河,相关市场主体将不得不在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中审视品种出口权所带来的法律风险。
2.3 我国植物新品种出口权的适用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中也增设了品种的出口权,但是既没有规定品种权的权利用尽制度,也并未对出口行为的目的加以区分,同时对于进口国的品种权保护情况也未做规定。相关规定的缺失为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有必要予以分析和明确。
2.3.1 出口权国内用尽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体系下,针对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生产(繁殖)、销售和(或)许诺销售、为前述目的的种子处理、出口和进口以及相关的收购、存储、运输行为,均需征得品种权人的许可。由于不同行为彼此之间相互独立,所以当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经品种权人许可进入流通市场后,原则上品种权人不能够对后续的利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进行限制,这是知识产权权利用尽制度在品种权制度中的体现。
知识产权权利用尽制度在理论上包括国内用尽和国际用尽两种情形,如果用尽的范围是国内用尽,那么合法获得的品种的出口则有可能构成对出口权的侵犯;如果用尽的范围是国际用尽,那么合法获得的品种的进一步出口则不构成对出口权的侵犯。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分析,如果采用国际用尽原则,那么品种出口权并无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由此可以推论,品种权体系下权利用尽其用尽范围是国内用尽,惟其如此,品种进出口权的规定才有实际意义。
品种权是否适用权利用尽仍有待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进一步确认。目前在缺少关于品种权权利用尽具体规定和理论储备的前提下径行规定品种出口权,对农产品进出口企业的正常国际贸易行为构成了潜在的法律风险。
2.3.2 不存在域外品种权品种权所具有的地域性决定了品种权国际保护的独立性原则。相同品种在不同国家所获保护是各自独立的,各国依据本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径行保护而无需考虑授权品种在他国的保护情况。
品种出口权涉及品种的海外市场,如果在进口国针对授权品种存在真实有效的品种权,那么无论该品种权是否与出口国品种权的权利人相一致,品种的出口均不会损及品种权人的海外利益。因为,如果出口国和进口国为同一权利人,那么品种权人大可以其在进口国的品种权为依据,针对进口行为予以规制并获得赔偿。如果出口国与进口国的品种权人不一致,那么即意味着品种出口并未损及品种权人在进口国的市场利益,因为该市场并非出口国品种权人具有垄断权的市场。
由此可见,只有在进口国不保护出口品种时,出口国品种权人的市场利益才会遭受损失。因此,品种出口权的保护应当将进口国对授权品种的保护情况作为考量因素,以进口国对授权品种不提供保护为救济出口权的前提。
2.3.3 非繁殖目的出口在品种出口权体系下,以繁殖为目的的出口行为应当予以禁止,因为繁殖会产生新的品种个体;以消费为目的的出口行为由于其不会产生新的品种个体,属于权利用尽的范畴,故不受品种出口权的限制。
受植物生长繁殖的特性所限,植物的果实往往兼具收获材料和繁殖材料双重身份。随着生物技术的发达,植物细胞全能性理论的提出进一步模糊了收获材料和繁殖材料的界限。依据该理论,即便常规情况下不被用作繁殖材料的收获材料,其本身也具有繁殖的可能性,也可以被用作繁殖材料。因此在具体的案件中,涉案材料到底是收获材料还是繁殖材料,往往只能够以其实际应用的方式进行区分,同时需要结合品种的常规繁殖方式、交易习惯以及交易对象等进行确定。
3 结语
UPOV 公约1991 文本规定的出口权并不必然赋予国内品种权人于授权国领域外行使权利的空间。新西兰法院的判决也并未突破品种权的地域限制,只是将品种权人所蒙受的域外损失作为判定侵犯品种出口权所需赔偿损失的酌定标准。可见品种出口权并不具备域外实施效力,但品种出口权的规定可以使品种权人在域外的损失获得“域内救济”,正如本案所表明的那样,域外损失可以通过品种出口权的规定,使侵权行为人为此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