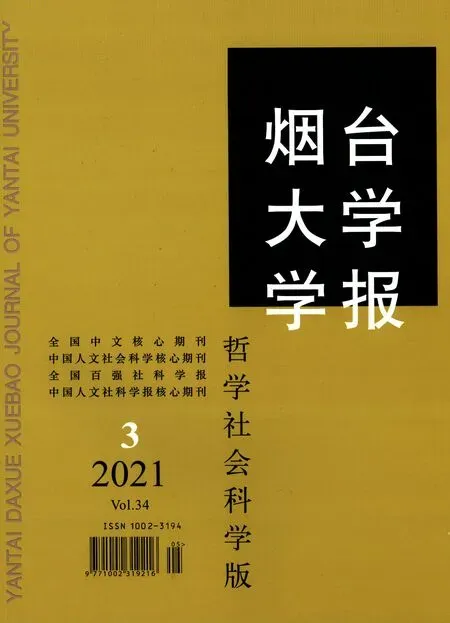理念、机体与消解
——辨析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学说批判的有效性
2021-11-29薛丹妮
薛丹妮
(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上海 200025)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要以黑格尔思辨哲学方法与黑格尔国家学说为批判对象:目前关于前者的“颠倒”指控研究颇丰,笔者以为马克思此一批驳是尚未摆脱费尔巴哈自然唯物主义哲学观影响的产物,很快就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立场的清算中被扬弃;关于后者的批判,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政治国家”及“真正的民主制”等概念的提出,掀起了消解资产阶级国家、证成共产主义社会思想与实践的序幕,意义深远却常被忽略。“很少人有冒险撇开致力于费尔巴哈颠倒方法应用的段落分析该文本……然而,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文本中关于黑格尔的批判却远比颠倒因素多得多。”(1)Gary Teeple,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s 1842-1847,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4, pp. 47-48.虽然近年对后者研究有增进趋势,但大多通过强调黑格尔国家学说中等级要素自身规定与其中介作用的矛盾性,直接确认马克思关于黑格尔国家学说整体是“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页。的批判:“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设置的等级要素的矛盾性……提出了自己民主制的立法权思想”(3)李淑梅:《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代议制因素的批判》,《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忽略黑格尔国家机体与国家理念的区分及马克思批判的有效性范围;或有注意理念之于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但只强调国家学说整体之于理念发展的环节意义,亦即“理念的发展经历了逻辑、自然、精神三个阶段……国家是伦理精神的统一形态”(4)潘斌:《理性国家的辩证想象:黑格尔国家观的创制逻辑与批判》,《现代哲学》2018年第1期。,主张黑格尔国家观本质就是一个矛盾综合体。
本文撇开颠倒因素,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文本中关于黑格尔国家学说本身的批判为对象,主张该学说包括国家理念即统一普遍和特殊与国家机体即等级代议制两个面相,马克思批判主要对后者有效。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国家机体的中介设置,包括作为直接和解中介的农民等级与作为间接和解中介的立法权等级要素的无效性与矛盾性,未能完成黑格尔原初赋予其调节现代世界市民社会(特殊)与政治国家(普遍)分立的使命;马克思继而提出真正的民主制方案取代之,通过将国家职权消解于社会全体,直接取消分立两极。常被模糊的黑格尔国家理念,则在马克思有效批判范围之外,因为它不仅是马克思真正的民主制方案的主要旨趣,而且具有多重积极意义,包括其对古代直接伦理型国家理念与现代意志契约型国家理念的超越,及其坚持以自在自为的意志为国家原则分析古典民主制之于现代世界的不可能性,间接开启符合现代世界的民主制道路。
一、黑格尔国家理念:统一特殊和普遍
黑格尔哲学要义之一是明晰现代世界原则(即主观特殊性原则)及其引发的现代世界分立即市民社会(特殊)与政治国家(普遍)对抗,并试图在包容现代世界原则基础上解决分立实现具体自由。现代国家,即“自在自为的国家……是自由的现实化”(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58页。,是黑格尔为统一现代世界分立两极所设中介;它包括国家理念与国家机体两个面相,前者是国家的本质环节与内在根据,后者是国家的具体制度与外部规定,并且黑格尔强调,“在谈到国家的理念时,不应注意到特殊国家或特殊制度,而应该考察理念”。(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259页。换言之,黑格尔国家学说要义不在个别国家机体,即无关具体国家制度选择与构建问题,而在于国家理念。
古代直接伦理型国家理念,特殊与普遍蒙昧同一;特殊个体尚未从普遍共同体中独立出来或不被承认,自然直接地遵循共同体法律习俗并以之为自身第二天性与全部生命本质来源,主体意志没有作用空间。现代意志契约型国家理念,特殊与普遍分离对立;依主体意志引导,普遍被把握为特殊实现私利达成的工具关联与形式统一,作为凌驾于特殊之上的政治异物调控统治着特殊。黑格尔国家理念超越前两者,旨在允许特殊与普遍充分发展基础上实现具体统一;特殊与普遍的现实性均建立在对方之中,并且互为目的,互相转化。“国家的理念具有一种特质……普遍物必须予以促进,但是另一方面主观性也必须得到充分而活泼的发展。只有在这两个环节都保持着它们的力量时,国家才能被看作一个肢体健全的和真正有组织的国家。”(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261页。不过,这一理念未能实现于黑格尔国家机体,即他建议的等级代议制中,马克思由此提出真正的民主制,主张“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才是解决世界分立,实现作为社会物质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有机统一体的现代尘世生活,从而完成人的解放的最恰当国家制度。“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迷。”(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
要言之,超越古代特殊与普遍蒙昧同一的伦理型国家理念及现代特殊与普遍分离对立的契约型国家理念,以统一特殊与普遍为旨趣,并最终被扬弃融贯于马克思真正的民主制方案中,是黑格尔国家理念的积极意义之一。此外,黑格尔在坚持卢梭关于公意与众意区分基础上,把公意规定为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并以之为支持其国家理念的意志原则,分析基于众意原则的古典民主制之于现代世界的不可能性,间接开启符合现代世界原则与国家理念的民主制道路,是为积极意义之二。
黑格尔以为,卢梭为探求现代国家理念作出了贡献,即“提出意志作为国家的原则”(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254页。,要求作为普遍的国家融含特殊,允许个人在一切方面以自己意志为决定根据;与马克思基本主张相合,即“在民主之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公意,即公共意志,作为现实意志本身具有真正普遍性;众意,即全体意志,作为主观意志总和只具有形式普遍性。卢梭先是明确主张以公共意志为国家原则,不论它是否符合大多数或全体意志,甚至全体在他看来“常常是并不知道自己应该要些什么东西的盲目的群众”(11)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8页。。“每个个人作为人来说,可以具有个别的意志,而与他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公意相反或者不同……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12)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24页。然而,卢梭稍后又将公意定义变更为“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13)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136页。,要求全体成员出席制定社会规约的人民大会,且“要有全体一致的同意”,与原初目标背道而驰。卢梭的全民参政与全体意志要求来自古典民主制:一切国家法律与社会规约须由公民大会规定,所有公民到场就某项提议做出表决;国家主权权威来自于全体公民意志,不包含在独立于全体的任何部分之中。他一方面以对公共意志丧失信心为前提要求全民参政与全体意志,一方面又认为全民参政与全体意志可达成公共意志,自相矛盾。
黑格尔首先提示,在现代世界,似卢梭般主张“实现每个自由人应参予决定和讨论普遍国家事务的理想是完全不可能的了”(14)黑格尔:《黑格尔政治著作选》,薛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33页。。因为,古典民主制以美德为城邦原则(1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徐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2页。,亦即古希腊城邦是道德政治共同体,道德与政治直接同一,政治生活就是道德生活,个体参与政治生活并遵从共同体规定同时就是在践行美德,就是古人追求的至善与幸福,全体公民大会因此可能。与之不同,现代世界以主观特殊性为原则,个体独立自主化,利益与贪婪渐入人心,理所应当地接受共同体规定并以之为自身隐得来希的古典式德性逐渐弱化,直至私人领域被确认并与公共领域彻底分立,无可能再现古典民主之美。以黑格尔时代的德国为例,一个公共领域与国家权力被私人分解了的国家,以私法为主,专注私利,严重缺乏政治意识与共同意识;不但不保证全体公民出席大会,而且即使出席,也不排除有选举冷淡表现。“在帝国时代,民主就不仅是未曾实现的,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实现……发现一种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相称的民主。”(16)斯坦利·阿罗诺维茨等主编:《控诉帝国》,肖维青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3页。
黑格尔继而批判卢梭之所以有上述古典民主制式要求是因为没能坚持区分公意与众意,其公意本质仍是众意,不可作支持现代国家理念的意志原则。因为,如果让众意泛滥,即以全体意志为原则或依靠纯粹主观意志集合,不但使国家政制与法律沦为偶然任意的契约结果,而且还可能会带来法国大革命式的极端个人主义动乱或多数人暴政,现代国家理念无从实现。“决不能把普遍的意志看成由一些表现出来的个别意志组成的……凡是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的地方,就没有自由……国家并不是那样一种包括个人任性的联合。”(1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4页。因此,黑格尔进一步把公意规定为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区别于完全特殊性意志与纯粹主观性意志对自身真理性的直接确认,它否定性自我相关,即是获得客观性的主观意志与获得普遍性的特殊意志,是意志理念的现实。“意志在自我规定之先,在这种规定被扬弃和理想化之先,不是某种完成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意志只有通过这种自我中介的活动和返回到自身才成为意志。”(1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18页。只有此种意志才能作为国家原则支持作为特殊与普遍真正统一的现代国家理念,其本身即具有现实性与合法性,与意志主体参与人数无关,无论是一个人、多数人还是所有人。
二、黑格尔国家机体:等级代议制
黑格尔规定,国家理念的直接现实化,是“作为内部关系中的机体来说的个别国家—国家制度”;并且,凡现实的东西在其自身中都是必然的,即作为统一体,依据自身理念分解为内部各环节以不断发展成就自身。“国家机体……就是理念向它的各种差别的客观现实性发展的结果……(因为这些差别是概念的本性规定的)、合乎必然性的创造着自己……这种机体就是政治制度。”(1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268页。黑格尔因此描画出权力分立又交互作用的国家制度,包括王权、行政权与立法权,其中每一权力的权能力量须接受其他权力限制与有机整体规定,不可有任意独立的权力要求。黑格尔进一步指出诸种权能力量由不同等级代表执掌,其国家制度本质是为等级代议制,“如果说,国家的第一个基础是家庭,那么它的第二个基础就是等级”:广义等级,即知识等级制,包括农民等级、产业等级与普遍等级;狭义等级,又称“等级要素”,即多数人的意志等级制,包括农民等级与议员,前者与君主一起构成等级议会上议院,后者则构成等级议会下议院,相互补充。不过,区别于封闭限制性旧等级,这里等级尊重现代世界主观特殊性原则,具有开放自主性,是黑格尔为解决现代世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或特殊与普遍分立而设置的至要中介调解机制,他强调“政治上的等级要素……只是当它的中介作用得到存在时,才能成为合乎理性的关系”(2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323页。。“代表制中介的理念构成黑格尔的国家理论。”(21)让-弗朗索瓦·科维刚:《现实与理性:黑格尔与客观精神》,张大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第345页。“代表议会就是‘等级’。”(22)让-弗朗索瓦·科维刚:《现实与理性:黑格尔与客观精神》,张大卫译,第339-340页。等级中介作用具体如下:
首先,市民社会特殊性个人通过等级提供的平台与机会参与普遍性事务,获得政治价值,为调节现代分立世界准备客观条件。这里实存于国家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的各等级意指广义等级,农民等级是其中最为自然无痕的中介等级,因其所有地产配搭长子继承制具有精确私有本性与独立自主性,与君主的规定性要素及生活方式极为相似,自带政治性同时又分属市民社会私人等级,所以被黑格尔视为表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直接同一,即凭借自身原则即可获得政治性的等级。与农民等级直接以道地私有财产为自身性质本质不同,产业等级关键在于对地产等自然材料进行反思作用的理智与勤劳,由此确立自由自尊感;它通常由市民社会诸种特殊利益集团,如有组织的协会、自治团体和同业公会构成,又作私人等级,其中各集团代表由成员委任,作为参政议员,分属议会下级。普遍等级,又称官员等级或中间等级,由君主委派的国家官吏与政府成员构成,被黑格尔规定为国家法制和知识方面的支柱,最具智慧,且被切断与市民社会的经济联系,依赖国家财产给付工资;它以普遍利益为目的着手处理政治事务,是担负中介调节个人与君主、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任务的主要等级,也是黑格尔区别于极权主义国家的得意设置。
产业等级与普遍等级是黑格尔等级设置的核心,两者相互补充,达成权力平衡与利益平衡,保障整个机制中介作用的现实有效。一方面,就产业等级来说,诸特殊集团成员利益被视为市民社会范围内和国家真正普遍物之外的特殊公共利益予以追求,扬弃市民社会纯粹营私个体与他人偶然需要的原子式集合,形成了相对必然关联的力量团体,个体可在其中获得相对普遍利益与政治价值;各特殊集团同时接受普遍等级官员的管理与监督,避免出身自本等级的工会首脑、代表及主管人短视偏私,远于普遍。另一方面,就普遍等级来说,官员虽最具智慧,却也需要来自产业等级诸团体代表作为议员的意见补充,并接受其监督,避免官员独断专行与滥用职权,陷入特殊。“国家的其他任何一种制度都和各等级一起来保障公共的福利和合乎理性的自由。”(2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320页。以立法事务为例,黑格尔规定产业等级与普遍等级同时参与,以保障属于国家公民的真正普遍利益不仅借君主与官员被动自在地实现着,而且还经由等级要素中介的市民社会个人主动自为地争取着。
其次,人民群众通过等级中介生发普遍性尊严与爱国心等政治情绪,为调节现代分立世界准备主观条件。在黑格尔那里,一般地论及人民是肤浅思维的抽象意识,过于模糊,无机群众只有成为国家有机体中的某种人,即分属某一等级,获得承认进入公意,才成其为人民。“人必须成为某种人物……隶属于某一特定等级……不属于任何等级的人是一个单纯的私人,他不处于现实的普遍性中。”(2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216页。同时,国家机体亦不可脱离人民及其意志仅作为纯粹制度形式存在,亦即不是强制外物,而毋宁是人民公意的对象化。普遍性尊严与爱国心等政治情绪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生发的,前者是个体自我意识,后者是对国家机体的意识,当两种意识相合并统一于前述客观条件时,即完成为自由全体,达成个体与共同体、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或特殊与普遍的和解。“单个人的自我意识由于它具有政治情绪而在国家中,即在它自己的实质中,在它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成果中,获得了自己的实体性的自由。”(2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253页。
最后,等级代议制能够有效实现人民主权,为国家机体的中介作用作基础保障。在黑格尔看来,主权本质是植根于实体性普遍的特殊,任何能够作为此种有机统一的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个人,包括君主、官员与议员均可成为委托代表,表征并践行人民主权,只要他们真正以普遍利益为自身根本目的。“代表制的意义……在于利益本身真正体现在自己的代表身上,正如代表体现自己的客观原质一样。”(2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329页。而未经任何组织中介的全体政见作为公共舆论,虽有实现主观特殊性的积极意义,却只是真理诉求的无机表达,自然混合着谬误与偏好任性,并不一定是主权的恰当来源。因为,意志作为成长着的理性,需要经历一系列特定的否定性环节才能完成自身为具有客观性的主观意志以及具有真理性的自我意识,国家机体及其各等级设置恰是将群众特殊意志教化为人民公共意志或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以备和解的重要手段。“一切人都应当参与国家事务这一观念所包含着的另一个前提,即一切人都熟悉这些事务,是荒谬的。”(2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326-327页。黑格尔因此拒绝市民社会无组织全体单独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亦不认为如此能实现人民主权。市民社会无组织个人毋宁是未经等级教化的贱民(28)黑格尔那里“贱民”的本质规定在于政治情绪的缺失,而非流行解读的贫困;在黑格尔看来任何偶然的、自然界的以及市民社会需要关系中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导致贫困,不是贱民形成的必要条件。“问题不仅仅在于防止饿死而已,更远大的宗旨在于防止产生贱民。”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242页。,或与人民公意相敌对,自私邪僻;由贱民组成的无形式民主毋宁是无定形原子式群氓集合体,是古典民主的堕落形式,不但持续分离有机群众并固化个人与国家的对立,而且国家也将沦为全民意志偶然同一的外部国家,现代分立世界无从得到和解。
三、马克思指证黑格尔国家机体的中介作用无效
概括来讲,黑格尔国家机体中承担中介作用的主要等级包括作为间接和解中介的诸立法等级(即产业等级与普通等级)与作为直接和解中介的农民等级,前者以“私人等级在立法权的等级要素中获得政治意义和政治效能”(2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322页。为根据,后者以道地私有财产为根据;它们都被马克思证明为矛盾且无效,毋宁在持续分化有机群众并固化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或特殊与普遍分立,与黑格尔国家理念相悖。“黑格尔每分析一步,马克思都试图演绎作为全体的政治国家与作为特殊的市民社会之间的分离这一内在二元对立。在马克思看来,就像黑格尔理论中那样,整体与部分构成统一关系的互相依赖的两个方面。马克思试图表明,这一关系在黑格尔关于现代国家的描述中,被构想着、预设着、坚持着,但从未被实际证成。全体与部分依然是分离与对立的。”(30)Gary Teeple,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s 1842-1847,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4, p. 83.
首先,关于间接和解中介,马克思指证包括产业等级在内的市民社会诸私人等级并不能通过立法权获得政治意义与政治效能,且立法权等级要素内部存在诸多矛盾。
法国大革命是现代世界主观特殊性原则的极致发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立得以彻底完成,私人等级隔绝于政治意义与政治效能。市民社会私人等级专注物质生活,与政治生活再无相关,任何公共政治设置都不过是个体间的外在偶性联结与异己性强制规定。单纯来自于市民社会私人等级的个人即无政治性原子,若要获得政治意义与效能,只能抛弃私人等级,跃出市民社会,否则普遍政治形式与特殊物质内容之间两不相合,但如此又隔绝于私人物质生活;现代分立世界始终不能达成统一,毋宁只是在片面领域中的虚假同一。“等级差别(市民社会的内部差别)在政治领域中获得了一种不同于在市民领域中获得的意义。这里似乎存在着同一,存在着同一个主体,但这种主体具有本质上不同的规定,因此实际上这里是双重的主体……幻想的同一。”(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3页。
作为私人与君主间至要中介环节,立法权等级要素本身不但内存未决矛盾,而且需要原被中介方即君主做中介,是矛盾的集中体现。具体来讲,黑格尔规定市民社会私人与君主之间的分立,通过来自私人等级的议员与来自普遍等级的官员共同参与立法事务达成和解。然而,议员本质是与政府相对立的缩小了的私人,官员本质是与私人相对立的扩大了的政府,立法权等级要素内部依然紧张。黑格尔试图通过追增第三参与方,即作为原被中介方的君主做中介,调解官员与议员。因为,立法权三环节分别是“作为最高决断环节的君主权和作为谘议环节的行政权……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等级要素”(3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318页。,显然不含私人这一原初极端,那么君主就似乎是其中最具中介资格方,据说既代表包括全体私人的国家,又是所有国家官吏的首脑。“荒谬性完全暴露……就像一个人本来介于争执双方之间,可是后来争执者之一又介于原调解人和另一争执者之间。”(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9-110页。
立法权诸等级要素,包括来自普遍等级的官员与来自私人等级的议员,本质均是伪以普遍形式的诸种特殊利益集团代表,并且其间的相互监督与平衡作用矛盾无果,是为官僚政治。议员来自市民社会私人等级委任,其据称的普遍性本质是市民社会诸特殊集团利益求获实现与保障的形式普遍性,并未成功将作为分裂着的群众组织为具有内在认同性的融贯有机体,与偶然确立的外在需要体系一样,借由“国家维护他们的特殊领域——它们的合法性、威信和福利”(3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309页。。官员虽然是将特殊归于普遍的中间等级,但其存在本身必将持续预设分离于普遍的特殊或私人等级,其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普遍事务本质外在并对立于市民社会诸特殊集团利益,是包装以普遍外衣的官员特殊利益与私人事务,是与黑格尔现实有机的国家理念相反的虚构分裂的政治国家,是官僚政治。换言之,所谓普遍等级官员本质与私人等级议员一样,分属特殊利益集团,不过生成范围不同,后者来自于市民社会,代表共同的特殊性,是市民社会中的政治国家,后者生成于政治国家,代表虚假的普遍性,是政治国家中的市民社会,因而又相互对立各自为谋。如此,黑格尔最得意设置的主要中介环节即普遍等级官员,作为与归于人民的 “普遍东西”与归于私人等级议员的“特殊东西”对立的虚假的“普遍利益”本质就被马克思披露无遗:“‘普遍利益’只有在特殊东西作为某种‘普遍东西’同普遍东西保持对立时,才能作为某种‘特殊东西’同特殊东西保持对立。”(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9页。此外,黑格尔规定议员与官员以相互监督平衡的方式通过践行立法权保障人民普遍利益,其中预设市民社会私人等级与国家普遍等级之间的利益一致,然而黑格尔在明晰议员对官员的积极作用并确保后者不滥用职权时又指出,官员等级“按照普遍法而行动和这样行动的习惯,就是这些本身独立的集团形成一种对立势力的结果”(3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315页。,自相矛盾。“黑格尔不会看不出,他把行政权构思成市民社会的对立面……怎样恢复同一关系……于是,如果我们问黑格尔:有什么东西保护市民社会以防范官僚政治……黑格尔举出官僚政治的无能及其与同业公会的冲突当作替官僚政治辩护的最终理由。”(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7-68页。
其次,关于直接和解中介,马克思指证农民等级本身并不能作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直接同一或最高合题,且关于农民等级地产之规定矛盾于一般私有财产。
在黑格尔那里,农民等级之为直接和解中介的基础在于本来意义上的私有财产与家庭关系。本来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意指农民等级所有的配搭长子继承制的地产,其根本要义在于无依赖性与不可让渡性:“它的财产既不仰仗于行政权的恩宠,也不仰仗于群众的青睐。它的财产甚至不为它自己的任性所左右……他们的财产就成为不可转让的长子继承的世袭领地。”(3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324页。换言之,不同于接受共同体规定与分配的社会性一般财产,世传地产具有精确且纯粹的道地私有本性,在一定意义上与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属性相同,亦终将消融一切社会纽带与伦理实体性联结,包括家庭在内的诸种共同体形式都将沦为此种财产形式积累与增殖的偶选手段。“土地占有等级由于以‘家庭生活’作为自己的‘基础’而得以被确立为‘政治关系’。但是……私有财产的原则在其最高发展阶段上是同家庭的原则相矛盾的。……土地占有等级则是反对家庭生活的私有制的野蛮力量。”(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23页。以农民等级作直接和解环节或最高合题,即默认道地私有财产或资本属性是国家机体的根本意志原则,后者是关于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私有财产法成为最高国家法,私有财产事务成为政治事务,吞噬一切的私域至高表现忽而成为控制政治国家的抽象权力,显然无法实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和解,也更不会是两者的最高合题。
此外,黑格尔国家法关于私有财产的规定,即关于农民等级地产的规定,与其私法关于私有财产的规定,即关于一般私有财产的规定,互相矛盾。黑格尔法哲学的论述基质是自由意志,一种独立于一切偶性仅根据理性自我规定的能力,人格就始于个体自由意志生发与自我意识觉醒之时,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但人格在形成之初是除单纯自我相关外没有任何内容的纯粹主观性,财产就是自由意志与人格得以现实化的直接外部领域,因此,人格在将抽象自我外化以谋取现实发展的过程中,同时要求财产私有化以表征我性,形成一般私有财产。作为一般私有财产的物是无意志且无人格的,私有财产所有者对它具有意志优越性,即其意志可随意进驻或抽离于财产物表达占有与转让;为规避占有与转让的偶然任意性,促使私有财产完善发展,黑格尔引入表现为契约形式的承认,确保在抽象法阶段关于私有财产的所有与转让有效发生。换言之,在私法阶段,作为私有财产的物是可被让渡的,不可转让的是人的本质规定,包括人格与自由意志。“那些构成我的人格的最隐秘的财富和我的自我意识的普遍本质的福利,或者更确切些说,实体性的规定,是不可转让的。”(4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73页。与私法关于一般私有财产的规定相反,国家法中作为道地私有财产的世传地产是不可让渡的,是实体性本质与主语,而作为具有意志优越性的所有人或流动性继承人反被颠倒为世传地产的偶然表现与谓语,沉迷于所有物并被它占有。“私有财产的独立性在私法中的意义竟不同于在国家法中的意义,这还算什么法哲学!”(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27页。
四、结 语
黑格尔时代德国人发展了的主观特殊性意志使德国处于解体状态,国家政治权力被私人分裂剥夺,国家法本质是私法集合,空有国家之名。基于德国分崩离析的历史现实,黑格尔主张重塑国家机体以调和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立,因此与分裂的德国国家机体相反,黑格尔国家机体“要求有一个普遍的中心,一个君主和一些等级,各种权力、外交事务、军事力量、与此相关的财政等等都结合于这一中心”(42)黑格尔:《黑格尔政治著作选》,薛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25页。,即其以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为原则的等级代议制国家。马克思指证黑格尔等级代议制国家本质是伪装成普遍的特殊官僚政治,亦即作为纯粹政治制度的抽象国家,不但不贯穿一切非政治领域,而且作为其物质内容的所谓普遍事务是关于道地私有财产的事务,真正的人民利益只在立法机构诸等级要素中具有形式性存在;虚构统一,固化分裂,与统一普遍和特殊的国家理念相反,中介作用无效。事实上,黑格尔形式普遍性政治国家是以资产阶级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国家之共同缺陷,后者作为公共权力从关于经济利益的阶级冲突中产生,凌驾于经济社会之上,始终是同人民物质生活相对立的彼岸天国。
与黑格尔着力构建现代国家机体不同,马克思主张消灭作为异物统治的现代国家本身,以消解政治于社会的方式将行政权归还全体人民,从而实现特殊和普遍、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等分立形态的现实有机统一,完成人类解放。“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于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44页。,政治国家在其中消失的政制就是“真正的民主制”(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消解政治国家的提议并不是在召唤无序社会,即不是要消灭国家本身,毋宁是要消灭具有形式普遍性与官僚政治性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及其私有财产的奴役人的性质;作为自由之前提的国家与私有财产将以高级形态出现在未来社会,这在本质上与扬弃私有财产并重新占有人的全部类本质的共产主义理念一致。换言之,马克思超越黑格尔以意志为基质叙说政治的路径,指出现代世界政治问题的根本是经济问题,更明确指向私有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掀起了证成共产主义社会思想与实践的序幕。“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64页。,“民主的马克思与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之间存有内在政治关联”。(46)Alexandros Chrysis, True Democracy as a Prelude to Commun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16.
要言之,有关黑格尔国家学说研究,区分其国家理念与国家机体,并分析国家机体建构的历史因素是必要的,避免盲目嘲笑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全部内容,笼统指责它是自我矛盾的混合物。事实上,马克思认同黑格尔关于现代世界分立的观点——市民社会(特殊)与政治国家(普遍)相互分离且对立,亦与之一样试图解决该问题,统一特殊和普遍,把人从片面生存样态中解放出来。不过,两者路径不同:黑格尔提出建构现代国家,并具体把握国家机体为等级代议制,赋予其中介作用以调解两极,实现具体自由;马克思则证明黑格尔等级代议制的中介作用无效,提出将国家职权消解于社会全体的真正的民主制,同时克服两极,实现全体解放。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主要对其国家机体有效,而被模糊的黑格尔国家理念,不仅是马克思替代方案的至要旨趣,而且具有多重积极意义。“对黑格尔的整体论证持赞成态度,而对他的建议的大部分细节内容提出异议是完全可行的。”(47)大卫·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黑格尔、海德格尔及其以后》,臧佩洪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