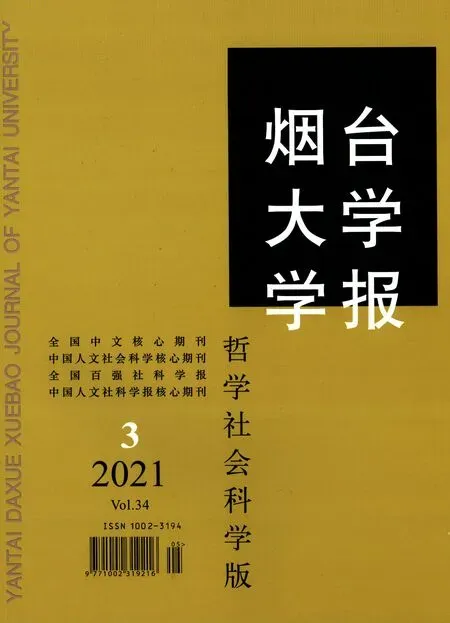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2021-11-29田广林任妮娜
田广林,任妮娜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春秋战国之际,伴随着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由分封诸侯的王制时代向设置郡县的帝制时代逐步过渡的历史大势,中国古代族群关系格局也相应地经历了由传统的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的深刻演变。其客观结果就是周朝版图疆域内东西南北各地族群对华夏文明共同体——古代“中国”的普遍认同,从而直接催生了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出现。仅从这一角度来说,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认同问题,乃是一个事涉承上启下、影响后世中国两千年发展格局和基本走向的重大历史问题。有关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认同,有渐成一个学术热点之势,以往的论者虽然多有涉及,(1)如史念海:《西周与春秋时期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及其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期)、颜世安:《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夏”融合与地域族群》(《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晁福林:《从“华夏”到“中华”——试论“中华民族”观念的渊源》(《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张富祥:《先秦华夏史观的变迁》(《文史哲》2013年第1期)等文,其所讨论的内容,都与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认同问题有所关联。但却鲜有专文论证这一问题。基于此,本文拟从西周宗法分封形成的夷夏关系格局入手,重点围绕春秋战国时期族群融合与诸族同源观念产生语境下的“中国”认同问题,试作讨论。如有不当之处,祈请指正。
一、宗法分封与夷夏异制
西周初年,通过“制礼作乐”等一系列制度建设,周实现了新的政治秩序重建,由此继商之后成为代表古代“中国”的第三个中原王朝。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建设,是在王朝全境实行的宗法分封制度,其核心是如史墙盘铭文所说的“分君亿疆”,即封藩建卫,巩固周疆,(2)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具体操作主要有褒封和实封两种形式。所谓褒封,是从法权意义上对古帝王后裔、商代原有各地土著方国势力在新兴王朝中政治地位、经济待遇的重新确认。一般情况下,周王无需另外划拨土地和人民来授予褒封者,只是通过“班赐宗彝”等象征意义的仪式来完成。(3)《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元年三月》,何休注曰:“有土嘉之曰褒,无土建国曰封。”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197页。史言周武王代商为天子,“……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今河南灵宝县),黄帝之后于祝(今山东长清县东北),帝尧之后于蓟(今北京市)……大禹之后于杞(今河南杞县)”,(4)《史记》卷四《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修订本,第1册,第163页。“而封殷后为诸侯,属周”。(5)《史记》卷三《殷本纪》,第1册,第139页。这种分封形式本质上反映出的是原为“西土之人”的西周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对三皇五帝以来的古史体系及其文化传统的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
实封是周王对同姓亲信和异姓功臣的授土授民,这是西周宗法分封的核心内容。受封者各自率领族人和宗族武装,到所封之地统领原住民,建立起大小不等的二级封国,形成拱卫西周王朝的军政藩屏。其中封在王畿者属于周王身边百官系统的内服卿士、大夫;封在王畿之外者为各地诸侯。这种形式的分封,本质上是以“西土之长”起家的西周统治者,在宗族分支、武装殖民的策略设计和政策原则下,分别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实施的军政势力渗透和领土极度扩张。春秋晚期的周室大夫詹桓伯曾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晋杜预在“吾西土也”文下注曰:“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国为西土之长。”(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九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修订本,第1307-1308页。通过这样的政治运作,西周从理论上把各地华夏诸侯封国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泛称曰“蛮夷”的部族邦国统一纳入到王朝的天下之中,从而使西周所属版图疆域出现了华夏系统的“诸华”“诸夏”共同体与蛮夷系统的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不仅如此,由于西周实封诸侯国统治集团成员均属于外来移民,因此这些二级封国内部,也普遍存在着族群交混、夷夏杂处的社会人口构成特点。《左传·定公四年》载卫国子鱼语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鲁公以……殷民六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殷民七族,……而封于殷墟。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怀姓九宗,……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定公四年》,第1535页。面对这种全新的族群关系格局,西周统治集团损益变通殷商以来的内、外服制度,在对畿内和畿外不同人群实行区别对待的基础上,制定并推行了灵活而务实的夷夏异制管理制度。
所谓夷夏异制,就是对由褒封的古帝王和前朝后裔、实封的同姓宗族、异姓功臣、殷遗多士组成的“诸华”或“诸夏”,以及与周王室关系较为疏远、社会文明化程度偏低的蛮、夷、戎、狄实行区别对待,分区管理政策。关于西周初年夷夏异制的顶层设计和具体操作的策略与方法,《国语》卷一《周语上》载穆王时期周室大夫祭公谋父语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皵,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韦昭注曰:“祭,畿内之国,周公之后,为王卿士。谋父,字也。”(8)左丘明撰,鲍思陶点校:《国语》卷一《周语上》,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1-3页。由此可知,谋父为周公后人,“祭”为谋父所在封国的国名,“公”乃爵称。这里的“先王之制”,系周公相成王之时所确立的职事内容和朝贡制度;“邦”是指周邦所在的王畿;邦内、邦外分别指畿内和畿外;而甸、侯、宾、要、荒五服,则是指周朝所属不同社会群体对周王承担的不同职事和义务。其中封在畿内的卿士列在甸服,封在畿外的诸侯及次一级大夫,分别列在侯服和宾服。这三者统属于华夏诸族系统,在军政上,形成拱护周王室的藩卫和屏障,在财政上,具体承担周王室“日祭、月祀、时(季)享”以及一应军政运作所需的日常用度开支。其他没有履行实际授土授民程序的邦国和部族,属于蛮、夷、戎、狄系列,各自以其与周王室关系的远近和联系的疏密程度,分别列在要服与荒服。其中,列在要服者,要求与周王室保持岁贡关系,列在荒服者,只要政治上承认周王室的权威地位,经济上则没有任何要求,即所谓“岁贡、终王”。在此基础上,西周对王朝所属各个阶层,制定并实施教化为主、惩戒为辅、区分对待的策略方针。对列在甸、侯、宾三服的华夏系统各级封君贵族,既要求经济上的贡赋,也要求军政上的守土保民,倘若违命失职,则要施之以或刑罚、或攻伐、或征讨的严历处罚。而对列在要、荒二服的蛮、夷、戎、狄,只是重点强调其政治上的认同,而不在于经济上的贡纳。倘有“不贡”或“不王”的事例发生,对其惩罚的措施也仅限于问责较轻的责让与警告,所谓“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如果“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9)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十九《季氏》,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48页。。周朝通过这种宽严兼济的民族政策和灵活权变的施政策略,把王畿内外的诸华、诸夏和蛮、夷、戎、狄统一纳入到了王朝的“天下”之中。从周天子的角度上说,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0)《毛诗正义·北山》,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3页。体现的是王权通行、天下一体的政治伦理认同。从各级封君诸侯和邦国部族的角度上说,则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七年》,第1284页。体现的是王畿内外各级封君和天下各色族群对以周王室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的政治归属与认同。也正是这种宗法分封、夷夏异制语境下的族群混居,为后世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空前民族融合,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二、诸族融合与华夷一体
最初,夷夏异制语境下的“蛮、夷、戎、狄”,是与“诸华”或“诸夏”平等对称的概念,用以指代居处于不同的地域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各异的非华夏族群,既无后世岐视与蔑称的意蕴,也没有东西南北具体方位上的限定。东方之人可以称戎,西方和南方之人均可称夷。周人甚至把地居“大邑商”的“中国”之人称之为“殷戎”,孟子曾称周文王为西夷之人。由于西周以来长期实行的诸华、诸夏与蛮、夷、戎、狄不同的管理模式,加之诸夏与蛮夷之间客观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到了春秋时期,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诸国与交错分布的非华夏邦国及其族群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更趋明显。此间,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于是,各地的强势诸侯纷纷趁机对周围的小国实行兼并,藉以实现自身的强大与扩张,进而演化升级为剧烈的大国争霸。而周边的四裔强族也于此时不断地向生存条件更为优越的中原地区流动迁移,导致“四夷交侵”现象的出现,从而给中原的周朝王室和华夏诸国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12)《春秋公羊传注疏·僖公四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49页。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一方面,直接唤起了各族的自觉意识,“华夷之辨”“夷夏大防”由此成为当时各国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这也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华夏民族与蛮、夷、戎、狄族群的空前融合和双向认同。
当时,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的事例可以征之以山戎的南伐“病燕”和楚人的问鼎中原。鲁国史书《春秋》载鲁庄公三十年(前664年),“齐人伐山戎”。《左传》曰:“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庄公三十年》,第246-247页。这里的“病燕”,即是指由于山戎的南下而给燕国带来的生存危机。春秋初年的“山戎病燕”,并不限于山戎本身,当时燕国东北一带的令支、孤竹等土著部族也曾参与其中。而远在黄河下游立国的齐国,也曾遭受到山戎的威胁。《史记·匈奴列传》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厘公与战于齐郊”。(14)《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9册,第3485-3486页。据现有的历史学、考古学研究成果,分布于燕北辽西一带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即为山戎遗存。(15)林沄:《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林沄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87-396页。目前,在天津蓟县刘家坟、宝坻区安桥,北京市延庆西拔子及唐山市雹神庙等地均有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陶器或青铜器出土,这是“山戎病燕”的确切证据。
燕国为成王母弟召公奭的封国,齐国为周初开国功臣吕望的封国。二者为周朝通过宗族分支、武装殖民的方式分别嵌入夷狄分布区域的华夏势力。四夷的交侵,遂使华夏民族的自觉意识被普遍唤起,尊王攘夷应运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而首倡其事者,便是北击山戎、救助燕国的齐桓公。史言齐桓在位之时,“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伐楚,济汝,逾方城,望汶山,使贡丝于周而反。荆州诸侯莫敢不来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16)左丘明撰,鲍思陶点校:《国语》卷六《齐语》,第118页。可以肯定,齐桓所平服的“三十一国”,多数都属于夷人邦国。这是华夏系统的齐国融合东夷的例证。
继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旗号帅服莱、莒、徐夷等三十一国,使齐成为东方民族融合中心之后,北方的晋国、西方的秦国、南方的楚国也都四出攻伐,灭国略地,先后成为区域性的民族融合中心。
其中的秦国,其公族原出东夷,西迁后长期与戎狄杂处,在东周以前始终被华夏民族目为戎狄。至非子时,受西北游牧民族影响,“好马及畜,善息养之”,被周孝王封为附庸,邑于秦,使为周室养马。传到襄公时,以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而受封为诸侯,并授之周人的故土——“岐以西之地”。由于受到周文化的深刻影响,到秦缪公之时,国势强盛,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霸业。此时的秦缪公,在与戎王使者由余对话时,俨然“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中国自许。《史记·秦本纪》引时人语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17)《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册,第223-230、245-247页。这是西戎出身的秦国融入华夏,并推动西北戎狄背景的邦国诸部对华夏文化高度认同的典型例证。
楚国国君族系出于荆蛮,其直系始祖是周文王时期的鬻熊,姓芈氏。《史记·楚世家》对楚国早期历史有明确记载,西周成王之时,“封熊绎于楚蛮”。周夷王时的熊渠曾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春秋初,熊通于立后三十五年(前706年),举兵以武力胁迫华夏系统的姬姓随国为其在周王面前争取封号,其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斡旋未果,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18)《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5册,第2042-2046页。楚武王熊通在礼崩乐坏、“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的情况下,通过随国请封尊号的举动和政治诉求,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出以蛮夷自称的楚人对华夏文明的热切向往和由衷认同。而楚庄王的观兵周疆、问鼎中原,(1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三年》,第669页。楚共王的“抚有蛮夷,以属诸夏”,(2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十三年》,第1002页。也都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面说明了楚人所在的蛮夷地区对华夏文明和当时“中国”的普遍认同。
经过各地族群的长期融合与相互认同,到了春秋中晚期,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阖日益消弥,夷夏和合、华夷一体的思想观念应运萌生。如当时称四裔之民为“远人”,这里的“远”,非指空间距离,而是指宗法分封语境下与周王室关系较为疏远的蛮、夷、戎、狄。孔子曾经倡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21)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季氏》,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247页。孔门弟子子夏则进而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命题,愈能彰显出华夏族群对四裔居民的深度认同。
战国时期,人们对夷夏和合、华夷一体观念有了更为明晰而深刻的认识。孟子曾经论证:属于东夷之人的舜,属于西夷之人的周文王,二者出生地望相隔千余里,生存年代相距千余年,但均以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事功“得志行乎中国”,最终被华夏民族尊为永世景仰的圣人。(22)朱熹:《四书集注·孟子章句·离娄下》,第415页。孟子的这种东、西夷人均可以品德和事功得为中国圣人的思想,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在华夷关系问题上的狭隘血统和地域视角偏见,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三、诸族同源与华夏认同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还可以在当时流行的诸族同源思想观念中得到进一步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族同源观念,有横向和纵向两种维度的考量:从横向关联的角度上说,是华夏与夷、蛮、戎、狄同源;从纵向历程角度上说,是三皇、五帝、虞夏商周一脉承袭,同根共体。
有关“华夏”一语的较早记载,见于《尚书》和《左传》。《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伪孔传曰:“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唐孔颖达疏曰:“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言蛮貊则戎夷可知也。言华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己,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纣也。”(23)《尚书正义·武成》,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5页。本属“西土之人”的“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入主中原一带的“中国”后,身份一变而为华夏,从此也成为“中国”之人。关于《武成》是否为西周初年文献,目前仍存有争议,但周人以与蛮貊戎夷对称的华夏自许,却是事实。《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参与宋国大夫向戌“弥兵”的声子,曾与楚国令尹子木论及从楚国流失的人才帮助晋国“侵蔡、袭沈”,复“败申、息之师”,遂致“楚失华夏”。(24)《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六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91页。这里的华夏,所指代的对象不仅是封在中原一带的姬姓诸国,同时也包括宋国这样的殷商遗裔。通过这两条史料可以确知,春秋之际的周族和姬姓邦国,以及夏商遗裔,均以社会进步、文化发达而通称华夏。
当时的“华夏”,又可以分而称之曰“华”、曰“夏”,又曰“诸华”或“诸夏”。如《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语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25)《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48页。《左传·襄公四年》晋悼公欲北向伐戎,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2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四年》,第935-936页。《左传·闵公元年》载“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诸夏亲昵,不可弃也。’”(2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四年》,第256页。
有学者考证,“华夏”一语,来源于“虞夏”。虞夏之“夏”,最初指代夏后氏或夏部族,随着夏朝的建立,遂转化为中原一带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代称,从而超越了当初仅仅指代夏部族的概念。其政治涵义是指中原王朝代表的“中国”,民族涵义是指“中国之人”,文化涵义则是指中原文化。(28)张富祥:《先秦华夏史观的变迁》,《文史哲》2013年第1期。要言之:夏王朝建立后,其所属的立国于中原一带的众多方邦,均以认同夏朝国家和中原文化而通称曰“夏”,又称“华夏”。
本来,夏、商、周三代各有其开国历史,夏族、商族和周族在血统上也并不同源。但发祥于东夷地区的商族后裔,却刻意强调其祖先发祥及殷商立国的地域均为“禹绩”。《诗经·商颂·长发》:“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29)《毛诗正义·长发》,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26页。又《殷武》:“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毛笺曰:“天命乃令天下众君诸侯,立都于禹所治之功。”(30)《毛诗正义·武成》,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27-628页。具有东夷背景的殷商后裔以立国于禹绩为荣而自矜的民族心理情结,明确地表达出对以夏为代表的“中国”认同。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周人因称殷商故地为“东夏”。《尚书·微子之命》载成王于平灭武庚叛乱之后,乃“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曰:“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伪孔传曰:“用是封立汝于上公之位,正此东方华夏之国。宋在京师东。”(31)《尚书正义·微子之命》,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0页。既然殷商故地为东夏,而“华、夏,一也”,二者平行对称,可以互训,则周人称之为“中国”的“大邑商”,既为中国,也属华夏。
与商人一样,周人也称自己发祥的“西土”为“禹绩”或“区夏”。如《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毛笺曰:“丰邑在丰水之西,镐京在丰水之东。”(32)《毛诗正义·文王之声》,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6页。《尚书·康诰》:“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孙星衍疏曰:“肇者,《释诂》云:‘始也。’夏者,《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区夏者,薛综注《东京赋》云:‘区,区域也。’越同粤,《释诂》云:‘于也。’修者,郑注《中庸》云:‘治也。’西土,谓岐、镐。言文王始造我区域于区夏,于我一二友邦,以修治我西土。”(33)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五《康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9页。周人以西土为夏区这种观念本身,就是周人对以夏商为代表的“中国”和华夏的文化与民族认同。这种认同,是周朝依以运作王权,维系天下共主政治地位的思想基础。
夏人和商人的文明化起步均早于周。西周初年的统治者在作出全面认同夏商以来华夏文明的理智决策基础上,乃迁殷遗顽民于成周,就近监管,但仍然给予土地,为之置邑,保留其贵族身份地位。所谓“尔乃尚有尔土”,“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34)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十《多士》,第431页。与此同时,封伯禽以条氏等“殷民六族”,于东夷之地的少皞之虚(墟),因商奄之民建立鲁国;封康叔以陶氏等“殷民七族”,“于相土之东都”的“殷虚(墟)”建立卫国,“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封唐叔以“怀姓九宗”之民,于“夏虚(墟)”所在的夏人故地建立晋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里的“怀姓九宗”,杨伯峻注引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曰:“唐叔所受之怀姓九宗,春秋隗姓诸狄之祖也。原其国姓之名,皆出于古之鬼方。”(3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定公四年》,第1539页。这些被封在西周王畿和姬周最顶层封国的夏商遗裔,无论怀姓九宗,还是殷民诸族,都属于完整地保留原有宗族势力,即“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地加入到周朝统治阶层的受封旧贵族。其受封之时,文明开化程度一般都高于“西土之人”的周族,因而对于周代的民族融合和周族的华夏化,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孵化”作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鲁国所在“少皞之墟”的东夷地区,还是晋国所在“夏墟”的戎狄地区,都早已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这种人文景观的出现,正是夏商周三族相互认同的结果。
春秋时期华夏与蛮夷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常见于时人有关部族祖先、族系的纵向追述与重构。《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朝鲁,在回答鲁国大夫昭子问及东夷先祖少皞氏以鸟名官时,郯子对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郯子出身东夷,为少皞氏后裔,以博学闻名于世,故有“吾祖也,吾知之”的自信。他所说的这段话,是对东夷部族远古历史的追述,其中所涉及到的黄帝、炎帝、共工、太皞、少皞、颛顼6位古帝王,除了少皞,其余多为传说中的华夏先祖,从中可以明显看出郯子华夷同源共祖的思想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当孔子听到郯子的说法时,对其学说高度认可,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36)《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十七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83-1284页。
华夷同源观念不唯存在于东夷社会,在南方的楚国,也同样流行。《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37)《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二十六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21页。祝融也为华夏族系远古神话中的传说人物,有出身于颛顼族和出身于炎帝族等不同说法。向以蛮夷自许的楚人奉祀祝融,于此足见当时华夷同源思想影响之深刻。而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观念普遍流行的内在机制,无疑是民族大融合背景之下各族人众对以华夏文明代表的古代“中国”的高度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