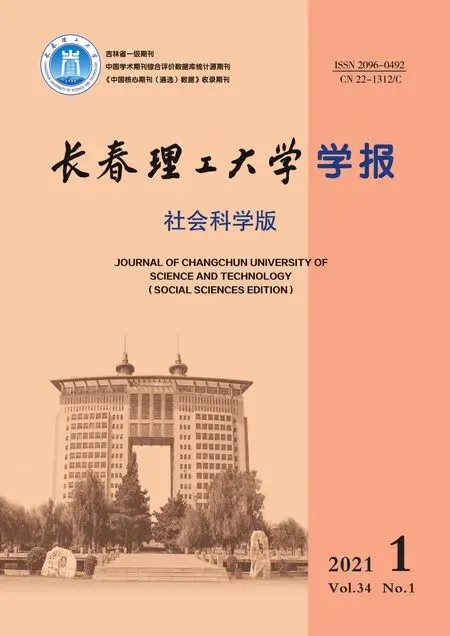福柯意识形态论及其认识论批判
2021-11-29王葳蕤
王葳蕤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是拒斥传统意识形态概念的,这不仅因为传统意识形态追求确定性,还由于传统意识形态被认为是与真理(即科学)相对立的似乎意味着某种虚假的东西,并且是物质与经济因素的产物。因此他认为要谨慎对待意识形态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福柯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他只是拒绝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框架。事实上,福柯在对知识、话语、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中,形成了自己的拒斥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一、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考古学和谱系学
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是福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工具,也是他的意识形态论的方法论框架。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分析方法,发现了科学和真理之上所附着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发现了这种意识形态运作的推动力量——权力。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区分了两种历史学研究方法:一种是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如经济增长的模式、商品流通的定量分析、人口发展和减退的剖析、气象及气候变化的研究、社会学常数的测定、技术调整及其传播和保持的描述等[1]1,文献在其中发挥着表述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实在;另一种是改造过的即新历史学方法,文献在其中变成了重大遗迹,它是诉说自己故事的话语本身,并对自身的特点加以描述。在福柯看来,传统历史学对文献的解释或判断不是曲解原意就是穿凿附会,历史研究应趋向于考古学,即“对历史重大遗迹作本质的表述”。[1]7在他看来,与传统思想史关注起源、连续性和总体化不同,考古学“更多地谈论断裂、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1]188它关注的是话语本身,旨在对话语方式进行差异分析,从而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和规则,是对话语对象的系统描述。它拒绝本质性的探讨,因为它把话语本身就看作本质性的存在。它关注矛盾和差异分析,把矛盾作为其描述的对象,而不是要克服的表面现象或应抽出的秘密原则。它强调对横贯个体作品的话语实践进行比较,探讨话语实践的类型和规则,否定创作主体的存在。它忽略时间的序列,强调断裂和非连续性,拒斥同一性。在福柯看来,考古学“贯穿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这条轴线”。[1]204
如果说福柯的考古学侧重于从话语实践的维度探讨意识形态问题的话,那么他的谱系学则侧重于从权力和主体的角度探讨意识形态问题。福柯的谱系学也更多地关注非连续性、差异性和反体系性。在他看来,不存在任何以科学或真理自称的话语体系,真理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因此,谱系学不是追寻起源的同一性,而是致力于探讨来源(Herkunft),关注偶然性、断裂和差异,它需要历史来驱除起源幻象,不是要在个体中寻找一般特征,而是要辨别细微、独特、属于个人的标记,从而将这些标记逐一区分开来。它不是要对历史进行回溯,不是要重建一种连续性,它旨在抛弃传统形而上学的连续性,打碎那些被认为是同一的东西,从而呈现它的异质性。福柯指出,尼采在研究来源(Herkunft)时,有时也用“Enstchung”一词。“Enstchung”在更大意义上意味着出现。因为传统形而上学在追溯起源的时候,往往把出现当作一种最终结局,但谱系学认为,出现并不是最终结局,而是“一系列征服的插曲”[2]153,它是对奴役体系的恢复,承认偶然的统治活动,产生于权力的纠结状态。福柯认为,在尼采的谱系学中,出现就意味着一个相互对峙、相互倾轧的场所,它既不是强者力量的炫耀,也不是弱者的挣扎反抗,而是“展开和隔绝它们的空间,是传递它们之间相互威胁、叫嚣的虚空”。[2]154确切来说,这个对峙场所毋宁是一个“非—场所”,它产生于裂缝,在它上面所上演的总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纠葛关系。因此,谱系学与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是以绝对性为坐标,设定了永恒真理、不死灵魂和自我同一意识的历史观。而谱系学则信奉变化,它把变化植入形而上学历史观所认为的永恒的东西当中,认为情感、本能、肉体等都是处于流动变化之中的。实际的历史是拒斥恒定性的,它不是为目的论和因果论服务,而是“要使事件带着它的独特性和剧烈性重现”。因此,事件应被理解成对立力量间的关系,这种力量既不遵循目的论,也不遵循机械性,“它总是显现于事件的独特偶然性”[2]157,这种偶然性是权力意志的冒险。其次,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总是关注遥远而高贵的东西,而谱系学的历史观则揭示衰落,怀疑崇高,试图还事物以本来面目,它更关注一些切近的东西。最后,历史学家倾向于消除知识中的自己的观察位置、所处的时刻以及采取的方法等,以使自己显得客观、公正和中立;而谱系学家则明了自己的透视性,承认不公允的手法,使实际历史坦然成为一种透视性知识。此外,福柯还将谱系学同历史的柏拉图主义模式相对照。在他看来,前者是对“实在性的反讽式的和破坏性的使用”[2]161,后者则是对实在性的回忆和确认;前者旨在消解同一性,致力于非连续性,而后者则致力于寻找同一性的根源,强调连续性或传统;前者认为不存在普遍的真理,“没有一种认知不基于偏见”[2]164,而后者则认为真理是基于认知主体的统一性产生的,一旦主体的统一性被打破,真理也就不复存在。实际上,谱系学与考古学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对历史形式的探讨,都反对起源论和目的论,都拒斥总体、同一性和连续性,都强调差异性和异质性。
总之,这种认识论方法贯彻于福柯思想的方方面面,因而构成了其意识形态论批判的主要方法论基础。正是靠着这个方法论,福柯发现了人们熟视无睹、但又非常普遍的社会微观生活层面的意识形态运作的种种痕迹与秘密。
二、意识形态运作的材料:科学与知识
在对考古学和传统思想史作了一个初步划分后,福柯进一步探讨了考古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引入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旨在对科学如何产生、科学与知识如何相互作用、科学话语如何使意识形态产生以及科学如何实现其职能等诸多问题进行研究。具体而言,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发现意识形态问题是与知识、话语和科学等密切相关的,知识、话语和科学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正是意识形态的角色,它们均为意识形态运作的材料、原料或载体。
如上所述,在福柯那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话语。在《知识考古学》中,他通过对话语及其实践的分析,揭示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的。他指出,意识形态产生于话语实践的过程中,而话语实践与科学和知识又密切关联。在他那里,话语是一种实践,但他并没有给话语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更多从比较分析的角度阐述了话语的特征。福柯认为,话语与语言不同,话语是由可能是无数的语义段构成的有限的整体,而语言是由话语事实汇集起来的规律的完成整体,具有无数的功能。此外,话语分析也与思想史不同。前者旨在揭示一种话语区别于另一种话语的特殊性,而后者只能在话语的某个确定总体上重建另一种话语。知识是由话语实践根据其规则构成的,它不必然产生科学,但却是科学形成的必要条件。每一种知识都有确定的话语实践,但不会有脱离话语实践而存在的知识。科学产生于话语实践中,并以知识为基础,它不等同于知识,又不排斥知识,而意识形态就发生在科学与知识的链接处。福柯一方面从历史的非连续性角度赞同阿尔都塞关于“认识论的断裂”的观点,即认为科学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的,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排斥科学性”[1]207,也不认为科学可以完全抛弃自身的意识形态性。福柯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解构了,在他看来,一切科学话语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产生于“科学从知识中显现出来的地方”[1]206,而不是产生于结构层次、技术层次或主体意识层次。
那么,科学是如何从知识中显现出来的呢?福柯认为这是考古学分析所关注的问题,即“从正面指出科学怎样进入到知识的成分中和发挥作用”。[1]206在他看来,话语实践在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话语实践不同,科学在不同的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向科学提出的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是科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存在问题,以及它在其他实践中的功能问题。在话语实践中,科学是置身于知识当中的,它构成知识的某些对象,并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区分知识,改变知识和重新分配知识”,另一方面“又肯定知识,使之发生作用”,从而“在话语的规律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因此在其他实践中发挥其功能。[1]206这就是科学的意识形态作用之所在。也就是说,在福柯看来,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是在有关知识的话语实践中发生的,意识形态早在科学的形成过程中就已渗透到科学话语中,而不是在科学形成之后才作用于科学。也就是说,科学是很难完全抛弃其意识形态性的,知识、科学的严密性的增长并不能摆脱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甚至理论的矛盾和缺陷也显示着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因此,在福柯那里,意识形态具有在场性,是不可解构的。
通过对话语、科学与知识产生的分析,福柯揭示了它们与意识形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令人耳目一新。或者更进一步地说,科学与知识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运作的主要原料,意识形态正是借助它们进行着日常生活中最惯常的运作运动。
三、意识形态运作的推动力量——权力
福柯竭力使自己的理论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决定论”阐释模式,因此从表面上看,福柯是将自己置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但事实上他不过是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理论。或者更进一步而言,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断言权力推动了意识形态的产生,而福柯则发现了权力是如何导致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产生这一过程本身。权力也因此取代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成为福柯意识形态批判的关键词。
那么,权力是什么?福柯又是如何运用谱系学方法研究权力问题的呢?权力的意识形态运作的主要表现是什么?福柯采纳了尼采关于权力的认识,即“力量与它所影响的乃至影响它的其他力量(激励、引出、促成、诱发等情感)的关系”[3],而不是力量与生命或客体的关系。换言之,在福柯看来,权力是各种关系的复合体,是一种关系,不能把它简单归为上层建筑的行列,因为它并不处在经济关系、知识关系、性关系等各种关系之外。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是把权力置于惩罚的历史中来讨论的。他把惩罚分为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法国大革命之前,肉体惩罚多采取反人道的酷刑形式。到了18世纪后半期,随着人们对公开处决的抗议日渐增多,改革者提出惩罚要以“人道”作为尺度。于是,逐渐出现了“一种关于惩罚权力运作的新策略”,这种新策略的目的在于使惩罚权力更有效、更普遍和更必要,从而使其“更深地嵌入社会本身”。[4]91福柯认为,在这些刑罚人道化的背后,那些看起来是要求仁慈的原则,实际上是精心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虽然这些原则把权力的作用点引向了精神而非肉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进入了非肉体惩罚的时代。根据福柯的观点,这不过是惩罚的符号—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权力”[4]113,它通过对思想的控制来实现对肉体的征服。在福柯看来,这种符号—技术的惩罚方法必将被一种新的政治解剖学所取代,即规训权力。它的主要功能是“训练”,一方面把个人看作训练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把个人看作训练的工具,由此实现对个人的造就。它“谦卑而多疑”,不同于君主的那种耀武扬威的“至上权力”,它是“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4]193规训权力的成功在于它对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手段的使用。通过对这些手段的使用,权力成功地将自身施于的肉体对象训化成了符合自己诉求的各种主体。
福柯正是通过对规训权力运作机制的探讨,将主体建构成与知识和权力相关的因素,揭示了权力对主体进行渗透和控制的途径,以及主体在权力—知识网络中是如何产生、又如何被控制和驯服的。在他看来,权力通过规训得以实现,主体是规训权力的对象和结果。但权力对人的控制不是对人的意识的控制,而是对人的身体的控制。权力正是通过把人的身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实现对人的干预和控制的。权力生产主体及其知识,但权力的这种运作带有意识形态的内容。事实上,福柯权力运作机制中的监狱、学校等,就类似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那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是知识、权力和意识形态凝缩而物质化的形式。福柯说:“如果没有真理话语的某种经济学在权力中,从权力出发,并通过权力运行,也就不能行使权力。我们屈服于权力来进行真理的生产,而且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使用权力。”[5]可见,权力为知识打上了烙印,但同时也使其失去了中立性,从而没有了科学与意识形态之分。因此,可以说,知识意味着一种权力关系,它受社会、政治和历史过程的影响,是一定权力的代表。所有知识都可以成为权力批判的对象,也即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马克思,福柯扩大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范围。总之,正是通过权力,通过它设计的种种精巧、细密、弥散广布的机制,权力展开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运作,并成为这种运作的主要推动力量。
综上所述,通过对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探究,强调知识的断裂和非连续性,福柯为其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在他那里,谱系学和考古学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考古学从话语实践的维度对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揭示了科学是一种话语实践的意识形态;谱系学则通过将权力概念注入到考古学中,对权力与主体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事实上,尽管福柯拒绝使用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但实际上,当他把科学看作一种话语实践的意识形态,把主体看作是权力生产出来的时候,他构建的何尝不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实质上,这不过是表明知识和真理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原料,主体的形成则是意识形态运作的结果,而权力本身则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动力源头。
四、福柯意识形态论的认识论批判
总的看来,福柯意识形态论所秉承的认识论方法(考古学与谱系学)总体上属于后现代主义范围。这种方法的主要特征强调相对主义、偶然性、断裂性、差异性和异质性,拒斥总体性、同一性和连续性。基于这种认识论原则,福柯的确开掘出了一系列极具冲击力的原创思想。然而,他所秉持的认识论方法却又陷入了某种极端。
根据唯物辩证法基本思想可知,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也正是普遍联系构成了整个世界。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一副演化着的世界图景:“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总的画面,……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6]而自组织理论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最新形式,则进一步证明普遍联系的实质即为形成事物的序,序的运动则形成了各类事物。序在一定条件下的演化运动中,从随机偶然性中形成了某种必然性,从断裂性中展现出某种连贯性,从碎片化中呈现出某种总体性。因此,序的运动是偶然与必然、断裂与连贯、差异与同一的辩证统一。局部地、片面地、极化地强调任一端,均会犯违背唯物辩证法基本原则的错误。福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拒斥,以及他独特的意识形态论所秉持的认识论方法,在部分地揭示出事情真相的同时,也跌入了形而上学的片面主义的泥淖。其表现至少有二:
第一,福柯对权力的揭示只强调其差异性,忽视了其同一性特征。福柯的权力概念可概括为关系,有关系的地方就有权力,权力就是各种关系的复合体。而在具体层面,任何关系均是世间独特的唯一的存在,犹如我们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所以,福柯正确地指出了权力的这种差异性,正确地指出了权力不仅仅是那种自上而下的外在于各种关系之外的东西,而是关系本身,所以与社会具有同构性。但他却将这一事实绝对化,表现为绝对地强调权力关系的差异性,否认其同一性特征,而同一性则是事物秩序形成的重要机制和根源。正是在形形色色的具体的权力关系中,逐渐演化出了可归为某些类别的权力,如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等,从而形成了国家政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类的权力关系。尽管在绝对意义上这些类化权力中的每一具体权力关系的发生都各不相同,但不能否认在某种条件下它们又是可以归类的和具有同一性的。由于福柯对权力关系的差异性和具体性的绝对强调,导致他看不到同一性和总体性,进而断言权力是“无头的国王”。实际上,任一权力都是被某一主体所占据的,只不过很多时候这个主体是隐形的,但追根溯源,仍能被揭示而出。
第二,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分析只强调偶然性,忽视了事情的必然性特征。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建立的基础是历史本身,历史又建立在人的情感、本能和肉体的活动基础之上,而这些均是流动不居的,因此,没有什么恒定的东西,没有目的论和因果论,事件只能被理解为对立力量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如前述“总是显现于事件的独特偶然性”。这种对偶然性的绝对化强调导致福柯看不到偶然性中展现出的必然性。在绝对意义上,任一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偶然的,但一定条件下大量的偶然性又会呈现出某种规律性或必然性。当然,形成这种规律的条件不存在,它的必然性特征也随之瓦解。
总之,福柯出于对现代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驳斥,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有关认识论理念,正确地揭示了传统认识论领域的某些错误,开掘了许多被传统宏大叙事和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原则长期遮蔽的事情真相。这是他的意识形态论可贵的价值所在。但另一方面,由于矫枉过正,他的认识论方法又陷入了片面化和绝对化的极端。这就违背了唯物辩证法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跌入了另一种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