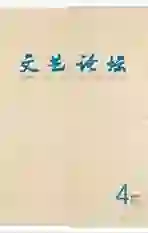卓见拔流俗笔锋利如锥
2021-11-28李铮
李铮(以下简称“李”):雷老师您好,很荣幸受《文艺论坛》杂志委托对您进行一次访谈。在访谈之前,我做了大量的功课,阅读了您的全部著作以及发表的论文,发现您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生态文学、边地叙事文学、乡土小说等几个领域,还发现您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在五六篇,而且几乎全是CSSCI来源期刊,想就此请教一些问题。
雷鸣(以下简称“雷”):感谢《文艺论坛》给予这次交流机会。辛苦你阅读了我的全部著作和论文。我很乐意与你这位“90后”的名校博士作坦率的交流,分享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粗浅的心得。
一、研究须生产新知
李:我注意到您最初的研究是从生态文学开始的,您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首先请您谈谈,当初为什么选择生态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雷:现在回想起来,我进入生态文学研究领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与我的生活经历相关,有时学术研究往往是与自己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联系起来的。我生长于毓秀清丽的湘南乡村,从小看到的天空总是水洗过般的湛蓝透亮,山上的翠竹郁郁葱葱,山涧里流水潺潺脆响,小河滩上青草如玉,还不时能看到白色的鹭鸶依偎在悠闲吃草的水牛旁边。在这样美丽的景色中长大的人,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好坏,可能有种天然的敏感,对关注人与自然的文学作品,也更愿意读。二是受我博士导师房福贤教授的影响。读博士时,他经常跟我们说,博士学位论文通常是做学术的起点,在选题上要有学术圈地意识,要有学术的可持续性,博士毕业之后也能延续、深挖,而不是做完学位论文就终结了。我感觉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态,彼时研究者寥寥,系统、深入研究者更是阙如,是一个值得深入进去的新领域,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学术选择。这点上,我很感谢导师当年的提点,比如我从事有关生态文学研究十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在这方面出成果,去年12月就在《中国文学批评》上发表了《论生态批评的阐释方法——以新世纪中国小说为例》,今年的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第4期全文转载了。
李:就中国而言,生态文学研究作为一个较新的领域,没有学术积累和成熟的研究范式,而您在这个领域,可以说是先行者,而且成果很丰富,仅这方面的论文就有数十篇,可以谈谈您的研究经验吗?
雷:谈不上什么经验,也是在摸索中有一些心得体会。那时做中国本土生态文学研究的学者极少,仅有零星的幾篇文章涉及。但介绍欧美生态文学以及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的学者不在少数,如厦门大学的王诺、山东大学的曾繁仁等。在研习这些学者介绍西方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理论之后,再反观中国文生态学,我为此进行多维的学术准备工作。一是文本的搜集。在综合有关学者对生态文学概念厘定的基础上,尽可能搜罗生态文学的文本,并细读批注。当然对西方的生态文学文本也尽可能多地阅读。二是理论的准备。我不但研读了有关生态批评理论论著,还包括大量有关生态学理论的书籍,以及社会学著作。三是研究范式的准备。生态文学不同于以往的文学以人为中心的书写维度,它还包括了自然书写的维度。挪用从前的评价坐标和价值体系来谈生态文学,难免言不及义,会是一种“不及物”的研究。找到一个契合生态文学文本,又有深度的研究路径,是很费思量的事情。文本阅读量足够丰富,掌握较为完备的理论工具,寻找不同于别人的切入点或者研究范式,就很容易找到论题,写出的论文会有创新性,刊物也愿意采用。
李:我研读您的生态文学研究专著及发表的论文,发现您的生态文学研究的思路,与其他研究者不同。其他研究者侧重阐释文本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而您是从现代性反思这一范式切入的,把生态文学定位于一种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的话语,比如您那本专著名字就是《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您能说说理论缘由吗?
雷:我觉得任何一种研究,须为现有认知提供一种新的认识,否则研究就是无效劳动。一些研究者着重阐析生态文学文本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书写,探析其中包含的生态思想,这样的研究方法没错,也很有意义。但我觉得这样的研究路径,容易导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会使生态文学无限泛化,书写人与自然关系,包含一定生态意蕴的文学作品,古已有之,比如山水田园诗,真正意义上生态文学产生于特定的条件,比如全球性生态危机,现代生态学思想的出现;另一方面生态文学研究仅拘囿于探掘生态文本如何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掩盖了作家对生态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之思考,难免显得很皮相,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学术研究如果仅止于现象的描述上,会遮蔽许多问题。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完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实际上也是人的价值危机、精神生态危机,更深层面是“现代性”文化、制度的危机,是我们现代人的价值信仰、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等因素合力引起的,如欲望贪婪、利益驱动、炫耀性消费、盲目崇拜科学与理性、对自然失去敬畏之心等。所以把生态文学/小说定位于一种反思现代性话语,以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作为研究范式,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便有了一个深度的阐释视域。
李:从2011年起,您的研究似乎转向了“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如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京师大学报》等刊物上的论文全是这方面的,您是如何发现这个研究领域的,能说说您转向的原因吗?
雷:你的判断没错,我是从2011年开始研究“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那年我成功申报了一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研究”,在完成项目的压力下开始向这个领域探究。选择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其实谈不上转向,只是原来研究的拓展与延续。我在研究生态文学过程中,发现很多作品的空间都写的是边远地带或边疆之类,比如你们可能最熟悉的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杨志军的《藏獒》之类,联系小时候曾经看过的边疆题材的电影比如《山间铃响马帮来》,寻根小说也多写边远之地,这些年颇为流行的写藏地的小说。我发现不同时期作家写边地的精神向度是不同的,觉得这个领地绝对是一个“富矿”,于是开始了系统研究边地小说。从“十七年”小说的边地书写开始,到新世纪的边地小说,先是分时段探究,然后综观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边地叙事。这样下来,我发现研究的空间极大,粗略地统计了一下,除出版了一本专著《映照与救赎: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还发表了大概有30多篇重点期刊论文。
李:您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都很独特,后来有不少研究者似乎对您的研究多有模仿与参照,比如您的生态文学研究从现代性反思切入,这几年有研究者也在分析生态文学时从现代性反思切入了。这几年有关边地书写的研究也多了起来。请您总结一下您发现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方面的经验,以便启发我们这些晚生。
雷:你过誉了,实不敢当。谈不上独特,仅有些自己的个人特色。要说体会,我想谈三点。一是要多读些理论书籍,提高自己的理论功底。这些年不少学者反对用理论去硬套文本,我也同意。但我觉得多读些理论书籍,练就深厚的理论功底,永远不会过时。当你具备一定理论视野之后,你发现问题的能力、眼光无形之中就显得与别人不同。同样的文本,你有理论也就容易穿透。比如我了解安德森的民族国家想象的理论,当我在阅读“十七年”小说的边地叙事文本时,就豁然明白了它们为什么与内地革命历史小说在叙事策略上既有相同,也有歧异之处,后来便写了一篇论文《民族国家想象的需求与可能——论十七年小说的边地书写》发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二是要有大量的文本积累。读大量的作品,才会发现问题。文本是文学研究的起点,不读作品,那是空中楼阁。三是掌握一些思维方法,比如联想思维、逆向思维、延伸思维。比如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或其他领域出现的问题域,有否可能在现当代文学领域出现,这即是联想思维。对已有定论的东西,反向思考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东西,这就是逆向思维。诸如此类吧。
二、批评的伦理原则
李:您的生态文学研究与边地叙事文学研究,可以说是文学史范畴的学术研究,但我发现您还写了大量的当下文学批评类的论文,尤其是对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批评与观察,我粗略地算了一下,从2008年起至今年,也有30多篇吧,能说说您从事文学批评的心路历程吗?
雷:我觉得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写文学评论文章是基本功,仅做些史料搜集、考释几篇轶文之类,那是远远不够的。具体就我而言,做当下文学批评,可能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我不太喜欢或者说不适合做史料类研究,尤其是对那些已被淹没的史料去殚精竭虑地发掘、追寻,没有兴趣,总觉得把一个不知名的作家、一个小社团或者一个刊物之类,搞得那么清楚意义不大,文学史本身就是减法,只留下经典。我更喜欢做些有“介入性”与“公共性”的研究,通过阐释文本表达自己的想法。其次,可能接受的学术训练更倾向于批评类,当年念博士,教我们的老师不少是著名的批评家,如吴义勤、房福贤、李掖平、吕周聚等。尤其是吴义勤老师,他给我们开设的课程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在讲授写文学批评的方法时,经常要求我们对最新的作品展开讨论,并且经常练笔。最后是可能个性有些疏懒之故,不太喜欢“东颠西跑”查资料之类的活,写批评文章,只要在家多研读作品,也可完成。
李:您的不少批评类文章,很多都是直接对批评对象“挑毛病”,指出问题的,这一点从您的论文标题就可看出来,比如《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三大病症》《新世纪长篇小说历史叙述的三种范式及其问题》《作家的中产阶级化与21世纪长篇小说的乡村想象几种方法》,我很想听听您的文学批评理念。
雷:呵呵,这点上,你可能有些误解了,文学批评是需要“挑毛病”,但又不能仅是挑毛病、找问题。我觉得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批评家,需要做到三点。一是要对作品的文学价值予以发现和阐释。批评的首要使命,是对文学作品的领悟、理解和阐释,发现、呈示和增值文本的意义,而非只是找问题。二是恪守批评的中正与学理。鲁迅曾说:“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 要么苛责、残忍地對待当代作家作品,全面否定,要么无底线地吹捧,不“挑刺”、不“剜烂苹果”,这两种都是批评家缺乏中正与学理的突出表现。通常被诟病的所谓“人情批评”“商业批评”以及“酷评”,正是典型表征。三是批评文本的可读性与美质化。现在批评界的主要力量是学院派,这些学院派批评家一般都受过系统的学术理论训练,他们的批评文章有理论深度与文学史的宽度,但有的学院派批评家的批评文章故弄玄虚,批评的语言闪烁其词,理论分析模棱两可,以“兜圈子”“弯弯绕”为能事,就是不愿意对作品做出直白、清晰的判断,或许是不能。我觉得这样的批评文章,也只能是自己把玩,没有人阅读的,更谈不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与引导。总之,做文学批评还是需要追求批评伦理原则。
李:我对您所说的批评伦理很感兴趣,能请您谈谈您所理解的批评伦理具体指什么吗?
雷: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只是自己在写批评文章过程中,有几点心得。一是个体生命伦理。这个是说,批评家阅读文本要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批评文章要表达作为一个读者的真实文学感受,要有个人的审美体验,个人独特的风格。唯其如此,批评文章才有感染力、可信性。批评家不能是作家、出版社的“新闻发言人”。二是公正伦理。做批评须在现象学意义上面对作品,不能悬置作品而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作家进行道德审判;不能文人相轻,不能因与作家的私人恩怨而彻底批判;也不能同行相轻,更不能为搏出名而有意菲薄名家。三是审美伦理。这是指批评文章要有审美特质,文字须优美、意蕴阐释清通、逻辑结构明晰,不能有意卖弄知识、术语,更不能把作品当成是炫耀自己理论学识的“跑马场”。坦率地说,这是一种对理想批评生态的要求,现实的批评界要做到这几点似乎很难。
李:我读您的批评文章,觉得文字优美、流畅,逻辑结构也很清晰,尤其是一篇批评文章涉及很多作品,您是怎么做到的呢?能分享这方面的“秘诀”吗?
雷:这方面还真没有秘诀,用一句当下流行的话,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多学点古文,《史记》《古文观止》《世说新语》,还有明清小品文之类,都可读读,提高文字的表现力;学习现代学术名家的著作、文章之类,比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艺境》等,琢磨人家的语言风格;还有就是学习当代优秀批评家的文字,如吴义勤、贺仲明、孙郁等,学习这些老师的文字表达、结构安排。久之,批评文章的水平便逐渐提高了。至于一篇文章涉及很多作品,我觉得这也是作为“学院派”批评的特点吧,喜欢站在文学史的视野中论述,对于文学史涉及的作品,当然是读过的,无论如何,必须广泛地阅读作品。
李:您最近在关注哪些作家作品,或者未来几年研究领域是什么,能简单说说吗?
雷:最近在做经典乡土小說的重读,想用新的视野对过去的经典乡土小说进行再解读。比如今年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1期,发表了《国家逻辑与农民经验——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一种读法》一文,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今年第4期全文转载了,这也激发我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兴趣与信心。未来几年的研究领域,会集中在乡土小说,这也是过去生态文学研究、边地叙事文学研究的一种延续、回归。
三、导师的“道”与“术”
李:雷老师,聊完您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方面的话题,我还有一个小的私心,问问您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您已经指导了多届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您在指导学生过程中有什么具体经验,或者是怎样要求学生的,以便我也对照学习。
雷:好的,不过也不是经验,正好有自己的一点想法。今天的研究生,不可能像1980年代或1990年代初的研究生心无旁骛地读书,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招生人数多了,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但作为一个导师,无论如何变化,对学生指导须围绕“道”与“术”两方面进行。所谓“道”方面,就是反复教育、引导学生,要求学生: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即便毕业后不从事学术研究,所学也助益于今后的工作;反复告诫、要求研究生自觉遵守科研诚信与学术道德,杜绝抄袭剽窃、论文买卖等学术不端行为。在“术”方面,我有些具体而微的做法。一是定期每月见面制度。每次见面,学生必须汇报一个月以来所读的书,我会检查读书笔记,对学生读书的要求是多维立体的,理论书、作品、研究论文必须每天阅读。二是定期组织读书会。每次读书会之前,轮流让每个研究生提交论文,然后其他成员进行评议,各抒己见,最后导师进行总评议,并挑选导师自己的或者学术刊物其他学者的论文进行分析,谈论文的选题、构思和撰写。三是读书方法介绍。介绍读书的一些方法经验,比如读论文,要注意选题、标题的拟法、结构安排、学术语言的表达。四是针对每个研究生制定个性化指导方案。虽然都是现当代文学专业,但要考虑每个研究生有不同背景,在知识结构上也有差异,作为导师,必须善于发现每个研究生的兴趣,根据其长处和不足,让其选择读书方案,建议学位论文选题。
李:我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当下我们这些硕士生、博士生似乎努力做学术、靠奋斗改变命运很难了,发表核心期刊的论文也越来越难,我们很焦虑。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吗?
雷:不可否认,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对你们博士生而言,难度大了。一是刊物评价体系问题,核心期刊要认同评价体系,保住自己的“核心”地位,喜欢发名家的文章,提高转载率和知名度。二是核心期刊的论文需求量增加,很多学校博士毕业都有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要求,导致竞争激烈,刊物自然会好中选优。这种情形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但我觉得,扎实做研究,切实写出高质量的论文,总会有刊物发表的,必须要有这个自信,因为任何一家刊物,都喜欢高质量的文章,尤其是核心期刊,更需要高质量论文来保持自己的水准。
李:您谈了不少有启发的观点,让我受益匪浅,感谢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