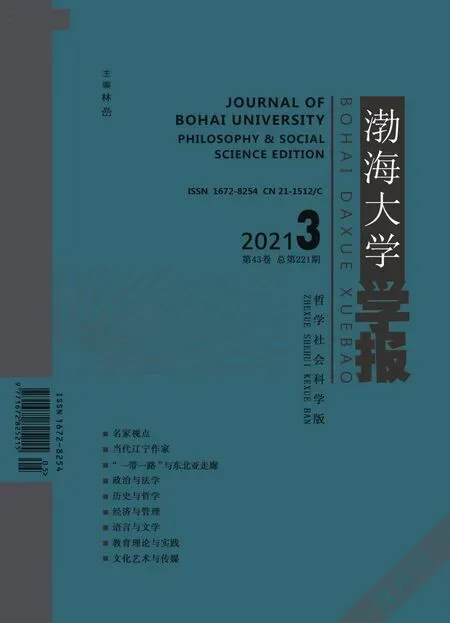叩开文明之门的动力系统
2021-11-28雷广臻渤海大学辽宁锦州121013
雷广臻(渤海大学,辽宁锦州 121013)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等以历代累积的用火技术、和合泥土烧制陶器的成就、筑巢(筑屋文化)的进步、解决食物问题对生业方式的拓展、完备服饰增进人的“礼仪体面”、祭祀礼仪的形成(事鬼)、“旁罗日月星辰”“知幽明”“通神明”创制的历法(事神)和使用铜器等形成基础,成为文明进步的一个个里程碑,形成了新石器时代集大成的文化高峰,叩开中华文明之门。后代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因素——天地人、日月星、四时序、鬼神祀、衣食住行、心物合、礼仪、敬天法祖等,均在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中体现出来。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什么?这是本文研究的主题。
动力,泛指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推动力量,本文指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呈同一性,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就,必有动力系统存在其中。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动力系统主要有复合工具子系统、复合思维子系统和抽象思维子系统,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一、复合工具的普遍制作和使用成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等发展的根本动力
工具,泛指人类从事劳动、生产的器具。在制作和使用工具方面人类与动物分野,这一观点并没有过时。我们知道,有的动物会把身边的物体当作工具,如有研究者观察黑猩猩会用薄树叶做成钓白蚁的工具。有时黑猩猩会使用草叶、木棍等多种不同类型的工具,这并不奇怪。人类在初始阶段也像黑猩猩会把身边的物体当作工具,也会使用草叶、木棍和石块等多种不同类型的工具,当然也会制作工具。但人类很快超越了简单制作和使用单一工具阶段,较快进入了更高级的制作和使用工具阶段,即制作与使用复合工具阶段。由此人类在制作和使用工具的此阶段与动物最后分野。
工具做功系统一般分为三个子系统,即动力系统、动力传递系统和做功工具。加工对象虽然在工具做功系统之内,但本文不做研究。工业革命只是改变了动力和动力传递的方式及工具的复合程度,而没有改变工具做功系统及其三个子系统的合成结构。信息时代也是如此,信息也需要动力、动力传递及做功“工具”。
人们最初使用单一工具。今天常见的有使用石块和加工石块而成的石斧。石块和石斧就是人们的工具,但是单一的工具。单一工具的特点是单一而未与其他工具组合,从物体上不可再划分。此阶段使用工具的具体形式是人握石块,直接做工或投掷出去,作用于劳动对象。工具是单一的,动力也是单一的,动力与工具之间是简单、直接的传递。
人类逐渐把单一的生产工具发展为复合工具。人类经过长期摸索,发明了用绑扎、黏合等方法,把不同物质材料制成的几个部件组合成一件工具,这就是复合工具。弓箭是较早的复合工具。弓箭的制作和使用改变了动力、动力传递与工具的关系,成为一种成熟的复合工具的运用体系。早在距今3 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国境内的人类就开始使用弓箭了。早期的弓箭用一根竹竿或树棍,截成箭杆,一端削尖。严格说来这不算是成熟的复合工具的运用体系,但以此技术为基础,人们逐渐把骨片、贝壳或石片磨制成锋利的形状,安装在矢杆一端,制成了骨镞、贝镞或石镞的弓箭(当今出土的实物往往仅留下箭镞,那是箭杆没有保留下来的缘故),用弓发射出去。有韧性的弓弦与有弹性的弓臂构成弓,直接做功的箭头、箭杆也要组合在一起成为箭,而且弓与箭组合在一起做功。这就告别了以往工具的单一性。也就是说,弓箭从物体上已经可以区分为弓弦、弓臂、箭头和箭杆等部分。此时,不仅工具不是单一的性质,动力传递也不是人直接作用于工具,而是间接地作用于工具。当人们用力拉弦迫使弓体变形时,把自身的能量储存进去;松手释放,弓体在迅速恢复原状的同时,把储存的能量立即释放出来,从而将搭在弦上的箭强力地弹射出去。这一过程,人力改变物体形状弹性,从而将弹性势能转化为动能。动力经过转换而传递,工具已经是复合系统。应当指出,复合工具产生之后,单一生产工具并没有被淘汰,仍然保留下来,这是人类的好习惯。人类经常是在发明新工具的同时保留下旧工具,使随着发明不断递进的生产工具呈现出历史性和层次性。
上文已述,复合工具的出现当在旧石器时代,但复合工具的普遍使用则在新石器时代。北京东胡林、浙江上山和小黄山等遗址及兴隆洼文化、裴李岗文化和河北磁山文化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盘、石磨棒,石磨盘与石磨棒组合成一种复合工具。一些考古学文化出土的石锄、石犁等都是捆绑在木柄上使用的,成为另一种复合工具。为石斧装上柄,为石锄、石犁等捆上木柄,把不同的东西组合到一起形成复合工具而做功,功效大增。
从新石器时代若干遗址中发现了骨柄石刃刀。红山文化系列发现了多种骨柄石刃刀。以骨器为柄,以石器为刃,二者组合,即为石刃刀装上柄,形成了细石器与骨柄组合的新型复合工具。人们把细石器镶嵌在骨槽里做成的骨柄石刃刀,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复合工具。
原初的骨柄石刃刀用的石刃是燧石类,后来在骨柄上固定了三片至四片玛瑙刀片,切皮、割肉锋利异常、轻便快捷。渤海北岸小河沿文化的骨柄石刃刀有了新的改进,在骨柄槽内填充了黑色胶质物质(结构要素),进一步把骨柄与石刃粘接牢固。
复合工具一旦在社会占有基本动力地位,由复合工具带来的思维方法会把复合工具应用于新石器时代的其他相关领域,复合工具思维和方法会支配社会的各个方面,到处可见“物”的组合。如诸多考古学文化居住区的道路、壕沟、中心房屋、周边居室、灶、灰坑和门道等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多室与单室组合,石块、泥土、木草与木柱建筑材料密切结合,所建的半地穴式房屋,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组合。河姆渡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卯榫结合技术。诸考古学文化的陶器形成了新的组合:饮食所用的钵和碗,炊煮所用的罐和釜,汲水所用的壶和瓶等形成独特组合,旋涡纹、几何纹、龙纹、鱼纹、花纹、谷穗纹和八角星纹等形成装饰艺术的组合。有的陶器形成了人的形象与其他要素的某种组合。
考古人员在渤海北岸的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二道杖房大南沟小河沿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4800—4300年的数件臂环饰。有三只臂环饰结构分为三层,内层衬有织物,涂黑色胶体,粘上数行小蚌珠。这是用胶体组合的复合式臂环。
复合工具实质上是一种组合工具。使用组合而成的复合工具,人们做工的力度、范围和效率都加大了。复合工具标志着生产力发生了革命,为新石器时代发生重大变革和进步提供了主要动力,也为新石器时代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新石器时代之所以走向文明也主要依赖于复合工具的普遍创造和使用。
复合工具普遍制作和使用的意义不仅表明复合工具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而且表明复合工具的普遍创造和使用本身是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分水岭,复合工具标志了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这涉及新石器时代的根本特征等重大理论问题。今天看来,以往以磨制石器的出现等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已经缺乏说服力。磨制石器的出现是某种力量作用的结果,是一个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力量和过程本身。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应该从“动力”上找,因此把复合工具的普遍创造和使用看作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更便于揭示新石器时代的本质特征。
二、复合(组合)思维是推动新石器时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
从根本上说,复合工具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形成复合(组合)思维,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组合的精神力量发挥作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空间上不同结构要素从而组合、创造了新事物;二是深度上思维不断抽象化使社会和思维更加有理性。
红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到处都呈现了复合工具及复合工具思维所带来的变化。人们懂得了不同物体可以组合成为另一个物体,组合(复合)思维由此产生并且延伸开来,在社会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复合工具而产生的复合思维的主要特点是告别了单一性思维,形成了组合性(复合)思维,并且在组合思维的作用下形成了组合“实践”。古人用石器(包括玉器)、陶器和木器等创造出了异形人、异形动物。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有许多出土遗物,把人与动物的肢体、器官移位组合,如把人的肢体加到兽、鸟和蛇等动物身上,或把兽、鸟或蛇等动物的器官移位组合到人身上。这是上古人类的一种组合性“实践”,也是社会进步带来的普遍的“心灵手巧”的表现(表明了技术和工艺的进步)。
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双鸮玉佩,两端雕琢对称相同的鸮首形象。鸟兽纹玉佩也是一种异形组合玉器,佩体依其造型的外部轮廓,雕琢出相互组合的一兽一鸟①。这是兽鸟合体思维的产物。
良渚文化玉器有人与兽面的多种组合关系的实物。良渚文化中晚期玉器上最通行的纹饰内容是神人兽面图像及其简化与抽象的图案,形成独特的风格。
新石器时代人们创造了异形遗物,上古文献也记载了异形人和异形动物,应该对这种巧合进行阐释。
东汉人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说到我们的人文先祖伏羲、女娲是蛇躯、鳞身。
《山海经》记载了更多的异形人或异形动物。一是人面鸟身,二是人面兽身,三是人面鱼身,四是鸟身龙首,五是多头、多身现象,六是兽首蛇身。
上述古文献记载的异形人和异形动物的一个共同点也是把动物的肢体或器官移位组合,如把人的肢体加到兽、鸟或蛇等动物身上,或把兽、鸟、蛇等动物的器官移位组合到人身上。这是上古人类的一种极具深度的思维。说到底是一种基于复合工具的组合思维。组合思维激励人类不断求索、不断进取。
上述《山海经》等古文献关于异形动物或异形人的记载,虽然与今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遗物暗合,但在漫长的岁月里曾被许多研究者斥为“荒诞不经”。其实,这些“荒诞不经”的含义极深、意义重大,给今人寻找上古人类的组合思维和行为之痕迹留下了文献依据。《山海经·海外西经》记到:“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今天发现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玉龙,其形象就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红山文化、安徽凌家滩文化和江苏常州青城墩遗址等都发现了“尾交首上”的玉龙。上古人们人为地创造了玉龙等异形物,正好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复合(组合)思维。
新石器时代的组合思维也扩展到古代音乐和舞蹈等领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南贾湖遗址(早中晚三期)出土了一批精致骨笛,红山文化区也有骨笛出土。五孔、六孔、七孔和八孔骨笛,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形成了声音的和谐组合。马家窑文化彩陶盆上的神化人物舞蹈纹,证明早期舞蹈和音乐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舞蹈已有埙、笛、鼓等伴奏,早已告别了“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的阶段。新石器时代人们的舞蹈和音乐的功能也是组合地体现出来,组合了敬环境、求生育、联众心、交四邻、聘四方、祈求五谷丰登和《总禽兽之极》(希望鸟兽繁殖达到最高极限)的综合祈求。
复合思维的空间要素组合与深度抽象化是并行不悖的。复合思维的空间要素组合是一个飞跃,复合思维的深度抽象化也是一个飞跃。后一个飞跃更深刻、影响更深远。
复合思维深度抽象化这个飞跃是循序渐进的。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通过分析“直观取象”认知方法的几个阶段来表述。
新石器时代先人认识事物,起初主要是观物取象或直观取象。据传述,孔子研究过这种方法,他编定后的《易经》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组合思维的形成经历了直观取象认知方法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三个阶段的演进。
初级的直观取象认知方法主要是简单直观取象。以特定事物为母范、摹本观物取象,形成具体事物之物象(象形)。思维中离不开具体事物的物象,但观物取象不是单就一个事物来“观”,要经过不同角度的对比观察,既要“仰观”,又要“俯视”;天地与“鸟兽之文”都兼顾;远近相较、大小相权。
古人直观取象,总是要把其要求、理念和意识等加于所取之象上。随着复合工具的进步,人们不满足于初级的直观取象,要求改变原有初级之象。客观需要和升华的理念都需要对象(象形)进行改变。需要有新的思维来处理,于是便有新的思维产生。
在初级直观取象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再提炼,就形成了变形之象,从而进入直观取象的中级阶段。变形之象的重要特点是以想象为桥梁,由一种物象跨越到另一种物象。
变形之象再进一步,进入组合象形思维阶段。组合象形思维与复合工具思维并进,把具体物象上升到一般物象,把握了物类的共同性质,实现了由个别到一般、由象及理的过程,提升人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
组合取象思维再进一步,上升为理性取象思维,也就形成了抽象象形。
组合之象变成理性取象或抽象之象,产生了两个重要成果,一是产生了龙思维,二是叩开了象形文字的大门。
三、组合思维作为精神动力催生了龙思维和早期象形文字
组合思维在空间上组合要素、在深度上高度抽象化,标志着新石器时代人们思维水平出现巨大飞跃。这个巨大飞跃催生了两个成果,一是龙思维(龙文化),一是早期象形文字。
(一)组合思维催生了龙思维,产生了龙形象。在许多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遗址发现了石龙、玉龙、堆塑龙和蚌龙等。辽宁省凌源田家沟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玉蛇龙,为龙形象的又一类型。
新石器时代普遍使用复合工具及其思维和经验,为寻找龙的起源提供了基本线索。
古人制作的异形物和古文献记载的异形人和异形动物其实就是龙的前身。龙思维为什么会形成?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人类早期生活在自然环境中,与动物相伴,要存活下来,必须向为伴的动物学习,而且要取各种动物之长,增加自己的本领,然后去创造、去征服。取众物之长,进而把其“长”(精华)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龙。
什么是龙?一言以蔽之,龙就是天地间一切事物的精华组合,这种精华组合的精髓是阴阳和合。
上古文献所记载,红山文化等文物所呈示,上古人类从直观取象到变形之象,再到抽象出万物集合之龙,是思维和行为的双重进步。
红山文化玉龙的组合思维是新石器时代人们思维水平的一个高峰,具有很高的思维价值,也为中华民族成为龙的民族提供了翔实的实证和思想材料。
(二)组合思维催生了早期象形文字。组合思维提升到抽象思维阶段,催生了早期象形文字。浙江义乌的桥头遗址最早的年代距今约9000年。目前在该遗址发现了短线组合纹和三个太阳纹饰,其中一个太阳纹饰中间划出一道线,表示冉冉升起的太阳。距今约8000年的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以利器把符号刻在龟甲、骨器上形成贾湖契刻,其中九个刻符在龟甲上,五个刻符在骨器上,三个刻符在陶器上。刻符与汉字的基本结构一致。渤海北岸距今约7000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宝国吐乡小山遗址,在2 号房中发现四灵纹陶尊,有猪、鹿、鸟和另外一种未读出的动物的图案。
安徽蚌埠双堆遗址的早期地层距今约7000年。双墩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也有大批刻画符号和泥塑艺术品。其中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达600 余件,还有特殊形符号等,已具文字的象形、会意和指事等含义。大汶口文化在陶尊上刻画符号,共有数种数十个符号。有学者认为已是表达语言功能的成熟文字。
红山文化玉器极具象形意义,有的直接入象形文字,如斜口筒形器类似象形“且”字,玉龟(鳖) 类似象形“龟”字,凤形玉器类似象形“凤”字,双首玉器(并封) 类似象形“虹”字,等等。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神庙后的山台入象形文字“邑”字。牛河梁红山文化神庙的形状类似甲骨文的象形“中”字形②。
渤海北岸内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小河沿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大口直腹罐陶器,器物外表刻有七个互相有关联的文字符号,表意完整。有人认为这些文字符号记录了一次大洪水暴发前后的情况。
四、文化交流也是促进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显示,中华大地区域之间文化与人员的交流很早就开始了,呈纵横交错强势交流态势。渤海北部的查海—兴隆洼文化及后继的赵宝沟文化等,交流、融合而为红山文化。以镇江营文化为代表的渤海西部文化与以查海—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渤海北部文化也曾密切交流。由镇江营文化发展而来的后岗一期文化,其红顶碗文化因素被红山文化继承;北京平谷上宅遗址与北方兴隆洼文化遗址发现了制作方法相同的骨柄石刃刀,只有用文化交流来解释这一现象;河北省蔚县的三关遗址,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器物同时同地出现,也是文化交流的证据。
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也已经相互交流。辽东半岛南部小珠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有来自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因素。山东龙山文化制作精美的蛋壳黑陶、红地红彩陶器、红地黑彩陶器等在辽东半岛出现。辽东半岛的玉器制品和直口筒形罐也传入山东半岛。美观的八角星纹,在辽西丘陵山区、内蒙古草原地带和山东大汶口文化都出现了。
在辽宁旅顺郭家村(上层)遗址发现了舟形陶器,说明当时已有的较为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为文化互动提供了工具。
辽南的小珠山文化和辽宁新乐下层文化都继承了辽西、辽中和辽南共有的石磨盘、石磨棒、细石器和之字纹陶器等文化因素。
河南裴李岗文化和河北磁山文化早于红山文化,这两种考古学文化影响过辽西的古文化。红山文化器物具有河南裴李岗文化、河北磁山文化的折线篦纹。河北磁山文化和河南裴李岗文化的折线篦纹也在沈阳新乐文化出现。
距今5000年前,红山文化强势发展,有越过燕山的明显迹象,不仅进入华北平原,而且一度进入山东。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在河北姜家梁遗址出现,甚至在陕西省韩城梁带村周代墓葬出现;红山文化的多孔玉璧在山东省野店遗址出现。北京、天津地区镇江营文化的釜、鼎、壶等在山东北辛文化发现。其他文化交流的现象不胜枚举。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融合的部族越来越多、融合的区域越来越大、融合的程度越来越深、融合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更加严格禁止一定范围内血缘亲属成员间通婚,必须实行族外婚,因而对外交流也是必然的行为,但从氏族来说实行的是族外婚,从部落来说则实行的是部落内婚。无论如何,只要实行族外婚,就有文化交流。
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的考古学文化已是“满天星斗”,各考古学文化之间几乎没有空置地带,有的是交叉地带,形成了文化的融合区(交叉区),文化的融合区正是文化的交流区,“鸡犬之声相闻”,物品的交换和文化的交流在空间上已没有障碍。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交流有时通过别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传导。一般说来,文化交流发生于两个不同文化体之间,但有时要通过其他文化的传导来实现。长距离的考古学文化遗址具有相同的文化因素,有些文化因素的形成不是直接交流而形成,而是通过中间的考古学文化传导而来,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文化的融合区有时范围很大,不能因为两种或多种考古学文化有相同的文化因素就误认为两种或多种考古学文化之间有直接交流,而忽略了其他考古学文化的中介作用,以致影响了对考古学文化本来面貌的认识。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开通便捷通道,交换物产、互相观察和学习,既共享了物质层面的因素,也学习了人与自然相处的能力。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交流、迁移和扩散虽然对作为对象的一个文化体来说是外因,但往往这种外因启动了内因,起到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红山文化玉龙对许多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产生了作用。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作为东北地区石墓文化的源头,经医巫闾山向辽东半岛的迁徙进驻,在辽宁南部和北部及吉林西南部,出现了与红山文化积石冢基本特征一致的积石墓、大石盖墓、石棚墓和石棺墓等墓葬习俗,该石墓文化经河北、山西又传至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地。
总之,文化的交流是新石器时代不可小觑的重要社会推动力量。
①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②雷广臻主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巨型礼仪建筑群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