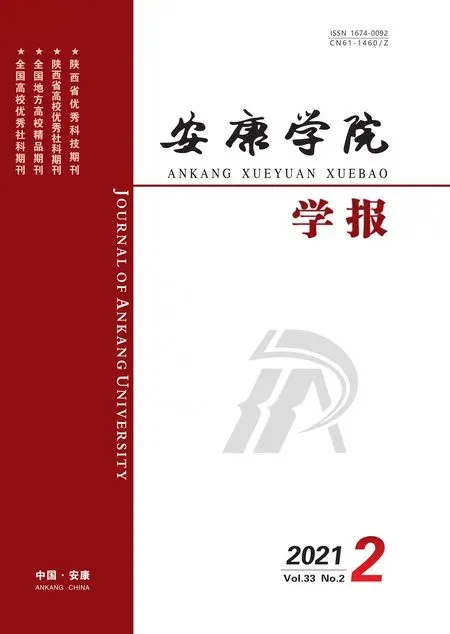知青文学中的陕北地域书写
2021-11-28陈娟娟
陈娟娟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地域文化与作家的创作密不可分,不同地域的自然风景、风土人情会带给作家不同的生命体验,从而造成作家创作理念的不同。金克木先生曾提出要“从地域学角度研究文艺的情况和变化”[1]。地域文化一般指的是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仍旧对人们的生活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的统一。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形成了具有独特性的文化体系。知青文学作为新时期以来重要的文学潮流,被打上了极具个性的地域特点,也因此彰显出知青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一、知青文学中的陕北地域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发表的“最高指示”的号召下,广大城镇知识青年远离家乡和亲人,来到贫困偏僻的山村或荒凉遥远的边陲地带。在贫穷荒凉的北大荒、陕北高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海南岛以及内蒙古大草原,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挥洒他们的青春热血。他们被称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知青们从繁华的大城市来到落后的农村,恶劣条件下生活的不适应和心理上的严重落差,致使他们从狂热的理性主义者变为现实生活的被迫接受者与反抗者,这段特殊的生活经历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以后,知青们再回首这段岁月,依旧刻骨铭心。返城之后,他们通过文学创作来记录这段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重述、回忆并且反思这段人生经历,因此形成了一个文学创作潮流——知青文学。据统计,曾有两万多名知青陆陆续续来到陕北乡下插队,而陕北知青作家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片独一无二的黄土地有着密切关系。他们的作品带有鲜明的陕北地域文化色彩,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他们对这片黄土地的接纳与反思,以及对陕北这片土地、对生活在陕北高原上淳朴善良的人们、对已逝去的青春岁月的深深眷恋。如作家史铁生的长篇小说《插队的故事》以及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回忆了在那段时光中真诚且单纯的人际感情;梅邵静的诗歌《她就是那个梅》 《母亲》都以母亲的形象赞扬了曾给予她真诚关怀的陕北人;叶延滨的诗歌《读陕北民歌集》 《嫂子》以及散文《圣地》 《魂牵梦绕》等都以“上山下乡”的真实经历为基础,抒发了对陕北这片土地的真挚情感;高红十的《哥哥你不成材》 《无话可说》也是对自己的插队经历进行文学化的叙述。陕北知青作家都是以插队时期的陕北生活经历作为写作素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了陕北这块土地上的人与事,批判地接受这块土地上特有的文化体系,因此形成了具有陕北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学书写。
二、陕北地域书写的具体表现
(一)自然风景
地理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心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学者莫伸曾说:“作家的创作都和所处的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长期积淀下来的心理模式和行为规范息息相关。对他们而言,自小生存和生活的地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依托,是他们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审美理想形成的产床”[2]。知青作家们的创作深受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乡村自然环境影响了知青作家们的艺术气质与风格,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乡村自然环境的描写随处可见,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知青文学对陕北自然环境的书写首先体现在对那片未经雕琢的自然景象的描绘上。地处偏远的陕北是一个较为闭塞的地区,天然的屏障保留了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乡村美丽宜人的自然风景与城市的高楼大厦、整齐划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深深吸引了来自城市的青年们,为他们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在知青作家眼中,乡村世界的安静、质朴为人们呈现出一幅幅原生态的自然美景。在作家史铁生的笔下,贫瘠的陕北是充满勃勃生机的地方:“野鸽子从悬崖上的洞里钻出来,‘扑棱棱’飞上天;野鸡‘咕咕嘎嘎’地叫,时而出现在崖顶上,时而又钻进了草丛……春天燕子飞来时,家家都把窗户打开,希望燕子到窑里来做窝;很多家窑里都住着一窝燕儿,没人伤害它们。谁要是说燕子的肉也能吃,老乡们就会露出惊讶的神色,瞪你一眼:‘咦!燕儿嘛!’仿佛那无异于亵渎了神灵。”[3]133通过史铁生的描述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机盎然、万物绽放的天然圣地,各类小动物的生命力点缀着偏僻遥远的陕北,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陕北高原上顽强生长的各类植物也为作家们提供了无限的希望,在作家高红十的笔下,最不起眼的苦苦菜也为贫瘠的生活带来无限的春意:“当袭人的春风刮起来了,雍容的暖意羼杂几丝倦怠。此时,脑际显现偏不是逐风的柳条,笼雨的花瓣,欢溜溜唱着歌一路奔跑的一渠绿水,而是陕北高原上遍地皆生得不起眼的苦苦菜”[4]。拥有顽强生命力的苦苦菜为陕北带来了第一抹春意,也为知青们带来了生活的希望。知青作家笔下的陕北更多时候充满生机与希望,是他们对自然的无限喜爱与敬畏,体现了他们在经历磨难后依旧对生活的热爱。
陕北独特的地理环境同样是知青作家们笔下的表现对象。贾平凹曾说:“陕北,山原为黄土堆积,大块结构,起伏连绵,给人以粗犷、古朴之感觉。”[5]这片雄浑的土地在千百年来的风吹雨打之下呈现出一种荒凉之感,但在荒凉之中承载着历史文化的底蕴。初入陕北农村,眼前的景象令知青们大失所望,连书本里描绘的滚滚前进的延河也失去波涛汹涌的豪迈。史铁生在他的作品中写道:“无边的黄土连着天,起伏绵延的山群,像一只只巨大的恐龙伏卧着,用光秃秃的脊背没日没夜地驮着落日,驮着星光。河水吃够了泥土,流得沉重,艰辛。只在半崖上默默地生着几丛葛针、狼牙刺,也都蒙满黄尘。天地沉寂,原始一样的荒凉……”[6]知青们眼前看到的是贫瘠、封闭与落后,与他们最初对陕北革命圣地的想象相差甚远。在自然与人为的双重作用下,陕北成为一片贫瘠且荒凉的土地,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这块贫瘠的土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质朴善良的陕北农民,孕育了坚强、勇于抗争的陕北精神。在作家叶延滨的笔下,陕北的山坡像母亲一样给予生命的滋养:“那些遥远了的黄土塬上浑圆的山峁,像母亲的胸,温暖地散发着乳汁一样的雾岚”[7]。这个奇妙的比喻不仅赋予陕北高原人性的光辉,更是对养育了千百万儿女的陕北土地予以高度的赞美与感恩。这片贫瘠的土地默默地为人们提供生存的养料,造就了陕北儿女坚韧不拔的精神。
(二)风土人情
提起陕北,首先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就是扎着白羊肚巾的陕北老汉以及陕北粗犷豪放的腰鼓和信天游。而这些质朴淳厚的民俗民情使知青作家们为之着迷,也成为他们远走他乡后能够寻找到的精神慰藉。知青文学作品中的陕北地域书写是对那一时期社会情景的记录,也是对那一时期生活的回忆与怀念,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大量乡村世界风俗人情的描写。
史铁生是一位曾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作家,他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陕北人们日常的生活习俗。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作者刻画了一位白老汉的形象,从白老汉的口中唱出了许多陕北民歌,“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的好光景……”[3]122,“揽工人儿难;哎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猪狗饭”[3]12。这些民歌唱出了陕北的民情,也唱出了陕北人民的艰辛与煎熬。此外,陕北人除了爱唱信天游之外,热情奔放的腰鼓、唢呐、秧歌也是陕北人民对于苦难生活的排解。热烈的舞动驱散了他们劳作的辛苦;声势浩大的唢呐仿佛也吹走了他们生活的艰难;欢快的秧歌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美好与欢乐。梅绍静的诗中写道:“敲吧,跳着敲,舞着敲,敲得人人心里都发热,多希望这金黄的土地做我们的鼓面,敲出最扎实、最宽广的欢乐。”[8]156在这有限的欢乐之中表现了人们苦中有乐的生活态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这些积极向上的日常民俗也给知青作家们带来了生活的希望,使他们在困苦的日子里找到些许的安慰。
陕北的风俗人情不仅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更体现在盛大的节日庆典中。陕北地方偏僻,封闭落后,这使得在此生活的农民长期生活艰苦,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能够改善生活享受一番。过年时家家户户都在烧得热烘烘的炕头上歇息,吃肉喝酒,当然还会有各类陕北特色吃食,这种热闹非凡的气氛让人们忘掉了过去一年的辛苦与艰难,沉浸在与家人团圆的喜悦中。陕北地理复杂,交通不便,每隔一段时间的集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大盼头。集市虽规模不大,但热闹非凡,这是辛劳的庄稼人在艰苦的劳作之余的一点消遣。这样的场景在梅绍静的诗中得以呈现:“这市集上的路,窄的像一根儿葱,扎白头巾的人,稠得像谷穗上的颗子”[8]143,人们沉醉在充满生机的集市中,享受着短暂欢乐的放松时光。陕北人的豁达坚韧给了艰苦岁月中的知青们莫大的精神鼓舞。
三、对陕北地域文化的认同与反思
历史上的陕北是文化的汇集地,北方游牧文明和华夏农耕文明在这里交流汇合,陕北逐渐成为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同时相对封闭的环境又造成陕北文化荒蛮落后与单纯淳朴共存。这种复杂的文化氛围蕴含在陕北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暂时生活于此的知识青年来说是一次强烈的文化冲击,他们在这方土地中生存,全方位地感受这块土地上的文化氛围,对陕北厚重的历史文化进行吸收与反思。
(一)对陕北地域文化的认同
学者李继凯说过:“陕北高原属草原文化过渡地带,人种与文化均呈现多民族融合的特征,昂扬悠长的信天游,狂跳猛擂的腰鼓,娱神娱己的秧歌等,是这一地区民间艺术的代表,其内蕴的生命文化精神对陕北作家很有影响。”[9]知青作家多来自城市,在插队之前或许他们从未到过贫穷落后的山村,甚至对农村人的生活习惯、民俗风情知之甚少,但在知青作家的作品中都蕴含着丰富的陕北文化元素,这与他们所经历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密不可分的。知青作家的作品运用大量的笔墨描写陕北风俗,包括方言、民歌、腰鼓、秧歌、唢呐等极具陕北意味的文化符号,并且借用主人公的口吻引用了大量的陕北信天游,将陕北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完整地展现于读者眼前。正如作家史铁生所言:“我在写‘清平湾’的时候,耳边总是飘着那些质朴、真情的陕北民歌,笔下每有与这种旋律不和谐的句子出现,立刻身上就别扭,非删去不能再往下写。”[10]由此可以看出陕北风俗民情对知青作家写作风格的影响。腰鼓、唢呐、信天游、秧歌等多种多样的民间艺术都具有陕北文化色调,是陕北人在艰苦生活中所能享受到的精神给养,知青作家们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通过对陕北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吸收,给知青文学打上了陕北文化的烙印。
知青作家对陕北文化的吸收还表现在陕北文化对作家的影响。由于陕北地理条件险恶,艰苦的生活环境造就了陕北人民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品质和博大的精神气度。这种坚韧与博大的文化因子深植于知青作家的生命中,让他们懂得生存的真正意义在于面对苦难,勇于抗争。1972年,年轻的史铁生因身体原因离开陕北回到北京,没过多久就瘫痪在床。面对自己的残疾,他曾经一度陷入迷茫与绝望。在他的散文集《我与地坛》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生命无常、世事变幻的无奈与灰心,继而在孤独的思考之中感受到生命的价值,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在陕北乡下艰苦生活的经历一一呈现在他眼前,陕北厚重的文化底蕴使他敢于直面人生的苦难与挫折。评论家李建军曾说过:“文学常常产生于心灵孤独、忧伤、痛苦、绝望甚至愤怒的时刻,但它本质上是爱、信念和希望的结晶。”[11]史铁生从陕北这块土地上所领悟到的抗争精神,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后能浴火重生的精神根基。此外,陕北人豪爽旷达的性格、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相助让知青们在苦难的生活中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使年轻的知青们感受到家的温暖,这给了承受着巨大心理落差的知青们莫大的鼓舞与安慰。
(二)对陕北地域文化的反思
对于知青作家而言,“上山下乡”运动既是他们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一段时光,也是他们遭遇磨难的一段经历。这场运动让许多城市儿女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他们离开城市来到贫瘠落后的乡村,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落后的生活习俗让他们内心深处对陕北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身处其中也让他们深刻认识到落后的生活习俗对民众的毒害。因此,在历经艰难重回城市后,陕北生活的经历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新奇与难忘,也有对陕北地域文化的深刻反思。
与史铁生笔下温馨质朴的清平湾相比,朱晓平笔下的桑树坪充满着贫瘠落后的真实意味。桑树坪是一块遥远且荒凉的地带,这里的人们沿袭着古老的生活习俗,婚丧嫁娶、生活作息都带有浓厚的先祖遗风,贫穷落后是这里的代名词。正是在这片真实的土地上,知青们看到了文化的闭塞与落后。在《桑树坪纪事》中,作者描绘了真实且残酷的乡村现实。桑树坪偏远落后,农民生活艰难,有时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更遑论结婚生子这样的大事,村子里很多人娶不上媳妇,娶妻就成为他们十分渴望甚至病态的需求,因此他们用原始手段获得女人。《桑树坪纪事》中的李金斗用种种残酷的方式逼迫他的大儿媳妇再嫁小儿子。《福林和他的婆姨》中的福林父母为了让儿子娶上媳妇,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送去当童养媳,而当福林与妻子青女在一起无法传宗接代时,他又残忍地将青女送给了自己的弟弟。这种原始而野蛮的婚嫁方式让人震惊,小说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深受其害的农村儿女的悲悯之情。
知青作家们插队的地方多是封闭且落后的偏远乡村,那里不仅有淳朴单纯的人性美,更有先民遗留下的落后风俗。插队的经历终将成为美好与伤痛并存的记忆,为他们带来心理上的双重体验。
四、结语
知青作家通过对陕北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的书写与反思,丰富了文学世界中的陕北地域形象,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真实的自然陕北和文化陕北。研究知青文学中的陕北地域书写具有以下意义:首先,拓展了陕西地域文学研究视野,将研究视野从陕西籍作家作品扩大到知青作家作品。其次,从地域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研究知青文学中的陕北地域书写,对陕北地域文化形象的传播与建构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