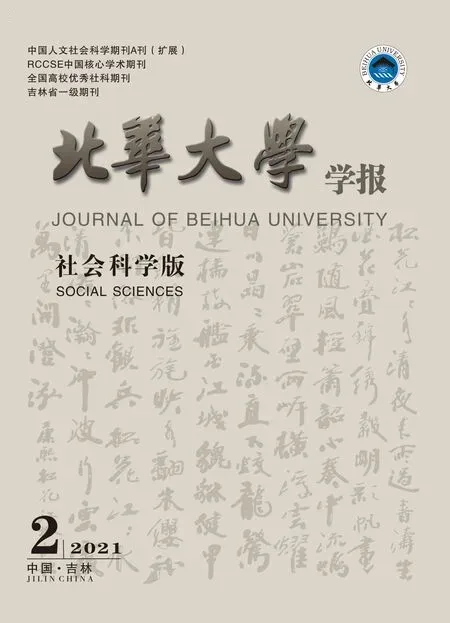宫崎市定“五霸皆夷狄论”考辨
2021-11-28孙志鹏李思佳
孙志鹏 李思佳
日本京都学派第二代代表学者宫崎市定在其1940年出版的《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中,首次提出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或夫差、越王勾践)皆为夷狄,即“五霸皆夷狄论”[1]15-22。时至1977年出版《中国史》时,依然坚持此说。[2]100关于五霸之华夷身份,国内外学界从农牧生产方式、地理位置、文化习俗等角度形成了不同表述,如将楚国视为夷狄[3]、五霸是半蛮夷[4]、晋国不是夷狄而吴楚越三国为夷狄[5]等。针对“五霸皆夷狄论”,本文采取史料比对和史实核查的方法,从礼俗文化、身份认同、朴素与文明的对立理论等方面,考察五霸的华夷身份,进而揭示宫崎市定提出此种谬说的理论原因。
一、“五霸皆夷狄论”的内容
宫崎市定认为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或夫差、越王勾践,他们皆为夷狄,理由如下。
齐桓公:(1)风俗不同,“在齐国的历史上,以桓公为首,包括其臣僚,屡屡出现同姓婚配现象,这种现象被视为东夷的淫乱之俗,因此,很难将之看成是西周建国以来的同盟民族”[1]17;(2)齐国并不拥护周王朝的统治,也不承认其权威;(3)语言不同,齐国在其统治区域内形成了“齐语”。
晋文公:(1)同姓婚姻,“晋国位于今山西省南部,与周最为接近,在习俗上受周影响颇深,但是直到春秋时期,晋国依然可见同姓婚的存在”[1]19;(2)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周王朝是不同民族,作为献公之子的晋文公也是夷狄;(3)齐、晋两国和周民族不是一个系统,是在周文化区域之外受其影响而兴起的国家。[6]71
楚庄王:(1)民族起源不同,“楚人原本是与周人完全不同的民族,据说可能与当今中国的苗族属于同一系统,因此,从周的角度来看,楚国可能不过是蛮夷而已。”[6]71(2)楚国并不遵从周王朝的统治权威,“楚国在春秋之初就开始称王,与周抗礼。”[1]20(3)楚王自称蛮夷。
吴王阖闾或夫差:(1)民族争斗,“未开化民族通常分为各个小部族,近邻之间往往持续不断地发生血腥争斗。”[1]22-23吴国不断与邻国发生冲突,符合宫崎市定对于夷狄的定义,吴王阖闾、夫差及越王勾践均为夷狄。“楚、吴、越三国在春秋时便被称为蛮夷之国,尤其楚国被称为‘蛮’。”[2]99-100(2)楚、越、吴是不同于周王朝的民族,不仅血缘上有差异,地理位置上也距离甚远,属于夷狄。
由上可见,宫崎市定区别华夷的标准主要有:(1)与周王朝是否属于同一民族;(2)是否承认周王朝的权威;(3)是否遵循“同姓不婚”;(4)语言交流是否无碍。简而言之,宫崎认为血统与文化习俗上的不同,造就了“华夷”差别。不过,若揆诸史实,上述理由均存在问题。
二、礼俗文化:“同姓不婚”与语言文字
华夷之辨以文化为基本标准,因此对五霸之国礼俗文化的考察,是辨识华夷的有效视角。宫崎市定提出“五霸皆夷狄论”时,前提是将周王朝作为“华”。具体而言,宫崎市定判断夷狄的主要依据是:五霸是否遵循“同姓不婚”以及五霸与周王朝在语言文字上是否有差异。[1]4
(一)“同姓不婚”
在宫崎的视野中,是否遵循“同姓不婚”是区别华夷的主要标准。周奉行“同姓不婚”礼俗,最早见于《左传》:“男女同姓,其生不藩。”[7]209《礼记·昏义》载:“昏礼者,合二姓之好。”[8]1680这部详细记录周王朝仪礼的书籍中明确记载着当时的婚姻习俗,即两个姓氏之间的婚姻,由此可见周奉行“同姓不婚”。周朝之所以坚持相同姓氏男女不结婚的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周人认为同姓结婚后所生的后代不健康,如果提倡同姓结婚的话,那么周人整体体质就会下降,不利于周王朝的发展。除生理考虑外,周王朝禁止同姓结婚也有政治用意,《礼记·郊特牲》载:“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8]1456周王朝认为与异姓联姻可获得更多异姓家族的支持,使国家更为强大。因此,周王朝将“同姓不婚”视为社会制度的基础。
宫崎判定晋国为夷狄,主要依据是“晋国的同姓婚”[1]19。不过总体上看,晋国自建立之初历经16位国君,整体上遵循了“同姓不婚”,只是偶尔出现例外,如宫崎所举之例:“晋献公娶于贾,无子。”[7]125但是,贾国本是姬姓国,以小国身份嫁女于晋,实则想获得晋国这一靠山,联姻只是一种政治手段,并非有意针对“同姓不婚”。在晋国历史上,贵族同姓婚仅有几例,不足以说明晋国整体上崇尚同姓婚,如:“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9]1669晋穆侯即位,娶齐国女子,正是异姓婚姻。再如:“五年,伐骊戎,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9]1669晋献公娶骊姬和她的妹妹,为异姓婚姻。出现这种打破周王朝规则的现象,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重要联系。春秋末期,周王室衰败,诸侯战争风起云涌,此时的晋国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才出现与姬姓国联姻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晋国历史上只是个例,并非晋国整个历史时期坚持的原则,晋国没有从原则上确立同姓可以结婚。从同姓不婚这方面说,晋国整体是普遍遵守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夷狄。
宫崎仅从个别案例便推导出普遍性结论,是片面且缺少说服力的。同样,宫崎认为齐国存在“族内婚、同姓婚”[1]17,故而属于夷狄。但是,与晋国相似,齐国的同姓婚只是个别现象。东郭偃劝说崔武子:“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7]608东郭偃站在礼制的角度劝说崔武子,表明同姓婚在齐国是不合礼制的。《左传》中仅记载整个齐国的两例同姓婚,上述是其中之一,《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7]650庆舍嫁女于卢蒲癸,卢蒲癸质疑:“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7]649卢蒲癸认为婚姻要避免姓氏相同的,庆舍却不这样做,庆舍为自身政治需要,违背同宗所遵守的“同姓不婚”。一方面,卢蒲癸问庆舍的话体现了在齐人的潜意识里都遵循着同姓不婚的原则,庆舍的做法让齐国遵循这一原则的人感到诧异;另一方面,庆舍用“断章取义”做比喻,表示庆舍的潜意识里也承认同姓不婚是应遵循的原则,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是在“断章取义”。在齐国历史上,有29个国君并未娶同姓妻子。可见,齐国整体遵守了“同姓不婚”。
楚国并未严格限定“同姓不婚”这一原则,由于楚国的民族构成较复杂,在整个国家中有因战争进入楚国的中原人遵循“同姓不婚”,也有楚国原本的居民没有这一禁忌。楚国在争霸过程中与中原国家不断进行战争,战争便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使中原地区有着“华”文化的人民与有着“夷”文化的楚国人民在一起生活。《史记·楚世家》载:“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9]1700在春秋时期,拥有姓的多为贵族,所以考虑越国同姓是否可以结婚主要从贵族角度来考虑。楚国芈姓,越国姒姓,此次联姻属于异姓婚。《左传·哀公六年》载,子期与子西欲立昭王之子为王,并迎娶了勾践之女,也属于异姓婚。越王曾献西施、郑旦给吴王,吴越之间的联姻是异姓婚。[10]84楚国的婚姻分两种情况,一是保留了当地的传统婚姻习俗,如同姓婚、近亲结婚、抢婚等,二是恪守周礼的同姓不婚,主要群体是因战争而逃到楚国的中原人。所以,不可一概而论楚国违反了“同姓不婚”。
从同姓不婚的角度来看,吴国虽然没有提出违反同姓不婚的相关原则,但相对于其他中原诸侯国来说,同姓婚事件较多,且吴国人对于同姓结婚并没有强烈反对。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9]593晋国将本国女子嫁到了吴国,这是出于晋国为整个国家考虑。晋国为姬姓大国,吴国也同为姬姓,原本有违周礼,陈司败因此在《论语》中询问孔子:“昭公如果知道什么是礼的话,那么天下还有不知道的人嘛?”[8]27由此可见,对吴国和鲁国同姓结婚吴国并没有明确的反对者,反应最强烈的为鲁国。在鲁昭公时期有吴国女子嫁入鲁国,女子本名吴孟子,在其死后,《左传》不记载她的姓氏。鲁国夫人的称谓一般是国名加自己的本名,鲁国人应将她叫做“吴姬”,但为避讳而称其为“吴孟子”。吴国与鲁国同为姬姓,因此,《左传》对其女的姓氏不予记载。有史可考的同姓联姻事件还有吴国和蔡国之间两次同姓联姻,其他吴国人对此现象并没有出现反对或者特别对待的现象,因此,可以看出吴国同样是同姓婚与异姓婚并存。
综而来看,晋、齐、越在整体上遵循了“同姓不婚”,楚、吴同姓婚现象较多,但并未公开反对“同姓不婚”,异姓婚不在少数。
(二)语言文字
春秋时期,各国虽方言有异,但文字基本相通。据《吕氏春秋》记载,楚国人生长在楚地,说楚国语言。[11]37楚人所讲的语言与齐语相异:“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辞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12]79吴越两国因地理位置相对较近,“习俗同,语言通”。吴越语言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12]80南方沾染着吴国、越国的语言风格,北方语言中有北方少数民族的特征,可见吴、越两种语言,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界线,其语言多有相似之处。宫崎认为齐国之所以为夷狄国家,原因之一在于“形成了以方言‘齐语’为特征的特殊区域。”[1]18《颜氏家训》有言:“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12]82颜之推认为春秋时期北方人读“矩”字多发“举”和“莒”的音,北方各国在语言发音上是相近的,即使出现不同地区音调长短不同的现象,但并不影响北方国家间的语言交流。齐与周同属于北方,两国语言交流并无大障碍。
语言交流即使有碍,但是尚有文字可以通行。楚国以金文为官方文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春秋中叶之前,与周金文相同;第二阶段从春秋中叶开始,楚国金文风格与周金文风格有所不同,走上了“楚化的道路”[13]。所以,楚与周的文字书写基础是相同的,文字交流障碍不大,其余各国情况与此类似。
可见,齐、晋与周同处北方,语言相通;吴、越与楚位居南方,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与北方诸国差异较大。所以,五霸与中原的语言交流障碍不可一概而论。况且,即使存在语言障碍,还有通行之文字为媒介。
三、身份认同:血缘与自他认识
在宫崎市定的华夷标准下,“夷狄”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与周王朝没有民族系统关系,即民族发源地不同;二是指与周王朝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语言不通且不拥护周王朝统治。简而言之,宫崎认为文化与血缘上的不同造就了“夷狄”和“正统”的区别。因此,需要在文化的基础上对五霸的血缘以及周王朝对五霸身份的认识角度审视五霸是否为“夷狄”。
(一)五霸的血缘
周人姬姓,起于西部地区。“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9]111弃的母亲去祭祀祷告,她在野地上看见了一个大脚印,踏上去后便怀了孕,后生出的孩子为后稷。后稷出生后,年幼时就掌握了种植的方法,后教导民众耕种,在有邰(今陕西武功县附近)地区建立了国家。从血缘角度考虑“春秋五霸”是不是夷狄,首先要看五国与周的民族发源地是否是同一地区,进而考虑五国是否为周王朝的旁系子孙。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载:“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9]1477吕尚的祖先在虞和夏时期被封于吕、申二地,后被封为齐。因此,从血缘角度看,齐国不是周王室在地方旁系的延伸。但晋与周同为姬姓国,与周同宗同源。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之弟。[9]1635晋国与周王朝从血缘上看有一定的关系,晋国与周王朝同为姬姓国,与周朝同宗同源。叔虞之子變,继位后将国号改为“晋”,變则为晋侯。晋文公作为晋国第二十一代君主,与周王朝有血缘联系,自然不属于夷狄。《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9]1689楚国先祖并非出于周室,或者与周室旁系亲属,而是出自帝颛顼高阳。吴回为高阳后代,生六子,其中一子名季连(芈姓),周成王将季连之孙封于楚地,是为楚国的开端。故而,楚与周无血缘联系。吴国在血缘上来说与周王朝则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吴太伯和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9]1445太伯与仲雍为使昌顺利继位,便逃到荆蛮一带,后称他们的部落为“句吴”,太伯为部落首领。虽然吴在地理位置上属于蛮夷之地,但吴国也是姬姓,阖闾、夫差分别为吴国第二十八、二十九代君主,与周王朝有血缘关系,是周民族的延伸。《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提及勾践是夏后帝少康的庶子。[9]1739可见,勾践先祖为夏朝之后定居会稽,与周王朝无血缘关系。
从血缘上看,晋文公、吴王阖闾、夫差与周王朝均有血缘关系,并非夷狄血统;齐桓公、楚庄王、越王勾践与周王朝没有血缘关系。
(二)五霸是否尊崇周王室
“是否服从周王朝统治”是宫崎市定辨别华夷身份的标准之一。
《史记·晋世家第九》载:“赵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9]1663赵衰劝说晋国君主,若想谋求霸主地位,倒不如送周王回周,遵从周王朝统治。“冬,晋侯会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9]1668晋国称霸后依然以周王朝为尊,率领诸侯朝见周天子,成为霸主国的晋国,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号召力,在军事上有强大的实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晋国依旧遵循周礼朝见周王。可见,晋国称霸后依然以周王朝为尊。周倾王、周景王离世时,晋国两次平定混乱,助周朝立新君。所以,晋国一直在维护周王室的权威,而非相反。《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记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9]1480可见周王朝对齐的信任,才会将平叛的任务交给齐。同样,“戎伐周,周告急于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9]1493周王朝在遭遇叛乱之际,会寄希望于齐。故而,齐对周也保持支持立场。
楚国对周王朝并非一开始就抱有敌对心理。楚在熊绎时,尊崇周王朝的统治,《史记·楚世家第十》载:“楚子熊绎,……俱事成王。”[9]1692熊通时,楚对周的态度发生转变:“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尔。”[9]1695熊通自封为武王,直至“楚(庄)王问鼎大小轻重。”[9]1472楚庄王问鼎,显示了对周王朝怀觊觎之心。可见,楚国自熊绎至楚庄王时期,对周的态度经历了由尊崇到觊觎的过程。宫崎认为楚国在春秋初年便与周王朝分庭抗礼,不符合史实。
吴国称霸后,并未以推翻周王室为目标,《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中记载:“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9]1472吴欲称霸以率领诸侯朝见天子,使周王室保持完整,据此可见吴国对周持尊重的态度。“吴王亲对之曰:‘无姬姓之振也,徒遽来告。孤日夜相继,匍匐就君。’”[14]611晋、吴起冲突,吴国劝说晋国放弃攻打同姓诸侯,将重心转移到振兴周王室上,体现出吴对周的尊崇。至于越国,“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致贡于周。”[9]1746越国称霸后进贡周朝,表明越尊崇周,无反叛之心。“太史公曰:‘……及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疆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9]1756吴王阖闾、夫差,越王勾践对周王室均持尊崇态度。
宫崎认为:“齐桓公、晋文公无一不是如此,他们虽打着尊王的旗号,但并不一定是真心尊崇周王室。”[1]19但根据史料来看,吴王、越王、齐桓公、晋文公并未兴兵攻周或废黜周王,尊崇周室并非戏言,宫崎的观点明显有违事实。
(三)五霸的自他认识
文化与血缘固然是判断五霸是否为夷狄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能从5个国家对自身身份的定位,以及周王朝在当时给予5个国家的身份定位来考察五霸是否为夷狄,更具有说服力。五霸的自他认识,即围绕华夷身份、五霸对自我的认识和周王朝对五霸的认识。
《国语·齐语》中记载,周天子将齐桓公称伯舅,并对桓公以礼相待。[14]244可见,周襄王并没有将齐国视为夷狄国家。齐国也认为自己不是夷狄,遵循了周王朝的朝贡之礼,“隐武事,行文道,帅诸侯而朝天子。”[14]242齐国不仅遵循朝觐之礼,并能维护周王朝不受作乱诸侯的危害。因此,齐国并非夷狄。《国语·周语上》载:“且礼所观忠、信、仁、义也,……臣入晋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晋侯其能黎矣,王其善之。”[14]41周内史评价晋国为讲求忠、信、仁、义之国,有着与周王朝相似的礼制,应得到周的认可。“八年,周倾王崩,……晋使赵盾以车八百乘平周乱而立匡王。”[9]1673晋国与周一样,都是以姬为姓的国家,有干预中原国家政事甚至周王室争端的资格。不论从周的角度,还是从自身角度,晋绝非夷狄之国。
在周王朝看来,吴、越均属于夷狄之国。鲁国认为吴国属于夷狄之国,且在诸侯国中地位较低,《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载:“《春秋》贤者不名,此何以名?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也。”[8]2313《越绝书》载:“吴者,夷狄也。”[10]23“子贡东见越王,越王闻之,……问曰:‘此乃僻陋之邦,蛮夷之民也。’”[10]52“成王恽元年,……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9]1692勾践被吴王打败后,任用贤臣,“夫越王勾践,东垂海滨,夷狄文身;……以败为成”。[10]1-2可见,吴、越两国在周、鲁看来均属于夷狄之国。但是,伍子胥曾劝吴国君主:“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讐,以是求伯,心不行矣。”[7]983此话表明,伍子胥并不承认吴是蛮夷之国。故而,吴、越可谓“介在蛮夷”。
据《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经)秋,宋公、楚子……会于霍,执宋公以伐宋。”[8]2256根据西周礼制判断可知,“楚子”之“子”这种书写方式,已表明楚被认定为夷狄。《春秋》并没有明确记录楚攻打宋国,原因在于鲁国认为楚为夷狄之国、宋为中原国家,记录夷狄之国攻打中原国家不符合礼制。《史记·楚世家第十》载:“楚曰:‘我蛮夷也。……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9]1694楚熊自认为楚与中原国家身份地位不同,请求周王室给楚国名号。“熊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9]1692周厉王即位后,楚熊虽主动表明自己的蛮夷身份,但其语境不可不察。楚熊自称夷狄实际上属于气愤之言,用意在于与周王室对立而自立为王。因此,从自他认识的角度来看,楚国是否自视夷狄,需根据语境而定。
由上可见,根据周王朝对五霸的身份认识以及五霸的自我定位来看,齐、晋并非夷狄,吴、越介于华夷之间,楚在内心并非以夷自视。总之,并非宫崎所言“五霸皆夷狄”。
四、“朴素主义民族”对“文明主义社会”的征服
从理论上看,宫崎市定提出“五霸皆夷狄论”的观点,目的是为了论证自己在研究中国通史时所提出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相对立的理论。
宫崎认为,中原王朝是“文明主义社会”的代表,而其周边的游牧民族则是“朴素主义民族”的代表,两者之间有诸多不同,比如文明社会的人有教养,朴素民族的人有自己的训练;文明人崇尚自由主义,朴素民族更崇尚集体统治主义,二者在诸多方面形成对立。[1]9宫崎认为文明主义社会具有早熟性,生活是奢侈的,忘记了文明进步的动力,即纯真的朴素主义精神。当文明社会中的阶级一旦固化,贫困阶层也一时无法宣泄其不满时,来自文明社会外部、具有朴素主义精神的野蛮民族就会侵入,成为“唤醒”文明社会业已麻痹了的不满情绪的力量。但文明社会中产生的种种弊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很难察觉到的,但尚未受到文明的毒害尚且具有纯真性的野蛮民族,从外部却能看得非常真切。而且,在中国这个文明中心的周围,分布着许多尚未开化的民族,虽然文明社会将他们视作蛮、夷、戎、狄加以蔑视,但这些被视作野蛮的民族中保留着朴素主义的精神,时刻准备对文明主义社会发起挑战或给予巨大冲击,比如元朝对南宋王朝的征服、清朝对明朝的征服等。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除了朴素主义民族对文明主义社会的征服外,还存在另外一种更常见的现象,即朴素主义民族在征服文明主义社会之后会被融入后者,朴素主义民族虽然表面上征服了文明主义社会,但却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文化或文明,自身的文化传统反而断裂、消失,比如元朝在中国不足百年的统治。对此,宫崎认为蒙古朝廷过于沉湎于喇嘛教并因此伤害到了政治,蒙古民族忘记了自身最重要的精神,即朴素主义的锻炼;在蒙古统治中国的百年间,蒙古人对中原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并非源于蒙古的文明,而是其朴素精神;中原人接受了朴素主义的锻炼,即接受了蒙古人朴素主义的再教育。[1]119进而,宫崎在此逻辑脉络之下指出,明朝驱逐蒙古人后,在内忧外患的境遇下,仍维持了300年统治,这得益于蒙古人留下的朴素主义;而明朝成为文明社会后,依然不能避免要接受清朝朴素主义的统治。[1]123九一八事变后,宫崎认为:“日本与满洲在朴素主义的锻炼方面一脉相通,虽然语言不通,但以心传心即可交流,真可谓好汉知英雄。……医治文明病,方子只有一个,那就是注入朴素主义。”[1]124那么,日本如何处理“朴素主义”与“文明主义”的冲突呢?宫崎认为日本一方面有古老的文明,同时保留了部分朴素主义精神,形成了处理二者矛盾的巧妙方式。
根据上述宫崎有关“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他提出“五霸皆夷狄论”的主要用意有二:其一,虚构“华夷对立”,即无视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与周边游牧民族之间的民族融合过程和文化内聚运动,反而将其视为民族对立结构;其二,歪曲“华夷之辨”,即通过强调五霸的“夷狄”身份,把中国自春秋至清朝的王朝交替历史,凸显为蛮夷入主中原的传统并将其视为一种历史惯性。然而,若比照1940年前后的东亚政治格局,宫崎虚构的这一历史脉络,正是日本以“异民族”身份“入主中原”进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表述,其现实指向性一览无遗。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国家意识形态直接影响下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和观念”[15]。
如果说宫崎市定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提出此说尚可从“国策呼应”的视角予以政治阐释,那么宫崎在战后依然坚持以“朴素主义民族和文明主义社会的对立”[16]作为中国文明演进的大纲,对此再进行政治阐释似乎就显得难以理解了。故而,需要进一步反思位于宫崎政治论之上的文明论。间野英二曾指出宫崎的文明论来自伊本·赫勒敦,不过并未进行具体分析。[17]继而,吕超将宫崎自身的学术兴趣、东洋学传统与伊本·赫勒敦的理论参互比较,认为宫崎的文明论是“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的二元论,但并未指出其问题点。[18]伊本·赫勒敦是宫崎在留法期间知晓的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学者,宫崎甚至称他是“世界历史哲学的始祖”。[6]255
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中,提出了关于国家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系统性观点,其中与游牧民族和城镇文明相关者集中在三种观点上:第一,游牧人优于城镇人。比如,游牧人比城镇人更善良、更勇敢、更有力量和勇气,游牧生活先于城市生活等。[19]154-158第二,权力的本质是追求独裁、奢侈和安逸,因此城镇文明会经历生长、壮大、分裂、没落和衰亡5个阶段,追求奢侈会导致国家走向衰落。[19]215-228第三,游牧民族不能夺取政权的障碍是沉湎于物质享受,游牧民族对权力政治缺乏经验。[19]178-194可见,宫崎在随后提出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理论中的要点,比如朴素民族优于文明社会、文明社会的衰落源于追求奢侈生活等,在伊本·赫勒敦的观点中皆有迹可循。宫崎在完成《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一书之前对“羡不足论”[20]的研究,以及此后对“东洋的近世”[21]体系的研究,可以说都是对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理论的持续论证。农耕社会与游牧民族的相互交往甚至冲突,确实可以成为一种把握世界史发展的脉络,宫崎在模仿伊本·赫勒敦的基础上提出的农业社会和游牧民族在对抗中形成“文明二元论”的认知体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具有“世界史的意义”。正是因为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的“文明对抗”理论与后来世界史编纂体系中“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文明交往理论存在形似之处,所以才导致宫崎对于自己在战争期间提出的暗藏政治目的的文明论缺乏理性的反省,进而导致其始终坚持在战争期间形成的带有中世纪烙印的文明论。实际上,宫崎的文明论存在三个问题:其一,天然地认为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是一种对立关系;其二,先天预设了朴素民族对文明社会的优越性;其三,在评价标准上,重精神而轻物质。正是这种先验预设的存在,才使得宫崎着迷于“朴素主义民族和文明主义社会的对立”而迟迟不愿正视“五霸皆夷狄论” 的历史实然状态。
结 语
宫崎市定在1940年《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一书中提出“五霸皆夷狄论”之后,直至1977年出版《中国史》,始终坚持此说不变,其立论依据主要是五霸出身于异民族、未遵循同姓不婚、不服从周王朝统治、语言交流有碍、文化习俗相异等。而若依照宫崎市定区别华夷之标准,在进行史料比对和史实核查后发现:五霸之国中出现的同姓婚只是例外现象,异姓婚姻仍为主流;五霸之国与中原各国虽存在一定的语言交流障碍,但南方、北方内部交流并无大碍,且文字基本相通;五霸在血缘上既有出自周王室者,亦有旁系,不可一概而论;五国称霸之后,均未公开反对周王的统治,反而设法保全周王室以提高自身威望;五霸之国在华夷身份认知上不一而足,但至少齐、晋两国在自他认识上均非夷狄。简言之,齐桓公、晋文公并非夷狄,吴王阖闾或夫差、越王勾践位居华夷之间,楚庄王虽自称夷狄但有其特殊语境。因此,在史实核查上,“五霸皆夷狄论”不成立。究其原因,这是宫崎市定为了论证“朴素主义民族”对“文明主义社会”的挑战和征服,进而配合日本侵华国策而有意构建的反事实假说。如果说宫崎市定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提出此说尚可从政治视角予以把握,那么他在战后依然坚持这种假说,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阐释,更是潜藏于宫崎市定思想根底的农业和游牧“文明二元论”认知体系。这种来自中世纪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的文明论体系,即使经过了宫崎市定的比附和改造,却依然保留了“夷”(游牧民族、朴素民族)优于“华”(城镇文明、文明社会)和“以夷变华”的先验预设,这也正是宫崎市定在战后依然坚持“五霸皆夷狄论”的深层原因,对此需保持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