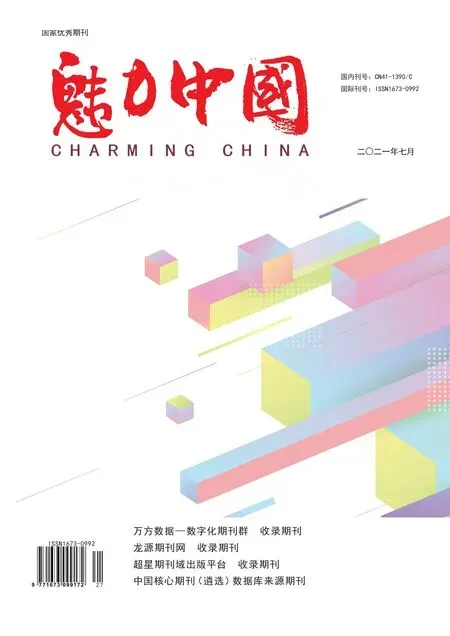论四书的教化体系与“道”之关系
——读刘强教授以“道”诠释四书之我见
2021-11-27胡珊霞
胡珊霞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90)
自宋代以来,四书便取代五经,作为中国人的主要思想教化体系之经典。基于此,阐述与解释四书的著作与日俱增。当然,其中用力最著的人就是南宋儒学巨擘朱熹,他影响最大的书无疑是《四书章句集注》——士子们科考的专用教材。其实,朱子对四书用力之勤,绝非一本《四书章句集注》所能尽的;朱子还编辑了《论孟精义》,汇集了二程、张载等十一名北宋理学家对于《论语》与《孟子》的阐述与解释。除此以外,平素与门弟子之切磋问答,被宋人黎靖德编入《朱子语类》,其中的卷十四-五十四,俱是关于四书之解释与申述,同时,还有《四书或问》一书行世。元代以来,因朱子之学被钦定为官学,学者们对四书用功益加精进,讲论四书之著作汗牛充栋,其中最著名的有明人吕留良的《四书讲义》、王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清人李光地的《四书解义》等。
四书何以重要?依朱子的理解,因四书乃进学之本、求“道”之要也。古之士子因四书为业,故重章句、注疏,由之而豁然贯通以求“道”,是以对“道”反而言之甚少。今之人职业分途,术数各异,很少以四书这样的经典为志业,自然无暇精读章句,细研注疏,由是豁然贯通以求“道”者鲜矣。于是,对今人讲论四书,宜直接豁显“道”而通贯之,陈立夫先生的《四书道贯》就是这一方面的有益尝试。作者在再版序言中解释以“道”通贯四书之理由时说:“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结集十二亿余人民为一家,持续五千余年光荣历史而不坠者,以吾祖先及早发明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的原理,垂裕后人,遵守弗渝,此一原理,称之曰‘道’。”①那么,如何以“道”通贯四书而演成之呢?60 年前,陈立夫先生依据《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结构,“然后将《四书》中固有材料,依其意义分章分节编入八篇中,使其成为一有系统之书,以明其道一贯之理”。②这是在儒学的八步工夫中论说“道”,逻辑层次清晰,是一种比较成功的诠释尝试。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刘强教授的新著《四书通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也力图以“道”来“通”讲四书,这是近年来新一代学人的又一较为成功的诠释尝试。
那么,为什么必须以“道”来诠释四书的教化体系呢?这一问题更好的追问或许是:四书所呈现的精神世界到底是具有的信仰体系,还是只具有一般的道德规训,别无超越维度,这个问题在学界争论已久,莫衷一是。《四书通讲》的作者刘强教授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即四书所呈现的精神世界一定是前者,而绝不可能是后者,故作者说:
任何伟大的哲学思想与信仰,无不涉及对形上之“道”的终极追问,也都会面临一个“弘道”和“传道”的问题。③
这里所说的虽然是针对普遍的信仰,但既然作者以“道”通贯四书,则无疑作者是认为四书涉及到对形上之“道”的终极追问的,亦即,四书是一种具有的精神信仰系统。正因为如此,四书才能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本教材;若四书只是一般的道德规训,则中国人未必一定需要读四书,因为一般的道德规训到处都是;依据黑格尔的看法,西塞罗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④黑格尔的意思很清楚,孔子的思想作为一种道德规训其实没那么重要,没有必要非得读孔子的书。
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黑格尔的判断正确还是《四书通讲》的作者的判断更正确。由此,我们不妨回到四书的经文中来。《论语˙里仁》篇有下面一句: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朝闻道,夕死可也”意味着:“道”足以安顿生命,且让生命具有了永恒的意义,而与时间的短长没有关系。但如果“道”只是一般的道德规训,则“朝闻道,夕死可也”这句话是说不通的,因为道德规训作为一种知识性的认知与外在的行为规范,是无法安顿生命的,因为安顿生命必须是具有终极性的东西,而任何知识与规范都不具有这种终极性。我们且来看朱子对此章的解释:
看得此章,圣人非欲人闻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可不闻耳。若将此二句来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闻道,虽长生亦何为。”便自明白。(《朱子语类》卷二十六)
受朱子之启发,其门弟子即刻回应曰:“然。若人而闻道,则生也不虚,死也不虚。若不闻道,则生也枉了,死也枉了。”(《朱子语类》卷二十六)这意味着,“道”让人成其为人了,是以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七引杜惟熙言曰:“闻道而死,犹老氏所谓死而不亡,释氏之入涅槃灭度,皆死其身而存其性也。否则要此朝夕间一了然何益?”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知,“朝闻道,夕死可也”这句话直接关涉到人的存在,或者说,“道”与人的存在是等价的,“道”之所以是必须的,是因为人作为人而存在是必须的,亦即“道”的显现意味着人的存在的到来。没有人会怀疑人的存在不是必需的,故“道”亦是必须的。故孔子启示给我们的是“道”,而不是一般的道德规训。作为孔子学说之继承的《大学》《中庸》与《孟子》,亦承袭了对“道”的揭示与弘扬: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所谓“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就是以下学之工夫而体证“道”,亦即是孔子所说的“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庸》)
这一句话进一步论述了“道”与人之存在的等价性,即若人作为人而存在具有片刻不可离的绝对价值,那么,“道”亦有片刻不可离的绝对价值。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
这句话乃是说:人若能在下学工夫中自家体证“道”,则能真正实现生命的圆满与自由,也就是说,只有人与“道”贯通,生命才能圆满与自由,律则性的道德规范并不能实现这种圆满与自由。
综上所述,四书作为一种教化系统,但决不只是一种道德的教化系统,必须是一种具有信仰化的系统。四书的教化系统当然具有道德的教化功能,但仅仅是道德的教化功能并非四书的价值诉求,其必有终极性的“道”的提挈与总领,故“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之所以一定要孔子为木铎,就是要让终极性的“道”显现,而不是解决一般的道德无序问题,是以《中庸》讲教化一定要从“天命之谓性”处讲。如实说来,若道德不与终极性的“道”贯通,我们真的不知道道德究竟意味着什么。道德可能只是人暂时性的理想,也可能是人功利性的盘算,总之,这样的道德与人之为人之存在根本没有任何关联。因此,若道德不与终极性的“道”关联起来,则任何道德不过是一个瞎子引导另一个瞎子,这种盲目性从根本上剥落了人的存在,这当然不是孔子所追求的道德,是以法国哲学家马里坦评价孔子时说:“无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是什么,我们都没有在孔子的著作中发现纯自然的伦理学。”⑤所谓“纯自然的伦理学”就是析出在终极性的“道”之外,依据世俗生活而确立的伦理学(道德学);这种道德学是根本无法实现人的圆满与自由的,因为“如果没有终极关怀作为它的基础,那么,每一道德体系就会蜕变为一种调节社会诉求的手段,……并被一种聪明的计算所取代。”⑥四书作为圣贤的教化,自然不是在这个层次上立论的。因此,要解析与讲论四书的教化系统,必须由“道”入,且只能由“道”入。
但“道”是什么?“道”并不是一个摆置出来的人人可见的存在。当终极性的“道”是一种可以摆置出来的东西的时候,它离自然科学更近而离精神科学更远,故孔子常不言“道”,是以子贡叹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因为“道”不是可以摆置出来的东西,故孔子不言而门弟子难闻也。但我们又说过,孔子的教化系统必由“道”入,而孔子又常不言“道”,这当然如何理解呢?牟宗三给了我们一个解释,他说:
因孔子毕竟不是希腊式之哲人,性与天道是客观的自存潜存,一个圣哲的生命常是不在这里费其智测的,这也不是智测所能尽者。……在德性生命之朗润(仁)与朗照(智)中,生死昼夜通而为一,内外物我一体咸宁。它澈尽了超越的存有与内在的存有之全蕴而使它们不再是自存与潜存,它们一起彰显而挺立,朗现而贞定。这一切都不是智测与穿凿。故不必言性与天道,而性与天道尽在其中矣。⑦
这就是说,孔子是在道德的践行中让“道”朗现出来,除却人的道德践行,“道”即挂空,纵千言万语也无法摆置出来,是以孔子又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即指孔子对“道”的指陈与开显都在道德的践履中。门弟子深得孔子之教,《中庸》特别记录了孔子下面一句话: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这意味着,“道”不可离开人之为人的真实生活,一旦离开,“道”即挂空而虚幻,这绝不是四书之教化系统所追寻的“道”。也就是说,“道”绝不是一个现成的摆置出来的终极性的神圣存在,进而人们顶礼膜拜而求其神恩,“道”是在人笃实的道德生活中演成的。刘强教授下面这句话正是这种义理的体现: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虽是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文化,但并非没有终极关怀。只不过儒家的关怀不是寄托于“神”,而是掌握在“人”。⑧
这里的“神”可以更换为“道”,俱是终极性的神圣存在,但这种神圣存在不是现成的摆置出来的,而是通过人笃实的道德生活开显出来的,它是在人的参与中演成的。依此而言,四书之教化系统之价值诉求虽是终极性的“道”,而其落实下来必是“道德的形而上学”。“道德的形而上学”意味着通过道德进路契悟一个终极性的本体,意味着人的道德力量通达一个存在感。
总而言之,四书之教化系统之价值诉求虽然是终极性的“道”,但这种“道”必须在人真实的道德生活中落实与演成,于是,世间有各种“道”,刘强教授总结这各种“道”为十三种,即为学之道、修身之道、孝悌之道、忠恕之道、仁爱之道、义权之道、诚敬之道、正直之道、中庸之道、治平之道、齐家之道、教育之道、交友之道。读者千万不要以为有那么多“道”,“道”是整全之“一”,哪里会有歧异而区分,实则各种“道”是相互通达的,正如刘强教授在《读法》中说:“本书所讲诸道,若登高俯瞰,好比一座园子,回环往复,义脉相通,可瞻前顾后,可左右顾盼”。这里所说的各种“道”,实际上就是在人的道德生活中演成“道”,即人的道德生活不只是给予人一种好的生活这种意义,最终必通贯“道”,从而达到朗澈生命、润泽万物、通化宇宙的目的。这才是四书教化体系的完成,而一切不以“道”来诠释四书的著作,皆不是对四书之周至理解,其偏枯必然抹杀四书教化体系之高义。
注释:
①陈立夫:《四书道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 年版,第1 页.
②陈立夫:《四书道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 年版,第9 页.
③刘强:《四书通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84 页.
④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119-120 页.
⑤马里坦:《道德哲学论》,见陈麟书编著:《重读马里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149 页.
⑥保罗·蒂利(里)希:《信仰的动力学》,成穷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98 页.
⑦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187-188 页。
⑧刘强:《四书通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89 页.